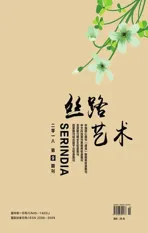返璞归真的当代伊朗电影
2018-04-01郭雪瑶武汉大学艺术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郭雪瑶(武汉大学艺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一、借用儿童视角的“返璞”
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起,“真诚电影”的力量在伊朗兴起,伊朗电影人经过一系列的探索,将儿童作为纯洁、美好的化身,审视成人世界的种种顽疾。然而儿童视角的创作并非伊朗电影人的最初选择,同样是经过本土电影人的创作和探索形成了一种独具国家特色的影片风格。伊朗本土电影尤为强调真实客观地记录现实、再现现实,同时特别指出电影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生活本身变成有声有色的场景,最终能够在电影这面多棱镜中体现其返璞归真。纵观世界电影发展历程,关于如何让记录生活的真实,揭示生活的本质,世界各国的导演都曾做过相应的探索,但大多呈现的均是一种个体行为,然而伊朗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基本构成了导演群体的一种自觉意识与群体风格。
这与伊朗电影的历史发展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伊朗新电影曾出现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达鲁什·默赫朱为代表,开拓了伊朗乡土写实电影的先河。随后在伊斯兰革命之后,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放弃了敏感的宗教题材的“伊斯兰电影”模式,采用一种温和的疏离政治意识形态的叙述方法,把镜头对准儿童的纯真世界,透过儿童的形象来展示人类的良心和人生的苦难,这一尝试使伊朗电影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至真、至纯、至爱的写实性表达使伊朗电影备受关注,随之衍生出许多形式、题材优秀的作品和导演,如马基德·马基迪《小鞋子》《天堂的孩子》,贾法·帕纳西《白气球》,巴赫曼·戈巴迪《乌龟也会飞》等,也将伊朗电影推上国际影坛。[1]到了21世纪,伊朗电影转变为现实性社会题材,电影平民化的题材选择、人性化的主题挖掘、纪实性的视听表达,都是它备受瞩目的原因所在。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伊朗文化政策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开放,众多伊朗导演开始主动探索电影中的人性关怀与美学艺术,新生代导演不负所望,阿斯哈·法哈蒂《推销员》、极具影响力的《一次别离》获得2012年奥斯卡美国金球最佳外语片,其形式与内容以及大胆的表现手法成就了伊朗更为回归本真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
女性与儿童始终是伊朗电影的偏爱,最早在伊朗获得认可的也是本土的儿童电影,谈到伊朗的儿童电影,最多被人们提起的应该就是《小鞋子》,影片中兄妹经历着世间的种种磨难,丢了鞋的孩子没有向窘迫的父母伸手要鞋子,没有指责也没有埋怨,反而更多的是兄妹之间以及家庭之间的互相体谅,受众或许可以从中感受到生活的不易与辛酸,但是却不会让人感到颓废甚至是绝望。这就是伊朗电影的独特之处,有人将其称为“苦难美学”,受众是在观察或者说是在倾听正在经历着某种苦难的人们的生命状态,但是影片的叙述角度是在给我们展现主人公尤其是小主人公们的积极阳光的状态。与我国的儿童电影对比来看,我们始终把孩子放在一个所谓的“安全地带”,禁止或尽可能减少其触碰社会的阴暗面或不利于儿童成长的因素,以免对其成长造成阴影或使其在没有独立判断能力的阶段对社会形成误判。
《天堂的颜色》同样借助儿童视角来表达“人性复苏”这一主题。莫曼双目失明却不乏乐观,眼睛看不到,他就利用声音感知和熟悉这个世界,即使家庭有意对他疏远甚至是抛弃,但他依旧坚持着被亲人接受的一丝期望,既不放弃求得亲人关怀的追求,也用自己细腻简单的方式爱着身边的每一个亲人。《乌龟也会飞》中,十三岁的少年卫星带领着同样遭受战争迫害的孩子们,但在孩子眼里,他们把战场看得是那样平淡,在战乱纷飞的年代里,在战争下畸形成长的少年们却不以为然的乐观生存着,他们的处境越是艰险,其人性的美好也才愈加动人。也正是在对这些久违了的、纯真的人性与人情之美的揭示中,一种超越平生活的真实洋溢其间,对于心灵蒙尘、精神生锈的现代人来说,这恰如冬日里投进的一缕温暖的阳光,美妙而又令人向往。
二、创作内容的“归真”
本文所说的内容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影片创作内容即故事的选择,其二是指导演进行视觉创作时对伊朗本土风情内容的选择。
(一)内容题材的选择
谈到伊朗电影就不得不谈其国家体制以及极其苛刻的电影审查制度。众所周知,伊朗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自1925年伊朗本土电影的制作开始后,历经了半个多世纪,伊朗本土电影工业也以较为温和的方式,以不触犯伊斯兰宗教道德戒律为前提,渐进式地发展起来。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颁布的第一部宪法规定,伊朗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神权统治高于一切,这一点也直接体现在了伊朗的电影审查方面,影片被分为A、B、C三级以决定电影的发行渠道和宣传方式。伊朗电影从未摆脱严格且尴尬的审查困境,影片禁止出现的内容至少包括: 紧身的女性服饰;除了脸和手以外裸露其他女性身体的部位;男女性之间的身体接触、暧昧的语言或笑话;关于关于伊朗军队、警察的笑话;长胡子的反面角色(会引发人们与宗教形象相联系);外语或粗鄙的语言;正面角色表现得喜欢独处,而不喜欢集体生活;士兵或警察衣冠不整或相互争执等等。[2]这些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同样也是其为何多数题材偏爱选择儿童世界来表现的原因。
伊朗女性在宗教和男权的挟持下,电影人将镜头对准这一群体,探讨伊朗文化对女性的特殊规范。在影片《生命的圆圈中》,通过展现女人一天内不同的遭遇来展示女性一生的缩影,无论是何种身份的女性其内心其实都有一种善良的天性存在,然而世俗就是将其像牢笼一般的笼罩,影片的片名也极具哲学意味,“圆圈”从图形上来看属于一个封闭形的图案,代表着女性被陈规世俗所牵绊束缚,从“圆圈”的含义来看,即循环往复,也是一种社会形态的隐喻。这一特点与玛兹耶导演的《女人三部曲》有异曲同工之处,发生在三个女人身上的故事,其实就是伊朗妇女一生的折射与概括。现实主义的创作是伊朗电影一贯的沿袭创作方式,并且尤为青睐社会底层边缘化的小人物,因充满着向往,在平淡的生活中才乐此不彼。无论是从故事情节角度还是从所选择的边缘人物性格命运来看,都极尽朴实,每一部影片甚至都能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情节甚至不强调一波三折,就是用极尽朴实的题材来拨动观众心弦。
(二)镜头叙事的选择
从影片的镜头语言来看,为了让影片更加贴近现实,更加触动观众真实的理解,更加原汁原味地反映生活,伊朗电影很多都采用现实、写实主义手法,其显著特征就是用纪录的形式感处理画面,很少刻意的加以修饰,尽可能的还原真实的表现方式拍摄影片。马吉德、巴赫曼·戈巴迪、阿斯哈·法哈蒂等众多伊朗导演的很多作品中都使用了这种手法,不同于好莱坞华丽的视觉体验,也没有欧洲电影的艺术浪漫色彩,更不像日韩电影的清新表达。伊朗电影是一种返璞归真的自然美。在影片《黑板》中,贫瘠的土地、破旧的黑板和战场枪声交相辉映。无论是导演镜头下的难民,还是视儿子为生命的女人,亦或是在黑板前谋生的老师,这些形象中都保留了现实中的真实,都可以透过这些衣衫褴褛的形象看到人本真的一面。伊朗导演强调内心的震撼和精神上的共鸣,真实地观察自然、记录生活,体现了东方美学中美与真实互为统一的审美观念,崇尚没有人工雕琢的自然之美。
伊朗电影特色的风土景色中给观众呈现一种真实美。过去在人们的心目中,伊朗是个神秘而陌生的国家,大量的西方舆论把伊朗扭曲化,更带有一种激进的有色负能量的展示。然而,通过影片我们将这层神秘的面纱一层层的揭开,让人们发现伊朗认识伊朗。影片《樱桃的滋味》中,在巴迪一路寻找的路途上,土山、土路几乎全都是伊朗风景的原貌,不艳羡当今的后期高科技,将所有的景色都不加修饰的搬进了屏幕里,呈现在观众眼前。《天堂的颜色》中,我们看到的绿树,随风摇摆的金色麦浪,古老的村庄里简陋的小土楼,纵横交错的狭窄的小石巷,传递着异质文化所独具的韵味与情趣。不得不说,大多数伊朗电影在色彩的运用上是“吝啬”的,除去不加利用后期技术的调整以外,在画面和色彩的选择上,伊朗电影人似乎不在乎我们现在所谈论的影调是否过低,画面是否存在美感,在他们看来相比整个国家影片的纪实性群体风格,以上人为元素和受众审美似乎显得不是那么重要。然而他们对环境景物的这种自然呈现虽看不到人为的强力介入的痕迹,但也并不等于“把摄影机扛到街上”去随便拍录,相反地,它们同样是经过了电影人的精心选取与审美观照。无论是从儿童视角还是普通叙事,伊朗电影始终有一种正能量存在,所有的不美好都不是为了表达破坏和不美好本身,反之是在给人以希望,灾难是不可知的,他或许像恶魔一样的固然可怕,但这并不代表生命为此不再美丽。 也正是在主观情感的浸润之下,自然景物的内涵变得充实丰盈起来。
如此看来,伊朗电影是一种有“性格”的电影风格。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电影从之前拼剧情走向了现在的拼技术,当代电影界存在一个普遍问题就是重技术而轻人文。好莱坞科技大片层出不穷,高投入、大制作的炫技电影高频率的冲击着也吸引着观众的眼球,当然这不是否定好莱坞电影的价值,只是相比真实人物真实情感的伊朗电影,不能给人以持久的感染与思考。
结语
随着国际化的发展和全球化的加速,具有国际化文化体征的影片和审美受众也随之发展壮大,市场对影片的要求也愈加多元化,然而伊朗电影仍然保持自己特有的让电影回归到电影传统、回归到为人的艺术,把镜头焦点集中在普通小人物身甚至是苦难的人们身上,让人沉醉于其电影原始的美,实则不易。而伊朗电影也正是以这样的人文观念,在当下人文缺失的视听界带来更多的思考和启示。
注释:
[1]伊朗新电影的三次浪潮,百度百科
[2]伊朗电影的审查制度,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