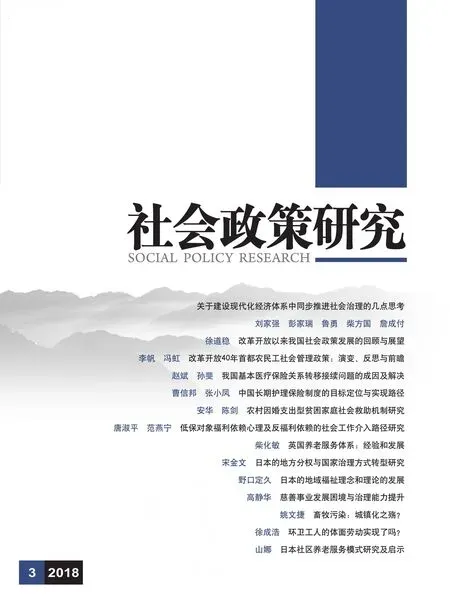“我们要吃饭”:食物中的激进政治
2018-04-01赵蒙旸
赵蒙旸
食物和水是对人类生存最为根本的东西,围绕食物发生的集体行动曾在社会运动历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面包价格上涨间接促成法国大革命;《谷物法》的出台导致英国城市的大规模骚乱;对食物短缺的恐惧影响到殖民时期东南亚的农民运动。
然而,以蒂利为代表的一波经典理论家认为,粮食骚乱等关于食物和水的政治抗争虽然普遍,却往往是本地化、昙花一现的,无法向其他地区扩散。但是,那种更系统、与权力持续互动的现代社会运动,恰恰是在食物抗争退潮之后诞生的。
然而,历史并非线性前行。过去的几十年间,以食物为主题的社会运动依然构成了发展中国家重要的政治景观:20世纪90年代后,阿根廷多次出现严重的食物骚乱和抗议潮;2016和2017年委内瑞拉的反政府抗议,也和长期的食物和药品短缺有关。
更有甚者,在许多运动主题与食物并不直接相关的社会运动中,食物元素也常常出现在示威道具中:埃及的抗议者擅长把法棍制成头盔,美国的运动家经常用批萨盒做标语牌,希腊的年轻人则有着投掷(希腊)酸奶的“优良”传统。
这些富含着食物气息的当代集体行动究竟意味着什么?关于食物和水的政治抗争究竟是一个早已远去的时代的零星回响,还是足以塑造当代政治进程的重要力量?
任教于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家Erica Simmons在2016年出版的新书《富有意义的抵抗:市场改革和拉丁美洲社会抗议的根源》(Meaningful Resistance:Market Reforms and the Roots of Social Protest in Latin America)中,将研究焦点对准当代政治中关于食物和水的抗争。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和历史社会学研究,她描绘了过去二十年中两场发生在拉美的反市场化运动:玻利维亚的“水之战”,以及墨西哥的玉米抗争。
她的研究表明,这些围绕水源和食物等基本生活品的抗争,并不是食物和水的短缺自然而然导致的。短缺本身不足以激发社会运动,只有特定文化编织出的社会网络,才可以承载斗争的动力。在这些抗争中,人们不仅仅是在抗议市场化所造成的水源和食物短缺,更是在捍卫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中原有的关系网络、组织方式、文化意义。
一、玻利维亚的“水之战”:跨越阶层的统一战线
1999年末到2000年上旬,结束军管十多年的玻利维亚第三大城市科恰班巴爆发了被称为“水之战”的社会运动。在其他领域的自由化改革进行了多年后,供水公司的私有化导致水价翻倍,终于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公民团体在半年多的时间内不断发起游行、设置路障、瘫痪城市,最终促使当局撤回了供水私有化的方案。
与其他围绕食物议题的社会运动不同,“水之战”的特殊之处在于城乡之间、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高度联合。加入抗议的甚至包括那些几乎完全没受水价上涨影响的中上阶层,乃至那些从来不用自己交水费的人。事实上,受到价格冲击最小的知识阶层反而恰恰是最先组织起来发起抗议的。
本研究表明,虾青素和黄体素均能有效改善大黄鱼的体色,大黄鱼能够更好的利用黄体素,并可能将虾青素经黄体素和玉米黄质最终转化为金枪鱼黄素。
在Simmons看来,“水之战”的成功动员,源于水在玻利维亚社会生活和文化意义中的核心地位。由于长期面临水源短缺的威胁,该地方言中有大量与水相关的概念,不仅指代管理水源的方式,也常常泛指一整套当地人的生活方式。
水在日常话语中的核心地位,不仅推动着围绕传统的“想象的共同体”的建立,也间接促进了社区网络和公民组织的发育。
1825年玻利维亚从西班牙独立,之后的几十年,新成立的共和国疏于管理殖民时期的公地,许多产权不明的土地纷纷归个人所有。但虽然土地归了个人,科恰班巴的大量土地却依然依赖集体灌溉。出于集体灌溉的需求,大量地区自发形成了本地化的团队协作网络和合作社,一直经久不衰。这些历史悠久的地方网络不只是一个个象征性的联盟,而是存在高度的强制力:加入的成员必须缴纳会费,选举负责人,参与讨论会,还被要求定期轮流参与社区劳动,不遵守的成员则会被处以罚款。
长期的社区协作使得一种超越“国有-私有”二元对立的公共产权观念逐渐形成。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缺位,又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合作社的重要性。1999年,15~20%的科恰班巴居民直接依赖合作社而非官方机构来获取水源。在一些地方,合作社负责挖井来提供额外的水源;在另一些地方,合作社统一从水务署“团购”水,再通过自己的组织渠道定期分发给居民。每周两次的集体取水日也常常成为居民之间沟通政治信息的机会。
除了每个社区组织内部的高度团结,一个城市内的组织之间还通过区域协会联结起来。1997年,3000多个社区灌溉组织的负责人创办了科恰班巴的灌溉者协会FEDECOR。通过召开区域大会,不同组织间有了构建政治联盟的可能性。这样一种依靠组织内强联系和组织间弱联系的动员模式,也成为“水之战”的组织骨架。
最终,FEDECOR不仅自身参与到“水之战”中,还呼吁发起了一个更大的运动联盟Coordinadora。这个联盟的覆盖面极广,包含工程师、教师、建筑师、律师等中产专业人士,以及多个行业的工会、农民协会,还包括更草根的社区组织和零散的非正式劳工。虽然代表不同阶级和社区的参与者对可行的水源政策有着截然不同的设想,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参与者也互不信任,但是私有化方案作为大家“共同的敌人”,构建了抗争的统一战线。 2000年1月初,Coordinadora帮助发起了最大规模的总罢工,科恰班巴全城停摆,主要道路和机场被切断,全国的交通运输都受到重挫。多日的罢工将政府逼上谈判桌,4月,官方正式撤回了私有化方案。
二、墨西哥的玉米抗争:家庭妇女“打响第一枪”
玉米和玉米饼在墨西哥文化中的地位已勿庸赘言,快餐工业中的玉米饼几乎成为了墨西哥菜的代名词。2007年初,玉米价格的突然上涨引发了一系列全国性抗议。1月31日,各界别政治组织发动全国大游行,墨西哥城标志性的宪法广场被人群填满。政府被迫邀请反对力量加入协商,采用一系列收买和分化策略后,建制派才暂时控制了局面。
Simmons认为,抗议的爆发和传播同样不只依靠对食物短缺的愤慨,更和玉米所激发的政治想象与社会网络密切相关。从20世纪初开始,出于扶贫和推进现代化的需要,墨西哥政治精英曾经多次试图用单位产量更高、营养价值更好的小麦替代玉米的地位,但由于有限的国家能力,玉米从未退出大众文化生活。时至今日,日常方言中依然包含无数玉米相关的词汇,城乡的节庆日,不论是农产品丰收节还是文娱活动,都经常以玉米作为主题。而墨西哥菜肴食谱的传播、商业印刷的发展,又进一步促成了围绕玉米文化的“想象共同体”。在Simmons的访谈中,所有的抗争参与者都提到了玉米在他们心目中的象征性地位。
相比之下,牛奶的价格也在同一时期出现了明显上涨,但因为牛奶在社会文化中并未占据什么关键地位,所以对参与者来说,他们只会对牛奶涨价感到“不安”,而不会有所行动。
2007年的这波抗议也依托了2000年前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威权统治的政治遗产。PRI对民间社会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对工会等体制化社会组织的收买和间接控制,而正是这些“官方”组织的强大,给了反对派可乘之机。很多独立工会和非政府组织正是靠着在官方组织内部招募成员,才得以逐步成长壮大。这些发展壮大的墨西哥的独立工会——比如全国乡村商业联盟(ANEC)——给成员提供玉米生产和销售上的指导,定期在首都召开的会议也帮助建立起密集的跨区域成员网络。
与玻利维亚“水之战”不同,性别政治在2007年墨西哥的抗议中扮演了更关键的角色。由于墨西哥社会严重的性别不平等,加上男性劳力大量移民到美国打工,留守的女性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家务。在乡村地区,邻居间常常聚在一起制作玉米片。碾压玉米的过程相当费时,本来原子化的家庭妇女得以在共同劳作中认识彼此。在机械化早就普及的城市地区,女性虽然不用再花好几小时准备主食,但她们在店铺或商店排队购置食材时,依然会短暂地交流本地政治话题,正如玻利维亚人在每周取水日上聊天谈论政治一样。
女性间跨家庭的网络,成为了墨西哥2007年抗议的关键。事实上,早期街头抗议的中坚力量就是不隶属于任何组织的女性,她们拿着自制的锅碗瓢盆和标语穿过大街小巷。根据Simmons的访谈,这些抗争参与者主要通过邻里交流、家庭讨论或者广播报道得知抗议的消息,直接受到政党和工会动员的人寥寥无几。直到抗议后期,组织化的反对党、农民协会、行业工会和各类社会组织才加入进来。也正是因为抗议从中下层妇女开始蔓延,在之后加入的任何团体都难以单方面主导运动形势,运动也就得以汇聚更宽泛的诉求、团结更广泛的人群。
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的这两场抗议,是食物和水激发社会动员的典型案例。我们在这两场抗议中都看到,只有组织渠道才能将个体不满转化为持续、有力的集体行动,而不是无序的暴动。
三、食物如何催生激进主义
Simmons对拉美运动的研究,揭示了关于食物和水的不满如何导向社会动员,也从反面论证了为什么今天的欧美发达国家较少出现围绕食物和水源的社会运动——在这些社会中,食物和水源往往不再是激发社群生活、把原子化个人联结起来的纽带。就水资源来说,在发达工业社会,自来水早就直接流入每个住户,水费每月从个人账单上扣除,取水不再需要多人的合作。水源的短缺和污染,除了激发出小规模不满以外,并不足以激活社区网络,也就无法进一步被政治化。
环境社会学者Colin Jerolmack在对美国宾州农村污染的研究中,甚至还发现了相反的现象:乡村居民在面对页岩气开采带来的严重饮用水污染时,并未责怪征用土地的水力压裂公司,而仅仅把这一恶果看作自己理性出售土地带来的副作用。水力压裂公司派人一家家入户评估土地价值,签署征地协议,给予每户不同的补偿,也有效分化了当地居民。居民把补助金额的高低和水污染程度都视作是随机事件,土地所有者协会的存在也未能扭转这一看法。污染区居民对专程前来抗议页岩气公司的行动者和NGO报以敌意,认为这些傲慢的城市精英入侵了自己宁静的生活。结果,运动组织的实践不仅未能促进当地的环境抗争,反而成为了居民继续接受污染的理由。
然而,与斯科特对农民反抗的理解类似,Simmons的研究视角其实也是相当保守的。为了突出文化符号的意义,大量笔墨被用于描述两地特殊的历史传统,而非什么样的过程构建了抗争的话语和主体。拉美的传统变成了一种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向映射:似乎正是它们和欧美社会发达程度的差距、正是落后的传统本身,决定了食物抗争得以在拉美国家出现。
然而事实上,激进的抗争运动之所以可能,不一定是因为它们处在前现代的社会环境中、没有受到发达的“后工业社会”的束缚,而更可能是运动本身早就超越了一套既定的思维框架。从这个角度看,Simmons依然是在“原始叛乱”的母题下,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去理解“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社会运动,她也就无法将拉美的个案和其他地方的斗争联系起来。
另外,Simmons默认只有跨阶级和城乡的运动才是更值得肯定的运动,单个群体的斗争要与更宏大的主题衔接才更有号召力。这样的前提假设让她看不到跨阶级联盟内部往往存在着权力不对等,也就无法呈现社会运动内部的张力、隐忧和解体的原因。
食物、宗教、土地这些看起来像是“前现代”的元素,并未像经典理论家所预言的那样,在当代政治中退场。相反,它们正以惊人的力量在当代抗争政治中现形。这种复苏不仅发生在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也出现在早就经历过新社会运动洗礼的欧美社会。欧美的右翼民族主义、移民权利、最低工资、环境正义运动,都越发融合了食物、宗教、土地的色彩。甚至可以说,正是“现代”的世俗化和多元主义,激发了保守宗教和民族主义的复兴;正是基于身份政治的社会运动,让原始的土地诉求变得独特而有力。
著名社会理论家Craig Calhoun曾经提出,传统可以是激进主义重要的来源。不论这种激进主义最终与怎样的意识形态合流,我们都不再能无视它背后已被点燃的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