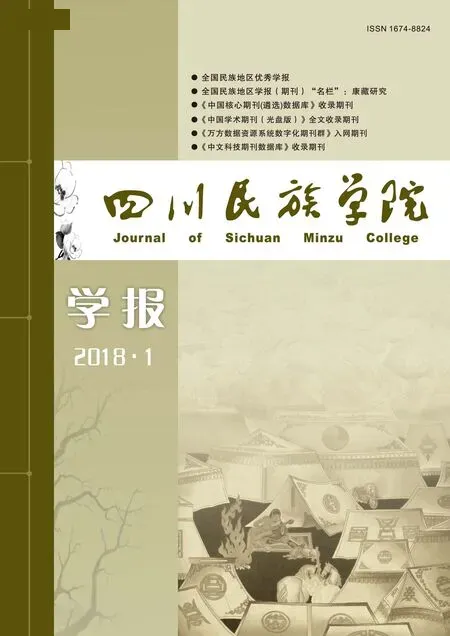八十年代藏族小说中的西方人形象书写
2018-04-01许琪
许 琪
作为中国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八十年代藏族文学,产生了众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其中就包括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八十年代小说对西方形象的塑造逐渐活跃,丰富的西方外国角色已经出现,明显呈现出了对西方人形象的建构,塑造了一批鲜明独特的西方人形象。形象学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最早是由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兴起并逐步发展起来,属于“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范畴。然而针对八十年代藏族小说视野中的西方人形象研究,却一直少有学者问津,有待于进行全景和整体的剖析、完善。本文借助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论,探讨藏族小说家们在八十年代前后期对西方人的形象不同书写,进而关注藏族小说创作主体,以及他们如何借助文学的方式描述和表现对西方人的想象的。从而试图把握这种想象和描述背后的时代、社会和文化的实质,彰显中国藏族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进一步探讨中西文化形象特质。
一、绪 论
(一)相关概念界定
1.西方人形象
“西方”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新华词典》解释为欧洲资本主义各国和美国。而广义上指作为文化概念的西方,那么本文所要探究的西方人即是处于西方文化体系之下,广义的西方人形象。同时,这里的“形象”与一般意义上的形象不同,而是指比较文学形象学意义上的“形象”,形象学意义上的形象可以是人物形象,除此之外还可以是器物、观念、风物、言词等等,它的研究对象是某国某民族文学中所出现的“异国”形象。正如莫哈指出“文学形象学所研究的一切形象,都是三重意义上的形象:它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1]因此,这里的西方人形象不仅仅是还原藏族小说中西方人形象的真实面貌,更重要的是探索这一特定时期西方人形象是如何被塑造的。
2.藏族小说
这里的“藏族”指的是广大的藏族聚居地,即卫藏、康巴、安多三个地区,其范围大致包括西藏族区以及云南、四川、青海等地的部分藏区。虽然这些区域在地理上分属于不同的省份,但在文化上都受到了藏文化的影响,社会结构相似。因此本文“藏族”是一个文化概念藏族,而不是行政区划概念。因而,无论是土生土长的藏族作家降边嘉措、益希单增,还是兼有多种民族身份血统的色波、扎西达娃等小说作品,都共同构成了文化意义上的“藏族小说”。按文化概念界定“藏族小说”,有利于打破藏族内部由于地域分布与行政规划的不同而造成的狭隘阈限,有利于将原本处于分散、割裂状态的藏族文学,联结成为一个统一的、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以此来凸显整个藏民族文化视阈下的西方人形象书写。
(二)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综述
比较文学形象学发生于欧洲19世纪,脱胎于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现已发展为比较文学一个专门的学科。代表人物有卡雷、基亚、巴柔、胡戈·迪塞林克等人。与传统形象学相比,当代形象学吸收了后殖民主义、接受美学、符号学、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的想象等后现代主义理论,不断革新研究方法,由“被塑造者”形象的真伪研究,开始转向形象“注视者”对“被注视者”的想象和接受,强调主体与客体、他者与自我的的互动关系。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郑振铎、钱钟书、范存忠等国内学者陆续涉猎形象学研究,为后来的形象学研究提供了非常可贵的实践经验。80年代以来,西方的形象学逐渐得到中国内地学术界的重视,主要代表人物主要有孟华、乐黛云、周宁等人。国内外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方向大都侧重于西方视阈下的异国形象研究,有关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形象学研究实践一度被遗忘。在中国现当代的少数民族文学之中,藏族文学是影响较大且较为活跃的一支,产生了众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近年来学术界对藏族小说越来越关注,评论者也逐渐增多。然而,相对于“西方藏学”研究的火热,目前学术界对于”藏族视阈下的异国形象”研究屈指可数。而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八十年代藏族小说中的西方人形象,之所以选择从藏族小说这一视域为切入点分析西方人形象,目的在于填补“中国藏族视角下的异国形象”这一研究缺憾,努力尝试比较文学形象学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实践。
(三)创新点及研究意义
中国的藏区作为古老东方国家的独特地域,从藏族的视角去看西方,则是把中国藏族作为形象学研究的“注视者”,融合了“西方主义”的视角去审视西方形象,展现出主观与客观的冲突与结合,使东方不再作为一个沉默的对象,体现了东方作为活跃的话语参与者的姿态,也是对长期以来以西方的形象学研究视阈为中心的一个解构与超越,是一种反观西方的形象学研究实践。本文力图呈现八十年代藏族小说作品中的西方群像,充分发掘这一时期西方人形象的主要特征和塑造过程,阐述藏族人民对西方国家的集体想象及情感变化过程。实现“他者”与“自我”形象的交流互动,获取中国藏族与西方在形象参照下的思考,同时也为正确认识西方形象提供客观性的参考。
“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2]对他者的剖析也是审视自我、建构自我的一种形式。探讨八十年代藏族小说中西方人的形象,不仅可以深入了解二者之间的形象关系,还可以解读藏族小说在塑造西方人形象过程中折射的民族心理情感态度的变化,并以此考察形象背后所隐含的社会历史文化影响因素,探寻西方人形象的真实面貌以及形象生成的机制,破除形象被制作的原因。在形象互动中正确认识自我与他者,在一定程度上加深自我对民族历史的客观认识,有利于进一步理解和把握藏族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促进二者相互认识的过程不再完全以自己的立场为出发点,增强文学交流和对话,促进良性的文化交流及平等客观认识,为正确认识西方形象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参考。同时,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形象作为一种重要的“软实力”和“声誉资本”,许多国家都重视自身国家形象的塑造。
二、八十年代藏族小说中的西方人形象概述
八十年代小说作品在整个当代藏族文学发展历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 就20世纪80年代的藏族小说而言,可以说迎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契机,小说创作蔚为大观,中长篇小说创作也开始崛起,小说中的西方人形象逐步开始出现在作家的笔端。其中涉及到西方人形象比较典型的小说作品包括降边嘉措《格桑梅朵》《十三世达赖喇嘛》,扎西达娃《西藏,隐秘岁月》,色波《圆形日子》,索穷《隧道》,通嘎《白色》等, 而这些小说家们也都是新时期最早登上我国当代文坛的一批优秀藏族作家。
(一)西方人被政治化的“入侵者”
八十年代出版的降边嘉措的长篇小说《格桑梅朵》《十三世达赖喇嘛》中,出现了明显的对西方帝国主义殖民者群体形象的塑造。如在《格桑梅朵》中,小说虽未直接描写西方人形象,但是却借藏族人民口中的“国外友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口,在小说叙事以及西方人前后的一系列行为中,塑造了一群英美帝国主义分裂分子,他们在背后挑唆中国与藏族的团结关系,试图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欲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而历史小说《十三世达赖喇嘛》则着重描写了英国殖民者这一形象群体。小说是全景式地反映了西藏人民英勇抗击英国侵略者的英雄事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帝国主义将侵略魔爪伸向西藏的宏大历史背景之下,西藏人民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尊严,与英国殖民主义者展开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但这里的殖民入侵者形象较之《格桑梅朵》更深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道德判断的价值模式与善恶分明的一元观念和方法,建立了历史判断的价值模式。小说在对西方人有泰、荣赫鹏、来协、德尔智等这些人物塑造上,表现出了性格的“二重组合”模式。小说塑造的西方人形象虽然是历史上真正的人,具有侵略者的身份及形象定位,但是小说客观地表现了他们。小说中的侵略者不仅毁灭了西藏人民的美好的家园和宁静的生活,也毁灭了他们自己,他们的悲剧是必然的。
同时,在八十年代小说扎西达娃《西藏,隐秘岁月》与色波《圆形日子》中,出现的西方人形象类型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被政治化”的形象趋向。小说《西藏,隐秘岁月》中的西方人形象一个是 F· M贝利中校,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随英国殖民者入藏;另一位是他的助手 H·T·摩斯赫德上尉。可见这两名西方人形象都是“被政治化”的,他们都包藏祸心,对藏族意图不轨;在色波的小说《圆形日子》中,出现了一位来自美国的摄影师形象,然而这位美国人在小女孩的眼中却是令人恐惧的“魔鬼”,从美国人乘坐龙卷风出现到之后与小女孩的接近,使小女孩感受到美国人背后的真实目的,隐喻了西方国家有太多的人在打藏族的主意,暴露了西方人窥探和觊觎西藏的野心,从侧面反映出了被赋予政治色彩的西方入侵者形象。
(二)八十年代的其它西方人形象
1.《隧道》中的美国徒步旅行家
索穷的小说《隧道》中出现了一位美国徒步旅行家,小说有这样一段对话:汉族商贩、穿羊皮袄的藏族小伙、美国徒步旅行家三人在一座小县城相遇,美国旅行家一身藏族人的打扮,“穷酸与滑稽中透着一股自负的神情”,仅学会了问藏族人们索要糌粑和酥油茶的几句藏语。虽然三人一开始很有兴致地交谈,但是由于语言不通,他们用眼神和手势交谈,后来发现就连手势等其他暗示也晦涩难懂,彼此根本无法理解,导致对话无法进行。后来,三人只能用嘴来交谈,但搜肠刮肚,三人能说出来的句子仍然有限:藏族小伙只会用汉语讲“他,哪里来?他…”;美国人故作神秘,却只能说一句藏语“糌粑没有嘛?”;汉族商贩也只能用英语重复着“中国,美国”。三人的相遇,暗示了三人各自所代表的文化的交流与沟通。而三人之间严重的沟通困难情况,以及最终的对话失败,也揭示了中西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中西文化之间的初次尝试与接触确实存在巨大的沟通困难。
2.《白色》中的美国业余传教士罗伯逊
通嘎的小说《白色》中,讲述了一个“我”与边珠、业余传教师美国人罗伯逊之间的一段经历和故事。罗伯逊来到藏区遇到许多热情好客的敬酒队伍,不小心喝多了进了医院,与“我”和边珠在一间病房。罗伯逊来到藏区却发现这里的人们心灵洁净,不需要自己的宗教洗礼和忏悔。罗伯逊与边珠在病房讨论宗教哲理与信仰的问题,罗伯逊给边珠讲述耶稣的故事,边珠不了解,“跟你一样的黄毛家伙吗”,罗伯逊宽恕边珠的无知,并解释说耶稣是“所有人的生命”。边珠也给罗伯逊讲述释迦牟尼与莲花生大师。后来边珠从一本英国刊物的一篇报道上,发现有关一位西藏活佛的转世灵童在欧洲出世的新闻,报道的内容写到灵童金黄色的头发,绿色的眼球,一幅西方人的面孔,却说着流利的藏语,因为种种原因滞留在外国无法回到拉萨。后来,罗伯逊比我们提前出院,“黄毛家伙就是体质好”,然而边珠的身体却日益恶化,他在梦里断断续续重复着“罗伯逊是好样的…基督在那里…”边珠驾驶的白色帆船不知道驶向何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 “因为他没有领航,因为他的帆是白色哈达制成的” 白色作为西藏族独特的色彩,是生命的底色,也是信仰的标志,它让藏族人民充满了神性的敬畏,感受信仰之下的生命。通嘎想象自己驾驶着白色哈达制作的帆船闯荡世界,却因为宗教传统的退潮与枯竭,白色哈达 “挡不住狂风的吹击” ,找不到信仰的栖息地,“以至再也不能漂浮他的船”。 内心迷惑的他,却在这篇关于 “西藏活佛的灵童在欧洲出世” 的报道中重燃起生活的希望,凸现出藏传佛教在藏民心口中的崇高与神圣,以及宗教信仰在当下时代的境遇。 并逐步呈现出藏族人在与西方人关于宗教哲理的讨论中,展开了对信仰的深入思考。
三、八十年代被政治化的西方“入侵者”
八十年代开放之初,作为藏族小说的刚刚开始,八十年代的藏族小说虽然有西方人形象刚刚跃出,但是小说建构的西方人形象还是呈现多种类型与不同面貌的。因此笔者只着重讨论八十年代比较集中建构的西方人形象类型,以此探索这个时期西方人建构的突出形象,探索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西方人形象的发生。八十年代前期的藏族小说创作受传统意识形态影响,小说家笔下的西方人物形象呈现出作家所在社会的身份特征。
(一)《格桑梅朵》中的“国外友人”
藏族作家降边嘉措于1980年创作出版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格桑梅朵》,“格桑梅朵”意为吉祥花、幸福花,是新时期藏族文学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小说揭露了帝国主义的阴谋,歌颂了党解放西藏的伟大功绩。在对西方人形象的塑造上,也可以清晰地看出作者应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对西方人物进行塑造和划分。正如巴柔所指出的“事实上,形象… 表达各种社会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范式”作家基于自身经历,从藏族人民特有的心理和视角,去看待和理解时所发生的事情。在这部小说中,降边嘉措虽未直接呈现具体的西方人形象,只是出现了英美帝国主义分子以及佚名“国际友人”这一群体的概念形象,但降边嘉措在小说《格桑梅朵》中借小说人物之口,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多次暗示那些支持噶厦暴动的“国外友人”的存在,极少数的反动分子在英美帝国主义分裂分子的支持怂恿下,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伟大行动。作者借助小说主人公边巴之口,表达对西方分裂分子的抗议“金珠玛米解放西藏人民,管洋人什么事”小说还揭露西方人在背后挑唆的阴险图谋,“告诉你们吧,在国外也有人给我们撑腰”,“他们正在积极活动,争取外国朋友的帮助”在英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外国反动派的支持和怂恿下,西藏反动分子比如小说中噶朵的叔叔桑登曲培等人,公开进行背叛祖国的阴谋活动。这些西方人形象在小说中虽然终未现身,却是提供支援和枪支设备的人物,他们总是在小说历史叙事的暗角若隐若现,显现出狡诈阴谋、幽隐、凶险的形象特质。
(二)《西藏,隐秘岁月》中的英国人
扎西达娃的小说《西藏,隐秘岁月》可以说掀开了西藏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大幕,小说以简洁的叙述技巧浓缩了西藏高原近百年的发展历程,用文学的手法暗示了英国曾经入侵藏区这一时期的历史,展现了西藏高原缓慢而坚韧地探索、进步艰难的历史身影。英国侵略西藏的第一步就是先派人来西藏进行秘密的侦查、测绘以全面掌握西藏情况。小说中的西方人形象分别是 F· M贝利中校及助手 H· T· 摩斯赫德上尉,他们名义上是来藏族考察雅鲁藏布江地貌,其实暗含殖民入侵的不轨意图。小说的这一段时间是1910-1927年,生活在廓康的藏民,七十五岁的米玛老人和他的老伴察香怀孕两个月生下次仁吉姆,“次仁吉姆”在藏语的意思是美丽古老的西藏的化身。次仁吉姆很小就表现出神灵化身的种种特征:可以画凡人无法看明白的深奥图盘,会跳西藏失传的格鲁金刚舞。最后因为英国人的出现,次仁吉姆的以上能力全部消失。察香有一次去小溪边汲水,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模样奇特,嘴上一撮胡子,脸上的皮肤又白又红”的“魔鬼”,便扔掉水桶慌忙跑进屋里死死地抵住门,并歇斯底里地高喊碰见了魔鬼,米玛问察香是不是人罴,察香的脸也像魔鬼一样可怕地说: 他们长着红头发,比魔鬼更可怕。于是两人抱着次仁吉姆跪在佛像前声音颤抖地连连祷告,请求菩萨驱除这些魔鬼 “别让它们闯进来残杀无辜的生命”。米玛将门打开一条缝,看到他们是“红发鬼”模样,眼睛是蓝色和灰色的。英国人拿出活佛的照片给廓康人看,并介绍自己是英国人,他的同伴生病了只是来考察雅鲁藏布江,不是魔鬼,廓康人才慢慢放松警惕。
英国人递给米玛一个望远镜,让他看远处的景象,米玛心里的反应突然莫名的紧张,因为“那些景象一下跑到他的眼前,连江面一只牛皮船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架望远镜可以很轻易地深入藏族,透视藏族的秘密,米玛“半张着嚅动的嘴唇”对英国人这种“法术”感到惶惶不安。米玛还发现“他们眼睛的颜色很怪,一个是蓝色的,另一个人是灰色的”,并问起这一带的地貌情况。就连“那些平时惯例来廓康饮水的贝母鸡,野兔和獐子凭着动物异乎寻常的本能嗅到了什么,始终没有飞到廓康溪水边的草地上来,只是在百米之外的乱石缝里叫唤着”,由此暗示出英国人表面友善,其实心怀不轨的考察行为。心肠慈悲的察香看到那个生病的英国人“感觉活不过今天晚上了”,于是为英国人做饭烧茶款待他们,还跪在佛像前为生病的英国人祈祷,但是第二天生病的英国人却突然好了,不禁让人猜想,英国人是否佯装生病,以骗取藏民的同情与信任。英国人不认识的达朗突然从岩石上冒出脑袋,英国人便愤怒地放枪,还对米玛笑笑“说他不过是用枪声把这个讨厌的小家伙赶走”,显露出英国人多疑、伪善、内心凶狠的形象。英国人临走在次仁吉姆的右脸颊上吻了一下。结果吻过的地方红肿流脓,米玛气得对英国人破口大骂,后来察香给女儿敷上药草并日夜祈祷,三天之后,红肿消失的次仁吉姆“她的目光不再透着神明的聪慧,也不会划沙盘,跳金刚舞,一切神灵化身的迹象全部消失,只是脸上永远印着几粒浅浅的黑痣”。而且次仁吉姆刚进入青春期就有一种洗浴狂,不洗便会奇痒难忍,涂任何药都不管用。然而米玛翻出英国人留下的绿色军服给次仁吉姆穿上时,奇痒便瞬间消失,直到次仁吉姆死的时候“她还穿着那件百孔千疮,早已看不出原来颜色的老式英军服,皇家工兵制服的袖口和衣襟边缘磨得碎条缕缕”,到死都没脱下来过。反映出西方人的闯入的历史事实,已经给藏族带来无法避免以及无法摆脱的影响。西藏作为中华民族半殖民地历史的一部分,小说暗示了藏族传统的文化在西方人的殖民之下逐渐消解和破解它的神秘,藏族的传统文化遭到西方文化的渗透和巨大冲击。
(三)《圆形日子》中的美国摄影师弗兰克
色波的小说具有强烈的现代主义色彩,《圆形日子》的整体框架就是一个首尾闭合的圆形结构,意义模糊、混沌,难以捉摸。它以女儿清晨对自己的“妈妈”的呼唤开始,在黄昏时母亲对女孩“朗萨”的呼唤声中结束。女孩在树下等待母亲的时候,蓬头垢面的‘黄发美国佬’弗兰克闯入女孩的视野之中,引发女孩的一系列不安的心理活动。美国人出现之前,女孩对面骤然刮起了龙卷风,由低矮、急剧旋转的一团迅速升高成圆锥体,贴着河面移动,躲到山后面又钻出来,最后“像给吸尘器吸走了似的,倏地消失了”,于是一个蓬头垢面的黄发美国佬出现,为女孩眼中的西方人“魔鬼”形象做足了铺垫。这个外国青年男子一幅西藏女人的打扮,仿佛是为了掩人耳目,他“晃了晃脑袋,又朝四周看看”,拿着长焦照相机突然停住,用夸张的姿势举起相机对着秃鹫和女孩“咔哒咔哒”拍照,然后走到树下一只手撑着树干喘息,灰色的眼睛,“瘦削的肩膀”一耸一耸的。可以猜想这个西方人将长焦镜头对准藏族,试图通过镜头闯入藏区,透视藏族神秘的文化。
女孩对西方人的出现满是疑问,西方人介绍自己叫弗兰克”。女孩对他说:“你是魔鬼吗?”,“我亲眼看见你是从河那边飞过来的”,“只有魔鬼才不好好读书,成天驾着龙卷风到处闲逛”;美国人回答:“不不”,“我是人。不信?那好,我站到太阳下面去,你看看有没有影子。”女孩说亲眼看到美国人从河那边驾着龙卷风飞过来,而且即使在太阳下依然没有影子。在女孩周围,形成了一种无形的恐怖“场域”,这种恐怖性主要作用于女孩的内心、情感。弗兰克左顾右盼,极力向女孩证明自己的身份,“叽里哌啦地吼叫起来,慌乱地在那里转圈”,俨然是对“魔鬼”形象的勾勒。当美国人找到自己的影子的时候,“一颠一颠”地回到树下,高兴地“一挂口涎从嘴角流出来”,然后“咝”的吸回去,弗兰克说“我把自己的影子挡住了”,其实暗示了他不能示人的真实目的,美国人滑稽可笑,同时又令人反感、具有恐怖色彩。美国人将脑门靠近女孩证明自己具备人的体温,并问女孩感觉到温度吗?女孩却没有回答,因此到目前为止,美国人的形象还是无法与“魔鬼”形象脱离开来。此时,女孩的内心活动是怀疑和担心,认为这个从美国来的黄毛小子“他是在打我的主意,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情。打我主意的小伙子真是太多太多了,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还有外星球的,他们都给我寄了照片”在这里,藏族女孩仿佛是整个中国藏族的代表,此处隐喻了不只是美国人,世界上还有诸如德国、意大利,甚至不知道的外国入侵者都在想方设法窥探和觊觎西藏,表现了藏族人民对西方人闯入的紧张和恐惧。
四、政治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形象生成
八十年代中后期藏族小说文本中的西方人形象,一方面体现了中国近代对西方人形象套话的延伸,另一方面反映了历史与时代衔接互动下作家主体创作意识的初步觉醒,是小说家面对传统与现代交融背景下创造的形象过渡,是中国藏族作家面新的写作姿态和民族文化意识的彰显,以及作家的历史记忆对他们建构西方形象的影响。
(一)外族侵略藏族历史下的社会集体创伤
西方人与西藏的直接接触,始于17世纪早期,第一批到达西藏的西方人,就是葡萄牙耶稣会的传教士安东尼奥·德·安夺德( Antonio de Andrade)一行。 19世纪70年代开始,英法俄等殖民主义者以传教、经商、调查、游历等名义, 进入西藏,以印度为根据地的英国殖民势力成为近代以来西藏面临的最大威胁。 比如,在《西藏,隐秘岁月》中,作家扎西达娃就揭示了以考察勘探为名义的两名英国人,进入藏族腹地进行秘密的殖民入侵活动; 在小说《圆形日子》中,作家色波塑造的一名“没有影子”的拿着照相机进入藏区的美国人,也暗示了一种以旅行、游历为借口的一类西方人形象,在暗地里悄悄地打着藏族的主意。
1876年,中英签订不平等条约《烟台条约》,英国人抢夺赴藏游历考察的权利,英国人频频入藏,于是噶厦政府在隆吐山设卡防御,由此引发了西藏人民的第一次抗英战争。1888年,格雷厄姆上校率部进攻西藏,西藏守军手持土枪、弓箭、刀等原始武器进行自卫反击,伤亡惨重,最终战败。从此,英国侵略势力侵入西藏。英国多年来对西藏的侵略,侵略者对所到之处抢劫与破坏寺庙等破坏活动激发了西藏人民的仇英心理,成为藏族人民的集体创伤,因而通过小说文本表现出来;1902年,英军入侵岗巴宗做试探,旋即撤出。1903年,英印政府以荣赫鹏为正帅,怀特为副帅为大规模侵藏做准备发。曲米辛果惨案之后,英军继续进逼江孜,1904年江孜保卫战打响,藏军顽强抵抗,江孜最终陷落,第二次抗英战争失败,西藏被迫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也为当代“西藏问题”留下祸根。 因此在降边嘉措的小说《格桑梅朵》中,就塑造了一些试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英美帝国主义分裂分子形象。在小说《十三世达赖喇嘛》中,以英军侵略江孜保卫战的历史为背景,塑造了众多西方殖民者形象,尤其是对英国殖民者的形象塑造更为深刻、突出。
藏族小说家固执地站在藏族民族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立场之上,依据本民族意识和社会背景建构出“被政治化”的西方“入侵者形象”。降边嘉措的长篇小说《格桑梅朵》《十三世达赖喇嘛》等小说均反映、记录和表现了藏族遭受外族侵略历史下的社会集体记忆。当代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巴柔称之为“社会集体想象物”的概念,比较文学形象学意义上的社会集体想象物,是以作家本人所属的社会和群体的想象为介质的,作家只是一个媒介,八十年代的西方人形象背后,隐藏着历史的际遇。正是外族侵略藏族的反映,因此小说中的西方人形象浓缩了中国藏族人民,对这段历史的痛苦创伤和对外国入侵者的仇恨,是整个藏族人民想象力同时,小说中的西方人形象也是素朴的民族情感的体现,从而形成藏族人民对西方人形象的固定看法。因此,藏族民众对西方人所表现出来的憎恶、排斥和抗拒心理就可以理解了。
(二)中国近代西方人形象“套话”的藏族延伸
近代中西文化的接触是在西方列强入侵的特殊背景下展开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西方人用“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大门。自那时起,人们在中国近代文学作品中经常发现“洋鬼子”或“鬼子”就是西方人的代名词。“洋鬼子是19世纪中页至20世纪中叶一百年间,中国言说西方人最具代表性的话语。”[3]除此之外,与西方人形象的套话还有“洋人”“洋鬼子”“红毛番”等,这种在某一历史阶段中被反复使用,具有多语境性的单一形态的具象,被称为形象学中的“套话”。套话“主要指一个民族长时间内反复使用、用来描写异国或异国人的约定俗成的词组”,是描述被注视者的一个重要术语,是形象的一种特殊而又大量的存在形式,“作为他者定义的载体,套话是陈述集体知识的一个最小单位。它释放出信息的一个最小形式,以进行最大限度、最广泛的信息交流”[4]因此,用“鬼”来形容近代以来的西方人形象是被套话了的,而中国近代西方人形象的套话在八十年代的藏族小说中同样的得到应用和延伸。因此,在八十年代藏族小说的西方人形象书写中,这一套话重新出现并发挥作用。
在八十年代藏族小说中的西方人形象始终与“鬼”字紧密连接在一起,如《西藏,隐秘岁月》中的英国人“红发鬼”,色波《圆形日子》中的“魔鬼”美国佬。除此之外,藏族小说中的套话也与“洋”字联系在一起,比如,《格桑梅朵》中的“洋人”,《十三世达赖喇嘛》中的“洋妖”等等。因此,研究套话就成为形象研究中最基本、最有效的部分。套话存在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深处,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对西方人形象的看法。这些套话不仅表达了藏族人民对西方入侵者的仇恨和轻蔑,而且与入侵者建立起了最直接、最简单的联系,标志了对“他者”的一种凝固看法,成了一个只有单一语义的信号。套话在某一时期中可以反复出现并使用藏族人一开始就用怪诞、鄙俗等词语概述西方人形象,并从中读出恐惧、憎恶、强盗般的入侵、相貌丑陋、居心叵测等。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文化中,西方人形象甚至可以说是被部分程序化了,成为一种象征语言,且趋向单义。
(三)政治主流话语与宗教传统
“凡按本社会模式、完全使用本社会话语重塑出来的异国形象就是意识形态的”[1]功能在于维护和保持现实及现实秩序。作家受不同意识形态影响,即便是受某种意识形态影响的程度不同,也都会对这段历史时期中的西方人物形象作出不同建构。在八十年代初期的官方主流话语中,社会主义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加优越的社会制度,政治控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八十年代作家写作的制约是十分明显的。因而,八十年代的西方人形象想象有大体一致的倾向,即倾向于一种“被政治化”的形象类型,比如降边嘉措小说中西方帝国主义,西方侵略者形象的塑造等等,西方世界的西方人形象是扁平化的,尽管八十年代中后期有扎西达娃、色波等作家们尝试着跳出概念化塑造的框架,但仍然没有足够的自信展开自己的西方想象。具体来说,小说家们受意识形态影响,因而小说家笔下的西方人物形象呈现出作家所在社会的身份特征。
伴随着西藏的解放,1959年,经过民主改革,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实现了政教分离,宗教不再左右政治、经济和文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了主人。但是,另一方面,藏传佛教千百年来仍然充斥着藏族人民生活的、精神的和心理的各个方面,因而,藏族小说中的西方人形象不可避免地带有宗教的渗透。在《格萨尔》中,外来入侵者即是恶魔,而藏族人崇拜的英雄格萨尔王则是善业和正义的化身,主张倾心向内,反对分裂,带领藏族同胞与入侵的敌人浴血奋战,保卫家乡,打击恶魔,显然也是符合藏传佛教的道德要求的。于是,西方入侵者对于广大的藏族人民来说,便是恶魔。这非常清楚的说明,藏民族对善心、善行的张扬和对侵略的野心、恶行的贬斥,与藏族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一致的。可见,这种反侵略、反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情愫很早就存在于藏民族的传统宗教道德之中了。因此,降边嘉措小说中的僧俗民众团结一致,在面对西方殖民者入侵的时候,不屈不挠、英勇斗争。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藏族小说对西方人形象的建构表现出一个明显的倾向,即小说中的西方人形象在这一时期藏族小说家的笔下一般都是殖民者或入侵者的形象,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些西方人形象大都遭到藏族人民的抵触或排斥,而藏族小说家对西方人形象的情感也往往持批判态度。
结语:综上所述,在八十年代前期,小说家们对西方人形象的塑造多以“殖民者”的形象呈现,且集中为英国侵略者形象。小说作品的西方人物形象塑造遵循了现实主义美学规范,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热衷于赋予西方人物阶级内涵;而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才出现了其它类型的西方人形象,西方人的身份、国籍等开始出现纷杂,各类改头换面的外国人物初露行迹,西方人形象以考察者、传教士等各种身份纷纷出现,甚至超出了藏族本土者和民众意识的认知速度和心理负荷,也往往带着明显的诱惑,引发藏族民众的不安、乃至惧惮。对英国人形象的书写开始转向其他西方国家的人物形象塑造上,最突出表现为对美国人形象的呈现,对西方人形象的建构开始关注对个体西方人形象的注视,从而使西方人形象逐渐开始聚焦,但是对于西方人形象的情感态度还是存在历史意识形态遗留的印迹。从总体上来看藏族小说家对于西方人形象的书写,无论是在情感上认同西方,还是坚持历史殖民记忆的西方立场,都是中国在当前的历史文化境遇中描述和想象西方的,难以摆脱整个藏族对西方的社会集体想象。
[1]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J].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p25、p35
[2](美)爱德华.W.萨义德.王宇根译.东方学·后记[M],三联书店,1999年,p426-427
[3]孟华.中国文学中一个套话了的西方人形象[J].孟华.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p12-16
[4]巴柔.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J].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p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