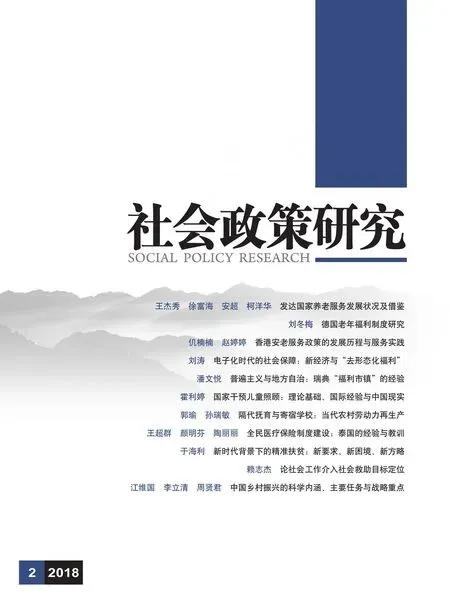社会运动的“第三条路”:领导管战术,诸众管战略
2018-03-31尤玲
尤玲
对于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政治秩序来说,过去的十年可谓是一个相当动荡的历史时段:2008年,长期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保驾护航之下高歌猛进、横行全球的金融资本主义,终于以震动寰宇的方式发生内爆,引发了规模空前的全球经济动荡;受到金融海啸猛烈冲击的广大民众,则在随后的数年里陆续发动了许多颇具声势的抗争运动。尽管问世于冷战终结时分的“历史终结论”至今依然不绝于耳,但全球资本主义所造就的封闭性历史视野,却已然在此起彼伏的民众抗争运动的冲击下展露出裂隙。面对这样的历史形势,如何发掘并激发社会运动的解放性潜能,使之不仅能够表达民众的不满,而且能够为人类社会开启真正的另类选择?这是摆在今日左翼思想家面前的关键难题。
在当代欧美左翼思想界,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堪称这一难题的最为积极的解答者。早在2000年至2009年间,这两位思想家就曾联手合著《帝国》、《诸众》、《共同体》三部曲,尝试借用“帝国”这个概念来描述去中心的、无疆界的、超民族国家的全球化政治秩序,进而尝试用“诸众”这个概念来指认一种处在“帝国”秩序之下、而又反抗着“帝国”统治的历史主体。在哈特与奈格里的乐观构想中,“诸众” 作为新时代的主体,一方面保持着多样性和内在差异,另一方面又能够自发地联合起来展开抗争性的政治行动,而他们的行动则是以各个“奇异性”在“共同体”当中共享财富为基础的。
在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的一系列全球“占领运动”爆发之后,哈特与奈格里又在2012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宣告》的册子,尝试从这波社运浪潮中提炼出自主组织、自由表达、直接参与、民主决策等政治原则,进而提出:新时代的解放运动应当致力于将这些在诸众抗争中获得宣告的政治原则转化为构建新社会的宪章。时隔五年之后,这两位始终与全球社运保持密切联系的重要思想家,又基于他们对社运动态的新近观察,出版最新著作《集会》,反思并发展了他们先前提出的理论构想。作为当代社运最具影响力的观察者、记录者与理论提炼者,哈特与奈格里的这本新书无疑值得我们关注。他们的著作蕴含着哪些富有启示性的洞见,同时又暴露出怎样的欠缺?
运动的“第三条路”:挖掘诸众的战略能力
哈特与奈格里为什么要写《集会》这本书?在2017年美国费城的新书发布会上,哈特就曾说过,他和奈格里的思想与其说是为了给未来的运动指明方向,不如说是对已有运动的总结和反思。两位作者敏锐地观察到,2008年之后的这波全球社运浪潮,体现出显著的扁平化、去组织化、去中心化倾向,它们往往缺乏自上而下的领导,依赖于人们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的自发参与和串联。这一波去组织化的社会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政治面貌,也没有取得持久的政治成果。曾经的阿拉伯之春迅速滑入寒冬,土耳其等地的占领运动则不仅未带来更民主的局面,反而造成了公共舆论的撕裂。
正是基于上述观察,哈特与奈格里在《集会》这本新书中尝试提出并解答这样的问题:如果去中心、无组织的社运模式并不完全可行,那么,期望通过社运来改造社会的左翼人士还能有什么路可走呢?
更重要的是,这种去中心、无组织的社运模式,又恰恰比较接近两位作者在之前的一系列著作中提倡的“诸众自发集结”的设想,也在运动最高潮的阶段获得了两位作者的热烈支持。这样一来,两位作者的自发反思就显得更加必要和珍贵:如何弥补“诸众自发集结”这一设想的缺陷?如何找到一条通往更持久、更有效的社运模式的道路?
两位作者在《集会》中提出,左翼运动既不需要回归传统的那种自上而下的运动模式——无论是曾经在20世纪主导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先锋队”模式,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工会”模式——也不需要完全拒斥领导或组织,左翼运动可以选择的社运模式,不应该只是在这两极之间摇摆,而应该找到“第三条路”。两位作者承认,对于社运来说,领导和组织是有必要存在的;但他们同时强调,领导和组织在社运中扮演的角色,却应该是与我们的传统想象完全不同的。
在两位作者看来,社会运动的核心工作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战略性”的工作,即掌控全局、制定长远的目标;另一部分是“战术性”的工作,即局部地、短期地解决具体运动场景中的操作性问题。在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社运模式中,往往是由运动领袖、上层组织来负责战略,而基层社运参与者则负责战术。但在两位作者对“第三条路”的设计中,这个关系应该发生根本性的逆转:领导管战术,“诸众”管战略。也就是说,关于一场运动根本的、长期的蓝图目标,关于“我们究竟要什么”的全局问题,应该由千千万万的基层抗争者在自我组织和自我串联中解决;而运动的领导只负责在危机时刻解决具体情境下的具体问题。
那么,我们凭什么认为,“诸众”具备设计战略性蓝图的能力或者潜能呢?
哈特与奈格里相信,诸众已经具备了把握运动宏观大局的战略能力。然而,按照两位作者的观点,如果我们想看到这种战略能力的体现,就不能只着眼于政治场域、社会运动,而必须要回到社会生产的场域,回到经济场域当中。在《集会》中,两位作者正是试图通过分析当代社会的经济生产,从新的社会生产模式中发掘出诸众的战略能力。
哈特与奈格里认为,在当今社会的经济体系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是一种可以被称作“非物质劳动”或者说“生命政治劳动”的劳动形态。所谓的“非物质劳动”指的是,这种劳动生产出的主要是诸如符号、图像、信息、知识这样的非物质性的产品;而所谓的“生命政治劳动”则是指,这种劳动不仅会产出可供流通的“产品”,而且还会在劳动过程中持续不断地生成劳动者的生命形式与主体性。
在哈特与奈格里看来,“非物质劳动”或者说“生命政治劳动”至少从四个方面生成劳动者的主体性:第一,当今社会的主导性劳动不再是单向度的机械化的高强度体力活动,而是需要劳动者动用智力、知识、语言、情感。虽然这个过程依然存在严重的异化,但毕竟动用了人的能力的各个维度,体现出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力。
第二,当今社会的主导性劳动不再是由资本家组织起来的原子化个体的流水线作业,而是高度依托于劳动者的自我组织,依托于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而劳动者的创造力也不仅体现在最终产出的非物质性的智识结晶之上,而且体现在他们不断通过自我组织创造出新的劳动合作形式与合作网络。
第三,“非物质劳动”主要依靠的生产资料不再是有形的资料,比如大工厂的机器,而更多是无形的资料,比如知识或算法。大工业时期的劳动者要夺取有形的机器是非常困难的,但今天的劳动者却已经在通过掌握知识和算法,踊跃地夺回无形的生产资料。
第四,“生命政治劳动”在高度合作化的劳动过程中持续生成着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与情感联结,这让人们看到一种以集体的民主的方式来管理与分配资源和产品的可能性,进而让人们看到一种超越既存的私有制或公有制、建设民主共享的“共同体”的可能性。
基于这四个方面的考察,哈特与奈格里提出,当代社会的新型劳动形态已经蕴含着极具抗争潜能的劳动者主体性,有理由相信这种潜能可以转化成社会运动中的战略能力。
新自由主义时代,劳动过程不断生成抗争性主体
可以看出,在《集会》这本新书中,哈特与奈格里依然延续了自《帝国》、《诸众》以降的乐观主义基调。两位作者甚至推出了“诸众创业”的概念,来解释新形势之下社会运动参与者所需要具备的政治素质。众所周知,“创业”一词一直都是新自由主义的专属词汇,而哈特和奈格里则试图从左翼的角度主动夺回这个概念的阐释权,用它来指涉劳动者对于新型合作形式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创造。
暂且不论这种争夺阐释权的努力能否取得成功,哈特与奈格里之所以会提出这种思路,首先说明了他们预设“诸众”(劳动)具有先于“帝国”(资本)而行动的能力。而这种预设植根于两位作者的“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立场。
从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工会运动和无政府主义思潮中应运而生的“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工人阶级的主体性,认为工人阶级能够主动地开展自治性的组织建设,从而与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和国家体系形成对抗,迫使资本主义体系发生转型。基于这样的理论立场,哈特与奈格里在他们的论著中提出,由工业化大生产向高度自组织的“生命政治劳动”的转型,在本质上并不是由资本主导的,而是由劳动者自下而上的创造力所推动的;而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建立,则是资本对于劳动者自行开发出的新型劳动形式的反应。
换言之,在哈特与奈格里的眼中,并不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是“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相应的调整”。因而,两位作者一再重申,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诸众”抗争——从新左派运动、民权运动到“工人主义”运动、“自治主义”运动——迫使资本不得不作出新的调整和回应,这才导致了“帝国”这一全球资本和权力的新融合形式兴起。
更具体地说,在《集会》一书中,哈特与奈格里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向度上贯彻了自治主义的视角,由此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示性的洞见。
就过去的向度而言,哈特与奈格里极其重视过往数十年间各种社会运动的成果。作为社会运动切身的参与者和观察者,哈特与奈格里的论述植根于社会运动本身。他们面对着社会运动在实践中发展出来的智慧,主动地修正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哈特与奈格里也非常准确地捕捉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化的本质,尤其是从大工业时代到新自由主义时代资本攫取模式的变化。在两位作者看来,不同于工业化大生产时代资本对劳动过程本身的严密操控,今日的资本已经越来越少去直接干涉劳动过程,而是往往要在价值由“诸众”通过自组织的劳动过程生产出来之后,再经由其他环节来攫取这种价值。而在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中,资本所借助的最主要的价值攫取手段便是五花八门的金融工具与金融衍生品。
两位作者还特别指出,当代社会的非物质劳动已然打破了“工作”和“非工作”之间的界限,在那些原本会被视作“休闲娱乐”的“业余时间”与“日常生活空间”中,作为消费者的我们也依然在不自觉地为资本创造着价值。例如,在具有强烈社交性的网络游戏中,玩家的种种活动为作为平台的游戏本身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又如,在谷歌搜索引擎的网页排序算法里,判定网页重要性的基础实际上是互联网用户的“注意力价值”。也就是说,我们在搜索引擎上看到的网页排序,事实上都可以视作互联网用户的媒介使用经由特定算法的整合而完成的协同作业成果。
对于哈特与奈格里的乐观主义论调而言,格外重要的观察是,当代社会的价值生产环节与价值攫取环节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离,生产领域逐渐成为一个由诸众自主发挥创造力的领域。由此而来的进一步推论是,今日的资本已然处在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资本不能过多地干预劳动过程,否则就会扼杀那种自组织的劳动过程的创造力;但另一方面,一旦价值攫取环节和价值生产环节保持距离、一旦资本是外在于劳动的,那么,劳动过程就会不断生成抗争性的主体。
按照哈特与奈格里的观点,无论劳动者是否自觉,基于密切合作的非物质劳动都不仅创造着价值,而且还创造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哈特与奈格里对未来抗争所抱有的期许,也正来自于他们观察到的这种源自社会生产的情感联系与协作网络。
诸众天然是运动的主体吗?
在笔者看来,哈特与奈格里的论述链条存在着一个核心问题没能解决,那就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体现出的创造力,就一定能转化为政治行动中的战略能力吗?换言之,我们真的能认为,生产领域所形塑的劳动者主体,就必然会转变成政治抗争的主体吗?
这种从经济场域到政治场域的转化,对于哈特与奈格里的理论设想至关重要,哈特与奈格里似乎预设了这种转化的天然可行。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转化绝不会自动发生,而是需要一个移植、转译、激发、动员的过程。究竟是什么力量和机制,能让人们以政治的方式理解自己的日常生活,将自己塑造成政治抗争的主体,从而参与到解放性的社会运动中来?对于这个问题,《集会》一书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解答。
诚然,哈特与奈格里的自治主义视角肯定了劳动者作为历史主体的创造力和斗争精神;但这一视角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反应性的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系统,又是可以根据现有的社会运动锋芒而进行一系列的内部调整、自我完善和更新进化。也就是说,它能够挪用并扭曲社会运动的一部分诉求,从而达到压制抗争精神的目的。
比方说,哈特与奈格里在书中就指出,面对着社会生产逐渐自主化的趋势,新自由主义挪用并扭曲了“自主”这个概念,在资本主义的模式里加入了许多与“自我管理”相符的元素,例如手机app自助购票、自助登机等等。新自由主义通过这种挪用、扭曲和内化,为人们布置了一种生活自治的幻象,从而抵御了劳动者所呼唤的更彻底、激进的自治。
更有甚者,两位作者在书中还指出,新自由主义在今天攫取价值的典型方式,就是先创造出机会和空间来让劳动者在自发参与、自我组织中自由地生产价值,再以不易察觉的方式将这些价值收割。但两位作者没能进一步意识到,这种由资本在暗中操控的自发参与和自我组织,完全有可能榨干劳动者的注意力、精力与热情,使当代的劳动者无暇也没有兴趣进行政治意义上的动员。典型的例子,就是伴随偶像工业崛起的大规模“粉丝动员”。围绕着“自家爱豆”的“粉丝动员”,的确体现了粉丝社群高超的自我组织能力。在文化产业资本的引导下,各类粉丝后援会不断创造着新的合作形式和应援战略,也让资本赚得盆满钵盈。同时,作为消费者和劳动者的粉丝们,付出的不只有金钱,更是大量的精力、创造力和情感劳动。但这种与文化产业资本亲密互动的粉丝动员越是高涨,粉丝们往往就离抗争性的政治主体越是遥远。
从劳动者主体到抗争主体的政治转化之所以困难,不仅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系统对抗争意识的微妙压制和对“诸众”创造力的收编,而且也和“诸众”自身所面临的疑难有关。
正如前文所述,哈特与奈格里的乐观主义论调是与他们对“非物质劳动”与“共同体”这两个概念的阐述息息相关的。然而,两位作者也都承认,无论是非物质劳动还是创造共同体的潜在可能性,都只是在“性质”而非“数量”的意义上占据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换句话说,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依然存在着大量从事物质性生产的劳动者,而全球的大部分资源和产品也仍然很难被视作劳动者共同体的共同财富。
按照哈特与奈格里的解释,共同体的共同财富似乎只局限于那些相对而言并不稀缺的资源,比如共享的知识或城市空间。这样来看,使用谷歌搜索的互联网用户们或者占据城市空间的社运参与者们之所以能够自发地开展资源共享实践,是否仅仅是因为他们尚未受到稀缺性的限制?
哈特与奈格里在书中多次提到,近年来全球联动的占领运动参与者,在运动期间自发形成各种共同体网络:从开罗解放广场到伊斯坦布尔的盖齐公园到美国的立岩(Standing Rock)保护区,抗议者们共享食物、帐篷、电力等资源,他们的行为超越了既有的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的二分法,展现了运动自我管理的潜能。而在归纳运动的失败原因时,两位作者又一致矛头对外,将原因归结为各种外部煽动者、警察暴力和媒体偏见的影响。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近年来许多运动的失败不仅在于外部的镇压与歪曲,而且也在于内部共同性契约的自我瓦解。我们不得不认识到,在互联网社交媒体和社会运动现场所创造出来的共同性或许是极端脆弱的,它也许需要一种专门的政治化过程才可以巩固下来。
换句话说,两位作者在《集会》中深入现有社会运动内部的观察视角,既是他们的长处,也成为了他们的弱点。当他们沉浸在已经成气候的社会运动中时,他们所看到的社运面临的所有问题,似乎都可以被概括为“战略问题”和“战术问题”这两类。在这一视角下,“如何动员人们参与到社会运动中来”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运动已经存在了,“诸众”已经自发地集结起来,“诸众”天然就是运动的主体——这是已经被预设的了。
然而,如果跳出那些已经成气候的社会运动,看到更多不成气候的社会运动、想动员却动员不起来的社会运动,就能发现:如何让人们将自身视作社会运动的抗争主体、如何让人们产生政治动员的兴趣和欲望,恰恰是极为关键的、决定运动生死的问题。这个问题,完全超越了“战略”和“战术”的二分法,而触及更根本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