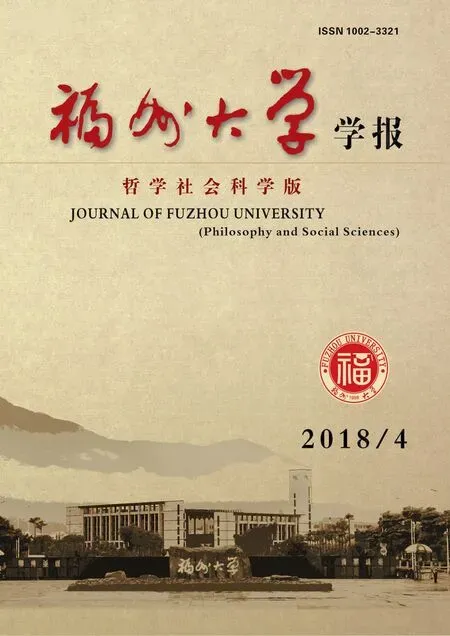欧阳修举荐苏洵的历史背景及其影响
2018-03-31潘殊闲
潘殊闲
(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 四川成都 610039)
三苏父子都应是欧阳修的门下,但一般论者关注苏轼、苏辙较多,而对苏洵与欧阳修的交集关注较少。这当中,对欧阳修举荐苏洵前后的历史背景的梳理尚不充分。本文以此为话题,欲通过对相关材料的钩稽梳理,还原欧阳修举荐苏洵的历史背景及其相关影响。
一、欧阳修之前举荐苏洵的蜀中贤达
苏洵出生于偏于西南一隅的小城眉州眉山县,性格豪宕,年青时未能一心向学。当其仲兄苏涣于天圣二年(1024)进士乙科及第时,15岁的苏洵“犹不知书”。[1]在父亲的督促下,苏洵尝试为应试而读书,学习句读、属对声律这些当时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但天性豪纵的苏洵难以为这些所束缚。这种“不情愿”的学习所带来的直接结果是,苏洵于天圣五年(1027)、宝元元年(1038)、庆历四年(1044)三次应试都铩羽而归。庆历七年(1047),苏洵父亲苏序去世。苏洵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由此开启了十年(1047-1056)闭门求索省思的生活。这时的苏洵,“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粹精,涵畜充溢,抑而不发。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笔,顷刻数千言,其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2]
脱胎换骨之后的苏洵,有强烈的出仕愿望。但再走科举应试之路,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苏洵做不到的。留在苏洵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拜谒达官显宦,以求荐举骤达。田况曾于庆历八年至皇祐二年(1048-1050)知益州,苏洵曾拜见田况,惜未引起田况的注意。苏洵后来在《上田枢密书》中曾追忆这段往事,有“曩者见执事于益州,当时之文,浅狭可笑,饥寒穷困乱其心,而声律记问又从而破坏其体,不足观也”之语。
机会悄然来临。至和元年(1054),张方平出任益州(今成都)太守。治蜀期间,他很注意访求人才。有人告诉他,眉山处士苏洵便是人才。苏洵果然去拜访张方平,张方平很赏识他,欲推举为成都学官。但苏洵对此不满意。于是,苏洵再去拜访雅州知州雷简夫。嘉祐元年(1056)春,苏洵携二子拜访雅州(今四川雅安)知州雷简夫。官职不高的雷简夫慧眼识珠,盛称苏洵有王佐之才,撰书鼎力推荐给当朝名臣张方平、欧阳修和韩琦,并在推荐信中称苏洵为天下奇才,将苏洵视为当代的司马迁。在给欧阳修的信中,雷简夫直言不讳,言辞恳切:“起洵于贫贱之中,简夫不能也,然责之亦不在简夫也。若知洵不以告于人,则简夫为有罪矣。用是不敢固其初心,敢以洵闻左右。恭惟执事职在翰林,以文章忠义为天下师,洵之穷达,宜在执事。向者洵与执事不相闻,则天下不以是责执事,今也读简夫之书,既达于前,而洵又将东见执事于京师,今而后,天下将以洵累执事矣。”[3]这位雷简夫视举荐民间贤能之才给国家为崇高的使命,因此,话语急迫,毫无掩饰。除推荐给欧阳修外,雷简夫还给韩琦和张方平推荐。在给韩琦的信中说:“一日,眉人苏洵携文数篇,不远相访。读其《洪范论》,知有王佐才;《史论》得迁史笔;《权书》十篇,讥时之弊;《审势》《审敌》《审备》三篇,皇皇有忧天下心。”[4]在给张方平的信中说:“简夫近见眉州苏洵著述文字,其间如《洪范论》,真王佐才也。《史论》,真良史才也。岂惟西南之秀,乃天下之奇才尔。令人欲麋珠虀芝,躬执匕箸,饫其腹中,恐他馈伤。且不称其爱护如此,但怪其不以所业投于明公,问其然,后云:‘洵已出张公门下矣。又辱张公荐,欲使代黄柬为郡学官。洵思遂出张公之门,亦不辞矣。’简夫喜其说。窃计明公引洵之意,不只一学官,洵望明公之意,亦不只一学官,第各有所待也。又闻明公之荐,累月不下,朝廷重以例检,执政者靳之,不特达。虽明公重言之,亦恐一上未报,岂可使若人年将五十,迟迟于涂路间邪?昔萧昕荐张镐云:用之则为帝王师,不用则幽谷一叟耳。愿明公荐洵之状,至于再,至于三,俟得其请而后己,庶为洵进用之权也。”[5]雷简夫推荐苏洵之心如此执着、坚定,且无所顾忌地替苏洵解围说话,称学官之职既非苏洵的理想,也非张方平本人的意愿,希望张方平发挥他的作用,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荐苏洵,直到成功为止。
有意思的是,雷简夫也是仁宗皇帝从草野中纳荐出仕的:“仁宗以西戎方炽,叹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收录之。杜丞相衍经抚关中,荐长安布衣雷简夫才器可任,遽命赐对于便殿。简夫辩给,善敷奏,条列西事甚详,仁宗嘉之,即降旨中书,令依真宗召种放事。是时吕许公当国,为上言曰:‘臣观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实效,今遽爵之以美官,异时用有不周,即难于进退,莫若且除一官,徐观其能,果可用,迁擢未晚。’仁宗以为然,遂除耀州幕官。”[6]同有草野经历的雷简夫对尚处在草野的苏洵渴望进达的心情是十分了解的,也是十分同情的,因而,施以援手也最为积极、直率和执着。
张方平虽无草野受拔经历,但对苏洵也十分赏识。他没有不悦雷简夫带有指责性的催逼与干涉,而是跟雷简夫有同样的求贤、荐贤的气度、雅量与胸襟。对此,张方平在《文安先生墓表》中有明白的叙述:
仁宗皇祐中,仆领益部。念蜀异日常有高贤奇士,今独乏耶?或曰:“勿谓蜀无人,蜀有人焉。眉山处士苏洵,其人也。”请问苏君之为人?曰:“苏君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然非为亢者也,为乎蕴而未施,行而未成,我不求诸人,而人莫我知者,故今年四十余不仕。公不礼士,士莫至。公有思见之意,宜来。”久之,苏君果至。即之,穆如也。听其言,知其博物洽闻矣。既而得其所著《权书》《衡论》阅之,如大云之出于山,忽布无方,倏散无余;如大川之滔滔,东至于海源也,委虵其无间断也。因以书先之于欧阳永叔。[7]
张方平、雷简夫均非生于蜀中之人,但到蜀中为官,仰慕蜀中良好的历史文化生态,不约而同地要不拘一格荐拔人才,为蜀中文脉再续新枝。张方平与雷简夫都看好苏洵,而张方平本与欧阳修曾有怨隙,但为了为国家荐选贤才,放弃个人恩怨,完全没有顾忌。《避暑录话》曾有这样的记载:
张安道与欧文忠素不相能。庆历初,杜祁公、韩、富、范四人在朝,欲有所为。文忠为谏官,协佐之,而前日吕申公所用人多不然。于是诸人皆以朋党罢去,而安道继为中丞,颇弹击以前事,二人遂交怨,盖趣操各有主也。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为翰林。苏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将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为重?其欧阳永叔乎?”不以其隙为嫌也。乃为作书办装,使人送之京师谒文忠。文忠得明允所著书,亦不以安道荐之非其类,大喜曰:“后来文章当在此。”即极力推誉,天下于是高此两人。[8]
张方平、欧阳修在荐拔苏洵问题上又高度一致。雷简夫与张方平、张方平与欧阳修,这两组伯乐的高度一致,为苏洵冲出夔门,闯荡京城,铺平了道路,提供了绝好的机缘与条件。
二、欧阳修对苏洵的举荐
苏洵到京城后,欧阳修可谓不遗余力举荐、推荐、引荐,诚如他在《荐布衣苏洵状》中的陈述:
右臣猥以庸虚,叨尘侍从,无所禆补,常愧心颜。窃慕古人荐贤推善之意,以谓为时得士,亦报国之一端。往时自国家下诏书戒时文,讽励学者以近古,盖自天圣迄今二十余年,通经学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胜数。而四海之广,不能无山岩草野之遗,其自重者既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闻,此乃如臣等辈所宜求而上达也。伏见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机策》二十篇,辞辨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为乡闾所称,而守道安贫,不营仕进,苟无荐引,则遂弃于圣时。其所撰书二十篇,臣谨随状上进。伏望圣慈下两制看详,如有可采,乞赐甄录,伏候敕旨。[9]
这篇给仁宗皇帝的举荐状,对苏洵评价甚高。欧阳修首言自己是“慕古人荐贤推善之意”而推荐苏洵的。在欧阳修看来,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因科试不中,“遂退而力学”。这种“力学”的结果就是“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具体到苏洵所献的《权书》《衡论》《机策》二十篇,“辞辨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其人文行久为乡闾所称”之云,显然是指益州守张方平以及雅州知州雷简夫的推荐。这说明,张方平和雷简夫所荐,已完全为欧阳修所接受。这里至少透露出这样的一些信息值得关注:
一是欧阳修能够捐弃与张方平的前嫌,合力举荐布衣苏洵;
二是欧阳修与此前的张方平和雷简夫都表现出惜才、爱才、荐才、识才、用才的智慧、气度与涵养,令人敬仰;
三是欧阳修并不是仅仅因为有张方平等人的推荐,而是通过阅读苏洵所提供的《权书》《衡论》《机策》等二十篇宏文,高度认可了苏洵不为空言,且“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的智识与才能,而这正是欧阳修推行诗文革新所需要的。苏洵庆历四年(1044)进京应试时曾认识了一位叫颜太初(字醇之,号凫绎先生)的人,对其诗文大加评赏,认为“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10]这也确实是苏洵所追求的。当然,这也恰好暗合欧阳修力矫时弊的初衷:“宋初承唐,习文多俪偶,谓之昆体。至欧阳公出,以韩为宗,力振古学。曾南丰、王荆公从而和之,三苏父子又以古文振于西州,旧格遂变,风动景随,海内皆归焉。”[11]
不可否认,欧阳修不仅对苏洵赏识有加,奉为上宾知音,还把苏洵及时介绍给朝廷重臣枢密使韩琦、宰相富弼、文彦博等人。苏洵也借机主动给韩琦、富弼、文彦博等人致信,阐发宏论,寻求理解,加深认识,希冀惠助。在给韩琦的第一封信中,苏洵主要探讨了天下国家大事。在给韩琦的第二封信中则直言请求给予官职:“洵年老无聊,家产破坏,欲从相公乞一官职。非敢望如朝廷所以待贤俊,使之志得道行者;但差胜于今,粗可以养生遗老者耳。”[12]考虑到屡被拒绝的现实,苏洵也以自己醉心于学术相表白,希望韩琦给个准信:“洵少时自处不甚卑,以为遇时得位,当不卤莽。及长,知取士之难,遂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实亦有得而足恃。自去岁以来,始复读《易》,作《易传》百余篇。此书若成,则自有《易》以来,未始有也。今也亦不甚恋恋于一官,如必无可推致之理,亦幸明告之,无使其首鼠不决,欲去而迟迟也。”[13]在给富弼的信中,先阐述了“古之君子,爱其人也则忧其无成”的道理,最后提出自己的愿望:“洵,西蜀之人也,窃有志于今世,愿一见于堂上。伏惟阁下深思之,无忽!”[14]在给文彦博的信中,苏洵主要谈了官吏的管理,最后说:“洵西蜀之人,方不见用于当世,幸又不复以科举为意,是以肆言于其间而可以无嫌。伏惟相公慨然有忧天下之心,征伐四国以安天子,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功遂,文武并济,此其享功业之重而居富贵之极,于其平生之所望无复慊然者,惟其获天下之多士而与之皆乐乎!此可以复动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公亮之!”[15]
此外,苏洵还给枢密副使田况写信,对自己在益州拜见之后的进步有一个总结与评价:“已数年来退居山野,自分永弃,与世俗日疎阔,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诗人之优柔,骚人之精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投之所向,无不如意。常以为董生得圣人之经,其失也流而为迂;晁错得圣人之权,其失也流而为诈;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贾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见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审势》《审敌》,作书十篇曰《权书》。洵有山田一顷,非凶岁可以无饥,力耕而节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与者不忍弃,且不敢亵也。执事之名满天下,天下之士用与不用在执事。故敢以所谓《策》二道、《权书》十篇者为献。平生之文,远不可多致,有《洪范论》《史论》七篇,近以献内翰欧阳公,度执事与之朝夕相从而议天下之事,则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陈于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与其身之可贵与否者,执事事也,执事责也,于洵何有哉!”[16]
时在谏院供职的右正言余靖,苏洵一直没有机会谋面,后来余靖上朝,正好与苏洵相见,遂有后来的致书。苏洵在信中先论述了他心目中的贤人与君子、富贵与贫贱的区别,又以余靖的人生经历为例,最后这样说道:“洵以为明公之习于富贵之荣,而狃于贫贱之辱,其尝之也盖以多矣。是以极言至此而无所迂曲。洵西蜀之匹夫,尝有志于当世,因循不遇,遂至于老。然其尝所欲见者,天下之士盖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见矣,而独明公之未尝见,每以为恨。今明公来朝,而洵适在此,是以不得不见。伏惟加察,幸甚!”[17]
三、欧阳修举荐苏洵的影响
由于有欧阳修的延誉推广,加上苏洵自己的自我宣扬与积极表现,苏洵的文才得到了京城诸公的赏识与礼遇,苏洵遂以一介布衣身份成为京城达官显宦的座上客。《石林诗话》有这样的记载:
苏明允至和间来京师,既为欧阳文忠公所知,其名翕然。韩忠宪诸公皆待以上客。尝遇重阳,忠宪置酒私第,惟文忠与一二执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参其间,都人以为异礼。[18]
这则轶事有苏洵自己的诗为证:“晚岁登门最不才,萧萧华发映金罍。不堪丞相筵东阁,闲伴诸儒老曲台。佳节久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暮归冲雨寒无睡,自把新诗百遍开。”[19]但苏洵是和韩琦的诗,韩琦原诗为《乙巳重九》,乙巳为英宗治平二年(1065),此时的苏洵已不完全是布衣,已有微官加身,所以,叶梦得的“布衣参其间”之说,稍微有点夸大,但从苏洵诗中的落寞之气看来,也有几分神似。
虽然欧阳修力举力荐苏洵,但毕竟还是有不同声音。《石林燕语》曾就此事有这样的记载:“欧阳文忠公初荐苏明允,便欲朝廷不次用之。时富公、韩公当国,虽韩公亦以为当然,独富公持之不可,曰:‘姑少待之。’故止得试衔初等官。明允不甚满意,再除,方得编修《因革礼》。前辈慎重名器。”[20]
的确,除欧阳修力挺苏洵外,其他当政者更多的是赏识苏洵的文、行,未能采纳欧阳修的建议,亦未能合力举荐给朝廷给予苏洵相应的官职,以至苏洵在给韩琦的信中曾发过这样无奈的感慨:“今洵幸为诸公所知似不甚浅,而相公尤为有意。至于一官,则反复迟疑不决者累岁。嗟夫!岂天下之官以洵故冗邪?”[21]
对于苏洵的简短仕履,欧阳修在《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中有准确的“交代”:“初,修为上其书,召试紫微阁,辞不至,遂除试秘书省校书郎。会太常修纂建隆以来礼书,乃以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使食其禄,与陈州项城县令姚辟同修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方奏未报,而君以疾卒。实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22]这段文字透露,刚开初欧阳修的荐举还是有效的,这就是“召试紫微阁”,只是苏洵推辞不去。对此,苏洵在给梅尧臣的信中有自己的解释:“自离京师,行已二年,不意朝廷尚未见遗,以其不肖之文犹有可采者,前月承本州发遣赴阙就试。圣俞自思,仆岂欲试者?惟其平生不能区区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穷困。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万里以就试,不亦为山林之士所轻笑哉?自思少年尝举茂才,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今齿日益老,尚安能使达官贵人复弄其文墨,以穷其所不知邪?且以永叔之言与夫三书之所云,皆世之所见。今千里召仆而试之,盖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进以求其荣利也。”[23]苏洵对科举之试已彻底失望,所以,他绝不就试。在他看来,欧阳修已作了推荐,代他所献的“三书”即《权书》《衡论》《机策》,大家都已看到,如果还要让他去考试才能决断,表明决策者尚有不信任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更不能贸然去追逐荣利。这一点,充分看出苏洵的矜持与刚毅。此事除给梅圣俞写信外,苏洵还给雷简夫写信,表达自己婉辞诏试的内心真实想法:“仆已老矣,固非求仕者,亦非固求不仕者。自以闲居田野之中,鱼稻蔬笋之资,足以养生自乐,俯仰世俗之间,窃观当世之太平;其文章议论,亦可以自足于一世。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权衡,以自取轻笑哉?然此可为太简道,不可与流俗人言也。向者《权书》《衡论》《几策》,皆仆闲居之所为。其间虽多言今世之事,亦不自求出之于世,乃欧阳永叔以为可进而进之。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则何所事试?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仓卒之言,又何足信邪?恐复不信,秖以为笑。”[24]苏洵给雷简夫的回信,说得更加清楚。他作的这些论世之文,本没有炫世的意图,只因为欧阳修觉得可以进奉朝廷,才呈递上去的。如果朝廷觉得所言可信可用,又何必再行考试呢?如果朝廷觉得本人平居沉心静气写出来的文章都不足信,那场屋中仓促写成的文字更何足信?苏洵此话的确在理。
苏洵是一个耿介刚直之人,有话直说,也因此会让当事者不悦。比如,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去世,韩琦为山陵使,要厚葬仁宗,苏洵作《上韩昭文论山陵书》,反对厚葬,建议薄葬。“初作昭陵,凶礼废阙,琦为大礼使,事从其厚,调发辄办,州县骚动。先生以书谏琦且再三,至引华元不臣以责之。琦为变色,然顾大义,为稍省其过甚者。及先生殁,韩亦颇自咎恨,以诗哭之曰:知贤而不早用,愧莫先于余者矣。”[25]苏洵的这种性格,多多少少也阻挡了他擢升的速度与进程。
但凡事需要辩证看。也就是说,看似短暂不起眼的苏洵的仕路人生其实也另有一番风致的。就苏洵本人言,虽然自己的仕路坎坎坷坷,最后也仅谋得文安县主簿这样象征性的不足挂齿的卑职,但与其卑职相对应的是,苏洵在京城乃至全国的影响。因为有当朝文坛政坛重量级人物的奖掖扶持,苏洵早已声名鹊起,正所谓“布衣驰誉入京都”[26],这甚至可以从苏洵治平三年(1066)震惊朝野的溘然长逝中窥探出来。当时为之作挽词的朝野之士多达一百多人,可谓“自天子辅臣至闾巷之士,皆闻而哀之”。[27]不妨来看以下几人所颂之挽词。
韩琦有《苏洵员外挽辞二首》,其一云:“对未延宣室,文尝荐子虚。书方就绵蕝,奠已致生刍。故国悲云栈,英游负石渠。名儒升用晩,厚愧不先予。”其二云:“族本西州望,来为上国光。文章追典诰,议论极皇王。美德惊埋玉,瑰材痛坏梁。时名谁可嗣,父子尽贤良。”[28]对没有及早“升用”苏洵,表示惋惜。好在“父子尽贤良”,也给人希望。
苏颂有《苏明允宗丈二首》,其一云:“观国五千里,成书一百篇。人方期远到,天不与遐年。事业逢知己,文章有象贤。未终三圣传,遗恨掩重泉。”其二云:“尝论平陵系,吾宗代有人。源流知所自,道义更相亲。痛惜才高世,赍咨涕满巾。又知余庆远,二子志经纶。”[29]苏颂以同宗落笔,盛赞“吾宗代有人”。又以《周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为背景,赞美苏轼、苏辙二兄弟“志经纶”。
陈襄有《苏明允府君挽词》:“礼阁仪新奏,延英席久虚。自从掩关卧,无复草玄书。东府先生诔,西山孝子庐。谁言身后事,文止似相如。”[30]陈襄以蜀中昔日名贤为喻,称赞苏洵的才德。
刘攽有《挽苏明允二首》,其一云:“季子才无敌,桓公义有余。空悲武儋石,犹得茂陵书。郢路营魂远,江源气象虚。康成宜有后,正使大门闾。”其二云:“汉仪绵蕝盛,周谥竹书存。益以春秋法,因知皇帝尊。百年当绝笔,诸子谢微言。诗礼终谁及,贤良萃一门。”[31]刘攽夸赞苏洵学力笔力了得,且“贤良萃一门”,后继有人。
郑獬有《哀苏明允》:“丰城宝剑忽飞去,玉匣灵踪自此无。天外已空丹凤穴,世间还得二龙驹。百年飘忽古无奈,万事凋零今已殊。惆怅西州文学老,一丘空掩蜀山隅。”[32]郑獬除叹惋苏洵的仙逝外,更赞美他的身后还留下已经出名的“二龙驹”苏轼、苏辙。
连后来迫害苏轼的王珪当时也写来挽词:“岷峨地僻少人行,一日西来誉满京。白首只知闻道胜,青衫不及到家荣。元猿夜哭铭旌过,紫燕朝飞挽铎迎。天禄校书多分薄,子云那得葬乡城。”[33]王珪的挽词仅提及苏洵的“大器晚成”,只字不提二苏的成长与声誉,确有别于其他人的挽词,从中可以窥见日后妒忌迫害苏轼的“苗头”与“伏笔”。
综观上述诸多人员的论评,可以清晰发现,苏洵进京干谒名公达宦,不仅使自己声名鹊起,更为重要的是,让自己两个风华正茂的儿子苏轼、苏辙能有机会尽早接触到当今政坛与文坛的巨擘宗哲,为二人日后的奋起打下了珍贵的基础。这或许比苏洵本人仕至更高职位意义更大,价值更重。对此,欧阳修、曾巩等众多当事者最有发言权。
如欧阳修评论道:“当至和、嘉祐之间,(苏洵)与其二子轼、辙偕至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得其所著书二十二篇,献诸朝。书既出,而公卿士大夫争传之。其二子举进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学称于世。眉山在西南数千里外,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34]
曾巩也有类似的概述:“嘉祐初,(苏洵)始与其二子轼、辙复去蜀,游京师。今参知政事欧阳公修为翰林学士,得其文而异之,以献于上。既而欧阳公为礼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于是三人之文章盛传于世,得而读之者皆为之惊,或叹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既而明允召试舍人院,不至,特用为秘书省校书郎。顷之,以为覇州文安县主簿,编纂太常礼书。而轼、辙又以贤良方正策入等。于是三人者尤见于当时,而其名益重于天下。”[35]
毋庸讳言,苏洵仕宦的不得意,换来了二个儿子的异军突出,更赢得了“三苏”的文名与口碑。苏洵的幸与不幸,在兹也实赖兹。由此回看欧阳修等人不遗余力的推誉扶持,确为国家发现、培养了三位杰出的文化巨匠,功莫大焉。
注释:
[1][2] [宋]欧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并序》,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卷三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02,902页。
[3][4][5] [宋]邵 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0,118-119,119-120页。
[6] [宋]魏 泰:《东轩笔录》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0页。
[7] [宋]张方平:《乐全集》卷三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清光绪宣统三年(1911)长沙叶氏观古堂校刊本。
[9] [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一十二,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968页.
[10] [宋]苏 轼:《苏轼文集》卷十《凫绎先生诗集叙》,[明]茅 维编、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13页。
[11] [元]刘 埙:《隐居通议》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13] 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52,353页。
[14] 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十一《上富丞相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07-309页。
[15] 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十一《上文丞相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14页。
[16] 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十一《上田枢密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19页。
[17] 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十一《上余青州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24页。
[18] [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清光绪宣统三年(1911)长沙叶氏观古堂校刊本。
[19] 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佚诗《九日和韩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96页。
[20]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五,侯忠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5页。
[21] 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十三《上韩丞相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53页。
[22][34] [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三十五,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513,512页。
[23] 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十三《与梅圣俞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60-361页。
[24] 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十三《答雷太简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62页。
[25] [宋]张方平:《乐全集》卷三十九《文安先生墓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 [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十四《苏主簿洵挽歌》,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35页。
[27][35] [宋]曾 巩:《曾巩集》卷四十一,陈杏珍、晁继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60,560页。
[28] 傅璇琮等:《全宋诗》卷三三八,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122页。
[29] 傅璇琮:《全宋诗》卷五三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432页。
[30] 傅璇琮等:《全宋诗》卷四一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084页。
[31] 傅璇琮等:《全宋诗》卷六○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211页。
[32] 傅璇琮等:《全宋诗》卷五八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875页。
[33] 傅璇琮等:《全宋诗》卷四九五《挽霸州文安县主簿苏明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9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