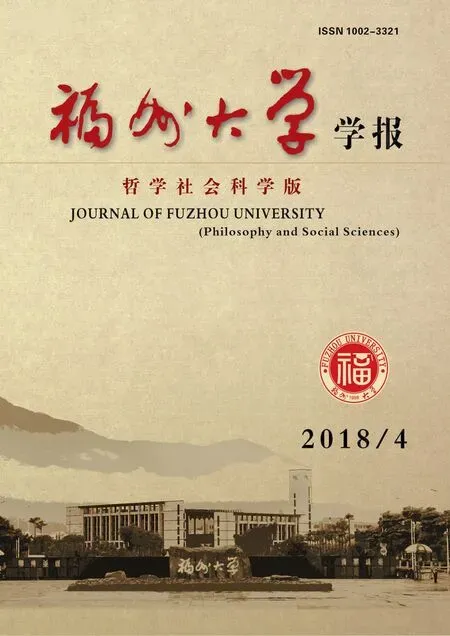欧阳修刘敞嘉祐唱和:京朝官的社交与私交生活
2018-03-31吕肖奂
吕肖奂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所, 四川成都 610064)
刘敞(1019-1068)嘉祐三年(1057)九月外任郓州归来后,与欧阳修(1007-1072)、梅尧臣(1002-1060)等人再次在京师相聚,到嘉祐五年(1059)孟夏梅尧臣去世、年底刘敞离开京师赴永兴军,以三人为中心而开放的小群体燕集唱和,是嘉祐诗坛的一道重要景观。
实际上自从欧阳修至和元年(1054)入京为朝官之后,在他周边就形成了一个唱和圈,其中就包括欧阳修知颍州(1049-1050)时期就参与其唱和的刘敞。刘敞嘉祐元年(1056)离开京师二三年间,欧阳修与梅尧臣、韩维等在京官员诗人继续进行小群体的唱和活动,外任的刘敞与这个小群体保持唱和联系。刘敞回京师任职后,小群体的活动更加频繁,达到高潮。
喜欢“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的欧阳修,具有较强的社交型人格,常常是小群体燕集以及唱和活动的组织者。他习惯同时与多人保持唱和交往,不仅与前辈、同辈唱和,还吸纳更多后辈如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等人,[1]他的唱和圈随着进京离京人员而随机扩大缩小,其中梅尧臣、刘敞因为长期且频繁参与唱和而成为嘉祐唱和圈的中心人物。
一、核心与外围:欧阳修等京朝官诗歌唱和圈的构成及其唱和活动
景祐庆历间就闻名政坛与文坛的欧阳修,其至和嘉祐间在汴京建立的唱和圈,可谓中上层京朝官诗人唱和圈,几乎可以反映这一时期京师乃至整个诗坛唱和概貌。
欧阳修《官舍假日书怀,奉呈子华内翰、长文原甫景仁舍人、圣俞博士》(卷五七),是嘉祐四年岁旦假日时欧阳修“书怀”之后,主动“奉呈”首唱而邀约的诗歌。被邀和的五人中,韩绛(1012-1088)与欧同为翰林学士,吴奎(1011-1068)、刘敞、范镇(1007-1088)同任中书舍人,[2]梅尧臣为太常博士。除梅官职稍低外,唱和的五位均是掌内外制的“清要”朝官。欧、韩、梅、刘是此前就经常唱和的诗友,吴、范则是这一时期因工作关系而新加入唱和圈的诗人,二人虽写诗但不以诗歌见长,存诗也较少。身为官员的欧阳修在诗题中很自然以官职的高低为即将和答者排序。作为年长而位低的梅尧臣,在这个圈子里感到一些压力,也感到一点庆幸,其《次韵和永叔新岁书事见寄》云“幸得从公持直笔,定应无复叹齑盐”,感谢欧阳修举荐他同修唐书,使得他的贫穷生活得以改善。而年少位高的刘敞在重大节日仍旧忙于公务,其《次韵和永叔岁旦对雪见寄,时某于上源驿典护契丹朝正使,人日当归,前一日始得此诗》[3],解释他因朝廷外事活动原因而滞后多日和答。三首唱和表现出京朝官的社会心理以及节假日不同生活。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因工作关系而形成的唱和圈,因而唱和的内容自然与各自从事的工作日程有关。根据刘敞《宿斋中书外省,答永叔京尹内翰朝回马上见寄,并谢子华次韵》以及梅尧臣《次韵和永叔退朝马上见寄,兼呈子华、原甫》[4],可知欧阳修作为翰林学士兼知府的工作尽管十分繁忙,却还有退朝后骑在马上书写日常的心情。欧阳修此次寄赠的诗人只有韩绛、刘敞、梅尧臣,欧首唱以及韩绛次韵均不存,从刘诗“会须一办如泥醉”、梅诗“载酒重思结客欢”可知,欧阳修诗中有因公务过于忙碌而有退朝后邀诸君聚饮消遣之意。升朝与退朝是常参官也即升朝官的特权与荣耀,但经常性的升退需要早起则令其苦不堪言,对于年长体衰的官员而言尤其如此,所以欧阳修及各位官员常有这样的怨叹以及工作之余聚会消遣的要求。这是欧阳修等人邀和式、非聚会唱和,唱和者处于非同一空间,时间也有先后,对各自的工作现状的情绪也各有不同。
欧阳修嘉祐四年于唐书局中置酒为陕州知州祖无择饯行,所谓“西掖门外驻征轩,修书院中倾别酒”(江休复和诗)。据祖无择《龙学文集》卷五保存这次唱和送别的七首次韵诗歌看,除了远行客祖无择外,几位送行者均是欧阳修的“寻常诗酒伴”(吴奎和诗),与该年岁旦唱和的区别是,江休复(1005-1060)代替了韩绛,其余几位都是旧人,祖无择称之为“高冠满坐皆贤豪”。
梅尧臣《次韵和永叔赠别择之赴陕郊》云“自言老大遇知难,愿得公诗为不朽”,补述了此次聚会是欧阳修因祖无择之请而举行的;祖无择诗云“主人名重闻四夷,典册高文推大手。发挥六艺无遗精,考黜百家如拉朽”,也证实了这一点。欧阳修首唱《小饮坐中赠别祖择之赴陕府》云“明日君当千里行,今朝始共一樽酒。岂惟明日难重持,试思此会何尝有。京师九衢十二门,车马煌煌事奔走。花开谁得屡相遇,盏到莫辞频举手”,强调尽管“冠盖满京华”,但大家平时各自忙碌,相聚小饮也不容易。祖无择概云聚会的诸位“谈笑喧呼时各有”,吴奎、江休复(1005-1060)描写更为具体生动:“席间骋辩何快哉,恰似纵丸临坂走。诙谐往往笑绝倒,同异时时瞋掉手。”“高谈扺掌华屋头,赋咏题诗乐难朽。飞觞举白至无算,击楫誓清不殓九。”诸位相聚无拘无束,没有官员的拘谨,只有诗人、友人的豪纵。尽管这种场合中,梅尧臣总有些自卑感:“我惭竹管厕宫悬,纵合律度应亦偶”,江休复也叹息“诸公磊落方具来,顾我衰迟亦何有”。送别诗中,各位官员的精神状态以及自我形象也得以呈现。刘敞《依韵和永叔即席送择之出守陕府》(《公是集》卷一六)对祖无择劝慰且鼓励云“男儿何曾计出处,时运由来有奇偶。莫嫌青云晚着鞭,会取黄金大如斗”,可见刘敞的豪爽之气。
在唐书局这个工作空间举行饯别宴会,属于公私兼顾行为。欧阳修作为唐书局的负责人兼宴会主人,其主导性作用在同道的描述中显现。七位唱和者在诗酒豪放中高谈骋辩间杂诙谐调笑的气氛,应该是欧主办聚会的一贯风格。欧阳修“诗酒歌呼”的爱好并没有因为年高官重而被改变。他首唱的七言歌行送别形式沿袭了景祐庆历崇尚古体奔放的风尚。
欧、梅、刘等人的私家聚会,参加的人物以及格局跟这个官衙聚会也差不多,而气氛更加亲密畅快。譬如嘉祐四年重阳节,梅尧臣“置酒延群公,掇英浮新黄”,主动邀请诸位到他的家里聚会赏花。据梅《九日永叔、长文、原甫、景仁、邻几、持国过饮》,这次参与私家聚会有六人,其中只有韩维(1017-1098)是新出现的诗人,但事实上他在嘉祐初就与欧梅刘多次唱和,也算是唱和旧友。这场赏菊聚会场景在十一月下旬欧阳修《会饮圣俞家有作兼呈原父、景仁、圣从》(卷八)以及梅、刘的次韵唱和中被记忆呈现。
该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六人中的刘、范以及上次未参与聚会的何郯(1005-1073),在欧阳修的率领下拜访梅尧臣:“朝罢二三公,随我如鱼鳞。”(欧阳修《依韵奉酬圣俞二十五兄见赠之作》)这是一场退朝之后偶然兴起便即时命驾的登门拜会。“谁谓四君子,蹈古犹比辰”(梅《十一月二十三日,欧阳永叔、刘原甫、范景仁、何圣徒见访之什》),四位高官像信陵君礼贤下士一样大驾光临寒舍,让官职卑微的梅尧臣深感意外和荣幸。梅尧臣用他善于叙事的诗笔描述了这场私人拜访以及招待过程:“上马后苑门,访我东城堙。为公开蓬户,沽酒焚紫鳞。银杯青石盘,共饮不计廵。薄暮各已醉,欢笑颓冠巾。来既无猜嫌,去亦无疏亲”(同上)。欧阳修的和诗表现了不拘礼数的宾主之欢:“君闻我来喜,置酒留逡廵。不待主人请,自脱头上巾。欢情虽渐鲜,老意益相亲。”(欧阳修《依韵奉酬圣俞二十五兄见赠之作》)官位的高低尊卑差别被长久培养的亲密关系消解。
欧次韵和诗之后,意犹未尽,又作《会饮圣俞家有作,兼呈原父、景仁、圣从》(卷八)云“京师谁家不种花,碧砌朱栏敞华屋。奈何来对两枯株,共坐穷檐何局促。诗翁文字发天葩,岂比青红凡草木。凡草开花数日间,天葩无根长在目。遂令我每饮君家,不觉长瓶卧墙曲”,梅尧臣的诗歌比他家的菊花更吸引欧阳修,让他不能自已,常常大醉于梅家。欧阳修称颂他带去的客人是“坐中年少皆贤豪”,而他自己则是“莫怪我今双鬓秃”。
梅尧臣补叙当时聚饮唱和的过程是“诸公醉思索笔吟,吾儿暗写千毫秃。明日持诗小吏忙,未解宿酲聊和属”(梅尧臣《次韵和永叔饮予家咏枯菊》),五位诗人酒后诗兴大发即兴作诗,梅尧臣的儿子参与记录,第二天由“小吏”持奉各家以便“和属”。范镇、何郯应该也和欧诗而今不存,刘敞、梅尧臣则都次韵和诗。刘敞次欧韵之后意犹未尽,又写一首吟咏梅家枯菊,据梅尧臣《次韵和原甫陪永叔、景仁、圣徒饮余家,题庭中枯菊之什》可知(刘原韵不存)。这种往复回环的多次次韵唱和,将这次私家燕集书写得意义非凡。
此外,欧、梅、刘还积极追和其他诗人诗歌。王安石首唱《明妃曲》,欧阳修有《明妃曲和王介夫作》,梅、刘以及曾巩、司马光等人也有和属;韩绛追和唐李山甫《崇徽公主手痕》,欧阳修有《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韩内翰》,梅、刘、王景彝等也有和诗,多人追和一个诗人,引起京师诗坛轰动。
无论邀约式唱和、主动追和,还是公私聚会式唱和,欧、梅、刘都积极主导或者参与。从唱和频率及私密度上看,他们是京朝官唱和圈的核心。京朝官唱和圈随着官员入京出京及其参与唱和的频率而发生变动,人员并不固定。江邻几、韩维是嘉祐初就与欧梅刘唱和的人物,而吴奎、范镇、何郯是则是唱和新人,他们参加唱和较少,和其他偶尔参与唱和的诗人一样,属于唱和圈的外围。
以欧梅刘为核心的京朝官,工作之外喜欢诗酒,其唱和诗基本不涉及政事、公务或具体事务,主要书写工作之余的欢聚时光,均为工作日常以及私人领域话题。景祐庆历议论争煌煌的主题以及奇险阔大风格基本消失,而开启的是苏轼等人元祐唱和之风。
二、贫贱交与莫逆交:群唱中的私交
欧阳修《依韵奉酬圣俞二十五兄见赠之作》云:“与君结交游,我最先众人。我少既多难,君家常苦贫。”出身卑微与经历坎坷,是欧梅二人三十年交游日益密切之基础,这种交谊使二人关系超过欧与其他人的关系。此外,欧梅年龄相仿,有更多共同语言。而刘敞属于晚辈,比欧阳修小十二岁,比梅尧臣小十六岁,他能与欧、梅经常唱和,应该说得益于他的年少老成。欧阳修《奉送刘赴永兴军》云:“文章惊世知名早,意气论交相得晚。”刘敞庆历六年高中榜眼,不久于皇祐初在颍州丁外艰,适逢欧阳修任颍州知州,欧阳修经常与吕公著等人组织分题分韵竞唱,刘是积极参与者,但因社会身份差距而交情不深,直到嘉祐时期,两人经过长期唱和才成为莫逆之交。
刘敞《送梅圣俞(赴许昌)序》云:“某少圣俞十六岁,然圣俞与我为友,所以从之游常恐不足。”(刘敞《公是集》卷三五)嘉祐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梅尧臣去世,刘敞《同永叔哭圣俞》则回顾两人交往史云:“我家江南再世前,与君通家情有连。见君总角今华颠,于我莫逆好已偏。今也已矣嗟绝弦,泪如翻波正沦涟。”(《公是集》卷一八)刘、梅的交往早于刘欧,三人之间因此得以无障碍交流。刘与欧梅之交可谓忘年交、莫逆交。梅去世后,欧阳修《哭圣俞》送别这位洛阳《七交》的最后一位友人,感叹“三十年间如转眸,屈指十九归山丘”。刘敞称赞欧阳修对待梅尧臣可谓仁至义尽:“翰林文章日月悬,凿石铭德埋九泉。上书立后禄绍先,分宅恤穷祭有田。呜呼岂非天下贤,义不背死而苟焉,念子可以无悁悁。”三人在嘉祐三、四、五年间的关系达到顶峰。
欧阳修嘉祐四年二月下旬因生病而免知开封府,移居城南,有《病告中怀子华、原父》(卷一三),感叹“世味惟存诗淡泊,生涯半为病侵陵”,诗题中将韩绛、刘敞并称。 但很快这个并称就变成刘敞、梅尧臣。欧阳修《有赠余以端溪绿石枕与蕲州竹簟,皆佳物也,余既喜睡而得此二者,不胜其乐,奉呈原父舍人、圣俞直讲》[5]就将刘、梅并称,并在诗中云“一从僦舍居城南,官不坐曹门少客”,将免知府后还能经常造访的梅刘二人视为最不势利最为亲近的朋友。
欧居城南后,与梅、刘私下唱和次数增多,并涉及一些较为私人化的话题。譬如嘉祐四年夏,梅、刘造访欧阳修,观看欧“所抄集近事”(刘敞《同梅二十五饮永叔家观所抄集近事》),如欧自云“简编记遗逸,论议相可否”,梅尧臣《谨赋》云:“自言信手书,字字事有因。往往得遗逸,烜赫见名臣”。欧将私人随手摘录的笔记给梅、刘看,基于对二人的信任。梅尧臣云“是日刘夫子,拍手气益振。重睹太史公,吾徒幸来亲”,与皇祐间观看欧《五代史》稿本时的拘谨不同(刘敞《公是集》卷九《观永叔五代史》),刘敞畅快放松地表达他的观感,但他的诗歌显然比其行为节制,仅云“观书太史氏,全性市门翁”(刘敞《同梅二十五饮永叔家观所抄集近事》),他的诗歌表达一向冷淡而理性甚至枯燥。欧阳修云“君子忽我顾,贫家复何有。虚堂来清风,佳果荐浊酒”,对梅刘的忽然光顾充满欣喜。而梅尧臣描写拜读欧作之后,“大笑举玉杯,陶然任天真。内乐不复热,岂以身为身”,畅饮与畅读一样成为三人消暑的最好活动。此后在小群体之外私下唱和颇多。
欧阳修《夜闻风声有感奉呈原父舍人、圣俞直讲》(卷八)表达出《古诗十九首》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况味:“扰扰贤与愚,流沙逐惊湍。其来固如此,独久知诚难。服食为药误,此言真不刊。但当饮美酒,何必被轻纨。”梅尧臣也能体会到“煎灼一如此,衰枯谁可完。消磨任寒暑,安有不死丹”带来的岁月流逝、人生短暂的无奈(《次韵和永叔夜闻风声有感》)。而年轻的刘敞无法理解已入老境的欧阳修叹老惧亡,对其身居高位却发此感慨有些不解:“夫子文章伯,已在青云端。且方济一世,讵肯哀盘桓”(《公是集》卷九《奉和永叔夜闻风声有感用其韵》)。刘敞的时间意识因与欧梅年龄差距较大而显示出较大差异,这一点拉大他与欧梅在交往深度上的距离。
欧阳修《对雪十韵》,以皇祐时期颍州聚星堂白战体的方式再次挑战诗人的创作能力,而且以十三元的险韵增加难度,刘敞是第二次参加,其《和永叔对雪次韵》(卷二六)“崩腾云将合,飒沓雨师屯。扫去蛟螭乱,堆成虎豹蹲”,不仅超越颍州时期费力生涩的《和永叔喜雪》(《公是集》卷一六),而且比欧阳修“远霭销如洗,愁云晚更屯。儿吟雏凤语,翁坐冻鸱蹲”、梅尧臣的“云衣随处积,水甲等闲屯。团戏为丸转,堆雕作兽蹲”(《次韵和永叔对雪十韵。玉月梨梅柳絮字皆不用》)都更加有气势,表现出后辈超越前辈的努力。公事的艰辛在唱和中发为牢骚,时光流逝的可哀在诗艺的切磋竞技中消解。
欧阳修《寄阁老刘舍人》[6],得到梅、刘和答,因刘的和诗没有次韵,引起欧刘再和,往复唱和至于五首[7]。三人都颇厌倦一春阴雨连绵,而刘敞还有“红药苍苔虽寂寞,多情肯作旧游看”(《奉和永叔雨中见寄》)这种邀欧阳修游观中书省的兴致,欧阳修虽云“得酒虽能陪笑语,老年其实厌追随”,但看到刘的邀约尚有“萧条两鬓霜后草,潋滟十分金卷荷。此物犹能慰衰老,稍晴相约屡相过”情致;梅尧臣却不仅不想骑马上雨后如鹅鸭池般的大街,“锦鞍切莫九衢去,拍拍一如鹅鸭池”(《次韵和永叔雨中寄原甫舍人》),而且连私下来往都无力参加,“浑身酸削懒能出,莫怪与公往还稀”(《和刘原甫复雨寄永叔》),梅尧臣体力精力都明显衰弱不堪。这是三人最后一场唱和,不久梅尧臣去世,欧刘唱和也急剧减少,以欧梅刘为核心的京朝官小群体的唱和基本终结。
欧梅可谓耐久交,欧梅与刘可谓忘年交,三人在嘉祐三至五年,用诗歌唱和展现了京朝官诗人的社交与私交生活以及心理状况、精神状态。社会地位的尊卑影响到欧梅交往心理感受、年龄长幼为刘与欧梅带来一些感觉错位,都呈现在他们对众多话题的唱和之中,仔细比较他们的唱和之作可以感受到三位诗人鲜明的个性以及细致的关系。
景祐庆历的文脉由欧梅在嘉祐亲传给刘敞,但刘敞诗才并不特别突出,加上英年罹病且早逝,未能继承发扬欧梅传统。嘉祐二年登第的苏轼,嘉祐三至五年不在京师,也未能经常参与欧梅刘唱和,却深得欧梅刘嘉祐唱和真传,并将其在神宗哲宗时期发扬光大,形成唱和诗史上最具特色的师友群体唱和圈。
三、太庙中的黄栗留:欧刘唱和的一个隐喻符号
欧阳修与刘敞私下唱和没有群唱多,这意味着两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私交或者秘密。但“黄栗留”意象的反复出现,却似乎成为二人之间较为隐秘的隐喻符号。
嘉祐四年四月九日,欧阳修摄太尉在太庙代皇帝享祭祖宗神灵[8],而刘敞在集禧宫(原会灵观)祭祀五岳帝。太庙与集禧宫相距不远,正如梅尧臣《次韵和永叔原甫致斋集禧》所云“庙饗灵祠属二公,斋心相望切朱宫”。欧、刘两人官阶官职虽不同,却因此次执事相似而在不同宫庙“致斋”,可以同时面对孟夏时节近距离的肃穆宁静而又富丽的皇家风景:“楼台碧瓦辉云日,莲芰清香带水风”(欧《文忠集》卷五七《原甫致斋,余亦摄事后庙,谨呈拙句,兼简圣俞》)、“贝阙碧城相绚烂,石林琪树共参差”(刘《公是集》卷二三《斋宿集禧观戏酬永叔见寄,时永叔在后庙摄事》)。
有意思的是,欧除了与刘敞、梅尧臣这一回合的七律唱和外,还有一首《夏享太庙摄事斋宫闻莺寄原甫》:
四月田家麦穗稠,桑枝生椹鸟啁啾。凤城绿树知多少,何处飞来黄栗留。
与三首律诗不同的是,这首同样作于皇家祖宗神位所在的太庙的绝句,却带有十分浓烈的乡村气息。麦穗、桑葚自非太庙内应有的景致,“黄栗留”的叫声在春末夏初本来常闻,但在太庙这样的清静之地打破宁静,带给斋戒的欧阳修不小的惊喜。欧阳修还专门自注“田家谓麦熟时鸣者为黄栗留”一语出自“诗义”。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卷下注释《诗经·周南·葛覃》之“黄鸟于飞”一语云:“黄鸟,黄鹂鶹也,或谓之黄栗留。幽州人谓之黄莺。或谓之黄鸟。一名仓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黄、一名楚雀。齐人谓之抟黍,关西谓之黄鸟。当葚熟时来在桑间,故里语曰‘黄栗留,看我麦黄葚熟’。亦是应节趋时之鸟。或谓之黄袍。”欧阳修或许是从这个注疏里得到了启发,而将耳闻的叫声历史人文化。
太庙在“凤城”之内,离皇宫不远,欧阳修却写出如此田家风味的场景,这多少有点意外。也许是因为《诗经》注疏出处让他想到博学的刘敞。而刘敞对这首诗的和答似已不存。
黄栗留的鸣叫作为当时实景应该是这首诗创作契机。这首诗歌或许像其他季节风物诗歌一样,在当时可能并没有太深刻的含义。但是后来欧阳修还有几首与刘敞与太庙有关的诗歌不断提及重复黄栗留这个意象,才使这个意象有了一些象征或象喻意味,他似乎有意无意地暗喻或暗示什么。欧阳修的诗歌一向以明白晓畅为主要风格,并不刻意追求暗藏的象征象喻意义,即便是以鸣鸠象喻夫妇如《斑斑林间鸠寄内》与《代鸠妇言》,以啼鸟、百舌象喻谗言如《啼鸟》,意思都很明白显豁。但黄栗留却似乎有些隐蔽的暗示意义。[9]
太庙祭祀,是国家政权象征。[10]《宋史》卷一百七《礼志》云:“宗庙之礼,每岁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则上食荐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其中“四孟时享”是《周礼·大宗伯》以来太庙的最常规祭祀之一,按规定要由皇帝亲自祭祀先祖列宗,但皇帝政务繁忙,一般都委派大臣代行,欧阳修就曾多次代行时享,孟夏的这次就是代行。但嘉祐四年十月,仁宗却要亲自举行孟冬的袷祭(又称袷享、大祀、大合祭),史书记载这实际上是北宋皇帝唯一一次亲行的袷祭。[11]
这次袷祭的预备工作很早就开始进行,其中许多细节问题都曾进行讨论。欧阳修《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云:“是岁天子卜以孟冬祫。既廷告,丞相(富弼)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号。公(知制诰刘敞)上书言:‘尊号非古也。陛下自宝元之郊,止群臣毋得以请,迨今二十年,无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虚名而损实美?’上曰:‘我意亦谓当如此。’遂不允群臣请。而礼官前祫,请祔郭皇后于庙,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别庙者,请毋合食。事下议,议者纷然。公之议曰:‘《春秋》之义,不薨于寝不称夫人,而郭氏以废薨,按景祐之诏,许复其号,而不许其谥与祔。谓宜如诏书。’又曰:‘礼于祫,未毁庙之主皆合食,而无帝后之限。且祖宗以来用之。《传》曰:丧祭从先祖。宜如故。’于是皆如公言。”[12]对于袷祭涉及的两个大问题,刘敞根据儒家经典以及祖宗之法,提出了异于丞相以及礼官的建议,虽被仁宗采纳,却无疑得罪了富弼及礼官。刘敞的异议如同太庙中响起田家的黄栗留,叫声虽然好听却有些不合时宜。《宋史》卷一百七《礼志》云:“嘉祐四年十月,仁宗亲诣太庙,行祫享礼。以宰臣富弼为祫享大礼使,韩琦为礼仪使,枢密使宋庠为仪仗使,参知政事曾公亮为桥道顿递使,枢密副使程戡为鹵簿使。”欧阳修、刘敞在嘉祐四年的孟冬袷祭中可能因为官职不够或者因为议论不合而没有做礼官。
嘉祐五年夏秋间刘敞因袷祭以及其他事情,受到台谏官攻击。欧阳修《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云“公既骤屈廷臣之议,议者已多仄目。既而又论吕溱过轻而责重,与台谏异,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于时矣。”刘敞因此借病告假,欧阳修《闻原甫久在病告有感》(卷五七)云:“东城移疾久离居,安得疑蛇意尽祛。诸老何为谗贾谊,君王犹未识相如。浮沉俗喜随时态,磊落材多与世疏。谁谓文章金马客,翻同憔悴楚三闾。”对“诸老”不容“贾谊”一样的刘敞表示愤慨,对刘敞如屈原一样的处境表示同情,其态度十分显豁。刘敞在此期间曾拜访欧家,正值欧阳修弹琴,刘听后写诗(诗不存),欧阳修《奉答原甫见过宠示之作》云:“紫微阁老适我过,爱我指下声泠然。戏君此是伯牙曲,自古常叹知音难。君虽不能琴,能得琴意斯为贤。自非乐道甘寂寞,谁肯顾我相留连。兴阑束带索马去,却锁尘匣包青毡。”(卷八)认为刘敞是难得的知音同道,刘走后他即将琴束之高阁。
可能在嘉祐五年七月,欧阳修代行孟秋时享,再次到太庙斋宫,作《斋宫感事寄原甫学士》(外集卷七)云:“曾向斋宫咏麦秋,绿阴佳树覆墙头。重来满地新霜叶,却忆初闻黄栗留。”[13]时过境迁,春末夏初标志黄栗留与绿荫已经不见踪影,欧阳修感慨万千。黄栗留的声音虽然清脆,却不够和谐。刘敞《和永叔宿斋太庙闻莺二韵》云:“碧树凋零满眼秋,黄鹂飞去使人愁。翰林仙老斋房客,犹恨人间岁月流。”(《公是集》卷二九)体味到欧阳修对时光流逝的那样喟叹。黄栗留再次出现在欧阳修的太庙诗中,而且还得到刘敞的应和,无疑有了一些象征意义。
嘉祐五年,“公知不容于时矣。会永兴阙守,因自请行。即拜翰林侍读学士充永兴军路安抚使兼知永兴军府”(欧阳修《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刘敞得到永兴军任命,即将离开京师,应邀到欧家做客,“醉翁手种菊,呼我宴西斋”(刘敞《九月八日晩会永叔西斋》)。刘敞因不被见容于朝而满心不快,“念离还作恶,处世亦安排。苍鬓聊相对,青云岂易阶。毋容烛见跋,能尽酒如淮。少作三年别,人生定鲜谐”,青云无路,别情黯然,边郡三年的偏僻艰辛定不出所料。而欧阳修虽然觉得有些依依不舍,“念君将舍我,车马去有期”,却认为刘敞此去是自我选择是逃离京师的牢笼,一定会十分快意:“君行一何乐,我意独不怡。飞兔不恋群,奔风谁能追”。且感叹他自己不能像刘敞那样离开京师,只能“老骥但伏枥,壮心良可悲”。
在正式送别刘敞的《奉送原甫侍读出守永兴(一作奉送永兴安抚刘侍读)》(卷八),欧阳修再次表达两人因年龄差距而有精力与精神上的区别:“爱君尚少力方豪,嗟我久衰欢渐鲜。”刘敞年富力强,此前官运亨通,此番受到打击后有些闷闷不乐。欧阳修赠给刘敞酒盏和笔,希望刘敞不要气馁,鼓励刘敞继续努力,继续饮酒赋诗,在永兴军愉快潇洒生活。
刘敞嘉祐五年十二月底到永兴军,此后跟欧阳修主要是书信联系,也寄给欧阳修不少金石拓片。[14]刘敞《九日龙华阁寄永叔》(卷二三)自注云“永叔有书见忆”,应该是现存最后一首寄给欧阳修的诗歌:
黄花欲落晓霜浓,极目秦川一望中。节物还如去年好,欢游不与故人同。接篱自恣风前落,羽檄宁妨席上通(是日得秦州檄调兵备边)。还畏简书归未得,寄诗黄阁付征鸿。
此诗可能写于嘉祐六年重阳节。去年的重阳节,刘尚在欧家宴饮,今年却东西相隔,且因为畏惧谗言而无法回到京师。
据欧阳修《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及居永兴岁余,遂以疾闻”,则刘敞“惊眩疾”在嘉祐七年已经发作。欧阳修此年曾为刘敞还朝而请命(见刘攽《彭城集》卷三五《刘公行状》)。
尽管刘敞于嘉祐八年“八月,召还,判三班院太常寺”(欧阳修《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但其身体状况一直不佳。[15]治平元年初春,欧为参知政事,再次到太庙代行孟春时享,作《斋宫尚有残雪,思作学士时摄事于此,尝有闻莺诗寄原父,因而有感四首》其一云:“雪压枯条脉未抽,春寒憀栗作春愁。却思绿叶清阴下,来此曾闻黄栗留。”(卷一三)即便初春到太庙,欧阳修都会忆及孟夏的那一声黄栗留鸣叫,而感叹岁月流逝,刘敞虽在京师却如黄栗留一样一去无踪,欧阳修只有借酒浇愁:“兴味不衰惟此(指酒)尔,其余万事一牛毛”。这是刘敞最后一次出现在欧阳修的诗歌中。此后,刘敞沉疴缠身,几乎无法正常生活工作,直到熙宁元年(1068)四月八日去世,而欧阳修这段时间忙于濮议之争、不久受到帷簿之谤外任,欧刘几乎没有唱和。
黄栗留成为刘敞的象征符号,在春末夏初歌唱然后消失,而刘敞正像黄栗留一样,在人生的盛夏到来之前就患病喑哑、英年早逝。
作为社交型诗人,欧阳修的唱和圈人员众多且一直都处于变动之中。他一生有很多的唱和对象,其中梅尧臣无疑是最长久、最固定的,而刘敞只是欧皇祐到嘉祐十多年间唱和比较频繁的对象,而且欧刘唱和多数在多人互动的语境中,其社交唱和多于私交唱和,因此无法将他们的唱和关系绝对孤立起来来分析。只有将其还原到欧这一时期的唱和圈中来考察,才能了解群体互动语境中的欧刘关系,了解京师乃至整个诗坛官员唱和概貌。
注释:
[1] 详参吕肖奂:《宋代唱和诗的深层语境与创变诗思——以北宋两次白兔唱和为例》,《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吕肖奂:《创新与引领:宋代诗人对器物文化的贡献——以砚屏的产生与风行为例》,《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吕肖奂:《宋代同题唱和诗的文化意蕴——以一次有关琵琶演奏的小型唱和为例》,《焦作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2] 欧阳修《暮春书事呈四舍人》所说的另一舍人是何郯。另外,范镇也同修《唐书》。本文所引欧阳修诗文主要出自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忠集》以及中国书店1986影印版《欧阳修全集》。判定写作时间时参考刘德清、顾宝林:《欧阳修诗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下文不一一注出。
[3] 《公是集》卷二三,从次韵可以推断是和答。刘敞:《公是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 据刘诗题所云“京尹内翰”,欧嘉祐三年六月权知开封府(司马光、钱公辅为僚属),嘉祐四年二月初因病免。因此刘德清《欧阳修纪年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19页将刘诗系在嘉祐四年初,准确。但该书第310页根据朱东润校注《梅尧臣诗编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而将欧诗、梅诗均系在嘉祐三年,似不妥。因梅诗与刘诗用韵(班鞍寒欢乾)完全相同。本文所引梅尧臣诗歌出自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宛陵集》以及《梅尧臣诗编年校注》。
[5] 《居士集》卷八。梅尧臣《次韵和永叔石枕与笛(蕲)竹簟》。王安石有和诗。刘敞和诗不存。
[6] 《居士集》卷一三。据梅尧臣《次韵和永叔雨中寄原甫舍人》次韵韵脚(衰时池),可知此首为首唱,即刘敞《公是集》卷二五《奉和永叔雨中见寄》所云的“雨中见寄”,诗中有“风雨闭门桃李时……明朝雨止花应在”。
[7] 可能有六首,据梅《和刘原甫复雨寄永叔》,刘尚有“复雨诗”,今未见。
[8] 详参胡柯《欧阳文忠公年谱》以及刘德清《欧阳修纪年录》。
[9] 与欧刘有唱和的韩维,其《锄园寄京师友人》:“荷锄中园立,飞雨洒清朝。黄鹂何处来,百啭绕林梢。感彼求友声,慨然念吾交。”其《莺二首》:“春风揺动叶阴低,上下林间弄暖晖。似惜清音知者少,孤吟不尽又惊飞。”“鸣声清滑簧温暖,毛羽鲜明金莹磨。剩拟墙边栽绿柳,好来相伴日吟哦。”这些诗歌都沿用《诗经·小雅·伐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以黄鹂意味着友人与知音。
[10] 郝宇变:《北宋宗庙祭祀制度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07年。
[11] 根据郝宇变《北宋宗庙祭祀制度的研究》第31页列表(据《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等资料),北宋皇帝亲郊朝庙、明堂朝庙、告谢太庙次数较多,但袷祭只有一次。
[12] 欧阳修《文忠集》卷三五。欧阳修对后一个问题也提出看法。《宋史》卷一百七《礼志》:学士欧阳修等曰:“古者宗庙之制,皆一帝一后,后世有以子贵者,始著并祔之文。其不当祔者,则有别庙之祭。本朝禘祫,乃以别庙之后列于配后之下,非惟于古无文,于今又四不可。”
[13] 刘德清、顾宝林:《欧阳修诗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692页。据文献中太庙享祭记载,认为此诗当写于嘉祐七年九月六日。但太庙常规享祭,史书并不每次都记载。加上嘉祐七年刘敞在永兴军且身体堪忧,似不能有后二首的和诗。又欧诗题中称刘为学士,刘嘉祐五年任翰林学士,九月以翰林侍读学士知永兴军。刘敞《和永叔宿斋太庙闻莺二韵》称欧阳修为“翰林仙老”,欧自嘉祐六年闰八月升任参政,所以不会是嘉祐七年。而可能是嘉祐四、五、六年的孟秋七月。
[14] 据《集古录》记载。陈湘琳《欧阳修私人书简中的交游》“欧阳修与刘敞”考证刘晚年生病,可能是老年痴呆症,不能唱和。陈湘琳:《欧阳修私人书简中的交游》,《新宋学》第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43-246页。
[15] 欧阳修《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及侍英宗讲读,不专章句解诂,而指事据经因以讽谏,每见听纳,故尤奇其材。已而复得惊眩疾,告满百日,求便郡。”(刘攽《彭城集》卷三五《刘公行状》云其得惊眩疾为治平元年之四月)。欧刘文字关系持续到熙宁元年刘去世后,欧为之写墓志铭,但其书信往来以及诗歌唱和在嘉祐七、八年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