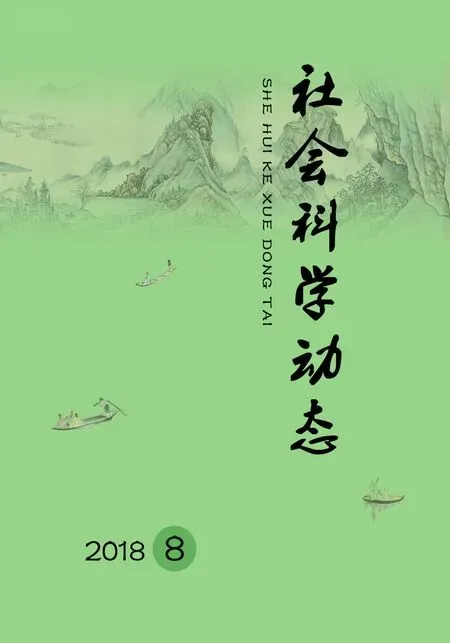社区治理改革的现实困境、关键要素与模式
——以第二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为考察对象
2018-03-31张继军陈蓉蓉
张继军 陈蓉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明确提出了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等改革任务,形成了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到社区治理一体贯通、一脉相承的治理体系,为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全国各地区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求,按照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框架指引,加快了治理方式的转变,积极推动社区建设和发展从政府单一主体向政府、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多元主体转变,从政府管理、控制社会向政府调控、引导、服务和整合社会转变,逐步构建起政府、社区居民、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
一、社区治理改革的现实困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层制治理由于 “狭隘的服务视野、政策目标与手段相互冲突、资源运作重复浪费、政府机构设置出现重叠、公共服务分布于各部门间,具有明显的分散性和不连贯性”①。此外,政府部门为追求自我权利的扩张,较少考虑政府和政策的整体目标,特别是面对棘手问题,容易出现执行工具相互冲突或隔阂状态,此时部门间就会呈现出碎片化状态②,进一步强化了部门主义、各自为政、管理分割、服务裂解等各种弊端。西方国家政府通过重塑公共部门协调和整合机制的改革,有效地应对了公共服务分散化和碎片化的治理困境。从我国社区治理的改革实践来看,社区治理和服务过程中呈现出两个结构性碎片化,即政府部门之间隔离产生的政府碎片化,以及因政府碎片化而生成的社区碎片化。换句话说,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碎片化具有特殊性,其根源在于政府碎片化,社区碎片化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也有着深层次的影响。因而,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改革实践过程中会存在若干困境。
政府碎片化。传统公共行政由于过度强调政府内部职责分工、层级节制和内部管制,造成了组织流程的分割,导致了部门间缺乏协调和 “本位主义”的盛行。以管理主义和市场化为革新理念的新公共管理则囿于单一政策或单一部门的成本效益分析,形成了部门利益的局限而忽略了部门之间的相关性和政策之间的整体性。③政府碎片化,也就是政府部门之间的隔离、不协调、不合作的状态,我国的各级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可认为是呈现碎片化(Authority Fragmented)的部门权威体系。这种部门权威体系造成了政府碎片化,表现为:官僚体系下的分工不合理或者过分专业化,缺乏部门协调,促使职能分工带来政府碎片化;部门主义下普遍存在信息孤岛、数据割裂,部门利益强化了政府碎片化;权力关系下的协调按照部门强势与弱势建立起来,部门协作不可持续,权力关系固化了政府碎片化;软预算约束下,每个部门希望多管事、多资源,造成职能膨胀和部门主义的加剧。④
社区碎片化。我国社区碎片化有其特殊性,论其根源,在于政府碎片化。条块分割,政府部门奉行部门利益至上的原则,各自为政,致使延伸到社区的资源、信息、服务呈现碎片化。加之社区在“只唯上、不看下”的导向下,生产虚假需求或扭曲真实需求,忽略了居民的真实需求,造成社会问题社区化,即 “生病的是政府,却总是由社区来看病”。在社区治理中,社区居委会、公共服务站、社区社会组织、辖区单位等主体间呈现一定程度的权责碎片化、权责冲突、协调乏力。与此同时,社区治理资源也呈现碎片化,这进一步加剧了社区治理效能的低下,造成社区居民的真实需求得不到有效回应。
政府碎片化、公共管理奉行部门主义、 “行政缝隙”的存在等因素导致了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效果不佳,进而扩大了服务缝隙、降低了服务效率、损害了服务公平。从功能上看,政府碎片化和社区碎片化在社区治理和服务过程中产生了四个低效,即公共管理低效、公共服务低效、居民自治低效和社会参与低效。
公共管理低效。治理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单打独斗,使得它们缺乏协调沟通、相互争夺地盘,公共管理效能自然不高。加之政府部门存在 “专业化—部门化—利益化—制度化”的路径依赖,使公共管理陷入 “高成本、低效率”的困境,部门管理也产生大量 “缝隙”。同时,对具有竞争性质的公共部门进行垄断,必然意味着对竞争的排斥和限制。正如公共选择理论所言,公共部门的垄断特性免除了部门外部竞争的压力,也免除了提高公共管理质量和效能的内在动力。公众监督参与主体和渠道的缺失,致使公共部门得不到有效监督,加剧了公共管理低效。
公共服务低效。碎片化治理存在着互相冲突和重复的项目,导致资源浪费并使服务使用者感到沮丧,在对需要作出反应时各自为政,公众无法得到服务,公共服务残缺,公共服务效能自然低下。在我国社区治理的具体实践中,专业部门的建设职能相比于服务职能被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即存在着“重建设、轻服务”的治理倾向。此外,社区治理实践中社会组织所能发挥的作用被忽视,导致公共服务提供和公民需求的背离,即政府提供的不是居民需要的,居民需要的政府却没有提供。
居民自治低效。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认为,“民主必须始于公民的家园,而这个家园就是我们生活的邻里社区。它们永远是培养民众精神的首要组织”⑤。何肇发认为,社区是区域性的社会,就是人们凭感官就能感觉到的具体化了的社会。⑥社区治理不仅是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更是社会治理的起点。在我国社区治理实践中,居民的参与意识并未显著提高,依旧会出现社区参与 “专业户化”的困境,即参与社区治理的都是 “老面孔”和“常客”, “陌生面孔”相对较少。可以认为,在我国社区治理中,居民自治能力低,居民自治水平低,居民自治低效。要提升居民参与,关键在于政府向社区赋权、社区向居民赋权,将个人利益嵌入社区公共利益,使社区成为真正的居民利益共同体。赋予社区居民自主权,其实质就是赋予和激活社区居民自治权,发挥社区居民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社会参与低效。在政府主导型的社会管理体制下,政府是 “包打天下”的全能管家。这一方面使基层社会对政府产生了依赖,另一方面又造成了政府对基层社会的主导、控制和强压。⑦由于历史因素,在 “政府强、社会弱”格局下,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近年来,各种社会力量不断壮大,但其社会参与能力不足、参与意愿不强、参与责任不够,社会参与自然低效。在社区治理中,社区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资源相对有限,政府也是有限政府,其投入社区治理的资源远不能满足社区居民的多样化需要。因而,在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需要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积极培育社会力量,释放更多社会空间,并通过赋权增能,增强社会力量参与能力,扩大社会组织参与范围。
二、社区治理改革的关键要素
革新理念:多元参与、跨界合作。跨界合作强调政府部门、私人部门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和相互依赖的关系,跨界合作在结构上有效地克服了以往公共服务提供分散化和碎片化困境。⑧不同领域部门的功能整合是跨界合作的本质,不同领域机构的伙伴关系是跨界合作的基本工具。⑨实验区革新理念,从包揽理念转向多元参与,从部门垄断转向跨界合作,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力度,从对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界定出发,理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政府简政放权给社区松绑,采用有利于合作的新型政策工具,如服务外包、服务购买、定向采购、项目补贴等,以提升社区治理和服务效能。⑩首先,跨越政府与市场领域边界的合作,将行动者锁定在共同目标下一起行动产生增值效益。广东省广州市罗湖区引入顺丰快递公司,开展社区服务,包括社区公益服务如就业、特殊群体免费邮递、政策宣传等。信息技术则为跨界合作提供了技术支撑。上海市徐汇区推出 “生活服务云”,构建便民服务、志愿服务、公益服务和专业服务的综合服务体系,组建线下服务供应商资源数据库,引入服务供应商600余家。其次,跨越政府与社会领域的边界合作,赋权社会,发挥社会的专业性、主体性功能。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启动社区公共服务外包试点,将公共服务整体打包,采取定向购买、公开竞标等方式交由民办专业社工机构承接,调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的积极性,促进公共服务社会化。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通过与 “NPI”上海屋里厢社区服务中心合作、引入“嘉兴市孝慈为老服务中心”社会组织,提供技术支持,培育本土专业机构 “新塍镇家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为居民提供专业化、个性化服务。最后,跨越政府、社会与市场的边界,通力合作,走向多赢。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促进政社合作;通过项目推介,引导企业向社会组织提供资源扶持;通过定向采购,引导高校专业机构为社工开展专业培训;通过社区与社会组织对接会和社区项目定制会,促进社 (社区)社 (社会组织)合作。
大部制改革:优化政府协调。跨越政府部门边界的合作,通过政府部门间系统协调和有效协作摆脱因刚性行政环境而出现的碎片化,打造 “无缝隙政府”、 “整体性政府”。各实验区都把推进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纳入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普遍建立了领导协调机构,明确了相关部门职责,形成了党委政府领导、部门密切配合、层层抓好落实的工作机制。⑪为解决政府部门协调问题,改变以往部门各自为政,政府组织走向大部制,进行组织分割和区域隔离,采用 “部门+”战略。第一种“部门+”行动,即在部门职责不变情况下,分大类建立一个协调机构来协调大类中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成立民政工作委员会,理顺职能关系、完善社区多元治理,统筹社区建设资金、基础设施建设、社区民生服务。具体机构不减,职责不变,但由民政工作委员会来统筹、协调,具体包括统一规划、统一资源配备、统一考核等。第二种 “部门+”行动,即机构合并,通过职能整合,机构合并建立大部制。如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建立社会事业局,这个部门由社会事业当中的七八个部门整合而来,包括民政事业、残疾人事业、养老事业、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等。第三种“部门+”行动,即根据政府权力运行流程再造部门,再造运作机制。上海市浦东新区在区级层面建立多层次的横向协调机构,促进条块结合。在区内成立区工作委员会,加强区级部门横向协调,实行大联动机制,解决街道乡镇面临的多头管理问题。在社区层面建立社区委员会,将其作为社区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加强与机构企事业单位的协商共治机制。
“社会组织+”:结构性变化。共同体需要社会组织才能够生成,我们要建立的社区社会共同体,没有社区社会组织这个共同体是无法生成的。基于此,政府采取 “社会组织+”行动,一方面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另一方面培育本土草根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具体做法一种是实施嵌入式三社联动,即由公益创投牵引的 “社区+机构社工+专业社会组织”的互动过程,也就是政府向社区外的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由专业社会组织向社区居民提供专业化、个性化服务的过程。例如,广东省深圳市坪山新区、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设立粤港澳合作社区服务项目,引入香港和澳门社工机构开展专业化服务,并培育本土专业社工机构。政府直接供给服务无法调动居民参与,就交给社会组织供给服务,但是,这更像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更像是另一种控制,而不是协调。⑫另一种是实施内生式三社联动,即由公益创投牵引的 “社区+内生社工+内生社团”的互动过程,也就是政府向社区居民委员会赋权,对社区居委会成员进行专业社会工作技术与方法培训,内生社区社工,内生社区社会组织。例如,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以 “院落+社团”为实验主体,细化居民自治单元,构筑多元治理模式:一种是 “老旧小区专委会+院委会”合作自治模式,二种是 “拆迁社区 (村改居社区)专委会+院委会+监事会”合作自治模式,三种是 “涉农社区居委会+集体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连心驿站+物管单位+区域协商共治联合会”合作自治模式,四种是 “企业社区政府+企业”合作自治模式,五种是“新建小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开发商”合作自治模式。
“硬技术+”:建构智慧社区。硬技术伴随硬科学发展而发展,是以物的 (物理的、机械的、化学的)属性来发挥其作用,具有使用性、反复性较低,成本较高的特质。 “硬技术+”,也可以称为“互联网+社区行动”,互联网具有业务整合、职能整合、信息互换、过程公开、资源整合、精简流程和结果透明等优势,可极大提升公共管理效能和公共服务效能。各实验区利用信息技术,实施 “互联网+”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便民利民服务、志愿服务等行动,实现了业务归并、信息交换、资源共享、流程精简,有效地促进了部门协作,减轻了社区负担,增强了社区管理和服务效能。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社区公众微信号、社区QQ群,实际上互联网还结合了物联网,包括数字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第一,构建智慧社区,使社区公共服务智能化。例如,上海市徐汇区建设社区治理服务云平台,即 “政务服务云”、 “管理服务云”和 “生活服务云”,通过 “云”技术和制度创新实现社区居委会事务、社区事务、部门事务的分流和分类治理。第二,建构 “互联网+成熟市场组织”,优化社区服务。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与常州本地 “互联网+”——“淘常州”合作,建立“O2O”社区服务点,打造智慧生活公共服务平台。重庆市渝中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实施 “互联网+养老服务”行动,建立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和网上养老院,引导专业机构加盟,实现养老服务需求与养老服务供给有效对接。第三,借助信息技术,实现资源交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建立社区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 “一次采集、多次应用”的大数据平台,GIS技术集成社区人、事、地、物、组织等基础信息,实现信息交换和资源共享。
“软技术+”:提升居民参与。软技术是随着软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是指人类用于组织、管理、协调、统驭社会实践活动的各方面关系的方法和手段。⑬“硬技术+”有助于提升服务效能和效率,但解决不了居民参与的问题。 “软技术+”就是依托社会工作技术,提升社区居民参与,培育居民自治能力的过程。 “软技术+”的具体做法包括:一是“开放空间会议+”技术,赋权社区居民。它是一种可以把诸如多方利益主体、技术、物品、事件等要素串起来,使这些要素发生协同效应,赋权居民,提升居民参与水平,使居民思维和行为发生改变的软技术。湖北省黄石市政府重视社区居委会的专业化建设,引入专业机构加强社区居委会社会工作实务能力训练,开展黄石市公益创投大赛,通过项目扶持,鼓励社区居委会成员用专业方法引导居民开展自治活动。二是 “参与式技术+”,赋权社区居委会。北京市东城区加强社区居委会的专业技术培训,实施参与式治理能力、参与式会议主持人技术应用与实践、社会工作人才专业督导等专题培训项目,提高社区居委会的专业能力。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搭建能力建设平台,开展参与式培训、专题沙龙工作坊,提升社区居委会专业能力水平。
创新制度:推进配套工程。制度创新是指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而对现行制度进行变革的种种措施与政策。社区治理制度创新则是指根据社区发展的主客观情况,运用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建立健全解决社区问题的配套制度的实践过程,达致弥合制度缝隙,发挥整体制度公平、高效、科学的结果。解决制度壁垒问题,制度间的配套化和体系化是关键,很多实验区探索完善配套制度来保障社区治理实验能够顺利进展。例如,上海市出台社区治理 “1+6”文件,在此基础上,上海市浦东新区结合区域实际出台 “1+20”配套文件,从街镇治理体制改革、居村治理体系建设、加强基层队伍建设、提高基层治理合力、完善基层治理保障等多个方面进行制度安排。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下发文件,规定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注册资金由 “实缴制”转变为 “认缴制”,同时建立社会工作发布机制,发布居民自治解决方案和案例,引导居民自治,提升居民自治水平。
“公共资源+”:撬动社会资源。社区治理是资源共享、利益互动的过程。地方政府需要依托职能部门,利用行政机制,整合财政资源;依托社区组织和草根组织,利用自愿捐资机制,整合社区资源;依托辖区单位,利用共建机制,整合单位资源。⑭社区治理过程也是资源整合的过程,前期需要依靠政府财政资金启动,如政府倡导的公益项目创投、政府定向采购、种子基金等,后期需要依靠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吸纳社会力量和社会资金参与社区治理。⑮“公共资源+”的具体做法一是实施企业和社区合作,链接社会资源。政府提供系列治理工具整合社会资源来推动社区公益事业建设和公益服务发展,以政社合作、政企合作模式,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实验区的建设。例如,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搭建资源整合平台,实施政社合作购买服务、企社合作资源扶持以及公益推荐、公益洽谈。二是发展社区基金会,挖掘本土资源。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以基金会形式为社区提供资金支持,探索社区发展基金会。新塍镇联合发展商会互助资金会与禾城农商银行合作推出 “禾城续贷通”金融产品,募集社会资金、整合社会资源,支持社区及社会力量创办各类公益服务项目,实现了公益资金来源渠道由政府主导到社会力量主导的转变。
三、社区治理改革的模式
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告诉我们,在考察社会历史问题时,不能仅仅从一国的视野来考虑,必须同时具有 “世界历史”的眼光。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社区治理的过程中,要自觉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潮流,以此来审视和进行我们的工作。纵观中西方社区治理历程,存在诸多社区治理模式的讨论,但是已经达成基本共识。西方发达国家社区治理可分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政府与社区行为紧密结合,政府对社区进行较为直接和具体的干预,政府行政力量对社区治理的影响和控制力较强的政府主导型模式。第二种是政府部门人员与地方其他社团代表共同组成社区治理机构,或由政府相关部门对社区工作和社区治理进行规划、指导,并拨给相应经费的混合型模式。第三种是政府与社区相对分离,政府对社区的干预以间接方式为主,其主要是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法规去约束主体行为,协调社区利益关系,提供居民参与的制度保障,社区内治理事务则完全实行自主与自治的自治型模式。就我国社区治理而言,学术界普遍认为存在三种模式: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自治型社区治理模式和合作型社区治理模式。但是,从第二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实践考察来看,我国社区治理不完全是行政安排型治理模式,也不完全是自主型治理模式,而是多元组合型治理模式。
行政安排型模式中,在政府主导的 “沙漏型”治理结构下,社区居民成为社区服务的 “被动接受者”,政府组织俨然成为全能主义的 “管家婆”,社区组织沦为其随意驱使的 “奴婢”,社区治理陷入“劣治”。纵观历史长河,国家性 (单一主体性)遮蔽公共性 (多元主体性)是中国乃至东方社会缺失经典意义社区的根本原因。⑯行政安排型中,政府是管理、控制,而不是服务、赋权;社区被动接受、被组织,而不是主动接受、主动参与。但从世界社区治理的经验和中国社区治理的未来趋势来看,社区治理就是要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跨界合作。在自主组织型中,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认为社会是自然形成的。埃莉诺·埃斯特罗姆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自组织处理公用资源,规避悲剧,不陷入 “公地悲剧”,即可以通过自组织解决困境。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人类是有自治能力的。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中, “皇权不下乡”,国家权力未能渗入底层社会,乡村依靠宗法伦理维持治理,国家干预程度较低,于是便形成乡贤治理基层社会的格局。社区治理的自组织意味着自我管理的网络,意味着政府的间接调控。社区自治组织是社区治理的自治者,政府是社区治理的原治者。在多元组合型模式中,学界逐步中和了 “国家政权建设论”和 “社会共同体论”两种理论视角,目前更多地强调 “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官方也逐渐使用“社区治理”替代过往 “社区建设”的话语。相应地,社区研究也突破了以往 “国家无涉”的传统,国家 “元治理”的作用被重新审视,社区治理被置于 “国家与社会合作”的视野中来。⑰在我国社区治理中,国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决定权力分散或下放多寡的功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不断发展,将成为进一步推动国家权力下放的稳定动力。⑱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认为,可能不会出现一个完全自治的社区治理模式,或一个传统的行政权力治理模式,而是行政权力和自治权力相互作用,继续推动社区治理体制的转变。⑲在这种环境之下,多元参与主体的角色也会随之发生调适和变化。国家转变为扶持者 (supporter),提供包括政策、资金、设施、资源、能力建设上的扶持,这一调适在于国家与居民在自治、自组织上理解达成共识,彼此之间获得信任。社区居委会转变为引导者 (guider),社区居委会自治不再替代居民自治,形式上改变,实质上也发生变化。社会服务机构转变为陪伴者 (accompany),伴随社区发展,服务社区居民、培养社区公民、唤醒或挖掘社区居民的主体性。社会力量作为辅助者 (subsidiary),助力社区治理服务和发展,满足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总而言之,基层社会治理和发展既不完全是社会自组织的过程,也不完全是国家建构的过程,而是命令式安排、个体自由选择、社群协商民主等多元方式组合运行的过程。
注释:
①⑧ 唐任伍、赵国钦: 《公共服务跨界合作:碎片化服务的整合》, 《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8期。
② 尹浩: 《碎片化社区的多维整合机制研究》, 《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5期。
③ 唐兴盛: 《政府 “碎片化”:问题、根源与治理路径》,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④ 孔娜娜: 《社区公共服务碎片化的整体性治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⑤白志武:《传统社区治理模式机制创新探析——以顺德社区治理改革为例》,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⑥ 黎熙元主编、何肇发副主编: 《现代社区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⑦ 夏建中: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33—134页。
⑨曾维和:《整合性公共服务——当代西方国家公共服务提供的新模式》,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⑩ 中共金华市委政法委员会课题组: 《困境与突破:金华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公安学刊》 (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⑪ 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和平区、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台区等实验区都成立了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 《关于第二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中期评估情况的通报》,2015年11月2日。
⑫ 王德福: 《协同与参与:社区治理改革的内在逻辑》, 《国家治理》2016年第11期。
⑬ 邢以群: 《软技术的特点、功能与作用》,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1年第6期。
⑭陈伟东:《公共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区建设——以武汉市社区建设为个案》, 《江汉论坛》2005年第12期。
⑮ 陈伟东、张继军: 《社区治理社会化:多元要素协同、共生》, 《社会科学家》2016年第8期。
⑯ 庞绍堂: 《论社区建设中的公共性》, 《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⑰吴晓林:《中国的城市社区更趋向治理了吗——一个结构—过程的分析框架》,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⑱⑲ 马卫红、李芝兰、游腾飞: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改革研究:以深圳 “盐田模式”为例》, 《中国治理评论》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