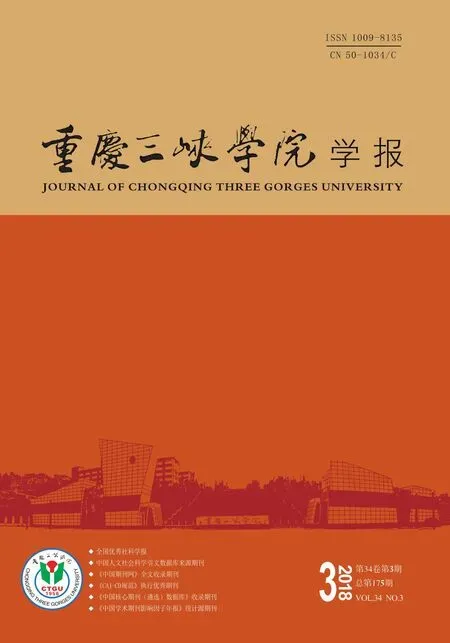宋代殿试赋的功用及其两个层面
2018-03-30
(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一、宋代的殿试与殿试赋的功用
宋代科举的常科考试有三级,分别是州郡解试、省试和殿试。在这三级考试中,殿试是最后一关,名义上由皇帝亲自主持,故又称廷试、御试、亲试。殿试在古代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是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手段之一,意义非同一般。殿试的雏形可溯至唐武后时期,但唐代所谓“殿前试士”多半只是一种形式,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考试。事实上,殿试作为省试之后的最高一级考试,始于宋代。
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后不久即开科取士,然而在宋初的前十余年里,科举沿唐五代之制,尚未举行殿试。直到开宝六年(973),因一场意外事件而引发,殿试制度才逐渐建立起来。《宋会要辑稿·选举一》载:“(开宝)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翰林学士李昉权知贡举,合格进士宋准以下十一人。后下第人徐士廉打鼓论榜,诏于讲武殿重试,通放二十六人,贬试官李昉秩。御试自此始。”[1]5274李昉在开宝六年知贡举,但他取舍不公,引起了下第举子的不满。以徐士廉为首的下第举子通过“打鼓论榜”状告李昉,因此宋太祖特地举行了一次覆试。这次偶然事件不仅为那些下第举子讨回了公道,其更为深远的意义是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变革,殿试自此成为常例,元明清三代的科举考试也继承了这一传统。
在开宝六年的这次殿试中,考试内容之一即为律赋①在律赋研究中,有必要首先厘定“律赋”与“试赋”的含义。“试赋”专指科场中的律赋,殿试赋、省试赋、解试赋是“试赋”最主要的三类,此外尚有馆阁试赋等。“律赋”的外延大于“试赋”,涵括科场外的作品。二者的运用当视语境而定。。此后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宋代殿试一直考赋,而且赋在殿试中还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诚如姚勉在《词赋义约序》中所说:“国初殿廷惟用赋取状元,有至宰相者,赋功用如此也。”[2]在宋人的科举佳话中,关于以赋夺魁的记载十分丰富,例如,欧阳修《归田录》卷一载:“真宗好文,虽以文辞取士,然必视其器识,每御崇政赐进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并列于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赐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试文辞有理趣者。徐奭《铸鼎象物赋》云:‘足惟下正,讵闻公餗之欹倾;铉乃上居,实取王臣之威重。’遂以为第一。蔡齐《置器赋》云:‘安天下于覆盂,其功可大’,遂以为第一人。”[3]又如,施德操《北窗炙輠录》卷下载:“章子平《民监赋》云:‘运启元圣,天临兆民,监行事以为戒,纳斯民于至纯。’方进卷子,读‘运启元圣’,上动容叹息曰:‘此谓太祖。’读‘天临兆民’,叹息曰:‘此谓太宗。’读‘监行事以为戒’,叹息曰:‘此谓先帝。’至读‘纳斯民于至纯’,乃竦然拱手曰:‘朕何敢当!’遂魁天下。”[4]此外,在《宋历科状元录》中常有这样的记载:“(咸平三年)四月,上御崇政殿试礼部贡举人,赋题《观人文以化成天下》,赐陈尧咨等三百一十七人进士及第。”[5]北宋前期的殿试通常考诗、赋、论三题,这里特意点明赋题而不及诗题、论题,也可见赋在宋初殿试中的功用是其他文体远不及的。
律赋讲究声律、对偶、辞藻,限制非常严格,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触犯“声病”。宋代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朝代,在儒家实用主义文艺思想的观照下,律赋便是无用之文,当时很多人抨击律赋,同时也批评诗赋取士这一制度本身。庆历新政时期调整了考试顺序,先策论,后诗赋,赋在殿试中的地位受到动摇。神宗锐意变革,熙宁三年(1070)的殿试开始用策,其后随着变法的深化,诗赋取士遭到全面罢黜。元祐年间旧党执政,诗赋取士得以短暂恢复,但还没来得及在殿试中推行,绍圣年间又罢诗赋。南宋虽以经义、诗赋分科取士,但仅限于解试与省试中,殿试仍然试策。此后元明清三朝的殿试也不再考赋,从整个中国历史流程上来说,殿试赋只存在于两宋时期(含辽金)①两宋时期,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辽金政权积极学习宋朝的科举制度,其殿试也考赋,然而关于辽金殿试赋的记载十分稀少,姑置不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二、宋代殿试赋的命题层面
殿试赋与解试赋、省试赋一样,皆是由“有司”命题,举子按照既定的题目写作。这种实际情况决定了对殿试赋的考察需要从两个层面入手,一是命题层面,它对应的是殿试赋的题目;一是作答层面,它对应的是殿试赋的作品。当然,这两个层面是紧密相关的,命题主导着作答,作品总是围绕着题目展开,如果作品与题目无关,就属于“跑题”,肯定会被黜落的。不过,命题与作答的主体毕竟不同,分开梳理有利于眉目清晰。兹先厘定题目,再根据题目确定传世的宋代殿试赋作品。
《宋会要辑稿·选举七》条列了宋代殿试赋的题目,记载非常完备。现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七》,将相关内容迻录于下[1]5387-5398:
1.《未明求衣赋》(太祖开宝六年);2.《桥梁渡长江赋》(开宝八年);3.《训兵练将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4.《不阵而成功赋》(太平兴国三年);5.《春雨如膏赋》(太平兴国五年);6.《六合为家赋》(太平兴国八年);7.《颍川贡白雉赋》(雍熙二年);8.《庭燎赋》(雍熙二年);9.《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赋》(端拱元年);10.《圣人不尚贤赋》(端拱二年);11.《卮言日出赋》(淳化三年);12.《观人文以化成天下赋》(真宗咸平三年);13.《以贤为宝赋》(咸平三年);14.《有物混成赋》(咸平五年);15.《天道犹张弓赋》(景德二年);16.《建用皇极赋》(景德二年);17.《清明象天赋》(大中祥符元年);18.《大德曰生赋》(大中祥符二年);19.《礼以承天赋》(大中祥符四年);20.《铸鼎象物赋》(大中祥符五年);21.《道无常名赋》(大中祥符七年);22.《置天下如置器赋》(大中祥符八年);23.《君子以厚德载物赋》(天禧三年);24.《圣有谟训赋》(仁宗天圣五年);25.《藏珠于渊赋》(天圣八年);26.《房心为明堂赋》(景祐元年);27.《富民之要在节俭赋》(景祐五年);28.《应天以实不以文赋》(庆历二年);29.《戎祀国之大事赋》(庆历六年);30.《盖轸象天赋》(皇祐元年);31.《圜丘象天赋》(皇祐五年);32.《民监赋》(嘉佑二年);33.《尧舜性仁赋》(嘉佑四年);34.《王者通天地赋》(嘉佑六年);35.《寅畏以飨福赋》(嘉佑八年)。
以上是35个殿试赋题,对应的是32个殿试年份,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其中的3个殿试年份(雍熙二年、咸平三年、景德二年)较为特殊,不只一次考赋。以真宗咸平三年(1000)为例,当时正值河朔用兵,为了照顾河北举人,专门殿试礼部奏名河北进士,赋以《以贤为宝》为题。正常情况下,每次殿试只针对礼部奏名进士考赋,一年一题。《宋会要辑稿·选举七》对宋代殿试赋题的记载已然详尽无遗,但由于其他原因,仍有两个枝节问题需要辨明。
第一,仁宗天圣二年(1024)有没有殿试《德车结旌赋》。这一问题的产生源于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四中的记载:“宋莒公(庠)殿试《德车结旌赋》,第二韵当押结字,偶忘之。考试官奏过,得旨,因得在数,以魁天下。其后谢主文启云:‘掀天波浪之中,舟人忘楫;动地鼙鼓之下,战士遗弓。’盖叙此也。故今《三元衡鉴赋》载此赋无结字。”[6]432宋庠为天圣二年状元,因此就有了一种说法:天圣二年曾殿试《德车结旌赋》。今人相关论著中多采纳此说①如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章《北宋前期(960—1071)进士科考试与文学》所列之“北宋前期进士科殿试题”表格,于天圣二年的殿试赋题内标明《德车结(原误作“载”)旌》,又如许瑶丽《宋代律赋与科举——一种文学体式的制度浮沉》(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五章《北宋中期律赋:变唐以自立》中有“今二宋集中省试之作不存,而有殿试之《德车结旌赋》,宋庠凭此赋取状元之衔”云云,均从吴曾《能改斋漫录》中的记载推演而来。,而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在此需要提到“谅暗”。“谅暗”,又称“谅阴”,是指皇帝服丧。宋代从真宗朝开始,若皇帝在“谅阴”中,则免殿试,以省元为状元。《宋会要辑稿·选举三》载真宗咸平二年事:“礼部贡院言:‘考试举人毕,请御试。’帝以谅阴中不许。”[1]5287-5288又,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三《谅暗罢殿试》云:“自咸平以来,人主有三年之丧则罢殿试,而以省元为榜首。”[7]天圣二年,仁宗仍在“三年之丧”中,这一年没有举行殿试,更不会有殿试赋,所以《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中没有开列这一年的殿试题。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四中的记载十分可疑,因为文莹《湘山野录》卷上也记载了宋庠的一则事迹:“宋郑公庠省试《良玉不琢赋》,号为擅场。时大宗胥内翰偃考之酷爱,必谓非二宋不能作之,奈何重叠押韵,一韵有‘瓌奇擅名’及‘而无刻画之名’之句,深惜之,密与自改‘擅名’为‘擅声’。后埒之于第一。殆发试卷,果郑公也。”[8]《湘山野录》与《能改斋漫录》所载并非一事,但有很多共同点,两处记载都说宋庠在作赋时出现了失误,都得到了考官的格外眷顾。假如两处记载都是准确的,省试失误一次得到眷顾,殿试再失误一次还得到眷顾,这样的好运气令人难以置信。对这两处记载合理的解释是,宋庠在省试或解试过程中的确曾在作赋时出现失误,而且确实得到过“贵人相助”,后来宋庠被擢为状元②宋庠被擢为状元的过程相当复杂,正常情况下,宋代皇帝在“谅暗”中不举行殿试,以省元为状元。但天圣二年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年份,当时仁宗年幼,刘太后垂帘听政,朝政实际上是由刘太后主持。该年的省元原是吴感,但礼部奏名后又重新编排了一次等第,且将宋庠的弟弟宋祁列为第一。刘太后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出发,认为“弟不先兄”,遂将宋庠擢为状元,而将宋祁退为第十。,他的失误与考官对他的眷顾便成了科场美谈,播之众口。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宋庠的事迹难免会出现种种夸大、失实的地方。《湘山野录》与《能改斋漫录》均属文人笔记,与史书相比,文人笔记多载社会上的传闻,内容真假参半。两处记载表面上说的是两件事情,其源头很可能就是同一件事。宋庠后来位至宰辅,他以状元身份成为宰相,是时人津津乐道的盛事。如果人们忽略了天圣二年仁宗在“谅暗”中这一事实,就极容易把宋庠在省试或解试中的失误附会到殿试上去。总之,天圣二年仁宗在“谅暗”中没有举行殿试是确定的,《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中没记载该年的殿试题也是确定的,《能改斋漫录》中的记载只是一处十分可疑的孤证,在没有更多的证据之前,实在不能认为天圣二年曾殿试《德车结旌赋》。
第二,英宗治平四年(1067)有没有殿试《刚中正履帝位赋》?解答这一问题,关键点还是在“谅暗”上。《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中同样没有开列英宗治平四年的殿试题,认为该年曾殿试《刚中正履帝位赋》完全是今人的一个错误看法①参见周兴禄:《宋代殿试诗赋论题考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年第6期。,其依据是《山堂肆考》卷八十四中的记载:“许世安,英宗治平四年状元及第,试《刚中履帝位赋》。”[9]按:《宋历科状元录》卷四载:“三月赐礼部进士许安世等及第、出身四百六十一人,赋题以《刚中正履帝位》。”[5]313《山堂肆考》中的记载存有两处舛讹,“许世安”当为“许安世”,“《刚中履帝位赋》”脱一“正”字。由许安世为英宗治平四年状元及“赋题以《刚中正履帝位》”推断本年曾殿试《刚中正履帝位赋》,表面上看没什么问题,但它忽略了一个事实,治平四年也在“谅暗”中,《宋会要辑稿·选举七》没有载该年的殿试题,是因为这一年根本没举行殿试。
宋代新登基的皇帝要为“先皇”服丧三年,乍一看,治平四年似乎不在“谅暗”中,毕竟治平四年时英宗为仁宗服丧的三年之期已过。但是,治平四年正月初八丁巳日英宗便已驾崩,该年贡举时,神宗已即位,只不过尚未改元。此时,是神宗要为英宗服丧,在“谅暗”中,没有举行殿试。《山堂肆考》与《宋历科状元录》中的记载是按照“谅暗罢殿试”的惯例,“以省元为榜首”,《刚中正履帝位赋》其实是治平四年的省试赋题。此外,《宋会要辑稿·选举一》《文献通考·选举考五》等文献中明载治平四年的省元便是许安世,他的状元身份的确是从“以省元为榜首”而来的。
通过以上的两则辨误可以看到,《宋会要辑稿·选举七》对宋代殿试赋题的记载是详尽而又可信的,若没有确凿的证据,仅凭借其他文献中一鳞半爪的记载就妄生异议,恐怕有“画蛇添足”、徒增谬乱的嫌疑。
三、宋代殿试赋的作答层面
宋代科举考赋,律赋写作在宋代有着深厚的制度保障,但留传至今的宋代律赋不足三百篇,散佚严重。现存的宋代律赋有的在题目上明标“御试”“殿试”等字样,这样的作品显然是殿试赋,但某些作品并无类似标注。此时,上文清理的殿试赋题目就能发挥作用了,将现存的宋代律赋与宋代历届殿试赋题目对照,自能判断出一篇作品是不是殿试赋。不过,仍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宋人经常在科考之前或入仕之后用既有的殿试赋题目进行拟作,这样的作品属于拟殿试赋,与完全意义上的殿试赋还是有区别的。判断一篇作品是殿试赋还是拟殿试赋,主要察看其作者的登科年份是否与题目对应的殿试年份相一致。也就是说,判断殿试赋的方法要分两步:第一步,比对作品题目与已清理出来的历届殿试赋题目;第二步,比对作者登科年份与殿试赋题目年份。今人编纂的《全宋文》①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合肥: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本文开示的宋代殿试赋及相关引文皆可见《全宋文》,下文不再一一标注。为爬梳传世的殿试赋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现以《全宋文》为工具遍检宋代律赋,并按我们所说的判断殿试赋的方法一一比对,共得宋代殿试赋7篇,条述如下:
1.田锡《御试不阵而成功赋》
田锡今存《御试不阵而成功赋》一篇,以“功德双美,威震寰海”为韵。在宋人中,田锡与欧阳修是三级试赋保存最完整的两位作家。除殿试赋外,田锡还存有《开封府试人文化成天下赋》(以“焕乎人文,化成天下”为韵)和《南省试圣人并用三代礼乐赋》(以“皇猷昭宣,礼乐备举”为韵)。《不阵而成功赋》是太宗太平兴国三年的殿试赋题,田锡也确实是在本年登科②本文提及的宋人登科年份不一一出证,皆可查龚延明、祖慧编:《宋代登科总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且为殿试第二名。是年四月,陈洪进献漳、泉二州;五月,吴越国主钱俶献其两浙诸州。殿试于本年九月举行,赋以《不阵而成功》为题,显然是为了颂扬太宗的功绩。田锡在赋中从礼乐仁政的角度做了恰到好处的赞美:“今圣朝以民济寿域,道洽人寰,将铸剑于农器,方虚候于玉关。弥祸乱于未形,恩能服众;布英威于有截,礼以防闲。下臣庚歌之曰:化洽无私兮,功符不宰。取仁义为胜兮,岂干戈砺乃。德上冠于唐虞,政下任乎元凯。孙、吴之阵法奚取,韩、白之兵机弗采。宜乎车同轨而书同文,至化方流于寰海。”北宋仁宗朝时,律赋的讽谏功能受到重视,田锡此赋一以颂美为主,颇能代表太宗朝的律赋风尚。
2.王曾《有物混成赋》
王曾为咸平三年状元,其殿试《有物混成赋》以“虚象生在天地之始”为韵。王曾《有物混成赋》在当时享有盛誉,《隆平集》卷五《宰臣》载:“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咸平中登进士甲科,所试《有物混成赋》,天下以为赋格。”[10]在宋代律赋中,王曾《有物混成赋》是表现器识的典范,里面有两句话常被称引,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十载:“王沂公(曾)《有物混成赋》云:‘不缩不盈,赋象宁穷于广狭;匪雕匪斵,流形罔滞于盈虚。’则宰相陶钧运用之意,已见于此赋矣。又云‘得我之小者,散而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为山川。’则宰相择任群材,使小大各得其所,又见于此赋矣。”[11]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七也曾引用《有物混成赋》中表现器识的名句,并称其为“有以自见”[12]。王曾后来位至宰辅,人们认为他在《有物混成赋》中已展现出了王佐之器的气象。
3.欧阳修《殿试珠藏于渊赋》
欧阳修现存《殿试珠藏于渊赋》一首,以“君子非贵,难得之物”为韵。除这篇殿试赋之外,欧阳修的解试赋、省试赋均可得睹,即《国学试人主之尊如堂赋》(以“堂陛隆峻,人主尊矣”为韵)与《省试司空掌舆地图赋》(以“平土之职,图掌舆地”为韵)。欧阳修为仁宗天圣八年进士,在入仕之前,欧阳修并没有修习古文,如其在《与荆南秀才书》中所说:“仆少孤贫,贪禄仕以养亲,不暇就师穷经,以学圣人之遗业。而射猎书史,姑随世俗作所谓时文者,皆穿蠹经传,移此俪彼,以为浮薄,惟恐不悦于时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13]360-361在任西京留守推官时,欧阳修与尹洙等人交游,这时才开始创作古文,并领导了影响巨大的北宋古文运动。《殿试珠藏于渊赋》是欧阳修创作古文之前的早期作品,骈俪色彩较重,还没有后来写作《拟御试应天以实不以文赋》那样横骛别趋。不过,欧阳修“本以辞赋擅名场屋”[14],他的律赋很受宋人推许,其《殿试珠藏于渊赋》也不乏警句,李调元《赋话》卷五曰:“宋欧阳修《珠藏于渊赋》,乃殿试作也。其佳句云:‘将令物遂乎生,老蚌蔑剖胎之患;民知非尚,骊龙无探颔之难。’又‘上苟赋于所好,下岂求于难得。’舒畅之中时露剀切,他日立朝蹇谔,斯篇已见一斑。”[15]
4.金君卿《应天以实不以文赋》
金君卿为仁宗庆历二年进士,其殿试《应天以实不以文赋》以“推诚应天,岂尚文饰”为韵。在这一年,欧阳修看到殿试赋的题目为《应天以实不以文》,他激动之下,拟作了一篇,即《拟御试应天以实不以文赋》。金君卿的作品是在殿试现场写作的,是标准的殿试赋;欧阳修的作品是在考场之外写作的,是拟殿试赋。欧阳修曾将其拟作进呈御览,并得到了仁宗的嘉奖,在进赋《引状》中,欧阳修说:“臣伏睹今月十三日御试《应天以实不以文赋》,题目初出,中外群臣皆欢然,以谓至明至圣,有小心翼翼事天之意。盖自四年来,天灾频见,故陛下欲修应天以实之事。时谓出题以询多士,而求其直言。外议皆称,自来科场只是考试进士文辞,但取空言,无益时事。亦有人君能上思天戒,广求规谏以为试题者……不敢广列前事,但直言当今要务,皆陛下所欲闻者。”[13]582与写作《殿试珠藏于渊赋》不同,庆历二年时,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已很有造诣,他写作《拟御试应天以实不以文赋》其实是用古文的某些因素来提升律赋的品格。从其《引状》中可见,欧阳修认为进士所试之赋皆是“空言”,“无益时事”,他对此心怀不满,所以特地拟作一篇。欧阳修的这篇拟殿试赋具有鲜明的特点,它以讽谏为目的,直言当下时事,如“至如阳能和阴则雨降,若岁大旱,则阳不和阴而可推(原注:去年大旱);阴不侵阳则地静,若地频动,则阴干于阳而可知(原注:去年河东地频动)。又如黑者阴之色,晦者阴之时,或暴风惨黑而大至,白昼晦暝而四垂(原注:康定元年三月,黑风起,白日晦)”。对于这些灾异现象,欧阳修认为“如此之类,皆阴之为”,而“阴为小人与妇人”,所以欧阳修进谏:“慎择左右而察小人,则视听之不惑;肃清宫闱而减冗列,则恭俭而成式。”在形式上,欧阳修的《拟御试应天以实不以文赋》也有很大的变化。正常情况下,宋代律赋都在四百字左右,以四六句式为主,欧阳修的这篇拟殿试赋长达七百五十字,句式参差不齐,而且具有古文的流宕气势。庆历二年已是庆历新政的前夕,庆历新政期间,欧阳修等人试图变革律赋的体制,在《拟御试应天以实不以文赋》中,欧阳修的变革意图已暴露无遗。在欧阳修拟殿试赋的对比之下,金君卿的《应天以实不以文赋》不免黯然失色,它整体上以议论为主,正是欧阳修所谓的“空言”。
5.刘敞《御试戎祀国之大事赋》
刘敞为仁宗庆历六年进士,是年,刘敞以殿试第二及第,他的这篇殿试赋毫无疑问是出类拔萃的作品。“戎祀国之大事”出自《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刘敞学问赅博,精通六经诸子、古今传记、天文地理以及卜医术数,尤长于《春秋》学,曾著有《春秋传》十五卷、《春秋权衡》十七卷、《春秋说例》二卷等学术著作。庆历六年的殿试赋从《左传》中出题,可以说正中刘敞下怀。所以,刘敞在《御试戎祀国之大事赋》中本经立意,对题目的阐发十分到位,如其前二韵曰:“戎在御侮,祀专飨神。皆有邦之大事,岂庶政以同伦?宜社而行,外伸威于殊俗;受厘以报,内均福于生民。盖所谓朝廷之先务,教化之本因者也。稽合前经,发挥至理,政有常法,事或殊轨。以保民者莫若戎,以驭神者莫如祀。善师不战,谅治体之孰加;精意克禋,眷彝伦之莫拟。”从第一韵的破题、小赋到第二韵的原韵,皆语义正大,体势雍容,深具学者之赋的风范。
6.郑獬《圜丘象天赋》
郑獬为仁宗皇祐五年状元,其殿试《圜丘象天赋》以“圜丘就阳,上宪天体”为韵。郑獬能够在众多举子中夺魁,与他的《圜丘象天赋》破题精警不无关系。《能改斋漫录》卷一四载:“内翰郑毅夫久负魁望,而滕甫元发名亦不在其下。既试礼闱,郑为南宫第四场魁,滕为南庙别头魁。及入殿试《圜丘象天赋》,未入殿门,已风闻此题,遂同论议,下笔皆得意。时刘后李公端梦滕作第三人,赋绯牙系鞋来谢,而郑亦有白龙之梦。将唱名,二公相遇,各举程文。滕破题云:‘大礼必简,圜丘自然。’及闻郑赋‘礼大必简,丘圜自然’,滕即叹服曰:‘公在我先矣。’……及唱第,郑果第一,滕果第三,皆如素望。”[6]416-417通过比较律赋破题的优劣来预测考试的排名,足见律赋在科场中的重要性以及律赋对破题的重视。滕甫与郑獬的破题相差无多,只是用字的顺序略有不同,但辞赋素来就以一字见工拙,郑獬将“礼”与“丘”提到了“大”与“圜”的前面,就产生了一种顿挫之势,倍显精神。郑獬《圜丘象天赋》的破题不仅为时人推许,也被后世称道。《复小斋赋话》卷上曰:“律赋最重破题,李表臣程《日五色》,夫人知之矣。宋唯郑毅夫《圜丘象天赋》一破,可与抗行。”[16]这是清人浦铣的评论,不为过誉。
7.范祖禹《寅畏以飨福赋》
范祖禹为仁宗嘉佑八年进士,殿试第四名,其《寅畏以飨福赋》以“祗畏天道,能飨隆福”为韵。如果说郑獬的《圜丘象天赋》破题精彩,范祖禹的《寅畏以飨福赋》则是收尾漂亮。收尾也就是律赋的第八韵,秦观对律赋作法很有研究,他说:“第八韵卒章,尤要好意思尔。”[17]18范祖禹《寅畏以飨福赋》的第八韵曰:“大哉!建功所以永年,宜人所以受禄。应如律吕之动,报逾影响之速。夫知天之仁爱人君,寅畏者飨其福。”这篇殿试赋的题目为《寅畏以飨福》,结尾一句是“寅畏者飨其福”,正是卒章点题,与第一韵的破题前后呼应,形成一个周密的回环。
除上述七篇殿试赋外,王禹偁的《卮言日出赋》(以“盈侧空仰,随变和美”为韵)曾被一些人误认为是殿试赋。《卮言日出赋》是太宗淳化三年的殿试赋题,而王禹偁是太宗太平兴国八年进士,两个年份不一致,他的《卮言日出赋》显然不是殿试赋。王禹偁《小畜集》卷二专收律赋,并有序言弁之于首。在《律赋序》中,王禹偁说:“淳化中,谪官上洛。明年,太宗试进士,其题曰《卮言日出》。有传至商山者,骇其题之异且难也,因赋一篇。”[18]在这里,王禹偁明言《卮言日出赋》是他贬谪商州时的拟作,是一篇拟殿试赋。胡宿今存有一篇《建用皇极赋》,只看题名,正与真宗景德二年的殿试赋题相同,但胡宿是仁宗天圣二年进士,所以他的这篇律赋也不属于殿试赋。另外,宋庠与宋祁两人各存有一篇《德车结旌赋》,若按《能改斋漫录》中的说法,这两篇作品便是殿试赋,但本文在考订殿试赋题目时已否定了《能改斋漫录》的说法,因此这两篇作品也不属于殿试赋。
综上所述,今厘定宋代殿试赋题35,作品7。从理论上讲,在宋代殿试考赋的近百年时间里,曾经参加殿试的进士均应该有写作殿试赋的经历,如果当时的殿试赋作品悉数存留下来,数量肯定非常庞大。但现存宋代殿试赋不足十篇,真可谓九牛一毛。不过,经过时间的筛选,流传至今的殿试赋大都是当时的精品,弥足珍贵。宋代殿试赋对科举文学、辞赋学研究均有重要意义,其文学文献价值更不容低估。本文旨在梳理宋代殿试赋的基本情形,至于它的艺术特征、文化蕴含等内容暂不涉及,容另文探讨。
参考文献:
[1] 徐松.宋会要辑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2] 姚勉.雪坡集(卷三十八)[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265.
[3] 欧阳修.归田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14.
[4] 施德操.北窗炙輠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23.
[5] 朱希召.宋历科状元录[M]//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1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286.
[6] 吴曾.能改斋漫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0:274.
[8] 文莹.湘山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15-16.
[9] 彭大翼.山堂肆考[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7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586.
[10] 曾巩.隆平集[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206.
[11] 吴处厚.青箱杂记[M].李裕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112.
[12] 叶适.习学记言[M].北京:中华书局,1977:700.
[13] 欧阳修.文忠集(卷四十七)[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4]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496.
[15] 李调元.赋话[M]//王冠.赋话广聚(第3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103.
[16] 浦铣.复小斋赋话[M]//王冠.赋话广聚(第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704.
[17] 李廌.师友谈记[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18.
[18] 王禹偁.小畜集(卷二)[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