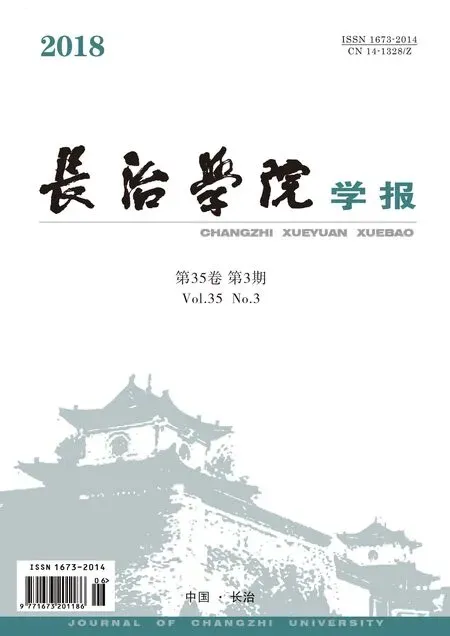舒位《春秋咏史乐府》初探
2018-03-29常亮
常 亮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一、引言
舒位,少名佺,字立人,小字犀禅,号铁云,直隶大兴县(今属北京)人。舒位是乾嘉时期的著名诗人,是性灵派的一员大将,与王昙、孙原湘并称为乾嘉“后三家”,著有《瓶水斋诗集》。乾隆五十一年,舒位在第二次参加顺天府乡试落第后,作《春秋咏史乐府》140首,后被收录《瓶水斋诗别集》。舒位看到了在咏史乐府诗的发展史上,所咏内容大多“详于后代而略于春秋”不足,为了补阙,所以创作了春秋咏史乐府组诗。对这一咏史乐府诗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组诗,学界并无专题性研究。因此笔者拟从《春秋咏史乐府》补咏史乐府诗之阙的创作意识、对《左传》史事的诗化书写及其艺术特色三个方面对《春秋咏史乐府》进行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二、《春秋咏史乐府》补咏史乐府诗之阙的创作意识
咏史乐府诗,即以乐府诗的形式咏写相关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就宋代以后咏史乐府诗而言,首屈一指的大家乃是元末以“铁崖乐府”著称的杨维桢。杨维桢自创新题的乐府咏史诗,其诗题根据所咏对象拟定,且多是三字为一题。杨维桢之后,李东阳以其为效仿对象,著有《拟古乐府》,此作一出,引起时人纷纷效仿。明末清初,咏史乐府诗的创作蔚然成风,且多为大型连章体组诗,如王士禛《小乐府》30首因读《三国志》而作,尤侗作《明史乐府》100首等。清代中晚期,咏史乐府诗的创作更是进入了一个繁荣阶段。此期较重要的诗人诗作,主要有熊金泰《三国志小乐府》一卷、洪亮吉《晋南北朝史乐府》二卷、《唐宋小乐府》一卷以及舒位《春秋咏史乐府》一卷。
通过梳理咏史乐府诗的发展历程可知,咏史乐府诗发展到清代中晚期时,在题目的拟定方面,诗人们几乎都自拟新题,而且诗题多以三字为一题;在篇幅体例方面,明末清初已出现大型连章体组诗。这两个特征,舒位的《春秋咏史乐府》都符合,可以说,这卷140首的长篇巨制,顺应了咏史乐府诗的发展大势。
《春秋咏史乐府》的题目都是“自拟新题”。这些题目都取材于《左传》,舒位拟定的诗题,颇有巧思,且具画龙点睛之妙。如《风马牛》一篇咏齐伐楚盟于召陵事,鲁僖公四年,齐桓公侵蔡伐楚时,楚王派遣的使臣回答齐侯,声称齐、楚二国“风马牛不相及”[1]45,这是题目《风马牛》的由来,同时也揭示了齐国发动这场战争的无理性;再如《鹤乘轩》咏叹卫懿公好鹤亡国之事,此题取自《左传》闵公二年:“冬十有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1]47。卫国之所以遭受亡国之祸,根本原因在于卫懿公的荒唐与无道,而“鹤乘轩”三字确将卫懿公的荒唐表现得淋漓尽致。
《春秋咏史乐府》是大型的连章体组诗,正如舒位在自序中所说的那样:“大旨以左氏内传为经,而以国语、公、谷梁为纬,并杂采他书之论春秋时事者,凡一百四十首”[2]726。该组诗以《左传》为经,以《国语》、《公羊传》、《谷梁传》为纬,并杂采了“他书之论春秋时事者”,如《诗经》、《史记》、《帝王世纪》等书。
《春秋咏史乐府》在咏史乐府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不仅因它在自拟新题与大型连章组诗方面顺应了咏史乐府诗的发展大势,还因为它扩充了咏史乐府的题材时段,越三国、六朝、明代而上,咏及春秋历史,诚如诗人自己所言:“顾皆详于后代而略于春秋。今兹所咏,若补其阙”[2]726,补咏史乐府诗之阙,更确切地说,该作品补以乐府体专咏春秋时事之阙。以乐府体咏春秋时事,杨维桢已有《吴钩行》、《要离塚》及《介山操》三篇,李东阳亦有《申生怨》、《绵山怨》、《屠兵来》、《避火行》、《挂剑曲》、《树中饿》、《渐台水》及《国士行》八篇,二者均间取史册所载,咏春秋时事不过是偶然为之,所存篇目也较少。而舒位则专咏春秋时事,篇目有140首之多。
三、《春秋咏史乐府》对《左传》史事的诗化书写
咏史乐府诗以咏史为诗之意、以乐府为诗之体。虽然舒位称自己的春秋咏史乐府诗为“春秋咏史长短句诗”,但该作品仍具有乐府诗的某些特色。“本事”是乐府诗歌中包含作品信息最多的要素。向回对乐府诗的“本事”作出了如下定义:“乐府诗的本事,就是指那些与乐府曲调、曲名或歌辞的创作、传播、变化等有关的历史事实或民间传闻。”[3]据此而言,《春秋咏史乐府》的140个题目均取材于《左传》,歌辞的创作也以“《左传》为经,可以说《左传》就是《春秋咏史乐府》的“本事”。140首春秋咏史乐府诗的叙事与议论均围绕其“本事”——《左传》展开。《春秋咏史乐府》以诗论春秋,是诗化了的《左传》。
乐府诗的叙事性较强,咏史乐府诗也不例外。纵览140首春秋咏史乐府诗,舒位采用了《左传》的编年顺序,并汲取了《左传》中大部分重要史实。《左传》的历史叙事,注重事件的过程性、完整性、严肃性与真实性。而《春秋咏史乐府》的叙事在继承《左传》历史叙事真实性的同时,还具有诗歌叙事的片段性和概括性,以及乐府诗歌叙事特有的诙谐性与灵活性。
如《风马牛》一篇咏齐伐楚盟于召陵事,全诗如下:“蔡姬荡舟齐侯惊,楚人胶舟周王崩。侵蔡伐楚良有以,矧无缩酒包茅菁。管仲方相齐,子文亦相楚。彼夸城池坚,此耀甲兵武。马牛其风南海波,犀兕尚多弃则那。乃知城濮之议战,不若召陵之议和”[2]737。我们具体来看《风马牛》一诗的叙事特点:舒位首先将齐伐楚的“借口”概括为“二舟一不贡”事件。“二舟”事件:一为蔡姬荡舟,该事发生于鲁僖公三年,“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荡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之絶也。蔡人嫁之”[1]45。这是齐侯侵蔡的理由,由于蔡侯将蔡姬又嫁给了楚王,所以齐桓公借此伐楚。《左传》叙事舒位将此事概括为“蔡姬荡舟齐侯惊”七字,简短有力;二为楚人胶舟导致周昭王南征不复之事,《左传》僖公四年中只提及“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1]46,语焉不详。周昭王乘胶舟驾崩事见于皇甫谧《帝王世纪》:“昭王在位五十一年,以德衰南征,及济于汉,舡人恶之,乃胶船进王。王御船中流,胶液解,王及祭公俱没水而崩”[4]92。很明显,舒位在诗中所言“楚人胶舟周王崩”,借鉴了皇甫谧的说法,作为对《左传》的补充。“一不贡”事件指的是“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1]46,楚国不贡包茅,舒位将此概括为“矧无缩酒包茅菁”。
《风马牛》一诗叙事的诙谐性主要表现在诗歌叙事的寓庄于谐,灵活性主要体现在诗歌的句式变化之中。该诗首句“蔡姬荡舟齐侯惊,楚人胶舟周王崩”,这是齐伐楚的原因。涉及两国交战大事,本该极为严肃庄重,而诗人却似不以为然,以此十四字将原因轻描淡写,诙谐之处可见一斑。句式方面,该诗的句式长短不拘,五、七言句杂用。舒位在《春秋咏史乐府》的自序中称自己的咏史乐府诗为“长短句诗”,这就表明了其咏史乐府诗在句式上所表现出的长短不拘的灵活性。
舒位不仅在春秋咏史乐府诗的本事上沿用了《左传》,还继承了《左传》的“君子曰”,非常注重咏史乐府诗中的议论。正如舒位在《春秋咏史乐府》的序中所言:“今兹所咏,若补其阙,或褒焉,或讥焉,或存而不论焉。”[2]726他对诗中所咏的史实和人物或褒或讥,或存而不论,以春秋笔法咏春秋。如《藐诸孤》一诗,咏鲁僖公十年晋国大夫荀息死殉公子卓事。《左传》的“君子”对此事评论如下:“君子曰:《诗》所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荀息有焉。”[1]51-52。《左传》对荀息死殉公子卓事的评价为“荀息有焉”,此语之意有争论。《晋语》认为荀息“不食其言”,司马迁认为荀息“不负其言”,杜预也认为荀息有诗人重言之义。而司马光则认为杜预曲解了左氏之意,认为荀息在晋献公托孤之际不但不能阻止献公废长立幼的行为,反而还轻易许下了“以死继之”的诺言,先是失言,后又未能力挽狂澜,所以左氏对荀息的评价应该是贬。司马光此论后,杨慎、朱鹤龄等人也认同司马氏的说法。
我们来分析舒位对荀息死殉之事的看法,《藐诸孤》全诗如下:“庆父杀般成季奔,里克杀卓荀息死。死者非,奔者是。非谓奔者是,死者不得其所死。君言藐诸孤,辱在荀大夫。大夫曰贞贞乃谅,大夫曰忠忠则愚。忠贞既竭股肱力,犹幸当年言不食。虽不食,竟何益!吾闻伐虢取虞皆荀息,奈何不能杀里克!信不近义谋不臧,白圭白圭磨不得。”[2]739首先,舒位选取春秋时期鲁国庆父杀公子般的事与晋国里克杀公子卓这件事进行了对比,认为这两件事的性质一样。但同样作为辅政大夫的成季和荀息,他们的做法却截然相反,成季出逃,而荀息却选择了死殉。舒位对此二人的评价是:“死者非,奔者是”,他对成季是褒,对荀息是贬。一字寓褒贬后,他接着分析了自己为何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非谓奔者是,死者不得其所死”,是因为荀息的死殉并无实际意义,乃是不得其死。虽然荀息之死履行了对晋献公的承诺,但他的死对晋国无益,只是枉死罢了,“虽不食,竟何益”。“信不近义谋不臧,白圭白圭磨不得”,舒位认为荀息的许下的“信”不符合“义”,乃是失言。如此看来,舒位对荀息死殉的看法与司马光、杨慎、朱鹤龄等人类似,并未拘泥于司马迁、杜预等人的说法。而且,舒位将荀息死殉之事娓娓道来,夹叙夹议,得出最后的结论乃是水到渠成。
四、《春秋咏史乐府》的艺术特色
舒位在其《瓶水斋诗话》中论及咏史诗时曾言:“咏史诗不著议论,有似弹词;太著议论,又如史断。”[2]822咏史弹词重在“叙事”,舒位认为若咏史诗中只重叙事不重议论,那便跟弹词这种通俗历史读物一样了。“太著议论,又如史断”,“太著议论”便会像“史断”一样失去了诗味。他在“著”与“不著”之间进行精心研磨,因此也在艺术上取得了相较一般诗人高出一筹的成就。
舒位在《春秋咏史乐府》序中言:“今兹所咏,若补其阙,或褒焉,或讥焉,或存而不论焉。长言不足,则他事相形;庄论易倦,则诙谐间出。”[2]726沈叔埏在《舒铁云位春秋乐府序》中也有同样的看法:“今铁云撷盲左之菁华,补西涯之遗漏,固非效颦学步者可同年语。而本事之外,刺取时事,相形无不吻合。精心结撰,亦复以谐噱,出之天然。”[5]72可见,舒位采用了对比与诙谐两种手法对140首春秋咏史乐府诗歌的议论进行了艺术化处理。
《春秋咏史乐府》以《左传》为本事,在叙事中已经隐括春秋史实,本身就是典故。舒位在对“本事”进行议论时,常在本事之外再提到与之具有相似性或关联性的其他史事,相形对比之下,新义自见。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的既有春秋时事,亦有后世史实。如《公伤股》一诗,舒位将齐鲁长勺之战与宋楚泓水之战进行对比,拈出两场战争的“不鼓”问题:“鲁人战齐人,公将鼓。刿曰不可,齐避鲁。宋人战楚人,公不鼓。公曰未可,宋逃楚”[2]743,极具画面感和戏剧性。再如《四字狱》一诗咏晋太子申生被骊姬陷害之事。舒位在叙述此事时,将申生的冤案与后世的两大冤案放在了一起:“于少保,两字狱;岳将军,三字狱;贼由太子四字狱。”[2]738于谦冤由“夺门”二字,岳飞冤由“莫须有”三字,而申生冤由“贼由太子”四字,呈递进次序,三大冤案齐聚此诗,增强了读者的悲愤之感。
舒位在创作春秋咏史乐府诗的过程中,意识到对“本事”的议论若仅仅以春秋笔法出之,则很容易出现“庄论易倦”的问题,所以他选择了“诙谐间出”的手法进行调节。如《庆父材》一诗末尾有言;“哀姜不足哀,文姜何以文?人言齐二女,能杀鲁三公。”[2]736舒位在此借哀姜和文姜的谥号讥讽了她们二人,哀姜不足哀,她的结局完全是咎由自取;文姜何以文,舒位认为文姜的淫荡和狠辣担当不起“文”的谥号。再如《绵上田》一诗咏晋文公火烧绵山之事:“既焚介推山,亦爇负羁宫。求贤与报德,皆用烈火攻。”[2]744介之推与曹国大夫僖负羁在重耳逃亡途中都对重耳有恩,但重耳即位之后,对两位恩人的回报都是“烈火攻”。虽说二者均非晋文公本意,但后果已经酿成,“皆用烈火攻”,是舒位对重耳的嘲讽。
总之,舒位《春秋咏史乐府》,传承良多。史事多采自《左传》,以诗传史;于诗史上,效法咏史乐府的杨李诸人。在传承基础之上,又展现出独特的铁云体风格,在咏史乐府诗史中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