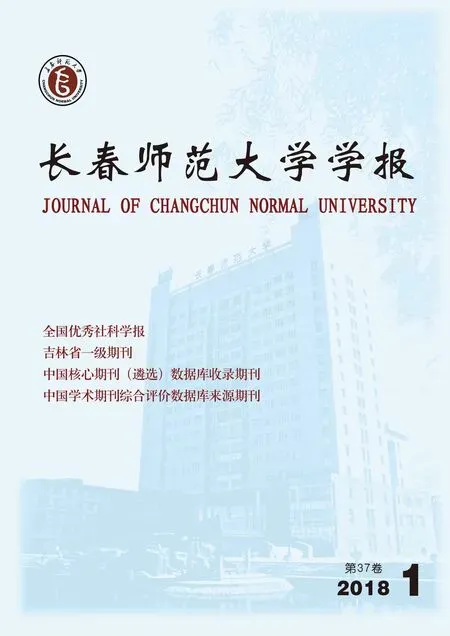唐诗在《牡丹亭》中的文学功用及价值论析
2018-03-29许文伯
许文伯,杨 萍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清代戏曲家孔尚任在《桃花扇》开篇中提到:“传奇虽小道,凡诗赋、词曲、四六、小说家,无体不备”[1]《桃花扇小引》。当时的戏曲家创作的作品尽管不受主流文学圈的重视,但从作家个体角度来看,却需要做到“积学以储宝”“研阅以穷照”,对各种文体的创作手法都要有所掌握。明代伟大的戏曲家汤显祖创作的《牡丹亭》正是一部被俞平伯先生大力赞扬为“窃观于文则有盲左,于辞赋则有三闾,于诗则有彭泽,则有杜陵,于词则有清真,此数子者所拳拳服膺,乃文章百代之师, 旷世而一见者也”[2]985的经典名篇。汤显祖在《牡丹亭》的上下场诗和曲辞、宾白中运用了大量诗词,绝大部分是从唐诗中集句成诗,使整部传奇具有“典雅清丽”的文人气息,达到了诗与意会、言随意转的艺术效果。
一、唐诗在《牡丹亭》中的文学功用
“集唐诗”指从唐诗中集句成诗。《牡丹亭》中的“集唐诗”有69 首280 句[3],引用诗句数量众多,牵涉诗人数量甚众,如李白、杜甫、韩愈、李商隐、白居易、刘长卿、韩偓等。这些诗人大多数出自盛唐及中晚唐时期,可以看出汤显祖在诗歌借用层面上直接选取的是唐诗成熟时期的作品。汤显祖所处的年代远远早于《全唐诗》之问世,可以看出其对诗词的理解、鉴赏甚至搜集是有较高水平的,他在运用诗词的过程中能够做到“合情合理”,将诗词与戏曲做到完美对接。
《牡丹亭》中的“集唐诗”大多用在上下场诗和曲辞、宾白中。上下场用诗进行开头和收尾,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戏曲的一个显著特征。“上下场诗乃一出之始终条理,倘用旧句、俗句,草草塞责,全出削色矣”[1]《桃花扇凡例》。《牡丹亭》与《桃花扇》《长生殿》相比,其上下场诗完全借用前代诗人作品,而不是作家进行独立创作,这一点正是其对前朝文学遗产继承性的直接表现,我们把这种引用方式称为“直接引用”;而在宾白、曲辞的运用中,大多会将原有诗句进行一定改动,即“巧妙化用”。这两种诗词运用方式在不同情节有不同的艺术效果,这也是本文拟重点讨论的部分。
上场诗一般是人物上场时的宾白,作用主要是介绍人物。如第九出《肃苑》中春香的上场诗:“花面丫头十三四,春来绰约省人事。终须等着个助情花,处处相随步步觑。”此处活用了唐代刘禹锡的《寄赠小樊》:“花面丫头十三四,春来绰约向人时。终须买取名春草,处处将行步步随”。春香介绍自己受老妇人指派,日夜跟随小姐,陪她理绣床、烧夜香。接着春香又念了两句上场诗:“年光到处皆堪赏(张仲素),说与痴翁总不和”,介绍迂腐的儒生家庭教师陈最良出场。上场诗多与宾白、曲辞混在一起,比较分散,形制与集四句唐诗为一体的下场诗有所不同。
下场诗一般是一出戏将要结束时,人物下场前的宾白,一般是四句“集唐诗”,作用主要是概括内容、预示情节和抒发情感等三个方面。
1.概括内容
概括内容颇有总结每一出戏曲情节的意味,通过下场诗将情节进行浓缩式提炼。如《劝农》(第八出)中的下场诗:“闾阎萦绕接山巅(杜甫),春草青青万顷田(张继)。日暮不辞停午马(羊士谔),桃花红近竹林边(薛能)。”诗与情节遥相呼应、珠联璧合。曲中杜宝所治之地,人口繁多,农事兴旺,景色优美。诗的第三句与杜宝在劝农过程中事必躬亲的行为对应,第四句描写的景色也与农家的自然风光相契合。诗歌展现的内容尽管不能做到像戏曲情节那么详细,但它更有助于意境的显现。曲中有大量对话穿插其中,使欣赏者的注意力集中在情节的进展变化之中。而用下场诗概括的手法,将景与情浓缩,既总结了故事,又使得故事在欣赏者心中得到一定升华,情节的主旨可以通过诗歌而得到咀嚼深化。
2.预示情节
预示情节也是下场诗在《牡丹亭》中的重要作用之一,《肃苑》《惊梦》《慈戒》《寻梦》四出可以看作是主人公杜丽娘情感发生质变的过程,这四出中的下场诗——“莫遣儿童触红粉”(韦应物)、“回首东风一断肠”(罗隐)、“素娥毕竟难防备”(段成式)、“从此时时春梦里”(白居易),把杜丽娘由不知情为何物到日日思春的转变以及情感波动的变化表现得淋漓尽致。《寻梦》中最后一句“一生遗恨系心肠”(张祜)与《慈戒》中杜老夫人“厮撞著,有甚不著科,教娘怎么”遥相呼应,预示杜丽娘情窦初开后必定遭受磨难,后来杜丽娘之死也契合了这一预示。对于长篇叙事性文学作品而言,合乎逻辑与情节暗示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牡丹亭》用下场诗预示情节,体现了诗歌的朦胧色彩,使得情节发展产生出既合乎情理又超出欣赏对象的意料,使各个事件的产生和发展有着紧密联系,故而今人徐朔方高度评价汤显祖的集唐诗:“诗句却同剧情吻合无间, 好像那些唐人特地为他预先撰写一样。”[4]2利用下场诗来预示情节,是中国古典戏曲的一个独特艺术手法,在《牡丹亭》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3.抒发情感
自古以来,“诗言志”与“诗缘情”作为中国诗论的两大理论源头,一直以来受到历代文人的推崇。每当文人墨客处于情感激烈变化又难以叙述的时候,往往通过诗歌来进行抒发,汤显祖在戏曲创作过程中继承了这一传统。
首先,抒发情感是表现人物特征的重要手段。“武林何处访仙郎(释皎然)?只怪游人思易忘(韦庄)。从此时时春梦里(白居易),一生遗恨系心肠(张祜)。”这是《寻梦》的下场诗。这出戏写杜丽娘在《惊梦》之后,去小院寻柳郎而不可得的情形。她不知折柳之人是谁,更不知其身在何处,因而抒发了“何处访仙郎”的感慨。作为一个至情女子,她因寻爱郎而不可得,在文本中感叹“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与“一生遗恨系心肠”相对应。《寻梦》的下场诗是一首抒情诗,它与预示情节、概括内容的下场诗是不同的,它更像是从作者口中自然抒发出来的,因而更容易突出人物形象,一个至情女子寻情郎而不可得的焦虑之情在这首下场诗中突出地体现出来。杜丽娘热情奔放,突破传统礼教,敢于为寻求爱情而赴死的品格在抒情诗中体现得更为立体化。
其次,利用诗歌来抒发情感,对于戏曲艺术来说更利于曲调的和谐优美。诗歌本身是讲求韵律的,而戏曲与韵律更是不可分割的。借用诗歌来抒情,既能集中表现情感,又可以展现戏曲的韵律,使得戏曲整体效果更加和谐。从文本角度来看,它不但使得戏曲雅化,使这种文学样式向正统文学靠拢,而且让更多的欣赏者尤其是阶层较高的群体得以接受。
二、《牡丹亭》对唐诗的文学借鉴
1.直接引用
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对前人诗词进行原封不动的引用,此谓“直接引用”,集中体现在每出戏的下场诗中。《牡丹亭》的下场诗以七言为主,以四句构成,且这四句诗分别出自不同诗人的诗句。如第七出《闺塾》中的下场诗为:“也曾飞絮谢家庭(李山甫), 欲化西园蝶未成(张泌)。无限春愁莫相问(赵嘏),绿阴终借暂时行(张祜)。”第二十三出《冥判》中的下场诗为:“醉斜乌帽发如丝(许浑), 尽日灵风不满旗(李商隐)。年年检点人间事(罗邺),为待萧何作判司(元稹)。直接引用是《牡丹亭》对唐诗借鉴的最广泛形式,作者能做到下场诗中的“集唐诗”不仅形式整饬、讲究平仄,而且简洁地概括了剧情内容, 预示了情节发展。
2.巧妙化用
巧妙化用是指作者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对唐诗稍加改动,进行再创作。文学创作的独特性就在于它的创造性,在借鉴前人成果的过程中要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不可为了模仿或借鉴而丧失个性,正如徐朔方、杨笑梅注本所说:“其中有一部分是作者有意加以改动的”。例如《牡丹亭》第一出上场诗中提到的“白日消磨肠断句,世间只有情难诉”中的第二句引自顾况的《送李侍御往吴兴》:“世间只有情难说,今夜应无不醉人。”将“说”字改成“诉”字,一字之改,在艺术表现上有着多样性变化,明显将读者和听众当作倾诉对象,将他们引入情境之中。随后,作者借情字来演绎柳杜二人的恋情,进一步阐述“至情”的具体表现。巧妙化用的结果使得欣赏者与情节紧密相联,只有增强作品与欣赏者之间的对话效果,才能够更容易感染欣赏者,调动欣赏者的情感体验。
还有一种化用,就是对原诗进行改写,但其主干仍然依托原诗框架,尽可能用最简洁的词语道出最想表达的内容。例如《牡丹亭》第四十四出中的“明月桥上听吹箫”改自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从情节来看,杜丽娘在柳梦梅赴试前夕希望其能够登科中举,早日归来团聚。“明月桥上听吹箫”从杜丽娘口中说出,实则表达出杜丽娘隐隐的担忧,劝柳郎莫贪图外面的富贵与繁华,要坚守住两人来之不易的爱情。可见,在改写过程中,作者抓住了诗歌最精华的部分。“明月桥上听吹箫”是一种享乐情景,直接将享乐情景道给柳梦梅,借以暗示其不可辜负“至情”,同时也给欣赏者传递出一个具体画面,便于理解与想象。化用诗歌来表达思想情感,使得情感富有境界、更为充实,同时话语更为凝练,且富有艺术美感。
总之,巧妙化用唐诗是《牡丹亭》独特的创作手法。如果说直接引用体现了作者在诗歌积累方面的能力是惊人的,那么化用诗歌则突出了作者对古代文学遗产运用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做到了游刃有余。
三、结语
《牡丹亭》是部传奇,诗歌作为戏曲重要的语言表现手段之一, 以服务于戏曲内容为主要目的。汤显祖在剧中不仅大量引用、化用唐诗,还有少量自己的创作,并在诗中用典。第十三出中的“家徒四壁求杨意,树少千头愧木奴”,前一句用杨意提携司马相如的典故,流露出柳梦梅希望有贵人相助;后一句用三国时期李衡将一千株橘树留给自己儿子的典故,表现柳梦梅正处于人生十分失意的时期,在为理想而苦苦挣扎。诗中用典,在内容与意境上更符合《牡丹亭》的剧情与戏曲风格, 增强了剧作的感染力,使得《牡丹亭》比其他“本色”的传奇更为文雅。[5]
汤显祖在诗歌运用与戏曲创作这对雅俗矛盾中一直进行着灵活多变的双向互动。一方面,作者为了提高俗文学的审美效果和地位,将中国文学中雅的部分——诗歌引入戏曲创作之中,由俗入雅,使得戏曲能够受到更多、更高的阶层关注;另一方面,作者为了照顾戏曲的特殊性,保持其通俗的个性,在诗歌引用中进行巧妙化用、适当用典。雅俗双向互动一直以来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它的目的在于使文学创作适应时代和大众的审美需求。可以说,没有读者的接受便构不成一个完整的文学活动。
中国传统戏曲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戏曲,对传统文学的继承是增添其艺术价值的重要手段。继承与创新一直以来是文学发展的永恒话题,对优秀文学传统的继承是文学民族性的表现。《牡丹亭》大量引用传统诗歌,使得俗文学雅化,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著名作家白先勇一直致力于昆曲《牡丹亭》(青春版)的弘扬与传播,在海内外受到广泛好评,《牡丹亭》的魅力可见一斑。
[1]孔尚任著,王季思等注.桃花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2]毛效同.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吴凤雏.关于《牡丹亭》中的“集唐”诗[J].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4]徐朔方.汤显祖全集·前言[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
[5]黄斌.略论《牡丹亭》中的集唐诗[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