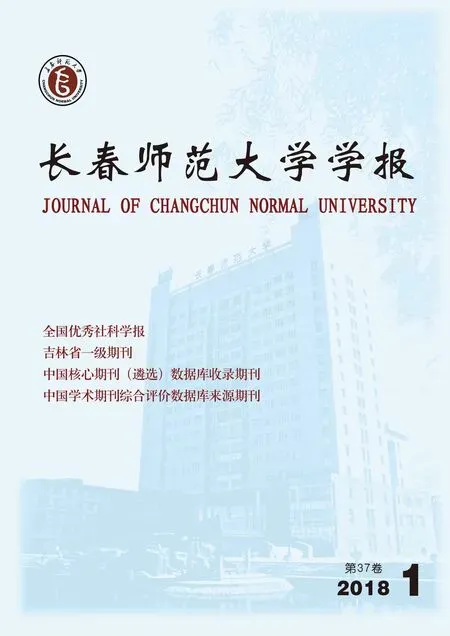“他者”之声
——美国华裔女作家的身份书写与嬗变
2018-03-29黄燕丽
黄燕丽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外语系,广东 东莞 523000)
当代美国华裔女性文学,是多元文化语境下东西方文化碰撞和融合的产物。作为美国白人主流、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是男权社会的“他者”,美国华裔女性的多重文化身份使她们在整体上更具有强烈的文化感知和身份危机意识。20世纪以来,一大批华裔女作家在美国文坛崛起,她们以文本叙事方式多方面地展现了华裔女性在美国社会的生存遭遇和身份追寻。可以说,美国华裔女作家的创作历程,就是她们在文化、族裔、性别意识中自我身份从迷惘、失落、困惑到重构自我、寻找自身价值的再觉醒过程,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发展脉络。
美国华裔女作家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和流动性,使其身份处于变动中,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不同时期的女作家对身份认同和主体建构的策略和态度各不相同。目前国内对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研究大多局限在某个主题或某几个作家的文本,而整体、动态地考察华裔女性生存处境和主体意识衍变的研究较为缺乏。鉴于此,本文通过对20世纪以来最具代表意义的美国华裔女作家及其作品的分析、梳理和总结,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以期在横向和纵向分析中简要地勾勒美国华裔女作家从“边缘”到“中心”的身份书写与嬗变轨迹。
一、早期的移民认同:流散者的困惑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经历了从被“他者化”、被“边缘化”到逐步迈入“主流”和“中心”位置的曲折而动荡的发展历程。整个进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被大多数评论家认为是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开创阶段。这一时期的华裔女作家大多采用自传形式,通过记载少数族裔女性在美生存现实和精神困境来再现和确认自我身份。水仙花和黄玉雪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作家。
艾迪斯·伊顿以独具东方格调的“水仙花”为笔名,于1912年发表了短篇文集《春香夫人》,记录了19世纪晚期华裔移民在美的血泪史,被视为美国华裔文学的开山之作。在那个仇华、排华情绪严重的年代,水仙花是第一个用英语写作的华裔女作家。她笔下的春香先生是一个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成功商人,这与当时猖獗的“黄祸”文学中描绘的愚昧、落后、缺乏教养的华人刻板形象大相径庭。写作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表述,“身份和他性都包含在并通过叙事来传达”[1]122。作为对抗白人霸权统治的一种策略,水仙花通过作品挑战和颠覆了当时宏大的帝国主义叙事背景下丑化华人的传统书写模式,为“西方看东方”提供了一种崭新视角,有意识地展现出华人文化的优势,以此表明她为被排挤、被边缘化、被妖魔化的华裔群体正名和抗争的强烈愿望。
当然,水仙花的创作意图具有明显的个人立场和倾向。她笔下的华人形象多是正面的,而白人是负面的,两者是一种对抗关系的呈现。徘徊在两个世界和两种文化之间,她的混血身份(父亲为白种人,母亲为黄种人)让她更具有跨国界、跨种族的思考,但同时又让她产生无所适从和无归属感——既受到主流文化的排斥,又和中国文化有着时空、文化以及种族距离。两者对她而言是撕裂的,是二元对立的存在。因此,从她带有自传性的创作中,我们清晰地感受到当她寻找自身定位时,她选择了华裔作为自己的身份和立场,这是她个人主动的选择。但在一个非“白”即被归为“异类”的时代背景下,她又不能自由地探寻自己的身份,这显然是视华裔为“他者”的主流文化立场决定的。因此,她身上充斥着矛盾、挣扎和无奈,她所构成的东西却不是个人所独有的,而是一种身份政治,是建立在对一个群体需要的肯定上作出的一种无奈选择[1]123。
由于历史、政治等多方原因,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忽略,而其真正被重视是在二战之后,黄玉雪的《华女阿五》(1945)尤为重要。《华女阿五》作为华人在美个人奋斗的典范被广为阅读,是一部反映华裔女孩玉雪在成长过程中遭遇到中西方文化冲突的痛苦,以及如何摆脱中国传统文化和家庭束缚,逐渐认同美国价值观,最终依靠自身奋斗走出唐人街并成功融入白人主流社会的自传体小说。黄玉雪也因此被评为“模范少数族裔”的代表。有诸多评论家认为,《华女阿五》之所以在美国被认可,一方面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符合美国人的基本信仰和核心精神——只要努力奋斗和抓住机遇,移民也能实现“美国梦”;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不自觉地迎合了白人的猎奇心理——黄玉雪在文本中穿插了大量关于中华文化和习俗的描绘,从中华饮食文化到婚丧嫁娶风俗,从唐人街的日常到中国陶艺,各种极具浓郁中国色彩的场景描写无不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东方的神秘、封建甚至落后、愚昧的偏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西方的文明、进步、开放和优越。读者从中不难看出作者对美国的理想化态度。对此,我们应该对黄玉雪所采取的边缘写作策略进行多维考量。
首先,作为华裔作家,其作品在美国发行,读者为美国白人,因此黄玉雪在写作中要考虑诸多因素,使作品打入主流话语。虽然出生在美国,黄玉雪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长大。她想通过创作来宣传中国文化,但同时她对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持怀疑和否定态度。为了融入主流,她在写作中将中国文化落后的一面以“偏颇”的方式呈现给西方读者,利用中国文化来建构自己独特的身份,事实上她不自觉地成了“新东方主义”的同谋[2]。
其次,作为流散在他乡异国的华人,想要在美国主流文化为绝对主导的语境下改变被隔离的状态,很大程度上必须通过自我调节和克制的方式接纳美国的价值观和依附白人的文化,这正是包括黄玉雪在内的华人所付出的代价。小说中玉雪的个人奋斗史和梦想的实现是建立在美国价值体系和衡量标准上的,而她与父母的冲突,从深层次来讲,“正是美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抗和后者被前者征服的过程”[3]。 实际上,她在潜移默化中已经被美国的价值观内化,选择迎合白人对华人——“他者”的身份规约,从而放弃少数族裔的固有族性,疏离构成自我的故国文化。如同水仙花一样,黄玉雪的身份认同表现出的分裂和矛盾不仅是个人认同的自我选择,更是社会认同强加于个人的选择,是二元对立思维内化的结果,是一种无奈的认同。这正显示了早期第一代华裔女作家身为流散者的困惑。
二、20世纪中期的主体建构:文化夹缝中的觉醒
20 世纪中期,随着民权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华裔妇女的生存状况有了一定改善。在追寻自我的道路上,在美国出生成长的第二、三代华裔女作家不再像早期的水仙花、黄玉雪那样仅仅希望通过调整自我来迎合主流文化以获得身份认同,她们不仅关注华人在异国的生存境况,还以女性的独特视角探讨族裔、身份、性别问题。她们在作品中着重表述作为白人和男权社会中的“他者”——华裔女性的独特历史感、身份观、性别意识以及对文化归属等问题的思考。汤亭亭、谭恩美是其中的代表。
汤亭亭被公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负盛名的华裔女性作家。她的处女作《女勇士》被许多评论家誉为“华裔女性文学的里程碑之作”,被克林顿总统褒奖为“一部划时代的巨著”,这部作品的问世更意味着美国华裔文学从觉醒走向成熟阶段。《女勇士》讲述了一个在两种文化夹缝中成长的华裔小女孩的童年生活及其周围女性的遭遇。作品通过五个独立篇章的故事熔美国华裔受歧视、受排挤的生活现实与中国的灵异鬼怪、仙风道骨、民族女英雄的神话于一炉。汤亭亭以细腻的笔触、芜杂的叙述以及神经质的呓语,表达了对旧中国妇女命运深切的同情和对父权社会的控诉。就文化归属而言,身处双重文化宰制下的汤亭亭比早期的华裔女作家更复杂。一方面,她对母亲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当程度的认同感——她“以主流社会的语言(英语)来运用/据用、转化、改编、重组甚或扭曲主要是听自母亲的、具有异域色彩的‘故事’”,从而完成了《女勇士》的创作[4],并在故事中获得了力量,通过个人成长过程中所遭遇到的诸多考验。另一方面,她又表现出与传统文化中的守旧、落后等观念和行为的疏离感甚至是鄙夷感,因而她笔下的人物属性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既不归属于中国传统,又不完全是被同化了的美国形象,而是杂糅、多样、兼具中西的混合体。比如《女勇士》中的“白虎山学道”一章,汤亭亭将中国传说花木兰、岳母刺字和西方童话《爱丽丝漫游仙境》的情节并置,塑造了一位刚柔并济的女勇士,颠覆了美国主流文化中华人女性的形象。至于女性身份认同问题,从作品中关于“失语”的无名姑姑、含蓄隐忍的姨妈月兰等人物的描写便可看出,汤亭亭无法接受中国旧社会施加于女性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精神枷锁。她的书写行为本身就违抗《女勇士》中母亲“不许说”的禁令,她借由这种违抗行为来挣脱中国传统父权和白人主流社会的桎梏并肯定作为女性主体的自我。整部小说可以被视作女性“从被迫失声到‘报复/报导’的飞跃,一次从‘沉默’到‘歌唱’的羽化”[5]。
汤亭亭对身份和认同的关注没有限于性别,而是上升到了族裔层面。她之后创作的《金山勇士》《孙行者》等作品都致力于建构美国社会语境下有别于主流社会的华裔移民对抗性历史,具有浓重的族裔和历史内涵。就作者本人而言,汤亭亭在多个场合申明自己是一个美国作家,她甚至主张去掉“Chinese- American”的连字符,从而强化华裔的美国性[6]。在《孙行者》中,她通过创作阿新这一兼具中西文化精神的混合体去打碎华裔的定势形象,试图构建一个超越种族的全新族裔文化身份。由此可见,作为“他者”,汤亭亭的身份诉求过程不再是二元对立的分裂,而是一个中西兼容、混杂并置的过程。她所采取的这种差异书写策略对后来的谭恩美等人影响深远。
被誉为20世纪美国少数族裔作家群里的“另一位开拓者”的谭恩美,其主要作品《喜福会》《接骨师之女》《灶神之妻》等都是通过母女关系的主题揭示中国移民的母亲们和出生在美国的女儿们在双重压迫下的遭遇及其反抗意识,其作品反映的离散与寻根、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自我身份的归属、女性主体构建等问题备受关注。尤其是在对美国华裔新女性的刻画中,谭恩美的女性主义思想深度更为突出。她笔下的母女冲突与汤亭亭的《女勇士》中代表美国文化的女儿要同化代表中国文化的母亲是截然不同的。比如在《喜福会》中,出生在中国的移民母亲起初都认同男尊女卑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但是最终她们都理解了女儿们作为“边缘人”的痛苦并毅然选择为自身利益奋起反抗。而女儿们在成长过程中,从不理解甚至是排斥到逐渐懂得自己和母亲冲突的深层次原因,最终她们认识到“华裔美国人是典型的美国人,而典型的美国人都是杂种人”[7],在自己的身份确认中必须融入中国文化元素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
谭恩美的作品深刻反映了当时美国“大熔炉”的文化理念和中国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比如,在《喜福会》中,她融合了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叙事模式、“麻将理论”和西方的“四季理论”等,颠覆了中国传统女性形象,描述了东西方文化从相互否定、质疑直到逐渐妥协、理解和包容的渐进过程。小说以女儿回到中国寻根结尾,表达了作者的美好愿望:创造一个求同存异、兼容并包、和谐共存的社会。这种意识消除了东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两种文化的融合也使移民两代人摆脱了身份危机。从这个角度来说,谭恩美的作品对华裔女性自我身份的认知和构建显现出更深刻的内涵和更为清醒的认知。
可见,汤亭亭和谭恩美等第二代华裔女作家通过书写积极参与华裔文化构建而不是默许被异化被排斥的华人刻板形象,并用开放的姿态挑战美国文化进而构建自身的身份认同,不失为后殖民时代少数族裔的一种有效身份诉求策略。
三、晚近期的身份观:流动中的融合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当代美国华裔女作家不断改善的生存状况、文化反思以及不同的文化适应性,使她们的视野变得越发开阔。她们的作品从寻找族裔身份的认同逐渐转向普世审美价值的追求,面向更为复杂、多变、动态的历史、文化、族裔、人际和信仰问题,从而形成对多元文化语境中美国社会的独特揭示和新的思索。汤亭亭《第五和平之书》、谭恩美《拯救落水鱼》等新作着重艺术性探讨,关注普遍的人性诉求,从较单一的传统层面扩展到更宏观的多元探索,带领新一代华裔女作家开启更多元化的创作尝试,促使华裔女性文学走向蓬勃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女作家,其中任璧莲是最受瞩目的一位。
以往的华裔女作家,从水仙花、黄玉雪到汤亭亭、谭恩美等人,她们把身份定位为游走在族裔文化和白人主流文化之间,因此她们有意无意地从中国神话故事中寻找素材。任璧莲则在作品中刻意淡化族裔身份的烙印,隐去中国符号,更多地关注中美文化冲突与融合下作为“个体”的华裔对中西方价值观、思维模式、伦理观念等方面的思考。在创作主题上,任璧莲对族裔身份的认识发展得更加多元化,她的作品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对华裔历史与族裔根性的超脱感。在代表作《典型的美国佬》中,她把小说中的主人公华裔移民拉夫尔·张追寻美国梦的经历看作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体现实经验,而不仅仅是涉及某一特定族群的身份和意识形态,进而从外在的美国文化角度重新审视“大熔炉”理念下“典型美国人”的定义,提倡建立“色拉碗”模式的多元文化国度。因此小说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这是一个美国故事”。在随后的一系列创作,如《莫娜在希望之乡》《谁是爱尔兰人》《世界小镇》中,任璧莲始终把主题集中在反映普通人在多元文化的美国社会中的自我奋斗和抉择,从而完成了当代华裔女性文学族裔性主题的转型。就人物塑造而言,任璧莲认同族裔属性的流变,她认为族裔性并非一成不变的、封闭的,而是浮动的、多重的;不是单面向的,而是具有内在复杂性的。她笔下的人物主要是知识分子华裔移民家庭,大多数具备高学历,能说一口地道的英语,而且具有“想成为什么,就成为什么”的美国精神特质,这是在流动过程中华裔美国人的内在变迁。此外,她的作品突破了以往拘泥于华裔的故事,将其探讨对象扩展到爱尔兰裔、非裔、犹太裔等少数族裔。不同种族背景下的人物在美国多元化社会中产生的各种冲突、矛盾和情感关系,正是任璧莲对不同族裔、文化和信仰之间关系以动态形式进行探索的尝试。从这一点上看,“跨越孤立的华裔身份而步入更加广泛的种族身份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已成为任璧莲的突出创作特点”[8]。它超越了以往华裔文学作品对单一族裔的呈现,并试图解构华裔身份建构的公共性,这种“反本质论”的意图也是作者本人文化身份书写的一种标签。
在叙事语言方面,美国少数族裔作家深受“美式幽默”的浸淫,而这也正激发了他们的族裔意识,从而创造出了自己独有的幽默形式——“金色幽默”。任璧莲的叙事策略由批判的写实主义转向现代主义的金色幽默,对反讽、暗喻等技巧的娴熟运用构成了其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因而被称赞为一个“善于运用金色幽默彰显华裔美国人生活光明面的作家”[9],这正好呼应了后现代语境下华裔文学的美学价值追求。
诸多因素的交互反应和不断变化,模糊并颠覆了族裔文化相对稳固清晰的界定。这一动态建构事实上是对第二代华裔女作家塑造风格的一种延续与变革,也预示着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发展的新方向。
四、结语:多元文化语境中华裔女性文学的发展和启示
回顾20世纪初以来美国华裔女作家身份书写大致经历的三个阶段,可以发现其表现形式虽然迥异,但都是少数族裔在东西方文化冲突、自我与“他者”的对立中或隐或显地抗争的真实反映。美国华裔女作家笔下的人物及其自身对身份的诉求与认知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嬗变。近年来,涌现了一批“80后”华裔文坛新锐,如伍琦诗、鲍嘉璐等,她们作品的个性化越趋于鲜明,其主体意识更强,内容关注的不再是狭小的华裔世界里的中国故事,而注重以个人日常感悟和经历为灵感,用独特的笔调展现当代华裔美国人的精神生活状态、人文关怀等,主题已经远超出文化认同的范畴。不管是哪种文本叙事方式,都反映了当代华裔女性族群对自我存在和身份认同进行的深刻思考。随着华裔女作家对美国社会的进一步融入以及现有队伍的新陈代谢,新时期的华裔女性文学势必呈现出更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总的来说,不同语境促成了美国华裔女作家不同的身份选择和变迁。华裔女作家的文化身份研究为我们反思中国文化传统、审视多元化语境中不同文化的交往带来了新的启示,使我们对民族文化、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因此,我们在关注当代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发展时,应当同时关注文化全球化趋势影响下华裔文学审美价值和格局的新变化。
[1]Julian Wolfreys.批评关键词:文学与文化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陈爱敏.流散者的困惑——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的母亲形象解读[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12).
[3]阎瑾,杜军.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身份构建[J].求索,2012(3).
[4]单德兴.“开疆”与“辟土”:美国华裔文学与文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4.
[5]金莉.20世纪美国女性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60.
[6]Maxine Hong Kingston.Cultural Nis-readings by American Reviewers, Critical Essays on Maxine Hong Kingston[M].New York: G. K. Hall,1998.
[7]单德兴,何文敬.文化属性与华裔美国文学[M].台北: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1994:167.
[8]刘婷婷.从《典型美国人》看华裔美国文学创作的新动向[J].江苏外语教育研究,2000(2).
[9]王建新.“金色幽默”:试论任璧莲《典型的美国佬》的叙事策略[J].长春大学学报,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