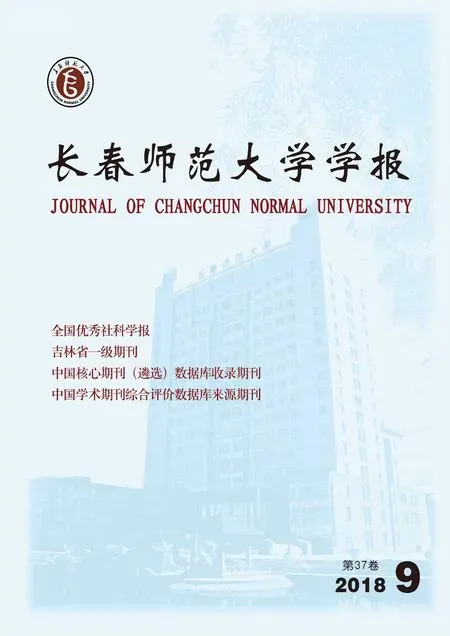从《中国文化要义》透视中国文化的内在延续性与同化力
2018-03-29朱静
朱 静
(长春工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人文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他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学思想和西方的“生命哲学”汇聚一起,而《中国文化要义》是他“认识老中国”的思想结晶。他认为中国文化既是人生意义问题与民族问题前途问题的根源,也是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关键在于要如何认识这种文化。“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通过文化的复兴”[1],基于这样的观点,他首次赋予中国文化以世界的形式,将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体系中考量。
一、西方文化映照下的中国文化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内涵深、外延广,其中包含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单指理论问题,更涉及诸多实践内容。“我们现在放眼去看,所谓的东西文化的问题,现在是怎样的情形呢?我们所看见的,几乎是世界上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欧美等国完全是西方化的领域,固然不必说了。就是东方各国,凡能接受吸纳西方文化又能运用的,方能使他的民族站得住;凡是来不及领受吸纳西方化的即被西方强力所占领”[2]。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有足够的资格同西方文化对话,但在100多年前的中国,“天朝大国”的美梦已经彻底破碎,它所暴露出的落后、陈腐气息已经将悠久历史文明散发出的书香气完全掩盖。面对这样的现实,部分中国人失掉了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信心,提出“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部分人则看到了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迸发出的力量;还有一部分人坚信中国文化不仅能够拯救这泱泱大国,也能拯救世界。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发生了激烈的交流、碰撞。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对时局变化进行了深入思考,普遍认为中国人需要在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发挥中国文化优势的同时学习先进的西方文化。
乡村建设一直是关乎中国发展的重要问题。在梁漱溟看来,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一个具有东西方文化长处的乡村自治组织的形成是实现中国乡村改造的初级阶段,中国传统乡村文化里的“宗族”“乡约”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独有的“理性”特征,而西方文化中的“科技技术”“团体精神”等思想是中国文化中所缺乏的。他从中国古代的“乡约”中看到社会救济、社会保障社会化的可能性,社会救济、社会保障实际是宪政条件下地方自治的基础。民国以来,国家的立法精神以及国家政权的机构设置开始“西化”,国家政权开始了自身的现代化步伐[3]。这些做法符合西方的法治精神,但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伦理本位”思想。要克服西方嫁接思想的水土不服,必然要因地制宜地加以改造。梁漱溟倡导将知识分子的文化知识融进乡村治理中,带动乡村文化建设,促成新型的乡村政治形式,协调乡村人际关系,以科学技术带动经济进步。依此而言,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中国文化向现代化延续,最终实现中国文化与时俱进的一次有效尝试。
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是什么?梁漱溟认为在于文化浸润下人们的人生观。他说,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为根本精神的,中西文化有全然不同的内在发展逻辑。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将对中国往后的发展提供持续且难以代替的重要价值。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如果没有认识本质,而只是观赏西方文化的外表,那对推进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不会产生丝毫助益的。“民主”“科学”思想作为西方文化的精华,对中国影响十分深远,即使在今天国富民强的中国也在四处回响。
二、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意蕴
在与西方社会进行对比后,梁漱溟得出了中国社会的特征。中国社会首先表现为伦理本位。“伦者,伦偶;正指人们彼此相与。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中国人的生活,即一向倚重于家庭亲族间,到最近的地方开始趋向于超家庭的大集团:因亲其亲,因友及友其路仍熟,所以遇事总喜托人,你若说公事公办,他便说你打官腔。法治不立,各图侥幸,秩序紊乱,群情不安”[4]。这种伦理本位思想是中国独有的一种特殊意识样态。在西方文化中,个人利益通常被置于首位;而在中国,家庭往往作为社会生活的核心单位而存在,并且家庭一直是社会伦理关系的发端。费孝通先生曾用“差序格局”来描绘传统中国社会的人际交往形式,这种形式也成为中国几千年家国同构的原因。
中国社会还表现为以道德代替宗教。梁漱溟先生认为,“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4],基督教强大的维系功能使得教徒们过的是“集团生活”,这种形式的生活经过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启蒙运动、人权宣言的加工,形成了民主的风气,也成为民主思想的根源。中国社会中也存在原始的宗教,但是经过演变,成为了统治教化的假借工具。中国有“尊天、敬祖、崇德报功”的宗教形式,但其实际内核是儒家思想,是以道德代替宗教。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理性价值思想,成为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导向,当然仅仅借助道德这种单一手段妄图治理国家是不现实的。
此外中国社会循环于一治一乱而无革命。纵贯中国历史,自秦汉以后天下确是在兴衰往复中来回循环,而“革命是指社会之改造,以一新构造代替旧构造,以一新秩序代替旧秩序,像资本主义社会代封建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代资本主义社会那样”[5]。原有的社会结构长久存续,社会实质并无变革。社会结构如果不发生改变,那么在整个社会运行中出现问题就根本找不到解决的良方。
三、社会学视角中的社会系统变革
从社会学视角看,社会系统发生改变是由于经济、政治、文化作为影响因子相互作用而实现的,这些影响因子对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变迁具有决定性影响。只有社会系统内部保持长时间的均衡运动才能够保证社会的稳定。这些因子犹如一个个节点,一旦有一个脱落,整个运行链条就将崩断,社会要实现变革就很难实现。当然运行中所产生的波动也需要被限定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中,否则任何不确定因素的介入都会导致意外发生。
中西方的社会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中国社会中并没有阶级对立,只有职业选择的不同。在中国古代,政治环境较为开放,官僚阶级更多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拨,分封建国在秦始皇时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人人各奔前程,鲜有集体合作,既不必相谋,亦复不相碍”,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农民、工人、商人,即便没有明设的考试制度,但是仍然能“行行出状元”,有本事可以尽情表现,白手起家处处可见,阶级结构分散加之当时的土地所有权相对分散,所以梁漱溟认为只有职业不同而没有阶级对立存在。梁漱溟认识到当时社会问题之根本,倡导“建立一种新秩序”,寻找一条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发展之路。
除此之外,外部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也会对社会变革产生重要影响。资本主义是在什么时候发挥出巨大影响力的呢?是在欧洲航海者的地理大发现及资本主义革命发动之后。资本主义现身,现代化也就尾随而来。所以,从更实际长远的角度来讲,只有通过中西文化交流,中国文化才能在参与中融入到世界现代主义潮流中。梁漱溟一直提倡以儒救世并被人视为“最后的儒家”,他却始终自认为是一个佛教徒。无论如何,梁漱溟这一关于人类发展的构想是超出了同时代人对中西文化差异那种二分式的僵化对比框架的。他所阐发的中国文化的核心要义也不单单是从时间或空间观念上进行简单的附和或排斥,而是需要持续学习、不断发问。
四、中国文化的延续性与同化力
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其特殊的生长土壤,而作为整个文化民族的历史积淀,它所包含的延续性和同化力在世界范围中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统一、同化的力量,首先来自人生态度礼俗信念、宗教观念等价值观层面的内容,还包括经验技术方法,比如文字、语言、科技手段等。在中国历史上,周边的少数民族多次入侵中原,元朝、明朝时中原地区被少数民族长时间入主,中华民族统治少数民族使其归顺也是常有发生。当中原人用中原文化统治少数民族时,中原文化能够迅速将少数民族的文化同化融合;而少数民族统治中原时,因现实原因不得不采用中原文化进行统治,所以自然而然地吸收了中原文化,最终被中原文化吸收。作为统治阶级的文化为什么让被统治阶级的文化同化了呢?一方面,中原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另一方面就是因为中原文化的先进性与少数民族的文化相比其先进性是不可比拟的。文化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必然要摒弃落后陈腐,吸纳先进优秀。
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对外影响力。亨廷顿说过,上帝与皇帝、教会与国家、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在西方国家始终是二元对立的。在西方社会,人类文化更多是以宗教为开端的,社会秩序的形成、思想学术的启蒙都源于宗教,科学技术也是精确、系统的。中国人的宗教观念不强,所以缺少宗教的束缚,较为通达开明。西方经常有宗教争端,各个教派之间壁垒相对;而中国讲究“和为贵”、协同合作,人有人交往有融洽相处的前提条件,人人信守,根植于心。同时,中国文化主张“仁者爱人”、“仁厚有容”、物我两忘、与世无争,这种中国式的“理性”所蕴藏的兼容并蓄与和谐合理,时时处处体现着强大的文化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