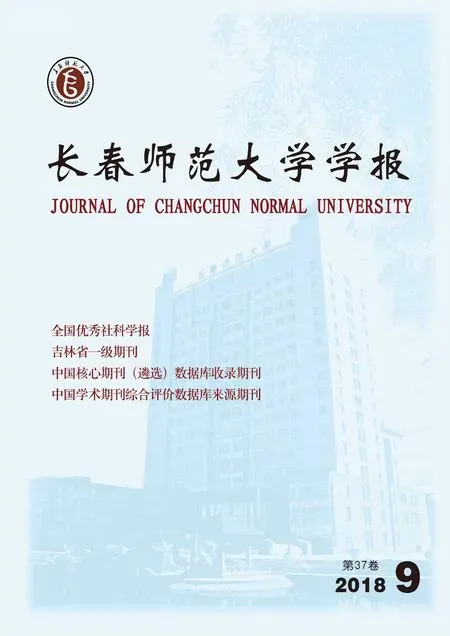论台湾生态散文对中外文学的借鉴
2018-03-29陈想
陈 想
(1.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2.福建师范大学 两岸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 350007)
在大自然中,人类长期扮演着征服者的角色。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化工产品被大量使用,随之而来的是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大量生物走向灭绝。人类终于开始认识到:征服者的角色不属于自己。环境教育作为解决生态问题的重要措施,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台湾生态散文正是在该地区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的背景下孕育而生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出现了一类富有特色、值得关注的散文——生态散文。经过三十余载的发展、积淀,台湾生态散文已结出丰硕的“果实”。然而,任何一种文类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台湾生态散文的产生、发展与既有的文学类型、书写题材等都具有或隐或现的关系。无论是中国古典山水田园诗、明清时期大陆文人的台湾游记,还是台湾地区的方志书写、日据时期日本博物学者的踏查报告,抑或是欧美国家的生态文学作品,都对台湾生态散文的产生、发展等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一、中国古代的自然书写
台湾生态散文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自然书写(以自然为书写对象的文章)在主题、情感等方面有一定的差异,但中国古代文学中对自然的描述和对自然的情感,在台湾当代生态散文中都得到了延续。
首先,山水田园诗是一类以自然景物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古典山水田园诗中的自然景物往往是作者自身思想情感的投射物,带有作者主体的情感特质,对描写的景物少有科学探究的态度。但是,诗中生动形象的景物描写十分深远地影响了台湾生态散文作家对景物的描绘。
其次,虽然诗人在创作山水田园诗时还没有自然科学知识和环境保护意识(古人自然不知何为“自然科学”、何为“环境保护”),但一些诗人早已有了生态环保思想和生态和谐观念,他们创作出来的山水田园诗中的景物的宁静、人与自然间的和谐、作者的超脱之情等与现代生态散文呈现出的自然界的和谐共生所差无几。事实上,还有一些文章虽不以自然为书写对象,但生动地传达出了中国古代文人对“顺天而行”(《周易》)、“不违农时”(《孟子》)、“以人为本”(《管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资治通鉴》)等的透彻理解与高度重视。
再次,中国古代游记文学,特别是《徐霞客游记》对地质地貌的记录、对自然山水的描摹及其体现出的对大自然的尊重、热爱与赞美之情等,无疑对当代台湾生态散文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然,最值得一提的,要数明清时期大陆文人的台湾游记。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大陆人民对台湾地区的自然地理、历史风貌、民族风情等所知甚少,也缺少必要的关注。明万历年间,陈第随攻打倭寇的沈有容将军到达台湾,后以其自身游台的经历撰写了《东番记》(1603)。这是“我国记载台湾情状和台湾先住民生活习俗的最早的一篇文献”[1],完整的原文已不复存在,现有的残篇还不到一千五百字[2],但为后人了解三四个世纪以前的台湾少数民族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东番记》的出现表明大陆文人早在明朝时期就开始对台湾进行关注。此后,中国古代文人撰写的台湾游记逐渐增多,如郁永河的《裨海纪游》、蓝鼎元的《平台纪略》和《东征集》、黄叔璥的《台海使槎录》、姚莹的《东槎纪略》等[3]152。其中,最被世人所熟知的是《裨海纪游》,2010年和2011年的“普通高级中学必修科目‘国文’课程纲要”都将其纳入在“酌选文言篇章”里。当然,《裨海纪游》在国文教育中拥有较高地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因为其在文学、美学、考据等方面的优势——为学生了解台湾地形地貌、动植物、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材料;二是因为台湾教育对本土的重视——主要体现在《裨海纪游》是记录台湾古代自然和社会风貌的重要作品。
二、台湾地区的方志书写
除了中国古典山水田园诗和明清时期大陆文人的台湾游记,台湾的“地方志”也为台湾生态散文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文献准备。
地方志内容丰富、分志众多,是研究社会、历史、文学等的重要资料。地方志中的“地理志”(又称为“疆域志”或“舆地志”)主要记载当地的山川河流、名胜古迹等[4],无疑为生态散文书写者展现了未能亲见的自然地理和人文风貌。根据方豪的考证,台南人王喜所撰的《台湾志》是台湾第一部志稿,但此稿已经散佚。因此,现存台湾方志中最古老的要数高拱乾修、王璋纂的《台湾府志》[5]。此后,台湾的地方志不断增加、修补,有《诸罗志》《凤山县志》《台湾县志》《苗栗县志》等。地方志多为本地人所撰写和修订,因而具有较强的真实性。不过,也有一些作者不具有实际踏查的经验,他们撰写的地方志大都是从其他书籍中抄录而来的。台湾本土的方志书写一直在发展,且不断细化,内容愈加丰富。如由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的《台湾省通志》就专门设了“植物篇”(被归入分志之“土地志”),十分详细地介绍了台湾植物的生存状态、研究历史及台湾各类植物的外形、产地、用途等,为生态散文书写者了解台湾的各种植物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资料来源。
台湾地方志作品展现了台湾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的各个方面,对台湾当代生态散文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自然资料的提供。如前所述,台湾地方志的内容较为完整地记录了台湾各个时期的自然状况,这些第一手资料共同组成了台湾自然环境的变迁史。而且,地方志多有图鉴。相对于文字来说,该类资料更直观、形象,克服了文字无法准确表达某些内容的弊端,为后人理解先人的著述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是台湾当代生态书写者了解过去自然生物、人文地理的最佳材料。当代生态散文书写者只要善于搜寻,就能从中找到有用的资料。
第二,故乡情感的积淀。生态散文的兴起大体上有两个原因:一是作家的关注点转向了本土,二是地方志中流露出的故乡情感与生态散文作家对自然(家园)的情感相契合,对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深得他们的喜爱,并成为他们创作的情感动力。这些作家不仅包括本土作家,还包括身处他乡但时常回望故土的作家,如洪素丽等。
第三,相处模式的借鉴。台湾诸多的地方志中都记载了台湾少数民族的饮食、服饰、样貌、分布等状况以及因移民者对台湾少数民族的入侵而改变了的自然景观。这可以让生态散文书写者对特定族群与自然之间的相处模式进行思考乃至借鉴,还可理解自然环境受到人类(特别是移民者)的冲击。
第四,书写主体的培育。在地方志编写的初期,书写者主要是政府官员或官派人员,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松动、社会的发展,民间知识分子也参与到了这支编写队伍中,为之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该支队伍包含了后来完全转向生态散文书写的作家,也包含了“两条腿走路”、兼写生态散文的文人。因此,台湾地方志在发展过程中为台湾生态散文培育了书写的主体。这不仅使台湾当代知识分子积极投入到生态散文的书写中,也使台湾知识分子以一种更为亲近的方式体察乡土。
三、日本学者的调查报告
甲午战败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割让给了日本。日据时期,西方和日本的众多博物学者被台湾多样的气候、繁多的生物所吸引,来到了台湾。他们给台湾带来的既是帝国主义霸权的深入,也是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不同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交锋。当时来台的外籍人士除了殖民政府的官员及家属外,主要有三类:一是随外国势力一同进入台湾的官员或官派学者,他们几乎将台湾视为物产丰富的殖民地;二是传教士;三是对台湾颇感兴趣的探险家、学者,他们大部分拥有专业的知识,对台湾当代生态散文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日据时期,日本的一部分博物学家应政府的要求而来台,另一部分学者因对台湾有浓厚的兴趣而来台。他们对台湾的人文与自然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类学、植物学、动物学等。1911年,“台湾博物学会”在台湾创办日文教育学术类杂志《台湾博物学会会报》[6]。除专门的杂志外,还有日本博物学者撰写的踏查报告和研究专著,如伊能嘉矩的《台湾文化志》《台湾踏查日记》等,对台湾少数民族的分布、文化、生计、墓葬、时空概念等进行了十分详细的研究。植物学方面主要有早田文藏的《台湾高山植物志》《台湾植物图谱》等。[3]178-179这些作品对台湾文人的影响不容忽视,甚至有台湾作家称“这些留下来的日文文本至今仍被我们这世代奉为对那个时代自我理解的知识圭臬,譬如伊能嘉矩的台湾民情踏查、鹿野忠雄的台湾博物学记录、矢内原忠雄对日本帝国下的台湾经济考察等等。”[7]除去台湾作家对日本学者、作品的情感不谈,客观而言,这些作品为台湾植物学、民俗学等的发展与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台湾生态散文的书写提供了借鉴。
与中国人不同的是,西方和日本博物学者通常以“非本土”的视角看待台湾,具有官方背景的日本学者将台湾视为资源丰富的“殖民地”,对台湾观察的出发点带有很强的政治性。需要指出的是,台湾一些学者对日本博物学者的钦佩与赞扬毫不掩饰,甚至为其“殖民意识”进行辩护,是十分不妥的。总体而言,日本博物学者及其作品对台湾生态散文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史料价值的提供。日本博物学者所留下的作品和资料为台湾作家提供了大量的自然生物和民风民俗资源。日本学者在明治维新后努力向西方学习,因此多数日籍博物学者具有相当深厚的科学的动植物知识。20世纪中叶以前,台湾自然科学基础薄弱,这些资料为台湾自然科学奠定了基础。生态散文作品需要生物知识的支撑,刘克襄、徐仁修等生态散文家在创作初期常常依据这些资料对台湾动植物加以了解。
第二,观察和书写模式的借鉴。前文提到,一部分中国人的游记和台湾地方志“借鉴”了他人的作品,其作者并没有实际的踏查经历;中国传统文学艺术注重的是审美、意境、想象、虚构等,而西方博物学者多注重运用科学工具进行实地考察,生态散文的观察模式和书写模式由之得以确立。被称为“鸟人”的刘克襄,独自去深山赏(观察)鸟;徐仁修为了观察鸟类,特意请人在森林里为之搭建了观鸟台;陈玉峰经过对垦丁的“每木调查”①和高山桧木的踏查、思考后,探索出了“隔代改造”的生态理念。这样科学性的观察模式和书写模式,是台湾生态散文的突出特点。
第三,探险精神的继承。日本人受限于本国地形等多种因素,十分崇尚出海探险,强调探险精神。与此相对,由于中国是农耕文明社会,且受“父母在,不远游”等思想的影响,中国人自古就有“安土重迁”的思想,轻易不离开自己的故乡,除徐霞客等少数人外,大部分中国人都缺少冒险精神。毫无疑问,台湾当代生态散文书写者继承了日本博物学家的探险精神,不畏艰险,深入自然,实地考察,进行创作。
四、欧美国家的生态文学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人大量地引介了西方的生态文学作品,进而开始向西方学习,思考如何治理生态环境问题、如何看待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同时,通过阅读和借鉴西方的经典著作,如梭罗的《瓦尔登湖》、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等,台湾作家也习得了野外观察记录的方法和各种生态伦理观。20世纪80年代之后,台湾文坛上涌现了大量的有关保护生态、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作品,生态散文尤其蔚为大观。
西方浪漫主义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生态作家无疑是梭罗。他的《瓦尔登湖》在1985年被《美国遗产》杂志评为“十本构成美国人格的书”之一,事实上,这本书不仅在美国,在全世界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梭罗提出的“荒野理论”,强调了荒野的重要性;他在《缅因森林》里对渴望登上地球上所有山峰的登山者有过强烈的谴责,认为山顶是地球上改造完整的地方,登山者对山顶的窥视即对神的秘密的刺探,是对神明的亵渎。[8]台湾生态散文书写者代表之一的徐仁修受其影响,从其作品集的命名便可看出,如《月落蛮荒》《荒野有歌》等。人类不得不干预自然运行的情况,如人工拯救濒危动物等,但决不能依据人类的喜好对荒野乱加改造。仅凭人类的好恶来增减大自然中的生物,很可能会给大自然带来一场无法想象的灾难。
《沙乡年鉴》既是一本散文集,又是一本哲学论文集。所谓“散文集”,是从其文体属性上来讲的;所谓“哲学论文集”,是因为在该书中利奥波德创造了一种新的伦理学——大地伦理学(Land Ethics)。在利奥波德看来,新伦理学要求改变两个决定性的概念和规范:一是伦理学正当行为的概念必须扩大到对自然界本身的关心,尊重所有生命和自然界,“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9];二是道德上的权利概念应当扩大到自然界的实体和过程,赋予它们永续存在的权利。为此,他专门提出了“大地共同体”的概念,指出:大地伦理学只是扩大了共同体的边界,把土地、水、植物和动物包括其中,或把这些看作一个完整的集合:大地。人只是大地共同体的一个成员,而不是大地的统治者,我们需要尊重大地。[10]
雷切尔·卡森是20世纪著名的生态学家,无论她的生态理念还是生态文学作品,都对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然,她在得到赞誉的同时也遭受过无数的攻击,特别是在《寂静的春天》出版后。《寂静的春天》用了大量的事实证据和科学依据,揭示了滥用杀虫剂对生态的严重破坏和人类健康的巨大危害,严厉地抨击了滥用科技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这对台湾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如洪素丽在《剃刀边缘的大肚溪口》中对工业科技带来的环境污染的批判明显受到该书的影响。总体而言,欧美生态散文的译介、传播等在生态思想、生态伦理、写作模式等多个方面为台湾生态散文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借鉴。
总之,中国古代的自然书写、台湾地区的方志书写、日本学者的调查报告、欧美国家的生态文学等,都对台湾生态散文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或为之奠定了思想基础,或为之铺平了创作道路,或为之开拓了观察视野,或为之提供了理论借鉴。台湾生态散文的出现固然和台湾作家对本土生态环境的关注密不可分,但是,如果没有对中外文学的借鉴,台湾生态散文就不会取得如此骄人的、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注释]
①每木调查:在标准地内测定每株树木的胸径、树高等因子的工作,亦称“每木检尺”。见:马克伟主编.土地大辞典,长春:长春出版社,1991: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