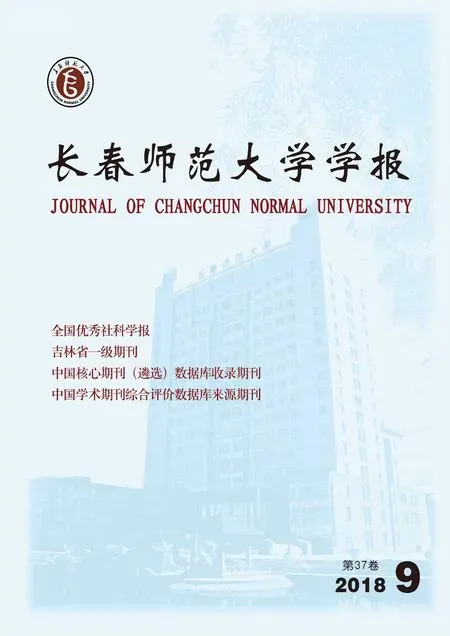“大东亚共荣圈”构想与伪满时期言语政策
——关于伪满时期初级日语教科书的考察
2018-03-29吕欧
吕 欧
(大连外国语大学,辽宁 大连 116044)
日本帝国主义在建设“东亚新秩序”、实现“大东亚共荣圈”野心的过程中,把大力推进日语教育和普及日语作为极其重要的统治政策。日语教材作为日语教育的出发点,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日语教育和言语政策的核心,其中必然隐含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言语意识。本文通过分析伪满时期日语教科书的内容,旨在研究伪满时期的殖民地言语政策及其背后潜藏的言语意识形态。
对于伪满时期的言语政策,中日两国学者一直存在很多分歧。磯田提到,在大连市举办的“中国东北教育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日方学者一直对两点问题存有疑问:一是中国历史学者的研究论调相似,却没有相应的事实证据;二是中方所说的奴化教育结论过于简单化,没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1]。牲川指出,言语政策史研究基本由非专业日语教育者推进和完成,日语教科书则由专业日语教育者进行分析研究[2]。从教科书和言语政策交叉关联的角度探讨伪满时期日语教育的成果并不多见。因此,本文以教科书内容分析作为事实依据,试图论证言语政策的可见性及其具体形态,并从意识形态层面考察中日双方存在争议的伪满言语政策及日语教育相关问题。
一、先行研究之所见
言语政策分为对内和对外两种。本文探讨的是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采取的言语政策,所指的是后者。言语政策的概念多种多样,但不管概念如何界定,都离不开特定的国家、历史、文化背景和言语主体国民的存在。川村指出:“日本曾经有过国家、民族、国语三位一体的时代”,“在日本这个国民国家社会条件下,不仅强制要求说日语,而且还必须对日本的风俗、习惯、文化无声或有声地服从”①[3]。西川和田中同样指出过这种言语意识形态问题[4-5]。言语教育是言语政策实施的最直接有效途径,因此考察日语教育以及日语教育的载体——日语教科书,是了解言语政策和言语意识形态的一个良好切入点。
笔者将日语教育政策研究分为“日本=日语”和“日语=日本精神”两个方面进行总结。这里的等号并不是指绝对概念上的等同,而是一种直接关联性的体现。
(一)“日本=日语”——日本近代的国家意识形成和日语
最初把国家和国语紧密联系起来进行阐释的是日语国语学者上田万年②。他在《国语和国家》的演讲中提到:“国语是一个民族全体成员身上流淌的血液,唯有通过这种血液方能感受国民的一体性。”③在1895年出版的论文集《为了国语》中,上田提到:“国语是守护国家的屏障,是全体国民的慈母。”这句被引用最多的关于国语的论述,诠释了日语之于日本的重要性。另外,丰田将“国语”定义为“从属于同一个国家国民的,从祖先继承而来的民族语,并且是正在被国民所使用的具有国家性格的语言”[6],进一步将“国语”与“国家性格”相关联。同样,石刚论及日本殖民地言语政策中的关键因素“言灵”思想和“神化了的语言”问题时认为,欧美帝国主义为自己的殖民统治提出的说辞是作为普遍原理的宗教,而日本用“神化了的语言”来达到这一目的[7]。这反映了日本人对“国语”的狂热崇拜心态。在言语政策方面,石刚把汉语和日语置于对抗关系进行论述,在描述日语言语意识形态的同时,用“言语输出”这一观点阐述日本对华统治中的日语教育。
(二)“日语=日本精神”——皇民化教育与日语教育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这已是不言自明的既定结论。但在殖民地统治下,这种相互联系更为紧密,更加清晰可见。宫地指出:“语言和文化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是不争的事实。”[8]因此,日语学习者往往会被日本人的思考行为方式“洗脑”。无论是殖民地时期还是当下,学习日语或者学好日语的条件之一就是习惯日本文化或日语思考方式。尽管这一点作为必要条件,一直被日语教育者和学习者接受,但政治形态上的差别决定了殖民地时期和当下的情况有着本质的不同。安田提到,殖民统治时期日本的为政者深信“国语”里面寄托着“国民精神”,而日语中包含着“日本精神”[9],因此日本在殖民地言语教育中不断强调这一点。
“日本精神”也是日语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何谓“日本精神”?川合解释道:“不单单是我国的国民性,也不单单是民族性,正是天皇陛下教育诏书所言之精神,正乃忠爱之道。”[10]此处的“忠爱”是对天皇的效忠,是本质上的天皇崇拜,更是“忠君爱国”的皇民思想。可见以培养和理解“日本精神”为目标的伪满时期日语教育的根本所在,即是培养忠于天皇的国民,而这样的日语教育更是披上了皇民化教育的色彩。
二、伪满时期的日语教育概况
1895年日本在台湾开展的日语教育可以说是日本殖民地日语教育的开端。随后,朝鲜“成功”复制了台湾的经验。1904年,日本在“关东州”成立了金州南金书院民立小学堂(后改名为金州公学堂),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语教育从此拉开序幕。1905年10月,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败,双方签订《朴茨茅斯条约》。自此,曾属于沙俄的辽东半岛租借地“关东州”交由日本管辖,日本同时取得了东清铁道南满支线④的管辖权,并进一步在这些地区开展日语教育。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932年伪满洲国宣布成立。日本强行将《国际法》并不认可的伪满洲国作为自己的傀儡“国家”,并把日语作为“国语”之一,加快了对东北地区的言语侵略进程。直至1945年日本宣布战败为止,日本在东北地区开展的日语教育持续了长达40年之久。
(一)日本在东北地区设立的初等教育机构
《初等日语读本》序言中第一条提到,本套教材为公学堂和普通学堂所用。日本人在东北地区面向中国人设立的初等教育机构分为公学堂、普通学堂和蒙学堂三种形式。公学堂是设有4年制初等科和2年制高等科,或者只设高等科的小学,基本等同于日本本土的小学教育。普通学堂是4年制的初等小学。有的小学只有一、二年级,也有的到四年级,是在中国私塾基础上开办的,叫作蒙学堂。
公学堂又称官立公学堂,最初在日本军方管制下设立,学堂长和教员均为军政首长认可的日本人。普通学堂的教师则为公学堂师范科或旅顺师范学堂(也是日方设立的官立高等学堂)的毕业生。平野指出:“公学堂为日本军方所设,聘请日本教员,是三种教育机构中日本色彩最为浓重的教育机构。”[11]其次为普通学堂;而蒙学堂因改编自中国的私塾,教员也多为中国的先生,是三种教育机构中日本色彩最轻的教育机构。
(二)伪满洲国的学制
伪满洲国的学制以1938年实施的“新学制”作为分水岭,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所谓“新学制”,指以天皇“圣旨”名义颁布的《学制要领》《学校令》《学校规定》《国民学舍及国民义塾相关规定》《国民优级学校》等一系列相关规定。根据这一系列诏令及“民政部”颁布的《国民学校相关规定》,将以往的4年制初级小学改为4年制国民学校;2年制高级小学改为2年制国民优级学校;中等教育机构的学制由6年制(3年制初级中学+3年制高级中学)缩短为4年制。学校名称也改为设有农、工、商、水产、商船5个专科的国民高等学校,或者是3年制、4年制女子国民高等学校。
三、伪满洲国日语教科书的发行状况及本文研究对象
伪满洲国的日语教材编纂机关主要有: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在满日教育会编辑部、奉天外国语学校编辑部、关东厅教科书编纂委员会、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教育研究所、关东局在满教务部教科书编辑部、“满洲国”文教部编纂部、“满洲国”民生部等。教材按照对象分为初级教材、中级教材、高级教材、速成教材四种。竹中宪一把以上编纂部门的教科书汇编成集,收录教材共计64册[12]。本文以竹中汇编教材中的初级教材共24册为研究对象。
四、伪满时期初级日语教材的特点
(一)教授方针特点
《初等日语读本》和《第二种 初等日语读本》在编纂时分别附有参考书,记述了初级教材的三个指导方针和四种教授法。三个指导方针即“口语本位”“应用主义”和“强调句型”;四种教授法即“直接法”“问答法”“发音矫正法”和“学生活动”。
1.教授方针
参考书中第一条就强调“口语本位”方针,这也是初级教材的基本指导方针。所谓“口语本位”,即“耳朵听和嘴巴说为主,眼睛看和动手写为辅”⑤,明确指出阅读作为家庭作业来练习即可。关于“应用主义”,参考书中的解释为:“重要的是教会一个知识点后,学生要学会灵活运用,这样学生们才会体会到表达的乐趣,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们要把这作为教学的根本目标”。而“强调句型”是前两种的必然要求。若只是“口语为主,着重应用”,最后就只是学到词和句。想要表达思想,需要正确的语法。因此,句型学习是初级教材教授方针中不可或缺的一条。
2.教授法
按照上述方针,教授参考书中对日语教学首先提出的就是“直接法”,并指出在教学中要尽量做到全部使用日语,同时配合挂图、实物、手势动作来进行。谈论“直接法”,不得不提到山口喜一郎。“直接法”源自法国语言教育学家弗朗索瓦提出的“续列法”,随后由国语学校教授桥本武介绍到台湾。山口在台湾致力于普及和应用这种“续列法”,并对其进行相应的改动,后逐渐形成“直接法”。[13]1914年,满铁⑥聘请山口来到东北并召开日语教授法讲授会。对于“直接法”,山口这样表述道:“只有用日语本身去记忆、想象事物,用日语思考,才能真正地感受语言的灵魂,了解日本文化,感受日本之精神”[14]。山口把日语和“言灵”思想及“日本精神”相结合,企图通过日语学习实现学习者的日本化。
“问答法”是为了强化“口语本位”方针而采取的针对性教学法。参考书中提到:“不进行问答的口语教学是无法想象的,并且问答法应用的好坏也直接决定了教学效果的好坏。只有把‘问答法’更好地应用,口语教学的效果才更值得期待”。而“问答法”正是“直接法”的一种具体教学手段。
“发音矫正法”是配合口语教学的方法。强调除了随时对学生的日语发音进行矫正,更要以长远的眼光看待这个任务。
“学生活动”是指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让学生更多地说日语。方法之一就是教师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说话时间,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练习。
以上的教授方针以及教授法,无一不体现日语教育中对学习者母语的抑制,强调日语使用的重要性和唯一性。通过日语学习,不仅要让学习者使用日语,更要使其掌握和理解日语中的文化以及精神内涵,实现对日语学习者的同化教育。
(二)形式特点
文字记述方面。《初等日语读本》和《第二种 初等日语读本》的序言中明确指出两种教材卷一均为片假名记述,从卷二才开始逐渐加入汉字。这完全体现了“口语本位”编纂方针。另外,去除汉字是为了进一步让中国学生远离汉字文化,尽早习惯日语的音韵文字。
语言表达方面。这四套初级教材在表达方面有一个共性,即大量使用拟声词和拟态词。比如南满洲教育会的《初等日语读本》第二卷的第12课《风车》中出现了拟态词“咕噜咕噜”,第19课《驴拉磨》中既出现了拟态词“咕噜咕噜”、拟声词“呼噜呼噜”;《第二种 初等日语读本》第一卷第29课中描述飘雪的拟态词“扑簌簌”。拟声词的大量使用与“口语本位”教学方针相互呼应。
(三)题材特点
伪满洲国初级日语教材按内容可以分为五大类:日常生活、风土人情相关内容;自然地理、科学相关内容;传统文化和近现代文化相关内容;国家、皇室相关内容;道德修养相关内容。其中有关日常生活和风土人情的内容最为丰富。南满洲部编纂的教材参考书中明确指出:“日语教学的首要目的是使绝大多数学习者都能够用日语说话”。因此初级日语教材中大量采用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题材,使日语渗透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之中,以期实现快速普及日语的教学目标。
初级教科书的另一特点是大量采用与中日两国文化相关的内容。有关中国文化的教材大多涉及清明节、春联、爆竹、春节等风俗习惯方面的内容;有关日本文化的内容则多以森兰丸、织田信长、乃木大将军之类的真实历史人物为题材。值得注意的是南满洲部的《初等日本语》卷五第14课《聪明的母亲》,其内容是著名的“孟母三迁”故事;奉天外国语学校编纂的《日本语读本》卷五第16课为《称量大象重量的小孩儿》,讲的是“曹冲称象”的故事。这些本应让中国儿童学习的经典传统文化故事,其人物姓名都被隐去。相反,《乃木大将军》《广濑中佐》两课中将乃木希典和广濑武夫这样的日本军人封为“军神”,对其加以歌功颂德。这些本应出现在日本国内教材中的内容原封不动出现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语教材中,此类抑制中国文化、颂扬日本文化的内容是日语教材进一步“日本化”的体现,同时反映了教材编者的编纂思想和教材的引导性目的。
五、伪满时期日语教科书体现的教学理念
(一)“口语化”教育理念
伪满洲国初级日语教科书整体的教学方针体现出“口语化”教学理念。文部省召开的“国语对策协议会”明确指出:“最有效的日语教学应以音声教学为重,因此相应的应该采用‘直接法’教学法。”[15]因此,初级教材中有大量口语化拟声词的使用,标记方法上减少汉字,更多地使用表示音韵的日语假名。另外,按照“直接法”,教学课文中去除了汉语译文。这些措施进一步抑制了学习者的母语使用,以求达到更大程度上的“日语输出”和日语普及。
(二)大量日本文化题材教材的使用
伪满洲国初级日语教材中有关文化题材的内容丰富,这不仅体现了教材“口语化”“生活用语化”的编纂方针,更是将文化融合在语言中,企图通过日语教育达到对学习者思想的同化。对于这一点,作为当时文部省重要官员的钉木久春曾指出:“日本的生活秩序,日本的文化感觉都作为日语本身具体的表现出来。因此,学习日语本身就是对日本精神的理解和体会”[16]。这揭示了日本企图通过日语教育实现民族文化输出并最终形成“民族同化”的日语教育目标。
六、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伪满时期初级日语教材,考察了伪满时期日语教育的基本概况。在具体分析教材内容的基础上,明确这些教材的编纂理念、教授法及编纂方针,同时重点考察隐藏在教科书背后的日语教育政策,最终发现无论何种教授方针或教学法,无不体现日本妄图通过日语教育建构“东亚新秩序”、营造“东亚共荣圈”的企图。
[注释]
①本文所引日语内容以及文献名称均为笔者译。
②上田万年(1867—1937),日本国语学家、语言学家,日本国语学奠基人。
③上田万年演讲文《国语和国家》(1894),笔者译。
④日本称之为“满铁”。
⑤竹中宪一编纂《满洲殖民地日语教科书集成》第一卷,《初等日语读本教授参考书》第170页。
⑥满铁全称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是1906—1945年在满洲设立的一家特殊的日本公司,是日本经营满洲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