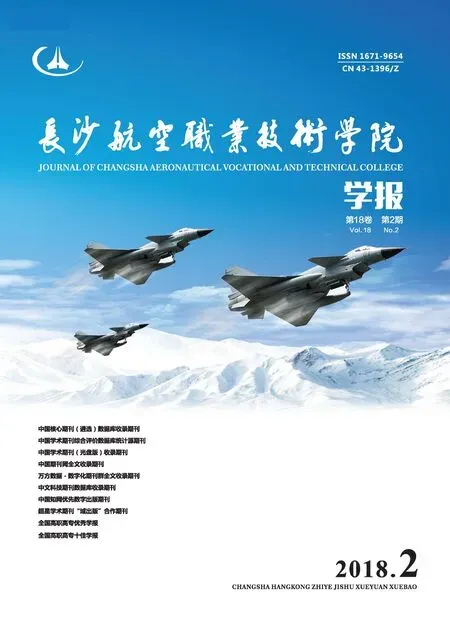牛汉诗歌的主体转变与诗艺特点
2018-03-29唐嘉
唐 嘉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牛汉诗歌的主题归纳起来主要有抗争命运、关注生命、直面苦难、追求自由这四点。牛汉诗歌创作格局较大,在他的诗歌中很难看到其个人情绪的倾述,“1941年至1943年我写了大量高昂的、追求理想境界的诗,表现了一个热血青年的壮志,个人的悲伤写得极少。高中时,我狂热地爱恋一个女同学,却没有写一首情诗。”[1]176学界将牛汉一生的诗歌创作高峰划分为两个时段:1940年到1942年,1972年到1975年。
一、牛汉诗歌的主体转变
牛汉认为自己诗歌的创作是一脉相承的,他一生诗歌恒定不变的主旨是对自由的渴望、对命运的反抗,他最突出的形象为倔强的诗人、苦难的歌者。“二十多年来,我写的诗,全部都是反抗命运的,基调悲壮,不悲伤,不消沉,不仅仅是个人的小情绪小天地。这与我早年的理想主义还是一脉相通的。”[2]96将牛汉前后两个高峰时段的诗歌作以对比,其同中有异。两个时期诗歌的不同点,首先体现在诗人在后期有明显的孤独感,前期虽然也有孤独时刻,但牛汉还是有着强烈的归宿感,他的孤独感可以被一起战斗着的伙伴们的共同理想消解,他内心设想未来的时候多数是从“我们”出发,后期在创作诗歌书写困境时,因为当时禁言的历史环境,他的诗多从“我”的角度出发。
前期流亡西北时,感受到了战乱中国破家亡的民族大悲剧,作为一名血性男儿,将诗歌作为参与民族革命的武器,主动承担了一个吹号者的角色,希望加入这场战斗实现民族独立、国富民强的理想。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鄂尔多斯草原》中,“我”以一个歌颂者的形象出现,“我”歌颂生命的乳汁、战斗的旗子、牧民的血、草原复活的笑,“我”和草原上的人民与亘古未变的生命是联系在一起的。对革命和现实充满积极参与性的牛汉,前期所写的诗歌主要围绕着革命主题开展,一类是反映人民生活苦难,一类是面对苦难现实号召勇敢斗争。同这一时期七月派的其他诗人一样,他们的诗歌都自觉地与时代政治、国家民族结合在一起,因为真挚的爱国情感发自于内心,他们的诗歌不会让人有图解政治、空喊口号的苍白感。在牛汉的诗中,土地所象征的人民、春所象征的希望,与他个人和民族大众都紧密相联,“我”是“小我”同时也是“大我”。这一时期时代的鼓手很多,个人的性格寓于救国救民、打造民族未来的洪流之中,牛汉的诗歌并没占据出类拔萃的位置。
第二个高峰期,牛汉自被划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后在生活上遭遇了巨大的苦难,这一时期的诗歌“我”与“我们”便不再如同之前的诗歌那样水乳交融,而是出现了明显的分离,体现了“知识分子”被迫从“民众”中分离出来,在被改造的痛苦中艰难跋涉的经历。《黎明前》(1947)“是我焦急地/期待着远行,/一个渡海去/找寻新大地的梦!”[3]48在这首诗里,海的彼岸是一个新的世界,在那里必然有新的人,“我”是有归宿的,“我”要加入“他们”,潜意识中诗人明显有着“我们”的概念存在。但在1985年发表的《远去的帆影》中,“我”发现了靠岸的艰难,“在我的背后/遥远的岸上/人们在闪电中瞥见我/我小小的/一闪一闪的身影/人们说/雷电多么绚丽啊/霹雳多么柔和啊//人们说/我这远远的帆影姿态翩翩/我多么飘逸多么神秘多么魅人/人们哪里能看得清楚/我的呜呜叫的创洞/我在浪涛上/怎样匍匐前进”[3]192,那种永远无法消失的孤独感极度强烈,“人们”即除了“我”之外的在岸上的人类,都成为了不懂“我”的异己,“我”在一个世界,“人们”在另一个世界。再例如1972年创作的《半棵树》中,“像一个人/为了避开迎面的风暴/侧着身子挺立着”[3]56,根深扎在土地深处,“春天来到的时候/半棵树仍然直直挺立着/长满了青青的枝叶”,即使“人们说/雷电还要来劈它/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盯住了它”[3]56,在这首诗中“半棵树”的处境是孤立无援的,没有花草树木,没有蓝天白云,唯一与之相伴的只是长在它身上的绿叶也就是它自己,“人们”只是充当旁观者的角色。从“我们”到“我”,是诗人处于磨难中孤寂却不屈的体现,从前期对未来简单明朗乐观主义的憧憬,转变为在艰难困境中对理想主义的坚守,这一转变也是他的诗歌创作第二次高峰比第一次高峰更有“个性”的体现。
“‘文革’后的这种自在和单纯,与40年代的单纯和简单差不了多少,是近似原生态的那种单纯的充满梦幻的生命状态。经过三十年的苦练,对人生、历史、世界以及诗,有了比较透彻的理解和感悟,获得净化之后的透明般的单纯。如果回避人生苦难,不是经受人生,绝达不到这个境界。”[1]187从意象的塑造上看,后期他的许多代表作中的意象多是带有伤痕的、处于困境之中的,如《华南虎》中被囚禁、被虐待满身伤痕、指爪流血的华南虎,《麂子》中,被正被猎人用枪口对准的麂子,《悼念一颗枫树》中被伐倒的枫树等等,写出了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和悲剧命运,但牛汉并没有因为所受的冤屈就放弃了文学之路和生命生活,而是在诗歌中更坚定更纯粹地坚守精神家园进行文学创作。回顾五七干校的生活,牛汉认为那是他和他的诗的一次命运的“再生”,咸宁被他看作三大故乡之一。
在咸宁的岁月里,他的诗歌更富有独属于牛汉的个性特点,他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勇敢顽强、从父亲那遗传来的对美的追寻都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了他的诗歌里,经受磨难却仍能够用最纯真的态度和感情去写作诗歌。“我与每一首诗相依为命。没有读者,也没有上帝,既不想发表,更不想讨好谁,自己写自己读。”[1]187诗歌从来不会放弃任何人,但在历史中有多少人因为命运的作弄主动放弃了诗歌创作呢?在咸宁的岁月里,诗歌创作被牛汉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他通过诗歌拥有了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诗歌不是达成任何目的的工具,诗歌是人生、是生命,牛汉用诗歌记录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用诗歌追寻命运的意义。他的诗歌在继承一贯精神气质的同时,无论是艺术水平还是思想内蕴上都有了极大的进步,让他超越了曾经作为七月派诗人的自己,有了飞跃性的提高。
从诗歌创作的状态来说,虽然牛汉认为两者的相似处明显,如都身陷危境、内心苦闷、精神纯净等,但两者还是有明显的区别,在40年代,七月派以及有其他创作倾向的诗人,他们能在自己的诗歌中畅快地抒发自己的所思所感,并将这些文字公开发表出来。而从批判胡风集团开始,许多诗人都放弃了在诗歌中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在不能说真话的世界里,坚持自我继续说真话,没有决然的勇气是无法做到的。文革时期文坛创作的荒芜,对于牛汉来说这种孤单和寂寞与40年代来说不可能完全相似,如果说在40年代,牛汉能够与战友们一起去战斗着写诗,并不缺少同路之人,融入“大我”之中摇旗呐喊,那么在62年后,牛汉就是以个人的角度去面对曾经信赖的组织对自己所造成的委屈,一个人继续高昂地歌唱着,歌唱着那些在困苦时期不屈的灵魂、对自由的向往和对光明不灭的希望。从而牛汉的诗歌有了不同于其他诗人的显著特点,在孤独和寂寞的岁月里,记录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展示了他从鲁迅那里传承的“绝望的反抗”。
二、牛汉诗歌的诗艺特点
“我是跟着一些诗人写起诗来的,从来不是按什么理论写诗的。”[1]140牛汉不主张刻意使用任何理论来进行创作,“诗或许是最难以分解、定性的,我指的是真正的诗。概念化的、非诗的有韵文字,那是很容易分析和图解的。……诗评家当然可以写这样那样的评论,但他们绝不会要求写诗的人和读诗的人被动地就范。诗是最不听话的抓不住的精灵。”[4]256但从牛汉的诗歌中可以发现他的创作明显地运用了一些诗歌技巧。
(一)象征手法的运用
牛汉的诗用中国传统的诗艺来研究,属于“言志”派,诗歌中有很明显的人生态度及情感脉动,如在描述苦难的诗歌中,总会倡导人在困境中应该坚持绝不屈服永远反抗的精神,但牛汉态度与情感的表达较少使用直抒胸臆的方式,多蕴含在象征性的意象之中。诗歌中的鹰、华南虎、汗血马、半棵树等形象,都具有很强的象征性,可以说象征了牛汉自己,也可以说是象征与牛汉有共同诉求的知识分子们,甚至象征了整个人类。
牛汉诗歌中象征手法的运用持续了一生,例如诗歌中多次出现的鹰,《山城和鹰》(1942)“鹰旋飞着,歌唱着:/‘自由飞翔才是生活啊……’//山城在浑浊的雾中匍匐着/叙述着远古的悲哀//山城在鹰的歌声的哺育下/复活了,鹰成为它的前哨”[3]5,《鹰的诞生》(1970)“鹰群在云层上面飞翔,/当人间沉在昏黑之中,/它们那黑亮的翅膀上,/镀着金色的阳光”[3]53,《鹰的归宿》(1981)“当隆隆的雷/在天地之间驰骋/仔细谛听吧/在风声雨声雷声中/有一阵一阵的/凄厉而悲壮的啸声/那就是鹰/向太阳/向大地/永远地告别……”[3]326,他笔下的鹰随着他的经历,呈现出不同的形象,有光辉的、充满力量的,又有悲壮的、充满苦难的,同样是鹰却是不一样的鹰,这些鹰象征了不同时期的诗人人生状态和精神追求。象征手法让诗人人格、诗歌主题与笔下形象生动地结合在一起,这些形象使诗人关于人生的思考探索、精神坚守都变得具体可感。
(二)对情境的重视
牛汉对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还体现在对诗歌情境的重视。牛汉有两本诗话书籍《学诗手记》、《梦游人说诗》,虽然牛汉的诗歌对他来说是抗争命运的武器,但是到了第二个创作高峰时,他对诗歌艺术性的重视,使得其诗歌在艺术水平上有了跨越式的提升。“在很长时间中,我喜欢并追求的是那种情境与意象相融合形成的诗。这种诗,对现实、历史、自然等的感受经沉淀或升华具有可触性。我的欣赏范围一般尚较广阔,但使我挚爱的是艾青的《礁石》、《鱼化石》,舒婷的《致橡树》,绿原的《重读<圣经>》,曾卓的《悬崖边的树》,蔡其矫的《波浪》等诗所显示的那样明晰、完整的情境和意象。”[4]257
以他的代表作《半棵树》(1972)、《华南虎》(1973)、《汗血马》(1986)为例,他就特别重视对情境的营造。《半棵树》中在荒凉的山丘上,被雷电劈成半棵的树傲然矗立,春来发芽,这种情境的设置,将那半棵树不惧悲剧命运、活在当下、珍惜生命的乐观坚强勇敢的性格特点刻画得淋漓尽致。《华南虎》中,叽叽喳喳的人群,人们对笼里老虎砸石块、厉声呵喝、苦苦劝诱,墙壁上一道道血淋淋的沟壑,写出了人们对华南虎各种各样的暴虐和华南虎顽强不屈的精神。《汗血马》中戈壁、荒漠、无风的七月八月天、火、闷热的浮尘、沁出的一粒一粒的血珠等词语的运用,将汗血马奔腾之路的艰险导致汗血马一路上流血流汗直至死亡的悲剧,以及汗血马在痛苦中不懈前行的勇毅水到渠成地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这些作品主题一致,都是用勇敢不屈的精神去面对命运的不公、去反抗悲剧的命运,但能够在同一主题下塑造生动鲜活的形象,一次次感动读者,不让读者感觉到雷同和重复,便得力于牛汉将他们置于虽相似却各有特色真实可感的情境之中。
(三)对话场景设置
牛汉提倡用心写诗,用诗歌持续着与自己内心的对话,同时作为一位勤于思考的诗人,在思想上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对这个世界的探寻、对人生的探索。此外,特别是在第二次高峰创作中,当他观察到在苦难面前人们展现出来的不同举动时,他简略却不吝笔墨地将那些人的消极、反面的形象暴露在诗歌中。他的诗歌中经常出现对话的场景,主人公与自己的对话、与他人的对话、与读者的对话,通过特定场景中不同立场思想语言的对话,表现诗人纷繁的思绪、心智的坚毅,社会生活的黯淡、环境的困苦,人们思想的困顿等等。
例如在《鄂尔多斯草原》的长诗中,“我”与“亲爱的读者”直接对话,《半棵树》中的“人们说”,《远去的帆影》中的“人们说”,《华南虎》中“我”心中的自我对话等等。牛汉在写诗的时候不仅仅是言自己之志,还用对话场景中各色人等的语言写出了与“我”完全不同的现实中的“人们”的各种面目,如袖手旁观、幸灾乐祸、麻木无情等,因此他的诗还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和批判力量。无论是言志还是反映现实,这些都源自牛汉对生命、对现实社会从未停止的哲学性思考,表现了他对世界、生活、人性以及人类命运持续一生的关注。
牛汉对自由体诗歌发展的贡献,有很多并未被学界触及,“人们谈论我的诗,最初总是归入现实主义的大类。后来觉得不适合,说我有超现实主义的情调,还带着某些象征主义的色彩。后来又觉得我这个人太野,拒绝定型,无法规范我。是的,我不属于任何‘主义’,我不在什么圈子里。我永远不依赖文化知识和理论导向写诗或其他文体的作品。我是以生命的体验和对人生感悟构思诗的。”[4]247对牛汉的研究还有许多空白空间等待深入。
牛汉的诗歌是富有生命火力的诗歌,他不拘于形式但并不代表他不重视诗歌内核外的语言艺术;他不追求用典押韵、美妙与新奇词汇的使用、写作套路的创建,却极其重视诗歌与生命体验、情感脉动的结合。他用诗歌证明诗是生命的语言形式,是灵魂深处流出的字符。即使牛汉自己认为他的诗歌与国内外最一流的诗人有很大的距离,但他对自由体诗歌持续一生的热爱、充沛的创作热情、众多的佳作,证明了只要人心中有诗的种子,诗就不会灭亡。“诗不颤抖”(《夜》)[3]233,诗不死。
[1] 牛汉. 何启治,李晋西 编.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339.
[2] 刘红伟,张洪波,林莽,等.牛汉先生关于人生与诗歌的答问[J].诗探索,1999,(2):89-96.
[3] 牛汉.牛汉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469.
[4] 牛汉.牛汉散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