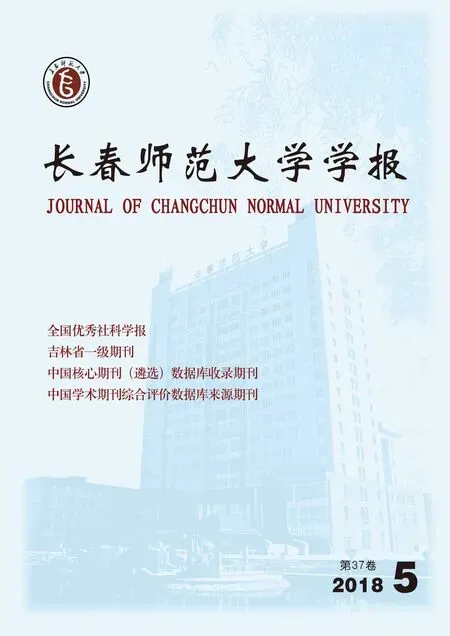论《新格拉布街》中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2018-03-28韩跃
韩 跃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外语与国际交流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乔治·吉辛(1857—1903)是英国文学史中一位奇特的人物。他于1880年发表了第一部小说《日出而作》,随后发表了《失去阶级地位的人》《伊莎贝尔·克拉伦敦》《德莫斯》,从意大利旅行回国后出版了纪念亡妻的《幽冥》、描写海伦·诺曼精神成长过程的《解脱》以及成名作《新格拉布街》。去世前几年在法国写了自传性小品文集《亨利·赖伊克罗福特私信集》和描写“一个普通人的罗曼司”的《威尔·沃伯顿》。除小说外,吉辛还写了很多评论和短篇小说,如《查尔斯·狄更斯评介》等。
吉辛在《新格拉布街》中以左拉式自然主义手法描绘了几位有崇高理想的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以敏锐精确的洞察力分析了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差距中的心理状态,正如戴维·洛奇[1]96在《小说的艺术》中评价的那样:“《新格拉布街》并不是一部能让你赏心悦目的书,然而,作为一部有关文人生涯的病理学研究,它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直至今日,它仍惊人地中肯。”《新格拉布街》不只是作者自传性质的小说,它实际是19世纪末英国文学界的缩影,反映了文学界普遍争执、作家普遍困惑的议题,即对商业与艺术、通俗与古典的取舍。本文以文本细读的方法着重从两个方面探讨《新格拉布街》中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文学创作与婚姻,同时兼顾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语境,将作者及其笔下的人物、《新格拉布街》文本与维多利亚后期的历史文本以及作家个人趣味与维多利亚后期大众读者群进行对比分析,以事实与想象重构维多利亚后期的文学、作家和阅读市场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大背景下观照《新格拉布街》(以下简称《新》)中主要人物的命运。
一、文学创作中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埃德温·雷尔登是《新》的主人公,他挚爱古典文学而拒绝创作迎合维多利亚后期读者大众的畅销小说,终至贫困潦倒、家破人亡。哈罗德·毕芬是雷尔登的好朋友,他们二人骨子里都有一种不肯向商业化文学创作妥协的执拗,即便饥寒交迫也心甘情愿沉浸在典雅高贵的古典文学世界里,创作符合自己心中理想的文学作品。两人对古典文学的挚爱,从他们平时的闲谈中便可见一斑。一次毕芬到雷尔登家拜访,想要借阅雷尔登家收藏的索福克勒斯的作品。雷尔登借给毕芬一本《牛津古典文学袖珍集》,但毕芬并不喜欢这个版本:
“I prefer the Wunder, please.”
“It’s gone, my boy.”
“Gone?”
“Want a little cash.”
……
“I’m sorry to hear that; very sorry. Well, this must do. Now, I want to know how you can scan this chorus in the Oedipus Rex.”
Reardon took the volume, considered, and began to read aloud with metric emphasis.
“choriambics, eh?” cried the other. “Possible, of course; but treat them as Ionics a minore with an anacrusis, and see if they don’t go better.”
He involved himself in terms of pedantry and with such delight that his eyes gleamed. Having delivered a technical lecture, he began to read in illustration, producing quite a different effect from that of the rhythm as given by his friend. And the reading was by no means that of a pedant, rather of a poet.
For half an hour the two men talked Greek meters as if they lived in a world where the only hunger known could be satisfied by grand or sweet cadences.[2]113(后文凡出自此著作的引文,只在文后注明出处页码,不再另行作注。文本译文均为笔者自译。)
通过以上对话,不难看出两人对古典文学世界的向往。而通过细读整本小说,我们了解到雷尔登的文学写作理想是在无外界压力的前提下用词语将自然流露的情感表达出来,而非在金钱和地位的功利目的下迎合读者的阅读趣味。毕芬以一种更为纯粹的方式去写作,甚至以弃绝婚姻和生计为代价,以左拉为榜样去追求自己的“绝对现实主义”。然而令读者惋惜的是,两人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都未能实现各自的创作理想,而是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走向了毁灭。作者乔治·辛与故事中的主人公雷尔登有相似的文学创作生涯,都在理想与现实巨大差距的压迫下抑郁而终。在阅读市场逐渐壮大、文学作品层出不穷的维多利亚后期,吉辛的文学创作生涯绝不是个案,而是很多作家都会经历到的。分析至此,我们有必要研究维多利亚后期读者大众的概况,以证明文学创作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在当时已是十分典型的症候。
约翰·斯图亚特·米尔在1836年发表于《希斯敏斯特评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是一个阅读的时代”。大约55年后,吉辛的《新格拉布街》出版,此时的读者群由于新闻出版的商业化和期刊杂志的扩张发行而进一步壮大。1800—1825年间,每年只有约580本书籍面世,而到了1850年已增长至2600本,时至1900年这个数字已超过6000。其中小说所占的比重也是逐年上升。1814—1846年间出版的小说占主要书籍的16%;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比例达到约25%;1880年后大约每年都有380本新小说问世[3]201。这个日益扩张的读者群体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包括商人、银行家、雇主及律师、医生、教师、公务员和其他商业界白领等。
此外,1850年通过的《爱德华法案》对阅读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此法案使得免费公共图书馆开始流行。当时影响较大的穆迪流通图书馆只需用户每年花一畿尼即可每次带出一本书。穆迪流通图书馆允许大量读者频繁借阅,使得小说家获得成功和知名度;但另一方面,穆迪本人的福音教派思想观念也决定了图书馆内小说的趣味导向。当时的中产阶级有钱有闲,已经开始大量阅读,但由于教育程度有限,他们的阅读内容未能引起深刻的智性思考,大多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
还有一个对读者群的扩大和构成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历史事件,即1870年通过的《教育法案》。此《法案》催生了一大批寄宿学校,从而创造了大量读者,使更多的无产阶级人员能读写识字。当然,能读书并不能保证一个人有好的品味。大多数下层阶级人员读的都是廉价的、会对社会产生“道德毒害”的轰动性小说[4]216-217。
吉辛本人曾诙谐讽刺地称其同时代的读者大众受过“四分之一的教育”(quarter-educated),只想要“最轻浅的闲谈信息——一段故事、一点愚蠢的想法、几个统计数据、一点笑话等等诸如此类,一切都要短,至多两英寸长,再长点儿注意力就会分散。即使聊天对他们来说都过于严肃,他们想要闲谈。”[2]419
吉辛是著名的英国文体家。在《新》中,他所写的每一章节都是经过仔细推敲和刻意修饰的。他喜爱希腊古典文学,讲究音韵之美,主张保存古典文学的形式。然而也正是他的古典学识和底蕴,使得他的作品创作变得尤为困难。正如Daley认为的那样,学识给吉辛的写作以技巧,但同时也由于吉辛的字斟句琢和追求完美而变得困难。这种追求极致的热情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他对社会所持的观点决定的,即吉辛对下层阶级的憎恨,对阶级差别的信念和他逃离现实生活遁入文学世界的做法[5]21-30。吉辛在智力上是个贵族和强烈的个人主义者,而他所钟爱的古典文学经典正是为贵族而创作的。
故事中的雷尔登与吉辛相似,也“属于那种不讲求实际的老式艺术家,”“他不情愿委曲求全,或者,说的更确切点儿,是不能够委曲求全;他不能迎合市场需要。”他严苛要求自己,希望在作品中既有丰富的文学艺术性,又能充满智性,这从他平时和朋友毕芬的谈话中就可见一斑。一次雷尔登问毕芬一个谜语,“为什么伦敦的房子像人体?因为大脑在上面。”[2]343阿尔弗雷德·尤尔同样是一位古典文学爱好者,他热衷进取,“被急切求知的欲望鼓舞着。他每天只让自己睡三四个小时;他拼命地啃语文,包括古代的和现代的;他试着翻译诗歌;他计划编写悲剧。他几乎是生活在一个过去的时代里;他研究包斯威尔的作品时,树立了他的文学标准。”穷困瘦瘠的毕芬与雷尔登相似,都崇尚古典文学,在许多方面趣味相投,所以回到伦敦后他们常常见面。“毕芬总是过着赤贫生活,住在很不像样的地方,经历过甚至比雷尔登更艰苦的考验。”他们谈希腊诗韵律,谈左拉,谈现实主义。故事中的这三位人物的结局都很悲惨,雷尔登在肺病中死去,毕芬自杀,尤尔双目失明,令读者无限感慨。
吉辛有意识刻画的这些典型人物对于揭示贫穷对人的摧残、读者大众的阅读趣味对作家的深切影响、经济和婚姻的相互关系等重大主题有不可替代的代言作用。反思作者吉辛及其笔下这三位男主人公的命运,可以发现他们悲剧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个人写作理想和当时读者大众的趣味相去甚远。如前文所述,1830—1880年间,英国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民主政治不断推进,中产阶级力量迅速壮大。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也要求改善自身的文化素质,提高修养水平;此外,政府对印刷出版业的政策扶持,使图书市场变得异常发达,作家数量空前上升,一大批作家能单纯依靠写作维生。据统计,1888年英国有14000个职业写作者。要在如此众多的作家中脱颖而出创造出经典之作,必须有异常的想象力、卓越的表达力和深刻的主题。或者说,要想靠写作谋生,必须既有天才般的创作力,又要充分考虑到市场需求、读者大众趣味等因素。而在维多利亚后期,后者很可能比前者还要重要。相比之下,与文中三位男主人公作比较的贾柏斯·米尔文是一位顺应时势的评论家。虽然他对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真正文学并没有实质兴趣,他的文学评论肤浅又哗众取宠,但他最后却能大获全胜。
除了阅读市场对读者阅读趣味的影响,维多利亚后期福音教派和功利主义社会思潮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当时人们的阅读取向。维多利亚后期的社会观察家T. H. S. Escott 敏锐地察觉到,“维多利亚时代实际上是宗教复兴的时代”[6]149。随着工业革命的日益深入,新兴的工业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矛盾激化,产生了很多严峻的社会问题。作为英国最大国教的圣公会未能对使英国社会转型的人口变化、经济变化及所有社会问题作出积极的应对,在这种形势下,低教派的福音教应运而生,并在维多利亚中层和下层阶级流行开来。福音教派信仰以《圣经》为中心的字面意义解读,强调个人的皈依体验和简朴的宗教祈祷仪式。事实上,福音运动在18世纪下半叶就已初露端倪,抵抗“理性时代”对教堂的形式化影响,并向大众传播福音。福音主义主张“代表仪式简单的清教派的复活,净化仪式和圣礼,清除天主教的最后残余”[3]103。另外,福音主义强调直接信仰耶稣的十字架和上帝的恩典而非个人的理性而获得救赎;强调成人皈依的内在体验而非正式的幼儿浸礼。福音主义的这种反智和反文学倾向使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更加局限于对字面意思的解读和更加务实的思维,正如卡莱尔在《追忆录》(1881)中所写的那样,他的信仰福音主义的父亲认为诗歌和小说总体来说“不仅无益,也是虚假的、犯罪的”[3]104。
除了福音的广泛传播,维多利亚后期也是“功利主义”盛行的时期。这个旨在追求最大幸福的哲学概念,其雏形在历史上早已出现,但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由英国哲学家边沁和米尔加以系统的阐释。功利主义哲学家认为最大的幸福可以由快乐和痛苦的总和计算出来,痛苦是“负快乐”。边沁和米尔都认为人类的行为完全以快乐和痛苦为动机。
对于大部分浸淫在福音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维多利亚后期读者大众来说,能引起轰动性的小说读物似乎更加有趣。而此时的商家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有意迎合读者需求,生产出数量巨大的轻浅休闲娱乐读物,如《趣味拾零》(Tit-bits),《问答》(Answers),《每日快报》(DailyExpress)等。
《新格拉布街》中最能体现当时功利主义和福音主义影响的是贾柏斯·米尔文。他白手起家,靠灵活的头脑抓住读者的趣味和关注,攀附中上层阶级为自己今后的仕途发展开辟道路,同时鼓励他的两个妹妹多拉和莫德尝试创作轻浅读物并结交权贵人士,最终都获得了幸福的归宿。米尔文完全认清并追随时代的功利主义潮流,很早就意识到了金钱、权利和地位的重要性。
二、婚姻中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在《新》中,另一个重要主题是婚姻中表现出来的理想与现实间的冲突。维多利亚时期贫穷未婚女子的生活是极其悲惨的,一般只有两条谋生途径:要么在工厂做苦工,要么在富裕人家做女佣。即便是条件好一点并接受过较好教育的单身女子,一般也只能靠做家庭教师或有钱人的同伴谋生,婚姻中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在她们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小说中,米尔文姐妹多拉和莫德与寡母同住在一个小村庄,姐姐莫德不定期地教人音乐,妹妹多拉做家庭教师。两姐妹虽受过良好教育,但生活得极为贫苦,因买不起漂亮衣服而无法参加社交活动,经常被同乡人误解:
The Milvain girls were so far from effusive, even towards old acquaintances, that even the people who knew them best spoke of them as rather cold and perhaps a trifle condescending; there were people in Wattleborough who declared their airs of superiority ridiculous and insufferable. ... Their life had a tone of melancholy, the painful reserve which characterizes a certain clearly defined class in the present day.[2]40
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反差令姐妹俩在婚姻市场极为尴尬——她们一方面对婚姻有崇高而美好的向往,但现实的经济状况又使得她们追求理想的婚姻成为天方夜谭。在小说的后半部,姐妹俩在哥哥贾柏斯·米尔文的安排指导下开始创作流行读物,结交上流社会,践行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事原则,并最终都获得了较为满意的婚姻。与此相对照,主人公雷尔登与艾米的婚姻因两人不同的价值观而终至破裂。作为有钱人家的女儿,艾米嫁给了暂露头角的年轻作家雷尔登,但婚后雷尔登在供养妻儿的压力下写作质量每况愈下。与丈夫对写作和婚姻理想化的态度不同,艾米是个较为现实的女人,她发现金钱是这个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东西:“若要在贫穷却荣耀与令人不屑的金钱、出名之间选择,我宁愿选择后者。”[2]40艾米与丈夫的价值观差异使其不能理解丈夫对文学和婚姻的理想化态度,可以说她未能在丈夫最艰难的时候给予他细致入微的关怀:
“Come here, Amy.”
His wife approached. It was not quite dark in the room, for a glimmer came from the opposite houses.
“What’s the matter? Can’t you do anything?”
“I haven’t written a word to-day. At this rate, one goes crazy. Come and sit by me a minute, dearest.”
“I’ll get the lamp.”
“No; come and talk to me; we can understand each other better.”
“Nonsense; you have such morbid ideas. I can’t bear to sit in the gloom.”[2]40
价值观的差异使艾米与丈夫雷尔登分道扬镳,而与怀有同样功利主义价值观的贾柏斯·米尔文最终结合。如果说艾米与雷尔登婚姻中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异源自于截然不同的价值观,那么小说中尤尔与妻子的不幸婚姻则主要源于两人不同的智力水平和教育程度。尤尔与未接受过教育、出身卑微的妻子几乎没有任何共同话题,经常把工作中的怨气发泄到妻子身上。米尔文虽然对玛丽安的温顺与才情青睐有加,但最终因为她的贫困和沉重的家庭负担放弃了与她结合的念头。所以在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对单身女性角色的期待极大地限制了她们的自我发展。
三、结语
与吉辛本人的经历相似,《新》中雷尔登、毕芬和尤尔等人的悲惨命运都发生于理想与现实不可消解的矛盾中。他们不能适应、不能接受新兴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沉溺在古典文学世界中追求完美与极致,被时代的快车无情地甩在身后,遭受贫穷的折磨和婚姻的不幸。有趣的是,读者可能会唏嘘感叹他们生不逢时、壮志未酬,但吉辛本人并不以为然,而认为他们“是无可挽救的”,而且“不必为他们设法”。他甚至说,“在现代,艺术必须谈痛苦,因为痛苦是现代生活的要点”[5]21-30。
[参考文献]
[1]戴维·洛奇.小说艺术谈[J].薛鸿时,译.名作欣赏,1994(6):96.
[2]Gissing, George. New Grub Street[M].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1996:40,113,343,419.
[3]Davis, Philip. The Victorians: 1830-1880[M].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201.
[4]Ford, Boris, Ed. From Dickens to Hardy: The Pelican Guide to English Literature[J].Penguin Books, 1979,38(1):216-217.
[5]Normal Schank Daley.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Scholarship of George Gissing[J].The Classical Journal, 1942,38(1):21-30.
[6]Arnstein W L,Bright M,Peterson L, et al. Recent Studies in Victorian Religion[J]. Victorian Studies, 1989,33(1):149-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