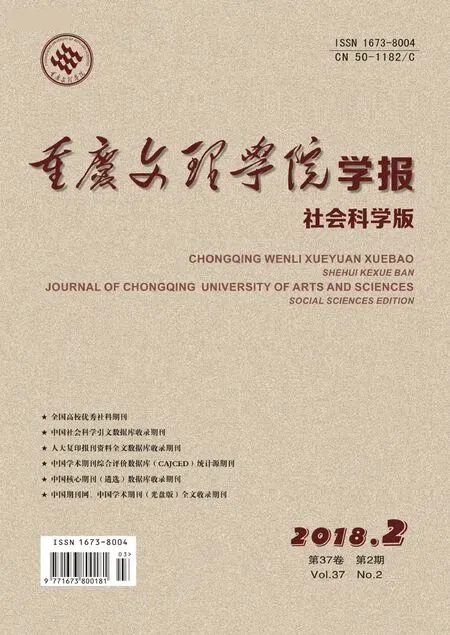期待“全考古学”时代的到来
——兼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建筑设计思想研究》
2018-03-28王先胜
王先胜
(重庆文理学院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重庆 永川402160)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考古学正处于其初生时期,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曾告诫弟子们“不要做沙发椅上的考古学家”,也就是与傅斯年先生“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所叙同一个意思。而今七八十年过去,中国考古学的情形与当年相比已是天壤之别。
一方面史前时代至夏商周的考古学文化体系已基本建立,一方面已经考古发掘的项目累积到10 000项以上,但其材料没有得到及时整理、出版,有可能造成中华考古遗产的重大损失[1]。因此,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考古学的重点不是考古发掘(除了因基本建设而被迫产生的清理和发掘以外),而应该是对已经发掘之材料的整理和深入研究。从长远和未来的角度看,发掘也终有结束之时,而研究未有穷期,因此对于考古学的认识应该有观念上的转变,即并非只有参加过考古发掘或者考古材料整理才叫考古研究,从不参加考古发掘而进行考古研究是一个符合逻辑与学理的必然过程和现象。即“沙发考古学家”是必然存在的。
厘清上述问题,在考古学和考古学研究的认识上,才不至于墨守成规、一叶障目。董婕、朱成杰著《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建筑设计思想研究》正说明“沙发考古学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们认为,该书正是不同于传统考古学著作的一本合格的考古学著作。
一、基本教义的考古学是残缺不全的
传统的考古学被定义为研究“物质遗存”,其基本理论层位学、类型学、考古学文化乃至聚落考古等都是围绕“物质遗存”而存在,脱离这个基本教义的研究则似乎不成其为“考古学研究”。但是事实上,仅限于基本教义的考古学是残缺的,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看。
古代研究包括物质、精神、制度各个层面以及从史前至历史时期相关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贯通,在此基础上才能继续研究“古代文明”“文明起源”等重大问题。文字产生之前以及文字应用初期主要依赖于考古学进行研究,因此基本教义的考古学必然先天不足: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既然被定义为物质的遗存,那么其对古代人类社会精神、制度层面的研究自然就是“无中生有”“无米之炊”,研究方法、路径不必深究,根据物质遗存猜测、估摸一下(当今考古学界提出“透物见人”就是这种艰难局面下的产物,实际“物”不能透,考古学家不是特异功能大师),这是考古学产生约两百年来其在理论、方法与实践上的基本困境与悖论——虽然西方自20世纪60年代“新考古学”后产生了不少考古学流派、理论,试图消弭这个困境与悖论,但因考古学定义是个前提性的“紧箍咒”以及机缘关系等,并没有解决问题①。“事实上,考古学诞生两百年以来,全世界各地发掘出海量的古代人类文化遗存,其中的刻画图案、符号及一些特殊遗迹、器物的文化内涵或其本来的意思表达,迄今为止并未得到全面、科学、合理的认读与解读,古代人类精神文化、科学文化及相关神话传说、古代历史未得确切与透彻的研究。”[2-3]也就是说,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看,考古学两百年以来的历史都并非完整与圆满。
有鉴于此,笔者主张对考古学的定义进行修正,即“考古学是根据发掘出土的人类文化遗存及其他相关出土物来研究人类活动与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其研究对象是“人类文化遗存”(包含物质、精神、制度等各个层面的信息)而非仅仅是“物质遗存”。这样,考古学研究古代人类精神、制度、文明等才能说从理论上、学理上得到支持,相关研究方法、路径才可以成为必然的追求。相应地,考古学和考古学研究才不局限于之前的基本教义,其空间才能符合逻辑与学理地扩展至研究古代人类精神文化、制度文明和国家起源等,考古学家当然也不局限于必须有参与遗址发掘及其材料整理的经历。
按照这样的思路,笔者将考古学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田野考古”,相当于种麦子;第二阶段“室内考古”,相当于磨面粉;第三阶段,探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写作历史等,相当于蒸包子、馒头,做面包(第三阶段也可以划归为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②)。三个阶段是三道不同的工序、三个不同的工种(当然作为考古学研究,三者不是截然分离的):“田野考古”以完整、准确、及时地报道和出版考古发掘材料为目标和任务;“室内考古”以最大限度地正确释读和理解考古材料为目标和追求;第三阶段以探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为工作目标和追求。三者在工作对象、目标任务、方法上均有所区别,但都是在“复原历史”,只是程度、层次不一样[4]。此前符合基本教义的考古学或考古学研究大体上在第一、二阶段之间,但是由于理论与方法都没有解决,它既没有也无法完成第二阶段;只有完成了第二阶段,我们才能顺利开展“古代文明”“文明起源”③这种宏大课题的研究,才能继续第三阶段的工作④,也才能说是完整意义上的考古学。关于第二阶段的理论、方法以及修正考古学定义后考古学研究的体系、理论、方法问题,笔者在相关文章中有所阐述[4-6]。
二、董婕、朱成杰著作的研究方法
董婕、朱成杰著《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建筑设计思想研究》正是考古学研究第二阶段的典型作品,其研究思路与方法也正吻合笔者主张和倡导的考古学研究第二阶段的核心理论,方法“考古纹饰学”⑤“考古象意学”⑥等认识:
该著作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现存地表上下的土石建筑遗迹,包括祭坛、墓葬、庙址、壕沟、灰坑、房址以及部分相关出土文物,同时还涉及牛河梁周边地区的喀左东山嘴遗址、敖汉草帽山遗址、阜新胡头沟遗址、凌源田家沟遗址等同类型文化遗址,以及早于红山文化对红山文化产生影响的兴隆洼文化的兴隆洼遗址、查海遗址、兴隆沟遗址等。这些材料都是考古发掘出土、互相关联而且不见于文献记载,它们主要属于考古学而非狭义历史学或其他学科研究的对象——其文化内涵、建筑设计思想探索清楚、可靠后才能用于历史学或者建筑学、建筑史、科技史、思想史等相关学科的著述或写作。
作者研究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建筑设计思想的路径和方法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在既有考古学研究成果基础上,严格遵守基本教义考古学的规则和思路,尤其是对“文化遗存”所处时空点、时空背景进行严格、准确地把握。如依据《发掘报告》,处于牛河梁遗址核心地带16个地点的材料,从早到晚分为下层遗存、下层积石冢阶段、上层积石冢阶段三期,有些地点的材料分别跨越其中的两期或三期,作者明确本课题主要研究的是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集中出现的上层积石冢阶段(距今5 600~5 000年)。作者在利用天文计算和天文软件等检验其有关遗址、遗迹设计理念、思想的认识时,始终坚持“将视角还原到5 600年前牛河梁地区的天文、地理背景”(他们认为牛河梁遗址群进行整体规划设计的大致时间即“上层积石冢阶段”开始的时间),使其研究和认识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可靠性。二是做到了研究的系统性,从宏观、中观到微观,多层次观照考察,层层深入,条分缕析。我们认为,牛河梁遗址群核心区域16个地点大部分属于“上层积石冢阶段”,它们是有整体规划和设计思想的。其主体建筑包括:祭坛性质的第一地点方台、女神庙和第十三地点的金字塔巨型建筑,以及有规律地分布其间的7个积石冢地点中心位置的第五地点。它们整体上构成“东北—东南”向,吻合一年中夏至日出与冬至日落的方位,同时顺着山梁的自然走势布局形成反S形,反映了当时“天圆地方”盖天宇宙观、北斗七星崇拜、观测太阳视运动规律与节气、祭天祭祖崇拜、顺天应地协调阴阳二气等设计理念。作者对已经发掘的第一地点、第十三地点、第五地点、第二地点、第三地点、第十六地点建筑遗迹的设计理念都分别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和论证其设计理念并对主体建筑宏观设计理念进行佐证,甚至通过这些遗址出土的器物及其纹饰分析进行进一步的佐证。三是多学科综合研究。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建筑群是史前时代罕见的高等级、大规模、综合性墓葬、祭祀遗址,涉及不同形制的祭坛、积石冢墓葬、庙址等及其他相关建筑遗迹、出土物,它必然与古人的宗教信仰、建筑思想相关,甚至可能反映当时的世界观以及科学文化、天文地理知识与水平等。今人要探索其规划设计理念,既要尽可能将其还原到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天文地理自然环境中,又要尽可能利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与科技手段,同时还必须严守和尊重基本教义考古学给出的时空框架、材料信息和其初步认识,在中国传统和古代的知识、观念、文化背景下来开展,所以它必然是个多学科融会贯通的研究模式。董婕、朱成杰两位学者的研究正是如此。他们充分利用了考古学、古代文献与传说、人文地理、古代天文学、现代天文计算与天文软件的模拟以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知识体系如宇宙观、“气”的观念、易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和手段,来完成他们对牛河梁遗址群建筑设计思想的研究。四是多角度的考察和分析。作者对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建筑设计思想的研究,并不局限于牛河梁遗址群,也不限于红山文化的同类遗址,而是上下左右内外巨细不同角度的反复观照,只要相关,就要考察。这从书稿的结构和章节目录就能够看出来:除了对牛河梁遗址主体建筑的宏观研究和其中每个地点的局部分析,其第四章是“牛河梁红山玉文化对建筑设计思想的佐证”、第五章是“牛河梁陶文化对建筑设计思想的佐证”、第六章是“牛河梁红山文化建筑遗址设计理念溯源”、第七章是“牛河梁红山文化建筑遗址与其他同类遗址的对比”、第八章是“牛河梁红山文化建筑遗址设计理念对后世的影响”,包括“牛河梁遗址的设计理念在《山海经》中的传承”“牛河梁建筑设计理念在皇家建筑中的传承”“牛河梁建筑设计理念在北方古代民族中的传承”三个小节。这样探索和追踪牛河梁遗址建筑设计思想的来龙去脉,也是对作者所主张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建筑设计思想的继续佐证。
综上所述,该著作的研究方法是:在严格遵守和尊重考古发掘以及层位学、类型学研究给出的时空框架、材料信息和其初步认识的前提下,采用了多层次、多学科和多角度的考察论证方式,形成一种立体交叉论证格局。这种方法当然不是基本教义考古学遵循的层位学、类型学方法,也不是狭义历史学的方法,而大体上属于“考古纹饰学”“考古象意学”方法。这种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明确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建筑设计思想,它是基本教义考古学方法(层位学、类型学、考古学文化)所无能为力的,当然也非狭义历史学范畴,而是属于笔者主张的“考古学第二阶段”,即“以最大限度地正确释读和理解考古材料为目标和追求”的室内考古阶段。因此说该著作是“不同于传统考古学著作”的一本考古学著作。
三、期待“全考古学”时代的到来
考古学产生约两百年来,纹饰只是物质遗存及其类型学研究的一个附属物。怎么探讨、研究纹饰以及一些特定遗迹的文化内涵,一直没有形成自己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其结果就是器物纹饰和一些特殊遗迹的文化内涵研究迄今是个难题,无从得到解决——虽然个案研究不难发现,但整体上是一片未知领域。这直接与考古学的定义有关,即考古学迄今为止被定义为研究“物质遗存”。因此,才需要将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定义为“文化遗存”,并分为不同的阶段给予处理,单独探索和建立释读纹饰与遗迹文化内涵的理论与方法。
基本教义考古学即使专门研究纹饰,它也不深究纹饰的文化内涵,当然事实上它也无能为力(一般只能随便给出一个理解或推测一下),因为它只是局限于层位学、类型学和考古学文化这些属于基本教义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超出这个范畴则不被视为考古学。这种研究模式在中国的早期作品以容庚《商周彝器通考》[7]、马承源《商周青铜器纹饰》[8]、朱凤翰《古代中国青铜器》[9]等著作中的相关研究为代表,近期以王仁湘《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庙底沟文化彩陶研究》[10]、李水城《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11]、段勇《商周青铜器幻想动物纹研究》[12]、陈振裕《战国秦汉漆器群研究》[13]、申云艳《中国古代瓦当研究》[14]等相关研究均为典型。这种研究当然是必需的,也为继续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但就考古学的终极目标“复原历史”来说,它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古代遗址、遗迹也是这样,比如为什么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流行方形与圆形房址,而大汶口文化仅流行方形房址,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流行斗形(带有斗柄部分)房址?这不仅是基本教义考古学可以不关注的事情,也是它无能为力去关注的事情。所以我们说两百年来考古学是不完整的。
为了叙述方便,同时希望引起学界对相关问题的关注、重视或讨论,这里提出一个新词语,即“全考古学”,也就是全方位意义上的考古学、完整意义上的考古学⑦。对于考古发掘出土的文化遗存,只有在某个方向基本完成或全部完成了(或者致力于完成)前述“考古学第二阶段”的研究,我们才视为“全考古学”。董婕、朱成杰著《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建筑设计思想研究》就属于“全考古学”作品。“全考古学”以前并非没有,如西方学术界对欧洲巨石阵遗迹的研究,中国学术界最近二三十年对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仰韶文化45号墓及相关蚌塑遗迹的研究、对安徽含山出土新石器时代刻画玉版的研究⑧等都是,但是“全考古学”专著却并不多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建筑设计思想研究》应该是中国史前建筑设计思想研究的一部代表性作品,也可视为“全考古学”早期的一部典型作品。
为了避免引起误会和歧义,这里有必要对“全考古学”做一个基本的界定,笔者认为其基本特征有几方面:一是其研究对象为考古发掘出土的文化遗存;二是“全考古学”第二阶段研究是在第一阶段即基本教义考古学研究完成后的基础上进行,同时必须严格遵守和尊重基本教义考古学给出的时空框架、材料信息和其初步认识;三是“全考古学”第二阶段的研究方法是全方位的、立体交叉式的,具体和主要方法即考古纹饰学、考古象意学;四是“全考古学”研究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正确释读和理解考古材料”;五是“全考古学”第二阶段的研究者不限于基本教义考古学学者,即没有参加过考古发掘及其资料整理的人也可以参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建筑设计思想研究》的两位作者就是这样,董婕是历史学专业研究生毕业、朱成杰是中文本科毕业,他们都没有参加过考古发掘和考古资料整理工作)。
提出“全考古学”并非耸人听闻。笔者认为它不仅是考古学和古代研究本身所需,也是从理论和观念上解决两百年来考古学界一直存在的困境与悖论,是考古学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全考古学”并非就能够完全解决考古学、出土文化遗存研究、古代研究的所有问题,但是它是从理论、观念、方法到实践上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符合逻辑与学理的思路、思想以及追求。“全考古学”研究可能容易出现阐释过度,但是它无法“藏拙”,比如回避问题、缺陷、疑难等,从学术的角度说,这是值得提倡的事情;只要自圆其说,它就是有益的,或者可能启发他人进一步探讨。学术问题,没有人能保证百分百正确,重要的是包容、开放、自由的讨论,因此“全考古学”的提出和尝试,比放弃和回避、存而不论有益。
回到《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建筑设计思想研究》,它提出和论证了一些新的观点与认识,比如牛河梁第一地点的女神庙其主体建筑七室结构表现的是十万年前北斗七星的形状,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遗迹、房址普遍存在的“东北—西南”向方位与北斗崇拜有关,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的龙与北斗崇拜有关,红山文化三重圆形祭坛及器物纹饰的三数设计也与北斗崇拜有关(斗魁三星天璇、天枢、天玑及其绕北天极的运转轨迹)等,不必视为定论但作者通过多方面的论证并且通过天文计算和天文软件进行验证,它们是自圆其说的,在没有充分有力的反驳意见之前不妨存在,也可视为一家之言(实际上,笔者就认为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的龙与北斗有关是可能的,而龙起源于北斗崇拜是不可靠的,待有时间再讨论)。
笔者觉得重要的是两位学者的研究模式与论证方法,如前所述,他们是全方位的立体交叉式论证,我们称为“全考古学”的第二阶段。这种研究从基本教义考古学的角度看有点离经叛道,也不会被承认为考古学研究,但实际上值得重视和提倡。张光直先生曾经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和理念:“把所解释的对象与它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广泛的联系起来,解释的说服力就增强了……作一个陈述容易,比如说某器物是做什么用的,某个社会是母系社会等。但这还不够,还要做进一步的证明。要把研究对象的特征和文化社会的接触点都找出来,接触点越多,就越令人信服。”[15]如果承认它还有一定道理的话,《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建筑设计思想研究》不过是这种思想和理念的一个实践。
中国考古学产生迄今的历程已近百年,考古发掘出土的自远古至夏商周秦汉的遗迹、遗物、纹饰浩如烟海,虽然史前至夏商周的考古学文化体系基本建立,但是这些考古发掘成果很少为民众和全社会所了解、认识,自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周极其丰富、斑斓的中华历史与文化更是罕为人知,即便是在学术界,考古学者虽然对物的部分比较熟悉,但对远古时代科学文化、精神文化、社会结构与发展历程所知也比较有限。因此,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和支持“全考古学”研究,期待“全考古学”时代的到来,也期待大批“沙发考古学家”的产生;只有发掘出土的文化遗存得到全面、深入地研究和解读,我们才可能走到前面所说的第三个阶段即“探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写作历史”,蒸包子、馒头,做面包给老百姓吃。
注释:
① 张光直说:“新考古学在很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国王的新衣……。”对新考古学之后的二三十年,他又认为:“考古学在这20多年的进步,不是理论,而是技术。所谓技术,就是产生新资料的手段。从地底下挖出新资料的手段就是技术,从旧资料中挤出新资料的手段也是技术。”
② 即狭义历史学。其最大特点是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研究人类社会历史。
③ 事实上,史无前例、规模浩大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从规划、设计到实施都出现和面临学理、逻辑的低级错误和尴尬局面,原因就在于理论、方法的缺失,没有经历第二阶段的研究就直接从第一阶段跃升到第三阶段,相当于一个拔苗助长的学术“大跃进”工程。
④ 白寿彝先生总主编12卷本《中国通史》集中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和考古学研究“复原历史”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其第2卷《远古时代》为苏秉琦等权威考古学家所撰写,对我国先秦史料中有关远古时代丰富多彩的历史传说仅在序言中作了不足2 000字的简介,而在30多万字的正文中极少涉及;以后各卷中考古成果与传统史学研究也基本处于“1+1”的简单加法状态。这个结果和局面正是没有完成考古学第二阶段的工作所必然导致。
⑤ 也称器物纹饰学。指通过分析古代遗迹、遗物的构造、形制、纹饰形态和结构,主要运用中国传统的象意思维、象数思维及其表达方式,结合相关知识和文化背景以及现代科技手段,进而探究其本义的一种方法。它是在层位学、类型学基础上的深入和细化,其对纹饰或遗迹本义的认识建立于相关知识和文化背景及一部分具有严密数量关系的纹饰或遗迹的解读之上。层位学用于发掘,类型学用于遗存排序及文化分区,纹饰学用于探究遗存的含义,三者构成最基本的考古学方法论体系。
⑥ 考古学的方法论之一。系根据发掘出土文化遗存之形态、形象、图像(含人类刻画)及其内部结构与组成、相互关系等探讨其内涵表达、寓意或者隐含其中的关于人类活动、社会组织结构及形态诸方面的信息、知识。它是在层位学、类型学基础上的深入与发展,同时也与层位学、类型学构成考古学的方法论体系。所谓“象意”,对文化遗存的生产者而言是以物象意或以象明意、以象达意,而对文化遗存的解读者、研究者而言则是据象求意、据象释意。象意学包含纹饰学与聚落学两大方法,前者侧重于精神文化探究,后者侧重于制度文化探究。
⑦ 比较而言,基本教义的考古学从理论、观念、方法到实践上都像中国明代小说里写到的那位外科医生,他拿把剪刀将中箭将军身上的箭杆剪去就是,认为射入体内的箭头不关外科的事,即使有人去拔出了箭头也不属于外科,但是考古学又把复原古代社会和历史作为终极目标之一,中国考古学长期以来热衷于“古代文明”“文明起源”研究,这就像那位外科医生一样,既坚持剪箭杆的外科理论又追求把中箭将军的伤处治好一样,学理和目标的逻辑困境、内在矛盾200年来迄今存在。
⑧ 这些文化遗存,学术界相关研究文献都很多,无法也不必一一列举。
[1]王先胜.关于中国考古学现状的深度思考及学术期待[J].社会科学论坛,2013(12):164-180.
[2]王先胜.中国远古纹饰初读[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5.
[3]王先胜.中国上古纹饰初读[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6.
[4]王先胜.据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一文检讨“考古学”——兼谈考古学的定义、理论与方法[J].社会科学论坛,2011(5):47-72.
[5]王先胜.关于建立考古纹饰学的思考[J].社会科学评论,2007(1):56-66.
[6]王先胜.解读纹饰:培育考古学科增长点[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9-29(7).
[7]容庚.商周彝器通考[M].北京:哈佛燕京学社,1941.
[8]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商周青铜器纹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9]朱凤翰.古代中国青铜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10]王仁湘.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庙底沟文化彩陶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11]李水城.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2]段勇.商周青铜器幻想动物纹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3]陈振裕.战国秦汉漆器群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14]申云艳.中国古代瓦当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15]陈星灿.中国考古向何处去——张光直先生访谈录[J].华夏考古,1996(1):7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