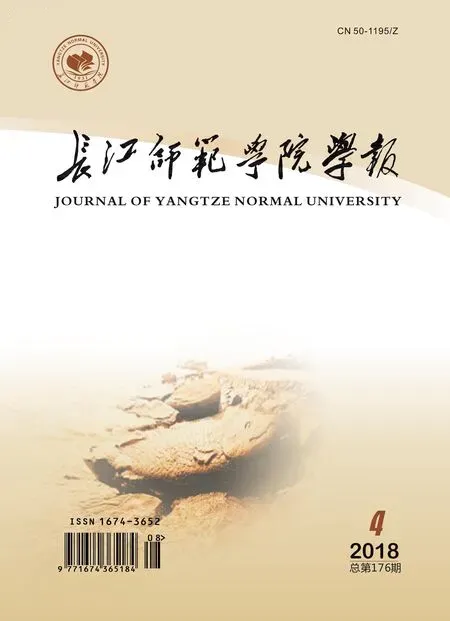福克纳和莫言小说非理性视角叙事与文本空间建构
2018-03-28杨红梅李凡响
杨红梅,李凡响
(长沙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 410022)
福克纳和莫言是20世纪以来世界文学的杰出作家,也是现代派创作的先锋作家。两人的创作在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体现了典型的现代主义创作的“现代意识”。在现代主义创作中,这种“现代意识”的中心是危机和荒诞感。“几乎可以说,现代派文学是广义上的荒诞文学。或者说,荒诞是西方现代派文学最显著的特征,一切现代派作品都包含着荒诞成分,不同程度地带有荒诞色彩。”[1]25
现代主义小说在表现“荒诞感”时,受到唯心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大量地引入了非理性叙事成分,表现了出了独特的艺术体验形式[2]1。赖干坚在《非理性主义与现代派小说的反向叙事美学》中,把“非理性主义与现代派小说的反传统艺术观的叙事美学可称为‘反向叙事美学’。它主要包括叙事内容的主观性、叙事方式的非逻辑性和叙述形式的平坦化三个方面。现代派对传统叙事美学的反叛,归根结蒂是在叙事原理上以非理性主义对抗传统的理性主义”[3]36。
福克纳和莫言在小说创作中体现了典型的“非理性主义”特征。在叙事中,两位作家有机地融入了非理性叙事,从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共同构建了小说的文本艺术表达的空间,表现和传递了一种与时代背景和艺术先锋创作休戚与共的“现代意识”。在小说中,由于视角的建构对文本内容的建构和艺术表达风格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视角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叙事的方式、叙事的内容及其表现的特点。以下将具体分析两位作家小说叙事非理性视角叙事特点及相关的文本空间建构。
一、福克纳和莫言小说的非理性视角叙事特点
在非理性视角的使用上,福克纳和莫言小说叙事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的创作都对一些视角进行了独特使用。这些视角主要包含儿童视角、“白痴”的视角、“特异”与“异化”的视角。
在这几个视角中,儿童视角是两位作家作品创作中相对使用比较多的叙事视角。儿童视角是指小说在叙述中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而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的儿童的叙事角度。福克纳和莫言在创作中都对儿童的视角进行了不同的表现。他们在作品中,都使用了两种类型的儿童视角:
第一类是纯粹的儿童视角。例如在《熊》中,福克纳通过对少年艾萨克视角的展现,描绘了美国南方丛林地区原始的自然景色,探讨和问询了人类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人类发展与自然和谐的问题。莫言在《透明红萝卜》《枯河》和《红高梁》中,通过黑孩、虎子和“我”,纯粹和自然的儿童视角记述和回忆了近代中国人的民族和心理感受史。
第二类是儿童和“白痴”视角的融合。福克纳和莫言在小说中往往把儿童视角与“白痴”的视角糅合在一起,这两个视角叠加在一起共同构建了小说儿童加白痴型的叙述视角。在《喧哗与骚动》中,33岁的班吉智力停留在3岁。在作品中,他一直用“儿童的思维”、儿童的“叙述的调子”感触和回味着生活的变故与满目疮痍。在《在我弥留之际》中的瓦达曼也是一个弱智儿童,它的智力水平大约只有四五岁。他不相信母亲已经死了,为了让她能在棺材里呼吸,他拿钻子钻破了棺材盖也在他妈妈的脸上钻了两个孔。莫言在小说叙事中也展现了相同的视角叙事。《檀香型》中的赵小甲与《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同样是一个典型的“白痴”,他的智力停留在幼儿的水平,他带着幼儿的纯真和傻笨的知觉感受着这个光怪陆离又充满着变化的社会。他无法理解成人的玩笑,当别人说他老婆眉娘是个“卖肉”的,他说她只是去给县令送狗肉。
除这两种类型的儿童视角以外,莫言的小说还采用了儿童视角和成人视角相结合的特殊儿童视角。这是莫言小说儿童视角有别于福克纳小说创作的一大特点。这个叙事特点在《丰乳肥臀》和《四十一炮》中都出现过。在《丰乳肥臀》中,上官金童虽然肉身已经长大,但是他的精神永远无法长大,有着终生不愈的“恋乳癖”。《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在和兰大和尚述说他的童年往事时,“他的身体已经成年,但他的精神还停留在少年”[4]400。在这种特殊视角的叙述中,罗小通“语言的浑浊冲决了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堤坝”[4]401。相比儿童加白痴型的叙述视角,这种叙事视角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人物类型叙事的阈限,立体和丰富了儿童视角的叙事表现。
在“特异”与“异化”的视角方面,福克纳和莫言在创作中也有着一定的运用。在这里,“特异”是指用非常态的人物叙述方式进行文本叙述。“异化”是指叙述中采用其它非人类的生物视角组织叙事。相比较而言,福克纳更倾向使用一些“特异”的非常态的人物视角展开叙事。这种叙述特点可以在《喧哗与骚动》和《在我弥留之际》中找到。在《喧哗与骚动》中,昆丁部分充满了大量意识流的叙述。在整个叙述特征上,根据埃尔普的统计,“此部分叙述中的时间或场景或意识的转换几乎达到200次”[5]109。对于这种非理性的叙事特点,埃里克·桑德奎斯特指出昆丁在《喧哗与骚动》中的叙述表现出了“从神经质美学到世袭式哀痛的梦魇的特性”,“并预示了《在我弥留之际》中具有超常洞察力的疯癫的达尔·班顿(Darl Bundren)的出现”[6]14。葛继红指出,在昆丁叙述中,福克纳运用了一种“梦呓语体”非理性叙事,为我们展示了昆丁极度忧郁与意识错乱的精神世界[5]114。在《在我弥留之际》中,达尔的叙述也是非理性的叙述。这种叙述方式与西方文学中那种“疯子—先知”的典型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达尔具有超能力,他能洞悉家里每一个人的秘密,能在远离家门时“看到”母亲的离世;与此同时,他也带着很大的毁灭性,他嘲弄着家中每一个人,焚烧了母亲的遗体,最终被家庭送进了疯人院。
相比福克纳“特异”的叙事视角,莫言更倾向于采用一些“异化”的视角组织叙事,其中最具有这样特点的小说就是《生死疲劳》。小说的主人公是土改时期被枪毙的地主——西门闹。小说叙述大部分是通过他六道轮回的不同生命载体——驴、牛、猪、狗、猴的动物视角展现的。动物叙事在中国志怪志人的小说中早已出现,与中国“志史”当中所出现的动物叙事不同的是,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借助动物的眼光对上世纪中国农村社会的变革进行“文本化”和“陌生化”的表现。动物不再只是叙事中涉及到的一个角色,而且是撑起了文本空间叙述的一块苍穹。这种叙事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已突破传统,展现了一种全新的解释与把握世界的方式。
在两位作家的叙事中,虽然“特异”和“异化”叙事视角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差别,两种不同视角体现了中西文化对世界的认知、理解和遐想的不同方式,但是两种视角都具有人类叙述非常规性的特点,展现了两位作者对现实世界的非理性的艺术表现。它们是两位作者从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建构现代艺术表现的尝试。
二、福克纳和莫言小说非理性视角叙事的文本空间建构
通过非理性视角的运用,福克纳和莫言建构了小说文本内容和结构空间。在小说文本内容上,两位作家在非理性视角叙事中对小说叙述的心理感知层面进行了充分和具有特色性的表现;在小说文本结构上,非理性视角从叙述层次上构建了小说意义表达和美学展现的独特叙述层次。以下将从文本内容建构和文本结构建构层面,对两位作家小说的非理性视角叙事进行比较分析。
美国作家亨利·詹姆士曾指出:“小孩子虽然说不清、道不明,但其感觉、眼光和理解力远比他们所能用词汇表达的更丰富敏锐、更深邃。”[7]29除了小孩的视角,“特异”与“异化”的非理性视角也有这种超乎常规、敏锐和深刻的表达能力。福克纳和莫言在这些非理性视角的叙事中,通过感知意识的呈现,艺术地表达了人心理表现层面的情感,建构了小说文本空间独特的叙述表达与意境,成就了小说创作先锋的现代风格。
在《喧哗与骚动》中,班吉是一个缺乏语言能力,只会哼哼唧唧的弱智。在怀念凯蒂的每一个夜晚,孤寂和内心异常敏感的他感觉到,“我能听见天色一点一点入夜的声音,我的双手看见了拖鞋……我蹲在那里,聆听着天色一点点变暗的声音”[8]72。每天晚上“黑暗像一团团的光滑,明亮的形状那样游散着”[8]75。昆丁在凯蒂结婚当天,感到“她就这么一路跑出了镜子,那玫瑰的芳香,那响彻在伊甸园上空的声音”[8]81。梦境的幻灭和种种生活的现实伴随着视觉、味觉、嗅觉和心灵的感受一起跃然纸上。在《在我弥留之际》中,悲伤哭泣的瓦达曼在母亲去世时,叙述到“我能听到树林的声音,静悄悄的……不过这不是有生机的声音,甚至也不是它的声音。仿佛黑暗正从它的整体里把它分解成一些毫无关联的零散部件——鼻息声、顿足声;正在冷却的肉体和腥臊马毛的气味……”[9]45母亲的离世支离了现实的生活,他们开始破碎成为无意义的部件。声音和气味的感触记录了悲戚和心碎的人物意识。
布雷德伯里曾指出:“在回忆或历史的叙述中,叙述者是回顾已经发生的事件。前者的内心充满着骚动,而不是情感冷后的‘灰烬’;矛盾往往是炙热的:欣喜是兴奋而热切的,痛苦和烦恼是催人肺腑的。叙述者仍在同他的烦恼搏斗着,这是奋争,不是和平,是正在悸动的伤口,不是愈合的疮疤。”[10]66方汉文曾指出,福克纳的作品“人性中残酷和愚痴的一面借助于非理性、无逻辑的特殊叙述显现得淋漓尽致”[11]124。在小说中,福克纳通过非理性视角的各种感官呈现,以一种更敏锐和深邃的眼光,把悸动在人心的各种骚动、热切的情感和催人肺腑的痛苦触手可及地描述出来,表现了凛冽、极致的现代审美艺术。
莫言在非理性叙事视角叙事中,也有这样的艺术表现。在《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娃眼中的“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苞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从美丽的弧线上泛起一圈金色的光芒”,“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在《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对红萝卜有着超乎寻常的感知。对于黑孩的创作,莫言指出“他具有幻想的能力,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奇异事物;他能够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譬如他能听到头发落到地上发出的声音;他能嗅到别人嗅不到的气味。”[12]15在《枯河》中,他同样塑造了具有超凡感知能力的虎子。在凄艳、水淋淋鲜红的月亮下,被悲愤的父亲责骂的虎子“更感到彻骨的寒冷,身体像吐丝的蚕一样,越缩越小,布满了皱纹”。在打骂的追赶之间,他觉得“父亲和哥哥像用纸壳剪成的纸人,在血红的夕阳中抖动着”。被苦难碾压的生活,让虎子找不到固有的温情,只感受到命运的薄如蝉翼。在写作中,莫言通过极具表现力的非常规性人物视角艺术地描写和表现了人物的客观现实生活,展现了人物在特殊时期丰富的情感体验和内心世界,建构了小说文本空间的内容和艺术表现之美。
这种艺术的审美性,正如莫言在创作黑孩时所说的:“他就用自己的眼睛开拓了人类的视野,所以他用自己的体验丰富了人类的体验,所以他既是我又超出了我,他即是人也超越了人。”[12]308在福克纳和莫言的非理性视角叙事中,不同的叙事主体都有着这种超能力叙述与表达的概括性。在《喧哗与骚动》中,凯蒂如树叶般的清香、忍冬花的气味和《透明的红萝卜》中晶莹剔透、泛着光芒的红萝卜一样,都是一种在非理性视角下对人类生存体验的独特表达。两位作家通过非理性叙事对小说的文本空间进行了一种概念和意义上全新的阐释与表现。
在两位作者的小说中,非理性视角除了丰富了小说感知和故事层面的文本空间表达之外;它也在叙述层次上建构了小说文本空间的意义表现。
在叙事中,“现实主义理性叙事是意识形态叙事,它所反映的是被意识形态删改的历史,而无意识脱离了理性社会的藩篱,只有非理性才能隔离理性主导的叙事”[13]203。在《喧哗与骚动》与《在我弥留之际》中,班吉、杰生、瓦达曼和达尔的叙述表达各有特色,这些叙述无论是疯癫,还是痴愚和神经质,它们都以不同的触角和对生活的感知方式表达了对南方社会问题的认识。李文俊曾指出,“福克纳凭借激情爱恨进行思考,使人们在人际疏离和人性异化的混合体中揣摩他的态度”[14]126。“人际疏离”和“人性异化”的混合体是小说叙述主题。班吉、杰生、瓦达曼和达尔的叙述从新的层面展开了小说叙述和表现的层次。小说的不同叙述层次也对这种“疏离”与“异化”的主题进行了更加明晰化的结构上的艺术呈现。
莫言在小说叙事中也通过非理性的视角对文本的叙述层次进行了不同的建构。例如在《檀香刑》中,赵小甲傻子的角色其实是一种非现实的、漫画和戏剧化的艺术表现。它与小说叙述的其它的视角一起映照了整个事件。在《四十一炮》中,罗小通夸张性叙述中的“屠宰村”“肉食节”其实就是一种象征意义的讽喻。它与《生死疲劳》中动物的叙事层隐喻化特征一样,隐喻化地表达和嘲讽了现实的荒谬,共同构建了现实及其艺术化表现的两个关联。
两位作家在小说的非理性视角叙事中,通过不同的非理性视角对小说内容进行了不同层次的叙述表达。这种表达在从叙述层次上丰富了小说。相对于福克纳的创作,莫言小说的非理性叙事更多了一些变形化和讽喻化的特征。整体而言,非理性叙事瓦解了传统理性叙事的话语表现,在新的表现范畴和艺术特征层面建构了小说内容和美学上的艺术表达。在这个基础上,两位作家完成了现代小说艺术表现“理性”与“非理性”叙述的“超级整合”,建构了小说的文本空间表现和艺术表达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