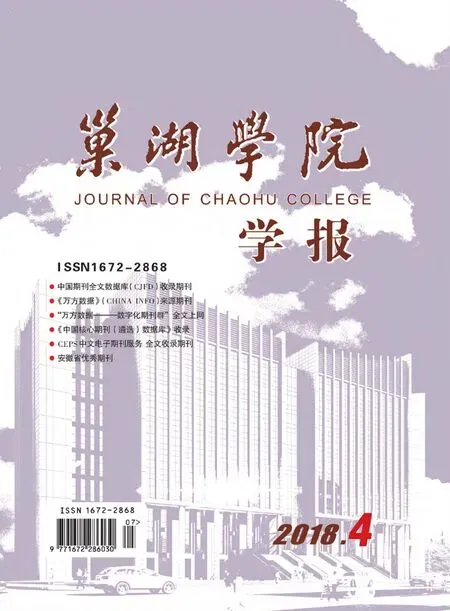合肥主城区空间形态的历史建构
——明清建成期的阶段性研究
2018-03-28徐亚哲
徐亚哲 尹 莹
(安徽大学,安徽 合肥 230039)
合肥建置至今已2200余年,城址几经变迁,先秦一代,合肥即作为楚国商业大都会,当时故城在今西门外二里。三国时期,合肥成为江淮军事重镇,依鸡鸣山筑合肥新城(今合肥旧城西北三十岗乡),隋唐时期,在今天合肥主城区南半部,又形成了新的商埠巨镇,名金斗城,庐州府商业兴盛一时,宋代扩建庐州城,逍遥津、金斗圩等大片土地划入城区范围,由此,元明清合肥城市的轮廓基本确立。然而直至明初,伴随着大规模的城垣建设,合肥主城区的外部空间平面才彻底稳定下来,城市内部格局也依此逐渐规制完善,自此而后五百多年乃至今天,合肥主城区的基本形制都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变化。无论是今天作为合肥主城区外环线(一环)立体交通枢纽的南熏门桥、拱辰门桥的命名也好,亦或作为核心城区分界线的环城路走向也罢,乃至于主城内道路主干线的布局以及重点文旅项目包公园、明教寺等对土地单元的利用,都和明清主城区建成期所逐步构建的空间形态有着莫大关联,基于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或是新时期的旧城改造和城市设计,对这一阶段合肥城市内外部空间的研究都不可或缺。
1 明清合肥城市整体规模及布局
由古而今,合肥城市的发展都是整个江淮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政治文化进步、军事战略调整的真实写照,在漫长的2000多年岁月里,合肥的城市发展除了跟随着封建社会缓慢的前进脚步,在不同时期,也展现出不同的城市特质,尤其是明清一代,合肥城逐渐在城垣建设和城市职能完善均衡之中形成了城市空间形态和城市景观的稳定架构。从基本定义上说,空间形态是城市建筑的具体形态,以及建筑与建筑组合以后形成的整体城市格局。空间形态涉及城市的平面格局、建筑类型和风格特质,而平面格局又反映了城市的整体规划,建筑类型与风格特质则关涉城市建筑的功能、材料、意象与意匠[1]。
中国古代城市很大的一个特点是建筑仅存在类型的区别,而很少涉及形式风格的区别。明清之际的合肥也是一座由官方和地方行政机关所营构的政治城市,再加上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环境,城市就显得更为隐性,呈现出一种固定的城市模式,城内建筑按照各种功能需求有各种类型,风格就几乎没有体现了,想要析出合肥自立的城市发展范式,由平面格局切入再去探讨内部功能分区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像隗瀛涛先生所说:“城市史应该以研究城市的结构和功能的发展演变为基本内容。”[2]因此可以将合肥城市研究的焦点聚集于贯穿于合肥城市内部、具有连续性且发挥结构性作用的城市元素上。合肥城市平面布局与中国古代大多数城市相比,较有特色的即是其整体形状的呈现。在一般印象里,中国大多数城市都是正方形或长方形构建,或是相拼接的结构,至少在原则上,应当是方形的[3]。而明清时期的合肥城却是罕见的近圆布局,不同于我们以往所熟知的古城如北京、西安等,四四方方的格局,中轴线贯穿全城,形成了严整的棋盘式道路网,也就是常说的“方整城池,皇城居中,棋盘路网,轴线对称”的特点,而地方城市没有宫城与皇城,但也大体按此形制进行规划。
圆形筑城技术本身较为困难,合肥采用近圆的设计,实际上受制于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南淝河自东南向西北绕城而过,汉代以前合肥在南淝河以北,后来逐渐移向南,为了利用南淝河这一天然护城之利和交通运输与灌溉优势,明代合肥城基本轮廓确定时城基大多顺河而定。合肥“为南方水网地带,河流多弯曲,旁河依湖筑城,其形状就不得不受河流制约,而且在河网地区,很难找到像北方地区那样整块平坦的地区建城,建成圆形是利用有利地形。”[4]这样,今天以围绕环城公园的环城路为城基的合肥旧城基本格局,东面北面保持着与南淝河走向一样的轮廓,城西与城南是同石河与黑水塘相贴合,这样中部相对平整的地带就作为主城区,这种近圆的布局反而使得合肥城显得不那么千篇一律而充满了独特韵味,也为现在的城市规划提供了些许便利。
“在帝制时代,中国绝大部分城市人口集中在有城墙的城市中,无城墙型的城市中心至少在某种意义上不算正统的城市。”[5]明清合肥城虽然在整体的平面布局上呈独特的近圆形,但仍是一座传统的封建城市,城内的格局还是依照着中国古代城市的基本布局来设计,除了城西北未开设城门,以致南边德胜门无所对应以外,其余六门纷纷对称布局,这样自然也就基本决定了城区东西和南北走向的主要道路网:威武门内是东门大街,时雍门内是小东门大街,拱辰门内北门大街,大西门内西门大街,自威武门入内,向西可以到达明教寺,最终与城中的县桥大街相连,从时雍门小东门大街向西经过奎星楼、饭巷口,再与西平门内的西门大街相连,南北走向的拱辰门内北门大街,向南一路经过南十字街、镇淮楼(今鼓楼)、奎星楼,第四条主要街道是南熏门内的南门大街,北首到达后大街城南,还有德胜门内的德胜门大街,一路向北经回龙桥、横街,北首到达卫山。城西最重要的街道是西平门内的西门大街,自西向东经洛水桥、东饭巷口与小东门大街连为一体,而城中的主要街道则为县桥大街,它的南端为后大街,北端为惠政桥,再向北则是金水桥与清华庵,这种街道布局深受中国古代城市传统规划的影响,也有作为中轴线贯穿全城的主干道。
七座城门基本决定了城内主要街道的形制,而这些街道与街道间,城区内的建筑与建筑间,也自然形成了许多巷道,明清时的合肥至少有100条小巷,较有名气且有明确记载的大致有东门大街的飞骑桥巷、七星街、九狮桥巷,小东门大街里的万寿寺巷、坤生巷,北门大街的教场巷、鼓楼巷、十字街东,城南南熏门大街内主要有饭巷口大街、庐江巷、双井巷,德胜门内回龙巷、前大街、后大街,大西门则有府城隍庙、庐州卫署、蜀源桥,而像饭巷口、飞骑巷、教场巷、回龙巷、凤凰桥巷、鼓楼东西巷[6],这些街巷名称和大致位置都与今天相同,为合肥城留下了深远且可寻的记忆。
2 明清合肥城市功能分区
小巷与城内街道组合就构成了城市街区,进而形成了最初的城市功能区。合肥地势西北高,因而按照一贯的衙署占据城中地利的城市布局理念,行政区都在西北位置,包括合肥县衙、庐州府衙、县丞署等,这也是明清合肥最重要的城市板块。寺庙主要分布在城东北隅,明教寺、地藏寺都在东门大街偏北的位置,文教区则在城市东南板块,当时的庐阳书院、包公祠、县学都在城南。这样,县衙府衙占据高地展现政府的统治权威,也可俯瞰全城保证城内秩序;寺庙则在人群往来密集的东门大街一侧,方便观瞻;而城南地势低平,又在包公河畔,环境优美,所处僻静自然就成为文教机构的首选,成为合肥城最具风雅的地区。不同的区位优势造就了不同的街区景观,而这些景观又将这些特征进一步固化和展现,明清合肥主城区空间形态的建构,基本遵照了中国传统城市的设计理念,又不乏自己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就源于这种与城市自然地理地势的高度关联,进而形成层次错落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内部地理单元。
尽管庐州府并没有主导着去构建一个以经济功能为主的综合区域,但明清时期的合肥还是拥有很活跃的商业因素,城隍庙一带在南宋就已是人口集聚,得益于北边金斗故道带来的巨大河运优势,这种盛景一直延续到明中期,繁华数百年。重修《安徽通志》载:(宋代)“自河入城之后,而民间之利甚溥矣。谷粒之出入,竹木之栖泊,舟船经抵县桥或至郡邑署后。百货骈集,千樯鳞次,两岸悉列货肆,商贾喧阗。因其地气疏通,人心愉畅,而官长之超擢者,缙绅之显达者,甲乙榜之多,土风之厚,民俗之醇,甲于他郡。”[7]意思是说,宋代金斗河带来了繁华的物流,河两岸商家众多,乃至这里官员的升迁、缙绅的显达、学子的金榜题名、民风的淳朴都比其他郡县要好。“清代是我国书院最为昌盛的时期,……在安徽地区,江南诸县位居第一,江淮次之,皖北又次之。”[8]
明代前中期,金斗河两岸遍布着码头货栈和妓院、牙行、酒肆、茶楼、当铺、卖绸布和皮货的商店。1505年,庐州知府徐钰为了防范明朝的刘六刘七起义军用金斗河水灌合肥城,强行堵塞了金斗河西北面水关的入口,“明正德时,知府徐钰塞西水关,河渐淤浅。”[9]金斗河水位大为下降,繁华盛景不再,原先今天杏花公园和老安徽日报社一带的商业区逐渐转移到三孝口(明代末年以前叫衙门口),这样合肥城的商业街区就转移到了东门大街(淮河路步行街),前大街(长江中路)一带,但城市物流已然大受影响。
不难发现,今天作为合肥旧城区商业中心的淮河路、宿州路、安庆路、蒙城路实际上在明后期以后就已经形成有一定规模的商业街了,再向东与三孝口一带的后大街相连,这也是行政军事区;庐州府衙、合肥县衙、三座粮仓(内仓、漕仓、永丰仓)、火药局、武器库、卫衙大关、庐州府学文庙都在城西北部;文教单位主要分布于城东南,合肥县学、庐阳书院、魁星楼、包公祠都在这一区域。寺庙道观主要分布在城东北部,包括明教寺、宝莲寺、地藏寺等,官绅世家的高档居民区主要集中于城市的南半部,如环翠山房、澄园、中和堂、三至堂、宜园、西岩书堂、安边堂、逸圃等。
城内也已经有了同外地进行经济联系的场所,清朝中期的合肥城已经有有金斗(合肥本地)、徽州、泾县、旌德、金陵(南京周边)、姑苏(苏州周边)、宁绍(宁波、绍兴)、镇扬(镇江、扬州)、山陕(山西、陕西)、山东、福建、江西、广府(广州周边)、潮汕(潮州汕头)、两湖(湖南、湖北)、龙游(浙江衢州)等地商人的会馆。再把视线转移到城外,合肥七座城门除了水西门以外,在城外都有民房区,西平门外的二里街(今长丰路部分)是当时的一个棉花、棉布市场,农闲季节会举行集市,而大东门、小东门外就是南淝河,自然成为客运码头的所在,当时的庐州百姓多在那里上船到外地。在城区的其他位置则分布着大大小小的街区,以各类标志景观为核心,环绕四周。
3 明清合肥城市人文景观
具有一定年代的历史古迹和景观建筑在明清两代也大都得到了留传与确证。首先是桥梁,合肥城市所处水网密集,作为与百姓息息相关的城市基础设施,桥梁建设自然有着很重要的地位。自宋孝宗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淮西元帅郭振扩建唐置金斗城,将金斗城重新规划,合肥城向北扩展几乎一倍,唐置合肥城的北濠——南淝河成为城中之河,建成宋置合肥,即斗梁城,现代合肥城的城貌大致显现。从那以后,合肥城的外延基本没有大的变化。我们今天所说的合肥城内,就是指宋置合肥至1952年以前的合肥城了。而直至1954年将内城河流全部填平,金斗河东段彻底被改造为淮河路,合肥城内两条水津金斗河与九曲水上约有大大小小20余座桥梁,可谓“依依杨柳飏晴晖,临水渔家半掩扉。”
合肥城内据嘉庆八年的《合肥县志》记载,有跨金斗河大桥3座,街桥5座,至今尚存有迴龙桥、凤凰桥、九狮桥、飞骑桥等地名。2006年宿州路改造工程中,曾出土清代鼓楼桥遗址,这都是明清合肥确定地名而一贯保存下来的。合肥城第一次系统的地名及地标确认是在嘉庆年间的1803年,当时就已经很严慎的考虑到了文化传承和当世作用。合肥城内河流,首推贯穿城池由西向东的古施水的一段金斗河。金斗河从西起,有五座跨河大桥;金斗河水流到东水关,左右各有两支支流,七星塘水绕过小史河由南向北汇入金斗河,上有两座街桥;窦家池水,由北向南汇入金斗河,上有两座街桥。九曲水是合肥城内另一条河流,其自合肥城西南角龚家塘汇城西诸水,穿过八座街桥汇入金斗河再向东注入南淝河,史载“东过回龙桥……至藏舟浦,入金斗河。”[8]
合肥城内还有些杂流水塘若干,如梁家池(现老安徽日报社东侧)、赵家池(现环城西路莲花庵北侧)、龚大塘(现龚大塘巷北侧)、放生池(现安庆路与大众巷交口西南角,有涵洞通石河)、金斗池(蔡大堂、现杏花公园南侧水域)、娘娘池(王大塘、现杏花小区北)、北门大街散水(现逍遥津公园西部)、逍遥津(窦家池)、四牌楼东散水(现中菜市路,流入金斗河)、七星塘水(省政府南门红星路上)等等,另有早在嘉庆年间就已经难觅踪迹的大名鼎鼎的曹操藏舟浦和笛筝浦等。这足可见当年的合肥城内,水网密布,河流纵横。粗略算来,仅仅合肥城墙以内,河流两条,浦塘众多,记名的大小桥梁十八座。这些城内的水道和桥梁,曾经沟通淮河和长江,运输着南来北往的货物,输送着东游西走的人流,这些水流,养育着居住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展现着水运交通对于都市发展的特殊决定作用,三千多年间,一度作为侯国、州治、府治,最终成为问鼎江淮的军事重镇,形成了现在的安徽省省会,可以说合肥,原本就是成长于水中的一座城池。时至今日,合肥城依然是四水环绕:东门外南淝河,依然有从巢湖逆水而上货船,南侧的包河和银河风景如画,绿树成荫,展现着明清两代作为文教区的浓厚文化底蕴,还有曾为西濠的黑池坝,庐阳西南成为省机关招待重地的雨花塘与稻香楼河,都展现了水与桥梁同这座城市的过往繁荣中密不可分的联系。
城市景观是城市中由街道、广场、建筑物、园林绿化等形成的外观及气氛。自然景观与人工景观的良好结合能够形成有序的空间形态。明清之际的庐州府城,从嘉庆县志以及光绪庐州府志等记载中可以看出已经有了较早的对于形胜和古迹的利用与保护思想。庐州府志对于庐阳八景的描述就可略见一斑。具体说来,的确展示了合肥城市在作为行政意义上的地方首府之余,不断的都市化进程中,还是充满了商业与文化因素的。城市空间不仅仅是一个通过直观获得的表象,伴随着市民意识的觉醒,也逐渐成为情感体验和理性反思的对象,我们时常关注江淮战事对于合肥城防的影响,行政功能对于城市布局的塑造和建筑的要求,再者就是文教上官府与民间的互动,然而明清之际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封建制度达到顶峰,市民对城市景致的主观体验对城市而言就有了愈发重要的作用。这些源自城市史、文明史的影像靠着三国故地、唐宋繁荣以各式各样的方式展现在合肥都市文化的各个层面,诸如藏舟浦,《太平寰宇记》:“合肥县藏舟浦,即曹操与孙权藏舰于此。唐贞观十年,刺史杜公作斗门,与肥水相接。”[10]还有镇淮楼,明黄道日《镇淮楼晚眺诗》:“台临河势曲,楼敞夕阳偏……雨消青野暗,风断杨柳烟。为惜湖山迥,长歌思悄然。”[9]逍遥津南侧的明教寺,坐落在“教弩松荫”之称的教弩台上,初建于南朝梁武帝年间(502—549年),旧经云:“昔魏武帝筑台,教强弩八百人,以御孙权棹船。”[9]《舆地纪胜》载:“在城岁丰桥北,即魏武教弩台。唐大历中,得铁佛一丈八尺,奏为立院。”[11]这些景致既在城市实体上留下印迹,也展现了自己绵延千百年的文化风韵。透过种种普通民众能够直接感受到的都市景观,城市的曾是状态、现在状态与将是状态实现了交融,一种由物理事实做载体的承载着合肥历史底蕴的都市文化和老合肥的市民心态就这样不自觉的形成了,从古具有的“风俗淳朴、崇俭重名”[12]之风代代相传,这也正是城市空间格局中带有知识性和历史性的公共文化场域对作为主体的人的一种知识传递的交互体验。
再说到一度作为商业中心的城隍庙与思惠楼,城隍庙大殿始建于北宋仁宗时期,公元1051年。城隍庙后的思惠楼始建于1509—1515年,城隍庙其他建筑建于1871—1879年,思惠楼由明代庐州知府徐钰募集地方资金始建,得名于“思民之惠”。《康熙志》:“在府城隍庙后水上。明正德间,知府徐钰建。登楼环望,烟火万家,即思惠及于民,故以名焉。”[9]而在合肥东南的文教区,这里最为核心的都市景观就是包河与包公祠,明代包公祠建筑群建在了合肥城南的护城河边,这段护城河因为包公祠、墓而得名包河。据《江南通志》:“在南城濠水中,为包孝肃公读书处。”[13]原先的祠堂曾在1129、1276年毁于金兵、元军攻城的战火,几经修复在1486年又因为意外的火灾而毁损。1488年庐州知府宋鉴重建被大火毁坏的包公祠时,见到城南护城河畔环境优美,将原本位于城内的祠堂迁到现在的位置,祠堂所在的这个小岛也就改名为香花墩,当时的名字是包公书院,除了祭祀包公外,还作为包家后人读书的私塾。1539年御史杨瞻改名包孝肃公祠,专门祭祀包公。合肥包公祠是祭祀时间最久、年代最古老、遗迹最多的一座包公祠,其整体建筑风格很富有合肥地区明清民居的特色。
根据清嘉庆《合肥县志》里所附地图重绘的合肥老城区古今对比,我们可以对明清合肥城市的大致格局有一个对比性的系统认知:城墙里从东到西横贯合肥城的是金斗河,西南部较长的河流是九曲水,东北部从逍遥津流到金斗河的是九狮河,又叫逍遥津河,东南部从今天安徽省委流到时雍门(小东门)的是时雍河,这些河流现都被填平,而这些古桥、古街道没有一座、一条留到今天。城墙里的八个水塘,只有西北部位于杏花公园里的金斗湖,和位于逍遥津公园里的逍遥湖保留至今,图上的古建也只有很少的几处留存下来,有很多不是毁于战争而是毁于二十世纪中叶的旧城改造。始建于1169年,长23里,直线距离8700米的古城墙在1952—1954年被彻底拆除。城中的笔架山和城墙西面将军庙所在的小土丘也因为筑路的需要早被铲除。合肥曾经是一座多水的城市,清代庐州城内有四条河流,城外1里之内有南淝河、拱辰河(在南淝河北一里,已填平)、包河(当时尚与南淝河相通,1938年日军为了从时雍门(小东门)进出方便填平东北面的河口)、石河(黑池坝、琥珀潭、雨花塘、银河原本连在一起称石河)4条河和一些水沟,人称“八水绕庐州”,稍远则有东门外3里的小河、南二里河、西二里河、白水坝湖等,但是自从1950年代以来因为城市建设已经有数十条河流和数不清的水塘被填平。
4 结语
明清时期是合肥主城区轮廓与形制的建成阶段,这一时期,就其整体规模而言东、北依南淝河,西、南靠石河、黑水塘的近圆形地带业已形成,合肥城已具有今天环城马路中之规模[14]。就其城市功能而言,同一种土地利用方式对用地空间和位置需求也逐渐具有趋同性,导致同一类活动在城市空间上的聚集,从而形成行政、文教、商业、宗教等具有明显特性的土地区块。在这些地理单元中,形成了各具风格的城市人文景观,很多景观得以留存并在今天成为一种具有公共文化特性的复合型场域。这些都是历经一系列的功能变迁与形态演进直至明清才走向稳定的,这其中包含城市土地和建筑使用、城市空间和街区风貌的一体化动态进程。总之,合肥城市自身在历史建设过程当中,有大量的城市布局、城市结构、城市管理的经验,以及历史资源积淀,这就需要需要寻找、保护、开发、宣传合肥的古迹和传统文化遗存,需要更好地进行古迹的保护开发与现代化大都市建设的并行发展。相较于目前长三角城市圈其他城市以及中部大型城市武汉、长沙等,合肥城市在历史文化街区上的探索有其可取之处,但更多的是展现出竞争力与吸引力上的孱弱,因而研究合肥明清阶段主城区的建成过程,也是探寻本源、经世致用的历史与现实需求。
再者说,合肥自明清以来形成的基本城市格局,以及现存可考的内部城市景观及其遗址,包括城隍庙、鼓楼板块,东南包公祠、明教寺板块,城市水系桥梁、历史街巷等,都是极为可贵的历史标记,亦是合肥都市建设应当重点考虑的历史空间。无论是老城区提升,还是新区三面整合,都需要从中去找寻开发的历史渊源与现实意义。当下城市建设者已经意识到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重要性,但相关措施仍不够有力,资金投入和历史文化产业项目打造还存在缺位问题。许多在大建设过程中被遗忘的地域和文化特征需要在保护恢复的基础上开发建设,以此来创造更有生命力的城市景观,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服务业规划开发的直接要求,亦是远景区域整合的重要战略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