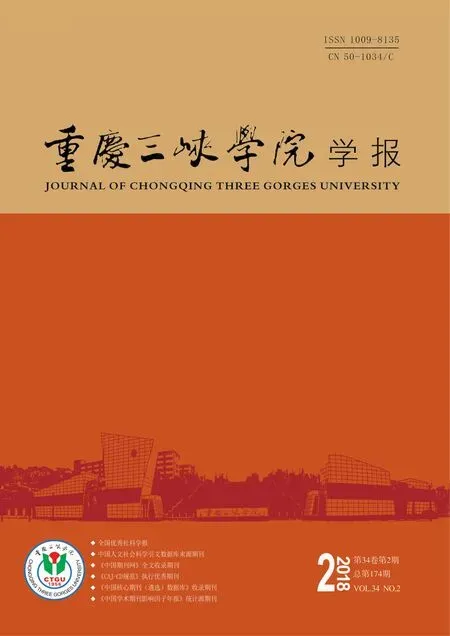清代吏员的制度“安顿”与吏弊关系刍论
2018-03-28陈一容
陈一容
清代吏员的制度“安顿”与吏弊关系刍论
陈一容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 430075)
吏员是清朝各级政府的具体办事人员,在政府职能履行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与此同时,吏员的弊端也甚严重,形象也多负面。深入挖掘清代吏员制度的顶层设计可以发现,导致吏弊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本身:额定编制太少,人手不敷,额外人员的控制、管理困难;法定地位低下,仕途基本无望;经济收入十分微薄,生计困难,办事积极性欠缺,甚至被迫法外牟利。因此吏弊的避免显然在于吏制变革,所惜者终有清一代未能根本解决。
额缺;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吏弊
清代的吏,又称“书吏”“书办”。它们一方面“治其房科之事”[1]卷十二129,与官共同发挥着“共天下”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以其舞文弄法,给清朝社会带来严重“弊窦”而遭致诟病和否定。事实上,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原非天生性恶,甚而是“皆有天良”之人,“夫胥吏即百姓也,非鬼蜮禽兽也”[2]卷二十一袁枚《答门生王礼圻问作令书》778,“只以人之才质不同,趋向各别”而为吏应役”[2]卷二十四陈宏谋《分发在官法戒录檄》915。可为什么“一受是役,鲜有不为害者”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清朝吏员制度“安顿不得其法”[3]卷七29-30:制度既令其以有限的额缺,承担国家管理中的全部“房科之事”,又不给予吏员最基本的利益保障,从而导致吏员人手不敷,法律地位低下,政治前途暗淡,经济收入微薄,终日“宵旰竭蹶”却生计难保,且被人视为猪狗不如的吏员“自弃于恶”[4]卷二十二鲁一同《胥吏论一》609便势所必然。
一、吏员编制、职责与吏弊
清初各衙门书吏“俱以政事繁简为额”,康熙七年(1668)“始定经制数目”[5]卷之十五《吏员》581。据笔者统计,京城中央各部院寺监等所有衙门吏额为1 328名。地方吏员额缺,总督衙门辖2省者典吏30名、承差20名,辖1省者典吏20名、承差10名;巡抚衙门除江苏、安徽两省书吏各30名外,其余各省书吏都是20名;直省各道的典吏、书吏编制不尽一致,如直隶典吏12名、书吏16名,江苏各2名,安徽2名3名,山西各2名,河南各16名,陕西10名14名不等,甘肃10名12名14名不等,四川3名8名不等;府以下吏额也各有不同,府衙门典吏7~24名,州衙门典吏6~12名,县典吏2~12名不等[5]卷之十五《吏员》581-616。康熙以后,“各随衙门添裁不一”[6]卷之二十一《吏员》975,但变化不大,到光绪年间,全国经制吏员为32 648人。
“吏役本为簿书而设”,其职责和任务在于治理“房科之事”。各级政府的“房科之事”,虽然因衙门类别、性质而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是方方面面,无所不包。“大命盗重情,小则户婚田土……州县一切招详及自理案件,势不能不假手于书吏。”[7]37“事权之重,虽欲不归之于吏,不可得也;为吏者虽欲避之,亦不可得也。”[8]213-214吏员的职责不仅范围广泛,而且十分复杂和具体,如州县除正常的文书报告外,每年竟另有100种以上的报告和保结册结必须拟制,且每一份报告必须同时制作副本多至6个到7个,公务繁忙的州县,因此需百名以上的吏员,就是政务简易之的县份也要吏胥数十名[9]69。而各州县吏员定制,如前所述,仅区区6~12名不等,即便是吏员编制最多的甘肃中卫县,经制吏员也只有25名;省级总督衙门的吏员编制,一般也就30~50人不等,额缺至多的闽浙总督衙门也不过59人而已。一位著名的地方大吏奏折称,总督衙门吏员人数,若照定制数目,那怕再增加一倍,各具体办事部门也“不过寥寥数人”,而不能办公无误[2]卷二十四田文镜《覆陈书役不必定额疏》907。经制吏员人手如此严重不敷,又要维系各级政府机构乃至整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行,各级机构、部门因此不得不再额外大量招募诸如贴写、书识、帮差等非经制名目的书吏来处理事务,各机构的实有书吏,因而自然会大大超编。湖北布政使衙门“除经制外,召募缮写一百六十名……一遇赶办奏销、详请题咨等项,事件丛集,又另倩清书帮办”,按察使衙门“吏书除经制外,召募缮写一百五十名,一切钦部及自理事件并奏销、秋审等项,亦另倩清书帮办”[7]30。事务殷繁的陕西布政使衙门“设有上下两班书役,迭相更换,各有一百四五十名;又雇用贴写六十余人,方敷分任书算之用”[7]31。总督田文镜所在衙门“办事书吏,头班二班,俱有百余名,是较经制十倍有余”[2]卷二十四田文镜《覆陈书役不必定额疏》907。各额外书吏补充入役,固然缓解了经制书吏人手过少的矛盾,使国家机器能够得以运转,但是,由于他们系经制书吏私人所雇之人,不入正式的职役编制,在性质上属于临时性质,这就加大了政府的管理难度。“吏胥之姓名,非若士人之登天列府贤书者,可一一稽也。朝而革,暮而复入,革于此,复移于彼。至万不得已,而又使其子弟为之。”[2]卷二十四储方庆《驭吏论》906他们也因此而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小则希免差徭,大则借端生事,自恃衙门情熟,因而包揽钱粮,把持行市,窝娼窝赌,无所不至”,成为吏弊的渊薮[2]卷二十四田文镜《覆陈书役不必定额疏》907。有清一代,作为吏弊整饬措施之一的“裁革之诏”也因之不能(实际也无法)得到落实。“今日汰而明日复矣……夫以朝廷之尊,立意欲革一时,去一人,易置大将,如呼小儿,罢遣卿相,朝下而夕出国门,独于吏胥之至微贱,额而限之,易若举手,乃若泰山之不可拔,决水之不可御。”[2]卷二十四侯方域《额吏胥》903
二、吏员的政治法律地位与吏弊
清代吏员“职役虽微,关系最重”[10]55,“上自公卿,下至守令,总不能出此辈圈牢䙌。刑名簿书出其手,典故宪令出其手,甚至于兵枢政要,迟速进退无不出其手,一刻无此辈,则宰相亦束手矣。”[3]卷七29官对吏“不能相离”[4]卷二十二鲁一同《胥吏论四》611,同时又“不能不用”[4]袁枚《答门生王礼圻问作令书》778并且“万不可无”[11]薛允升《读例存疑》卷七《吏律之一》137。可清政府对吏员法定地位的设计,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歧视,却与其职能、作用严重背离,清代的吏弊也就大大加剧。
具体而论,清代吏员的政治、法律地位,与历朝历代一样,首先是与“吏”的定义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据《说文》解释,“吏,治人者。”也就是说,“吏”原本主要指的是治理庶民之官员,大约自汉代以降,“吏”之地位逐渐下降而成为低微官员的称谓;隋朝大小官僚统一由朝廷任命后,“吏”便不再包括在品官范围,逐步沦落为官府招募的差役;元、明,由吏出职为官者固不乏人,然与官已成泾渭之势。到清代,经制书吏虽有额缺,且经过一定的方式和手续而被录用,进而为官府办事,但是,他们并无所谓品级,也没有职务、官阶,只为职役之人,即所谓“庶人之在官者”[12]卷三十五《选举考八·吏道》1024,与意为“给使役之人”的古代之“胥、徒”类似。更重要的是,清朝具有“宪法”性质的《大清会典》,更从法律上对吏员的内涵、地位做出了清晰的界定:“设在官之人以治其房科之事,曰吏。”[1]卷十二129这样,虽然从笼统或广义的意义上,清代的“吏”与“官”似有相同或近似之处,从而在文献典籍中或行政机构如吏部的指代等方面似与“官”相通,但就严格的意义而言,吏只是一种职役,与“胥役”在性质上并无二致,因此时人往往将其与胥合称,而曰“胥吏”“吏胥”“吏役”等等。“内外衙门之有书吏,犹古之有曹掾……今有召募充役,官府故皆名之曰役。”[13]卷二十一《职役考一》
由于《大清会典》对吏的基本定位及其制度设计,有清一代的吏员,便没有作为官员标识的官阶品级、顶带补服,也因此,他们不能入公堂正门,不能坐公堂之公座。考职后的书吏,如果冒戴顶帽,将照假官例,处以杖六十、徒一年的刑罚。即便是在考职之后候选期间,也是不能穿补服的[11]薛允升《读例存疑》卷四十二《刑律之十八》734,卷十九《礼律之二》311。至于“未经考职书吏,冒戴顶帽者,照假冒职官例,杖六十,徒一年”[11]薛允升《读例存疑》卷四十二《刑律之十八》734。“奴仆、皂隶人等”若“入正门、驰当道、坐公座”,才“杖七十,徒一年半”,而吏员、承差人却较此更“加一等”即杖八十,徒两年,说明吏员的地位连奴仆皂隶都不如。这样的规定,直至吏弊十分严重的晚清,也被认为“太重”[11]薛允升《读例存疑》卷十九《礼律之二》308。
清代吏员政治地位的低下,在其职役年限上也反映明显。比较言之,按照清代官制,官员只要其在任期间没有过犯,通常是不会被革职的,即便革职,只要不是革职永不叙用,在一定条件下,是有可能开复处分得以东山再起的。也就是说,清朝的各级官员为官任职到年老致仕,是有制度的保障的。然而,对于吏员,其制度设计的一般工作年限只有短短的五年,哪怕他们无任何过犯也是如此,即所谓“内外衙门书吏以著役五年为满”[7]卷二十一《吏员著役考职》1009,“五年而更焉”[1]卷十二129。由此出发,清政府还从行政法典、刑事法律两个层面制定了对于五年役满不退的吏员予以处罚乃至刑事制裁的依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明确规定:“倘有五年役满不退者,将该役斥革治罪。”[14]卷九十八《吏部·处分例》570《大清律例》进一步明确了“治罪”的类别、形式:雍正年间,清政府规定,吏员役满不退,处以“杖一百,徒三年,革役”,乾隆五年(1740)后制裁有所减轻“杖一百,革役”[11]薛允升《读例存疑》卷七《吏律一》136。封疆大吏如署理广东巡抚策楞欲留用役满书吏,也不得不加奏明。不仅如此,康乾时期律例还规定:“凡部院衙门书办,或因有疾,或因不谙文移,退役之后,倘有更名重役者,杖一百,革退。”[11]薛允升《读例存疑》卷七《吏律之一》136也就是说,不仅五年正常役满后,吏员不得重操旧业,就是五年期间的因病等特殊情况而退役,即便日后病情痊愈,也不能再为吏员,继续为吏的道路既断绝,非但生计无着,而且希望破灭,进取与上进心没有了。制度如是,也就难免使得吏员产生出不如在役期间提前捞一把的心理。
吏员役满,唯内阁、六部、太常寺等少数“事繁”的中央衙门,经该衙门堂官考察无过后,可作为从九品、未入流兼掣选用之外,其余事简的中央各部门以及地方省、道、府、州、县的全部吏员,虽然例准“考职”“以为仕进之阶”,但是,第一,吏员考职的人员范围有限,不是所有吏员都可以考职。会典则例及大清律例等,对此的规定十分繁密、具体,概而言之,只有那些家身清白、职役期间表现突出,并经相关人员证明的经制吏员,才有考职资格[6]卷二十一《吏员著役考职》1016-1019。第二,吏员考职入仕在铨法中的地位大为下降。明代文职铨法,进士、监生、吏员三途并列[11]薛允升《读例存疑》卷七《吏律之一》135,实际“亦有吏员累官卿贰者,况钟为郡尤有贤名”[4]卷二十二冯桂芬《易吏胥议》616。清朝“凡满汉出身之途,由科目,由贡监,由荫生,由荐举,由吏员迁秩改除”[15]卷五;“凡官吏之出身有八,一曰进士……八曰吏”[1]卷七80。可见清代入仕虽然多途,然吏员始终为殿。第三,考职规定严格并不断变化。清初,吏员役满考职,先由吏部考功司查准收考,然后送考选司复考授职。顺治十二年(1655),又题准在外收具原籍印文,在京取具同乡京官印结,并五人互结投部,复查照前册磨对相符者,方准收考[6]卷二十一《吏员著役考职》1016-1017。到雍正十二年(1734),地方又改令巡抚衙门考试,“议准,各省吏攒役满,各衙门印官取具本吏亲笔亲供、里邻结状,粘连地方官印结保送巡抚,巡抚于每年七月内齐集考试,其所考试卷即行封固,并各典吏著役日期、履历清册送部,定限十月内到部,考定名次品级咨发巡抚存案,仍将执照一并给发各巡抚转发各该衙门,令吏员自行领取”[16]卷十二《吏部》。乾隆十五年(1750)议准,“嗣后役满吏攅考试后,吏部严加校阅,分别去取,在京者吏部三月一次考试,将试卷固封,在外者各督抚于每年七月严考,将试卷固封,于年终汇齐校阅”[14]卷八十四《吏部·处分例》413。不过,除了特殊情形并经报准外,具有考职资格的吏员的考职机会只有一次,落选者,地方官员将其姓名、籍贯随同录取者名单一并送达吏部存查,以防止再考。第四,考职录取率甚低,其中被得取者多为虚衔而非一定能得实缺,就是候得实缺者,非但历时甚长,而且也不过是佐杂微员,几无晋升空间。清代吏员考职录取定制,“取者,京吏无过十之七,外吏无过十之五,其仅止一人,不敷录取者,如果当差勤慎、文理明通,亦准录取,一等为从九品,二等为未入流,咨部给照,遂注册入于铨选”[1]卷十二130。康熙后,考职录取吏员只授定职衔,并不即用,须先回籍候选,等得到实缺后才领凭赴任。“各部院衙门考授职衔之吏员,一经吏部榜示,即令司坊官严催回籍……如有潜住京师者,其藏顿之家,一并从重治罪……如仍潜住京城,亦交刑部从重治罪、递解押回。”[6]卷二十一《吏员著役考职》1015-1016雍正元年(1723)上谕:“自今以后书办五年考满,各部院堂司官查明,勒令回籍候选,逗留不归者,著都察院饬五城坊官稽查遣逐……各部院一年一次保结具奏,倘仍有潜居京师者……将保奏之大臣官员一并治罪。”[14]卷一四六《吏部·书吏》422由于铨选“颇难”,出仕渠道阻滞,故“有候至二三十年不得一缺者。及至得缺……其人大半老迈聋钟”[10]55。史料记载,从康熙十七年(1678)到康熙四十三年(1703)长达26年的考职裁取应选正八品以下官员的应选吏员,竟然到雍正二年(1724)也未能铨选[6]卷二十一《吏员著役考职》1021。即使已获实缺者,例仅低级杂职官。“凡吏员出身,顺治十二年题准,分为正八品、从八品,正九品、从九品,一等杂职,二等杂职,三等杂职。十五年,题准,吏员出身,止与九品以下职衔,分为五等。一等授正九品,二等授从九品,三等授一等杂职,四等授二等杂职,五等授三等杂职。康熙三年,题准,吏员考职,分为四等。一等以正八品经历用,二等以正九品主簿用,三等以从九品用,四等以未入流杂职用。”[6]卷二十一《吏员著役考职》920因而“其能干者,仅得从九、未入职衔”。清朝后期,“考职之例,现已不行”[11]薛允升《读例存疑》卷四十二《刑律之十八》736,吏员的考职进身也就名存实亡。有清一代官员出身资料显示,“由吏胥而为官者,百不得一焉”[17]《卷施阁文》甲集卷一《吏胥篇》25。由上可知,清代无论制度的设计还是事实,绝大多数甚且近乎百分之百的吏员,在五年役满之后,合法的官场服务生涯即告结束,必须另谋职业,重求生路。至于吏员捐纳入仕,自雍正起,虽然例属可行,且咸、同时代有所增多,但毕竟系另一路径,非考职入仕之途;各级官场中役满执役者虽然客观存在,但终究是非法的,且属于应当整治乃至打击的“吏弊”范畴。
中国历史上的贱吏之风,尽管由来已久,但“汉时县令,多取郡吏之尤异者”[2]卷十七顾炎武《补选》618,“元时小吏可致宰执台谏,明亦有吏员累官卿耳者”,只是到明中叶以后“始贱吏不用”[4]卷二十二冯桂芬《易吏胥议》615。到清代,吏员法定的政治地位低下,势必影响到社会对他们的客观评价,贱吏、仇吏之风进一步加剧。清朝官绅士人非但不正视吏员在实际政务中的主体地位,仅视其为“供奔走佐使之职而已矣”[2]卷二十一袁枚《答门生王礼圻问作令书》778,且普遍歧视甚至蔑视、侮辱吏员的职业,乃至人格。在他们眼里,“吏胥之役,岂可与官长之职同日而语哉?”[2]卷二十四储方庆《驭吏论》906其品性“原系寡廉鲜耻……惟利是图”[7]31,“类皆乡里桀黠者流,不肯自安于耕凿”,其行为“异于常人”,甚至“行己若狗豚,噬人若虎狼”[2]卷二十四储方庆《驭吏论》,牟愿相《说吏胥》905-906、915。一些官吏士绅提出“防吏胥如鬼蜮”[2]卷十六韩梦周《与阎阜宁》608,告诫子孙“勿作吏胥,勿与吏胥人为婚姻”[18]922。仕途既多无望,社会“贱而恶之者亦太甚”[2]卷二十四陈弘谋《分发在官法戒录檄》916,吏员的自我价值实现以及尊重层次的需要因此得不到满足,于是采取种种非法手段以达到对实际权力的追求及社会认同的补偿,也就成为自然、必然的选择。
三、吏员的经济待遇与吏弊
对于吏员的俸禄问题,有论者指出有品级者各按品级支给,无品级者一般按未入流支给(即岁支给银31.5两),有一定的俸禄和养廉银;但另一方面又说享受此俸禄、养廉银的吏员属于少数,主要是典史、吏目,其他吏员仅支给工食银,似乎吏员一般没有俸禄,只有工食银[19]597-598。那么,清代吏员到底有没有俸银呢?笔者查阅史料,没有发现有关吏员俸禄、养廉银制度的记载。唯于乾隆元年十二月初一日(1737年1月1日),浙江布政使张若震就严禁书吏迎送官员一事所上奏折中,见到“嗣又给与薪水、饭食,以资养赡”之语[10]54。相反,无俸银的记载倒有不少,如《清通考》卷21、《皇朝经世文编》卷24、王凤生《学治体行录》、汪辉祖《佐治药言》、方大湜《平平言》卷2、徐栋《牧令书》卷4、《畿辅通志》卷87等等[9]78。至上述有俸银之说,以及所举典史、吏目,严格讲他们已不是一般职役性质意义上的“吏”,而是经过考职录取的“官”了,也不是五年役期之时,而是役满之后的情形,因此并不能说明清代吏员有法定俸禄。
那么清代书吏的法定报酬如何呢?答曰“饭食银”。饭食银的标准,因时因地而异,且时断时续。顺治九年(1652)前直隶省各州县书吏的年饭食银为10.8两,金库书吏、官仓书吏都是12两[9]78。本年四月,“户部以钱粮不敷”遵旨会议做作出13项决定,其中之一就是减少吏役的工食银:“在外各衙门书吏人役,每月给工食银五钱,余应裁。”[20]卷六十四,顺治九年四月丁未499经此次减银,直隶州县的十二房书吏的年饭食银为4.8两[9]79。其后大约自康熙元年(1662)起,书吏的饭食银又被取消[9]79。从另外的史料看,各地实际情形可能不尽如此。河北东安县库书、仓书年支工食银12两,书办支7.5两;道光《祁门县志》显示,安徽祁门县学书工食银7.2两,书办工食银6两[19]598。光绪年间,山西巡抚衙门书吏的饭食银和“衙门各项人役工食银”定额银是2 192两(除去减成,年实支1 380两),该衙门有经制书吏20人,写本贴书、写揭贴书和随班贴书64人,另有其他各项人役数字不明,姑且不论,仅以书吏82人计,人均岁额银仅26.7两,除去减成,人均年实支16.8两[21]。此外,乾隆年间封疆大吏关于书吏饭食银的记载也是两歧。前揭浙江布政使张若震说浙江此前给书吏薪水、饭食,云南总督庆夏乾隆六年(1741)奏称:“窃查各省督抚藩臬衙门,书吏办理通省公务,岁给纸张、饭食……臣查滇省督抚衙门吏书饭食……奏明在□正额盐务盈余项下动给,其纸张银两在云南府税款项下支给;藩司衙门吏书饭食、纸张银两,详明在于公件、合平等项分别酌给……惟查臬司衙门管理通省刑名吏书八十余名,无款可动,各书待哺维殷。”[7]26湖北省书吏有饭食银,但标准多变,雍正十年(1732)经布政使徐本、按察使唐继祖请准,两衙门的书吏饭食、纸张银分别为500两,但这笔费用后来“屡被要求俭省”,乾隆九年(1744)经湖北巡抚晏斯盛再次奏准,才得以恢复500两银的水平[7]30。上述诸省书吏是有饭食银的,但下列几条史料似说明有的省份则没有。乾隆初云南布政使陈弘谋说:“直省各衙门门皂等役均有额设工食,惟书吏并无额设工食。”[10]55乾隆十年(1745)署陕西布政使慧中说:“陕藩事务殷繁,设有上下两班书役,迭相更换,各有一百四五十名;又雇用贴写六十余人,方敷分任书算之用。伊等身虽在公,原无工食,每年仅给公用并额编正项册籍等银一千二百余两,不足以资养赡。向日亦未定有章程,止所各书随事需索。各属给与陋规,或多或寡,每年约数千两不等。”[7]31
吏员中虽不乏家庭殷实的挂名书吏,然他们“足迹不至衙门,经年不见本官,不知办案为何事,差遣为何事,按册有名,服役无人,惟津贴纸笔之费,以帮办事书役”[2]卷二十四田文镜《覆陈书役不必定额疏》907。各级衙门的房科之事,实赖挂名书吏之外的一般书吏。这些书吏的绝大多数实来自穷苦民人,获得衣食之源是其为吏的主要动因之一。但他们服务终年,却没有作为报酬的俸禄,只有微薄得无以复加的“饭食银”,还得自己花钱购置包括毛笔、墨汁和纸张等在内的办公用具。严重的收支倒挂,不但与劳动付出极不相称,而且有违为吏之经济初衷,难以维持自身和家人的生计,“灯油、纸张、饭食均无所出,纵欲竭蹶办公,势难枵腹以应”[10]55。制度既定的合法收入有限,制度之外的非法利益获取就成为最后的必然的选择。于是“吏部之赴选有规、起用有费、考察有仪”[7]34。“上宪之书吏则鱼肉州县之书吏而并能挟制其官。州县莅任,先索到任陋规,其后交代有费,盘查有费,经征有费,奏销有费,滋生烟户有费,赋役全书有费,蠲除有费,工程有费,恩赏有费,领有领费,解有解费,划扣有划扣费,举州县毫毛之事,莫不有费。”[2]卷二十四周镐《上玉抚军条议》913康熙八年(1669)六月监察御史赵璟所上条奏,也清晰揭示了官员报酬多寡与为官廉贪的内在逻辑联系:“查顺治四年所定官员经费银内,各官俸薪心红等项,比今俸银数倍之多,犹为不足,一旦裁减,至总督每年支俸一百五十五两,巡抚一百三十两,知州八十两,知县四十五两,(若以知县论之),计每月支俸三两零,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亦得费银五六两,一月不足五六日之费,尚有二十余日将忍饥不食乎?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若督抚势必取之下属,所以禁贪而愈贪也。若初贪不得已略贪下赃,赖赃以足日用,及日久赃多,自知罪已莫赎反恣大贪……臣以为俸禄不增,贪风不止,下情不达,廉吏难支。”[22]卷九151该御史所论对象虽是职官而非吏员,然对清代吏员之弊缘由的认知不无意义。盖定制收入大大优厚于吏员的职官尚因不足而贪污,本无俸禄、仅少得可怜的饭食银的吏员,其生活窘境及法外勒索,更可想而知。所谓“书吏索钱,功令虽严,犯者究不能无;名为画革陋规,而暗地索取究不能免,盖为此也”[10]55。
清朝国家吏员制度“安顿”的“不得其法”,与吏员的法外舞文、营私牟利之弊,具有直接的因果联系。清朝吏弊问题的根本解决,当然在于吏员制度本身的变革。不少官绅于此“最难安顿”的问题也多所探索,四度署理封疆的梁章钜,就曾借杨芸生之言批评朝廷吏员制度“安顿不得其法”,进而在其《制义丛话》中以海盐彭孙贻“耕者之所获”一节题文所云,提出予吏员“食于农”“获于耕”的生计之路[3]卷七30。如此解决吏员政治待遇、生存困难,避免其法外牟利之弊的“安顿”建言本属不少,惟作为国家层面的吏员合理“安顿”制度,直至清朝的最终覆灭也未有实质改变。吏弊之锢因此日盛一日,最终连同“不得其法”的吏员“安顿”制度及其母体——清朝政府一起被葬送。有清一代吏员制度的不良及所导致的吏弊丛生,虽然已成为历史,但它给予后世的社会成员政治、法律地位的公正公平,以及基本生存的兜底、保障,国家顶层“安顿”制度设计之不可或缺的历史警示,是十分深刻并应当汲取的。
[1]昆冈,等.钦定大清会典(光绪)[M].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2]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G].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本.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
[3]梁章钜.制义丛话[M].上海:上海书局,光绪十八年(1892)石印本,西南大学图书馆藏.
[4] 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续编[G].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本.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
[5]伊桑阿,等.大清会典(康熙朝)[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本.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
[6]允禄,等.大清会典(雍正朝)[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本.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4.
[7]哈恩忠.乾隆年间整饬书吏史料(下)[G].历史档案,2000(3):25-39.
[8]赵世瑜.吏与中国传统社会[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9]瞿同祖.清朝地方政府[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0]哈恩忠.乾隆年间整饬书吏史料(上)[G].历史档案,2000(2):53-59.
[11]胡星桥,邓又天.读例存疑点注[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
[12]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3] 张廷玉,等.清朝文献通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14]昆冈,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M].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5]允裪,等.钦定大清会典(乾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6]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乾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7]洪亮吉.洪亮吉集[M].刘德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
[18]王夫之.传家十四戒[M]//船山诗文拾遗书.船山全书:第15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19]黄惠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20] 清世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1]刚毅,安颐.晋政辑要[M].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22]蒋良骐.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
(责任编辑:滕新才)
Discussion on the System about Officials in Qing Dynasty
CHEN Yirong
In the Qing Dynasty,officials were clerks of governments of all levels,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performing governments’ functions.But there were also many drawbacks of officials,and negative description of officials counts more.Through research on official system in the Qing Dynasty,it can be seen that the primary cause of these drawbacks was the system,such as lack of work out,the management of additional personnel were difficult,low official status and hopeless political prospect,poor economic treatment,leading to the lack of career enthusiasm.Therefore,only official system transformation can overcome these drawbacks.Unfortunately,the problems were not be solved by the late Qing Dynasty.
work out;political status;economic treatment;drawbacks of officials
陈一容(1961—),女,四川大竹人,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州县问责制度与地方社会治理”(12YJA770007)后期成果。
K249
A
1009-8135(2018)02-007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