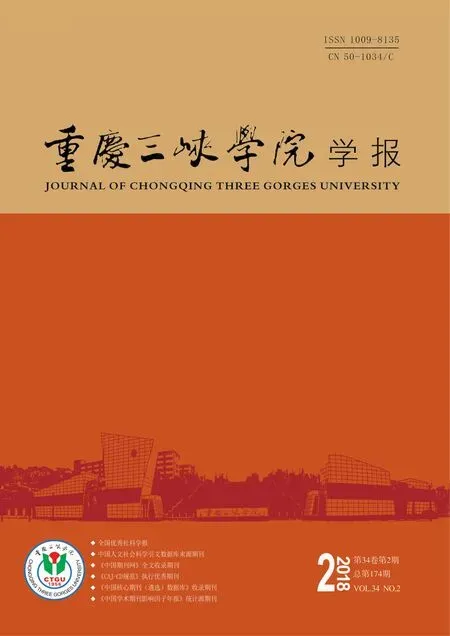明初黔江军事移民与本土化研究
2018-03-28曾超
曾 超
明初黔江军事移民与本土化研究
曾 超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重庆 408100)
在明初,因黔江守御千户所的设立,一批原籍江南的军户移驻黔江,成为黔江的军事移民。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军户及其后裔弃武就文、弃武经商,通过本土化而逐渐演变成为黔江地区的民众。
黔江;军事移民;本土化
明初因朱元璋的统一战争,蓝玉征黔,原籍江南的一大批军户入驻黔江,成为军事移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批军事移民在黔江建基立业,开枝散叶,演变为黔江民众,其千户、百户之官如孙氏、宋氏、谢氏等逐渐成为地方大族。这个过程应当说是一个转换、调适和土著化的过程。对此,前人少有研究,故此对黔江军事移民的土著化聊陈己见,敬请方家指正。
一、明初黔江的军事移民
在中国古代,移民地域广布,数量庞大,类型不一,移民文化丰富,移民影响深远。就移民类型而言,有强制性移民和自愿性移民之分,有政策性移民与自发性移民之别,有政治移民(迁徙豪强、官员流贬、仕宦留驻、避难移徙等)、军事移民(募民实边、移民屯垦等)、商业移民(经商定居等)之类。在黔江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移民现象多有表现。就其军事移民来说,早在先秦时代就有巴人移居黔江,唐代有庞氏移居黔江,清代亦有焦君玉征战黔江而留驻黔江。当然,秦汉以后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军事移民是明初。
(一)军事移民的原因
明初,一批以孙氏、谢氏、宋氏为代表的江南地区军户移民黔江。这与元末明初的社会情势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与明初蓝玉征黔关联甚大[1]。
元朝末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社会矛盾集聚激化,以致天下分崩离析,群雄逐鹿中原。朱元璋采纳朱昇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其势力迅速崛起。1368年,朱元璋称帝,改元洪武,国号明,以南京为京城,标志着明王朝的建立。为了推进明王朝的一统大业,朱元璋开始布局、谋划翦除地方割据的一统战争。其时,主要的割据势力在北方是蒙古残余势力(北元),在西南则是明玉珍所建立的夏政权。洪武三年(1370),明军以徐达为大将军北伐,远征北漠,取得辉煌的战果,解决了北元势力,北方边庭得以解决,由此开始处理、解决夏政权问题。
大夏本为明玉珍所建农民政权,后演变为地方割据政权,以重庆为都,据有巴蜀之地。1351年,韩山童、刘福通、韩林儿杀白马盟誓,起义反元,元末农民战争正式爆发。乘此天下大势,各地豪杰纷起反元,徐寿辉、郭子兴、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先后崛起。明玉珍乃屯兵青山自雄,后加入徐寿辉领导的红巾军,担任元帅一职。至正十七年(1357),明玉珍西征入蜀,攻克重庆。十八年,攻克嘉定,拥有全蜀。二十年,因陈友谅篡弑谋杀徐寿辉,乃自称陇蜀王,走上独立自雄道路。二十一年,南征北讨、东进西击,击溃四川元军主力。二十二年,正式称帝,改元大统,国号大夏,以重庆为都。
1368年,明庭肇建,为推进江山一统的大业,朱元璋致函明玉珍之子明昇,望其“度德量力”“审机识变”,渴望“不战而屈人之兵”,和平解决夏政权归属问题;次年,又派湖广行省杨璟对之招降,虽然“恩威并用”,但明昇拒不听命,招降没有取得实质性效果。在招降不成的情况下,朱元璋决定运用武力解决问题。1371年,朱元璋集结重兵,以汤和、傅友德为帅,以周德兴、廖永忠、杨璟、顾时、何文辉为将,从南北两路水陆并进,直取重庆。是年六月,明军进抵重庆,明昇出降,夏政权灭亡。此后,明王朝继续经略原夏政权属地,黔江即在其中,因之朱元璋以蓝玉为大将军,率兵西征,进驻黔江,史称“蓝玉征黔”。
黔江,元末为夏政权属地,这里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民情复杂,民风剽悍。黔江本境虽在汉末即纳入全国一体化的郡县制体系之中,设立有丹兴县,但随之“五胡乱华”“僚人入蜀”,黔江沦为“夷境”。唐代虽然加强对黔江的经略,设有石城县,但晚唐乱离,再次沦为“蛮域”,“为龚、胡、秦、向土豪分据”。同时,黔江周边土司林立,酉阳、唐崖等环伺。故在这种情况下,蓝玉征黔既有封建王朝一体化经略的性质,也有封建王朝开疆拓土、赶苗夺业(赶苗拓业、赶苗图业、赶苗夺籍等)的意蕴。故新版《黔江县志》说:“公元1372年,明军征黔,掀起所谓‘赶蛮拓业’。”[2]
蓝玉征黔分别在洪武五年、洪武十一年两次进军黔江。关于蓝玉首次征黔,清光绪《黔江县志》卷三《武备志·武事》[3]、咸丰《黔江县志》卷二《武功志》[4]、酉阳《冉氏家谱》引黔江朱衮、潘澄夏《复镇夷乡碑记》[5]、新编《黔江县志》等均有反映。至元二十二年(1285),明玉珍割据巴蜀,黔江成为夏政权属地;洪武五年(1372),蓝玉征黔,部将赵士英率兵士3 000人从巴东进兵,经施州,直取黔江,“赶蛮夺业”,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省黔江入彭水县,同时修建石城,屯兵戍守。
蓝玉首次征黔虽然获胜,但后坝、峡口、水寨、栅山等处仍然为蛮酋土豪龚氏、秦氏、向氏、胡氏等占据,这无疑是不利于中央王朝强化统治的巨大隐患。为有效打击蛮酋势力,真正确保明王朝在黔江的统治,蓝玉决定二征黔江。鉴于黔江周边溪洞蛮夷错居杂处的特殊情况,洪武十一年(1378),“彭水知县聂原济言,黔江地接散毛、盘顺、酉阳诸洞,蛮寇出没,屡为民患,宜设兵卫屯守”[6]卷三十七,洪武元年十二月壬辰1944,乃设黔江守御千户所,由朝廷派驻军队镇御。
(二)军事移民的姓族
在元末,最早由湖广地区移民黔江的当在明玉珍入川时期,因为陈友谅篡弑徐寿辉,明玉珍率领大批湖广籍子弟入川,同时还采取不少优惠的政策招徕、吸引湖广子弟入川,这已为广大从事移民研究的学者所关注和证实。蓝玉两次征黔,当亦有不少军士留驻黔江。当然,更为直接的则是因为黔江守御千户所设立而进入黔江的卫所军士。就目前所见史料,黔江军事移民多在洪武初年。时间定在洪武二年(1369),参见《黔江县地名录》收录的城北公社石峡大队地名“孙家营”条[7]。问题是洪武二年黔江仍为大夏政权辖地,明王朝何以在未解决夏政权之前就移民屯驻黔江呢?
明初移民黔江的军户主要是以孙氏、谢氏、宋氏等为首的江南“十九大姓”。目前能考见的姓族主要有:
孙氏:黔江守御千户所千户孙旺之后,原籍安徽和州。孙氏移民黔江,主要有三类史料。其一是方志,如《黔江县志》:孙姓,始祖孙旺,原籍和州,其后裔分住城北、南海、正阳、后坝、太极等乡和冯家坝镇[2]619,584。其二是地名录,如前述“孙家营”的解释。其三是墓志,据《黔江文史·墓志铭专辑》[8],言及孙氏移民黔江的墓志有《上寿孙维清墓志》《清诰耆英孙公德松字光先墓志》《清例赠将仕郎孙公克开寿藏志铭》《例赠修职郎孙公祖植字玉科墓志铭》《明授骁骑将军孙公云锦墓志》《清故岁进士孙公颍川墓志铭》等。除这3类史料外,还有黔江孙氏族谱、姓族、宗谱一类的家谱。
宋氏:武略将军宋陆之后,原籍凤阳府宿州。《黔江县志》说:宋氏,以武略将军宋陆为祖,原籍宿州,洪武十三年(1380)入黔,定居落业,后裔分居联合镇、青冈、正阳等地[2]445。宋氏入黔,在黔江遗存的墓志铭中亦有反映。《宋远长墓志》载:“始祖陆公,武略将军,起自江南凤阳府、宿州市奉拨星大上。当洪武十三年践祚之初,拨发驻防,合十九大姓,奉旨率兵万二千余,起自南京,扎营黔邑平蛮。领旗,而总旗百户而千户,迄今历历名人已五百余年相传十有数辈。”[8]445据此可知当时入黔的姓族较多,共有“十九大姓”。
谢氏:督领百总谢昂之后,原籍江南。在《复镇夷乡碑记》中有督领百总谢昂[5]。如今,黔江尚有谢氏家族院落。谢昂后裔谢庆锡据《谢氏族谱》记载,洪武年间,护国将军谢钧杰被派驻黔江,定居正谊,“世守其地,世袭其爵”,其后谢昂(或称谢荣昂,谢钧杰之孙)任黔江守御千户所百户,封忠武将军;其子谢遇扬袭职,封昭信校尉;其孙谢春袭职,封诚信校尉;其曾孙谢志贤袭职,封忠武校尉[9]。
钟氏:黔守御千户所掌印钟天保之后,原籍江南。《皇明诰封明威将军钟公正阳墓志》称:“沐明洪武皇帝以武功承袭选卫黔守御千户所,掌印一十五年,勋猷丕著,驰赠明威将军……吾宗自始祖天保公由江南将军领兵入川有功,赐袭千户。”[8]78—79
程氏:明千户程涛之后,原籍湖广麻城。《黔江县志》说:程涛,原籍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洪武二年,以武举授职千户,西征入川平蛮至黔江,有武功赐田宅于城东一带,遂落业。后裔分居联合镇、青冈、正阳等乡[2]。
王氏:据《冉氏家谱》,冉氏祖妣杨夫人墓碑题名有黔江守御千户所掌印指挥使、本司督工儒学教授王之藩,则入黔移民有王氏。
邢氏:据《冉氏家谱》,冉氏祖妣杨夫人墓碑题名经历司刑维谷。则入黔移民有邢氏。
徐氏:据《四川省黔江县地名录》,在原南海公社大路大队有地名徐家咀,从其解释可知有洪武入黔移民徐氏。
朱氏:据《四川省黔江县地名录》,在原南海公社有地名朱家沟,从其解释可知有洪武入黔移民朱氏。
肖氏:据《四川省黔江县地名录》,在原南海公社大路大队有地名肖家坝,从其解释可知有洪武入黔移民肖氏。
余氏:据《四川省黔江县地名录》,在原白石公社龙洞大队有地名余家营,从其解释可知有洪武入黔移民余氏。
(三)军事移民的遗存
在中国古代,移民到达新的居地后,往往会留下诸多的文化遗存,如建筑、家谱等,毕竟这是一种文化生成和创造。目前,在黔江有关洪武初年移民的文化遗存是《黔江县地名录》所载的部分地名。对这部分地名的解释反映了该地名的来历。在《黔江县地名录》中,作为入黔军事移民的地名主要有:
三屯乡:在原联合镇。得名之因是:清朝设乡置里时,因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黔江守御千户所千户孙旺屯兵于城郊之南沟、桃子坝、茶园三处,因名三屯乡。
孙家营:在原城北公社石峡大队,得名之因是:洪武二年千户指挥孙旺于此屯兵[7]。
肖家坝:在原南海公社大路大队驻地,得名之因是:明洪武年间,曾有肖姓人居此[7]23。
孙家坝:在原南海公社大路大队,得名之因是:洪武年间,当地居住的全是孙姓人[7]。
徐家咀:在原南海公社大路大队,得名之因是:洪武年间,徐姓人居住[7]23。
宋家坝:在原南海公社桥梁大队,得名之因是:明洪武年间,此地宋姓人多[7]23。
大营:在原南海公社田坝大队,得名之因是:明洪武时代,曾在此地驻过兵营[7]。
芭蕉盖:在原黄溪公社洋河大队,得名之因是:300年前,当地住户开始种植芭蕉[7]。
余家营:在原白石公社龙洞大队,得名之因是:明洪武年间有一余姓,带入来此定居[7]92。
孙家营:在原寨子公社蓬西大队,得名之因是:明朝指挥千户孙旺,曾率兵驻扎于此[7]。
朱家沟:在原南海公社,得名之因是:明洪武年间,有朱姓居此山沟[7]232。
二、黔江军事移民的本土化
黔江守御千户所的设立,其主要目的是控遏周边土司。因之,洪武初年入黔的移民,本身是有军事任务的。他们战时为兵,平时为民,且耕且战,服务于兵民合一、军政合一的军事体制。具体地说,他们的军事任务主要有三,其一是征战;其二是镇戍;其三是屯田。
以征讨而言,据新版《黔江县志》记载,洪武十六年(1383),黔江守御千户所官兵击破入寇施州的石柱蛮;二十三年(1390),驻节黔江的蓝玉官兵,平定散毛土司之乱,擒获剌惹洞长官覃大旺等1万余人。
又如屯田,据《酉阳直隶州志》卷十《武备志·兵制》《黔江县志》《邑令潘澄夏碑序》等记载,蓝玉平定黔江,设立黔江守御千户所,有正千户1员,副千户1员,管领百户5员,有“调设官兵”1 216名,其中守军608名,屯军608名。“守军分响给屯,屯军分粮以给守,互相通济”;“官军就地开垦,旧职指挥孙旺、督领百总谢昂等,自龙桥起,开鱼滩、小江、大堆坝、上下庙溪、官村、谢家坝,过小河泉门口、桐车坝,穿过高碛口、两河口,耕种为业。”黔江守御千户所的屯田,有桃子、茶园、南沟等三屯,后据此设为三屯乡。与彭水水田等处军屯,共24份。黔江守御千户所的军屯,无疑对有效解决官兵的粮饷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这些入黔移民,不仅在这里屯田戍边,而且还修建了黔江守御千户所的衙署,直到明万历年间始所、县衙署合一。据《黔江县志》记载载,洪武十四年,重新设置黔江县,县署与黔江守御千户所衙署并存,各为一城,文武兼治。到万历二十三年(1595),黔江知县何珩乃将二署合一,以致东南半城为石垣建筑,西北半城为土垣建筑。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由江南移驻黔江的移民逐渐著籍于黔,成为黔江人,这就是其本土化。这些军户的本土化应当说经历过一个漫长的调适过程,或者说极长的本土化过程,而且主要是这批军户的后裔逐渐完成的,明万历年间所、县合一即是这一本土化完成的标志。
所谓本土化,就是指移民由外地人变为本地人及其过程。黔江守御千户所的这些军户后裔之所以会本土化,是因为一方面本就带有一定的家小,他们早已与其原籍处于隔绝状态,且他们逐渐适应了黔江当地的生活。另一方面,这些军户及其后裔虽有军籍存在,但由于人口的繁衍,不少人随通过婚姻的方式,娶妻生子,从而转化为本地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积极寻求本土化的途径,以便更早、更好地融入当地,尤其是黔江守御千户孙氏的积极引导,不少人乃弃武就文、弃武经商、弃武力农。如孙旺之子黔江守御千户孙文在黔江“创文庙,兴学校”,于是这些军户后裔的生活于当地人完全无异。这里不妨以孙氏为例加以说明。
耕读传家:“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中国古代,“耕”以解决衣食问题,“读”以谋求社会发展,“耕读传家”成为中国人基本的传家模式。外迁入黔的孙氏也是如此。据《例赠修职郎孙公祖植字玉科墓志铭》,孙氏后裔“半耕半读”以致“富甲一乡”;据《上寿孙维清墓志》,孙氏后裔是“笃前烈而不忘耕读”。
忠孝传家: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宗法为本位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家国同构,家国同位,家国一体。家是国的缩小,国是家的放大。“在家为孝子,在国为忠臣”,故“忠孝传家”“忠君爱国”“忠事爱民”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上寿孙维清墓志》就记载,孙氏后裔是“持身独以忠厚为本”。据《清例赠将仕郎孙公克开寿藏志铭》,孙氏后裔是“惟孝友独存,敬养慎终”。
建立宗产:由于中国是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社会,因之家族、宗族管理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方式之一。为了有效增强家族、宗族力量,强化成员归属感,家族、宗族往往会采取诸多重要的举措,如修宗祠、修家谱、立宗产、祭祖扫墓等。孙氏在入黔以后也积极增进家族、宗族荣誉感、归属感,其中之一就是建立宗产。据《清例赠将仕郎孙公克开寿藏志铭》《清故岁进士孙公颍川墓志铭》,孙氏的宗产是“江左场四五楹,岁租二十金”,“环山一带,概属墓田暨坟山园子、石灰溪等业,年出租谷”。建立宗产的目的,其一是供清明等节日祭祖之用,“供春秋祭祀”,“准备清明祭费”。其二是为孙氏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员提供经费资助。“储为后代读书、应试需”,“储为后嗣游泮需”。其三是修建宗祠等公共建筑,《清故岁进士孙公颍川墓志铭》云:建立宗产可以“兼修宗祠”。其四是资助族中贫困者。
锐意功名:“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在中国古代,科举入仕是广大士人改变生活命运、提升家族、宗族荣耀的重要途径之一。因之,“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成为广大士子的基本追求,也是各大家族、宗族的基本追求。孙氏虽然其出身是军籍,但更深知科举之重要。特别是随着国家政治由崇尚武功到崇尚文治的转变,军屯体制的发展变迁,孙氏“创文庙,兴学校”,其目的即在于让其子孙驰骋于科举功名场,孙范就曾对其子孙祖植说:“人当有大志,汝其锐志功名,勿以家事累。”孙氏对科举功名的重视应当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据《清诰耆英孙公徳松字光先墓志》《例赠修职郎孙公祖植字玉科墓志铭》《上寿孙维清墓志》等,孙氏后裔弃武就文,偃武修文,锐意功名,终致“科第蝉联,书香不断”,“后嗣繁衍,科名不绝”。而孙氏也因为“创文庙,兴学校”“有功学校”演变成为黔江的“巨族”。
修建宗祠:中华民族是一个极为强调和讲究“尊祖敬宗”、重视孝道文化的民族,因之,各家族和宗族均不惜重金修建宗祠。宗祠即祠堂,不仅是广大城乡中规模最宏伟、装饰最华丽的建筑群体,更是凝聚族人荣誉感、归属感,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据《清例赠将仕郎孙公克开寿藏志铭》,孙克开是“老尤急宗祠”。据《清故岁进士孙公颍川墓志铭》,孙氏建立宗产的目的之一即是“兼修宗祠”。
力农经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驱”永远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对于广大的一般民众来说,对于那些善于经商理财的人来说,为了弥补家庭的窘境,为了发挥经商致富的聪明才智,为了解决科举失败的生计问题,不少人遵循“以末致富,用本收之”的准则,在强化“力农”的基础上,也“经商”致富,并“用本收之”。据《例赠修职郎孙公祖植字玉科墓志铭》,孙祖植善居积,敦本力农,“开阡陌,教树畜”,发扬“克俭克勤”的艰苦奋斗精神,集聚财富,终致“富甲一乡”。据《内兄孙君淑安先生墓表》,孙槐卿善于居积,开设大十字街钱庄,以长子综理财权。次子孙淑安科举考试失利,于是“慕陶朱、猗顿之为人”,改习商业。孙槐卿乃“运土货出,输外货入”,20余年间往来于武汉、荆州、沙市、黔江之间,终致“获利甚丰,家道日兴。”
急公好义: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诸多优良传统的民族,急公好义即为其中之一。进入黔江的孙氏也秉承了急公好义的这一优良传统。据《清诰耆英孙公德松字光先墓志》,孙德松生平行事,一生所为,刚正不阿,亢直敢言,无所阿附。“居闹市而乡曲平允”,终致“公道致富”,赢得了人们的赞誉。据《清例赠将仕郎孙公克开寿藏志铭》,孙克开为人豪爽,赋性刚直,排难解纷,排解秉公,以息事宁人、息事康人为要旨,以致“戚族咸从”,成为“领袖乡里”的民间精英。据《例赠修职郎孙公祖植字玉科墓志铭》,孙祖植是急公好义,乐善不倦,热心公益。“卷价不足,则施田产以助之;饥民可悯,则出谷米以周之。”正是由于孙祖植的急公好义,“邑有歌而里有颂”,得到了人们的充分肯定,称赞其“惠我无疆,作善必昌。”
总之,洪武年间入驻黔江的这些军事移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他们逐渐本土化、土著化,最终演变成为黔江地区的本土民众。
[1]曾超.黔江移民姓族孙氏略考[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3):31-38.
[2]四川省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黔江县志[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
[3]张九章.黔江县志[M].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4]张绍龄.黔江县志[M].咸丰元年(1851)刻本.
[5] 冉崇文.冉氏家谱[G].咸丰元年(1851)活字本.
[6]胡广.明太祖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7]黔江县地名领导小组.四川省黔江县地名录[G].内部资料,1985.
[8]重庆市黔江区政协学习文史委.黔江文史(墓志铭专辑)[G].内部资料,2006.
[9] “护国将军”黔江谢氏家族院落探秘[EB/OL].http://cq.qq.com/a/20090911/000243.htm.
(责任编辑:滕新才)
A Study on the Military Immigrant and Localization of Qianjiang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ZENG Chao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a group of military who came from the South of Yangtze River moved to Qianjiang area because of the foundation of Qianhusuo,a monitoring institution in Qianjiang,to become the military immigrants.Bu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theose military and their descendants abandoned weapons to be writers and business men,through these ways of localization,they gradually evolved into the people of Qianjiang region.
Qianjiang;military immigrant;localization
曾超(1966—),男,土家族,重庆黔江人,博士,教授,长江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执行主编,中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学院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民族文化和区域文化。
K248.1
A
1009-8135(2018)02-006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