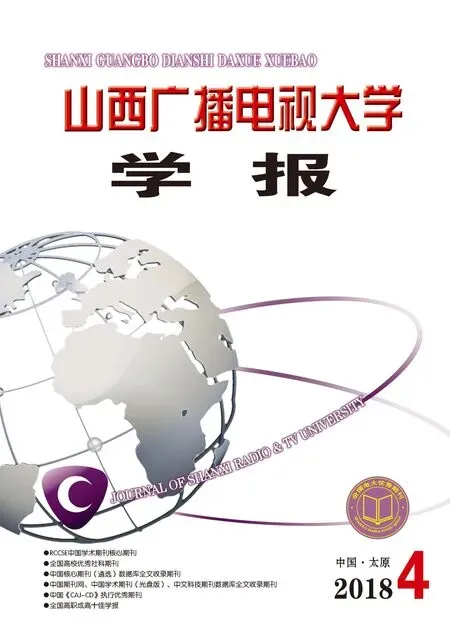《镜花缘》韩译本的多元影响因素探究
2018-03-21□王潇,胡健
□王 潇,胡 健
(安徽大学,安徽 合肥 230601)
一、引言
清代李汝珍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镜花缘》在中国出版后不久便迅速流传到了韩国和日本,稍晚一些流传到了西方,出现了韩译本、英译本等,促进了中国古典文学外传与走向世界。《镜花缘》的英译经历了从最早的1877-1878年汉学家Herbert Allen Giles(翟理思)的节译、1946年安德鲁斯与王际真合作的节译、1965年林太乙翻译的截至目前最完整的英译本FlowersintheMirror以及1973年张心沧的两个节译本分别收录在他的两本专著里面。[1](81)与英译本循序渐进的发展史截然相反,《镜花缘》的韩译本经历了较早的开端、漫长的沉寂与突然的爆发,自从1840年被朝鲜两班贵族洪羲福用古朝鲜语即谚语译出全译百回本之后,对该书的韩语译介便戛然而止,经过172年近两个世纪的沉默之后,《镜花缘》的现代韩语译本于2012年悄无声息地突然问世。我们禁不住会思考在这近两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镜花缘》为什么没有现代韩语的译本出现?为什么在2012年又出版了现代韩语译本的《镜花缘》呢?韩国人的视线是为何、如何转回到中国文学上的呢?从《镜花缘》的现代韩语译本的翻译这个窗口中又会传达给我们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吗?本文将从《镜花缘》韩译本的赞助人、翻译策略及译者身份建构等方面入手,探寻译本的产生与使用的翻译策略背后国内外政治、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等诸多要素暗流涌动的博弈。国内关于《镜花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李汝珍的生平交游,女性主义,文本生成与审美创新,与《西游记》《山海经》《格列佛游记》《绿野仙踪》等中外文学比较,小说中茶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等的文化意蕴研究以及文化资源产业化建设等方面[2](65),对《镜花缘》译介的研究也只集中在英译本上,对于韩译本的研究处于空白阶段。本文通过剖析《镜花缘》的韩语翻译,探讨中国文学的外传,为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各地提供参考。
二、韩译本赞助人背后的政治风云
传统翻译的探讨多聚焦于原著、原作者、译著和译者,后随着康斯坦丁学派姚斯、伊塞尔为代表的接受美学的发展,对读者接受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可是,在翻译的整个过程中,很多其他影响极大的要素依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赞助人”(patronage)便是其中一个具有控制性作用却又常常被忽视的课题。[3](44)文化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1945-1996)在其著作Translation,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中分专章正式言明并探讨了赞助人在翻译活动中的重要地位,文中指出:“按照俄国形式主义理论,文学是一种文化,是构成‘复杂的系统中的系统’的其中一个系统。文学和其他各个系统从属于社会系统,它们彼此开发、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其所属的文化逻辑中。而‘文化逻辑’由两个因素共同控制,以确保文学系统不会脱离其他社会子系统太远。两个控制因素分别来自文学系统内部和外部,来自文学系统外部的控制因素即“赞助人”,是可以阻碍或促进文学书写、阅读和改写的力量。赞助人可以是单个的人或机构团体。赞助人基本上由三个要素构成,一是意识形态构成,约束着形式和主题的选择和发展;其次是经济层面上,赞助人以提供作者或重写者年金或某些职位来解决其生存问题;最后还包括社会地位因素,接受赞助意味着加入特定的团体,接受该团体的生活方式。[4](16)翻译的进行和最终的结果不是仅仅由译者这一单一因素决定的,译者的翻译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赞助人的制控,而赞助人的制控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系统密不可分。

中韩两国自1992年建交之后,两国政治关系由建交时的善邻友好关系逐步提升为合作伙伴关系(1998)、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3)、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8)。[7](1-2)《镜花缘》的韩译本翻译计划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确立之后递交了大山文化财团的审查委员会,并通过审查正式立项,于2009年公示为大山文化财团的资助项目,经过2009年12月-2011年12月29号两年的翻译、修改、定稿、编辑,最终得以初版印刷。2012年与读者见面之时恰逢中韩建交20周年之际,可以说《镜花缘》韩译本赞助人的创立、该翻译项目的谋划、韩译本最终与读者见面分别在1992年中韩建交、2008年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确立之后、2012年中韩建交20周年这三个关键点上,它的孕育和新生给我们展示了中韩国际关系的政治风云变幻。
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国力与国际地位快速提升,吸引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中国的重新关注,伴随这种政治经济变化对中文的关注和相关人才的需求也在急速地增加。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一经出台,便得到邻国韩国的密切关注和对未来两国关系的良好期待,韩国政府教育部大力鼓励韩国的大学开设中文系,韩国1977年以前只有11所4年制本科开设中文专业,在政府的呼吁下1979年-1991年新增48所4年制大学开设中文相关专业,[8]紧接着在中韩正式建交之后1992年-2013年间共新增61所4年制大学开设中文相关专业,[9]从韩国大学两个阶段中文专业井喷式的增长中可以看出,在两国政治政策主导和经济发展的潜在需要下,韩国社会对中国文学的重新关注自然也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在关注、学习中文的韩国人数急剧上升的态势下,韩国民众对中国文学的韩语译介更是如饥似渴,更有韩国全南大学的郑荣豪教授在其2006出版的专著《读东洋经典4-文学(下)》中万分遗憾于韩国还没有《镜花缘》的现代韩语全译本,暗示出以韩国学术界为代表的韩国社会对于《镜花缘》韩译本的呼吁与渴望。[10](100)而富商出身的韩译本赞助人,则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精准的社会洞察力和对韩国未来文化消费走势多元化、世界化的大胆预测,推出了许多世界文学的韩译本,《镜花缘》的韩译本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可见,《镜花缘》韩译本的出世背后既流露出中韩国际关系的变迁,该译本赞助人的成立与发展与中韩政治关系的变化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又在中韩政治政策的主导,加之韩国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迫切需要下,导致了《镜花缘》现代韩语译本的最终面世,即经过漫长的孕育过程,在国际、国内政治和经济、社会、文化等多股势力的暗流涌动与合力推动下,最终导致了《镜花缘》韩译本的成熟与诞生。
三、目的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的韩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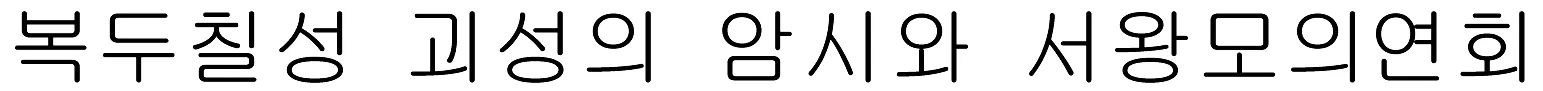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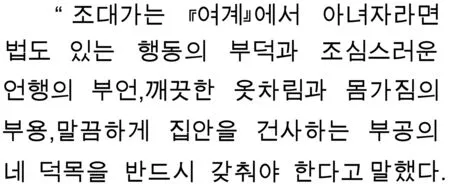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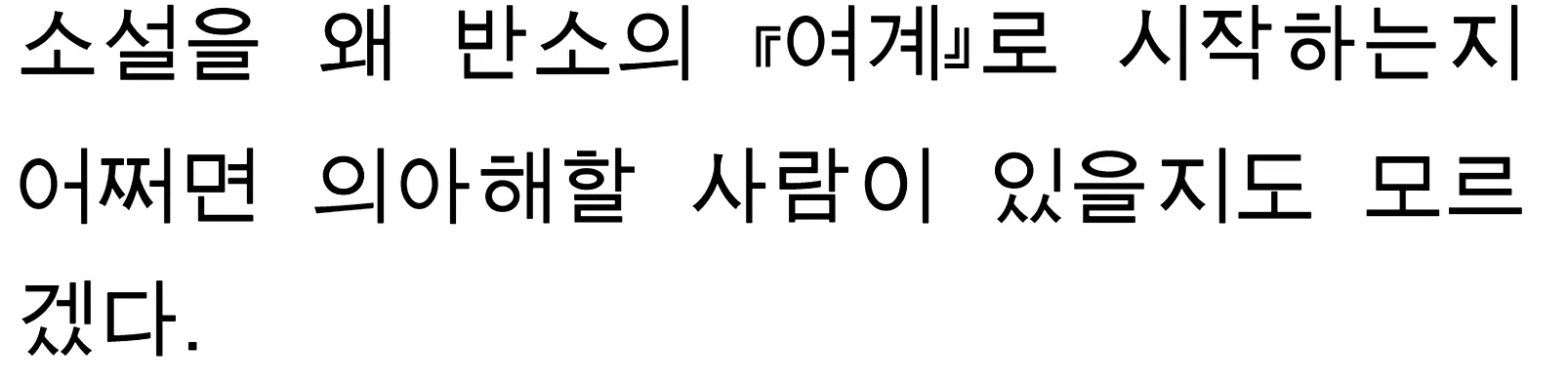
(曹大家在《女诫》中说只要是女子就要一定要具备行动有法度的妇德,言行谨慎的妇言,衣着装扮干净整洁的妇容,家里收拾干净的妇功。小说为什么以班昭的《女诫》开始,可能会有惊讶的人。)”[13](14)

译者在韩译本故意扭曲原著的意思,有意遗失了“女魁星”,选择女性的贬称来翻译“妇女”,对于李汝珍以《女诫》开篇又添加上“可能会有人感到惊讶”。皆是由于韩国从公元前3世纪到1866年这两千多年间一直是儒家思想处于显性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地位,1866年7月,美国配有大炮的商船“舍门号”率先入侵韩国,随后法国、美国又先后入侵,1875年5月日本持续入侵韩国并于1876年最终占领韩国。日占期和独立后的韩国,汉文学逐渐式微,新儒学兴起,西方思想涌入韩国,现当代以来韩国奉行法制,儒学思想逐渐从显性的统治地位走向了隐性的支配地位,却仍然是规约韩国道德社会、男女关系的主流意识形态。[14](13-20)儒家思想的建立是为了维护传统农业社会所奉行的父权家长制(patriarchy)。[15](13)自从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上》提出“五伦”,建构了古代社会五种人伦关系和言行准则,“夫妻之间挚爱而又内外有别,故应忍”。西汉董仲舒进一步构筑了影响深远的“三纲五常”理论,提倡“阳尊阴卑”“夫为妻纲”,强化了男尊女卑的思想,“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男主女从”始终是儒家思想的性别意识的核心,儒学女性观在随后的朝代不断得到巩固并逐渐纲常化、系统化、本体化日益苛刻和严密。[15](49)韩国社会自古以来在性别思想上全盘接受儒家的性别意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韩国社会忙于民族独立、祖国统一及民生发展,对于女性解放的关注度甚少,1948年大韩民国建立成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上模仿西方,赋予妇女选举权,韩国社会随即出现了众多女性独立运动团体,主导了韩国的女性解放运动,但是这些女性团体大都是在韩国政府的政治领导及资金资助下建立和活动,以传统儒家思想为基础,在韩国家长制及资本主义父权社会的大背景下展开,与西方以争取政治权利和独立自主的女权运动形成了鲜明对比,呈现出以家庭为中心的温和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16](47-53)进入现代以来,韩国不但未把儒学视为社会发展的阻滞力量予以批判和丢弃,反而认为儒学对高速发展的社会生活起到稳定而积极的力量,它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成为社会健康发展的一种保障力量,依然是社会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基础。男尊女卑观念较重,妇女家务劳动甚重,在家庭、社会上的地位和待遇远不如男性。[14](115-122)可见,在韩国社会,儒家的性别意识在已经潜移默化中积淀成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内化为女性自觉自律的宗法伦理,即使在现当代韩国社会这种性别意识仍然是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17](13)
韩国历史上意识形态的斗争由来已久且异常激烈,早在韩国三国时期,印度佛教经由中国传到韩国,被韩国接受并得到发展。高丽时期佛教一度在势力上压倒儒家思想成为国教,进入李朝朝鲜时期,封建制度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倡导“排佛弘儒”,对佛教实行了一系列排斥乃至压迫措施,如减少、拆除寺院,禁止新建佛寺,减少寺院土地,毁佛像、钟磬等。1784年天主教最早传播到李朝,从此开启了李朝对天主教的残酷镇压,从1784到1866年年间,李朝不间断镇压天主教活动,造成“珍山事件”“辛亥教难”“辛酉教难”等等众多惨案,死伤无数。[14](136-143)在儒家性别意识形态的内化及惨烈的意识形态斗争历史为鉴下,译者即使通晓《镜花缘》原著主题思想,仍选择顺应韩国社会菲勒斯中心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考虑到读者接受与期待视野,合理避免触及政治敏感地带,减少对主流性别意识形态的过度挑战,对李汝珍积极进步的女性观作了缓和化、去棱角化的调适。
四、译者身份的建构:隐身与现身的交织
在文学作品的译介中,译者是有着双重身份的特殊存在。相对于原作来说译者首先是读者,是源著作信息的理解和接受者;相对于译作来说译者又是输出者,是原文的阐释和重写者即再创作者。译者的译文使一般不懂原文语言的读者也能正确地感受到原著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因此,译者在翻译时要考虑翻译文本的接受效果,在全新的文化语境下促成原文文化与读者的沟通和互动,创造新的文本意义。又如加拿大知名翻译理论研究者芭芭拉·格达德所说:面对异质文化圈内的新读者群,译者除了完成语言文字的转换,更要与原作者合作,有重点的理解和阐释原作的文化与美学系统。译者是传情达意的积极参与者,是作者的合作者。”[18](82)在《镜花缘》的译介过程中,译者既是读者也是译者,在最大限度传达原著文本内信息的基础上,也拒绝做逐字翻译的奴隶,创造性地增添译者对原著的理解和阐释,对原著的结构形式、内容等方面做了众多调适。译者通过隐身与现身的交织与切换,在翻译活动中完成译者身份的建构。
古罗马翻译思想家昆体良认为,虽然异质语言、文化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人们表达情感、思想与观点的方式是多样的,尽管翻译不能等同于原作,但接近原作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如果原文是诗歌,可以用散文的形式翻译,使原先松散的东西有了密度。中世纪时的翻译家阿尔弗烈德认为只要将原文的内容完美传达出来,可以不用考虑原文的语言形式。[18](34)《镜花缘》韩语译本中,译者首先在结构形式上做出了调整。例如原著中第八十四回第一段中“春辉道:‘对曰:‘否’,共七十杯了。’玉芝道:‘怎么今日忽然钻进‘迷魂阵’了?’青钿道:‘据我看来:左一杯,右一杯,只怕还是‘酉水阵’哩。’”[12](513)韩译本中译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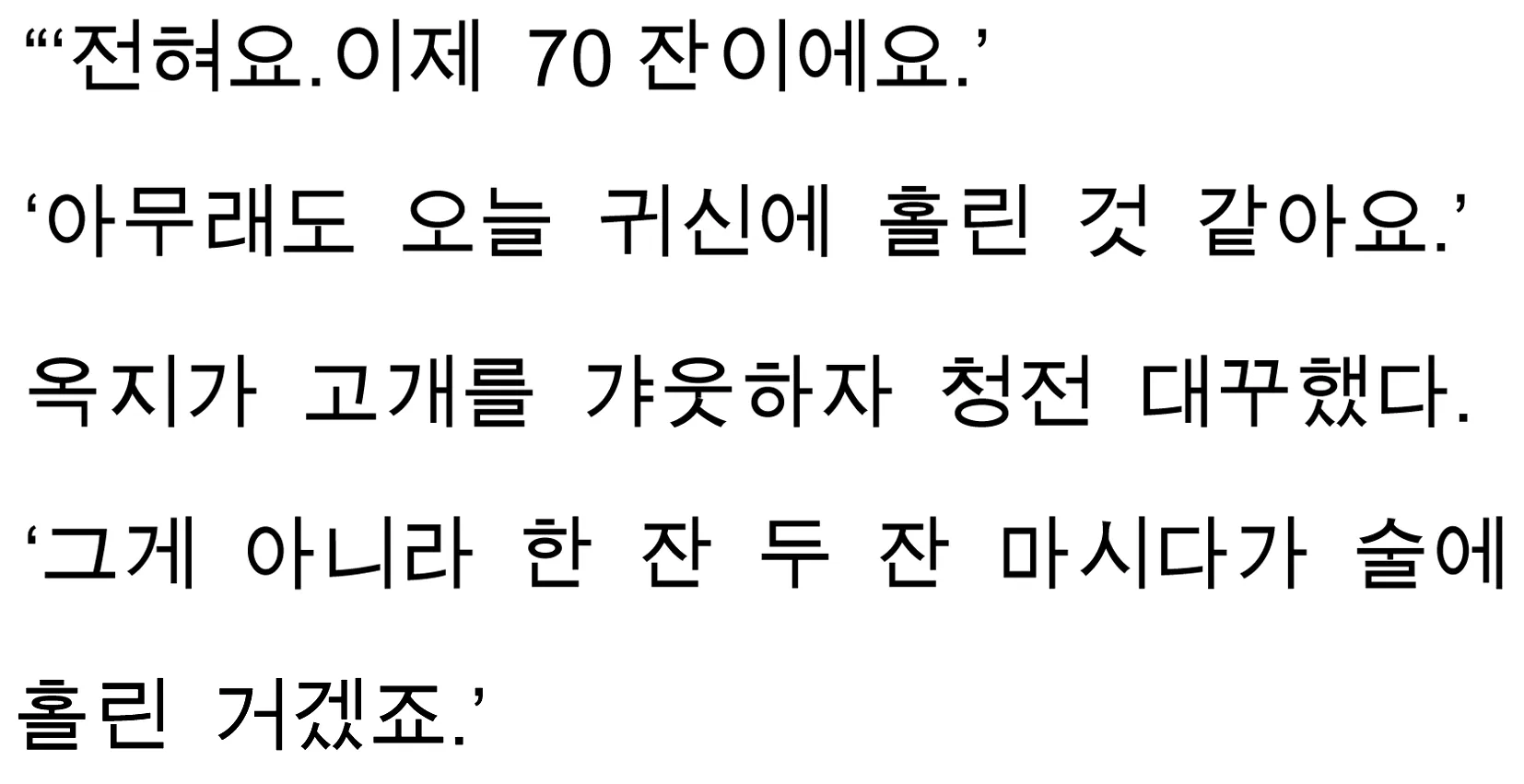
(‘不是。现在是70杯。’
‘今天好像见鬼了。’
玉芝摇头道,青钿答道。
‘那倒不是,一杯两杯喝下去就醉了。’)”[5](332)
译者通篇对小说断句、分段作了分化,将原著中的一大段话分为韩语的几个段落,这样虽然在内容上丝毫没有删减对原著的翻译,却因为改变了原著结构、调整语序,达到简化原文的目的,将大段大段的原文,以对话的形式译出,增加了译文的可读性,使得译文易于译语国读者的阅读和接受,促进源语国与译语国两种文化的理解与互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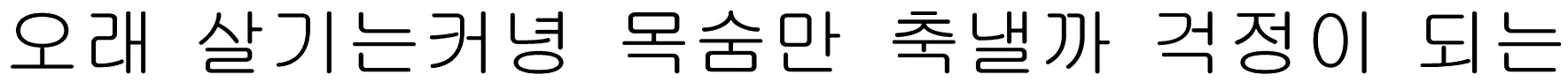
《镜花缘》原著中没有一处脚注,而译者在韩译本中共作了484处脚注,通过大量的脚注,向韩国读者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学者、人物、典籍、语言、神话故事、天文、节气、医药、地理、风俗等诸多中国古代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如小说第一回开篇的“曹大家”,注解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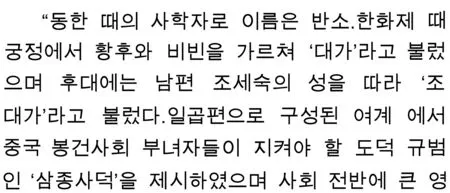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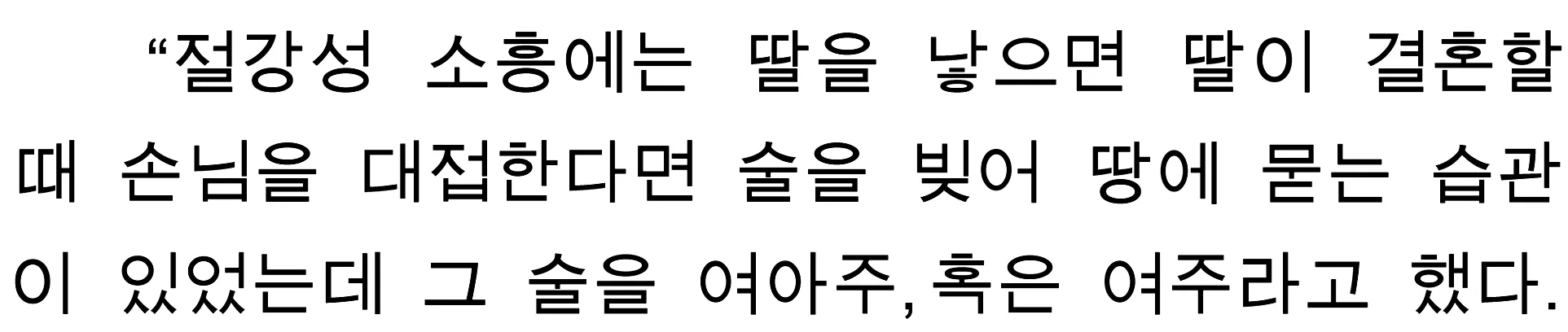
(在浙江省绍兴,如果家里生了女儿有酿酒然后埋在地里,等到女儿出嫁那天用这个酒招待客人的风俗习惯,这种酒就叫做‘女儿酒’或‘女酒’。)”[5](P173)
我国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贾公彦《周礼义疏》中对翻译的定义即翻译不仅是语言文字的转换行为,还应该包含帮助和促进操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际。[18](228)文化翻译派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及安德烈·勒菲弗尔认为,当我们谈及“文化”或“接受文化”时要始终铭记文化不是一个完全统一的整体存在,但总有一种张力存在于一种文化和不同的集体与个体之间,翻译则由影响文学发展的张力组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受的诸多制约中,来自语言的制约是最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要促成原文文化与读者的沟通和理解。[4](8-9)大卫·丹穆若什在其《什么是世界文学?》中探讨了是什么导致了不好的翻译?提出翻译的失败主要体现在两个基本的方面:要么是直截了当的错误——就是弄错了——要么没有传达出原作的力与美。另一方面,一个严重同化的翻译,将原文全部吸收进目标文化,也就消除了原文的文化和历史差异。[19](187-188)《镜花缘》韩译本中,译者通过隐身于现身的自由转换,有效调和了这一矛盾,达到隐身与现身的基本平衡,完成了对韩译本语言、审美、读者接受、传播介绍中国文化的协调。
五、结语
文学经典的译介过程尤其复杂,从翻译行为的发起到进行,再到最后的结果、接受和影响等,必然要受到多种社会文化因素多元系统的制约。[19]综上所述,《镜花缘》韩译本背后隐藏着中韩政治关系的变化、目的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译本的影响以及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对译者身份的建构。译本在经历了近两百年的沉睡、孕育与新生中,包含了除传统翻译研究关注的原著、原作者、译著和译者以外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和支配。对这些因素的关注和研究使得翻译研究被放在了社会文化的背景里,讨论的范畴得到扩展。从对这些因素的考察中,有助于探明中国文学外传过程中被忽略的细节,对于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