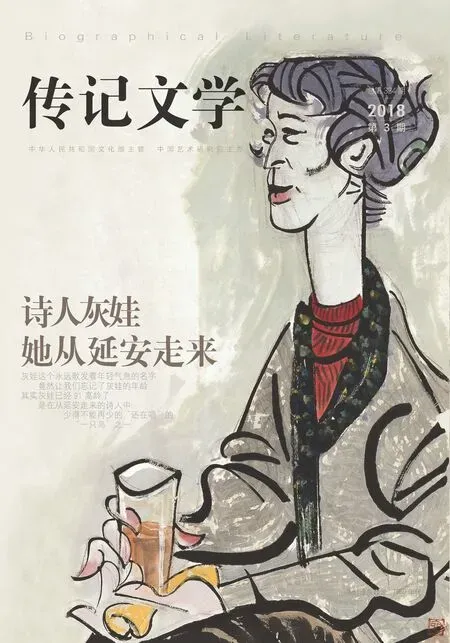时光慢慢流过
——汤晓丹:为大众讲好故事的电影艺术家(上)
2018-03-21丁亚平
丁亚平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

他,1932年开始从影,经历不同时代,在时逾70载的导演生涯中,一直视电影为自己永无止境的追求。他,年逾古稀,依然有蓬勃充裕的精力,适应新的时代,主动请缨出外景拍片。直到80岁,人问今后有何愿望,他不假思索地答道:今后还想工作!他就是汤晓丹。
自我意识的可能性
汤晓丹对电影的入门就是从看电影、背电影开始的。1929年,汤晓丹来到上海,结识了《大众文艺》的编辑沈西苓和他的朋友许幸之,并常与沈西苓一起去“泡”电影院。他后来回忆道:“那时,上海虽然已有好几家电影院,但多数票价昂贵。只有虹口大戏院因设备简陋,票价便宜点。我们两个人总是带着干粮进去,连看几场(那时不是一张票看一次,而是一场一场连看下去)。直到把一部影片的镜头结构、场次设计、转场方法、对话内容(外国电影有对话)、字幕、音乐……都能背出来为止。”
1932年,通过沈西苓和苏怡介绍,汤晓丹一头扎进天一公司,开始了他的电影旅程。“天一”成立于1925年,至1937年共拍片111部,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与“明星”(1922-1937,拍片218部)、“联华”(1930-1937,拍片96部)鼎足而三的电影公司。天一公司最初看中了汤晓丹的美术才能,让他负责绘制布景。第一部电影是裘芑香编导、吴蔚云摄影的有声片《小女伶》,在当时无声电影占主体的年代,可称之为“概念艺术”的作品。此片由袁美云、王慧娟、田方、魏鹏飞等主演,商业诉求明显。汤晓丹负责布景设计,成绩得到肯定。

青年汤晓丹
1933年,身为天一影片公司布景师的汤晓丹,意外得到一次执导影片的机会,拍摄了自己的处女作《白金龙》。《白金龙》原是一部由粤剧名家薛觉先与夫人唐雪卿合演的粤剧舞台剧,因为受到观众欢迎,薛觉先决定和天一公司合作拍成电影。原计划由天一老板邵醉翁执导,开拍之前邵醉翁因病不能正常工作,为更好与薛觉先合作,考虑到汤晓丹会讲粤语(据说汤晓丹是天一公司内唯一会讲粤语的人),有能力,就让汤顶上。当时的报纸这样介绍他:
汤晓丹君,籍隶福建,年二十四,美丰姿,少年英俊,一有为青年也。昔年负笈扶桑,攻美术与建筑,均极有心得,归国后,任上海中国商业美术广告公司职,声誉益噪:一时人士之往求君设计建筑图案与美术广告作品,络绎接踵。去年“一·二八”事变,上海沦成战区,该公司适处战地,为国难而牺牲。君遂入天一,任布景主任,新奇伟构,细巧堂皇,开天一公司有史以来之新纪录,该公司老板邵醉翁先生昆仲,对君器重逾恒,大有相见恨晚之慨。
近广东知名戏剧家薛觉先夫妇在沪组织之南方影片公司,商天一合作开拍之《白金龙》,君充该片导演,我们愿望这位美术家成为未来之名导演家。
汤晓丹首次执导粤语戏曲片《白金龙》,便得到了肯定,使其电影艺术疆界得到拓展。他的拍摄速度惊人,不到20天的时间,加上后期剪辑、印出拷贝,前后也不过3个月时间。影片由上海天一影片公司和南方影片有限公司合作出品,先在广州、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上映,后又在上海隆重推出,观众反映热烈。当时有人这样赞道:《白金龙》在南中国有了空前的轰动,汤晓丹这名字在南国也就响了起来。据《邵逸夫传》记载:一部《白金龙》,便给邵醉翁创下百万的票房价值,“堪称奇迹”。影片的票房成功,使邵醉翁对电影的创作、生产抱有更大的信心,天一公司随之决定在香港开设分公司,天一港厂转年即正式成立。

《白金龙》广告
这部影片是汤晓丹身兼导演、布景、剪辑三职完成的一部作品。剧情化、时装化、豪华布景,以及一些喜剧噱头,加上薛觉先、唐雪卿等名伶加盟,契合了市民观众的心理。虽然取得极佳成绩,但当时的汤晓丹,对于影片演绎的这个爱情故事并不满意,而且初遭电检会无情的大剪刀(虽然仅仅是对于歌词内容略有删改),也使他不能不深有所感、所悟,认真考虑在变化莫测的时代自己未来事业的走向。

《废墟》剧照
当然,对于年轻的汤晓丹说来,容他认真充分考虑与选择的时间并不多。他只能通过不断的实践,设计他一生的人生画卷。只要有电影拍,即使低成本、小投入,对他也是一种不断的学习、造就;至少,从生存的意义上,也给了他从业的机会。他懂得珍惜,而由此,他也牢牢确立了一个信念:电影是大众化的消费艺术。不能忽视大众趣味。更不是只有精英们肯定的“大众性”才是真正的大众性。为弱者洒一掬同情之泪,寄托一个英雄梦想,引发一种深心里的共鸣等,运用长久以来约定俗成所认可的电影语言,为大众讲述一个个出奇制胜的好故事,就会受大众欢迎,就能富有生命力。
在《白金龙》之后,“天一”老板交给汤晓丹的是《飞絮》,再接着是《飘零》。关注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叙述一个来自农村的不幸的弱女子的命运,成为这两部互有关联的无声片的主题与“卖点”。汤晓丹对光、影、布景精心设计,以颇为独特的方式批判了时代和社会。拍摄时,他对画面语言和镜头语言的运用独到,“非常注意画面造型对剧情气氛的营造”。《飞絮》的剧旨,是在抨击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五行八字的迷信观念和婢女养媳制度的存在,所以影片“在表面上,似乎在叙述一个弱女子,骨子里却在暴露封建社会的恶势力”。影片上映后,即有评论肯定了它的现实批判意义,且认为导演技巧较为成熟。《飘零》展示女主人公秀贞的最后命运,像一片秋天的树叶,飘落了。在片子的末尾,一条字幕告诉观众,剧中女主人的受害以至于死,是“这万恶的社会害了她”的。影片中的女主人公的遭遇,为什么会这样?问题被引到社会与思想上的结论上来。当时的一篇评论,甚至还特别指出:“我们对天一影片公司过去的作品稍一检讨,便可知道,他们只是一贯地注目于城市中等以上的家庭中的各种不同的纠纷——关于恋爱、婚姻、遗产者几占该公司全部出品之绝对多数。现在,竟一转其目标以至于农村社会,这也许是值得欣慰的事。” 确实,对电影创作者抑或电影公司说来,进步的或是“先锋”的题旨与表达,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视作“天一”商业电影运作的一种策略。
在这风浪叠起、四周险恶的环境里,别家公司都在风雨飘摇里过日子,而天一却能始终稳固地站立着。《天一公司十年经历史》 写道:“我们知道:时代在进展着,艺术也无时无刻不在进展着!我们更知道:艺术是永远无止境的,事业也永远是无止境的!”影视评论家高小健分析说:在1933年这个被称为“中国电影年”的年头,左翼的、进步的电影大量登场,电影界“转变作风”的呼声呈压倒之势,“天一”公司亦有所动。公司这一年拍摄的10部影片中有近半数的影片不同程度地带有反封建的内容。“天一”公司走商业电影之路,当然不会忘记时时以自求上进的思想吸引并紧抓观众。它先后邀请洪深、沈西苓、苏怡、许幸之、汤晓丹、吴印咸等参加工作,其意也在通过拍摄进步或比较进步的影片来获得利益。总之,不断求变、求“进步”,于经济上的好处,也是很显然的。40年代的“国泰”等公司,也曾有相类的情况。
1933年底,“天一”安排汤晓丹拍摄《一个女明星》。影片体现“天一”之前的老路线,并以有声故事片作标榜。故事内容为女明星因意志薄弱受物质的引诱而堕落。汤晓丹在回忆录中说当时极想婉言谢绝执导,和几个好朋友商量,沈西苓的看法是,如果当时没有巧妙的借口脱身,日后只能受老板的冷遇或赐予一双小鞋。迫于生活,迫于权势,汤晓丹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刚到上海两三年常常为一日三餐发愁,现实是残酷无情的。汤晓丹说自己没有沈西苓为了《女性的呐喊》宁可卷起铺盖离开“天一”那样的魄力。1934年2月此片上映后,获得很好的票房,“天一”公司相当满意。黄嘉谟在电影评论文章中还指此片“摄制尚佳”。
从某种意义上说,汤晓丹的电影创作,融汇了商业电影的手法与意识。毕竟,商业片尤其是宽泛意义上的商业影片,往往要占有一个时期或阶段中不小的比例,即使从电影艺术角度,它们可能不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但从反映世道人心的角度,它们却是重要的、意味深长的,其价值意义不可低估。商业电影运作和反映世道人心,不仅往往不相悖逆,而且还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汤晓丹的电影创作道路,一步一个脚印,非常执着。他从一开始,甚至是不惜走在其边缘薄刃上。他的创作活动在这方面所显示的潜力与某些征兆,具有着极大的提示性。
影坛“疯子”
电影是大众化的艺术。市民生活是其深厚的土壤;公共空间的扩展,大众生活和思想多样化选择与审美要求,以及个别历史发展和趋势,是其殊途同归的伴生物。当电影家努力身体力行将这世界给予表达的时候,就逐渐深入内涵,接近人文叙事的本质核心了。
汤晓丹对观众趣味进行细加研究,努力改变自己观念,跟上观众选择的步履。他在上海接连拍摄了几部影片之后,到香港拍片,他努力以一种走向成熟的心态,去拍摄一部部关注本土化人情化的影片。抗战全国紧急总动员,人们热血沸腾,他敏于感受,积极寻找电影表达方式与手段,激活民众的民族主义感情与同仇敌忾的精神。其抗战影片描写近实,形容白描自然生动,其萧森之气,悲壮激烈,耸动后人,即在当时,也无可置疑地成为一种精神力量,成为人们现实体验的一部分。《最后关头》(集体合作)、《上海火线后》《小广东》《民族的吼声》……其真实的诉说,折射光彩,达到了激动人心的效果。30年代末在香港导演的抗日三部曲《上海火线后》《小广东》《民族的吼声》,都是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既反映时代面貌,又精心刻画生活在大时代背景中各式各样的人物,以其充满血肉的银幕生命力“活跃在观众心中”,是汤晓丹比较满意的作品,也可以说是把他的爱憎付托在银幕人物的心灵深处。蔡楚生在港看了《民族的吼声》后发表评论文章说:“在抗战四周年的今日,在争取民主的浪潮正在继续增高的今日,我们能看到像《民族的吼声》这样能够适应‘时势’的需求的制作,真不知应表示如何兴奋!……我们谨向所有参加《民族的吼声》的每一个工作者致最大的敬意,并希望他们能本着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继续努力下去,同时,并希望全华南的电影工作者大家来一个进步电影的大竞赛!” 以一种新的姿势拍摄影片,使电影走出个人趣味的阴影进入更广阔的天地,这是值得肯定的第一点。
其次,适应“时势”需求的制作,以达成与民族、时代的交流和共鸣,虽然艺术的价值有时也并不与它的接受者多少成正比,但在抗战烽火燃遍神州大地时,追赶大时代,发出民族的吼声,契合更多观众心理,自然也是颇为值得肯定的。
再次,走向时代与普通观众,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与批判精神,就可列入“进步电影”之列——“进步电影”对40年代和1949年以后的汤晓丹,起了一种有形无形的保护以至标签作用。蔡楚生等人的肯定评论,对汤晓丹此后的电影之路,意义是比较重大的。仿佛此后,他拍的片子,较前便发生了显著变化。最初在“天一”公司,他是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被作为一位能赚钱的人留住并邀往香港拍片的。所拍影片,一般地说,往往视野并不很大,自叙或个人化的色彩浓重,在赢得了不俗的口碑的同时,也为公司挣了大把的钞票。现在他的注意力似乎较多地转向了别处,更加去适应“时势”的需求了。
其实,汤晓丹仍然在以自己对电影的理解,努力维护着他作为一个纯粹或比较纯粹的电影艺术家的独立人格与追求。1940年出版的电影刊物上有文评述:

夏瑜、蓝为洁著《汤晓丹:影像为语长乐翁》
汤先生是一位稳健沉着有责任心的工作者,八年前他就早在上海天一公司里任导演,天一公司南迁之后,他亦南下,为粤语电影效力,那时,香港的一家大观公司正在奄奄一息,无法维持,他便为该公司客串导演一部《金屋十二钗》,大观公司便因为这一片而重新奠定坚固的基础,安然渡过了难关。同一时期,天一公司一部轰动全华南与海外的巨片由名伶薛觉先主演的《白金龙》,亦是出诸他的手下。
他的作品,以拍摄精细,态度率真富有人情味见称,他的作品公映,俱为轰动一时之作,六七年来在他手下制出的作品,数目虽不多,但平均每年必四部左右,最近在上海大红特红的李绮年,过去在他手下导演的作品,不下十余部,俱为名重一时之作,李绮年之有今日地位,汤君的力量实在是不容埋没的一位功臣。
1934年,“天一”公司计划在香港建厂,邵仁枚负责,同时把汤晓丹请到了香港。但由于创作和技术条件比较差,汤晓丹的第一部影片《并蒂莲》未获成功,放了“哑炮”。接着汤晓丹应邀与“艺华”香港公司合作拍摄了影片《糊涂外父》。《糊涂外父》中的外孙女由香港当时最走红的紫罗兰担任,吴楚帆饰青年,林坤山饰糊涂的外祖父。“因为是讽刺喜剧片,汤晓丹特地挑了喜剧演员大口何,让他担任重要角色。汤晓丹认为大口何是罕见的喜剧演员,天生的一张大嘴,使他的面部形象严重失调,人们只要看见他就会从心里发出笑声。”汤晓丹对所有演职员说:影片既要让观众跟着银幕人物的嬉闹笑出眼泪,又让观众含着眼泪思索,思索中有省悟。这是一部“歌唱片”,叙述一个糊涂的外祖父,把自己从小抚养到大、非常疼爱的外孙女许配给了他讨厌的男子,结果闹出了种种笑话,具有喜剧色彩。观众扶老携幼进影院,场子里笑声不停。有的观众看了十几次还不满足。“这个故事有点类似于郑正秋1913年根据其家乡陋习编写的《难夫难妻》,中心题旨也是批判封建婚姻观念。”《糊涂外父》大获成功,“艺华”公司赢得了高额利润。因为《糊涂外父》的轰动,让汤晓丹获得了个人最大的荣誉。“他在香港电影界站稳了脚跟,为以后的拍片打下了扎扎实实的基础。” 就在这一年,汤晓丹接着为“大观”导演了影片《翻天覆地》。1935年至1937年,又先后拍摄了《金屋十二钗》《花开富贵》《时势造英雄》《有女怀春》《金屋十二钗(续集)》《闺怨》《再生缘》等,数量比较多,创作勤奋,以至被媒体称为影坛“疯子”。汤晓丹体会到电影拍摄是一个需要体力和综合能力的工作,也敏感地意识到经济资本的利益对电影家的艺术创造的影响与作用。他拍的影片大都成为获得高额利润的商业片,“一次次掀起观众的看片热潮”。《金屋十二钗》创造了当时中影发行的最高纪录,在香港和澳门连演两个月,场场爆满。汤晓丹成了“大观”的功臣,成为“金牌导演”,他的电影总能在市场和票房上赢得成功。
1938年,汤晓丹在执导有声歌舞片《舞台春色》(粤语、国语两个版本)、粤语古装片《嫦娥奔月》和《窈窕淑女》之后,连拍多部抗日故事片。这些抗战影片,即便不能被列为高水平的艺术作品,也仍然表达了影片主创判断时代的能力,反映了电影艺术与时代政治的一些核心问题。这固然也反映了他抗日爱国的热情,但这种热诚关注与再现民族生存处境,激活民众抗争的现实主义热情,是汤晓丹那个时代电影人的精神气质,反映了他们批判社会、塑造人生理想与民族理想的自觉的使命意识。汤晓丹的社会电影的进步含义,严格地讲,在这时绝非单一的意识形态含义,而包含了正义,对社会保持热情和关怀的人文叙事内容,更多地体现了一种精神与人格。《民族的吼声》的主旨是歌颂劳苦大众的正义行为,揭露和批判奸商与官僚的罪恶。汤晓丹在当时发表的一篇有关《民族的吼声》摄制的文章中说道:“我们制作这部电影的主旨,就是要尊重人民,拥护抗战。反对贪赃枉法,反对发国难财,反对操强权于少数人手中、置正义于死地的贪官污吏。”这个思想,差不多是从“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路传袭下来的。这个传统,是坚持社会正义、倾听民间疾苦声的知识分子所维护的。历史给了这样的契机,让电影家继承这样的遗传密码,表达正义的呼声,让观众心有灵犀,产生深深的共鸣。
1942年初夏,日占领军头目矶谷廉介宴请梅兰芳、汤晓丹、金焰、胡蝶、吴永刚等近20人,又通过翻译和久田约汤晓丹导演《香港攻略》。汤晓丹对此坚决拒绝。无奈之下,他逃离香港,奔赴大后方。1943年,汤晓丹在“中制”拍摄完成了影片《警魂歌》。此片采取侦探片的形式,讲述的是国共合作的抗战故事。此片曾被196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归为反动影片。汤晓丹在生前对妻子蓝为洁说:“我认为那些写书的人根本没有看过电影,就误以为是美化国民党。其实抗日是国共合作的抗战,而且故事发生在大后方重庆某个地方,侦破案子不可能没有正规的政府工作人员参加。”不过汤晓丹不受其影响,继续用作品展现自己的艺术追求:“我是老老实实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比与人争得不欢而散有益、有利、有收获。现在大家不是都不再谈《警魂歌》是反动影片了?”
国是日非,民族国家与政治格局急剧变动,这样的大环境,为电影人提供了一个积累经验、迈步向前、认真精进的契机。

《天堂春梦》剧照
《天堂春梦》这部最富人道精神的电影,是抗战后汤晓丹的第一部作品。此片由中央电影场第二厂1947年摄制。导演汤晓丹,编剧徐昌霖,主要演员蓝马、石羽、路明、上官云珠、王苹等。影片讲述了工程师丁建华的悲剧故事,手法扎实精炼,演员表演甚具感染力。《天堂春梦》遭到了“中电”当局的八处删减,丁建华最后坠楼身亡的结局也被改为茫然不知去向。梅朵说这部电影“透过对人情的细密的叙述,却使我们领略着时代的痛苦”,是真正触及到了影片的内涵。弘石认为,作为战后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天堂春梦》既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它的感性魅力,来自于场景设计、镜头运用、演员表演到心理刻画的不露痕迹;而它的理性魅力,则来自于总体构思上的对比蒙太奇出色的运用。”弘石曾经有机会采访过汤晓丹,在谈到总体导演构思时,汤晓丹说“在‘春梦’上做文章”,意在让人惊醒。我们不难体会到他何以要在影片中用长达6分钟的篇幅来营造“胜利带给我们的美梦”的用意。“战时艰苦生活中对未来的憧憬,与现实中的因公平丧失而导致的悲剧性生存境遇,就这样构成了巨大的落差。这正是影片强劲的思辨力量之所在。” 此片通过生动、朴实、独具特色的艺术处理,透过丁建华与龚某截然不同的命运对比,真实地再现了抗战后的社会现实问题及其正统思想蔓延下的恶果。当时,中国的外患变成了内忧,这为电影家所做人文叙事提供了一个突破的方向。面对现实,汤晓丹不仅非常失望,而且有切肤之痛。他曾表示:“胜利以后一连串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令人不快(即使官方的通讯社也不能讳言‘惨胜’和‘劫收’)。真正有良心的公教人员过不了日子,卑鄙下流的奸伪摇身一变而为地下工作者。这些颠倒乾坤、黑白不分的现象,凡有良知的人都非提出控诉不可。” 这种心态与感受,使影片既带上了属于自己的良知、个人化的感受与情感特征,又融入了痛恨黑暗的强烈的批判意识,两者形成十分有力的结合,使之成为“有中国人骨气的各阶层人士”(汤晓丹语)看后都很解气的作品。尖锐的现实感受和“救治的药方” 被放到了影片中,其中对比性的艺术表现,尤为启人深思。当时舆论称影片为“‘惨胜’后中国社会大悲剧的缩影”,并不过誉。艺术家通常可能由于平庸环境制约的创造力,因此得到了充分释放。这其实也证明,生活的真理与人民的伟大思想,以及由此出发的独立的人文叙事立场,对一个真正的电影知识分子的重要与必要。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