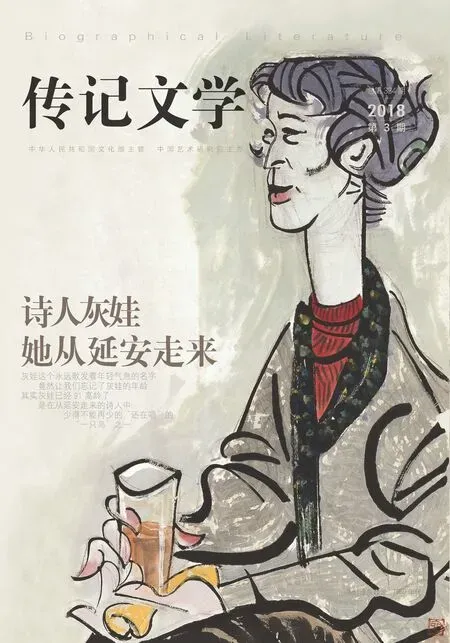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记政治学家周鲠生(下)
2018-03-21刘猛
刘 猛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

一
1945年6月2日,周鲠生乘飞机回国,经纽芬兰、摩洛哥、埃及等地到印度加尔各答转机;候机五天,于12日深夜回到重庆。到渝后,“为讲演、开会、应酬及会客所忙杀,至以为苦”。
1945年6月26日,行政院决议周鲠生继王星拱任武汉大学校长,7月周鲠生正式接任,“无日不为武大事操心”,8月8日到校宣誓就职。8日下午三点,学生齐集大礼堂,周鲠生做介绍,教育部次长杭立武训话,“学生到得很多,情绪也很好,完全是为欢迎周校长。他一站上去,那老学者的风度不由得令人生敬”。到任不久,周鲠生即于9月初马不停蹄地赶赴重庆,出席全国教育复原会议,10月下旬才返回武大。
抗战胜利,百废待兴。周鲠生就任武大校长后,整天忙的都是行政事务,“除同人之日常生活所需之煤米油盐酱菜茶问题外,尚有更繁重之搬校及建设问题待解决”,推动学术之事尚谈不上,他颇引以为苦,深觉个人言论行动自由、学术研究、生活上自由均受牺牲,不愿久任此职;而且“觉得人力不足,许多事都办得很苦了”。但此时只能迎难而上,他积极谋求校务改进,调整行政机构,改善教职员和学生的生活,增加教学的效能,组织学校复员珞珈山。
当时周鲠生的家庭成员都在重庆,他一个人住在乐山同事家里。没有家务琐事分心,可以全身心地忙于学校行政工作,但个人生活实在寂寞。学校虽然逐渐步入轨道,但是问题颇多。从校际层面来说,当前的问题是“如何改变空气,振刷精神”;经过十四年抗战,“因为教员生活太苦,多数人的精神都消磨在家计私事,很不容易提起急公有为的精神。学校的消沉更不待说”,这种状况他早有预料,故也不觉得失望。从宏观的教育层面,大学制度需待改革。他觉得当初“在北大时候,尽管在军阀政府之肘腋下,可是学校内部行政及教育工作完全是独立的、自由的;大学有学府的尊严,学术有不可以物质标准计度之价值,教授先生们在社会有不可侵犯之无形的权威,更有自尊心。现在呢,学校已经衙门化,校长简直是待同属吏,法令重重的束缚,部中司科人员的吹求,奉公守法的人弄得一筹莫展”。周鲠生在教育复员会议公宴席上,很直率沉痛地向当道者们说:像现在大学的制度,恰和蔡元培先生在大学院时所提倡之“行政学术化”的原则相反,现在真是学校衙门化;因之,好的校长做不出事来,不好的校长直是一个坏官僚。但是这个问题也是积重难返,一时改变不了。他向政府建议做一彻底改革。即使状况不尽人意,周鲠生并不失望,也不悲观,他认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问题可以一一解决。
抗战复员面临几重困难:首先是经费问题。战时武大校舍被占用,胜利时校舍虽然保存完整,但“珞珈山房屋破坏、荆棘纵横、校具设备一空”,教育部总共拨发经费二十九亿三千万元用于旅运及校舍修建,距离实际需要甚远。其次是房屋问题。战后的武大和战前相比,学生增加了三倍,达到两千人,教职员增加了两倍,达到百人以上,原有的宿舍和住宅不敷之用,“学生宿舍由每室2人住4人,也还是挤不下”,教员则需要去东湖中学借住。再次是师资问题,聘请人才因经费、设备等原因,并不容易。
周鲠生自1946年2月间起离开乐山,十来个月在重庆、武汉、南京等地东奔西走,洽商校务。此外,在重庆,他还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宪草审议会;在南京,参加了制宪国大,对于民主的到来期待殷殷。
为了复员珞珈山,武大成立了以杨端六为主任委员的复校委员会,筹划布局迁回武昌的各项事务。从1946年3月开始,武大的器材图书设备和人员分水路和陆路两路东迁,10月31日完成复员工作,在珞珈山举行开学典礼。
在周鲠生的教育理念中,大学的职责首先在于提高学术,造就人才;此外,大学还负有社会使命,要将知识社会化,把优美的文化和高深的知识向社会传播,担负起建设社会文化的责任,大学应该影响社会,做社会改造的动力。周鲠生认为,武大的基本任务,主要在学术的发展,“要想维持武大的长久历史,就必须充实学术,就必须加入新的人才,用新的人才来充实学术文化”。此外,在人才培养上要理论与应用并重,扩大武大的规模,从两千人扩展到五千人甚至一万人。他勉励学生“以日进不已之精神,做继往开来之工作”,这大概也是他自己对校长任内的期许。在延聘师资方面,他深受蔡元培的影响,认为大学应兼收并蓄,摒弃门户之见;他在美国时就积极延揽人才,邀请留学生回武大任教,张培刚、吴于廑、韩德培、黄培云等人都是他邀请回国任教武大的。胡适曾当面夸奖他:“周先生,你真配当大学校长,你看你身边有这么多年轻教授,你很爱人才。”
周鲠生认为,武汉大学不能仅仅满足于一个好的、普通的高等教育机关,要将其建成华中学术文化的中心。经过几年的奋斗,周鲠生领导下的武汉大学成绩显著。武大恢复了抗战裁撤的农学院,新建了医学院,完成文、法、理、工、农、医的六院规模;在东厂口旧校舍开办了医学院附设医院,设有病床250张;学校还添置大量的仪器、设备及图书,比战时和战前都有所提升;教员的受聘人数也在增加,李剑农、燕树棠等教授相继回校任教。
教育的发展,需要充实的经费加上全面安定的环境,周鲠生是这样期望的,但形势却不容他乐观。经过十四年抗战,国家和人民都很疲惫,抗战虽胜建国未成,各行各业渐次复苏,似乎昭示了光明的开始,但又笼罩着内战的阴霾。对于周鲠生主政下的武大来说,除了经费困难,亦是多事之秋。受时局的影响,物价上涨,人心波动,教育界也不例外。“地不论南北,校不分大少,都在吵闹个不停不歇:不是教员们闹着薪水太少,请愿、罢教,便是学生们动不动开会、游行、罢课!再不然便是校长先生们吵着要涨价。”而武大的罢课风潮,“尤推为其中之佼佼者”,其“不特声势浩大,而且一罢再罢”,让周鲠生一筹莫展。
1946年12月,北平“沈崇事件”发生,各地学生纷纷罢课响应,学生运动愈演愈烈。1947年1月17日,武大学生以补发复员费等理由进行罢课,周鲠生迭次劝导无效,“学生全部罢课,现更转移目标,攻击个人,自维书生本色,应付无方,自应引咎辞职”,于是电教育部请辞,随后停止到校办公;教授会议和校友会纷纷出面斡旋,劝告学生复课。但学生方面坚持三原则:一、补发复员费;二、先解决同学福利问题;三、增聘新教授。教育部慰留周鲠生,并派督学吴兆棠前往武大协助处理学潮。经校友会斡旋,1月25日左右学潮暂告平息,学生开始复课,周鲠生态度转趋积极,同意留任。1月27日武大学生全面复课。之后,校务会议议决开除经济系四年级生徐卓敏。经济系四年级尚未复课,要求校方收回成命,从轻处罚。杨端六坚辞教务长,周鲠生又尚未回校,武大陷入群龙无首状态。
几天不到,风波又起。2月1日,周鲠生回到武大,发表三千言告同学书,内容引起学生反感,“三百余人围集校长住宅,要求收回开除学生成命。教部督学吴兆棠出面训话,亦被哄退。学生群情激昂,并将彼等认为‘奸细’之经济系助教甘士杰、政治系四年级生许日暄拖出罚跪,嗣经理学院长桂质廷、生物系主任张珽趋前解围,一场风波始平。周鲠生已再电教部坚辞”。他愤而离校,5日到南京,再向教育部坚辞。教育部长朱家骅电武大校务会议维持校务,对此事从严处理,整饬校风,并当面慰留周鲠生,请他返汉主持校务。教育部决定对学生从严处理,派高等教育司司长周鸿经赶赴武汉,协助处理。周鸿经表示,已开除学生仍维持原议,至于学生的福利,学校应尽力改善。2月22日,蒋中正接见周鲠生,婉劝他返汉主持校务。2月25日,二次学潮平息,学生恢复上课,周鲠生也将返校。教务会议议决处分学生十人,其中五人记大过两次,二人留校察看,二人记大过一次,一人记过一次。
1947年的反内战运动席卷到武汉,武大学生也举行游行示威。6月1日凌晨,武汉警备司令部包围武汉大学,军警与学生发生冲突,学生三人被杀,师生多人受伤被捕,这就是“六一惨案”。周鲠生闻讯后,当天中午即匆忙从南京赶回武汉,进行保释学生、抗议不实报道的工作,并要求追究责任。教育部长朱家骅电武大校务会议负责人,表示慰问,并派教育部次长杭立武与周鲠生专机飞汉,抚恤受伤人员,查明事实真相,协同办理善后事宜。6月3日,蒋中正电周鲠生暨武大全体职员:“悉武汉大学发生不幸事件殊出意外,尤违中正平日爱护武校之素怀,实深感痛惜。刻已电令武汉行辕程主任负责查办,秉公处理,望对伤亡学生代为抚慰为盼。”周鲠生认为,“六一惨案”“纯属政治问题,惟有用政治方法可获致合理解决。武大作风向主独立与宽大,只要无破坏政府之行动,则师生之安全与自由,学校绝对负责。本期既未任意开除学生,从不藉端解聘教授”。
1948年初,武大再起风潮,约占武大全体学生六分之一的自费生因物价高涨经济困难要求公费待遇,半公费生要求改为全公费,公费生要求改善副食。经自治会系级代表大会决议和一千三百四十余人签名赞成,1月23起罢课三天,并请周校长即日赴京向教育部请愿。同时,讲师助教会也要求提高武汉区待遇等级。周鲠生发表告同学书,劝导全体学生即日复课,并明白表示四项处置办法:一、商请奖学金委会提早开会审补缺额;二、助学金以优先分配给自费生为原则;三、万一助学金一时不易拨到,可由学校先拨一部分,以应付目前困难;四、自费生请求发给膳食贷金,由学校转请教育部,希望学生权衡利害,发挥理智,以待部命。
不仅校内有风潮,武大还面临外来的侵袭。1848年6月,由沙市来汉的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学生数百人,侵占武大医学院附设医院新建病房,侵占一个多月后一度大闹医院,“殴人毁物,横暴之至”,激起医院员工罢工三天。周鲠生向中央及地方呼吁警告若干次,无奈“地方束手无策,教部置若罔闻”,让他连叹“此事骇人听闻,尚不知如何解决。此诚今日办大学教育者之悲哀也”。

时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的孙洪芬(左四)为支援武大理、工两院购买设备的部分经费,来武大考察,与叶雅各(左一)、查谦(左二)、皮宗石(左三)、周鲠生(左五)、陈源(左六)合影
如此密集的运动让周鲠生心力交瘁,时势如此,校长真不值得做。作为掌舵者,既要应对繁苛的行政,又要应对频繁的学生运动,工作完全背离了教育家的本职。周鲠生觉得,“当教授易于接近学生,办行政则无形中与同学同事疏远,精神上至感痛苦”。作为教育家,周鲠生虽然不赞同学生涉足政治,牺牲宝贵学习时间去搞运动,但是在自己的学生受难时他都会挺身而出,保护他们。
服务教育和潜心学术多年,周鲠生收获了应得的奖励。1942年8月,教育部在全国各大学及独立学院遴选“部聘教授”,选聘任教十年以上且对于学术文化有特殊贡献的人担任,名额30人,分24个学科,每学科一至两人。周鲠生作为政治学学科的教授,获得选聘。1948年3月27日,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评选出第一届院士81人,其中数理组28人、生物组25人、人文组28人,周鲠生以政治学专长,以“研究国际法及外交,主持政治学系多年”的贡献当选为人文组院士。
1948年初,周鲠生在报刊上就当时的政治形势发表了题为《历史要重演吗?》的论文。他以一战后的国际局势为先例,评点当下的国际政局。一战结束后签订《凡尔赛和约》,给予了德国严苛的惩罚。但战胜国在执行和约时起了分歧,导致《凡尔赛和约》自始即未获得彻底有效的执行;保守主义的英法政治家只想着以德意势力抵制苏联,却对于德国的军事复兴缺乏省悟,这种姑息终于再次导致欧洲大战。如今,二战已经结束两年,对德对日和约迟迟未订成,其主要原因便是列强对德对日政策存有分歧,各怀打算。本来战胜国的政策是永久防止德日两国侵略势力的复活,但由于美国和苏联的对抗,政策已经变得不一致了。西方民主国家转而重新考虑对德对日政策的倾向,它们认为将来的危险在于苏联,不应极端削弱德国,而应该扶助民主的德意志复兴。因此,对德和约应该宽大。而在日本问题上,战后日本和中国的对比,使西方民主国家觉得在远东对抗苏联,日本仍是值得重视的势力。总而言之,在西方民主国家有些人士的心目中,对德对日的根本已经不在于如何防止德日的复兴,而在于如何扶持德日以抵制苏联。周鲠生认为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为防止重蹈一战后的覆辙,战胜国应该本着防制德日侵略势力复活的大方针,切实管制两国。即令以后会有侵略国,解决措施也应该是运用联合国的力量,“决不可以为着要抵制一个现存的侵略势力,又来扶植培养另一个潜在的或许更危险的侵略势力”。
周鲠生的言论,引来了老朋友胡适的商榷。胡适在报纸上发表给周鲠生的公开信。信中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对德对日的政策并未改变,少数人士的观点不能代表国家政策,而且防制德日的复兴只是防制其武装和侵略势力的复兴,而非扼杀国家发展;苏联在二战前的所为和二战后对中国的所作令人惊叹,不能不说苏联已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势力。
周鲠生的观点和胡适的观点并无根本差别,但周鲠生觉得人类不可以再遭受一次浩劫,故对苏联以能忍则忍为宜,要以政治方法而非战争应付苏联,应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外培养一种中和的第三势力,作为缓冲。其他民族要扶植,德日这种好战民族也不能不严厉制裁。
抛开具体的细节层面不论,若单从理念上来看的话,这场争论昭示着周鲠生理想主义的合作外交观和胡适现实主义的对抗外交观,在世界形势需要抉择时同时登场。这场争论,固然无损于他们的友情,但在深层次的理念里,或许暗示了他们随着政治现实的变迁终究会分道扬镳的结局。而此时的形势,已是山雨欲来。
二
1949年武大师生给周鲠生举行祝寿会,抱着不同目的的各方势力同时在场。周鲠生和夫人端坐在台上,各院系代表上台发言,朗诵诗词,赞扬校长的品行学问和开明的政治态度,还演出了一幕话剧,将周鲠生为师生爱戴的大学校长形象搬上舞台。
周鲠生曾对学生自治会的人说,白崇禧告诉他武大有几百个中共党员,他回答说:“说那里有几名共产党员还差不多,说武大有几百名共产党员,那根本不可能。”经历过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周鲠生何尝不知道武大共产党员之多,他只是以校长的立场保护学生罢了!随着国共内战的进展,国内局势很快明朗起来。面对人心动荡的局面,周鲠生明确表示:“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迁校。”在这点上,他和老朋友胡适的观点是一致的。
此时此刻,周鲠生不仅需要考虑武大,还需要考虑自身。他本来决定国民政府撤离武汉时离开,并已经嘱两个儿子先行赴台,但他自己“系因白崇禧离武汉时,未予彼以预告,以致无法离开武昌”。
1949年5月解放军进入武汉,5月22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四个接管部,其中文教接管部部长为潘梓年。6月10日潘梓年带人接管武汉大学。8月24日成立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邬保良任主任委员,查谦任副主任委员。校务委员会取代原有的行政机关,成为全校最高行政领导机构。周鲠生的武大使命至此终结。
1949年12月5日周鲠生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0年3月28日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1月19被免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鲠生从武汉来到北京,他的主要身份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这项职务自1949年12月开始,直到逝世,期间还一度代理会长职务。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的宗旨主要是:“团结全国对国际问题有研究素养或有实际外交经验的人士,根据新的科学方法,研究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探讨国际问题,普及国际知识,并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供有关外交的具体意见,以协助实现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外交政策。”他作为学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迎来送往,接待各国来访人员。
1950年4月,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周鲠生被任命为外交部顾问,同时获得任命的还有曾任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此外,他的兼职还有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理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各国议会联盟的人民代表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
1954年,周鲠生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提交会议的宪法草案“是真正人民的宪法,是代表人民的意志,符合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服务的宪法。它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奠定国家的法制基础,保证国家通过和平道路达到社会主义社会”;“无论从它的实质或形式看,将是国家一个很好的宪法,是一个适合过渡时期国家总任务的需要和人民要求的宪法,虽则不能说绝对不会发现有缺点。”他还认为,“我们的国家行政机关,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质言之,我们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都由出自间接或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受它们的监督,并可以由它们罢免。而组成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都受原选举单位或选民的监督,可以由他们罢免。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所谓民主之下,统治的剥削阶级,政府人员和国会议员,骑在人民头上;我们的国家机关负责人员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内,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勤务员。在我们的国家,人民才真正当家作主。”像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新社会里与时俱进一样,周鲠生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思想不断进步,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周鲠生的主要工作领域在国际法实践和外交领域。他任外交部顾问期间,对重要的外交问题按照国际法和中国外交政策,提出处理意见。周恩来很重视他的意见,一般都会采纳。在领海宽度、渤海湾作为领湾、恢复联合国席位、印度侵犯边境等问题上,周鲠生也以自己的专业学识,提出建议,影响、推动外交实践。
1964年,周鲠生完成专著《国际法》,该书除了介绍国际公法的一般理论,还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外交和国际法实践。那时很多成名的学者纷纷表态,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作著述。周鲠生的新著,也是以新立场写作的,其吸收了苏联法学的观点,承认了国际法的阶级性,认为国际法是各个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
1971年4月20日,周鲠生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他一生两袖清风,少有积蓄,临终前决定将全部遗产作党费上缴;他的全部藏书赠送给了外交部图书馆。八年后,周鲠生的追悼会在京举行,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政法界知名人士和生前友好等约二百人参加。追悼会由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主持,外交部部长黄华致悼词:
周鲠生同志痛恨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十分关心台湾归回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事业。他工作一贯认真负责,对我国的外交和立法工作做出了贡献,学术上很有成就,是一位在国内和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国际法专家。他在晚年还带病坚持工作,写成了约六十万字的《国际法》一书。他为人正直,作风正派,谦虚谨慎,生活俭朴。
我们沉痛追悼周鲠生同志,要学习他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周总理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高贵品质,学习他严谨和勤奋治学的精神,要把国际法的研究工作大力发展起来,使国际法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争取建立平等的新的国际秩序和全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的正义斗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