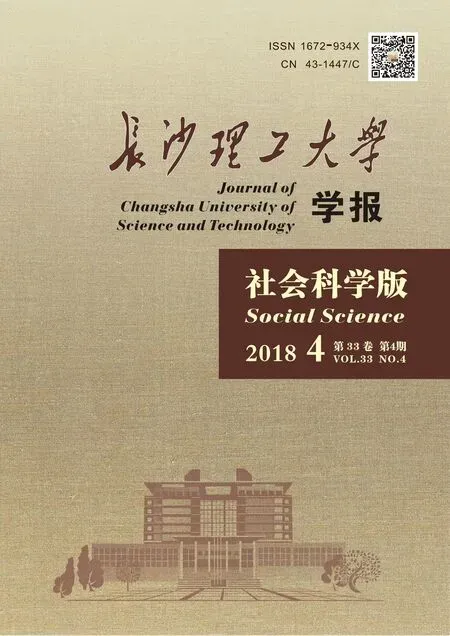工匠精神与工程理性的哲学认知
2018-03-20黄正荣
黄正荣, 张 浩
(重庆建工九建公司,重庆 400080)
一、引言
工匠作为一种职业始于手工业时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工具理性开始复苏,工匠精神在机器大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升华,以更加关注形式的、结构的、美学的和属性的东西为特征,对于助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工匠精神中“工匠”注重匠人的专业操作技能,而“精神”则强调人的理性或理念的职业价值追求。所谓工匠精神,是指工匠对自己的产品或服务耐心专注、执着坚守、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爱岗敬业、追求完美的精神理念,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职业精神,是职业品行和道德的体现,是工匠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对工匠精神的认识与思考,没有注意过或者意识到工匠精神超物质性的理性力量和核心价值,从而陷入一种经验主义的窘境。
2016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工匠精神”,并在报告中指出:“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1]。近年来,工匠精神已开始成为学界和产业界讨论的热点,很多学者和企业界人士从不同的角度对工匠精神的内涵、性质、特征、价值、意义、培育路径,工匠精神与工匠文化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2]。 “更为重要的是,‘工匠精神’作为一种优秀的职业道德文化,它的传承和发展契合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与广泛的社会意义。”[3]工匠精神具有普世意义上的核心价值,无疑是当代学术界和产业界的焦点议题,将会占据哲学社会科学谱系的显要位置,对工匠精神的思考和践行必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项重要思想任务。目前,工匠精神的理论研究还处于零散、浅层、表象的肇始阶段,尚未提升到哲学(精神哲学)的学理层次对工匠精神进行较为深刻而系统的思考和研究。为此,本文试图从哲学的视角探析工匠精神的哲学内涵、工匠精神与工程理性的关系,以期达到对工匠精神更深入的理论认识。
二、工匠精神的哲学内涵
哲学作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纵观哲学史,哲学几乎都是围绕形而上学、逻辑学、认识论、伦理学以及美学等哲学门类来展开其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的。工匠精神既是哲学的理论问题,又是哲学的实践问题,它跨越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两大领域,这当中不仅涉及到纯粹理性问题,而且也关联到实践理性问题,最终通过精神哲学将其统合起来。工匠精神是人的精神,人是理性的动物,古往今来都是哲学思考的对象。关于精神的哲学研究,黑格尔将人的精神发展分为主观精神(一般心理学)、客观精神(法哲学、历史哲学)和前二者高度统一的绝对精神(美学、宗教哲学、哲学史)三个阶段,从内容上讲,这也是精神哲学的三个组成部分。精神之成为精神,或者精神之所以是精神,其区别于自然,就在于它里面所实现的对外在事物的外在性的扬弃和克服的观念化活动,精神是理念的实现,其根本属性是它的观念性。从康德理性哲学开始,经过费希特、谢林,直到黑格尔精神哲学才真正建立起系统的关于人的理论学说。
一般意义上讲,精神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精神,既要分析人的精神个体或自然本质,也要分析人的精神的共同(类)本质,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哲学问题,黑格尔在《精神哲学》著作(绪论)中指出:“关于精神的知识是最具体的,因而是最高和最难的”[4](P1)。在黑格尔看来,主观精神指个人的精神,是“在与自己本身相联系的形式中”的精神,即只在自身内存在的、尚未与外物发生关系的精神,因而主观精神就只是一种主观自由的精神。客观精神是主观精神之表现在外部世界(法的、道德的、家庭的、政治的、社会的等制度和组织)中的精神,即“在实在性的形式中”的精神。而绝对精神是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的统一,是“在其绝对真理中”的精神,即最终在人的哲学思维的最高阶段上实现了对自已的完全认识的、主体与客体绝对同一的、完全显示了自身的、完全达到了自由境地的精神。“绝对精神是永恒地在自身内存在着的、同样是向自身内回复着的和已回到自身内的同一性;是作为精神性实体的唯一的和普遍的实体,又是分割为自己和一种知的判断,而它对于这个知来说就是实体。”[4](P325)实际上,工匠精神已超越了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它不是对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的否定,而是扬弃或否定之否定,从而上升到一种绝对精神,它反映了人的精神的类本质、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统一,是人的精神之“自在存在着的普遍性”和“自为存在着的无限性”。工匠精神除了具有精神的成分外,它还包含着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实践的成分。毋庸讳言,工匠精神的根本标志是凸显人性或人道主义,而不是人的工具化和异化。
工匠精神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绝对精神、一种存在方式,其真实的、必然的形态只能是一个科学的、伦理的、美学的精神体系,它把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意识与物质的关系从对立的范畴中统一起来,从精神哲学的高度来得以认识与建构。工匠精神的哲学内涵可以概括为祈真、至善、唯美,三位一体,从而成为一种职业信仰。
其一,祈真。祈真是指工匠基于产品制作而形成的崇尚科学、认真负责、耐心专注、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职业品质和行为准则。正如老子在《道德经》所云: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在中国古代,与“科圣”墨子同时代的鲁班是土木建筑工匠的鼻祖,被誉为“百工圣祖”。鲁班以手工木作为职业,钻研营造技艺,精雕细琢,集大工匠和发明家于一身,把工匠营造法式发挥到了极致。以鲁班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工匠,以其聪明才智和动手能力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正是这种文明支撑和延续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这当中既有工匠营造技艺的延续,更有工匠精神文化的传承。这种传承与孔孟儒家思想一样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珍贵的瑰宝。孟子曾称赞鲁班“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鲁班祖师是第一个讲究规矩的匠人。
对于每件产品、每项服务、每道工序精心打造,求真务实,追求极致。专注一事,不浮不贻,坚定一种“真知、慎独”的工匠精神。祈真意味着凝结工匠的智慧和力量,坚持真理,讲求科学,不因循守旧,敢于突破,勇于创新,不断超越自我,“术业有专攻”。正如黑格尔所讲:“精神的整个发展过程无非是它自己本身提高为真理的过程,……精神就既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有机的东西、系统的东西。”[4](P7)
一个只有8 000万人的德国把工匠精神发挥到极致,创立了奔驰、宝马、巴斯夫、西门子、阿迪达斯等2 300多个世界知名品牌,跻身世界制造业强国,对此,西门子公司总裁维尔纳·冯·西门子说:“这靠的是我们德国人的工作态度,对每个生产技术细节的重视。我们承担着要生产一流产品的义务”[5]。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之所以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各自的行业和领域秉承祈真、精益的工匠精神。央视八集系列节目《大国工匠》讲述了长征火箭焊接发动机的国家高级技师高凤林等八位不同岗位劳动者,追求高超职业技能、巧夺天工的故事,为工匠精神的弘扬塑造了中国的行业典范。他们技艺极致、精湛,其中沪东中华造船集团焊工张东伟能在牛皮纸一样薄的钢板上焊接而不出现一丝漏点;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02所顾秋亮可把密封精度控制在头发丝的五十分之一;中交港珠澳大桥项目部钳工管延安检测手感堪比x光般精准,海底沉管对接做到零缝隙,叹为观止。工匠精神有着明确的技术逻辑(合理性),在技术逻辑上要求普遍的有效性和可实现性,这样的技术逻辑是以科学的客观性为其基础和前提条件的。
其二,至善。至善是指工匠在道德理性(善)基础上对其产品或职业一种热爱、痴迷的精神状态,即所谓“艺痴者技必良”。试想,一个人带着厌恶、仇恨的心态,会产生工匠精神吗?爱岗敬业、忠于职守是工匠精神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说:“行为的发生不仅仅应当合乎职责(作为快乐情感的一个结果),而且应当出于职责,这必须是一切道德教养的真正目的。”[6](P148)在生产、服务活动中,工匠们几乎都会面临各式各样的道德困境问题,解决办法一般要从理性、善、伦理、责任、权利、义务、理想等方面来考虑,作出道德抉择。工匠的美德(包括态度、倾向和行为)就是对负责任的工匠精神的弘扬,体现为忠诚、胜任、谦虚、公正、敬业、诚实等职业品行,从而提升形成一种称之为美德伦理(善行)的实践理性,特别是对工程伦理中的义务-责任而言,至关重要。“一个理性的行为,受到善意驱动,即受到责任驱动的行为,才是道德意义上善的行为。”[7]工匠精神蕴含着工匠的一种职业的快乐(道德快乐),而不是痛苦和厌烦。
实际上,“责任”的概念是与“善的意愿”紧密相联、内在一致的,善意与责任的结合产生善行,与善行相关的行为,必然伴随着快乐,因为理性(善)本身是一切道德价值(快乐)的源泉,工匠精神则意味着这样一种道德理性的核心价值所在,离开了道德理性,也就无所谓工匠精神。康德说:“至善在现世中的实现是一个可由道德法则决定的意志的必然客体。然而,在这一意志中,意向与道德法则的完全切合是至善的无上条件。”[6](P155)善的东西,并未超出道德行为,而是内在于道德行为之中。
其三,唯美。唯美是指工匠对产品或服务的劳动美学意义上的审美体念。工匠精神的美的对象表现为制作(或生产、服务)的过程和产品(或者作品),通过以理性为行动基础而制作(或生产、服务),一方面要合目的性,另一方面则要合情感性。黑格尔说:“美一般地就仅仅成为精神东西对直观或意象的渗透,——即成为某种形式的东西,以至于思想的内容或表象就像它在想象时所使用的材料那样,只能是极其各种各样的甚至极其非本质性质的,而作品却可能是某种美的东西和一个艺术品。”[4](P327)工匠精神的美学意义强调工匠在生产或服务的操作过程中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充分利用材料、结构、工艺等来展现质感、形态、功能、色泽、线条等方面的技术美,即属于对审美对象超出表象的实践性反思的美学范畴。它基于在一种美的对象上感到愉悦,而自然流露出的纯粹的、自由的精神情感,这种情感既有来自心理学的,也有来自社会学的审美评判。被全球誉为“白金工厂”的LEXUS雷克萨斯九州工厂,以“匠”修心,以“心”炼技,每一位工人都是“匠”文化的践行者,他们把对完美的追求融入到每一个生产环节,以“匠心”打磨每一件作品,为“自働化”加上人字旁,精益求精,从人性化、自然化角度出发,呈现超越用户期待的美的体验和创造。
工匠精神作为一种对美的艺术的塑造形式,它必然要考虑审美理念在人的精神状态及物化的产品中固化、侵蚀和延伸,这也是它的目的所在。正如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到:“人们可以一般地把美(不论是自然美还是艺术美)称为审美理念的表述:只是在美的艺术中,这个理念必须通过关于客体的一个概念来诱发,但在美的自然中,为了唤起和传达那个客体被视为其表述的理念,仅仅对一个被给予的直观的反思就够了,无须关于应当是对象的东西的概念。”[8]工匠精神内涵中的真和善最终要通过美的形式表现出来,美既是真和善的终结,同时也是真和善新的起始,它们都是以理性或者说理念为其前提条件的。
三、工匠精神与工程理性之间的关系
为了获取知识或者采取行动,除了感性、知性外,还需有理性。理性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是人类系统思考的倾向和能力,为每一项“知其然”提供“所以然”,是精神或意识的范畴,理性最初起源于希腊语词“逻各斯”,开启于柏拉图的理性主义,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主题。启蒙理性的提出,冲破了神学的羁绊,理性以其它的产物——科学知识,成为了消解当时盛行的神学的世界图像最有力的工具,推动了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进程,人们深信理性具有无限的精神力量。黑格尔曾在其著作《精神现象学》中说:“理性之所以成为精神,在于‘知道自己是全部实在性’这一自身确定性已经提升为真理,理性意识到自己就是世界,世界就是自己。——精神的转变过程揭示出了此前刚刚发生的那个运动,在这个过程中,意识的对象,亦即纯粹范畴,已经提升为理性的概念。”[9]
理性既不是本能的、情绪性的或带感情色彩的,也不是传统的,它具有深思熟虑和现代化的特征,理性的原则表现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理性在康德哲学中有系统而深刻的研究,康德重点从先验理性与实践理性两个方面探讨了理性问题。如果说,先验理性揭示理论的活动规律,那么,实践理性则提供用来处理各类事实的方法。在康德看来,“理性,作为种种原则的能力,决定着一切心灵力量的关切以及它自身的关切。它思辨应用的关切在于认识客体,直到最高的先天原则;而它实践应用的关切则在于就最终的和完整的目的而言的意志决定”[6](P152)。受康德实践哲学的影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使用理性这个概念是为了规定资本主义的社会活动方式,他最早将理性划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两类,据以理性二分法用之于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分析。
工程理性也可划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两种类型,是二者的辩证统一,其涵义、分析方法和适用范围与社会学不同。工程理性从本来意义上讲是实践理性,实践性是包括工程理性在内的工程活动方式的本质特征,其主要行为方式是通过有理性的行为者,按照经过自己理性思考而选择的原则进行有意识的造物实践行动,包括价值合理的行动和目的合理的行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0]价值理性通常考虑的是行为者某种信念、价值和意义的追求,如人本的、伦理的、精神的、美学的、宗教的等方面的价值,这当中,价值可以是主观的,同时又不失其客观性。价值理性行为注重行为的内在价值,涉及到“应然”领域。工具理性则更多地关注行为者的技术有用性和效率(功利)最大化,以及可计算、精准、精确、完美等极致性筹划。以可计算性为特征的工具理性着眼于行为的客观性和中立性及计算带来可验证性的技术化过程,这一切都与价值无涉。
工程理性是工匠精神的源泉。追溯人类的文明史,工匠精神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和文化启蒙的理性而产生、勃兴和成熟,工匠精神始终充满理性原则。应该看到,工程理性是工匠精神论的核心范畴,是工匠精神分析与重构的逻辑起点,同时,也是工程哲学的根本性问题。工匠精神本质上呼唤人类的理性,唯有理性才能提供精神领域普遍的和必然的原则,无论是提供给知识,还是提供给行动,莫不如此。因为理性的原则与精神或者意识彼此是相关联的,精神受到理性的支配,并通过理性而呈现,黑格尔认为,“精神对之拥有一种理性的知的那个东西,正由于它以理性的方式被知,就成为一个理性的内容”[4](P222)。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理性作为有自我意识的,确信它的存在是精神或意识的本质规定,又是它自己的思想,这样的理性就是进行着知的真理,即精神,可见,精神的实存是知,其知以理性的东西为目的。这个精神领域经历了从人的纯粹的思想状态向实存的转化,并扬弃有限的实存形式而达到人的绝对精神的理性化过程。作为精神存在物,人类又是超自然的,以其自己的理性选择,来建构起理性的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说过:“精神的基本活动是双层的:一种力量是欲望,它驱使人去做这做那;另一种力量是理性,它教导和解释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结果就是,理性指挥,欲望服从。”[11]
确切地说,作为一种精神的形式和类型,在工匠精神的演变过程中,价值理性旨在预设一种对特定行为内在价值的判断和肯定,而工具理性则表征一种特定行为可计算性的计量和确定,两者都以此作为理性化的方向和路径。应当看到,在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技术催生了工具理性。在工匠精神里,技术与操作、制作、使用等实践活动之间的联系大多集中体现为匠人的技能或技艺,作为一种可选择的手段,工具理性的成分会更多一些,因为技术往往与工具理性联结在一起,共同支撑着工匠精神的完善和升华,技术为沟通工具理性与工匠精神开辟了一条道路,它们有着内在的相通性和渗透性,通过技术的运用来达到效用最大化。每一次的技术革命和技术创新都为工匠精神提供丰富的养料,有助于提高工匠精神的技术(理性)水准,扩大工匠精神的浸润和影响范围。随着技术的进步,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等工匠精神就不断凝聚着工具理性中的精准性、精确性等成分而得以提升,工具理性的成分既包括设备、工器具等的更新,也包括新理念、新技术、新工艺的涌现。工具理性自身无所谓善恶等伦理标准,它是技术中性的或者中立的,其目的的实现依赖于人的意志活动,但要受到价值理性的约束。
四、结语
在精神与理性的讨论中,如何阐明工匠精神、工匠精神与工程理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应当成为工程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只有从哲学的高度廓清工匠精神的意涵及其本质特征,才能在理论上提纯工匠精神的职业理念,使其具有一种理性的自我意识,嵌固在人的精神形态里。工匠精神蕴含了真、善、美等三个最基本的哲学要素,受到工程理性决定并具有时代特征的精神哲学体系。在工程理性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互为条件,相得益彰,共同支撑着工匠精神的完善和升华。失掉了理性,工匠精神是残缺的、不可持续的,进一步讲,是难以上升到哲学意义上的绝对精神层面。无论是自然工程,还是社会工程,总之,作为改变物质形态或者社会形态的工程,它们都交织着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精神与理性、存在与意识、理论与实践、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亟待从哲学上来回答这些问题。总之,工程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哲学问题,工匠精神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