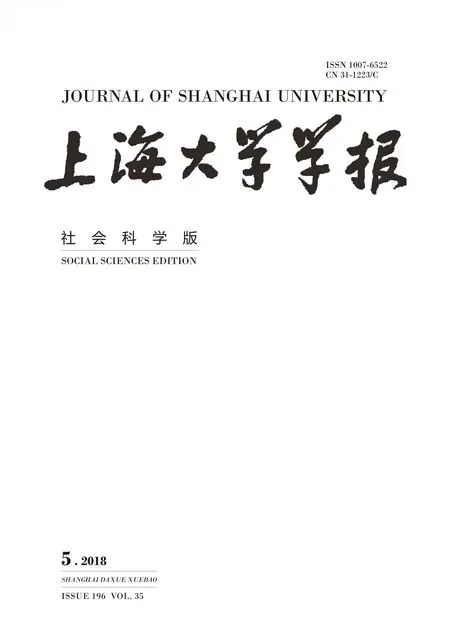海外第六代电影研究的新西方主义—与毕克伟教授商榷
2018-03-18周文姬
周 文 姬
(上海大学 上海电影学院,上海 200072)
引言:第六代电影的东方主义与新西方主义问题
众所周知,第六代电影把自己定位为当下现实的观察者,但是,一些学者认为其缺乏历史感和国族文化精神。一些批评者甚至认为大多数的第六代电影具有新西方主义特色。①按照毕克伟( Paul G. Pickowicz)的观点,第六代电影人制造了国外观者尤其是国外艺术电影院的观者和评论家想要看的电影。毕克伟引用了陈小眉的西方主义观点,进而认为“正如东方主义视觉在西方被国内优先历史性地驱使,中国的西方主义同样在中国被国内学者所优先塑造。详见Paul G Pickowicz.Social and Political Dynamics of Underground Filmmaking in China[G]. From Underground To Independent. Ed. Paul G. Pickowicz and Yingjin Zhang. New York: Roman & Littlefield, 2006:13。然而即使第六代电影展示了自身的盲点,仍然值得学者们去进一步探究。第六代电影的制作时间当值中国卷入全球化之际,此时西方进入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中国不均衡的地域发展状态也有着相应的空间再现,即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同时并存。《我的摄影机不说谎》(2002)①程青松、黄鸥著《我的摄影机不说谎》,中国友谊出版社,2002年5月。聚焦在出生于1961-1970年的电影制作者,展现了八个男性电影人的自传式信息、对他们的访谈以及导演记录,他们分别是姜文、贾樟柯、路学长、娄烨、王超、张元和章明。(简称《摄影机1》) 和《我的摄影机不说谎》(2003)②《我的摄影机不说谎》(2003)是电影记录片,聚焦于第六代导演、其他中国独立电影人以及女导演比如李玉(《象与鱼》)和唐晓白(《动词变位》);记录片由Soleig Klassen和Katharina Schneidere-Roos这两位欧洲女性学者制作。(简称《摄影机2》)表明,第六代电影希望绕开由第五代构建的国族神话和传奇,以便能呈现一个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同时并存的真实中国。如张元所说:“我做电影因为我关注各种社会问题和各种现实……我不喜欢主观的,我希望我的电影很客观,是客观性赋予了我力量。”[1]张英进在分析第六代电影的主题时,认为“让独立电影人最着迷的问题不是‘我的摄影机会说谎吗?’而是‘我的摄影机怎么才能捕捉到我所认为是事实的东西’”。[2]28-29结合第六代电影中的代表作品《我的摄影机不说谎》(2002、2003),第六代导演在努力呈现真实的空间,尽管呈现的真实空间来与其主观视点密不可分。而学者们批评第六代电影缺乏历史感和传统文化精神,则多少与这些电影人如何去感受和理解中国现实有关。那么第六代电影导演从不同的个人视点去展现现实方面,是否再现了一种新西方主义的现象呢?还是再现了一种自我审查和自我东方化的行为形式?
东方主义是萨义德《东方学》中的思想理论,由于第六代电影身份认同来于各种国际电影节的参赛与获奖,那么,在研究这个群体作品的时,是否会遭遇到来自后殖民话语的干扰。迄今为止,除了2016年第5期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刊出了台湾学者谭逸辰的《论“第六代”电影的东方主义困境》,国内学界并没有把第六代电影置于东方主义话语中进行专门探讨。国外学者在研究第六代电影与东西方主义话语关系方面,只有毕克伟把第六代直接并系统地与西方主义进行学术性对话,其他多数学者只是偶有提及,并未进行系统性的学术探讨。毕克伟的论文《地下电影制作的社会和政治动力》③这里的地下电影作品指的就是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大部分集中在政治与新西方主义层面上进行探讨,忽视了其他因素对作品创作的作用,认为第六代电影的美学特质逃脱不了新西方主义的影响。
在论及第六代电影的主要特色时,毕克伟列出如下论点:第一,通常情况下,人们会把“地下”或“独立”电影范畴与美学相联系,但在中国,第六代导演早期的所谓“地下”或者“独立”电影与其说与形式有关,不如说与内容有关;第二,在独立电影中,对妓女、民工、吸毒者、穷人等的生活刻画只是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交流对话的间接方式;是对社会进行直接批判的再现方式,是不被接受的;第三,这些独立电影呈现的空间没有历史和文化承载,内容是肤浅、空洞且令人失望的,而且很多电影专注于自我世界,影片呈现出自我沉溺、自我关注的特色;第四,地下电影中的自我源于以下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即自我审查、后社会主义失范(postsocialist anomie)和西方想象;第五,在地下电影中显现的诸如自我沉溺、肤浅和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也在中国的感官“垃圾”小说中有所呈现;第六,专注于自我和世界(尤其是资本主义世界)以及缺乏国族意识这种现象,与巧妙的自我审查、全球化和商业化的动力作用以及内在因素有着密切关系。[3]1-22
就以上六个方面而言,如果从后殖民理论去审视,我们看到了毕克伟的东方主义论调以及他认为的中国电影人所持有的新西方主义思想。考虑到有关后殖民理论与第六代电影之间关系的论述在学界中的阙如状态,本文拟沿着毕克伟的思路去分析探讨,试检第六代电影是否如毕克伟所言的受新西方主义思想所驱,同时审视第六代电影是否印证了前述毕克伟所提出的六个方面。
一、话语实践与中国式西方主义
关于第六代电影聚焦于边缘话语的论述,毕克伟认为在第六代电影文本中展现了从“‘集体、集体、集体’到‘我、我、我’”的转换过程。[3]14这类身份主体总是被刻画成“我无家。我是妓女。我是俱乐部歌手。我是同性恋者。我很迷茫。我是瘾君子。我是拉拉。我是民工。我真的很迷茫。我是一个波西米亚……我很疯狂”。[3]15毕克伟认为,挫败感的身份以及对自我的固着与社会环境相分离,也没有任何人物深度,而只是多种力量交融的结果:自我审查、后社会主义失范、西方想象。的确,在第六代电影的早期阶段,许多电影人以边缘群体如歌手、妓女、民工等作为主要关注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形象刻画属于西方想象。相反,这种现象更应该是一种书写现实的另类方式。或者,沿着毕克伟采用陈小眉的西方主义来阐述第六代电影的途径来观察,亦如此。陈小眉明确指出,西方主义正是“这样一种话语实践:通过建构西方他者,东方本身——尽管它可能先被西方他者建构和吸纳了——得以主动地、带有本土创造性地参与到自身建构、自我理解中来”。[4]5显然,与西方世界支配的东方主义不同,中国式的西方主义是一种话语实践,是压制与解放并存的话语。这里的西方主义也包括了本土对西方的主观美好想象。但对陈小眉来说,叙述者用美好的想象作为批判社会的一种方法,这就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自我-他者之间的想象关系。也就是说,第六代电影这种“我、我、我”可以被认为是借用西方的主体性话语来反省当下中国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时的身份主体问题。
与此同时,后现代的书写方式挪用了西方的艺术风格来进一步突显个体以及当下中国的身份主体性话语之呈现。在涉及第六代电影的中国式后现代话语时,以路学长的《长大成人》和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为典型代表,其后现代特质以戏仿为甚,然而戏仿在此处不同于西方后现代的戏仿,中国式戏仿在这两部片子中保持了意识形态的警醒。另外,在胡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简称《馒头》)对《无极》的戏仿中,以角色置换的方式更清晰地呈现了一张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混合共有的图景,这里,戏仿暗示了对主流文化的抵制,同时希望在主流与边缘之间有发声的机会。到2005年,胡戈的戏仿现象同样具有颠覆性,同时通过戏仿性地颠覆原作来凸显其中的问题。对戏仿的挪用在陈小眉探讨中国式的西方主义中成为重要论题,以此来表明中国文化界以西方主义为话语实践。同样,千禧年前后第六代电影并没有沦为追逐后现代的游戏;贾樟柯、王小帅、娄烨、张元、王超、陆川等人仍然在探索当下的现实,再现空间(列斐伏尔语)呈现了一个遭遇全球化冲击的中国。
另外,许多学者认同了第六代电影聚焦于当下现实的方式。刘帼华(Jenny Kwok Wah Lau)就认为是否有史诗特色成为区分两代电影的主要标准。[5]17-19比如,第五代电影与第六代电影之间的典型区别在于角色转变,即从传统英雄到普通边缘人的转变,比如小偷(《小武》)、苦丧者(《哭泣的女人》)、民工(《十七岁的单车》《扁担姑娘》《盲井》《陈默和美婷》)、妓女(《扁担姑娘》)、歌手(《北京杂种》)、艺术家(《冬春的日子》)等。在这些影片中,失业、卖淫、性、官僚主义等都在故事角色身上有所体现,但这些影片既没有使用史诗风格,也没有去质疑社会问题和道德堕落。相反,影片对个体世界进行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刻画。这正如刘帼华所认为的,第六代电影反映了对平庸现实的兴趣以及对直接在场的关注。[3]17-26难怪毕克伟认为这种刻画是对自我的固着。当然,另有学者如吴凯特( Wu Kat)用“个人”的说法来论及电影中的“自我”,但他指出了“自由市场经济已使得电影人能用他们的个人经验去阐释现实,而不是跟从集体阐释”。①转引自 Jenny Kwok Wah Lau. Globalization and Youthful Subculture: The Chinese Sixth Generation Film at the Dawn of the New Century[C]. Trans. Jing M.Wang. Multiple Modernity: Cinema and Popular Media in Transcultural East Asia. Ed. Jenny Kwok Wah Lau. Philadelphia: Temple UP. 2003:20.对毕克伟来说,自我沉溺的电影和被碎片化的身份正是与体制、自我审查以及西方想象共舞的结果。鉴于现代性之旅在东亚和中国的状况,第六代电影的转变是本土文化历史与当代西方社会之间辩证运动的影像呈现。这正如学者们所提到的“多样现代性”和“另类现代性”的概念,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她自己的特点。第六代电影通过现实主义方法来传达全球化过程中正在变化的中国现实。这正如刘帼华所言:“第六代电影是个体的,因为他们通常再现了电影人自己的视觉而不是如一些传统的社会主义电影那样去假装传达宏大的普遍真理。”[3]20在这个层面上,如果以个体性的生活空间来诉诸主体性的生存空间,显然,个体的主观性视觉不可避免地呈现了电影人独立批判的一面,如果按照毕克伟的论调,这种情况具有新西方主义特色的话,那么陈小眉的西方主义却认为“中国的政治和知识文化不过是对西方思想不加批判地复制,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不论这些‘中国观念’在源头上是多么的西方,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在非西方语境下被表述,就不可避免地在形式和内容上被重新修订”。[4]4由此,与其说是第六代电影中呈现的自我审查与电影节中的要求和西方想象不无关系,不如说是在挪用西方思想的同时又对之进行了一次本土化表征的自我审视。边缘群体和现实问题是一种话语实践,而不是在东西方二元范畴中的一次对于西方想象的自我贩卖。当然,由于自由市场逼迫第六代电影人去寻找投资人,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考虑到国际市场的因素。
这样,在全球化时代,第六代电影文本又是如何再现处于本土与全球之间辩证运动的中国现实呢?在这方面,第六代电影展示了人们在全球与本土辩证运动中生活的具体空间。后者涉及主体身份和不断变化的空间。比如贾樟柯的电影,从《小山回家》到《山河故人》,每部电影讲述的都是关于人(农民、各类民工、下岗工人、社会青年等)与地方(村庄、小城、中等城市、大都会、三峡)的生活景观;人物/角色在空间的变化中挣扎、妥协、顺应和抵抗;地方由于内外原因而进入一个不断调整的转变中;在影片中重新被建构的中国不可能回避历史与文化,因为空间的真实图景必须面对过去,这正如戏仿必定与过去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比如《昨天》和《儿子》中的主角们,即使影片聚焦于个人经验,仍然能找到过去的各种轨迹。在这个层面上,毕克伟的论点确实是有问题的,即他认为的第六代电影没有历史与文化承载。
二、空间话语与历史传承
按照毕克伟的论点,第六代电影由于只关注他们的全球化身份与全球化概念,由此构建了一个没有历史与文化承载的中国。尽管这个论点具有片面性,但是在涉及全球市场、自我东方化方面,确实有必要予以再度思考,因为中国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发展变化,而且电影具有第三电影的美学特点。毕克伟在详细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第六代电影构建的中国之所以没有历史与文化承载,是由自我审查、全球市场力量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三者逻辑博弈的结果。对他来说,第六代电影中展现的自我审查意味着讲述自我与世界是没问题的,而讲述中国的权力与政治、过去与现在却是不允许的。[3]18全球市场力量使得中国电影人成为边缘群体,也迫使他们自我东方化,这就使得电影人认为西方喜欢关于自我探讨方面的影片。这样,灵魂缺失、空洞以及第六代影片中描述的城市青年的无方向感等,应该归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而不是全球化。这样,不难理解毕克伟强调了三个因素(新西方主义,全球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对第六代电影现象的影响与作用。
当罗伯特·斯丹谈到第三电影理论时,他认为“原生混杂性”“时空多样性”“对废墟救赎的普遍主题”是第三电影的主要美学特征。[6]尽管中国在第三世界的位置很微妙,斯丹的理论更加适合于拉美电影,但是第六代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上述三个特征,这是因为中国的后殖民空间和第三世界的地位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全球化时代,像其他第三世界电影一样,当全球化使得外来文化思想流入国内,诸如性别、文化之类的主题以及与国家传统相关的另类电影必然会涌现,并且挑战支配性主流话语。例如,王超的电影就呈现了“对废墟救赎的普遍主题”的美学。显然,由于中国在世界的复杂地位,中国电影包括第六代电影有着第三电影的美学特色,从而重新界定了当代文化。第六代电影所具有的第三电影的特色主要在于对边缘话语的探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第六代电影聚焦于现实空间。中国在第三世界中的位置,意味着后殖民特色与后社会主义互相交织,所有这些均促使艺术家对在场进行思考。正如戴锦华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描述,[7]159在场飞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无处不在。这种生活看上去具有超现实感,这主要体现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者并存,而且也呈现出斯丹所说的“原生混杂性”和“时空多样性”特征。
另外,第六代电影以边缘话语的方式(性、腐败、失业、吸毒、卖淫、艾滋等)大多表现了“对废墟救赎的普遍主题”。然而,他们并没有把这些社会议题放到社会与道德反思的层次上。相反,他们执着于对个体世界的现实主义刻画,而后者充满疏离感、迷茫和挣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毕克伟认为第六代电影着迷于自我世界。在探讨第六代电影的现实主义特征时,刘帼华借用玛利亚·伽里克瓦斯基在《1949-1984年中国的艺术与政治》中提出的“生活流”概念。按照其论述,“生活流”艺术对低调的非政治的主体进行详细的个人刻画,是反对传统社会主义艺术/媒体中明显政治化的一种行为反应。第六代电影并没有去详细阐述“宏大主题来反思文化根本与社会主义传统”,而是诉诸相异的另类叙述。[3]18由于第六代电影执着于现实主义刻画,其“生活流”是对现实空间的再现,“生活流”并没有呈现主体的一种政治场景,但它最终暗示了某种意识形态语义。列斐伏尔的“现场空间”和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指出,空间既不是中性的,也不是指诸如感知空间/第一空间的物理空间或者诸如构想空间/第二空间的想象现实。空间是被生产的,正如三个空间的三元辩证运动。第六代电影通过对主体予以物理定位的空间来聚焦于生活流;①周围环境与人物同等重要,两者都被等同刻画且互相映衬,但有时物理空间远远盖过人物,尤其在那些新现实主义电影中。物理空间更像是影片中的主要角色,比如在《十七岁的单车》《三峡好人》等影片中。影片呈现的是一种被体验的现场空间或者是第三空间,这在某种程度上传达了语义学视域下的社会现象。因此,第六代电影包含了艺术家对社会的思考,这就像他们所宣布的:他们的摄影机不说谎。
然而,摄影机不说谎就意味着电影没有历史与文化传承吗?毕克伟认为,第六代电影中的人物生活被抽离掉任何社会背景,因此他们的电影缺乏历史与文化感。通过对第六代电影的谱系分析,其碎片化身份如“我无家可归,我是妓女……我是一个伪艺术家” 等,确实展示了边缘空间的再现,甚至带有人种学叙述的意味,比如《流浪北京》 (1990)、《冬春的日子》(1993)、《北京杂种》(1996)、《小武》(1997)、《站台》(2002)等,但这并不意味着电影就缺乏历史与文化传承。福柯在《尼采、宗谱系、历史》中探讨了历史与身体的关系,他认为身体就是传承领地;所有被传承的东西把自身依附在身体上面:“身体的表面被各种事件铸满烙印(用语言可以追踪这些事件,用思想去解决这些事件)……宗谱系,作为对传承的分析,因此位于对身体和历史的表达之中。它的任务就是要暴露身体完全被历史烙印以及暴露身体的历史解构过程。”[8]众所周知,围绕身体的议题涉及身份、主体性、阶级、伤痛、性别等各个方面。此处运用福柯的思想,从那些被碎片化的身份中能追踪一个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因为身体本身就是碎片化身份与人物生活状态的具体体现,后两者可以追踪社会状态和“一个分裂的自我的场所”背后的原因。列斐伏尔用身体的概念也是指向现场空间/再现空间。社会或群体成员中的主体空间的关系对应着他与自身身体的关系,社会实践预设了对身体的使用,这是一个感知范畴(感知空间)。对身体的空间实践来说,身体是感知场所(为外在世界感知的实践基础);[9]40身体的再现来自科学知识的积累,比如解剖学、生理学等知识,从身体与自然以及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来说,所有这些知识随着与各种意识形态的混合而传播。[9]40对于身体的现场空间来说,由于具有幻象即时性特质的文化因素介入,具体体验可能会变得复杂且特殊。因此就身体的现场经验来说,地方化就不能被完全想当然,因为在道德压力之下,要获得无器官身体的这种奇怪想法甚至也是有可能的。[9]40显然,身体空间是现场空间、感知空间和构想空间的综合,它不能逃脱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烙印,它有着与现场息息相关的具体经验,这种经验并非由后殖民理论用东西二分来决定其文化的产生方式与程序。
三、“新”西方主义与第六代电影的空间化
毕克伟谈及第六代电影的新西方主义时,引用的是华裔学者陈小眉的西方主义理论。陈小眉的著作《西方主义—后毛泽东时代抗衡话语理论》是以萨义德的《东方学》作为能指参照。其实,与陈小眉的著作同年出版的关于西方主义探讨的还有詹姆斯·G. 卡莱尔主编的《西方主义:对西方的意象》,此书是九位人类学家的论文集。卡莱尔在导论中提到两种西方主义:一是由西方主体建构的西方表征;二是由非西方主体建构的西方表征。但卡莱尔并没有对它们进行二分,也没有加以严格地理论化。进一步对西方主义进行理论化阐述的是朗姆·林德斯特朗(Lamont Lindstrom),他在论文中指出:“我会忽略历史运动场中的倾斜,相反,我会用自为东方主义(auto-orientalism)去指涉东方人中的自我话语,因此,在这个结构中,西方主义是东方人关于西方的话语。我认为卡莱尔和其他学者所称的西方主义应该叫自为西方主义—西方人的自我话语……拟西方主义(pseudo-occidentalism)(关于东方人可能言说西方的假定)。”[10]在文章中,林德斯特朗认为货物崇拜主义(cargoism)的材料是由模糊甚至消除差异的多种因素构成。①林德斯特朗在文章中分析了“货物崇拜主义(cargoism),货物崇拜主义是关于货物崇拜的访电话。进来许多学者对货物神话展开研究,把重点放到西方意识形态上来。林德斯特朗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详细探讨,提出货物崇拜主义的资料由内东方主义(internal-orientalist)、支持-东方主义(sympathetic-orientalist)、拟-西方主义(pseudo-occidentalist)、同化-东方主义(assimilative-orientalist)因素组成,这些因素模糊甚至消除边界和差异,而后两者对我们和他们起到了分离作用”。参见Lamont Lindstrom: Cargoism and Occidentalism, Ed. James G Camier, Occidentalism:Imapes of the we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36-37.这里,人类学家从认识论上提出了东西方之间的边界和差异。该论文集中,乔乃森·斯宾塞在论述亚洲的西方主义时,更是意识到西方在想象南亚社区时所持有的本质主义思想,以及西方的这种思想对人类学研究所引发的差异性。同时,他希望避免“把后殖民情境同质化成一种对真正后殖民的‘策略性本质主义[斯皮瓦克语]’的无批评性的辩护”。[11]显然,论文集呈现了人类学家对西方主义的反本质主义思考的实践,也指出西方主义与东方主义并非二元对立。卡莱尔在探讨西方主义时,也提到陈小眉用西方主义策略来支持或者批评现存的社会和政治实践。[12]这也正如陈小眉所强调,她的西方主义并非来自东方主义的二元范畴,而是一种话语工具,用来批评、思考当下在场的各种关系和权力。
然而,毕克伟虽然引用了陈小眉的西方主义概念来探讨第六代电影,并将后者界定为“新”西方主义,但其最终结论仍然把第六代电影装进传统的东西方主义的二元对应中,即第六代电影中的文化表征是电影人对西方的一个想象,是为了迎合西方人旨趣的一种西方想象,这显然仍是原来的二元话语权力的文化表征。东方主义总与西方主义相伴随,这种自我/他者式的论调与当年学界将第五代电影界定为东方主义中的“自我东方化”在本质上并无多大差异。另外,如果引用本土学者王岳川的观点:“有中国学者提出‘西方主义’,即东方人眼中的想象性‘西方’。就中国而言,也有三重视界:其一,制造西方神话,追求全盘西化,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在追逐西方中制造出西方神话。其二,对西方解魅化,强调中国精神化而西方物质化,认为西方是物质的,而中华民族是精神的,坚持有泱泱大国的精神再加上西方的物质文明,就能超过西方。其三,西方衰亡论……”[13]5-6这里,王岳川针对国内的西方主义想象进行分析梳理,显然与海外陈小眉的西方主义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若用王岳川的西方主义想象与毕克伟对第六代电影的阐释进行对话,无疑同样能衬托出毕克伟的东西方二元思维模式。
与第五代电影景观相比,第六代导演把第五代电影的集体记忆转换到当下现实,把辉煌宏大的视觉转到纪录片和各种风格的现实主义上来。因此,批评家诉诸政治/美学变化理论,认为其作品以西方视觉为主来吸引国际市场的兴趣,又一个新“东方”中国从西方视点中产生了。于是毕克伟论道:“西方主义和东方主义观点被认为是对被想象的‘他者’的粗鲁的歪曲,因为‘他者’与其说告诉我们关于被想象的人们,不如说是那些正在努力想象的人们。”[3]13因此,这个被建构的中国并不遥远和神秘,而是在场的且具体的,然而,它毕竟是表面性的,是波德里亚式的一个拟像。
诚然,即使以第六代电影的三个集群来分析,作品中构建的“他者”和拟像远非西方学者毕克伟思考下的二分模式产物。第六代导演的三集群中,其一以路学长、王小帅、王全安、娄烨和陆川等为代表,他们的电影语言更多与电影史有关,传承了先锋、实验、欧洲艺术电影和好莱坞经典的一些语言特征。总的说来,他们作品的电影语言与叙述手法呈现出本土与经典艺术电影进行对话的特征。比如,娄烨的《苏州河》呈现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维罗妮卡的双重生活》、希区柯克的《眩晕》和乔治·卢卡斯的《美国涂鸦》的美学踪迹。王全安的《月蚀》沿着《维罗妮卡的双重生活》的美学进行探索。陆川的《寻枪》与杜琪峰的《PTU》相比,可谓是通过现实主义刻画了一个社会空间;同时,它混合了其他的电影美学来质疑社会空间中的社会现象。其二,与具有市场智慧的艺玛电影(Imar Film)有关,张扬的《爱情麻辣烫》《洗澡》和施润玖的《美丽新世界》《走到底》都与艺玛公司紧密相关。这个集群中的第六代电影则回归到主流价值和大众文化,但会关注国内外市场效果。通常来看,现代爱情和城市生活方式成为其主要题材。这类电影在艺术与市场之间追求平衡,因此电影的票房比其他集群的第六代电影显然要高出很多。而且,在《洗澡》《昨天》和《太阳花》中,以父权、父亲和儿子的关系,以及父爱与家长制社会相平衡来启发观众去思考。此类电影也对处于现代化与全球化情境下的社会进行不同程度的探索,比如《回家》呈现了关于当代中国的一些问题。其三,张元、贾樟柯、王超和刘冰鉴的电影则采用现实主义手法,打破虚构与纪录片之间的界限。这个集群还包括纪录片制作人如吴文光、段锦川等,他们记录下那些在中国大变化环境下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个集群的作品聚焦于普通人和边缘群体,如民工、同性恋者、妓女等。像其他第六代电影一样,他们也关注城市题材。如即使贾樟柯的电影大多聚焦于中国正在经历的大变化,但在《世界》中仍然有着城市主题。他们的关注主题也存在众多争议,有学者指出,他们的作品带有自恋特色,如管虎的《头发乱了》,张元的《昨天》,娄烨的《周末情人》等。在这个层面上,难怪第六代电影有时被批评为自我审查和西方想象。
实际上,第六代电影的题材远比以上三个集群丰富复杂。题材的多样化并不仅仅是西方电影节口味转变的产物,也是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互动作用的一个再现。珍妮·斯泰格(Janet Staiger)认为电影的标准构成与变化中的政治有着紧密关系。比尔·尼克斯(Bill Nichols)更是强调电影节起到了生产“艺术性成熟”的作用,这意味着把一位新兴导演放在国际性的大导演圈子中,同时,电影节也产生了“有特色的国族文化”,后者与好莱坞电影有着巨大的区别。[14]16与此同时,尼克斯采用了安·开普兰(E.Ann.Kaplan)的论点来阐明电影节行业关于文化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艺术性成熟”与美学相关,而“有特色的国族文化”则与政治策略有关。[14]19因此,美学与政治策略对电影节起到本质性的影响。第五代电影通过西方电影节嬗变成权威模式,这个事实在国内意识形态话语与电影节权威模式的进程中无疑产生了互为辩证运动,这里,“批评资本(critical capita)”①“批评资本”由Liz Czach提出。Czach依据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资本的概念提出“批评资本”来阐明一部电影通过在电影节流通的圈子中获得成功后所增加的价值。卷入美学的政治维度。另外,西方对中国所持有的形象多少与历史遗留有关,比如冷战中的意识形态。正如戴锦华所指出的,正是冷战意识形态把第六代描绘成不合法的存在,并且这种现象也与西方在中国文化中强调颠覆性因素有关。[7]156-157
众所周知,在90年代,中国经济日益卷入全球化。相应地,中国处在本土和全球化之间被不断塑造,而全球资本主义在融合本土的同时也与后者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在全球化逐渐渗透整个世界市场的时候,中国空间也相应地具有了一定的抽象性;支配性与碎片性同时并存;当城市和乡村被卷入全球化时,相应的社会空间也卷入抽象、同质、可交换的状态。全球化加强了本土中中心与外围、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差别,也使得诸如全球/本土的差异在日常生活与政治、美学和意识形态层面上都有显现。一些学者认为,这个时代应该被界定为后社会主义(尽管后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存在很大的争论),比如毕克伟、克里斯·贝利(Chris Berry)、玛丽·安·法夸( Mary Ann Farquhar)、艾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和张旭东都集中在后社会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上进行探讨。他们质疑后社会主义和它的美学实践是否是后现代主义的对立面,还是其本身就属于后现代主义现象。在这点上,张英进把后社会主义看作一个多样的文化景观而不是一个概念,[15]52因为后社会主义呈现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种模式的并存状态。言及第六代电影,则匮乏、疏离感、幻灭感和失望在其作品中四处可见。由于这种并存状态的复杂性,其未来进程处在本土与全球化的相互动力作用之中,那么,这些精神状态或许表征了本土在此进程中一个关于自我探索的能指符码。
在20世纪80年代,制片是由国家投资的,第五代导演不必担心投资问题。当下第五代导演与第六代导演同样不得不考虑到国内外市场。显然,市场对电影制作产生了很大冲击。90年代开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发生变化,这使得第六代电影的美学实践不同于以往电影人,他们逃脱不了本土和全球市场的影响。这种情况在进入21世纪尤为明显。张英进对千禧年中的后社会主义电影制作做了深度分析。在艺术、政治、资本和边缘性之间的选择和共谋,可以被认为是后社会主义制作的一种方式。在张英进看来,电影人不得不受制于“在后社会主义电影制作中的资本、政治、艺术以及边缘性(希望是边缘)的力量”。[13]75用“希望是”来修饰边缘性,张英进对四种力量中的边缘性提出了质疑。在论及政治与边缘性的关系时,张英进认为,只有边缘性与政治的关联才使得异议与抵抗成为可能的唯一场所。然而,“由于政治禁止和被艺术所放弃,因此边缘性冲击以及它的现实画面反而被海外国际电影市场所注意”。[13]72由此,张英进指出,私人资本可以吸引对边缘性感兴趣的电影人到艺术层面上来,从而使得作为异议与抵抗场所的边缘性的未来变得不确定。张英进对边缘性的讨论是有道理的,因为电影制作必须涉及资本力量,而后者也与国内外政治相关。资本力量降低边缘性的意识形态话语这种论题从而也被放大。难怪一些学者认为,第六代电影对边缘性的刻画是为了迎合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现实,这样做是为了获得资本投资。因此,尽管第六代电影丰富多样,并且通过不同镜头去阐述中国现实,但是他们最终逃脱不了后殖民话语。
与张英进的多重探讨相类似的是聂伟对第六代电影的概念分析,他并非从文本本身出发,而同样是在多重语境中去分析第六代电影。在论文《一个概念的熵变:“第六代”电影的生成、转型与耗散》中,聂伟从上下文背景、东西方之间、资本市场与电影之间、新媒体与传统媒介、第六代群体的电影探索情境等方面详细阐述了第六代概念的生成与变化,认为“进入2011年,传统大银幕意义上的 ‘第六代’概念自我解体”。[16]这里,暂且不论概念上的第六代电影是否延续了代际概念,毕竟,在中国电影进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第五代电影的美学同样并非原来的固定美学,也在国内外市场、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下生产出与早期相异的风格。尽管如聂伟所说,进入2011年,第六代电影这一概念将由遵从熵的变化,走向耗散,然而,这种耗散现象正如第五代电影目前的多元叙事,耗散本身暗示了第六代电影仍然在路上。正如聂伟在文末所言,第六代电影在进入新媒体时代,能否借助后者,能否形成新的视频美学,能否始终坚持曾经举起的“现实主义的灯光”,有待时间验证。
结语:不只是现实主义
按照以上分析,《摄影机1》和《摄影机2》至少阐明了电影人想从不同视点去传达他们所认为的真理。尽管按照张英进的论点,对电影人来说,“真理与其说是与外在现实(比如物理景观)有关,不如说是与他们的某种超验实体(比如灵魂或精神)的主观感知有关,而这种超越实体的主观感知要么超越于视觉或可见领域,要么存在于视觉或可见领域的背后”。[2]28如果电影人想从主观感知方面来探讨真理,那么影片必须包含一定的历史和文化因素。对个体来说,即使他/她以主观感知来追求和探讨真理,始终很难脱离社会空间,这是因为真理本身来自现实,而后者是多种时间进程和运行的状态。
事实上,第六代电影并没有深究诸如“我是谁”这样的问题。影片只是刻画了人物的生活状态;也没有呈现正在塑造或已然塑造的人物的内外在因素,比如“我很迷茫”这种表达。如果电影中描述的现实或内容是创作者与体制妥协的产物,那么就能理解创作者必须学会在内容与投资之间达成的平衡,因为获得投资是最基本的一步。当人们把电影内容与国际电影节相联系,那么这些电影被批评为自我审查和自我东方化这方面就变得复杂了。显然,电影人并不能逃脱来自后殖民视点的批评。因此,张英进提醒电影人在海外投资和个体表达之间的微妙关系。[2]39在这个层面上,第六代电影的内容并非来自他们自己的初衷,而是一个内外在系统相互冲突的结果。
然而,如以上分析,第六代电影把写实生活放在首位,表现出不同的美学风格。鉴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40年代后期的批评现实主义、50年代和6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当下的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电影中,现实主义手法是探讨社会空间的一种途径。尤其适用于关注底层生活的题材。当然,如上分析,各种主题不仅是西方电影节口味转变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中国现代化与全球化相互辩证运动的呈现。巴赞在《什么是电影》中强调了内容比形式重要,并认为新现实主义首先应该呈现人性,其次才是导演的美学风格。尽管不是所有的第六代电影都具有新现实主义特色,但巴赞的思想仍然可以运用到他们身上,因为第六代电影的内容传达了某种现实,而且其风格努力遵循他们的摄影机不说谎。运用巴赞理论来分析第六代电影,尤其是那些具有“极端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探讨现实中的真实,那么,这样的现实主义电影被认为是新西方主义现象是值得质疑的。或者说,身为西方学者的毕克伟引用的陈小眉的后殖民话语,而在分析文本时又陷入了自我/他者的东西方二元模式,也即陷入了萨义德东方学建构的模式中。可见,以毕克伟为代表的海外学者们并没有分析第六代电影和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去学术性地探讨电影再现的真实性,而只是用理论话语中的二元模式去套用与第五代电影相异的电影语言,然后盖上新西方主义的印章。诚然,由于第六代电影人正处在本土与全球之间的碰撞当中,而且,传统、现代化、全球化、意识形态、资本、观众等是中国电影人不得不探讨的议题。在这样复杂的语境下,具有现实主义特色不应该被简单地描述为西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