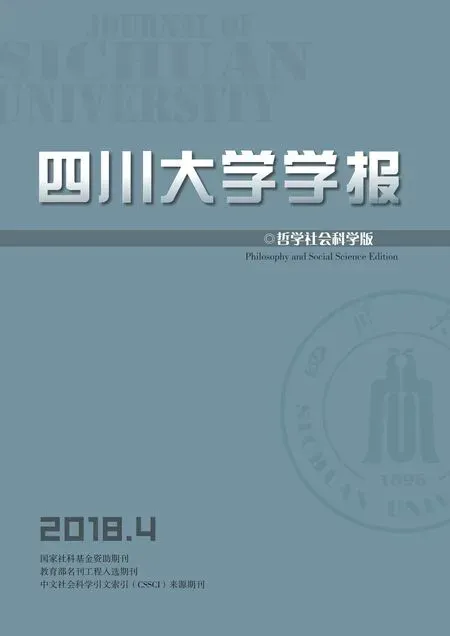音乐起源论探微
2018-03-17
一、“大音希声”:中国古代主客统一的“混沌”音乐起源论
中国古代不乏对乐之由来的讨论,如《吕氏春秋》:
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咸当。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尽其行。四时代兴,或暑或寒,或短或长,或柔或刚。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萌芽始震,凝寒以形;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吕氏春秋·大乐》,廖名春、陈兴安译注:《吕氏春秋全译》,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400-401页。
这是极富代表性的中国音乐起源论。音乐本于太一,太一即“道”,“道”的特性是“混沌”——大象无形,道隐无名,故“大音希声”。*《道德经》第四十一章。“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故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在中国古代,《吕氏春秋》第一次明确陈述了音乐起源的问题,规定了音乐起源于“道”,使音乐具有了非常规意识可解的神秘性质。
《吕氏春秋》进而曰:
成乐有具,必节嗜欲;嗜欲不辟,乐乃可务。务乐有术,必由平出。平出于公,公出于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与言乐乎!*《吕氏春秋·大乐》,廖名春、陈兴安译注:《吕氏春秋全译》,第401页。
只有能“节嗜欲”的得道之人才可领会乐的真义。可见,《吕氏春秋》的“乐”非今天大众性的音乐;除了重视“音声相和”的音乐形式外,其更加推崇的是“乐”所承载的天地意义:“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吕氏春秋·大乐》,廖名春、陈兴安译注:《吕氏春秋全译》,第401页。这是古今音乐观的重大差异。
魏晋阮籍承《吕氏春秋》,第二次系统讨论乐之起源:
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阴阳八风之声;均黄钟中和之律,开群生万物之情气;故律吕协则阴阳和,音声适而万物类;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欢,九州一其节;奏之圜丘而天神下,奏之方泽而地祇上,天地合其德,则万物合其生;刑赏不用,而民自安矣。乾坤易简,故雅乐不烦。道德平淡,故五声无味。不烦则阴阳自通,无味则百物自乐,日迁善成化而不自知,风俗移易,而同于是乐。此自然之道,乐之所始也。*《阮籍·乐论》,陈伯君:《阮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8-81页。
阮籍,竹林七贤之一,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采取谨慎避祸的态度,古琴曲《酒狂》描绘了其为躲避杀身之祸而大醉九十天不醒的故事。阮籍主张调和儒道,既强调音乐合阴阳五行的天然秩序,又提倡音乐在人类社会中的政治功用,认为二者合一才为“自然之道”。可见,阮籍比《吕氏春秋》的音乐起源观多了一层调和儒道的论调。
唐代《乐书要录》再提乐之起源的问题:
夫道生气,气生形,形动气缴,声所由出也。然则形、气者,声之源也。声有高下,分而为调,高下万殊,不越十二……然声不虚立,因器乃见,故制律吕以纪名焉。十二律者,天地之气,十二月之声也,循环无穷,自然恒数,虽大极未兆,而冥理存焉,然象无形,难以文载,虽假以分寸之数,粗可存其大略,自非手操口咏,耳听心思,则音律之源,未可穷也……
以度量者,可以文载口传,与众共知,然不如耳决之明也。此诚知音之至言,入妙之通论也。*《乐书要录·辨音声审音源》,王耀华、方宝川主编:《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第二辑,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286-287页。
《乐书要录》为唐武后时敕撰,参与撰著的传有元万顷、范履冰等人,认为“音律之源,未可穷也”,道家“混沌”生万物的思想非常明显。其后类似的言论有:“夫七声者,兆于冥味,出于自然,理乃天生,匪由人造,”“声无形象,默识者希”等,*《乐书要录·辨音声审音源》,王耀华、方宝川主编:《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第二辑,第287页。这些论述使道家“混沌”生乐的意味更加浓厚。
白居易也非常明显地秉持儒道共提的音乐观:
夫礼乐者,非天降,非地出也。盖先王酌于人情,张为通理者也。苟可以正人伦,宁家国,是得制礼之本意也。苟可以和人心,厚风俗,是得作乐之本情矣。盖善沿礼者,沿其意,不沿其名。善变乐者,变其数,不变其情。……礼至则无体,乐至则无声。*《白氏长庆集·沿革礼乐》,《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编:《和刻本四部丛刊》,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25页。
白居易很巧妙地把乐之人伦功用与“乐至则无声”的境界论联结起来,使二者不仅不相互抵触,还互相彰显,从而奠定了唐以后音乐本体儒道兼论,或者说以道统儒观点的基础。在唐以后的乐论中儒道合流,而又以道家思想为主,讨论音乐境界、技巧的论述非常普遍。
综上所述,《吕氏春秋》第一次提出了音乐起源思想,规定了音乐起源于混沌之道的特性,开了道家思想影响音乐本原的先河。尔后,阮籍在玄学与名教相争的时代背景下,竭力融合儒道两家思想于音乐本体之中;随后在白居易等人的推动下,形成了儒道兼论,尤以道家思想为重的中国音乐起源观。以道家思想为重的中国音乐起源观主要体现在大音希声、音声相和、希声通于反听等带有“混沌”性质的音乐境界的描绘上。
当代学者胡孚琛先生创21世纪新道学文化,他这样解释《道德经》第四十二章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
这段话是道学文化中关于宇宙创生和演化的基本图式,道学的道就是一种自然生化之道。其中“一”指先天混沌一气,道教内丹学家称之为元始先天祖气,是宇宙创生之始混沌状态中隐藏着的秩序,是产生万物普适的内在节律的信息源。“二”是阴阳二性,即引力和斥力对立统一、相互作用的状态。“三”是有象、有气、有质的信息、能量、物质三大要素。在宇宙创生之前,道从虚无空灵状态中先化生出先天混沌一气,继而分出阴阳二性,再依次转化为信息、能量、物质三大基本要素,在宇宙大爆炸中由信息、能量、物质组成万物纷纭、生机勃勃的世界。*胡孚琛、吕锡琛:《道学通论》增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32页。
胡先生的阐释,对中国古代音乐起源论的研究也多有启发:把音乐视为“万物”,音乐是由心、物、能的整体合和而生的,这是“三”的层次;“三”遵循阴阳互补的统一原理,这是“二”的层次:“二”皆开端于“一”,“一”是“混沌”。
宇宙创生之始的一片混沌状态隐含了万事万物最初的全息“模本”,掌握了开端的“模本”就掌握了事物的起源及衍生过程的要害。《吕氏春秋》中“音乐之所由来于太一”的思想与老子思想及胡孚琛先生所言如同出一辙。“太一”即混沌,即万事万物最初的全息“模本”,亦是音乐之源。
老子和胡孚琛先生阐释的宇宙创生和演化图式,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音乐创化的原理提供了指引。胡先生认为:“人的心灵或精神本质上是信息的高级形态……新道学的宇宙图式,消除了西方哲学史上心和物(包括能)的对立,给出了心、物、能一元论的宇宙观。”*胡孚琛、吕锡琛:《道学通论》增订版,第733页。无论是阮籍、白居易在音乐起源观上的儒道兼论,或是《乐记》中讲“凡音之起,由人心生”,都不是在主客二分的对立关系基础上论音乐创生的过程。反而,乐论一再强调的是主体的道德践履,心、物、能一元论作用下的心灵超越而获大音希声的境界意义。这种理论与音乐实践也十分吻合。
二、“道”“器”分离:近现代主客对立的音乐起源论
(一)西方主客对立的音乐起源论不能揭示音乐起源和音乐境界的真正奥秘
近一百多年来,国外学者把音乐一分为二,对其形式诸要素的起源做科学考察,从而得出劳动说、语言说、巫术说、模仿说、情感表现说等主客对立的音乐起源说: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中认为,艺术的境况归根到底是受它的生产力状况和它的生产关系制约的,德国经济学家米歇尔在《劳动与节奏》中也提出音乐和诗歌等艺术形式是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法国哲学家卢梭对旋律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旋律美是音乐美的根源,英国哲学家斯宾塞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认为歌唱在夸张表现情感方面比语言更胜一筹;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提出在原始人的巫术活动中相继产生歌舞和乐器的观点,此论一直被中外音乐史沿用至今;英国的海里斯认为在无生命的大自然中,音乐几乎可以模仿任何音响,艾涅斯库和列夫·托尔斯泰都提出音乐是表达情感的最有效途径,音乐起源于人类表达情感的需要……
西方科学主义的音乐美学观首先把音乐的本质设定为一个“实物”,确认音乐这个“实物”建立在两个假设基础之上:一是音乐存在着一个本质,二是这个本质可以被人们所认识。一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事物的本质相一致,音乐的真理便产生了,人们便用此真理来判断音乐的高级与低级、美与丑。西方的学者们便用此“真理”来阐释音乐的起源。
西方的真理产生在主客关系之中,离开主客关系,真理无从谈起,这是真理本身所无法解决的永恒矛盾。唯物、唯心之争,他律、自律之辩,正是从真理内部诱发出来的矛盾。音乐起源论中“他律”与“自律”的对立,就是西方真理知识“唯物”观与“唯心”观在音乐上的直接反映。唯物主义流派坚持客观决定论立场,唯心主义流派坚持主观决定论立场,两种哲学观都以主客二元思维模式作为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这种假设的两端对立永远无法破解音乐起源的秘密。
近年来众多的音乐起源说都以西方科学主义音乐美学观为基础,其弊端都是首先把音乐的本体设定为“实物”,再将音乐与人对立起来做研究。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音乐的精神本体因无法用理性认知,而人为地将其忽略掉,理所当然地只研究音乐的物质形态,从中得出结论认定音乐的起源或音乐的本质,这是西方科学主义音乐美学观的根本错误。这种学说对音乐的物质形态(即各构成要素)的起源做了诸多分析,而这些分析的结果却与音乐的本质无关。这种“道”“器”分裂的观点无助于音乐起源问题的解决,所以至今音乐起源仍为千古之谜,还没有公认的答案。
其实从诸说产生起,质疑声就不绝于耳。如马克斯·德索就对劳动说持怀疑态度,认为音乐起源于劳动的说法完全是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并不符合事实。科斯文对音乐起源于劳动的观点也持否定态度。
我国当代学者对诸说也相继存疑,*秦序:《努力探究音乐起源的奥秘》,《中国音乐学》1988年第2期,第14-16页;袁宏平:《史前音乐起源之我见》,《音乐探索》1988年第2期,第57-59页;蒲亨建:《在自由天地的翱翔中诞生——重拾音乐起源问题》,《人民音乐》2008年第4期,第70-73页;江海燕:《对“音乐起源”问题的几点认识》,《中国音乐学》2006年第1期,第58-61页。认为“音乐起源于××”的说法过度强调了音乐的功能性、实用性,将创造主体平庸化、弱化了音响发生的情感因素,均不可取。蒲亨建主张用带有“自律”色彩的“循声说”来解释音乐的起源,认为“大音希声”的混沌境界才是音乐的根源,从而与中国古代乐之起源论殊途同归。
(二)我国近现代部分音乐学者割裂主客的音乐起源论也不能自圆其说
我国音乐界也有学者用分裂之知来解释音乐的起源,认为音乐发生之初就有简单的音高组合、音程结构甚或旋律片断,这些音响关系固然反映了本体的某些特性,但不能被当做音乐的本质而存在,只能被解释为音乐的物质音响形态,属于音乐形而下的内容;另有学者把音乐的起源分析成“音乐各要素”的起源,如节奏的起源、旋律的起源、和声的起源、复调的起源等若干小问题,并提问哪种要素的起源才能代表音乐的起源,诸如此种细节的分枝令问题的解答更加扑朔迷离;甚而有的学者把古籍中对音乐的描绘也理解为音乐起源的历史证明,如《吕氏春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效八风之音”,被解释为音乐起源于模仿;类似的还有亚里士多德《诗学》“摹仿及音调感和节奏感的产生是出于我们的天性”,*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3页。也被误解为音乐起源于模仿。以上言论之弊端都在于试图从人类可以认知的物质因素中找出音乐起源的答案。然而,这些所谓的答案离“大音希声”还差好几个层次,只能相当于“三生万物”的阶段。
还有学者拿艺术的物证作为音乐起源的标志。认为人类的诞生至今大约有四五百万年或更长的时间,而“艺术”“音乐”的产生,仅是人类发展至旧石器时代才出现的,如出土了8000年前发明的河南舞阳贾湖骨笛,就断定在我国8000年前音乐已产生;又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距今7000年的陶埙,又得出我国7000年前音乐已产生的结论……其实这些“音乐已产生”的物证只能作为艺术物质形态产生的证明,物证只能说明此时期音乐发展的状态,而不能就此与“此时音乐已起源”画上等号。乐器考古是一门科学,但不一定非要将考古结论与音乐起源挂上关系。乐器的历史应该做科学的考证,乐器的考证能够证明该时期音乐发展的程度,而不能够就此得出此时或彼时音乐已经产生了的结论。
三、“以心契道”:主客统一的理路方可揭示音乐起源的真正奥秘
要克服上述音乐起源说的弊端,就必须从“道”“器”合一出发,遵从心、物、能一元论的宇宙观,找到一个超越于主客两端的更高明的参照。而中国古代的“混沌”说即强调音乐的精神与物质本非二物,音乐的本质和形态毫不对立,而是一个统一体,仅有本质或仅有形态都不成其为音乐。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深造以道”的思维路径,超越了西方科学主义音乐美学观的主客对立思维,无疑是解释音乐起源的最佳思路。
西方的真理不但不能解释音乐的起源,也无法解释音乐最高境界的奥秘,对于音乐的起点和终点它都无能为力。因此,在艺术的起点和终点问题上恐不能采用科学式的真理判断。*从宇宙发生论上说,艺术是无所谓“起点”和“终点”的,因起点是为混沌,终点没有止境,仍是混沌,此处使用“起点”和“终点”的说法只为文字表述方便而已。庄子言: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庄子·齐物论》。仿若诡辩似的言论,却道出了真谛——世人只有在有关“道”的认识问题上抛弃主观之思和理性之辩,纯任“无问其名,无窥其情”的“混沌”,方可领悟“物固自生”*《庄子·在宥》。的大化流行。倘若对音乐的起点和终点非要得出科学式的实证判断,落到实处,只会成为庄子笑谈的翻版:音乐有它的起源,还有没有起源的起源,还有没有起源的没有起源的起源,无限循环,得不出世人想要的科学答案。所以,对于音乐起源的思考,甚至是宇宙起源的探索,需要从心、物、能一元论的宇宙观出发,使用超越的“混沌”之思才能够解悟。*西方音乐理论对于起点和终点之间的音乐的过程倒是有它厉害的手段,如乐理、曲式、复调、对位等音乐“科学”,将现代音乐的音响提高到非常精密的高度,但对于音乐的起点和终点等终极问题西方音乐理论是束手无策的。
“混沌”即整体。中国音乐“乐道”的精华就是整体观。这个整体观就是胡孚琛先生提出的心、物、能一元论的宇宙观。中国音乐把音乐的“体”和“用”,“道”和“器”,“心”和“物”看做整体,音乐之体先用而生,却并不独立于“用”之外而成另外一物。体在用中,用可返体,体用二者有无统一。这样一来,音乐的功用可暗通音乐的本质,音乐的本质可创生音乐的功用,这是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家智慧来解释当代“音乐社会学”的基本理论。
从中国古代的音乐起源论来看,道所生的“一”,在产生宇宙根本节律的信息源中已经孕有万事万物最初的全息“模本”,这个由“一”开端的“模本”已包蕴着音乐在其中,“通于一而万事毕”,*《庄子·天地》。这才是音乐的起源。这时音乐的起源是个无声的世界(无现代乐理学认定的标准音高),老子所言“大音希声”、庄子所言“浑沌无窍”“大美不言”都是对无声世界的境界意义的表达。但这个无声的世界是通达有声世界的,中国古代音乐起源论非常强调有声的物质世界与无声的境界世界的通达与交流,我们甚至不能理解为在有声的物质世界以外另有一个无声的境界世界,实际上,音乐本身就是既有声又无声的,有声与无声相辅相成,互为因缘,即此即彼,这才是老庄道家思想的真义,也才是中国古代音乐起源论的定律。
当代量子力学研究亦已证明:人类的主观意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基础——客观世界很有可能并不存在!一般人认为客观物体一定要有一个确定的空间位置,这种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一个物体不在A处,就在B处,两者必居其一。但量子力学研究发现意识没有加入时,一个电子既在A点,又不在A点,意识一旦加入,对物体进行观察,电子就真的只在A点或者真的只在B点了。量子力学的理论与佛教、道教“非有非非有”“有无双遣”“空寂两忘”以及胡孚琛先生讲的心、物、能一元论的宇宙观十分相似,佛教、道教等宗教家早已对宇宙的奥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现代自然科学发展到量子力学,已经发现人类的主观意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基础。那么,对于音乐和艺术起源的研究难道还不应该“以心契道”,以人类心、物、能一元论的宇宙观为基础吗?中国音乐美学正是以“人”为出发点,从音乐的角度研究人的心、物、能一元活动的学科。现代量子力学证明意识是量子物理现象,人文学科的精神性研究也不是无用之“玄学”,尤其是哲学、艺术等人文学科采取心、物、能一元论的宇宙观来破解难题是非常有必要的。受此启发,笔者认为,如果采用心、物、能一元论的宇宙观,音乐的起源就不是音乐史的问题,无需器物考古的论证得出其确切的发源时间、地点;音乐起源就是一个“以心契道”的问题,它应该是一种意念,或者如佛教和老庄所言,是一个念头。
中国古代心、物、能一元论的“混沌”音乐起源论告诉我们:如果要用物质世界的时间、空间去测量,音乐就从来没有起源过,因为音乐的起源不在物质的层面。音乐的起源是“道”,而“道”超越时空,即在当下,即便是音乐起源于宇宙发生之初的“混沌”,也不能理解为音乐的起源就是一个时间点,固定于此处,停止不移。中国古代心、物、能一元论的音乐起源论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揭示了音乐是随心而起,随心而落的真谛。这也是音乐的境界。音乐的最高境界与起源一样,也非物质性,只能是一种意识,一个观念,一个念头。
讨论至此,笔者认为,对于乐器、音乐家生平、乐理等知识产生的时间、地点应该有准确的界定,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的、考古的科学问题,但音乐仅有物质要素和上述知识并不成其为音乐,当论及音乐的本质时,必须继承中国古代心、物、能一元论的宇宙观的智慧,把音乐视为心、物、能统一的整体来做体验式的研究,此时,音乐的起源就变成了一个哲学、美学,甚至带有宗教意味的问题,得不出一个具有实证性的唯一答案。由于研究音乐起源的目的不外乎是让当代的音乐得到更理想的发展,因而可以考虑把音乐的起源与音乐的境界联结起来做研究;将两者进行整体的分析,或许是未来音乐研究的合理思路。在音乐的起源与境界的统一研究中,诸多难解的音乐之谜,如乐感、情感、灵感、终极体验等心理、精神意义上的高层次音乐节点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对音乐起源问题的探析,实际上揭示了以“人”为对象的中国音乐美学与以“音”为对象的近代西方科学主义音乐美学的明显差别。*有学者讲中国音乐是“乐”本体;西方音乐是“音”本体,其意一样。中国音乐美学追求人的“心灵完整”,即心、物、能的一体化,一体即“混沌”。西方科学主义音乐美学追求人耳听觉、演唱演奏技巧、创作理论、音乐原理、乐器制作、传承传播体系等的科学化,科学即“技术化”。一者求心灵的超越,另者求技艺的高超。了解这种差别对于我们准确把握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心、物、能一元论的特点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