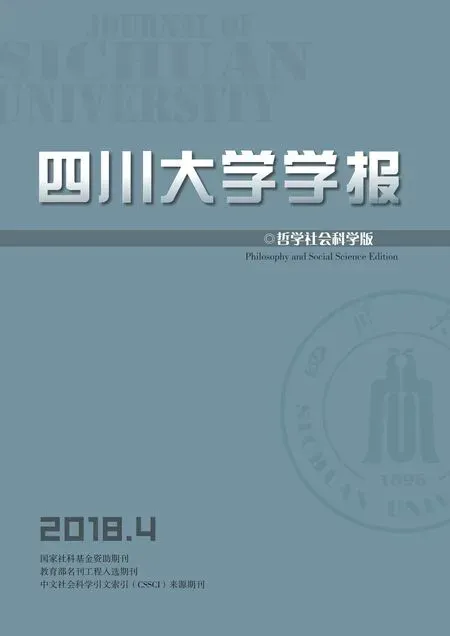从宋人关于扬雄仕莽的争论看忠节观念的强化
2018-03-17
“忠”的观念起源较早,*魏良弢:《忠节的历史考察:先秦时期》,《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宁可、蒋福亚:《中国历史上的皇权和忠君观念》,《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范正宁:《“忠”观念溯源》,《社会科学辑刊》1992年第5期;陈筱芳:《也论中国古代忠君观念的产生》,《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曲德来:《“忠”观念先秦演变考》,《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3期;裴传永:《忠观念的起源与早期映像研究》,《文史哲》2009年第3期。在经过秦汉的强化之后,*魏良弢:《忠节的历史考察:秦汉至五代时期》,《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郝虹:《东汉儒家忠君观念的强化》,《孔子研究》2000年第3期;吕红梅:《两汉时期忠君观念的泛化》,《历史教学》2006年第6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完全坠入低谷”,*郝虹:《汉魏之际忠君观念的演变及其影响》,《山东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61页。唐代虽然有所重振,*魏徵曾编纂过类书《励忠节钞》。参见方南生:《唐抄本类书〈《励忠节钞》残卷〉考》,《文献》1994年第1期;屈直敏:《从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看唐代的知识、道德与政治秩序》,《兰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汪仕辉:《论中唐之际忠君观念的提升》,《理论月刊》2009年第6期。但宋代毫无疑问是忠节观念强化最为关键的时期。*魏良弢:《忠节的历史考察:秦汉至五代时期》,《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路育松:《试论宋太祖时期的忠节观建设》,《中州学刊》2001年第6期;路育松:《试论王安石的忠节观》,《江汉论坛》2007年第7期;路育松:《从天书封祀看宋真宗时期的忠节文化建设》,《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路育松:《试论北宋忠节观建设的成效——以楚政权和南宋建立为中心的考察》,《求是学刊》2009年第6期。研究者一般都将宋人对冯道评价的转低作为宋代忠节观念强化的关键案例,*路育松:《从对冯道的评价看宋代气节观念的嬗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陈晓莹:《历史与符号之间——试论两宋对冯道的研究》,《史学集刊》2010年第2期;张明华:《论冯道“不知廉耻”历史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史学月刊》2012年第5期。但是冯道身历四朝十君,且位至宰相,其实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相比之下,扬雄与政治并无多少瓜葛,终其身也不过位列朝散大夫,他主要是以文士或儒生甚至儒家道统人物的身份为人所知。*郭畑:《扬雄身份角色的历史转变》,《蜀学》第七辑,成都:巴蜀书社,2012年,第14-23页。考察宋人关于扬雄政治忠节的争论以及最终扬雄“莽大夫”身份的成立,当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宋代忠节观念强化的具体过程。近三十多年来,不少学者致力于为扬雄“平反”,或否认扬雄媚莽,*周全华:《扬雄附莽辩》,《上饶师专学报》1988年第6期;问永宁:《〈太玄〉是一部“谤书”——“刺莽说”新证》,《周易研究》2005年第6期。或认为扬雄乃是发自内心地推崇王莽之德政,而因为已经打破传统忠节观念的约束,且近代以来对于王莽代汉的评价已愈趋正面,*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已评论说:“王莽失败后,变法禅贤的政治理论从此消失,渐变为帝王万世一统的思想。政治只求保王室之安全,亦绝少注意到一般的平民生活。这不是王莽个人的失败,是中国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大失败。”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53页。所以认为推崇王莽并不构成扬雄的道德污点,甚至进而肯定扬雄称颂王莽的进步意义。*方铭:《〈剧秦美新〉及扬雄与王莽的关系》,《中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2期;孟祥才:《扬雄述论》,《人文杂志》1999年第2期;刘保贞:《扬雄与〈剧秦美新〉》,《山东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王玫:《论扬雄》,《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2期;刘保贞:《从〈孝至〉后半篇看扬雄对王莽的态度》,《晋阳学刊》2003年第3期;纪国泰:《扬雄“莽大夫”身份考论》,《蜀学》第二辑,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106-115页;纪国泰:《扬雄“美新”原因考论》,《蜀学》第三辑,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124-132页;纪国泰:《浅议扬雄的“幸”与“不幸”》,《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三辑,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第69-76页。虽然一些学者述及宋人关于扬雄仕莽的争论,*王青、杨世明、郭君铭对扬雄地位的盛衰及其原因作了探讨,李祥俊、刘成国则专就宋人对于扬雄的争论及其地位演变进行了讨论。参见王青:《扬雄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杨世明:《扬雄身后褒贬评说考议》,《四川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郭君铭:《扬雄〈法言〉思想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李祥俊:《北宋诸儒论扬雄》,《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刘成国:《宋代尊扬思潮的兴起与衰歇》,《史学月刊》2018年第6期。但既不够全面,也不够深入,而且着力点也都只是集中在扬雄地位本身,并不注意宋代忠节观念的强化过程。有鉴于此,本文将先梳理宋人关于扬雄仕莽的争论以及扬雄“莽大夫”身份的成立过程,再引入宋人对冯道、屈原、陶渊明、杜甫等人的评价为参照,进而勾勒两宋忠节观念不断强化的具体表现和演进过程。
一、北宋前期关于扬雄颂莽的争论
扬雄潜心学思,著述甚丰,在当时即已形成巨大影响,《汉书》竟以两卷的篇幅为之作传。扬雄与王莽等人本无政治瓜葛,但王莽代汉后,扬雄还是写下了《剧秦美新》,其《法言·孝至》末亦云:“周公以来,未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其庶矣乎!辟廱以本之,校学以教之,礼乐以容之,舆服以表之,复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汪荣宝:《法言义疏》卷二〇,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559、562页。不过,即便“纬《六经》,缀道纲”的《汉书》,也是将扬雄视为“潜于篇籍,以章厥身”的代表而为其作传,虽然其中不时借用“诸儒之讥”来表达对于扬雄的敌意,但并不提及《剧秦美新》,也丝毫没有批判扬雄媚莽、仕莽的迹象。*《汉书》卷八七上、下《扬雄传》、卷一〇〇下《叙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13-3587、4271、4265页。此后直至唐末,扬雄长期保持着持续性的文学和思想影响,*参见郭畑:《扬雄身份角色的历史转变》,《蜀学》第七辑,第14-23页。也极少有人指责扬雄媚莽、仕莽。晋人李轨和中唐柳宗元注《法言·孝至》末句,均以为是箴讽王莽之言。*汪荣宝:《法言义疏》卷二〇,第559页。晋人范望《太玄解赞序》则以扬雄仕莽为“朝隐”,*司马光:《太玄集注》附录,刘韶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31页。而刘勰《文心雕龙·封禅》更将《剧秦美新》视为封禅书之代表作而加以表彰,*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95-296页。唐初李周翰也认为扬雄剧秦美新乃“意求免于祸,非本情也”。*李善等:《六臣注文选》卷四八,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11页。只有北齐颜之推、唐初李善、唐末皮日休和陈黯指责扬雄媚莽。*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59-260、237页;李善等:《六臣注文选》卷四八,第911页;皮日休:《皮子文薮》卷五,萧涤非、郑庆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4页;陈黯:《诘凤》,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三六〇,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850页。
关于扬雄与新莽关系最为激烈的争论主要发生在宋代,不过,这一争论之思想脉络的起源则要追溯至唐代中后期,而争论关涉扬雄的道统地位问题。皮日休《法言后序》针对李轨和柳宗元的注解批评说:“说者以为扬子逊伪新之美,又以为称其居摄之前云。……既有其文,不能无其论,吾得之矣,在《美新》之文乎,则雄之道于兹疵也。”*皮日休:《皮子文薮》卷五,第54页。皮日休应该是将此视为韩愈认为扬雄“大醇而小疵”的原因,*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马茂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37页。但韩愈事实上对扬雄颇为推崇,他曾说:“己之道乃夫子、孟子、扬雄所传之道也。”*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二,第136页。他的很多追随者既继承其孔子传道于孟子的看法,又将扬雄视为孟子的继承者,并以韩愈继之,如林简言便上书韩愈云:“去夫子千有余载,孟轲、扬雄死,今得圣人之旨,能传说圣人之道,阁下耳。今人睎阁下之门,孟轲、扬雄之门也。”*林简言:《上韩吏部书》,姚铉编:《唐文粹》卷八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页。从韩愈以至宋仁宗时期乃唐宋儒家道统系谱建构的第一阶段,参与其中的士人仍大多以叠加这一道统系谱为主,而扬雄乃这一道统系谱中继孟子之后最为重要的承递者之一。*郭畑:《宋代儒家道统系谱演变研究:以孟、荀、扬、王、韩“五贤”为中心的考察》,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1年。很长时间里,皮日休对扬雄媚莽的批判并未得到其他士人的呼应,相反,北宋诸多士人为了维护扬雄的道统地位而极力为其辩护。
宋初,柳开即作《扬子剧秦美新论》以反驳皮日休,他认为扬雄通过贬低极恶之秦来称颂新莽,其实是一种高明的修辞手法,扬雄不仅可以以此自保,而且还暗中讽刺了新莽。*柳开:《河东柳仲塗先生文集》卷二,四川大学古籍所编:《宋集珍本丛刊》,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1册,第450-451页。赵湘也作《投阁辨》,认为扬雄投阁未死是因为“天之未丧斯文也,莽其如予何”,而扬雄此后“不能谢病,复为大夫”,则系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之意。*赵湘:《南阳集》卷四,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4页。僧人智圆在其《广皮日休〈法言后序〉》中否定了李轨、柳宗元和柳开的辩解,认为曲意维护扬雄,“意欲大子云之道,反小之”,扬雄颂莽其实并不影响其人其书的道统地位。*释智圆:《闲居编》卷一二,台湾藏经书院编:《续藏经》,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95年,第101册,第89-90页。宋仁宗时期,宋咸和吴秘注《法言》“阿衡”一句发挥了李轨的见解,注“汉兴”一句则否定柳宗元认为扬雄因学极阴阳而预测汉代中兴的思路,转而以贬斥新莽乱政、民思汉德的思路来肯定扬雄对汉代中兴的预测。*汪荣宝:《法言义疏》卷二〇,第559、562页。石介则云:“寻、邑三公,舜、歆高爵,不作符命,甘投于阁,见之子云。”*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一八,陈植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15页。其师孙复也作《辨扬子》一文,认为扬雄“耻从莽命,以圣王之道自守,故其位不过一大夫而已”,并认为《太玄》“非准《易》而作也,盖疾莽而作也”。*孙复:《孙明复先生小集》,四川大学古籍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3册,第158-159页。按,孙复对《太玄》的这一解释在明清和近代得到不少附和、发挥,近来问永宁又添新证,参见问永宁:《〈太玄〉是一部“谤书”——“刺莽说”新证》,《周易研究》2005年第6期。李觏《吊扬子》也说:“其(《太玄》)指在于三纲兮,尤切切于君臣。君道光而臣道灭兮,尊卑之分以陈。……必称孝而称忠兮,异乎剧秦而美新。”*《李觏集》卷二九,王国轩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29-330页。同样解读出《太玄》惩前毖后的忠节意味。章望之《书扬雄传后》以考证的方法,断定《剧秦美新》和《法言》“阿衡”一句乃仇视扬雄者编造的伪作,他依据“汉兴”一句说:“雄知莽之必灭,汉之必兴,潜著是言于言之末,欲以刘氏之复立者,是其怀忠履洁若是之炳炳也,又何以致疑于雄哉?”*《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四川大学古籍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94册,第692B页。
宋仁宗末年,随着古文运动渐入高潮和对儒家之道探索的深入,士人对于扬雄的态度开始出现分裂的迹象。欧阳修说:“子云、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欧阳修全集》卷四七,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64页。对扬雄思想的评价相当低。而在扬雄与新莽之关系这一点上,郑獬曾云:“子云迫于莽,投之阁,此又何也?”*郑獬:《郧溪集》卷一八,四川大学古籍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15册,第167B页。刘敞则说:“扬子剧秦美新,畏祸投阁,苟悦其生,而不顾义。……为畏而投与刑而死同,为投而死与刑而诛异。”认为“扬子不知命”,*刘敞:《公是先生弟子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20页。其《西汉三名儒赞》也持同一看法。*刘敞:《公是集》卷四九,四川大学古籍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9册,第746-747页。僧人契嵩也批评说:“《美新》之言,苟言也,……是皆不宜为而为之也。”*释契嵩:《镡津文集》卷七,四川大学古籍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4册,第394页。
以上这些辩解和批评,大多都只针对扬雄是否媚莽,很少就扬雄仕莽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展开争论,但到北宋中期,关于扬雄是否失节的争论重心已开始逐渐转移至仕莽一点上。随着宋代新儒学的发展和分裂,不同学派对于扬雄的态度变得极为分歧。司马光一系和王安石一派虽然势难两立,但都极力推尊扬雄,司马光积极为扬雄仕莽辩护,王安石一派则为扬雄仕莽寻求儒家义理上的合理性解释。然而,苏氏蜀学和二程理学则极力贬低扬雄,前者尚仅着眼于否定扬雄之思想地位,二程则更抓住扬雄仕莽的政治道德软肋大力抨击,其影响至于南宋,且最终导致了扬雄“莽大夫”身份的成立。
二、北宋中后期关于扬雄仕莽的争论
针对以往对于扬雄的批判,司马光的《〈法言〉集注》在注解“阿衡”一句时花了很大的力气为其辩护。司马光认为“阿衡”一句是扬雄“不得不逊辞以避害”,并云:“当是之时,莽犹未簒,人臣之盛者无若伊、周,故扬子劝以伊、周之美,欲其终于北面者也。”即以此为规谏王莽之语,这其实仍然不出李轨的思路。针对扬雄既不能死国之难、又未能离朝而隐、却反而作颂莽之语的责难,司马光一方面强调扬雄“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的事实,认为扬雄作逊辞绝不可能是为了爵禄;另一方面,他强调王莽不容名士退隐的政治背景,认为扬雄没有全身而退的可能;最后,在司马光看来,与“据将相之任”的社稷重臣不同,扬雄“位不过郎官,朝廷之事无所与闻”,不应承担死国之难的政治道德义务。*汪荣宝:《法言义疏》卷二〇,第559-560页。司马光在《迂书·辨扬》中也同样大力为扬雄辩解,思路与《〈法言〉集注》相同。*《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四,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在其极力维护纲纪名分的《资治通鉴》中,他甚至还特意在新莽天凤五年(18)下把“扬雄卒”作为一个重要事件书写其中,并在其下着重刻画了扬雄“恬于势利”和排辟异端的道统人物形象,*《资治通鉴》卷三八,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216-1217页。而对于其他阿附王莽的重臣则全以“死”书之。
晁说之是司马光的忠实追随者,在尊崇扬雄一点上同样如此。他钩沉史料,撰作《扬雄别传》上下两篇,其为扬雄辩护的意图非常明显。他继承司马光关于扬雄无法隐退的看法,又继承柳开《剧秦美新》乃是讽刺新莽的解读,还找到了其他一些扬雄“言无阿倚”的证据,认为扬雄的诸多箴言之作乃其目睹新莽乱政,为了“劝人臣执忠守节,可为万世戒”而作。文末总结说:“(扬雄)无仕进心,……至于投阁事,余亦疑焉,而世已有辩之者。”*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一九,四部丛刊续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18页。着意刻画扬雄“恬于势利”的形象。所谓“世已有辩之者”,当是接下来将要讨论的王安石。
王安石说:“孟子没,能言大人而不放于老、庄者,扬子而已。”*《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68页。将扬雄视作孟子的继承者。关于扬雄投阁一事,王安石有诗云:“岂尝知符命,何苦自投阁。……史官蔽多闻,自古喜穿凿。”*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卷一二《扬雄三首》之二,高克勤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95-296页。其《与北山道人》诗亦云:“子云识字终投阁,幸是元无免破除。”*《临川先生文集》卷三六,第392页。关于扬雄仕莽,王安石撰《禄隐》从儒家义理解释其合理性,其文云:
圣贤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迹也。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非君子也。……饿显之高,禄隐之下,皆迹矣,岂足以求圣贤哉?唯其能无系累于迹,是以大过于人也。……《易》曰“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言君子之无可无不可也。*《临川先生文集》卷六九,第730-731页。
在王安石看来,圣贤之道永远是相同的,只是圣贤会根据不同的历史处境而有所权变,因而可能导致不同的具体实践,所谓道同而迹不必同。因此,扬雄“岁晚天禄阁,强颜为《剧秦》。趋舍迹少迩,行藏意终邻”,*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卷一二《扬雄三首》之一,第294页。这并不构成扬雄的道德污点。王安石还引用儒家经典作为阐释依据,在《答龚深父书》中,他也再次强调“扬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二,第765页。在王安石看来,扬雄几乎可以作为士人进退出处的典范。
王安石之论得到不少士人的支持和发挥,林希即以“扬雄为禄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九,《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51页。而王回更“谓扬雄处王莽之际,合于箕子之明夷”,即认为暴君在上,贤臣在下不得用,而且可能有杀身之祸,所以不得不明哲保身。不过,王安石和王回的解释也引起友人的一些驳难,常秩便注意到“箕子乃同姓之臣,事与雄不同”,而且他认为“无不可者,圣人微妙之处,神而不可知者也。雄德不逮圣人,强学力行,而于义命有所未尽,故于仕莽之际,不能无差。又谓以《美新》考之,则投阁之事,不可谓之无也”,且“谓《美新》之文,恐箕子不为也”。*《曾巩集》卷一六,陈杏珍、晁继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65、266页。不过,常秩对扬雄的判断应该也是源于王安石,王安石曾说:“自秦汉已来儒者,唯扬雄为知言,然尚恨有所未尽。”*《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四,第786页。常秩以扬雄剧秦美新与投阁之事相参证,反对王安石否认扬雄投阁的判断。
曾巩对扬雄的评价较王安石更高,他曾说:“承孟子者,扬子而已。”*《曾巩集》卷一二,第199页。又说:“自斯以来,天下学者知折衷于圣人,而能纯于道德之美者,扬雄氏而止耳。”*《曾巩集》卷一一,第177页在其《答王深父论扬雄书》中,他极力反驳常秩而发挥王安石之论。他一方面维护王回之说云:“不去非怀禄也,不死非畏死也,辱于仕莽而就之,非无耻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故吾以谓与箕子合。”又反驳常秩“无不可”不可学之说云:“在我者不及二子,则宜有可有不可,以学孔子之无可无不可,然后为善学孔子。”而对于《剧秦美新》,曾巩认为这是扬雄“不得已”之作,是“诎身所以伸道”,并引孔子见南子为说,认为《剧秦美新》并不构成扬雄的政治道德污点。最后,曾巩又以旁证支持王安石否定扬雄投阁的判断。而其结论是:“雄于义命,岂有不尽哉?……雄处莽之际,考之于经而不缪,质之于圣人而无疑,固不待议论而后明者也。”*《曾巩集》卷一六,第265-266页。
宋神宗元丰年间,在新党的努力下,扬雄的道统地位得到官方的制度化肯定。熙宁七年(1074)十二月,“常秩等乞立孟轲、扬雄像于孔子庙庭”,因翰林学士杨绘极力反对,“后不果行”。元丰七年(1084)四月,陆长愈请以孟子“与颜子并配”,太常寺反对,但以林希为首的礼部则极力支持,并进而建议增加荀子、扬雄和韩愈从祀;五月壬戌,神宗从礼部议,诏孟子与颜子并配,并准“荀况、扬雄、韩愈以世次从祀于二十一贤之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八熙宁七年十二月庚寅条、卷三四五元丰七年五月壬戌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304、8291页;林希:《上神宗论孟子配享》,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九一,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986页。这两次礼议的主要支持者常秩和林希,都曾讨论过扬雄出处,而且都受到王安石见解的影响。
由于司马光一系比王安石一派更为尊崇扬雄,所以新党制度化地提升扬雄的地位也得到一些旧党士人的附和。元祐年间,朱光庭奏请经术取士“第三场试论一道,乞于《荀子》、《扬子》、《文中子》、韩吏部文中出题”。*朱光庭:《请用经术取士》,吕祖谦编:《宋文鉴》卷六〇,齐治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902页。元祐七年(1092)五月癸巳,又“诏秘阁试制科论题,于九经兼正史、《孟子》、《扬子》、《荀子》、《国语》并注内”出题。*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三元祐七年五月癸巳条,第11284页。宋徽宗政和年间,极其推崇扬雄的许翰甚至还建议将王安石清除出孔庙而继以扬雄配享。*《许翰集》卷四,刘云军点校,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8-69页。
然而,苏氏蜀学和二程理学却极力否定扬雄。大概受欧阳修的影响,苏洵作《太玄论》彻底否定扬雄的思想价值,*曾枣庄、金成礼:《嘉祐集笺注》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69-203页。苏轼的看法也完全相同。*《苏轼文集》卷四九,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18页。不过,苏氏的批评都只是从学术思想着眼,并不涉及扬雄的忠节问题。与苏氏不同,理学阵营尤其是二程则不仅否定扬雄之思想价值,更就扬雄媚莽、仕莽极力攻击。邵雍虽然颇重《太玄》,认为“夫《玄》之于《易》,犹地之于天也”,*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一〇,第1页。但他也有诗云:“荀扬若守吾儒分,免被韩文议小疵。”*《邵雍集》卷七,郭彧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70页。张载认为扬雄在儒道上“止得其浅近者”,并说扬雄“所学虽正当,而德性不及董生之博大”。*张载:《经学理窟·周礼》,《张载集》,章锡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51页。二程的议论更多,否定也更激烈。如程颐说:“荀、扬性已不识,更说甚道?”又说:“扬子,无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断,优游而不决。”除此之外,二程抨击更多的是扬雄仕莽一点,程颢说:“扬子出处,使人难说,孟子必不肯为扬子事。”程颐则直接断定“扬雄去就不足观”。二程认为扬雄既“无先知之明”,事后“则欲以苟容为全身之道”,针对传统的“言逊”说,程颐认为“言逊”须“迫不得已,如《剧秦美新》之类,非得已者乎”?而针对《剧秦美新》实乃刺莽之作的说法,程颐认为王莽族诛“亦未足道”,“讥之济得甚事”?二程也赞同王安石否认扬雄投阁的判断,但是,“扬子云之过,非必见于美新、投阁也。夫其黾勉莽、贤之间,而不能去,是安得为大丈夫哉”?二程认为:“扬子云仕莽贼,谓之‘旁烛无疆’,可乎?隐可也,仕不可也。”同时程颐完全否定林希以扬雄为“禄隐”的义理解释。而针对司马光等人认为扬雄不可能全身而退因而被迫留在新莽的辩护,二程则说:“苟至于无可奈何,则区区之命,亦安足保也?”*《二程集》,第255、325、136、231、231、68、251、73、403、251、1235页。几乎将以往对于扬雄颂莽、仕莽的辩护全都进行了驳斥。
二程的批评得到一些士人的响应,其门人周行己即以《剧秦美新》是否构成扬雄的政治道德污点策问士子,*周行己:《浮沚集》卷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32页。李新也说:“雄一不胜,即大言《美新》。”*李新:《跨鳌集》卷一八,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5册,第17页。林季仲亦云:“《美新》之书,亦得已而不已矣。”*林季仲:《竹轩杂著》卷三,四川大学古籍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42册,第161页。不过,苏轼、程颐等人对扬雄的批评,“仅作为边缘的思想潜流而存在”,*刘成国:《宋代尊扬思潮的兴起与衰歇》,《史学月刊》2018年第6期,第44页。二程对扬雄仕莽的批判仍然主要被司马光和王安石的辨解所掩盖,但这一局面至宋室南渡而突变。
三、南宋扬雄“莽大夫”身份的成立
仕否异姓的问题对于君主来说本来就很敏感,宋神宗就曾说:“扬雄剧秦美新,不佳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八元丰六年八月辛卯条,第8149页。而北宋灭亡过程中的惨痛经历,则直接将这一问题置入到现实政治之中。伴随着王安石新学被塑造为北宋灭亡的替罪羊,对扬雄仕莽的批判也日渐高涨,而且成为具有现实紧迫性的政治问题。
宋室南渡后,很快便有人在攻击王安石之学误国时一并批判扬雄。邓肃于建炎三年(1129)就既指责王安石新法误国,又说:“自荆舒……尊扬雄以赞美新之书,故学者甘为异姓之臣。”*邓肃:《栟榈先生文集》卷一九,四川大学古籍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39册,第788页。沈与求在与宋高宗的对话中同样如此立论,时间在绍兴元年(1131),与邓肃相近,史载:
上尝从容言王安石之罪在行新法,与求对曰:“安石以己意变乱先帝法度,误国害民,诚如圣训。然人臣立朝,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心术之邪正。扬雄名世大儒,主盟圣道,新室之乱,乃为美新剧秦之文;冯道左右卖国,得罪万世。而安石于汉则取雄,于五代则取道,臣以是知其心术不正,则奸伪百出,僭乱之萌实由于此起。自熙宁、元丰以来,士皆宗安石之学,沉溺其说,节义凋丧,驯致靖康之祸,污为卖国,一时叛逆,适逭典刑。愿陛下明正其罪,以戒为臣不忠者。”是时上欲究僭伪事,因与求之言遂大感悟。*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四十七》,台北:大化书局,1979年,丙集,第225页。
绍兴六年,陈公辅又依循沈与求的思路再次上疏攻击王安石,将北宋灭亡归咎于新法和士大夫忠节之凋丧,而后者则因王安石赞赏扬雄和冯道而起。*《宋史》卷三七九,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694页。胡寅在给秦桧的信中也持同样的思路,*胡寅:《斐然集》卷一七,《崇正辨·斐然集》,容肇祖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53-354页。在他为高宗代笔追废王安石孔庙配享的诏书中,“高言大论,诋訾名节,历事五代者谓之知道,剧秦美新者谓之合变”和“废绝《春秋》”成为王安石最为主要的罪证。*胡寅:《斐然集》卷一四,《崇正辨·斐然集》,第313页。
在两宋交替的政治背景下,批判扬雄和冯道不仅可以攻击王安石和新党,从而为北宋灭亡寻找替罪羊,并且直指那些在两宋之交有着政治污点的士大夫,宋高宗“欲究僭伪事,因与求之言遂大感悟”正是这一政治氛围的写照。由此,批判扬雄媚莽、仕莽的声音不断出现,沈与求有诗云:“结缨季路空遗迹,投阁扬雄亦厚颜。”*沈与求:《沈忠敏公龟溪集》卷三,四川大学古籍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39册,第256页。胡寅也让士子讨论扬雄仕莽。*胡寅:《斐然集》卷二九,《崇正辨·斐然集》,第638页。邓肃更著《书扬雄事》一文,极力抨击扬雄不忠不智,认为扬雄“欲作《美新》之书久矣,岂迫于不得已而后为乎”,攻击扬雄“身为叛臣,无所容于天地之间”。*邓肃:《栟榈先生文集》卷一九,第786页。后来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如此批判扬雄,可能还是受到了邓肃的影响。*《栟榈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七,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52-1353页。绍兴十八年(1148),四川类省试“策问古今蜀人材盛衰之故”,德阳士子何耕对策有云:“扬子云作《美新》以媚贼,又蜀人所羞。”*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八,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562-2563页。可见对扬雄失节的判断已经成为普遍共识。此后,沈作喆于淳熙年间说“扬子云作符命显,是隳丧大节”,而后人为他所作的辩解“是教人臣为不忠”。*沈作喆:《寓简》卷四,《全宋笔记》第四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5册,第37页。当然,对扬雄作出决定性评价的,乃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
二程虽然否定扬雄,但仍有所保留地说:“自汉以来,惟有三人近儒者气象:大毛公、董仲舒、扬雄。”*《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二程集》,第232页。而朱熹却对扬雄批评至极,他说:“扬雄则全是黄老。某尝说,扬雄最无用,真是一腐儒。……他见识全低,语言极呆,甚好笑!”又说:“扬子云出处非是。当时善去,亦何不可?”他认为扬雄对明哲保身的理解完全是“占便宜底说话,所以它一生被这几句误”。*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七、卷八一,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155、3264、2137页。朱熹对于扬雄之人品、学术都极力否定,他在《楚辞后语》论及扬雄《反离骚》时,特意说这是“汉给事黄门郎、新莽诸吏中散大夫扬雄之所作”,并云:“王莽为安汉公时,雄作《法言》,已称其美比于伊尹、周公。及莽簒汉,窃帝号,雄遂臣之。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又仿相如《封禅》文献《剧秦美新》以媚莽,意得校书天禄阁上。”根据这种几乎无中生有的解读,他断定扬雄“为屈原之罪人”,而《反离骚》“乃《离骚》之谗贼”,*朱熹:《楚辞后语》卷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9册,第248-249页。将扬雄之仕莽与屈原之死国形成鲜明对比。《楚辞后语》又录蔡琰《胡笳》,其意则“非恕琰也,亦以甚雄之恶”。*朱熹:《楚辞后语》卷三,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9册,第265页。在《楚辞辩证》中,他也仍然不忘指责扬雄“专为偷生苟免之计”。*朱熹:《楚辞辩证》下,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9册,第215页。
当然,朱熹对扬雄最彻底、影响最大的否定乃是其在《资治通鉴纲目》中书“莽大夫扬雄死”,其下注释大体节略《汉书·扬雄传》,但是末尾却说:“所作《法言》卒章盛称莽功德可比伊尹、周公,后又作《剧秦美新》之文以颂莽,君子病焉。”完全逆转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扬雄的刻画和评价。至于为何如此苛责扬雄,朱熹解释说:“所以事莽者虽异,而其为事莽则同,故窃取赵盾、许止之例而概以莽臣书之。所以著万世臣子之戒,明虽无臣贼之心,但畏死贪生而有其迹,则亦不免于诛绝之罪。此正《春秋》谨严之法。”*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七,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1册,第1632页。按,《资治通鉴纲目》是否全部出于朱熹之手存在争论,而此条尤甚,如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史学略说》云:“然《纲目》于天凤五年下大书‘莽大夫扬雄死’六字,则有意与温公立异。官职卑微者,史不必书其死。史书凡例,蛮夷君长盗贼酋帅曰死,大夫则称卒称薨。故曹操、司马懿之奸恶,其死也,亦不能不曰卒,乃于扬雄特书曰死,此晦庵不能自圆其说者也。惟此书出赵师渊手,故有此体例不纯之事。其后,尹其莘为之发明,刘友益为之作书法。恐亦彼辈逞臆之说,不免村学究之陋习耳。”但朱熹《答尤延之(一)》其实已经有所辨明,其云:“《纲目》不敢动着,恐遂为千古之恨。……按温公旧例,凡莽臣皆书‘死’,如太师王舜之类,独于扬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称而以‘卒’书,似涉曲笔,不免却按本例书之曰‘莽大夫扬雄死’,以为足以警夫畏死失节之流,而初亦未改温公直笔之正例也。”则此条应出自朱熹之手无疑,而且他在《楚辞后语·反离骚》中也有“雄因病免,既复召为大夫,竟死莽朝”之语,与《纲目》相同。不过,罗大经《鹤林玉露》的一些版本则作“莽大夫扬雄卒”,倒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章太炎的判断,因为《纲目》作成后一直在修改,或有“死”“卒”的不同版本。以上参见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史学略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48页;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七,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1册,第1631页;朱熹:《楚辞后语》卷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9册,第249页;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六“莽大夫”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0页。关于《纲目》的成书过程和作者问题,可参见汤勤福:《朱熹与〈通鉴纲目〉》,《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2期;汤勤福:《朱熹给赵师渊“八书”考辨》,《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3期;郭齐:《关于朱熹编修〈资治通鉴纲目〉的若干问题》,《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仓修良:《朱熹和〈资治通鉴纲目〉》,《安徽史学》2007年第1期。尔后大多数士人都接受了朱熹的“笔法”,罗大经称颂朱熹此笔与“《春秋》争光,麟当再出”,*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六“莽大夫”条,第340页。邹应龙也说朱熹“去取之意”在于“明三纲五常之义,如读《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邹应龙:《楚辞后语跋》,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9册,第311页。尹起莘更“发明”朱熹之意云:“士君子当安于命义,不当以苟活为心,诚使遁迹丘园,饥饿而殁,既能不辱其身,所获多矣。昔程颐子有言:‘饥饿死最轻,失节事最大。’观《纲目》所书‘莽大夫扬雄死’,则雄之失身于莽,尽东海之波,不足以湔其耻矣。”*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卷八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689册,第500-501页。由于《纲目》不管在思想上还是编纂体例上都是“一部历史好教材”,加之此后朱熹思想地位的影响,使得宋元以来形成了“《纲目》热”,而《纲目》在明清时期也成为上自科考士子、下至启蒙幼童必读的历史书,*仓修良:《朱熹和〈资治通鉴纲目〉》,《安徽史学》2007年第1期,第22页。扬雄之“莽大夫”身份越来越成为定论,终于成为了失节士大夫的符号性人物,直到章太炎都还说扬雄“阿附巨君”,又说“子云投阁,其自得者可知”。*章太炎:《国学讲演录》之《史学略说》《诸子略说》,第148、179页。
不过,即便在南宋,也还是有少数士人以较为正面的立场来看待扬雄。洪迈就说扬雄“仕汉,亲蹈王莽之变,退托其身于列大夫中,不与高位者同其死,抱道没齿,与晏子同科”,又赞同扬雄《剧秦美新》实为讽刺新莽之作的说法,*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三,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69-170页。并且采用柳宗元注“阿衡”一句“不可过,过则反”的解释。*洪迈:《容斋五笔》卷五“万事不可过”条,第881页。黄履翁也遵循孙复《太玄》嫉莽说。*黄履翁:《古今源流至论别集》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42册,第572-573页。尤袤则至少两度致书朱熹,指出《纲目》苛责扬雄太过而无当。*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七,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1册,第1631-1632页。而陈亮和叶适更对朱熹的评价不以为然,陈亮认为“扬雄度越诸子”,*《陈亮集》卷九,邓广铭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8-100页。而叶适则认为扬雄“虽巽而不谄明矣”,并特别注意到哪怕东汉之时也没有人指责扬雄剧秦美新,他针对《纲目》云:“千载之后,方追数雄罪,为汉举法,惜哉!惜哉!”*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四,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62页。然而,这些声音终究很快边缘化,而朱熹的评判则成为“定论”。理宗宝庆三年(1227)初,在追封朱熹后不久,朱熹子未在便以扬雄剧秦美新为由,向理宗建议罢祀扬雄。*李心传:《道命录》卷一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15页。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扬雄终因“臣事贼莽”而被罢去从祀孔子的资格。*《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五,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3年,第5册,第3555页。《明史》卷五〇《礼志》误系为洪武二十八年,参见《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87页。
四、两宋忠节观念的强化
以往关于忠节观念强化的研究大多笼统地将宋人的观念与秦汉做对比,对两宋忠节观念强化的具体表现和转变过程则较为忽略,而且也不大注意忠节观念是否对不同层次的士大夫和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要求。从宋人大多为扬雄辩护以至扬雄“莽大夫”身份的成立,显然与两宋忠节观念的强化相伴随,而如若引入宋人对冯道等人物的评价之转变作为参照,则这个过程将更为清晰。
扬雄和冯道受到愈发严苛的批评这一大趋势虽然相同,但是二人的身份和经历毕竟不同,所以宋人对两者的否定过程并不同步。以现存文献看,宋初四朝对冯道的批评很少,且主要来自于君主。《旧五代史·冯道传》云:“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旧五代史》卷一二六,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666页。宋真宗也说:“冯道历事四朝十帝,依阿顺旨,以避患难,为臣如此,不可以训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五景德四年闰五月庚寅条,第1461页。宋仁宗则认为冯道“相四朝而偷生苟禄,无可旌之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一皇祐三年八月乙巳条,第4108页但冯道在士林中的形象尚属正面。与此相应,此时士人也大多为扬雄仕莽辩解。如石介不仅说扬雄“不作符命,甘投于阁”,而且说“五代之乱,则瀛王扶之”。*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八,第84页。颇有意思的是,后来石介文集的一些版本将“瀛王”改作“太祖”,此亦可见冯道地位转变之一斑。胡瑗也未指责扬雄仕莽,还认为:“当五代之季,生民不至于肝脑涂地者,道有力焉,虽事仇无伤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四,《二程集》,第73页。不过,从仁宗后期开始,这种局面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首先,欧阳修重写《五代史》,将冯道列于“杂传”之首,又在传首以303字的篇幅极力否定冯道,将其定性为“无廉耻者”。*《新五代史》卷五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11-612页。此后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不仅照抄了欧阳修的评论,更接着以502字的篇幅进一步指责冯道“全身远害”乃事君不忠。*《资治通鉴》卷二九一,第9510-9513页。然而,如前文所述,欧阳修虽然看轻扬雄之学,但是并不提及扬雄仕莽之事,而司马光及其后学更极力为扬雄仕莽辩护。以司马光为坐标,很容易看出王安石和程朱的不同观念。王安石继承北宋前期的一般看法,他既为扬雄仕莽寻求儒家义理上的合理性解释,又对冯道持赞赏的态度。*魏泰:《东轩笔录》卷九,李裕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9页;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上,郑世刚、杨立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4-15页。然而,二程不仅极力批判扬雄仕莽,而且反对胡瑗的评价而认为冯道“不忠”。*《河南程氏遗书》卷四,《二程集》,第73页。待至南宋,沈与求、陈公辅、胡寅诸人更将王安石推崇扬雄和冯道视作其心术不正的两大罪证。后来朱熹同样对扬雄和冯道都大加挞伐,他在《纲目》中既书“莽大夫扬雄死”,又书“周太师中书令瀛王冯道卒”,*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卷五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1册,第1021页。以讥讽冯道不知廉耻。
从宋初士人大多既肯定扬雄又肯定冯道,到司马光等人一面肯定扬雄一面否定冯道,再到程朱对扬雄和冯道双双彻底否定,宋学不同派别在忠节观念上的差异和两宋忠节观念的强化过程都清晰地显示出来。刘咸炘先生曾说:“议论宽厚者,亦北宋士大夫之风,异于南宋之竣厉者也。”*刘咸炘:《宋学别述》,《推十书》(补全本),上海: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247页。此诚卓识。不管是扬雄还是冯道,其形象的决定性转折都发生在南宋,这虽然直接由塑造王安石为北宋灭亡罪魁的意识形态建设之需要而起,但金人入侵,赵宋难而未亡,此种现实政治局面急需忠节观念以维系王朝稳定,这是导致忠节观念强化的现实背景。
两宋(尤其是南宋)忠节观念的强化,不仅表现在对扬雄和冯道这样的“负面”人物之否定上,同样也表现在对屈原、陶渊明、杜甫等“正面”人物的再发掘和新诠释上。朱自清说:“历代论陶,大约六朝到北宋,多以为‘隐逸诗人之宗’,南宋以后,他的‘忠愤’的人格才扩大了。本来《宋书》本传已说他‘耻复屈身异代’等等。经了真德秀诸人重为品题,加上汤汉的注本,渊明的二元的人格才确立了。”*朱自清:《陶诗的深度》,《朱自清全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6-7页。对陶渊明“耻事二姓”的解读,主要是在南宋才确立起来的。*唐文明:《隐者的生活志向与儒者的政治关怀——对〈桃花源记并诗〉的解读与阐发》,《思想与文化》第11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2-61页。屈原和《楚辞》在宋代的“兴盛程度远远超过魏晋南北朝以至唐五代”,而宋代以前,士人对屈原褒贬俱有,褒之者也大多只是推崇屈原“其志洁”“其行廉”而已,但是到宋代,尤其是南宋,屈原“忠君爱国”的形象被突显。*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2期。而在宋代,原本对君主不免有些抱怨的杜甫,也被树立成了“一饭不忘君”的典型。*葛晓音:《略论杜甫君臣观的转变》,《中州学刊》1983年第6期;孙微:《论杜甫的君臣观》,《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对扬雄和冯道形象的翻转,以及对屈原、陶渊明、杜甫等人的新读,如此大范围地改写历史人物评价,本身就显示出忠节要求在群体范围上的扩大。不管是屈原这样的同姓之卿,还是冯道这样的异姓之臣,抑或扬雄、杜甫这样的政治边缘人物,甚至陶渊明这样的“隐逸诗人”,从上到下的士人全都卷进了这场以忠节为标准的评价改写运动之中。忠节的要求对象大大地扩展了,不再局限于最负政治责任的高层士大夫。
宋人早期关于扬雄政治道德的争论,大多集中在扬雄是否媚莽一点,极少触及扬雄仕莽,而到司马光和王安石,已不得不为扬雄仕莽进行辩解,此已可见忠节要求强度的提高。司马光说:“国之大臣,任社稷之重者,社稷亡而死之义也。向使扬子据将相之任,处平、勃之地,莽簒国而不死,良可责也。今位不过郎官,朝廷之事无所与闻,奈何责之以必死乎?”扬雄的经历与冯道的显赫仕途大为不同,所以司马光才指责冯道而为扬雄辩护,而且他也认为“夫死者,士之所难”。*汪荣宝:《法言义疏》卷二〇,第560页。然而,如前所述,二程却否定扬雄退隐不得而仕莽自保的辩护,并认为:“苟至于无可奈何,则区区之命,亦安足保也?”则更可见不仅忠节的要求对象在群体范围上扩大到了从上到下的所有士人,而且同时大幅地提高了要求的强度。
在南宋灭亡前后,不仅涌现了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历史上著名的忠义之士,而且还出现了比较普遍的忠义自杀现象,其中不仅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朝廷官员,而且包括为数甚多的官员家眷,这些家眷之中又有一定数量的女性,此外,忠义自杀者中甚至还有一些没有明显政治背景的平民。*参见戴仁柱:《十三世纪中国政治与文化危机》,刘晓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第267-272页。这显然是南宋忠节观念强化的实践结果,由此也可以看出忠节的要求仍在不断扩充和加强,不仅在群体范围上扩大到官员的家眷和普通的平民,而且其在强度上的要求也并未随着政治责任的减弱而降低。而宋、金、元、明、清末分别出现的大量政治遗民,同样是忠节观念强化的结果。
两宋忠节观念的强化,并非如以往研究所强调的那样只与加强君主专制有关,而是有着相当深刻的政治和社会背景,而且影响颇为深远,但限于篇幅,只能另外专文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