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了一个
2018-03-16庞羽
庞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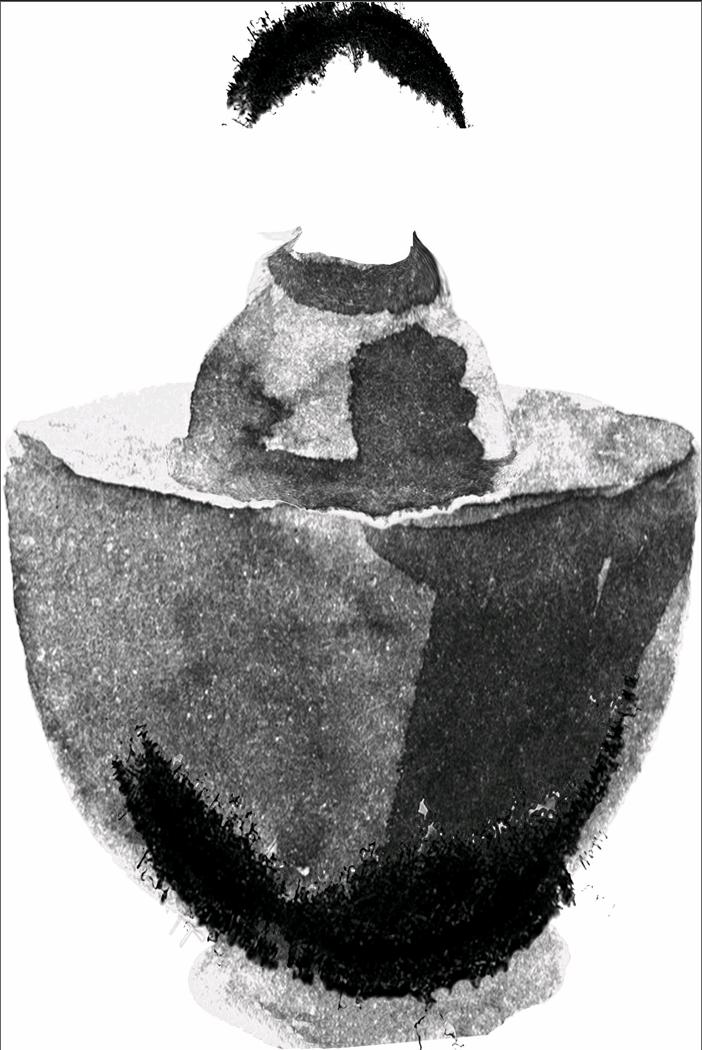
登机前,杏之又给对方打了电话。今日必须到达,明早就开机了。杏之瞧着时间,还没到早餐的饿。端着腿信步一段,刚冒出的日头把她的影子刷得油亮。蔡导好。不对。蔡导,您好。还是不够味。微微鞠躬。30度没诚意,45度太过。伸出的手不能有汗。头发昨天洗了。香水在背包里,淡淡的茶氛,不讨人嫌。还有什么呢。步子。右脚向前,距离别太大。要收腹。这次换了隐形眼镜。特地化了裸妆。嘴唇是玫瑰沙色,不张扬。手腕上一条细细的银链子,品位好歹不坏。指甲剪了,磨圆了。本想着带帆布鞋,土气。说什么都要穿着高跟鞋。山上路难走,夜里也冷。怕什么。她是林杏之。
这飞机肯定漏了。林杏之感受到了风。上面的风和下面的风不一样。上面的风冷,冷得心甘情愿;下面的风暖和一点,却总带着腌臜气。杏之期待龙卷风,它有通天的本事,可以把她卷到上头去。杏之倚着机窗。前方窄而尖,两侧风抽紧。上方的空调卷起微凉。杏之伸出手,想起了自己此行的目的。有什么在飞逝。杏之望向窗外,白的云,青的天,灰的地。远方,除了相似,还是相似。
在社会上滚了两年,杏之已经学会把自己的梦想轻拿轻放。才华是需要运气加护的。杏之老是数着她的学姐们。前两届的夏末,写了一出民国戏,红了半个地球。上一届的岑今今,跑到台湾做戏去了。杏之小了她们两岁,能伸展手脚的圈子小了不知几轮。这次的机会要抓住。她在微博上看见蔡导要去九寨沟拍戏,急征几个青年编务,要求尽快到场。
川航的空姐给杏之倒了一杯咖啡。浓酽的色,泛着的泡泡像星球。杏之对着咖啡吹了吹。星球破了,远了,又冒上来了。杏之感到鼻头一阵酸涩。宇宙太小了。它之外肯定还套着什么。宇宙太短暂了。一定有更宏大的东西使之站立。杏之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了一个套娃。这是她去俄罗斯交换学习时买的。杏之觉得套娃很眼熟,像她在子宫里梦到的母亲。最外面的生了里面的,再一层层地生下去。套娃才是历史的真理。
上面的风小了,没了。飞机落地,滑行。成都像是呲着火花一样掠过去。那是辣的山,麻的地,呛的水,一身油泼辣子的人们热气腾腾地走着。杏之拿了自己的背包。相机在箱子里托运。里面有电池,不让带。背着行李,挎着包,手里拎着自己的小半生。母亲说,当什么编剧导演,哄人的玩意儿。父亲说,老家今年的公务员比往年好考,报社也在招人。三听四听没什么,可年纪过了五,六亲都有了家,日子七上又八下,满腹的小九九,末流也没搭上。箱子里装着什么,上帝也无意让她猜。
机场里,簇簇人群,浪浪声波,不知哪里飘来红烧牛肉面的味道。杏之忽然觉得很安心。还有人要往远方去。还有人和她吃得一样。天热,机场空调足。她的手抓向自己的领子。落了空,索性垂下来,攥着包里的套娃。这么多人陪着她呢。少了一个,又是一个。
前面停着一轮的士。太阳还没有爬到中央。杏之的肚子碾过一层饿意。咬咬牙,她拿了午餐的钱,叫了一辆的士。地铁、公交都可以的,但没有诚意。杏之知道,对万事怀有诚意,万事多少温柔些。对万物怀有诚意,万物会帮衬着她。要说她两年前,刚毕业那会儿,眼白是云,眼瞳是星,舌头卷着潮汐,十指闪闪的贝壳,从大腿根往脚腕捋过去,像三贯钱一寸的罗绸,腰肢也长得俊俏,裹着微咸的珍珠粉。几个豆眼、葱眉、鱼肚嘴的女生讥诮她。她说,没人编,她编。没人导,她导。没人演,她演。
的士轰轰地觳觫着。杏之把鬓发绾到耳背去。人往老里走,怀里的东西会变的。被第六家影视公司拒绝的那晚,她抱着一厚叠剧本,坐在拥挤的地铁里。城市的五光十色,只配作被剪掉的空镜头。短裤的腿,系带的高跟,低腰的西装裤,泛黄的背心,一个男孩吞咽着劲脆鸡腿堡,一阵阵的香,却刺激着她的倦。她靠着旁边的玻璃板,眼眉垂垂下坠。剧本散了一地,她又惊醒。好好地待着呢。没用的东西最坚固。她卷了眼角,细细地锥入梦乡。梦里,她变成了钟摆,摇过来,摇过去,把地铁从微亮摇到浓黑。朦朦胧胧中,有手推她。望去,车厢里空无一人。底站了。那边哪像现在,满路的的士。
车站里聚满了人。成绵高速的车被困在了半路,只有成灌高速的车能够发车。从成灌高速到都江堰,滔滔的水涌过去,就到了都汶高速。汶川就在一边,毁灭与繁华从来都是骨与肉。再一路往下去,过了县走了乡,上国道了。随后是九寨沟。算上路上耽搁的时间,晚上8点前可以到达目的地。
此时正值九寨沟旅游旺季,成绵高速那边误了四班车了。没能准时上车的旅客所幸改了车票,拥到了这个窗口。要发车了。可不能耽搁一秒钟。杏之蹙起了身子,想把五官贴到车门上去。检票员一个错手,遣回了她。走了一辆,人群松弛了些,又密匝匝地往前凑。杏之擒着自己,煸着自己,挲着自己,想把自己卷成烟,好歹能飘出去。人群长满了刺藤子。贴不住脚,就随着人的气儿走。左边空了两寸,斜来一只手。右侧又稠了三分,肩踵叠着背,搓出了汗臭味。前面的耸着背,把杏之包里的套娃嵌入了她身体。硌得疼。仿佛套娃是她的孩子,藏在她的子宫里,人稍一挤压,孩子就疼,她也疼。
登车的闸门开了。恰似一道猛浪,杏之还没有回神,就被冲到了水尖。两个苗条的女子瞅着缝钻出去了,几个壮实的大汉绕不过去,一个劲地在后面推波。检票员对着话筒嚷,却嘈嘈切切听不见。杏之齁住了脑子,仿佛是被前面的人背出去的,也好像是被后面的人踢出去的,两边的人把她勾出去,也很有可能。检票员骂骂咧咧地关了门,里面的人群松弛了些,又密匝匝地往前凑。
一群人,闹哄哄地上了车。杏之摸准了一个靠后的位置。骂娘的、抢位置的、收拾行李的,像龙卷风下的一茬茬麦子,无主,无序,无神论。杏之眼皮酸涩,埋下自己的身子,想打个盹。不料传来一个女人的尖叫:谁抢了我的位置!杏之睁开眼,前面的人回头,后面的人伸长了脖子。是个歪脸的中年女人,叉着腰,哼着气。杏之缩回眼,屏住呼吸。她的嘴巴快到耳垂上去了,一只眼瞇成了一条缝,整张脸长成了东非大裂谷。
歪脸女人走到车头去,一个个座位数过来,不差。满当当的人,就是少了她。人们不说话,看着东非大裂谷从他们身边穿过,静静地、默默地、一寸寸地再次开裂。歪脸女人在车尾站住,伸出食指,东西,左右,上下,都一个个地点了兵:你抢了我的位置。你也是!站起来,滚出去!人们按捺着脑袋,没有一个人表示回应。歪脸女人上前,揪住一个女孩的衣衫:就是你,小婊子!女孩吓白了脸,些许的红晕又泛上来,圆眼睛一瞪,微翘着红指甲的手,把歪脸女人的手指拨拉开了:阿姨,我可是买了票的,不信,给你看看?后面童花头的小姑娘笑了。歪脸女人松开手,阴阴沉沉地望着她。小姑娘被看得噤了声,左手摸索着右手,右手互相掐红了,也难怪,那个歪嘴太吓人了。歪嘴女人可能觉得还不够,右手搭在椅背上,左手慢慢探过去,指甲尖利,指骨奇崛,满手的青筋。小姑娘咕隆一声,想把自己嵌回去。一旁的大人看不下去了,打开歪嘴女人的手:凶什么凶!
歪嘴女人望着自己垂下的手,两眼也变得浑浊起来。突然,她又抬起了眉目,朝小姑娘送去一个扭曲的、可骇的、铺天盖地的歪笑。小姑娘吓得哭了出来。大人推开歪嘴女人,捂着小姑娘的眼睛。歪嘴女人站住了脚,气定神闲地说,别看,小姑娘,你长大了也这样子。
在一车人的吵闹声中,墨镜司机走上了车。墨镜照出了四个歪嘴。谁也看不见司机的表情,只听见他说:多一个人就走不了。下来一个。这下,全车人都坐不住了,纷纷举起手里的车票,嚷着让歪嘴女人下车。歪嘴女人也从兜里掏出了一张车票:司机先生,我可是买了票的,不信,给你看看?
杏之一直坐在后头。按照车的构造,她位置下应该是后轮。后轮还冒着热气,蒸腾腾地往上冲,汗密密、湿漉漉的。车里很嘈杂,她想起了小时候。老师让他们上台讲“我的梦想”,有的是作家,有的是科学家,有的要做宇航员。她说,她会成为中国的卡梅隆。小朋友问卡梅隆是谁,她说是泰坦尼克号的爸爸。小朋友炸锅了,说林杏之长大了会生出泰坦尼克号。有几个懂事的,偏问爸爸怎么生孩子?想到这,杏之嘴边抹了一丝笑。说当作家的做起了微商,当科学家的开了奶茶店,还有那个当宇航员的,没有放弃理想,四处碰壁后,从山上摔下来,成了瘸子。那个班上,离梦想最近的是她自己,离梦想最远的也是她。
车厢里开始推来搡去。歪嘴女人拽着红指甲女孩的头发,偏要把她拉下车。女孩尖叫着,用红指甲划着女人的脸。有个男子上来劝架,歪嘴女人的力气比他大。墨镜司机咳嗽几声,三个人都住手了。司机问:这个女孩抢了你的位置?女孩抢先反驳:先来后到,你问问大家,谁按照位置坐了?墨镜对准歪嘴女人。歪嘴女人伸出手,手上全是拽下的发,栗色的,带卷的,尔后她缓缓地拍手,头发扑簌簌地下,嗓音凉飕飕地起:对,她抢了我的位置。就是她!男子看不住了:阿姨,你稍微讲讲理好不好?歪嘴女人朝他眯起了眼,一口痰啐到他脚下:你们男人,都一样。
杏之想起了好几个男人。比如她的爸爸,从小把她架在脖子上,逢人都说这是他女儿,可聪明了。比如她的中学老师,老是给她补习奥数,毕业时,说以后发达了,可别忘了老师。还有她的初恋男友,坐公交乘地铁,就是为了给她买最爱的烤红薯。对呀,他们都一样。打开爸爸的身体,就是中学老师,打开中学老师的身体,就是她的初恋男友。打开到最后,是空心的,还是实心的呢?就像这个宇宙,大宇宙生中宇宙,中宇宙生小宇宙,物质、细胞也都是相生的。她最喜欢的电影,托马斯·麦卡锡的《聚焦》,影片的表达只是外层,而它所讲的故事,“神父性侵儿童案”是内层。题材、风格、技巧、视角都是一致的,就像套娃,无论里外,都是一样的形状与花纹。权利的勾结、宗教的盲从、法律的无助、性向的歧视,这一切,打开一个,还有一个。最后剩了什么,大概就是无力吧。杏之觉得,即使她成为了中国的卡梅隆,她也会无力。宇宙后面还有宇宙,那无限空间后面呢?无尽时间后面呢?她处于哪一层?杏之看着窗外。隔着隐形眼镜,隔着车窗,隔着空气。那她看见了什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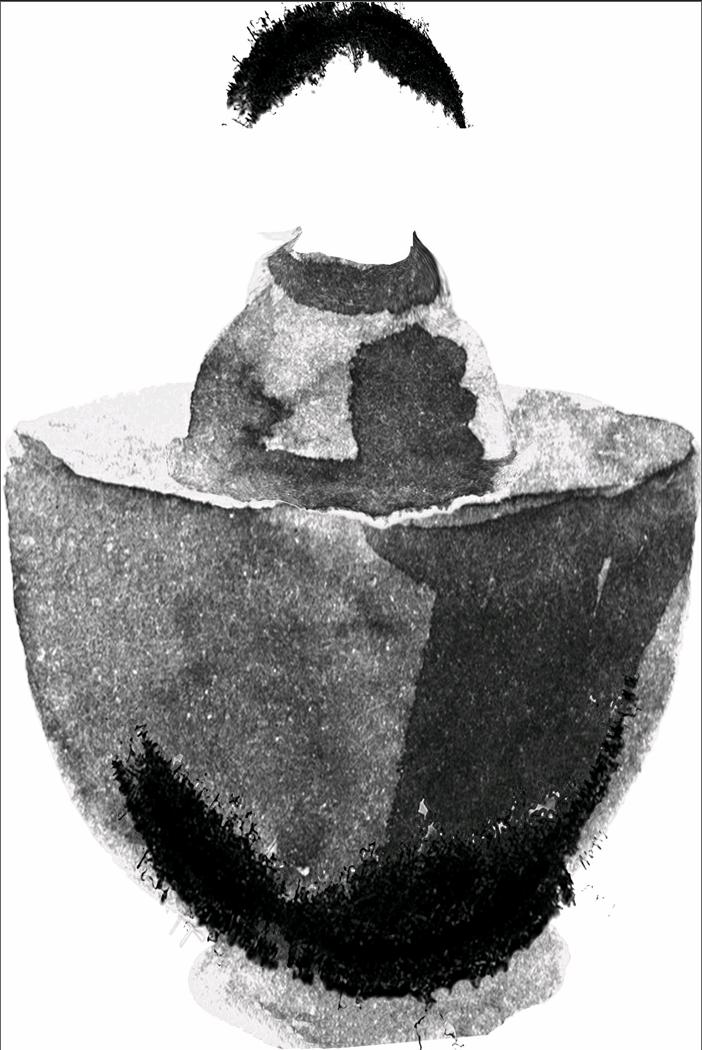
车厢里还在闹腾。那个男子和墨镜司机,架着歪嘴女人的胳膊,把她往后拉。歪嘴女人一个撒泼,往下面一倒,赖在了车上,边哭边捂着歪嘴,说什么她得了淋巴癌,刚做了手术,嘴巴歪了,男人也走了,带走了孩子,反正她也活不长了,这次就打算去个风景好一点的地方,再看看这个世界,再想一想,要不要了结自己。现在好了,死都不让她死,要是不带她去九寨沟,她就钻进车底下,和行李一块儿去,甩来甩去,甩死了,也是命……
大家都沉默下来。红指甲女孩用手指梳着自己的头发,男子半曲着膝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那个被吓哭的小姑娘,一直在打噎,一个,两个,三个。司机的墨镜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光,他说:多一个人就走不了。这是规定。下来一个。
那几秒钟里,杏之看见了很多。她看见车底下,她的父亲,正一遍遍地朝她挥手,同时迅速老去,佝偻着背,拄着拐杖,化为骨灰。她看见她的中学老师摸了女学生的屁股,锒铛入狱。她看见她的初恋男友,和她的閨蜜生了一窝孩子。她看见了很多,那些豆眼、葱眉、鱼肚嘴的女生去韩国整成了网红,川航的空姐和乘客一起消失在云端,九寨沟的蔡导伸着食指,对着一众女演员说,女一号?到我房间来。这些都是她看见的。在宇宙里,能看见的只有光。看不见的呢?
下了车,杏之感觉她把肚子里的套娃生出来了。她生的是大的,大的生中的,中的生小的。车上的人向下注视着她。车轰隆隆地发动。下了这辆车,就不可能准时到九寨沟了。的士也不愿去,她也付不起。九寨沟啊。蔡导好。不对。蔡导,您好。还是不够味。微微鞠躬。30度没诚意,45度太过。伸出的手不能有汗。头发昨天洗了。香水在背包里,淡淡的茶氛,不讨人嫌。还有什么呢。步子。右脚向前,距离别太大。要收腹。这次换了隐形眼镜。特地化了裸妆。嘴唇是玫瑰沙色,不张扬。手腕上一条细细的银链子,品味好歹不坏。指甲剪了,磨圆了。本想着带帆布鞋,土气。说什么都要穿着高跟鞋。山上路难走,夜里也冷。
怕什么。她对自己说。怕什么。没其他人对她说。穿过那长长的车厢,穿过她长长的梦想,窸窸窣窣有人说着话。红指甲女孩嘟囔,早点下嘛,疼死了。男子尴尬地清嗓子。小姑娘指着杏之说:她抢位置,是坏蛋!歪嘴女人一声不吭,一屁股坐下了。怕什么。杏之又对自己说。不管怎么说,这辆车少了一个。
林杏之看了看手机,赶得上下午茶呢。她走出人群,退了票。车站外一溜的的士,她择了一个。关了车门,司机问她去哪里。
成都。我去成都。
位置,成都哪个地方?司机转过头。
杏之没拿眼看他。成都。我就去成都。
司机笑了:姑娘,成都大着呢。你倒是具体说说。
成都!我说就去成都!杏之憋不住了,“哇”的一声,眼泪啪嗒嗒涌出来,一颗一颗堕下地,砸了一个个黑色的窟窿眼。窟窿眼逐渐扩大,形成了黑洞,把这个世界都吃了。
那个司机说,姑娘,你心情不好,我就把你放在这。这儿人多,热闹,你就散散心,心情好了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吧。
杏之抬起头,是著名的宽窄巷子。出口就团着一群人。每个人几乎都握着几根串串。串串油亮的,冒着辣红的光。杏之听见了肚子的一声哀怨。人活着,滚着,爬着,都不能忘了填饱肚子。杏之掏着挎包。钱包旁边,还是那个套娃。眼睛大大的,睫毛翘翘的,嘴巴弯弯的,缠着异域的纱巾,肚子上的花纹,像哆啦A梦的口袋。杏之感到一丝舒缓,要了一份糖油粑粑,滚一滚,蘸一蘸,放进嘴里,甜蜜而黏滑。
转了一圈,天色暗了。对于宽窄巷子,暗了有暗了的风韵。水蓝色的天,藏青的地,暖黄色的香槟,酒红的吉他。和熊猫玩偶自拍了几张,尝了刚熬好的辣椒酱,买了两个小手工艺术品,杏之自语,对万事怀有诚意,万事多少温柔些。对万物怀有诚意,万物会帮衬着她。
天彻底变黑了,看不见云和月。点点几粒星子,像遥远的某种东西。杏之停住了脚。像什么呢。黑痣,芝麻,蝌蚪字。不不不。这个东西很遥远。望着望着,杏之颤抖起来。几粒星子滑下来了,顺着她的脸颊往下落。
杏之点了一杯“星空”。这里是白夜酒吧。她没来过酒吧,源于她不胜酒力。对呀,连酒都喝不下,混什么混呢?杏之对自己苦笑一声。“星空”鸡尾酒端来了。下面是深蓝,往上越来越浅,中间缀着银亮的点。杏之啜了一口,没啜到点。再啜一口,酒甜甜的。直到啜到了中间的点,有点磕牙,仔细咀嚼,比酒还要甜。杏之按着酒托边的吸管,对着深蓝吸了一口。辣辣的,涩涩的,回旋在口里,把魂儿都钓出来了。杏之不喜欢这个味道。但她就是想喝,把深蓝的天喝进肚子里,把深蓝的九寨沟喝进肚子里。
朦胧中,一个背头的男人坐到了杏之身边。杏之把吸管对准他的嘴:你喝,你喝不喝?背头男人微微一笑,一口含住了,咕咚咕咚,星空越来越浅。杏之叫嚷起来:别!你别都喝了!她的手一偏,酒液泼到男人的身上,像星云。
看着星云,杏之一个激灵:蔡导好。不对。杏之站了起来,微微鞠躬:蔡导,您好。她又想了想,收腹,右脚向前,伸出了手。男人捏着她的手,随即揉了起来:坐。
杏之打了个酒嗝,坐了下来:我昨天可洗了头了,三遍,那洗发水是英国的呢。香水是伊丽莎白雅顿的,茶氛。祖马龙迪奥太冲了。还有,我戴了隐形。你看,我手上戴的银链子,是我得了第一笔编剧费,1000元,自己买给自己的。指甲剪了,剪了。高跟鞋不好爬山,但是,你是蔡导啊——杏之一个惊醒,胡乱翻起自己的包:哎呀!蔡导,对不起对不起,忘了补妆了,我的假睫毛掉了没?粉底也褪了吧?遮瑕膏,遮瑕膏在哪里,最近火气大,冒了几颗痘痘,蔡导多见谅!啊,刚刚吃了东西喝了酒了。为了搭配您的这出戏,我特地买的玫瑰沙色的口红,即使是个编务,也不能丢蔡导的脸啊……
背头男人顺着她的手往上摸,现在的她,和毕业那会差不离,眼白是云,眼瞳是星,舌头卷着潮汐,十指闪闪的贝壳,从大腿根往脚腕捋过去,像三贯钱一寸的罗绸,腰肢也长得俊俏,裹着微咸的珍珠粉。只是压力大,面皮泛油,多了几颗痘,气色不好,常年奔波的原因,整个人黑了点。可蔡导好像不介意。杏之睁睁眼,皱着眉头说:蔡导?你是蔡导吗?
男人嘿嘿一笑,抹了抹自己的大背头:我就是蔡导啊。你看,天色这么晚,我带你找个地方,谈谈明天的戏,好不好?
林杏之半是醉了,半是被男人挟持着,一步步走到了巷子口。黄色的的士。放了行李,背头男人打开车门,杏之一个巧身钻进去,锁住车门,杏眼一瞪,对着司机喊:走!离开这个地方!
杏之瘫在了车后座。的士司机默默地沿着公路开着,两个人心有灵犀,互不言语。这回,是她拒绝了蔡导。这回,她导出了比卡梅隆还要好的电影情节。杏之弯起嘴角。城市的五光十色。被减掉的空镜头,都比她那些烂掉的剧本过得好点。短裤的腿,系带的高跟,低腰的西装裤,泛黄的背心,劲脆鸡腿堡。你说,光是宇宙最孤独的东西。可它被注视过,被看见过,打开一个,还有一个。杏之皱起了鼻子,睫毛扑闪扑闪的。她曾经是个钟摆,把少年摇成暮年,把白日摇成黑夜。可是钟摆也是靠着光,才被世人所见的。我们看着光,光也看着我们,我们看着时间,时间也看着我们,这就是套娃,这就是存在。
路过一家宾馆,杏之喊了一声,司机把她放下了。给了押金,看了身份证,杏之领着门卡进了房间。缤缤纷纷的夜色。杏之冲了个澡,用了宾馆的洗发水、沐浴露。管他英国的、雅顿的呢。银链子别戴了,隐形眼镜也摘了。粉底假睫毛遮瑕膏口红,通通一边去。换上平底的一次性拖鞋,也别鞠躬了。杏之擦干了身体,换上黑色的边框眼镜。镜子里的她是她。过去的她还是她。就是死了,她也还是她。扑哧一声,她笑了出来。
躺在床上,杏之唱起了歌。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嘿!吃烤鸭,嘿!吃猪蹄,吃牛排,吃羊腿,嘿嘿嘿!她被自己逗乐了,在被单上滚来滚去。一个不留神,她差点滚下地。疯过了,魔怔过了,她从包里取出套娃,打开一个,还有一个。数一数,七个。排排站,站在床头柜上。那一年,学校流行出去交换,说巧不巧,她中了莫斯科大学。在俄国待了半年,吃了黑面包,吃了鱼子酱,食堂的土豆烧牛肉也是一绝。就是不能喝伏特加。国内的朋友,还找她做代购。莫斯科的奢侈品价位比较低,她帮人带过MK、蔻驰,还有LV方壳包,赚了一点点钱,又请朋友们去看了莫斯科舞女。舞女很美,但她最爱的是这个夜市买来的套娃,那个摊主还和她讲了套娃的传说。
很久以前,一个男孩在牧羊时把妹妹领丢了,他非常想念妹妹,就照妹妹的模样刻了一个木头娃娃,每天带在身上。过了两年,他想,妹妹应该长大一些了,更漂亮了,于是又刻了一个稍大一些的木头娃娃,就这样,过了十几年,小男孩成了小伙子,身边还一直带着自己刻的七个大小不同的木头娃娃,后来,他把大娃娃掏空,把小的装到大的里边,一个套着一个,想妹妹的時候,就一个一个地打开。
杏之喜欢过卡梅隆,也喜欢过托马斯·麦卡锡的《聚焦》,但她觉得,最好的电影,就是套娃。二个、七个、无数个不同的时空,交错在一起,可以说是七个人,也可以说是一个人,可以说是一个故事,也可以说是无数个故事,而它的意义,打开一个,还有一个,层层筛选,生生不绝,这才是电影。可惜,杏之没处说,也没有机会表达。
七个套娃,像七个小矮人,守着杏之,守着夜的缱绻,变作梦的点点星子。
杏之是被整个城市的慌乱吵醒的。她看看手机。昨晚睡得晚,居然快到中午了。起得晚有起得晚的罪过,但不至于让外面哄哄闹闹的吧?杏之趿拉着拖鞋,漱了口,洗了脸,换了衣服,走下楼梯。大厅里散乱着几张椅子。电梯口竖着停运的牌子。街上的人都跑出来了。几个服务员神情紧张地四处看着。她拦下一个女服务员,问她怎么了。女服务员的胸脯一起一伏,呼吸急促:九寨沟地震了,你知不知道?
怕什么。杏之响当当地对自己说。随即她又回到了房间,打开了电视机。蔡导一个团的人都在山上呢,要是出事了,肯定有新闻。
电视翻了一圈,没有摄制组的消息。杏之好歹放了心。画面还在播放,倾倒的客车、受伤的人群,都让她心情沉重。然而,她在一个镜头里,看见了那个歪嘴女人。除了身上脏了一点,她没事。她活下来了,还冲着镜头笑。也仿佛是地震震了一下,她的嘴不歪了,整个五官都正了,笑得可开心了。
垂下眼睑,杏之自言自语,一场大地震,居然就这样被她睡过去了。震源在九寨沟,成都肯定也有震感。杏之看看自己的挎包,稳稳的,箱子也纹丝未动。扫描扫描房间,也没什么歪掉了。目光再往回收。床头柜的套娃。一、二、三、四、五、六、七……不是七个吗?
杏之从床上一个起身,把床周围翻了个遍。少的是最小的那个,肯定震到地上了。杏之把手探进床底,依然一无所获。杏之在房间里仔细找了一圈。不可能啊。杏之又整顿了挎包、箱子,难道飞了?杏之扒着窗子往下看。底下是平整的水泥地,看不见有小的东西。那个小套娃,真的不见了。街上的熙熙攘攘传了过来,有人约去吃火锅的,有人呵斥着要打麻将的,有人还说,家里多了几顶帐篷,不收费不收费,四海都是兄弟。
杏之倒是被这些话逗乐了。她觉得,那个最小的套娃就是她。那个最大的是什么呢?是宇宙吗?还有比宇宙更宽阔的吗?如果说,彼世界套住了今世界,并且一层层循环下去,那今世界有限吗?彼世界难道就无尽了吗?时间是否有静止,空间是否有极限?这些问题,她这辈子都无法知晓。可是,杏之望着远方。白的云,青的天,灰的地。无论是今世界,还是彼世界,少了一个,到底少了一个。
责任编辑 吴佳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