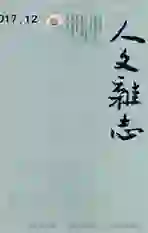近二十年汉语政治新词新语翻译研究述评
2018-03-13杨红燕姚克勤
杨红燕 姚克勤
内容提要 汉语政治新词新语的翻译已经成为我国翻译研究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指向性、目的性和策略性三个视角梳理了近20年来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回顾了关于“政治等效”的争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新词新语本体研究、走出“对等”误区和成立官方机构等建议,以期对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 汉语 政治新词新语 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12—0061—07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政府工作报告和外交文献中不断涌现出大量的反映中国“新制度、新体制、新思潮”的政治新词新语。由于其独特的中国特色语言特征和语义内涵,政治新词新语的翻译往往成为对外宣传翻译中的一个难点,也成为我国汉英翻译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近年来,学者们对政治新词新语翻译从不同角度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例如,廖志勤、文军基于跨文化视角提出了新词新语的翻译原则;杨明星基于外交新词的特点等提出了外交新词的翻译策略;张健围绕外宣翻译的特点探讨了外宣翻譯的“变通策略”;施燕华和叶小宝等通过对本体意义的解读探讨了具体新词(如“不折腾”“任性”等)的翻译方法。本文拟从指向性、目的性和策略性三个研究视角对近20年来该领域的研究进行梳理,以期对政治新词新语的翻译研究提供借鉴。
一、政治新词新语
过去的20多年,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我国在世界舞台上影响力的与日俱增,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的话语权不断增强,汉语政治新词薪语的翻译已经成为我国翻译研究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总的来说,在现有的相关涉及政治新词(新语)研究,多论及具体的词或用语,即从一个切面纵向探讨,⑥鲜对汉语新词新语做体系性、本体论式的探讨。从目前的研究文献来看,与“政治新词新语”翻译研究有关的主题主要有“新词新语”“外交新词”“政治概念”“时政新词”“政治术语”。另有学者则从更广阔的视域中将“政治新词新语”看作“中国特色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也未能提出政治新词新语与科技等领域新词新语在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上的原则性差异。本文所论及的政治新词新语,主要指的是政治文件、外交翻译等中出现的新创词语(如“一带一路”“四个全面”等)和已有词语的新用法(如“不折腾”“韬光养晦”等)。
二、政治新词新语的翻译研究
对于“政治新词新语”翻译的研究,诸多学者在感叹新词新语翻译之难的同时,从现实的翻译研究出发,进行了指向性、目的性和策略性三个方面的研究。
1.指向性研究
对汉语政治新词新语的指向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现有政治新词新语翻译的疏漏上。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1)译语违背源语的政治内涵。政治新词是体现时代政治特色的官方术语,表达“党和政府立场,涉及国家大政方针”,但一些译语过度依赖国外媒体或政府的翻译,没有能够从历史文化、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等方面审慎地解读源语的政治内涵,难以准确传递我国政府的政治立场和政策态度,甚至导致国外媒体和政府的误读或歪曲。例如,杨明星认为,一些译文在翻译“新型大国关系”时盲目借用美国译法,将其中的“大国”译为“major power,great power”,甚至“The Group of Two(G2)”,“Chimerica”等。译语的生搬硬套顺应了美国政府的政治意图和外交宗旨,使其他国家认为中国已成为强国,甚至是强权国家。这些译语完全背离了我国领导人提出的构建中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外交思想。因此,他认为把“大国”译为中性词“major country”,既能“表达中方新型‘大国外交理念和独特的价值观”,又“可以避免美方不必要的战略忧虑和外交误会”。
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译文引起的争论。该政策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外交战略思想,“主要内涵是中国要保持谦虚谨慎,不当头、不扛旗、不扩张、不称霸,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是一致的”。但国内外的一些译文却曲解、甚至歪曲了“韬光养晦”的政治内涵,简单地以中国古代成语的含义“收敛锋芒,隐藏自己的声名和才华,养精蓄锐,等待时机”解读这一重要的外交战略思想。例如,“美国政府在2003-2009年有六个年度的《中国军力报告》中,都把“韬光养晦”翻译为‘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完全违背了源语的意义,反而体现了“中国威胁论”的隐含意义。杨明星认为“keep a low profile”,“keep a low international profile”和“maintaining a low profile”等具有正面意义,是最贴切的译法。但熊光楷认为这一译法“离完全准确表达其内涵也仍有一定距离,国外人士还难以理解到原词中深邃的含义”,借用英语成语将其译为“hiding its light”,虽然不够确贴,但也给我们的翻译带来有益的启示。总之,为了向国人和世界讲清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一战略思想,译者要以中国话语解读这一思想在特定语境下所体现的政治内涵和实质。
(2)译语缺乏统一规范。不同领域的译者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解读、翻译政治新词,导致不同版本的译文交错使用,译语之间的内涵意义相去甚远。“不折腾”一词在国内外先后出现了30多种译文,导致外国读者无所适从,美国媒体The New Yorker甚至将其译为“avoid making a fuss”。他认为译文“No Z-turn”具有意境美、形式美和音韵美的特点,“Dont rock the boat”体现了该词的基本意义、政治内涵和情感意义。然而,王国文却认为新华社的译语“Dont sway back and forth”符合“不折腾”产生的语境信息和语言背景,是最佳的译语。至今,关于“不折腾”的翻译还在争论之中。endprint
译语的统一规范有利于“构建中国的话语和价值体系,在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中赢得话语权,促进世界文化的融合與建设”。2015年9月23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外交部、商务部等部门对“一带一路”英文译语进行了规范,统一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英文全称译为“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 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一带一路”作为简称译为“The Belt and Road”,英文缩写用“B&R”,并且明确说明,“一带一路”是一种倡议,使用“initiative”,不使用“strategy”“project”“plan”或“agenda”等词汇。规范的译文既能够体现新语境下“丝绸之路”的内涵,又保留了原有译语中的既有名词“belt”和“road”,易于为国外读者接受。
(3)译语缺乏术语意识。“中央文献政治术语是政治领域使用的特定语言符号”,政治术语同样是“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语言符号”。然而,中国的政治新词新语是西方政治知识谱系中很少用到的概念,在翻译实践中,必须创造性地进行不同谱系概念之间的转换,也就是术语的再创建。由于政治新词新语鲜明的原创性,译者的术语意识尤为重要。“在英语中再创建中国政治术语时要遵循术语学中术语定名的相关原则,要符合术语规范化和统一化要求”。在翻译实践中,一些译语不够专业,术语国际化意识不够。例如,“科学发展观”的译文最常见的有:“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a Scientific Approach to De-velopment,a Scientific Strategy of Development,a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十七大报告的英译本中把“科学发展观”作为专有名词译为“the Scientifie Outlook on Development”“准确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层含义”,符合术语定名的理据性和确切性原则。当然,一些新词新语是否可以界定为术语,还需要结合术语的概念进行审慎判别。例如,王平兴认为把“韬光养晦”和“不折腾”认定为“外交新词”不够严谨,因为这两个词并不具有“专业性、唯一性”,也不是“专门用语或概念”,也不具有“单义性和排他性”。
由于中国特有的新词在英语语言中本身就属于语义空缺,所以对应词的选择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指向性研究而言,笔者认为,在评价一个译语时,不应强求一个简短的译语足以全面反映一项政策所包含的丰富内容,首先考虑的应该是语义的准确,因为语义出现偏差,政治性准确就无从谈起。例如,英文词power本身强调的是国家的影响力,即country with influence,而country更多地指的是国家的物质存在,即area 0f land with its own government。所以,ma-jor country的说法并不常见。“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大国”,更多地指的是影响力,翻译为major power应该更为准确。再如,“一带一路”和“一国两制”表面上都是由两个数字构成的结构,但其中数字的含义各异。因此,不能依据“一国两制”的“one country,two systems”译法翻译其中的数字。“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并不局限于数字概念上的“一”条带和“一”条路,而是多维度、多元化的合作发展理念和国际合作倡议。因此,虽然译语“One Belt and One Road”具有词语的结构美感,但“one”更多地是突出其实指的“一”的数量意义。译语“The Belt and Road”使用定冠词“the”代替“one”,传递了“belt”和“road”抽象的特指意义,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2.目的性研究
对汉语政治新词新语翻译的目的性研究,主要集中在译语是否能够准确传递新词新语的政治内涵和源语的文化内涵,有助于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并构建中国对外术语体系。
(1)新词新语的政治内涵。多数研究者认为,在翻译政治文献时,译者要准确掌握国家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仔细衡量用词的政治含义与影响,在政治上忠于原文;杨明星等提出对外翻译首先要考虑“政治等效”原则,强调政治新词翻译中政治内涵对等的重要性,一方面要反映源语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语境,另一方面译入语和源语的政治信息含义要等值;惨志勤等认为汉语新词的翻译要遵循“政治考量原则”,译者要把自己的政治觉悟意识始终贯穿于翻译行为之中。王弄笙认为,在政治翻译中,对涉及大政方针、领土、主权问题等有政治含义的词句,要从政治方面深入解读,译语必须准确无误地反映源语的准确定义。“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一表达在不同语境下经常出现在各种媒体。该表达的译文通常是“hurt(或lacerate)the feelings of the Chinese people”。程镇球认为,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感情”的意义,将其翻译为“feelings”或者“na-tional feelings”用词太轻,在一些语境中将其译为“wound the national dign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更合原意。再如,在翻译中遇到大陆、台湾时,不应译为“mainland China,Taiwanese China,Taiwan(China)”,而应译为“the mainland of China;Chinas mainland;Taiwan,China;Taipei,China;Chinese Tai-wan”,表明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把“中国大陆”译为“mainland China”,其中的隐含意义是“Taiwan China”,与“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根本原则背道而驰”。endprint
(2)国家形象的塑造。政治新词新语翻译,受目标读者及文本类型的制约,具有严肃性和正式性,关乎国家形象。許多研究者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政治新词新语这个概念,却对其翻译的重要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余秋平认为,外宣翻译应该“树立对中国的正确形象,宣传中国,使国际受众尊重并信任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是维护和塑造中国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必需途径”。杨明星提出,作为一种特殊领域的话语形式,外交语言的政策性强,往往关涉国家利益和对外关系,在翻译工作中保护国家利益,实现国家的政治目标。对于“和平崛起”一词中“崛起”的英译,使用频率最高的译语是“rise”一词。然而,“在世界近代史上,‘rise这个英文单词,对于某些国家的发展进程而言是有特殊含义的,意味着武力征服,这些国家的霸权、扩张都是同它们的rise相连的”。“和平崛起”的本质内涵是“和谐发展”和“和平发展”,而“软实力”是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并是“和平崛起”的前提条件。把“和平崛起”译为“peaceful development”能够体现中国的崛起是依赖文化、意识形态、制度等方面的软实力,而不是“与战争、武力及海外扩张相伴随,成为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挑战者”。
(3)源语的文化内涵。一些研究者从文化交流角度,审视政治新词新语的翻译目的。杨明星认为,中美两国在语言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对同一概念的认知、解读和翻译并不完全一致,在翻译时要敢于摈弃西方外交逻辑和语言传统习惯,创新翻译方法。袁晓宁提出,在外宣翻译中,要充分考虑英汉两个民族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对译语做出调整,使目标语读者能够有效掌握译语内容和要旨。李瑞认为在翻译汉语新词时,译者要有意识地认知东西方文化背景之间共享的认知基础,在充分认知语言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求同”于西方受众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冯志杰更是强调,重大政治术语的翻译要坚持源语取向原则,译语不但要准确传达源语的内涵意义,还要彰显源语中所具有的文化和风格特征。例如,如果在对外宣传中把十八大首次提出的“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直接译为“The whole Party should have every confidence in our path,in our theories and in our system”,由于两种文化在内容和性质上的差异,目标语读者可能无法获取我们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充满信心。因此在译文中明确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有益于忠实地传递源语的文化内涵。潘苏悦的译语“have every confidence in our socialist path,theories and system(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也许更能够为不同文化系统的英文读者所接受。
(4)术语翻译体系。术语在本质上就是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语言统一体,也就是所谓的语言符号。中国政治新词新语是用来表达中国政治领域专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将中文的政治术语译为英文是不同概念体系间的翻译形式或概念间的术语迁移,因此,在二次命名或再创建过程中,政治新词的翻译应该遵循术语的相关定名原则,译语应该符合专业性、单义性、理据性、确切性、系统性和国际性等原则。杨明星指出,外交概念和术语的翻译要运用专业、经济的表达和措辞,避免以俗语或者大白话翻译政治概念或者术语。“获得感”源于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2月27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的讲话,该词一出现就迅速流行起来,并在意义和形式显现出固定化的趋势。“获得感”一词本身就结构简短,符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其译语“sense of gain”既能体现词汇的本义获取利益后所产生的满足感,又能表达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的幸福感。⑩另一方面,译语与英语中的“sense of humor,sense of superiority”等表达方式相同,符合目的与读者的表达习惯。在翻译“认同感”“幸福感”“存在感”和“成就感”等与“获得感”构词形式相同的词语时,可以采用“sense of XX”词语模,形成系统性、国际性的系列概念。
新词新语的目的性考量是在语义准确的前提下,如何做到译语政治性和文化内涵的最大限度的传递,并在此基础上尽量顾及术语的体系性,因此这一点对译者的要求更高。例如,中国过去几十年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具有中国国情色彩,“计划”指的是“限制超生”。而有些国家人口数量下降,出现“无子化现象,所以其“family planning”则是采取措施“鼓励生育”。因此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翻译为“one-child policy”则有效地传递了该政策的文化内涵。
3.策略性研究
近年来,针对政治新词新语翻译,诸多研究者结合语言学新理论,从语境的动态性、译语与源语信息等值、创新翻译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翻译策略研究。
(1)语境的动态性。程镇球指出,“政治文献的翻译有较强的时间性”。随着政治语境的变化,译文也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否则就会导致政治性的错误。杨明星提出,翻译的等效必须是动态的,译者必须与时俱进,紧贴源语的时代内涵和译入语的最新发展和相关语境。陈风华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要考虑语境因素,充分理解说话人所用词汇的外延含义,领会话语的真实含义,原汁原味传递发言人的真实意图,做到“功能等效”翻译。刘润泽、魏向清借鉴概念史研究方法探讨政治术语的翻译时指出,基于历史文本语境对政治概念进行深度解读,对于当代中国政治话语的建构和跨语传播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中国梦”在国内外被广泛使用的主要译语包括“(the)Chinese Dream,(the)China Dream和the Chinas Dream”。他们认为,不能简单地从语言形式上借用“American Dream”和“European Dream”把“中国梦”译为“Chinese Dream”,因为中国本土情境的历史人文特性在“中国梦”的跨语传播与接受中基本是被遮蔽或缺失的,而“China Dream”更能基于历史文本语境对政治概念进行深度解读。然而,杨明星却认为,“the Chinese Dream”既符合政治等效原理,也符合西方读者的语言习惯,而为了区别“中国梦”和“美国梦”,将“中国梦”译为“the China Dream”是不合理的,因为国名China和Dream一般不搭配。贺文照等通过英语媒体历时语料分析发现,“Chinese Dream承载的梦想与时俱进,和中国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China Dream”尤其指“西方人的投资梦和发财梦”,也用来指“中国国家军事强盛的梦想,高耗能、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等”。他们认为,“‘中国梦在英语媒体中出现已有20多年,仅仅规定‘中国梦译为‘Chinese Dream或者是‘China Dream恐怕很难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在翻译时,“有必要采用‘译+释的方式,通过‘释将中国梦的内涵有效传播出去,减少可能存在的误解”。endprint
(2)译语与源语信息等值。“政治新词的翻译要用接受方所能理解的译入语来表达,使双方得到的政治含义信息等值,使译文能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冯志杰提出,重大政治术语的翻译要“坚持信息等价性原则,即译文的信息要忠实于原文的信息,既避免原文信息发生缺失,也不能发生增溢,更不能使意思发生扭曲,译文信息与原文信息应当保持等价”。李学军在探讨习总书记提出的“三严三实”重要论述的翻译时提出,根据“严”和“实”的含义,“严”可以译为“strict”,而“实”的含义较多,“踏实”译为“steady”既符合“三实”中“实”的内涵,即谋事、创业、做人要踏实、坚定、不屈不挠,且与布什、希拉里等人使用该词的含义对等。他认为把“三严三实”译为“Three Stricts and Three Steadies”不但比较忠实于原文,且体现了翻译的美感。
(3)创新翻译方法。汉语政治新词新语的翻译是话语的再构建,是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再创造。创新翻译对中国特色语言学、翻译学乃至外交学、国际传播学,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学术自信和话语权具有重要的意义。2012年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后,习总书记在与中外记者见面时讲到“打铁还须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张顺生认为,根据讲话的上下文,“打铁”解释为“打击腐败”更为合理,将其创新性的译为“To strike iron,one must stay strong”或“To strike iron,you must(first of all)strengthen yourseff”,译文既有“要反腐败自己就必须行得端、做得正”和“反腐要坚定有力”的喻义,效果也和原俗语更契合。对于“四个全面”及其具体内容的翻译,黄长奇从语言和传播的角度分析了国内外主流媒体和翻译专家的主要译文,建议将其译为“the 4Cs Strategy refersto:1.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2.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re-forms;3.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le of law;4.comprehensive enforcement of Party disci-pline”。他所提出的譯法,避免了把关键词“四个全面”译为“Four Comprehensives”在形容词后加复数的问题,也解决了把主要内容“全面依法治国”译为“im-plement/advance the rule of law”导致的源语含义的曲解问题,把“全面从严治党”译为“comprehensively be strict in governing the CPC”或“Comprehensively apply strictness in governing the CPC”的翻译腔问题。
策略性研究尤其关注译语在语境中的灵活性处理,更强调信息的对等和语言的地道,对译者的创造性有进一步的要求。例如,前文提到的“计划生育政策”,翻译为one-child policy较为准确,但在行文过程当中,依据英文语篇习惯则可处理为“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或者“the policy”。同样,“四个全面”无论翻译为“the 4Cs Strategy”还是“Four Com-prehensives”,但在首次出现时还应出现其具体内涵,不然西方读者会难以理解。
三、启示
对近20年来汉语政治新词新语翻译研究现状的梳理,对今后政治新词新语的翻译研究不无启示,笔者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第一,新词新语翻译要走出“对等”的禁锢。指向性、目的性和策略性研究对新词新语翻译的考量各有侧重,但是在具体翻译实践中往往三个方面难以兼顾,译者需根据具体情况有所取舍。杨明星和王平兴关于“政治等效”的争论,其根本原因在于难于兼顾三者之间的关系,无法实现“对等”。③因此,译者要走出“对等”的误区,探究汉语新词新语的语言、文化、社会、政治差异,在译入语中尽可能再现源语信息,传达原文内涵。在有些情况下,甚至需要采用音译的方法。例如,中国的民主党派是许多党派的统称,译为“democratic parties”隐含意义可能是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民主的党,所以直接音译为“Minzhu Dangpai”或“Minzhu Parties”能够传播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
第二,新词新语翻译不应盲目强调中国特色。新词新语大多具有中国特色,但在英文中已有对应词汇或句法结构的情况下,不宜为特色而特色。例如,“中国梦”与“美国梦”在汉语构词结构上完全相同,在译文上人为设置China dream和American dream的区别,只能引起读者的误解,并不能区分其内涵上的差异。
第三,要加强政治新词新语的本体性研究。汉语政治新词新语的特点在于“新”,往往要求译者对其语义内涵、政治内涵和文化内涵进行准确把握,才有可能在指向性、目的性和策略性上全面考量,做出取舍。在施燕华《“不折腾”英译大家谈》一文中,专家学者们的翻译都是基于对“不折腾”的政治语境含义和语用含义的解读,由此可见在翻译中对新词新语本体研究的重要性。
责任编辑:魏策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