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司法服务中的ISDS裁决承认与执行问题研究
2018-03-13全小莲刘步蟾
文/全小莲 刘步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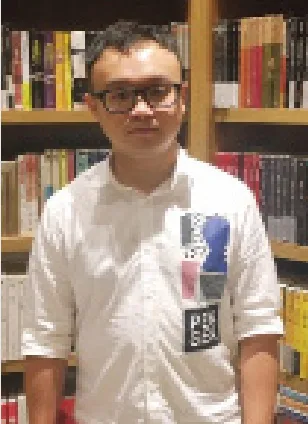
2016年12月1日起深圳国际仲裁院实施新规则,首次规定我国内地仲裁机构可以受理投资者—国家争端(ISDS)案件。此举是仲裁机构在最高法支持下为“一带一路”提供有力法律保障的重要创举,但人民法院在承认与执行ISDS裁决时仍然面临重重困难。本文以“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和SCIA新规发布为背景,重点研究了ISDS裁决在我国承认与执行上的困境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全小莲 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
刘步蟾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ISDS裁决承认与执行的时代价值
(一)为“一带一路”提供有力司法服务
201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指出人民法院应当加强承认与执行涉“一带一路”仲裁的司法审查,保障仲裁机制能够为加强“一带一路”司法保障、化解投资纠纷发挥积极作用。2016年10月,深圳国际仲裁院(以下简称深国仲或SCIA)发布新规,规定可以在案件当事方同意的前提下受理投资者与政府之间的投资争议(ISDS)案件。这意味着深国仲成为内地首个可以受理国际投资争议案件的仲裁机构。
201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涉“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第二批)中,我国认定与新加坡之间的互惠关系,首次承认和执行了新加坡法院商事判决,这体现了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沿线国投资提供有力司法服务的决心,也打开了人民法院执行涉“一带一路”生效裁判文书的新局面。
在SCIA向投资者与政府之间的投资争议案件敞开大门的背景下,要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就必须加强对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以下简称“ISDS”)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研究,对于可能出现的需要人民法院执行的情形进行预判,加强人民法院对ISDS裁决的审查。
(二)抢占争端解决制度建设先机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国旋即退出TPP,贸易保护主义披上“公共利益”外衣卷土重来,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反全球化的浪潮。“一带一路”倡议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要保障“一带一路”倡议顺利落地生根,相应的投资争端解决ISDS机制必不可少。
在ISDS中,投资争端解决国际中心(ICSID)是运用最为频繁的机制,但它也因为仲裁费用高、透明度差、案件之间裁决结果不一致等问题被人诟病。深国仲在这个背景下出台新规则,受理国际投资仲裁案件,志在为“一带一路”搭建更为便利的ISDS平台,抢占争端解决制度建设的先机。人民法院对深国仲的ISDS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是这种制度能够赢得良好国际声誉并吸引当事人选择使用本规则的根本保障。
(三)打破执行豁免主义壁垒
基于国家主权豁免立场和国家安全等问题上的考虑,中国仅在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接受国际投资仲裁,不接受外国法院审理国际投资争端案件。在加入《华盛顿公约》后,我国逐步探索通过仲裁机制解决投资者—东道国之间的争议。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背景下,ISDS裁决在我国得到承认与执行则更具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从立场上而言,中国仍然坚持绝对执行豁免主义,这使得无论是即将出现的SCIA裁决还是更为主流的ICSID裁决在我国的承认和执行中都必然面对主权豁免问题。
要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打消沿线国到中国进行投资的顾虑,必然需要打破法院执行的主权豁免壁垒。另外,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有巨额的海外投资,对等原则的要求使得中国要求对方国家保护中国海外投资的同时,也为对方国家在中国的投资提供法律保护和司法救济。因此,一味地坚持执行豁免立场将会使得中国在海外的投资遭遇对方的执行豁免,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济。
ISDS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的现实困境
(一)受阻于主权豁免原则
近年来ISDS裁决因为被诉方政府主张主权豁免而无法得到承认和执行的案件屡见不鲜。美国AIG公司投资了哈萨克斯坦的CJSC公司。1999年,哈萨克斯坦政府取消了CJSC公司的某建设投资项目,并将该项目所涉土地收归政府且没有进行任何补偿。随后AIG公司向ICSID提起仲裁,仲裁庭作出了有利于AIG公司的裁决。然而在执行阶段,哈萨克斯坦政府没有实际履行裁决,随后AIG公司向英国法院提起执行哈萨克斯坦在伦敦的国家银行财产,并获得同意。最后,哈萨克斯坦政府援引英国1978年国家豁免法中关于执行豁免的条款,英国法院撤销了执行决定,最终该ICSID裁决没有得到实际执行。
此案是近年来当事国援引主权豁免原则,导致拿到胜诉裁决的投资者无法执行ISDS裁决的典型案例,本案涉案的国家均属于《华盛顿公约》的缔约国,都承认该裁决具有终局效力,但是第三国英国在执行该案的过程中,即便高等法院作出了执行的命令,但只要哈萨克斯坦提出了主权豁免,执行命令就变成了一纸空文。
就中国而言,绝对执行豁免主义是我国的一贯立场,实践中司法体系从未有过承认与执行ISDS裁决的案例。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生效裁决的顺利承认与执行是投资活动的重要保障,如果国家豁免原则出现滥用现象,将极有可能带来严重的法律、经济风险,损害沿线国之间的信任基础,进而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二)国内法上无法可依
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我国将不可避免地面对ISDS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人民法院在处理争端一方的申请时,必须要找到相应的国际条约或是国内法依据,然而即便是执行保障机制相对完善的《华盛顿公约》依然没有在我国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落地。一旦出现执行ICSID裁决的申请,人民法院可能会无所适从。《华盛顿公约》中还规定各缔约国应当指定专门机构,对ISDS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事务进行统一管理,但是截至目前我国尚没有指定专门机构。
非ICSID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同样不容乐观,我国在缔结《纽约公约》时明确提出了保留,声明承认与执行的范围不包括ISDS裁决。在后来缔结的部分BIT中通过具体承诺接受了ISDS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但是目前我国并未与所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缔结BIT,也就意味着涉及部分国家的ISDS裁决无法得到承认和执行。
截至目前内地已经拥有超过250家仲裁机构,SCIA作为商事仲裁国际化的先行者,在数十年的仲裁实践中栉风沐雨后已经积累了足够丰富的经验和专业能力来处理国际投资仲裁。SCIA出台新规则意在构建“一带一路”投资者—国家仲裁的深圳主场,是一项意义深远的规则创新。然而,我国仲裁法依然没有突破“平等主体间”的受案范围,应然与实然间的鸿沟将成为SCIA投资者—国家裁决承认与执行不可回避的问题。
ISDS裁决承认与执行困境之根源
(一)绝对主权豁免立场无法满足时代需求
1.限制豁免原则的发展
二战之后,限制豁免主义开始受到青睐。《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虽然尚未生效,但其文本体现了限制豁免主义的立场。中国已经签署了该公约,但未批准。随着司法实践中主权豁免的案例增多,部分国家转而通过国内立法来规范主权豁免,例如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英国国家豁免法等。
在《华盛顿公约》中,将该问题交由各缔约国国内法来决定。这在充分尊重各国选择的同时也带来了执行豁免问题的风险。就目前的国际国内立法来看,仅部分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通过国内立法确立限制执行豁免,区分出国家的商业行为。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这些确立了限制执行豁免的国家中,对“商业行为”的界定也不尽相同,这也是导致当前ISDS裁决承认和执行难度较大的重要原因。
2.我国并未放弃绝对豁免立场
作为坚持绝对主权豁免的国家,我国在立法、司法和外交活动中都有所体现。立法方面,我国并没有完整的整体豁免立法,外交豁免等事项均散见于其他法律中。司法方面,我国法院几乎不受理以外国国家作为被告的案件。2011年香港法院受理的美国公司诉刚果(金)案涉及执行外国国家的仲裁,但该案最终也驳回了起诉。在外交活动中,我国在参与《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草案谈判时,发表意见认为,在豁免问题上虽然接受在具体案件中予以灵活性考虑制定一些例外的规定,但是这些例外必须是最低限的,否则不符合公约的目的。
在司法实践中,中国政府也可能在持有限豁免立场的外国成为被申请人,中国的国家财产仍然可能被强制执行。此外,由于绝对豁免立场,我国投资者在海外投资受到外国国家的侵害既无法在我国申请仲裁,也无法在我国执行外国国家的财产。因此,绝对豁免立场无法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维护国家利益。
3.豁免法缺失与立场混乱并存
主权豁免问题之所以成为ISDS裁决在我国承认和执行的阻碍,更主要是因为我国国内法上缺乏全局性豁免法。虽然我国签署了《华盛顿公约》等国际条约,但是并没有相应的国内法予以支持,使得国际条约在实践中成为没有国内法依据而难以落地的空中楼阁,也使得法院在认定主权豁免问题时感到困惑。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司法现状与立法趋势不同步。虽然我国坚持绝对主权豁免立场,但是近年来已经开始出现接受限制主权豁免立场的趋势。早在2005年,我国就参与了《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谈判,近年来出台司法解释也强调仲裁在化解投资争端中的重要作用,紧接着SCIA出台新规则受理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争端都体现了我国逐步接受限制主权豁免主义的趋势。但是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在面对执行豁免问题的时候却进退两难。
(二)立法缺失导致法院执行失据
1.“仲裁范围”的障碍
《华盛顿公约》第53条规定,裁决具有终局效力,各国在处理执行申请时仅对裁决进行形式审查。该条延续了一裁终局的惯例,但在承认与执行裁决的时候,由于国家具备国际法主体资格,而投资者并不构成国际法意义上的法律人格,因而只能通过国内法院来强制执行裁决。由此可见,ICSID裁决的承认和执行的依据既包括国际法又包括国内法。ICSID并非唯一的机构,例如UNCITRAL特设法庭、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以及出台新规后的SCIA均可以受理投资者—国家争端案件。
《若干意见》第八条要求法院正确适用和理解《纽约公约》,积极承认与执行相关裁决。我国作为《纽约公约》的缔约国之一,如果外国仲裁具备在我国承认与执行的条件,理应按照要求承认与执行裁决。但是ISDS裁决在我国尚不能依据《纽约公约》承认与执行,原因在于我国加入《纽约公约》时就提出保留,明确排除了投资者—国家争端案件。SCIA探路先行打开了受理ISDS案件的大门,但是SCIA受理ISDS案件是根据UNCITRAL规则,将裁决认定为裁决地仲裁,因此SCIA裁决应当被视为国内仲裁机构作出的涉外仲裁来承认与执行。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仲裁法第2条明确将仲裁机构的受案范围限制在平等主体之间,这显然与SCIA的新规则存在冲突,仲裁的合法性是承认与执行裁决时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在仲裁法尚未修改的背景下,承认与执行SCIA的ISDS裁决将存在投资仲裁主体合法性的困扰。
2.缺乏执行国际条约的国内法规定和互惠关系认定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83条,争端方需向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执行申请,法院根据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或是根据互惠原则进行处理。在国际条约的适用问题上,民商事条约可以直接并优先适用,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华盛顿公约》在我国具备适用的条件,是ICSID裁决执行的依据,而非ICSID裁决可以依据互惠原则进行承认和执行。但是实践中对国际公约的适用往往需要对公约进行司法解释,否则下级法院不会在个案中直接适用国际公约,这使得人民法院在承认与执行ICSID裁决时深陷进退两难的境地,无论是同意还是拒绝申请,都必须上报最高法院。而运用互惠原则承认和执行非ICSID裁决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尤其是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这可能损害沿线国之间的信任基础,影响企业的投资活动。
对国际条约的配套不足还体现在我国尚未按照《华盛顿公约》要求设立专职处理承认与执行事务的机构。为了促进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大部分国家制定了专门的机构来处理该问题,如特定法院、检察长、内阁大臣等。但是截至目前,我国并没有承认和执行ISDS裁决的先例,遑论指定承认与执行事务的专门机构。
推动ISDS裁决承认与执行的构想
(一)完善执行豁免与仲裁制度设计
人民法院想要顺利承认与执行ISDS裁决,执行被申诉方政府的商业财产,必须在执行豁免制度设计上符合国际投资规律和豁免立场的国际趋势。转向限制执行豁免立场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势所趋,符合投资者和政府走向国际市场的需求。
考虑到我国缺乏专门的豁免立法,笔者建议可以在限制执行豁免主义立场的前提下,进行专门的豁免立法,并通过直接定义法和列举定义法对商业行为进行定义,在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将认定的决定权交给人民法院。对商业行为的认定直接关系到ISDS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美国和加拿大是通过直接列举商业行为来定义的。我国并不是判例法国家,加上有关ISDS裁决的承认和执行在我国的案例本来就屈指可数,在经济活动日益多样化的背景下仅仅通过直接定义法可能无法涵盖所有的商业行为,且难以紧跟时代的潮流。因此,建议我国可以采用以色列的豁免法规定模式,既对商业行为进行定义,又通过列举的形式进行兜底,并将具体的认定决定权交给人民法院,以保障对商业行为的规定能够符合“一带一路”倡议日新月异的投资模式。
另外,仲裁主体的合法性关系到仲裁裁决本身的合规性,是裁决能够被承认与执行的前提,因此我国仲裁法对裁决范围仅限于平等主体间的规定应当进行修改,将我国国内仲裁机构的受案范围拓展到投资者—国家争端案件。
(二)出台司法解释与指定专门机构双重保障
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公约的适用往往是建立在最高人民法院对公约的司法解释上的。最高人民法院应尽快出台《华盛顿公约》的有关司法解释,来面对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蓬勃发展极有可能出现的ICSID裁决承认与执行问题。为了保障《纽约公约》的顺利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就曾两次出台司法解释。这个思路是值得借鉴的。
《华盛顿公约》关于指定专门机构处理承认与执行事务的规定有利于强化ICSID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在该问题上需要照单全收。我国应该指定专门机构,但是该机构不应当仅仅限于在《华盛顿公约》的框架下专门处理ICSID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事务,应当综合处理整个ISDS裁决。由于我国并没有承认与执行国内仲裁机构作出的ISDS裁决的经验,该机构应当将重点放在SCIA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事务上,以推动更多“一带一路”中的投资争端被提交到SCIA处理。结合国外的司法实践,笔者建议可以在我国涉外事务较多的地区指定几个处理涉外案件能力较强的法院专门办理涉“一带一路”ISDS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管理。
(三)积极认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的互惠关系
201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第二批)》。人民法院通过认定我国与新加坡的互惠关系,首次承认与执行了新加坡法院商事判决。虽然该案承认与执行的是新加坡法院的判决,但是也为推动“一带一路”背景下ISDS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正如上文所述,非ICSID的ISDS裁决在我国只能通过互惠关系进行承认和执行,但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中大部分国家与我国并没有签署相关的协助条约,因此,如果人民法院在审查裁决时能够积极合理认定“一带一路”沿线国与我国的互惠关系,将会极大地促进对涉“一带一路”的ISDS裁决尤其是非ICSID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作为当代的“凿空之旅”,“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需要人民法院提供强力的司法保障,而ISDS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关系到沿线国投资者参与投资的积极性,甚至可能影响中国在海外投资的安全。我国突破性地在SCIA打开受理ISDS案件的大门,展现了我国着力化解“一带一路”投资争端、为沿线国与投资者提供坚实法律后盾的决心。期待人民法院能够为当代的“凿空之旅”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