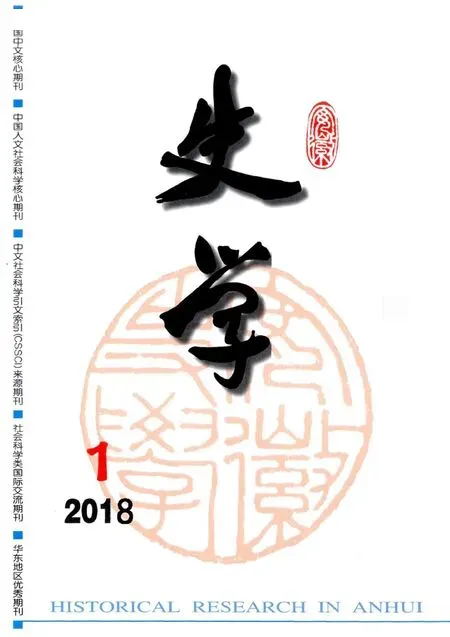胡适与梁启超学术关系之考察
2018-03-13李勇
李 勇
(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胡适学术思想深受梁启超影响,学界有过讨论。*张朋园的《胡适与梁启超——两代知识分子的亲和与排拒》(《“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6年第15期下)、董德福的《梁启超与胡适:两代知识分子学思历程的比较研究》第三章(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以《清代学术概论》、《墨子校释》、《中国哲学史大纲》、两个“国学书目”和白话诗为案例,论述胡、梁学术上的分与合。刘巍的《钱穆与胡适梁启超关于清代学术史整理的思想交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1999年卷)注意到梁启超和胡适都推崇和宣扬戴震,肯定其科学精神、重“情欲”思想和反“理学”形象。董德福的《梁启超与胡适关于〈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论辩刍议》(《复旦学报》1998年第3期)从文化取向和新旧之争角度,看待梁启超评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梁启超没有认识到这部著作在中国近代学术和思想史上的革命意义。杨建民的《梁启超的风度与胡适的雅量》(《报刊荟萃》2006年第5期)、苏育民的《胡适与梁启超》(《铜仁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认为梁启超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率真令人感佩,为学界树立榜样,胡适回应评论有不俗雅量,有利于学术发展。胡、梁围绕《清代学术概论》、《墨经校释》、《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国学书目”、白话诗等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受到普遍关注;而两人关于《管子》、《老子》和孔子的不同意见则被忽视了。他们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上互相启发,有待探讨;两人学术关系线索需进一步梳理;梁启超去世后,胡适关注其年谱编纂和印行,并为之作序,这些值得思考和揭示。已有研究成果所涉问题,诸如胡适是否因对梁启超执弟子礼而未公开反唇相讥,胡适对梁启超盖棺定论是否仅有消极而无积极评价,都需商榷。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撇开“国学书目”、白话诗问题,聚焦学术史,就以上诸项展开讨论,不当之处恳请学界宽宥。
一、胡适学术思想深受梁启超的影响
胡适毫不讳言其学术思想受益于梁启超:“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第1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9、61—62页。
关于第一点,这里无须讨论,暂且抛开;至于第二点,要稍加留意,胡适说得明了:
《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所以我最爱读这篇文章。不幸梁先生做了几章之后,忽然停止了,使我大失所望。甲辰以后,我在《新民丛报》上见他续作此篇,我高兴极了。但我读了这篇长文,终感觉不少的失望。第一,他论“全盛时代”,说了几万字的绪论,却把“本论”(论诸家学说之根据及其长短得失)全搁下了,只注了一个“缺”字。他后来只补作了《子墨子学说》一篇,其余各家始终没有补。第二,“佛学时代”一章的本论一节也全没有做。第三,他把第六个时代(宋、元、明)整个搁起不提。这一部学术思想史中间缺了三个最紧要的部分,使我眼巴巴的望了几年。我在那失望的时期,自己忽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第1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9、61—62页。
照胡适说法,《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使他对于中国学术有一个新认识,有了学术史概念;但梁著缺春秋战国时期学术、南北朝和唐代佛学、宋元明时期学术,故胡适感到失望。胡适提到甲辰(1914年)后梁启超续作,当指《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确如他所说仅有绪论而无本论,使胡适再次失望,并萌生补阙念头。
胡适所言梁著缺失确实不虚,不过并非如他所说梁启超只补了《子墨子学说》,事实上还补有《管子传》、《老子哲学》、《孔子》、《墨子学案》、《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佛典之翻译》等,只是所补不够,宋元明理学部分仍阙如。
胡适对梁启超学术史确有补阙和深化。他总论春秋战国诸子者有《先秦诸子进化论》、《先秦名学史》。分论中关于道家者有《庄子哲学浅释》;涉儒家者有《儒教的成立》;关乎墨子者有《论墨学》、《墨家哲学》。关于南北朝唐代佛教史,总论禅宗者就有《禅学古史考》、《论禅宗史的纲领》、《中国禅宗的来历》、《中国禅学的起来》、《中国禅学的发展》、《禅宗在中国:它的历史和方法》、《禅宗的方法——道不可告,告即不得》。关于宋元明理学,著有《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朱子语类的历史》、《朱子与经商》、《朱子论生死与鬼神》等。须指出,尽管胡适做了大量补阙工作,然关于宋明理学者依旧偏少。
无论如何,《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让胡适具有中国学术史概念,并引起他补阙雄心,以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这点确信无疑。
可是问题并非这么简单,胡适在补阙中,其学术观点与梁启超发生歧异,并影响两人学谊,以下分述。
二、胡适不同意梁启超关于《管子》的意见
1909年梁启超作《管子传》,其《叙论》道:“《管子》一书,后儒多谓战国时人依托之言,非管子自作。虽然,若《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则史公固称焉,谓其著书世多有之,是固未尝以为伪也。……且即非自作,而自彼卒后,齐国遵其政者数百年。亦见《史记》本传。然则虽当时稷下先生所讨论所记载,其亦必衍《管子·绪论》已耳。”*梁启超:《管子》,《梁启超全集》第6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0页。
据1916年4月8日胡适日记,他写《读〈管子〉》上、下篇,“下篇乃驳梁任公《管子》中语”。*胡适:《写定读〈管子〉上、下两篇》,《胡适全集》第28卷,第339页。4月13日,胡适日志还有:“梁任公著《管子》(宣统元年),其论《管子》书中之法治主义及其经济政策,皆有可取之处。惟梁先生以此诸项为管子所尝实行,所尝著述,此则根本错误,不容不辨。”*胡适:《评梁任公〈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胡适全集》第28卷,第339—340页。胡适所说《读管子》“下篇”,实为1916年6月《留美学生季报》夏季第2号所载胡适《读〈管子〉》。他驳梁启超之说,原文甚长,这里述其大概。梁启超依据《史记》,认为《管子》并非全部出自后人依托,即使不是管仲之作,亦必是稷下学人衍管子遗绪者所作。胡适以为《史记》记载未必是定论;至于说《管子》为管仲遗绪所为则无证据,也违背思想进化之理。*胡适:《读〈管子〉》,《胡适文集》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29—730页。实在跟梁启超唱了绝大反调。
1919年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出版名为《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29年收入“万有文库”改名为《中国古代哲学史》,《胡适全集》中仍名为《中国古代哲学史》。坊间还有《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讲义稿),是《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基础,两者大同小异,不赘述。梁启超所评《中国哲学史大纲》当是1919年出版物。,重申《读〈管子〉》之论:“《管子》这书,定非管仲所作,乃是后人把战国末年一些法家的议论和一些儒家的议论……还有许多夹七夹八的话,并作一书;又伪造了一些桓公与管仲问答诸篇,又杂凑了一些记管仲功业的几篇;遂附会为管仲所作。今定此书为假造的,证据甚多。”*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胡适全集》第5卷,第208—209、209、209、209、504、224页。胡适接下来提出证据三类:第一类,《管子》记管仲身后事。例如,《小称篇》记管仲将死之言,又记桓公之死、西施之事这些管仲身后之事;《形势解》、《七臣七主》也记管仲身后事,“皆可见此书为后人伪作”。*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胡适全集》第5卷,第208—209、209、209、209、504、224页。第二类,《管子》有后世思想。例如,《立政篇》说寝兵、兼爱,《立政九败解》说兼爱,《法法篇》求废兵之语,这些都是墨子学说,“远在管仲以后了”。*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胡适全集》第5卷,第208—209、209、209、209、504、224页。第三,《管子》中的思想后世不见呼应。《管子》有法治思想,然管仲身后百余年贤如叔向、孔子竟无一毫法治观念,因而“《管子》书中的法治学说,乃是战国末年的出产物,决不是管仲时代所能突然发生的。”*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胡适全集》第5卷,第208—209、209、209、209、504、224页。无疑,胡适再次未指名地跟梁启超唱了对台戏。
1922年3月4日,北京大学哲学社邀请梁启超演讲,题目是《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其中谈到《管子》问题:“《管子》这部书,胡先生断定他不是管仲所作,我是完全赞成;若说管仲这个人和后来法家思想没有关系,我便不敢说。……《管子》书中许多奥衍的法理,我绝对承认是由后人引申放大;但这种引申放大的话,为什么不依托令尹子文,不依托狐偃、赵衰,不依托子产,独独依托管仲?便可以推想管仲和这种思想渊源一定有些瓜葛。”*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全集》第13卷,第3986—3987、3988页。
其实,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称管仲“是实行的政治家,不是法理学家,故不该称为‘法家’”*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胡适全集》第5卷,第208—209、209、209、209、504、224页。,梁启超则不赞成;除此之外,他们在《管子》真伪问题上,见解完全相同。至于胡适1916年4月8日在日记中批评梁启超言《管子》中 “十之六七为原文,十之三四为后人增益”为殊无证据,可以这样理解:梁启超以模糊语言表述,意思是《管子》大部分可靠;而胡适以自然科学语言评判,认为梁启超结论无据。他们之间实无根本分歧。然经此一事,两人原本未说破的关于《管子》的意见分歧,现在却公开化了。
三、胡适和梁启超关于《老子》的分歧
1904年,梁启超作《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道:“道家对于法之观念,实以无法为观念者也。既以无法为观念,则亦无观念之可言。”*梁启超:《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梁启超全集》第5卷,第1267页。1916年4月13日,胡适在日记中批评梁启超上述观点:“梁氏此论,大谬有三”,“第一,梁氏不知老子之自然法乃儒家法家言治言法之所自出”;“第二,老子未尝不许应用自然法以为人定法也”;“第三,梁氏谓老子既以无法为观念,则亦无法之观念可言,则尤谬矣,老子之自然法,‘无为’而已,‘自然’而已。”*胡适:《评梁任公〈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胡适全集》第28卷,第347页。胡适这段论述,当时虽未公开,但已显示日后与梁启超在老子问题上的全面分歧。
1919年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认为:“中国哲学到了老子、孔子的时候,才可当得‘哲学’两个字。我们可把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当作中国哲学的怀胎时代。”*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胡适全集》第5卷,第208—209、209、209、209、504、224页。他在第一篇《导言》和第二篇《中国哲学发生的时代》之后,第三篇就是《老子》,写出老子略传,考订《老子》,视老子为革命家,讨论老子天道、“无”、“名”、“无为”等观念,分析了老子的人生哲学。
1920年梁启超写《老子哲学》,其中老子传略与胡适所写大致相同,以佛学解老子学说不同凡响。他认为老子的历史本体论为“不许思议”*梁启超:《老子哲学》,《梁启超全集》第10卷,第3113、3114、3115、3116、3117页。;其名相论为“分别心才生出种种相对的名”*梁启超:《老子哲学》,《梁启超全集》第10卷,第3113、3114、3115、3116、3117页。,“宇宙万物自然而有动向,亦自然而有静相”*梁启超:《老子哲学》,《梁启超全集》第10卷,第3113、3114、3115、3116、3117页。,“种种妄见,皆由‘我相’起”*梁启超:《老子哲学》,《梁启超全集》第10卷,第3113、3114、3115、3116、3117页。;以罗素创造和占有理论解读老子作用论“常无为而无不为”。*梁启超:《老子哲学》,《梁启超全集》第10卷,第3113、3114、3115、3116、3117页。诸如此类,确有独到之处。
原本两人都在构建逻辑体系,各说各话,可梁启超却要使自己占据上风。1922年他《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不同意胡适从老子开始讲哲学史:“应否从老子讲起,还是问题。这却不能怪胡先生,因为这问题是我新近才发生的:我很怀疑《老子》这部书的著作年代,是在战国之末。”*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全集》第13卷,第3986—3987、3988页。
《史记》中老子作为传主有三个化身,梁启超提出六处可疑,作为上述观点的支撑:《史记》中有神话,所记前辈老子八代孙和后代孔子十三代孙同时,不合情理;孔子乐道人善却不称道老子,墨子、孟子好批评人却始终只字不提老子;老聃拘谨守礼与五千言精神相悖;《史记》一些材料来自《庄子》,而《庄子》所言不能作历史看待;《老子》中一些激烈语言不是春秋时代可有的;《老子》中一些术语或者表述不是春秋而是战国时期产物。
因此,他提出疑问:“胡先生所说三百年结的胎,头一胎养成这位老子,便有点来历不明了。……不晓得为什么象他这样勇于疑古的急先锋,忽然对于这位‘老太爷’的年代竟自不发生问题?”*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全集》第13卷,第3989、3990—3991、3991、3992、3992页。
1922年3月6日,胡适在《日记》中就梁启超提出的六个疑点逐一辩驳:既然任公视《史记·老子传》最不可靠,但又信此中世系;孔子不提及老子,但其言论似受老子影响,老子未被孟子等提及不足为奇;老子本是很退缩谦卑的人,许多革命思想家是很拘谨的;《庄子》我们本不信它;《老子》中的激烈言论在《伐檀》一类的诗里就有;《老子》中的一些术语在《易象传》(离卦)、《诗》里都能找到。他的结论是:“《老子》虽不可全信为原本……但此书非作伪者所能为。”*胡适:《日记1922年》,《胡适全集》第29卷,第533页。除《史记》一些材料来自《庄子》外,梁启超提出的另外五条怀疑,胡适逐一辩驳,但是没有公开。
其实,胡适跟梁启超争议的问题可归纳为三:《史记》记载可靠性,春秋战国诸子极少提及老子,《老子》中术语、思想的时代性。从这三个主题来看,胡适的辩驳确比梁启超的逻辑严密。
但是,若把两人关于《老子》的辩难与两人关于《管子》的争论结合考察,则可发现胡适言论有跟梁启超置气的成分。第一,本来梁启超依据《史记》记载,断定《管子》大部分可靠,胡适却提出《史记》记载未必可靠,从而为认《管子》是伪书设定逻辑起点。第二,胡适以孔子、孟子等无法治思想,从而旁证《管子》为孔、孟之后著作;梁启超使用类似思维,依据孔子、孟子等不提老子,而旁证《老子》在孔、孟之后,可是胡适又称这不足为据。第三,胡适依据《管子》记载管子身后事,从而断定《管子》为伪作;可是梁启超依据《老子》中有战国时期术语和思想,从而断定《老子》为战国人所作时,胡适却说梁氏之论“似是而非”。
四、胡适和梁启超在孔子问题上的抵牾



在孔子问题上,梁启超的批评切中胡适要害,故胡适没有像在其他问题上那样辩解或者反击。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孔子一方面受捧,另一方面遭抑。

相反,胡适把孔子思想影响下的旧制度和旧思想称为“孔渣孔滓”、“孔教”,把孔子学说和后儒学说喻为“老店”和“冒牌”,主张“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胡适:《〈吴虞文录〉序》,《胡适全集》第1卷,第763页。
早在1915—1917年完成的《先秦名学史》中,胡适就声称:“儒学已长久失去它的生命力”,“我确信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胡适:《先秦名学史》,《胡适全集》第5卷,第11页。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发表胡适《孔教精义》,讥讽军阀尊孔。*胡适:《孔教精义》,《胡适全集》第21卷,第186页。甚至到了1934年胡适还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认为过去年年祭孔子、天天拜孔子“曾何补于当时的残酷的社会,贪污的政治?”而“‘近二十年’比那个拜孔夫子的年代高明的多多了。……这都没有借重孔子的力量”。*胡适:《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胡适全集》第4卷,第529页。
晚年胡适在《口述自传》里,认为自己“并不要打倒孔家店”,虽然“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第18卷,第424页。胡适痛诋包括北洋政府在内的民国时期尊孔、倡孔教的做法,证据确凿;而尊孔、倡孔教,与当时的孔家店形同意合,胡适痛斥尊孔、倡孔教,自然是痛斥孔家店,因此梁启超对其批评不是捕风捉影,胡适也无须为自己推脱。
五、胡适和梁启超在《墨子》上的分歧
1904年,梁启超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说:“墨子不认自然法,因亦不认人民总意。”*梁启超:《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梁启超全集》第5卷,第1268页。1916年4月13日,胡适日记批评梁启超“真厚诬墨子矣”。*胡适:《读梁任公〈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胡适全集》第28卷,第351页但是,胡适的反对意见并未公开。
1904年,梁启超著《子墨子的学说》,即《墨学微》*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1号,胡适发表《归国杂感》,他说:从美国回来“又看见《饮冰室丛著》内有《墨学微》一书,我是喜欢看看墨家的书的人,自然心中很高兴。不料抽出来一看,原来是任公先生十四年前的旧作,不曾改了一个字!”引文见《胡适全集》第1卷,第593页。,以为墨子之教为“尊天之教”、“鬼神教”、“非命”,“所以普度众生,用心良苦”,然于“灵魂”,“墨子暗于此,此其教之所以不昌也”。*梁启超:《子墨子的学说》,《梁启超全集》第11卷,第3167、3167、3175、3176、3178页。又以为墨子“以利为目的”,“以利为手段”,“利之一字,实墨子学说全体之纲领也”。*梁启超:《子墨子的学说》,《梁启超全集》第11卷,第3167、3167、3175、3176、3178页。以为墨子“兼爱”之说“为维持社会秩序、增进社会幸福之不二法门,其意不可谓不盛”。*梁启超:《子墨子的学说》,《梁启超全集》第11卷,第3167、3167、3175、3176、3178页。还说:“墨子之政术,民约派论之政术也。”*梁启超:《子墨子的学说》,《梁启超全集》第11卷,第3167、3167、3175、3176、3178页。“墨子之政术,非国家主义,而世界主义社会主义也。”*梁启超:《子墨子的学说》,《梁启超全集》第11卷,第3167、3167、3175、3176、3178页。
1919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之前,胡适在1918年9、10、11月《北京大学日刊》,及1919年4、7月《太平洋》第11、12号,发表《墨子哲学》,后收入《胡适全集》第7卷,与《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相关部分大同小异。,跟《子墨子的学说》唱起反调。胡适指出孙冶让《墨子间诂·非攻中》考证不如汪中《墨子·序》精确*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讲义稿)》,《胡适全集》第5卷,第317—319、323—324、327—329、336—344、406—407、345—405页。,让梁启超采毕沅之说相形见绌。胡适分今本《墨子》53篇为5组,述其价值和问题*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讲义稿)》,《胡适全集》第5卷,第317—319、323—324、327—329、336—344、406—407、345—405页。,比梁启超精细得多。他说墨子的“利”字是改善、运用,被世人误解为“财利”、“财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讲义稿)》,《胡适全集》第5卷,第317—319、323—324、327—329、336—344、406—407、345—405页。,潜台词是梁任公误解“利”字。胡适所论墨子“宗教”*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讲义稿)》,《胡适全集》第5卷,第317—319、323—324、327—329、336—344、406—407、345—405页。,比梁启超细致。胡适论墨学消亡三原因*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讲义稿)》,《胡适全集》第5卷,第317—319、323—324、327—329、336—344、406—407、345—405页。,超过梁启超。胡适讲杨朱、别墨比梁启超详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讲义稿)》,《胡适全集》第5卷,第317—319、323—324、327—329、336—344、406—407、345—405页。
1920年梁启超作《墨经校释》,反驳胡适疑《墨经》,算是对《子墨子的学说》的补救。第一,其《自序》概述清代墨学,可补《子墨子的学说》疏漏。第二,其《读〈墨经〉余记》,反驳孙冶让、胡适疑《经》上下和《经说》上下,认为“孙胡说非也”。*梁启超:《读〈墨经〉余记》,《梁启超全集》第11卷,第3198页。
1921年2月26日,胡适作《梁任公〈墨经校释〉序》以正《墨经校释》之讹。梁书有条凡例:凡《经说》每条之首一字,必牒举所说《经》文此条之首一字以为标题,此字在《经》文中可与下文连续成句;在《经说》中决不许与下文连续成句。梁启超利用这条公例校改许多旧注。胡适以为这样“一定要发生很可指摘的穿凿傅会”*胡适:《梁任公〈墨经校释〉序》,《胡适全集》第2卷,第157、158、158页。,且梁任公“也不能完全谨守”。*胡适:《梁任公〈墨经校释〉序》,《胡适全集》第2卷,第157、158、158页。他反对梁启超删去《经》与《经说》原文末几条,认为它们“不像有后人附加的文句”。*胡适:《梁任公〈墨经校释〉序》,《胡适全集》第2卷,第157、158、158页。
1921年4月3日,梁启超写信,答复胡《序》,承认牒经标题公例过于严格,但援例辩解,坚持公例。针对胡适反对删去末几条,他说:“吾观察此书,与我公立脚点有根本不同之处。”*梁启超:《1921年4月3日致胡适》,《胡适全集》第2卷,第166页。同时反攻胡适《墨子新诂》之误。1921年5月3日,胡适作《答书》,未有实质性内容。*胡适:《答梁启超书》,《胡适全集》第2卷,第167—170页。
1921年梁启超作《墨子学案》,以托尔斯泰利他主义解墨子“兼相爱”,以克尔泡特金互助主义解墨子“交相利”,以马克思批判资本家观点解墨子“节用”、“节乐”。他视墨子“天志”,“纯是用来做兼爱主义的后援”,而“明鬼”则“不外借来帮助社会道德的制裁力”。*梁启超:《墨子学案·墨子之宗教思想》,《梁启超全集》第11卷,第3272页。他以卢梭“民约论”解墨子“尚同”、“尚贤”,以20世纪20年代初俄国社会“平等而不自由”来认识墨子心中的理想社会,它“和欧洲初期的‘民约论’很相类”,“和现在俄国的劳农政府,很有点相同”。*梁启超:《墨子学案·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梁启超全集》第11卷,第3275—3276页。梁启超以基督精神来比喻墨子身体力行,并认为“秦汉之间,任侠之风还大盛,都是墨教的影响”。*梁启超:《墨子学案·实行的墨家》,《梁启超全集》第11卷,第3278页。书后附有《墨子年代考》,结论不同于胡适。
1922年《先秦政治思想史》,重申其关于墨子“兼爱”、“交利主义”、“民约论”的见解。*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12卷,第3661—3669页。
1922年梁启超《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称赞胡适:“我除了赞叹之外,几乎没有别的说。”*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全集》第13卷,第3993页。不过,对胡适把《墨经》认为惠施、公孙龙之作“有点替墨子抱不平”。*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全集》第13卷,第3993页。他又说:“胡先生讲墨学固然甚好,讲墨学消灭的三种原因还不甚对。依我说,第三种‘诡辩太微妙’应改为‘诡辩太诡’。更有第四种原因,发于墨学自身,就是《庄子·天下篇》说的‘其道太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全集》第13卷,第3993页。
在《墨子》问题上,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超越梁启超《子墨子的学说》。梁启超著《墨经校释》化解危机,请胡适批评并作序,无非是想请胡适认可自己的贡献。然胡适是否不识其中之趣,不敢定论。但是提出批评意见确为事实,这就逼得梁启超在后续墨学著作中或克服弱点,或辩解,或反攻胡适。特别是他淡化胡适所写之序引起胡适不满。可见,在《墨子》问题上胡适有学者较真精神,而梁启超多少有失风度,但梁启超的行为从当时情境来看又是可以理解的行为。
六、胡适和梁启超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上互有启发
梁启超研究清代学术受到胡适鼓励。1920年10月14日,梁启超为《清代学术概论》写《自序》,表明写作动机之一:“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自序》,《梁启超全集》第10卷,第3067页。1920年10月18日梁启超《致胡适之》:“公前责以宜为今文学运动之记述,归即嘱稿,通论清代学术,正宜(拟)钞一副本,专乞公评骘。”*梁启超《1920年10月18日致胡适之》,《梁启超全集》第20卷,第6031页。
胡适为《清代学术概论》提出修改意见。1920年10月18日梁启超《致胡适之》:“得百里书,知公已见矣。关于此问题资料,公所知当比我尤多,见解亦必多独到处,极欲得公一长函为之批评(亦以此要求百里),既以裨益我,且使读者增一层兴味。……望弗吝教。”*梁启超《1920年10月18日致胡适之》,《梁启超全集》第20卷,第6031页。
11月29日,梁启超又写《第二自序》,称:“此书成后,友人中先读其原稿者数辈,而蒋方震、林志钧、胡适三君,各有所是正,乃采其说,增加三节,改正数十处。三君之说,不复具引。非敢掠美,为行文避枝蔓而已。”*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二自序》,《梁启超全集》第10卷,第3068页。
1921年5月2日,胡适在《日记》中称:“此书的原稿,我先见过,当时曾把我的意见写给任公,后来任公略有所补正。《改造》登出之稿之后半已与原稿不同,此次付印,另加惠栋一章、戴氏后学一章、章炳麟一章,皆原稿所无。此外,如毛西河一节,略有褒辞;袁枚一节全删;姚际恒与崔适的加入,皆是我的意见。”*胡适:《日记1921年》,《胡适全集》第29卷,第232页。因梁启超原稿、胡适所写意见和《改造》所登之稿不得而见,胡适具体提出怎样的修改意见,不得而知,只是从梁启超《第二自序》和胡适《日记》中获得以上大概印象。
胡适继续梁启超关于戴震哲学的研究。1923年梁启超作《戴东原哲学》,认为《孟子字义疏证》以识字为手段,以闻道为目的。*梁启超:《戴东原哲学》,《梁启超全集》第14卷,第4189、4190、4191、4191—4200页。戴震“对于敌派的攻击,是很公正的,很稳健的”*梁启超:《戴东原哲学》,《梁启超全集》第14卷,第4189、4190、4191、4191—4200页。,“东原的诵法孔孟不是因袭,乃是创造”。*梁启超:《戴东原哲学》,《梁启超全集》第14卷,第4189、4190、4191、4191—4200页。他梳理戴东原思想渊源,从多方面展示其哲学的丰富内容。*梁启超:《戴东原哲学》,《梁启超全集》第14卷,第4189、4190、4191、4191—4200页。这一年他还作《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特别是1923年为安徽屯溪所建戴东原图书馆作记,文称:“戴东原先生为前清学者第一人,其考据学集一代大成,其哲学发两千年所未发”。*梁启超:《戴东原图书馆缘起》,《梁启超全集》第14卷,第4217页。胡适《戴东原的哲学》作于1923年12月,成于1925年8月,分析戴震哲学产生的学术背景:“反玄学”运动,以实用来补救空疏、用经学来代替理学。他阐释戴震哲学《孟子字义疏证》、《原善》思想:戴震特异于清儒者在于以训诂为明道之法;所明之道或为人道或为天道,其天道论是自然主义,天道产生人性;情、欲、知一律平等,理是事物的条理关系;“就事物剖析至微,求其必然不可易”;注重生养之道,主张“无私而非无欲”;不空谈知行合一,主张“重行须先重知”。他梳理戴震对后学的影响:朱筠最赏识戴震但不解其哲学之重要;洪榜为戴震辩护而不能光大戴学;程晋芳专骂戴震却算不得驳论;段玉裁身为大弟子可未获真谛;章学诚懂戴震但未免卫道;翁方纲推崇戴震考订治学而盲目反对其哲学;姚鼐对戴震考订和哲学双双排斥;凌廷堪对戴震哲学重视但不欣赏;焦循佩服戴震但根本不容;崔述主张与戴震最为一致;阮元是戴学最大护法;方东树斥戴学但完全不明戴震宗旨。胡适的路数显然不同于梁启超。
梁启超、胡适都在论戴震哲学,但两人侧重不同,不过推崇戴震则完全一致。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称戴震治学为“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第10卷,第3081页。胡适《戴东原的哲学》推崇戴震:“戴震的哲学,从历史上看来,可以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也可以说是新理学的建设——哲学的中兴。”*胡适:《戴东原的哲学》,《胡适全集》第6卷,第396页。
梁启超启发胡适为戴震辩诬。1923年,梁启超写《戴东原先生传》,提到魏源的东原不敬江永之说,并为戴震辩护;*梁启超:《戴东原先生传》《梁启超全集》第14卷,第4182、4184页。胡适先是在1943年12月7日写出《戴震对江永的始终敬礼》,接着1944年1月19日写出《再记东原对江慎修的敬礼》,为戴震辩诬。梁启超《戴东原先生传》涉及戴震和赵一清《水经注》公案,以为他们“盖纯属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绝不成为道德责任问题”。*梁启超:《戴东原先生传》《梁启超全集》第14卷,第4182、4184页。胡适花半生研究《水经注》,写有《戴东原、赵东潜〈水经注〉疑案的考证》、《戴震未见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十组证据》、《从校勘学方法上论戴氏未见赵书》等*胡适相关文章还有:《略记赵戴两家〈水经注〉的一些大不相同地方》、《论杨守敬判断〈水经注〉案的谬妄》、《总论一百年来许多学者审判〈水经注〉疑案的方法的大错误》、《杨守敬审判全赵戴三家〈水经注〉的错误》、《批评杨守敬审判〈水经注〉疑案的考证方法》、《戴震校〈水经注〉最早引起的猜疑》、《平定张穆“赵戴〈水经注〉校案”》、《评论王国维先生的八篇〈水经注〉跋尾》、《真历史与假历史——用四百年的〈水经注〉研究史作例》、《〈水经注〉案第九证》、《驳杨守敬断定“戴之袭赵,昭然若揭”的谬论》、《孟森先生审判〈水经注〉案的错误》。,为戴震辩诬。
关于戴东原不敬江永之事,梁启超所指持说者仅魏源一人,依据戴震《江敬修先生事略状》表明戴震敬礼江永,又说戴震是否受业于江永而称弟子难以确考,还依据戴震对待自己弟子理解为半友的习惯,为戴震辩护。胡适接过这个问题,把研究推向深入。他把持说者又增加张穆、王国维两人;找出三人言论出处,张穆语见《方牧夫寿序》,魏源语出《书赵校〈水经注〉后》,王国维语在《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他找遍戴震著作发现,戴震提到江永除了两处都称“江先生”,那两处为“吾郡老儒江慎修永”,一处是在《声韵考》卷三“古音”,另一处《六书音均表序》,都是在叙述历史,且“老儒”意为“老先生”,不可谓不敬。他认为魏源、王国维之说“近于恶意的诬枉”*胡适:《戴震对江永的始终敬礼》,《胡适全集》第14卷,第29、31页。,这样做的原因,“都要用这‘背师’的罪状来帮助他们证明东原‘攘窃’《水经注》的一案”。*胡适:《戴震对江永的始终敬礼》,《胡适全集》第14卷,第29、31页。
关于戴震抄袭赵一清《水经注》校本之事,梁启超在《戴东原先生传》中提出闭门造车,出门合辙这一观点,但未考证。倒是同年《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中有详考。在《直隶河渠书》疑案上附和段玉裁《赵戴〈直隶河渠书〉辩》意见,认为“盖赵草创而戴删改必矣”。*梁启超:《戴东原先生传》,《梁启超全集》第14卷,第4208、4210—4211页。与此相关,提出赵、戴校释《水经注》疑案。梁启超注意到段玉裁提出赵、戴都未抄袭对方,是梁玉绳校刻赵书之经,碰到不合者则采戴本以正之,从而造成公讼。段玉裁致书梁玉绳诘问此事,而梁玉绳未作辩解算是默认。张穆、魏源为赵鸣不平,认为赵书收入四库,戴在四库馆窃取;可是根据段玉裁、孔荭谷所言,戴书在其进四库馆之前就有部分刊行。鉴于以上,梁启超认为:“赵戴之于此书,皆用过十年苦功,造诣各臻其极,其治学方法又大略相同,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并非不可能之事。茂堂尊师太过……引起反动,终有石洲默深之反唇,实则两皆失也。兹案关系东原人格,吾故不惮词费,胪列两造之说而平亭之如右。”*梁启超:《戴东原先生传》,《梁启超全集》第14卷,第4208、4210—4211页。
胡适赞同梁启超观点,但比梁启超细致多了。1935年9月3日,《致杨联陞》中说:“这样大热天,老兄竟为我摘抄任公先生的《戴氏书目考》中关于《水经注》的全文!真是感谢之至!任公判断此案,大致甚平允,但此文(书目考)作于王静庵、孟心史两公发表文字之前,——作于《永乐大典》本半部出现之前,更在《大典》本全部影印出现之前,——故尚不足使后来读者(三十年来的读者)心服。”*胡适:《致杨联陞》,《胡适全集》第25卷,第543页。他揭示公案缘起,列举戴震未见赵《水经注》校本的证据,比勘赵戴两本的不同之处,反驳张穆、魏源、杨守敬、王国维等人对戴震的诬词,分析他们致误原因,或不懂校勘本质或心存他意,总之,“材料相同,方法相同,故研究的结论也就自然的大同而小异。”*胡适:《真历史与假历史——用四百年的〈水经注〉研究史为例》,《胡适全集》第17卷,第348页。
可见,在清代学术史问题上,两人几乎没有分歧,倒是互相启发,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七、胡适对梁启超从推崇到心存芥蒂
胡适早年除关于《管子》、《老子》、《墨子》个别具体学术观点不同意梁启超的意见外,总体上景仰梁启超。
1912年11月10日,胡适日记载:“阅《时报》,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矣。”*胡适:《留学日记》卷二,《胡适全集》第27卷,第222页。
早在留学美国之前,胡适对梁启超就非常景仰。20多年后的1931年3月18日,胡适完成《四十自述》之《在上海(一)》,其中有:“我在澄衷一年半,看了一些课外的书籍。……梁先生的文章……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往前走,他却打住了,或是换了方向走了。……跟着他走,我们固然得感谢他;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我们更得感谢他。”*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第18卷,第58—59、60页。胡适所说“在澄衷一年半”,是胡适入澄衷学堂到考入中国公学前,即1905年春到1906年暑期。期间梁启超此前发表的论著,胡适都可能看到。
他继续道:“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他在那个时代(我那时读的是他在壬寅癸卯做的文字)主张最激烈,态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第18卷,第58—59、60页。胡适在这里除了重申梁启超影响力外,还明确他所读梁启超的著作为“壬寅癸卯做”,也就是1902—1903年间的著作。这期间梁启超著述很多,其中就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说》、《天演论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等。
1931年,胡适在《我的信仰》中述其1904—1910年上海读书所得:“从当代力量最大的学者梁启超氏的通俗文字中,我渐得略知霍布士(Hobbes)、笛卡儿(Descartes)、卢梭(Rousseau)、边沁(Bentham)、康德(Kant)、达尔文(Darwin)等诸泰西思想家。梁氏……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字……开了给我,也就好像开了给几千几百别的人一样,对于世界整个的新眼界。”*胡适:《我的信仰》,《胡适文集》第1卷,第11页。此文收在《胡适全集》第36卷,为英文,题为Essay in Living Philosophies。
胡适因推崇梁启超,故而渴望见到梁启超。1918年11月20日,回国后的他曾致信梁启超,主动求见:“适后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将来天津南开学校演说,拟留津一日。甚思假此机会趋谒先生,一以慰平生渴思之怀,一以便面承先生关于墨家之教诲,倘蒙赐观所集‘墨学’材料,尤所感谢。”*胡适:《致梁启超》,《胡适全集》第23卷,第222页。
可惜胡适未能如其所愿,他得以首次会晤梁启超是在1920年3月21日,胡适是日《行程》称:“初见梁任公,谈。”*胡适:《日记1920年》,《胡适全集》第29卷,第121页。之后,见面频繁起来,例如,1920年3月22日,胡适记:“有任公谈学生事。任公谋保释学生,未成。”*胡适:《日记1920年》,《胡适全集》第29卷,第122、159页。5月6日,又记:“见梁任公。他谈做中国史事,颇有见地。”*胡适:《日记1920年》,《胡适全集》第29卷,第122、159页。
1920年是胡适和梁启超学术关系的分水岭。这一年,梁启超在学术上揄扬胡适,其《墨经校释·自序》说章太炎、胡适对于《墨子》“时有征引浚发深造盖迈先辈”。*梁启超:《墨经校释·自序》,《梁启超全集》第11卷,第3196页。《清代学术概论》将胡适与章太炎相提并论:“樾弟子有章炳麟,智过其师,然亦以好谈政治,稍荒厥业。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第10卷,第3071页。梁启超比胡适年长18岁,能这样评价胡适,当是对胡适的抬爱。同时,梁启超《老子哲学》、《墨经校释》也多反驳胡适,上文已及,这显然是长辈对后学的期待。
就是从这年开始,两人在学术上对峙起来,胡适有分庭抗礼乃至取代之意。
胡适很在意梁启超的批评,1921年初致信陈独秀,认为梁启超讲中国哲学史,“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胡适:《致陈独秀》,《胡适全集》第23卷,第287页。
1920年10月18日梁启超《致胡适之》:“超对于白话诗问题,稍有意见,……亦欲与公上下其议论。对于公之《哲学史纲》,欲批评者甚多,稍闲当鼓勇致公一长函,但恐又似此文下笔不能自休耳。”*梁启超:《致胡适之》,《梁启超全集》第20卷,第6031页。
1921年5月2日,胡适日记语及《清代学术概论》:“任公此书甚好,今日亦只有他能作这样聪明的著述。此书亦有短处。他日当为作一评,评其得失。”*胡适:《日记1921年》,《胡适全集》第29卷,第232页。
据此两条材料,可见20年代初,胡适已不满梁启超对自己的单方面学术批评,流露出互相批评之意。同时,作为后学,胡适对梁启超在学术上有分庭抗礼之意,这可在胡适日记里得到互证。
1922年2月15日胡适记:“其实任公对于清代学术的见解,本没有定见。”*胡适:《日记1922年》,《胡适全集》第29卷,第518、729、529—530、614、653、700页。8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认为旧式学者有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半旧半新的学者就是梁启超跟胡适等人。*胡适:《日记1922年》,《胡适全集》第29卷,第518、729、529—530、614、653、700页。这里胡适要与梁启超在学术上比肩的心扉洞开。
梁启超在1922年3月4日,公开评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尽管梁启超在演讲开头说不少给胡适捧场的话:“哲学家里头能够有这样的产品,真算是国民一种荣誉。……他的立脚点很站得住。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全集》第13卷,第3985、3986、3986—3987页。然而,同时认为:“总不免怀着一点成见,象是戴一种着色眼镜似的,所以强古人以就我的毛病,有时免不掉。”*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全集》第13卷,第3985、3986、3986—3987页。他指出《中国哲学史大纲》两大缺点:“把思想的来源抹煞得太过了”,“写时代的背景太不对了”。*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全集》第13卷,第3985、3986、3986—3987页。之后是具体的对先秦诸子的不同看法。
次日,胡适在场,心中不想去却不得不作出洗耳恭听的样子。实际上这件事使得两人本来就有的芥蒂更结实了,对此,胡适承认:“他当时不免有点介意。我当时也有点介意。”*胡适:《日记1929年》,《胡适全集》第31卷,第321页。1922年3月5日胡适日记对梁启超公开批评《中国哲学史大纲》明显表现不悦:“昨天哲学社请梁任公讲演,题为《评胡适的〈哲学史大纲〉》,借第三院大礼堂为会场。这是他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胡适:《日记1922年》,《胡适全集》第29卷,第518、729、529—530、614、653、700页。
胡适的不满延伸到他们关于《墨经》的讨论。1922年4月30日,胡适日记道:“梁任公的《墨经校释》出来了。他把我的序放在书末,却把他答我的序的书稿放在前面,未免太可笑了。”*胡适:《日记1922年》,《胡适全集》第29卷,第518、729、529—530、614、653、700页。5月6日致信钱玄同:“任公的《墨经校释》出版了,他把我的序放在书尾,却把他答我的书放在书前。因此,我觉得我不能不发表我答他的第二书。”*胡适:《致钱玄同》,《胡适全集》第23卷,第332页。
胡适还引申这一不悦到梁启超的其他行为。1922年6月11日,胡适日记表述对梁启超删去《秋蟪吟馆诗钞》中的艳诗、艳词很不满:“删的人不是‘方袍幅巾’的人,却是新学家梁任公!”*胡适:《日记1922年》,《胡适全集》第29卷,第518、729、529—530、614、653、700页。
八、胡适对梁启超从心存芥蒂到最终释怀
梁启超评论《中国哲学史大纲》后主动示好,1922年8月2日胡适记:“任公邀吃饭,座有在君,我们大谈诗。”*胡适:《日记1922年》,《胡适全集》第29卷,第518、729、529—530、614、653、700页。这似乎是一个趋于平静的信号。
不久梁启超再次发难。1923年3月,胡适应清华学校胡敦元等之请,作《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于4月26日作《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其中《附录三》对胡适有批评,认为胡适所列“文不对题”,“胡君这篇书目,从一方面看,嫌他挂漏太多;从别方面看,嫌他博尔寡要,我认为是不合用的。”*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梁启超全集》第14卷,第4245页。梁启超书目无论是学理还是实际使用,确比胡适胜出一筹,梁启超没有放过教训后学的机会,后来胡适再也不愿提起此事。同时要看到,梁启超对胡适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从过去既赞赏又批评,发展到只剩下批评了。
胡适也不甘落后,1923年11月29日作《〈科学与人生观〉序》,批评梁启超助长“科学破产”说的威风。*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全集》第2卷,第195—199页。

可是,胡适跟梁启超的间隙很难弥合了。1926年8月24日胡适日记里说:“任公一派的人最爱胡乱夸奖人,真是害人不浅。”*胡适:《日记1926年》,《胡适全集》第30卷,第245、395页。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的去世改变了这种分庭抗礼局面,胡适流露出取代梁启超学界领袖之意。次日胡适日记把梁启超看作旧派学者:“以《墨经校释·序》一事而论,我因他虚怀求序,不敢不以诚恳的讨论报他厚意,故序中直指他的方法之错误,但这态度非旧学者所能了解。”*胡适:《日记1929年》,《胡适全集》第31卷,第321、323、321、321页。这里胡适从内心深处再不像从前那样把自己和梁启超看成比肩的新派学者,而是把梁启超从新派中剔除出去。2月2日,胡适日记写道:“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统系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名一篇一书。后来我的结论是他的《新民说》可以算他一生的最大贡献。”*胡适:《日记1929年》,《胡适全集》第31卷,第321、323、321、321页。胡适本来对梁启超学术史观点就有不同意见,又不断被梁启超批评,其言有意气之嫌。
梁启超去世,胡适感到惆怅。1929年1月20日胡适记:“今日任公大殓,在广慧寺。……不觉坠泪了。”*胡适:《日记1929年》,《胡适全集》第31卷,第321页。类似材料还有:1929年9月4日《致周作人》:“赴任公的大殓,忽然堕泪”,见《胡适全集》第24卷,第21页。1月20日又记:“近年他对我很好,可惜我近年没机会多同他谈谈。”*胡适:《日记1929年》,《胡适全集》第31卷,第321页。1958年6月10日,作《〈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梁启超去世“那天晚上我从上海到北平,很想见他一面,不料我刚下火车就听见说任公先生已死了八个钟头了。次日,任公先生的遗体在广慧寺大殓,我和丁在君先生,任叔永先生,陈寅恪先生,周寄梅先生,去送他入殓。任公先生的许多老朋友,如贵州蹇季常先生等,都是两眼噙着热泪。在君和我也都掉泪了。”引文见《胡适全集》第19卷,第744页。他还对过去两人的芥蒂加以反思:“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们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胡适:《日记1929年》,《胡适全集》第31卷,第321、323、321、321页。他认识到梁启超以往做法的天真可爱,表明胡适对梁启超品行还是认可的。
不过,胡适说“我很原谅他”*胡适:《日记1929年》,《胡适全集》第31卷,第321、323、321、321页。,则不太符合事实。1929年5月,胡适作《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跟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唱反调。1922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里称三大进化:民族扩大、科举制废除、国民政治自觉*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梁启超全集》第14卷,第4028—4032页。。胡适认为康、梁这些30年前维新党人思想方法,“其实是没有方法,这种思想其实是不思想”。*胡适:《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胡适全集》第21卷,第415、416页。他特别攻击梁启超自以为豪的废科举之事为“维新党人的第一件大罪案”,“却不曾造出一种新式的考试制度”,“遂造成廿五年的政治腐化的现象!思想不精确,危害如此之大!”*胡适:《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胡适全集》第21卷,第415、416页。
1931年8月《北平图书馆馆刊》第5卷第4号,发表3月26日胡适《论〈牟子理惑论〉——寄周叔伽先生书两封》,认为批评梁启超《〈牟子理惑论〉辨伪》“未免粗心,殊为贤者之累。”*胡适:《论〈牟子理惑论〉——寄周叔伽先生书两封》,《胡适全集》第4卷,第163页。
1933年4月3日胡适作《〈四十二章经〉考》,对梁启超《〈四十二章经〉辨伪》有所辩驳和突破。梁启超文根据现存《四十二章经》的思想和文笔,依据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所引《旧录》文字和僧祐《出三藏集记》关于道安所撰录阙此经的说法,他得出结论:“道安与苻坚同时,安既不见此经,则其出固当在东晋之中晚矣。”*梁启超:《〈四十二章经〉辨伪》,《梁启超全集》第13卷,第3729页。胡适在《〈四十二章经〉考》中赞同汤用彤的说法:“我相信汤锡予先生之说大致不误,所以我不怀疑《四十二章经》有汉译本,也不怀疑现存之本为支谦改译本。”*胡适:《〈四十二章经〉考》,《胡适全集》第4卷,第193页。
这三例证明胡适在梁启超去世后未放弃对梁启超的批评,说他原谅梁启超,不能令人信服。
可以肯定的是,胡适对梁启超新民说的推崇没有变。1929年9月10日《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胡适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文中道:“梁启超先生办《新民丛报》,自称‘中国之新民’,著了许多篇《新民说》……确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新纪元。”*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胡适全集》第21卷,第442页。
胡适关注梁启超年谱事宜,并为之作序,算是后学尽了应尽之谊。1957年10月9日,《致杨联陞》:对于丁在君《任公年谱长编》,“很愿意写序”,“我一定写序”。*⑤胡适:《致杨联陞》,《胡适全集》第26卷,第119、131页。1958年1月3日,《致杨联陞》:“我很忧虑此唯一的存本《任公年谱》或有失落或散乱之危险。”⑤次日,《致李济》,关心丁文江编纂油印本《梁任公年谱长编》出版事宜。*胡适:《致李济》,《胡适全集》第26卷,第133页。6月10日作《〈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
九、胡适与梁启超学术关系之结语
从两人学术关系演变看,梁启超学术研究引起胡适兴趣和追随;胡适初生牛犊不怕虎,对梁启超多有批评;梁启超对于后生挑战按理不能不有所反应,一方面补救以往缺漏,另一方面反批评胡适,激起胡适更强烈批评。在《管子》、《老子》、孔子、《墨子》等问题争论上,两人各有所长,其争论多在学术层面,不过正如胡适所言确有意气成分。胡适关注梁启超年谱并为之作序,或许可被理解为后王对前王后事的处理,但确实体现后学对师辈的尊重。顺便指出两点:
第一,关于胡适是否反唇相讥。一般认为胡适未公开反唇相讥梁启超,事实不是这样,而是有所指摘。确实,梁启超批评《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并未立即回击。但《胡适文存》(二集)出版于1924年,其中指摘梁启超者就有《梁任公〈墨经校释〉序》及其答梁任公书、《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科学与人生观〉序》。1927年10月15日《现代评论》第6卷第149期上,胡适发表《〈孔雀东南飞〉的年代》,对梁启超有批评。可见,胡适对梁启超的批评有公开的回敬。
第二,关于胡适对梁启超的盖棺定论。一般情况下,学者论此问题,使用两段材料,第一段是1929年2月2日胡适日记上的,上文已征引的说梁启超不得系统训练、不得良师益友、影响大而成就甚微、《新民说》是一生最大贡献,等等;第二段就是胡适挽梁任公:“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胡适:《日记1929年》,《胡适全集》第31卷,第322—323页。其实,还是这天日记,胡适又写一段,说任公为人和蔼可爱、天真烂漫,等等。把这三段放在一起,可表明在胡适看来,除学术史成就乏善可陈外,梁启超为人和蔼可爱、天真烂漫,新民之说传世不朽。胡适这样评价,一方面表明自己学术上的王者之尊,另一方面体现对前辈的尊重。
总之,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胡适有互助之需。梁启超为耆旧宿儒,胡适借重他有利于成名成家;胡适为潜在后学领袖,梁启超借助之可赓续盛名。胡适对梁启超新民说始终欣赏,但对其学术史成就一直有分庭抗礼乃至一决高下之意。两人关于管子、老子、孔子,尤其墨子问题的分歧,引发梁启超公开批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他的批评导致两人从相互欣赏到心存芥蒂,激起胡适更为坚决的反驳,遂发生两代学人领袖的激烈角逐。在角逐中彼此互相促进,为免口实,各自在学术研究上都精益求精,特别是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上互相鼓励、互有启发,才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胡适对于清代学术的研究,写出《戴震的哲学》,特别是对戴震《水经注》公案的清理,并成为《水经注》研究方面的权威。同时要看到,梁启超有长者风度,主动示好;胡适关注梁启超年谱出版并为之作序,实尽到后学应尽之谊。这种不苟同、不限辈分的学术争鸣,这种互相批评、共同提高和互相珍惜的行为,总体上是健康的学术生态,难能可贵,值得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