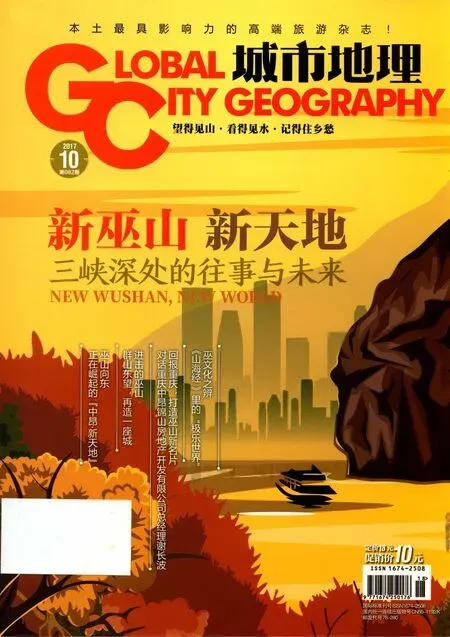郑州杂记
2018-03-11
我是2007年12月14日早上到郑州的。此前虽来过郑州五六次,但每次都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过来看一眼如水就走。见了面,如水就领我去老远老远的一家老字号饭店吃烩面。这烩面地道,味道好,它打开我的胃口时,也打开了我潜意识中对郑州的种种记忆,亲切感油然而升。
你以为早就忘掉的事情,其实已扎根于你的潜意识中。若触碰到一个暗藏的机关,就会哗啦啦地全涌现于你的眼前。早年当知青时,学过一些维吾尔语,后来离开了维族地区,就一句也不会说了。及至三年前去了新疆喀什,看到维吾尔女子拿刀子给我剖甜瓜,就指了指那个刀子,脱口说出“皮恰克”。自此以后,一个个维吾尔词语,就从嘴里冒出来,自己都觉得奇怪。
皮恰克是我潜意识中的一个暗门机关,烩面是另一个机关。吃到郑州烩面,就想起以前郑州人就蹲在马路边上捧着海碗吃,吃完将海碗扔地上,结账时数一数地上有几个碗。
第一次在郑州住夜,是住在市区北面的西藏干休所,那是1979年8月。蓝天叫我去他家找他,那是一幢上下两层楼的别墅房子,卧室里有卫生间。偌大的一所房子,当时只有蓝天一个人住。他知道我喜欢文科方面的书,就给我看了他父亲收藏的二十四史,给我看当时书店里买不到的那种写苏联的内部书,让我一个人睡在楼上的一个房间。
其后的几次,都是来郑州看如水。他知道我要半路出家写小说,眼睛里闪出疑惑的目光,怕我得了神经病,而另一面却给我备了一纸箱方格稿纸,看我什么时候能用完。纸箱很沉,得扛在肩上才行,背上还背着一个包,手里还拎着一个包,我要继续搭火车前往兰州。如水要送我到火车站,可当时年轻气盛,不要他送,结果进不了站。那是1983年的事。
记忆中,以前的郑州火车站是一排高大的苏式建筑,广场也比较大。那天车站里面外面都站满了人,水泄不通,哪里挤得进去!一个晚上就扛着一箱子纸头,跟着人群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地乱跑,可无论签了哪一趟车,都进不了站。
狗急了跳墙,人急了也不能傻站着。到了天亮,我就去了对面的汽车站,搭上去开封的长途汽车,去前面一站挤火车,以避开郑州蜂拥的人群。当年郑州是全国最大铁路枢纽,春节后客流量骤增,形容那一夜是人山人海,一点也不为过。想必开封站容易上车,也顺便看一看这个自己久仰的汴京古都——龙亭、相国寺以及铁塔和繁塔。
如水送我的那一箱子空白稿纸,至今还收藏在我书柜底层的最里面,用了百分之一不到。当年他为我辛苦寻觅,怕我天分很高,下笔如神,纸头不够,一下子就给我弄来这么多。也是我写小说写得晚,到了1992年,才发狠码字,又于次年就拿电脑打字,结果把笔和纸全都扔到一边去了,糟蹋了如水的这番好意和那一箱子纸。
至于他知道我想去外地写东西,打算一面看看外面的世界,一面集中时间及精力写长篇稿子,就劝我来郑州写;若觉得郑州闹,就安排我到登封去,到嵩山脚下的一处偏僻房子里,由我奋笔疾书。于是,我拖了一只很大的棕皮拉杆箱,带了布努艾尔的书,来郑州写一个20万字的口述自传体书稿,写耄耋老人汪韵芝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