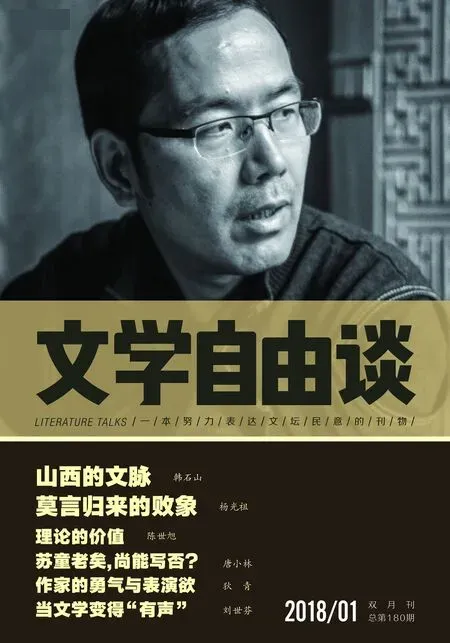山西的文脉
2018-03-07韩石山
韩石山
这篇文章,叫《山西的文脉》,不是说古代的,也不是说近代的,是说现当代的,也就是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的。
我不敢保证我的结论是正确的,我只想说,我尽量用准确的事实说明问题。若有一天,有人指出,我用的事实是错误的,而这一事实,从逻辑上说,又不足以证实我的结论,那么我愿意承认自己是错了。
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在自己糟蹋自己
好几年前了,有事去南方,酒席上聊天,一位半生不熟的朋友说,老韩呀,你可是个山药蛋派呀。我笑笑,没接这个茬儿。出门多了,我知道,凡是用这个方式开头的,没有几个是好料子。果然,酒过三巡,他的邪气就出来了,说有一件事他总也弄不明白,《徐志摩传》这样的作品,怎么也该是个江南人写的,怎么会是一个山西人写的?话说到这儿,哑巴也得说话了。我说,我见过一本南方人写的《徐志摩传》,开头是,轰的一声,一架飞机撞在山上,大火冲天而起。此人是大学教授,教授都这个水平,别人可想而知。出版社不想再“轰的一声”,只好偏劳我这个山西人了。
我知道,我这是诡辩。
他说的是实话,从正面说,我无言以对,也无颜以对。
我曾跟马烽、西戎诸前辈,认真地说过这个话题。我说,我是不赞成这个说法的。他们也说,山药蛋派这个说辞,是五六十年代,文学界那些自以为洋派的人,说了奚落山西作家的,可说是个鄙称,相当于民间的起外号。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起,有山西的评论家,在报上发表文章,说这是怎样的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学流派。此后省内报刊上,多有附和之声,等于是集体认领了这个鄙称。于是鄙称不再是鄙称,而是美誉了。我曾在一次会上说,多亏人家说我们是“山药蛋”,还能以丑为美,胡搅蛮缠,要是人家说是个别的什么蛋,也能化腐朽为神奇吗?
可别小看了这么个改变。我的感觉是,自从山西作家认领了这个鄙称,山西文学的品格,是越来越低了,连带的,山西文化的品格,也越来越低了。说得再严重点,连山西人的形象,也越来越低了。
一想到自己是个“山药蛋”,我都想搧自己一个耳巴子。
山西这个地方,说来真是可怜。经济,是靠煤炭支撑的;文化,是靠山药蛋作标签的。说是“表里山河”,实则是穷山恶水,你看看满世界,哪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是出煤炭的?这样的地理,这样的经济,这样的人文,你让人家怎么看这个山西,怎么看你这个山西人?
真的,到了外地,人家说我是山药蛋派,我脸上无光,觉得还不如骂上我两句好受些。骂了你可以还口,这样说了,你只有干受着。地理上,经济上,不好说什么,但我认为,在人文上,尤其是在文学的脉络上,这么多年,我们实在是自己在糟蹋自己。我写这个文章,就是想把这个偏差给纠正过来。
近代以来的山西文脉
2012年初冬,我病了住院,谢泳先生从厦门回来,和张发先生一起到医院看我。谢带去他考证陈寅恪诗的文章,还有几本书让我看,其中一本是郭象升的《文学研究法》。郭是山西泽州人,1881年出生,山西大学堂的学生,后来又当了山西大学的教授,在山西名气很大。《文学研究法》里有篇《白话文平议》,对当时的新文学人物,都有颇为中肯的评价。可见那个年代,山西的文化人,还是能容纳新的文学观念的。
最近看了一本书,对此又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这些年,赁居京师,陪老伴看孙子。有一天,一位叫王静若的女士,来到我的赁居之处,留下他祖父王念祖先生的一叠诗稿,希望我能推荐给山西的一家出版社出版。我不是个轻易帮人忙的人,但反正没事,就看了这位王先生的诗,还真的起了推荐的念头。后来回太原,我的老领导张明旺先生请客——他来作协前,曾任省出版局的副局长——同时请来了两位现任的出版社老总,一位是三晋出版社的张继红先生,一位是北岳文艺出版社的续小强先生。我原是想推荐给张总的,觉得这样的人物,还是他那儿合适。续先到,说起此事,续说,他们那儿正印一套《民国诗丛》,王先生的诗既然这么好,就加入这套丛书吧。我便将带去的诗稿,交给了续总。这是春天的事,到了秋天,这本书就出了,叫《王念祖诗集》。
现在可以说我之所以推荐的理由了。我不懂诗,不全是看他的诗好,我看重的是,这是一个有功名,且自许甚高的文化人。功名者,旧时之学历也。且看他有着怎样的功名。
王念祖先生,1882年出生,山西浑源县人。1900年十八岁时,首次参加童生选拔,获案首,成为秀才。1902年入山西大学堂西斋读书,同年山陕两省举办一场并科乡试,王先生前往西安,参加科考,顺利中举。原拟三年后进京参加会试,成为浑源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进士,不意1905年兴新学,废科举,只好重返山西大学西斋学习。1908年完成西斋预科学业,成为山西大学西斋第四期毕业生,被清政府授予新举人称号,成为新学旧学双举人,授候补知县衔,且不分单月双月,均可补缺。1911年8月,完成西斋法科学业,与其他同学进京面圣,被宣统皇帝赐进士。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任进士。
且看两个参照。鲁迅是1881年生人,参加过县考,未进学,后来也就没有资格参加乡试成为举人,进士就更不用说了。他那个年岁,是可能取得这些功名的,而他没有取得。民国后,学部有新进士考试,记得早年看书,郁达夫是参加了这个考试的,没有考取。
至于王念祖的才能,只要看看这两联就行了,一联是“杜陵寄食平生痛,王粲依人半岁闲”,一联是“王粲于今寥落甚,何时把盏一登楼”。王粲者,建安七子之首也。前联说的是1958年王念祖被划为“右派”,在随后的食堂化中,旧宅建为食堂,后又让村人占据,只好蛰居他处门洞旁的小屋里,一直到去世。
在那个年代,山西学子,功名上一点也不后于他人。
我在山西大学念书时,历史系教授郭吾真先生,与吴晗是清华同班同学,她的丈夫常风先生,外语系教授,是钱钟书的清华同班同学。中文系教授姚奠中先生,是章太炎的学生,可以说是鲁迅的师兄弟。我写过《李健吾传》《张颔传》,他们都是杰出的文化人。李是作家,张是考古学家,也可说是诗人,新旧诗都写。
这些文化人,他们身上,可有一丁点的山药蛋的气息?
怎么我一跨进文坛,就掉进了“山药蛋”的堆子里?
我是怎样掉进“山药蛋”堆子里的
我上大学时,学制是五年,1970年8月毕业,分配到山西汾西县一个村子教书,过了一年,到了另一个村子。我的老家在临猗县,调回去绝无可能。在这样的地方,前程是一眼就可以看到底的,年轻教员熬成老教员,退休了回老家。
要改变这个命运,对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来说,只有写作。三下两下,居然薄有声名。出名跟当强盗是一个道理,得干一票大的才行。当时的电影,八个样板戏之外,只拍出一部《青松岭》,我就想,若能写上个电影文学剧本,拍部电影,还怕调不出这个鬼地方吗?于是便写了个本子,叫《山里的秋天》,寄给北京电影制片厂。没想到的是,当年秋天,北影把我叫到北京,不是要拍这个电影,是觉得我的本子还有点基础,他们要办个电影文学剧本学习班,一个半月,让我来提高提高。
三十几个人里,后来也还有名的,一个是安徽来的张锲,一个是江西来的杨佩瑾。张后来当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杨后来当了江西文联的主席。认识他们对我没用,有用的是,认识了也在这儿改本子的两个山西作家,一个是马烽,一个是孙谦。我们住三楼,他俩住一楼,一人一个房间。有次我去了,马烽说,老孙昨天晚上咳嗽,浑身抖动,腿一抬,脚一挑,一边的小脚趾,不偏不倚,恰好挑进了床头柜上放的茶杯的把儿里,甩出老远,摔个粉碎。
这是1973年的事。此后我去了太原,就去看望二位。看望了马烽,顺便也去看望了西戎。在山西,这两个人的名字是连在一起的,都是《吕梁英雄传》的作者。
一晃改革开放来了,刊物多了,发表的作品也就多了。1980年,刚刚恢复的中国作家协会,办了个文学讲习会,学期半年,通知我参加。三十一二个人,山西就我一个。去了才知道,这是中国作家协会通过北京的文学单位,自个确定的名单,跟本省没有关系。也是去了才知道,这个讲习会的开办,与丁玲大有关系。上世纪50年代前期,丁玲主持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时,办过一个中央文学讲习所,招收解放区的年轻作家来进修。知道了这个情况后,讲习会的同学们兴奋不已,一致要求改名并延长学习期限。一闹腾,学期没动,名字还真的改了,叫成文学讲习所第五期,意思是,跟50年代办的四期接续上。
半年的时间里,多半是请有名的作家学者来讲课。学者们是讲课,作家来了是谈经验。真正的经验,往往就是经历,经历是最见性情的。记得一次请了萧军来,大谈在上海时怎样跟张春桥打架,又谈在刚刚开过的第三次文代会上,他们几个老作家,怎样向周扬发飙,弄得周扬很是尴尬,连连鞠躬,检讨自己过去整人的错误。
文讲所的负责人徐刚,是老讲习所的人,知道我是山西来的,曾跟我谈起文讲所的旧事。说丁玲办所初期,马烽和西戎都是第一批学员。山西来的,第一期是马烽、西戎,第二期是胡正,第三期是少数民族班,山西没人来,第四期是编辑班,来的是陈志铭,《火花》的副主编。
“怎么后来就不办了呢?”
“丁玲出事了,还怎么办下去?”
“那些人呢?”我是问一二期那些青年作家。
“哪儿来的回了哪儿。马烽、西戎、胡正,不都回了山西吗?”
隐隐约约地,我感到,我是站在了一个战阵的一侧。
文讲所结业回去,承马烽、西戎的关照,我从学校调出,到汾西县城关公社挂职,担任副主任。1984年,我正式调进省作家协会,成为专业作家。不久又去太原近郊的清徐县,挂职县委副书记,深入生活。
就这样,我掉进了“山药蛋”堆子里,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山药蛋”。
我不喜欢这名号,但我喜欢这待遇,这荣耀。
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可怜的老太太
1984年12月底,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西宾馆举行。我是山西的与会代表。行前,西戎让我去他家里,说省上正开人大常委会会议,他不能去北京,告了假,有份礼品,两瓶汾酒,还有一封信,让我带给丁玲。
到北京住下,当天晚上,我就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找到木樨地22号楼丁玲的家。房子很大,客厅里,好几个客人,正在谈笑中。听说我是山西来的,老太太很高兴。人多,不便说什么,问候几句,鞠躬退出。
回到京西宾馆,有人跟我说,会上有人在活动,要把丁玲选下去。山西代表中,也有人在做这个事。我对这种事向来反感。丁玲是个受尽磨难的老作家,解放初就是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主持工作,七老八十了,还是个副主席,忍心这么糟蹋吗?
第二天一上会场,我就知道我是多么幼稚了。
大会在一层会议厅里进行。从我们住的楼层下去,往右一拐,正是会议厅的后门。进去右手的墙上,有张大红纸写的致敬信,一看,是周扬同志病了,不能参加大会,许多受他栽培,或没有直接栽培,也受到他精神感召的作家们,对他为中国文学事业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祝愿他早日康复云云。两整张纸,竖着连在一起,下一张的大半空着,满满的全是签名,全是当时最叫红的,或是过了一段也叫红的作家们,有青年作家,更有一批重放异彩的右派作家。
开大会时,丁玲坐在主席台上,前排右边倒数第三或第二的位置上。上身是一件宽大的红毛衣,看去像一团火。
选举在最后一天进行。我心提得老高,为老太太担着心。是当选了,但票数不高,明显不是她这样的人物应得的那个数字。
再后来,是大型文学刊物《中国》停刊事件。一个复出的老太太,领着几个老弱残兵,想办一份刊物,也叫停了。真能做得出来。
关于丁玲是“老左”的话题,我是有自己的看法的。1996年,我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说:
十年动乱不提,粉碎“四人帮”后,各行各业都是受迫害最深的人出来掌权,按文艺界的情况,理当是丁玲出来,倡导思想解放才是。事有不尽然者,一来是周扬等人仅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本身又是政界人才,自然辨得风向,知道该何去何从;再则当时的中央对右派问题尚未全面平反,丁玲等人“案情重大”,而平反的大权操在周扬手里,实在不行了,也会拖一拖。丁玲所以会“二次平反”,其源盖出于此。待到丁玲彻底平反出来,世事已大变,周扬已经坐稳“思想解放领袖”的地位,两人既然势不两立,留给丁玲的是什么角色,就不言自明了。
文章名为《酒醉的探戈》,一年后收入我的《黑沉中的亮丽》一书。
周文和《吕梁英雄传》
进了山西作协,免不了会跟马烽、西戎两位师长聊聊天。我对30年代的文学,兴趣颇浓。想不到的是,他俩在晋绥根据地的老领导,竟是一位30年代的作家,名叫周文。
西戎给我说过,周文最著名的,是“盘肠大战”。他简略地说过事情的经过,详细情形,还是我自己看书知道的。
约1935年的时候,周文写了个短篇小说,叫《在山坡上》。其中有个情节是,一场血腥混战之后,一个腹部被刺破,肠子流出的士兵,醒来看到与他交战的敌方士兵还活着,又起来继续拼杀。《文学》的编辑傅东华,发表时将此情节删除。周文大为不满,写文章争辩。那边不依,两边就争论起来。因为是肠子引起来的,删去的又是文章中间的一段,故名曰“盘肠大战”。
周文的经历,有点像沈从文。1907年出生,四川荥经人,年轻时,曾在川军部队当文书。1930年出川,在江浙一带谋生,爱写小说,很快出名,由丁玲介绍入党,后来成了“左联”党组成员。与鲁迅关系亲密,鲁迅下葬时,是十几个抬棺人之一。
抗战开始后,周文撤到重庆,过了两年,去了延安。1942年过河到山西这边的晋绥分区,任宣传部秘书,后来当了秘书长。1945年初,《晋绥大众报》社长他调,周文兼了社长。此时马烽和西戎两个年轻人,已是这个报社的副刊编辑。1945年5月,晋绥边区召开战斗英雄劳模大会,英模材料很多,《晋绥大众报》是个小报,五六天出一次,无法悉数登载,经周文同意,由马烽与西戎执笔,将这些材料改写为章回小说,名为《吕梁英雄传》,逐期刊登。
抗战胜利后,周文奉调到重庆,任《新华日报》副总编辑,将已经发表的三十几章,带到重庆,在《新华日报》上连载。再后来,上海出了《吕梁英雄传》,前面有周文写的序言。可以说,《吕梁英雄传》是在周文一手扶植下写出来的,也是在周文一手策划下,走出吕梁山,走向全国的。
周文后来的命运,甚是悲惨。1952年在马列学院的“三反”中,他先是运动的领导人,后来成了“大老虎”,不明不白就死了,胡乱埋掉。直到1975年,才获得平反,迁葬八宝山。1987年,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在北京成立,马烽出任会长,以倡导文学大众化的名义,写了纪念文章,深情怀念周文先生,说是经过周文的运作,“给国统区的人民带去了解放区军民艰苦奋斗的一幅图画”。
马烽和丁玲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让儿子为我在网上买了一本书,马烽写的,叫《马烽与〈吕梁英雄传〉》,2016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马烽与丁玲,我原来只知道两人关系甚深,看了这本书,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比我所知道的还要深。
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举行,会后马烽留在了中国作协(当时称“文协”)创作组。不久之后,丁玲从东北调来,主持作协工作,两人由此相识。真正成为师生关系,并有工作上的交集,则是丁玲创办文学讲习所之后。这个组织,最早的名字是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来改名为中央文学讲习所。马烽和西戎都是第一期的学员,也是工作人员,马烽的职务更高,是讲习所的党支部书记,也就是说,是丁办讲习所的主要助手。
丁玲主持中国作家协会,周扬是中宣部的副部长,分管文学艺术,等于是将两人的不和,从延安时期,经过解放区时期,延续到了建国后。周扬对丁玲发起的第一次攻击,是1955年夏天对《文艺报》办报方针的批判。批判的内容,很快就转到丁玲办文学讲习所,说是意在培植个人势力,搞独立王国。批判会上,马烽看不下去,觉得自己是支部书记,什么事都晓得,便主动发言,为丁玲辩解。有人当场痛斥他是为丁玲抬轿子、吹喇叭。会后领导找他谈话,要他作检查。检查他是作了,但心里是不服气的。待到丁玲被打成右派,虽说作协领导有意安抚他,委以重任,他还是坚辞不干,回到了山西。
此后二十多年,两人没有来往。
“文革”后期,马烽知道丁玲夫妇发配到山西某地劳动改造,也没有去看望。
他是知道感恩的人,一直记着丁玲的恩情。解放初,他与杏绵要结婚了,杏绵的工作单位在保定,是丁玲通过组织关系,将她调到北京,又安排两人住在颐和园的邵窝殿,度了一个星期的“蜜月”。
最最重要的是,马烽绝不相信丁玲是叛徒。1952年夏天,他曾陪丁玲、陈明夫妇去南京参观访问。有一天,丁玲特意领上陈明和马烽,去南京郊区看了当年软禁她的那个地方。马烽的感觉是,革命队伍里,谁会拿上自己的污点给人夸耀?
1978年,马烽在山西已恢复了职务,抽调派赴晋东南地区工作。带车下去,一到长治,听文艺界的同志说,丁玲夫妇劳动改造地址,就在长治市北郊的杖头村。他不去报到,当即驱车去村里,看望丁玲夫妇。
过后不久,丁玲即获平反,但是,仍留下了一个遗憾,就是所谓的叛徒问题,仍然悬着。直到1984年冬天,开第四次作代会前,才由中组部发出文件,算是彻底平反。
再一件最能说明两人关系之深的事是,1986年2月22日,丁玲病危,陈明立即发电报给马烽。马烽得信后,买不上火车票,只好用站台票上了车,由送站的人向列车长讲明情况,才补上软卧,赶到北京,看望了弥留之中的丁玲老人。
鲁迅——周文——丁玲——马烽
1989年冬,马烽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兼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实际掌门人。有人大为惊奇,觉得,怎么也轮不上一个“山药蛋”!
山西更有所谓的耿介之士,找上门去,劝说马烽,这个时节,怎么也不应当进京,担任这样的职务。
我听了只有冷笑。但我不能说什么。后来见有外地的朋友,也持这样的论调,遂觉得,有必要将此中缘由说个清楚,便写了一篇文章,名为《酒醉的探戈》。写是写下了,发?哪儿肯发呢?便一直搁着。1995年冬天,去天津开中国小说学会恢复活动的会议,会上见了《文学自由谈》主编任芙康先生。他对我说,有适合他们发表的作品,但请寄来无妨。回去后,便将那篇文章寄去,第二年第一期便刊发了。文章里,我说了对中国文艺界几十年来的争斗的看法,不是要说服谁,只是想说,这世上有人有这样一种看法——
这种争执,可上溯到30年代初期,先是“左联”的领导权,后是两个口号的抵牾,于是进步文坛上形成了互不相让的两派,鲁迅为一派的主将,麾下有冯雪峰、胡风、丁玲一干人马;周扬为另一派的主将,手也有一干人马。都称得上兵强马壮,气吞万里如虎。从创作实力与社会影响上说,还数前者,从年龄优势与党内地位上说,则要数后者。在上海没有争出个你高我低,一则是鲁迅去世了,再则是抗战爆发了,于是战场又转移到延安。冯雪峰、胡风都没有去延安,去了延安的是丁玲。丁玲去延安的时间最早,大约在1936年秋,先是到了保安,后来才去了延安。周扬去延安在1937年。此时,时势不同而人事又大变,一进了根据地,丁玲就显得势单力薄了。有一个职务上的变化是很有意思的,在保安时,丁玲当选为文艺家协会主任,可是到了延安,成立边区文艺家协会时,周扬就是主任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居然还担任了鲁迅文学院的院长。
接下来说,丁玲在延安待不下去了,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去了山西。回到延安,又因为一篇文章受到批判。解放后,原本应当平安相处的,不料世事有变,使丁玲沦为阶下囚。马烽坚决辞职,退守山西,也就成了是无奈,也是明智的选择。
历史老人,绝对是个文章高手,早在丁玲遭受厄运之前,便埋下了一个深深的伏笔,这便是办了中央文学讲习所。对这一点,我是这样说的:
富有戏剧性的是,在延安办过鲁迅文学院,且以此拼凑了自己班底的周扬,胜利后一朝大权在握,忘了办学校的重要性,竟让丁玲棋先一着。未必是有意为之,起初或许仅是一种责任感,50年代初期,丁玲办了个“中央文学讲习所”,到五七年反右前,接连四期,培养了一大批解放区出身的作家。这些人,有作家的一面,也有革命干部的一面,在中国的政治运动中是不易倒台的,后来大都成为各省区文艺界的铁腕人物。这样一来,当上面的丁玲一干人纷纷落马后,全国的文艺界便呈现了一种奇怪的格局,上面是周扬一派掌权,各地又多是丁玲的弟子掌权,如山西的马烽,安徽的陈登科等。政令不一,各行其是,这也可以解释,为何那些年,有的人在上面备受冷落而到了下面却礼渥有加,有的人在下面平平常常,却会不断擢升。
于此便可以看出,山西的文脉,是怎样一个线索。影影绰绰的,是不是这样几个点,连成了似显不显的一条线:
鲁迅——周文——丁玲——马烽。
我不敢说,我说清了一个问题。我觉得,曲曲折折地,总算说清了我要说的意思。
最后要说的是,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一半是出于公义,一半是出于私情。所谓的私情,不是别的,是三十多年前,马烽和西戎两位先生,将我一家从吕梁山里调到省城,改变了我和我家人的命运。两位老人的晚年,并不怎么顺遂。这世上,总得有人为他们说上两句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