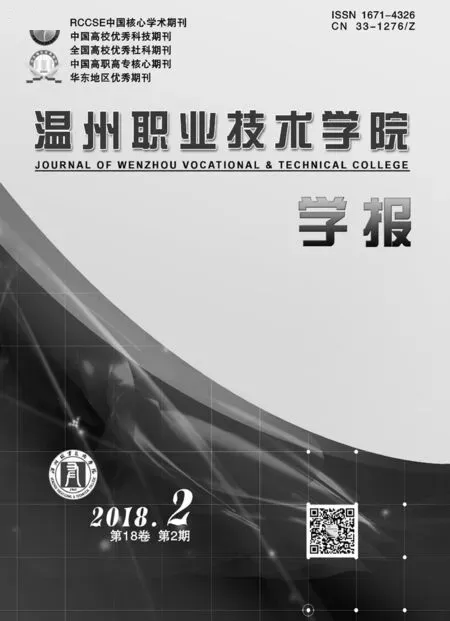《卷耳》中诸“我”的考辨
2018-03-07贺留胜
贺留胜
(台州市明珠外国语学校,浙江 台州 318000)
《卷耳》是《诗经·周南》中的一首诗,学者历来对其在字词句、艺术手法、思想主旨等方面的歧解可谓“繁多”,其贯穿全诗的“我”尤其值得关注。截至目前,已有学者对《卷耳》中的“我”进行研究。其中郭全芝《也谈<卷耳>诸“我”》一文从考察《诗经》时代婚姻制度、社会风习等方面入手,专论全诗诸“我”[1]69,反映了《卷耳》诸“我”的难解性与重要性。关于《卷耳》中“我”的歧解,主要集中于“我”的指代、性别及“我”与采卷耳人的关系。相关研究成果大多从《卷耳》本体之外进行探求(外求法),从《卷耳》本体之内进行探求(内求法)反而被忽略。但基于本体之内的探求,对理解《卷耳》诸“我”乃至全诗的历史性本体意义都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我”的指代
《卷耳》中“我”的指代的歧解主要体现在“我”到底指代多少人(哪些人),大体经历了“三人说”“二人说”“一人说”。这样的论断轨迹,既从整体上反映了《卷耳》的难解,也反映出《卷耳》诸“我”的歧解空间给学者带来巨大困惑。而“‘我’指代一人”所蕴含的“我”的性别问题又给学者带来困扰。
1“.三人说”:“我”至少指代三人
《卷耳》全诗分四章。孔颖达《毛诗正义》申述毛《传》郑《笺》之意,认为“嗟我怀人,寘彼周行”中的“我”(以下简称首章的“我”)乃是指“后妃自我”[2]37;第二章中“我马”句中之“我”乃是指“我使臣”,“我姑”句中之“我”乃是指“我君”[2]38;虽然第三章中没有单独注明“我马”句中之“我”和“我姑”句中之“我”具体指向谁,但由《郑笺》《 孔疏》之意看,“我马”句中之“我”亦当指“我使臣”[2]38,“我姑”句中之“我”亦当指“我君”[2]39-40;第四章中“我马”“我仆”中的“我”也没单独注明,但由《郑笺》所言“此章言臣既勤劳于外,仆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忧矣,深闵之辞”[2]40看,“我马”“我仆”中的“我”,又当全指“我使臣”或“我臣”[2]38。可见,《毛诗正义》认为《卷耳》中诸“我”至少指代三人。其对“我”的理解有以下四点值得注意:一是首章的“我”与后三章中的“我”并不是指同一人;二是同一人称代词“我”至少指代不同的三人;三是“我”有具体的指代对象;四是作诗之人是首章的“我”,即后妃。“三人说”并没有被学者广泛接受。
2.“二人说”:“我”指代二人
“我”指代二人,按诗章人物性别身份划分,又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模糊二人说”。此说以焦延寿《焦氏易林注》为代表。“玄黄虺隤,行者劳罢疲。役夫憔悴,逾时不归。”[3]9(《易林》)“玄黄瘣虺隤,行者劳疲。役夫憔悴,处子畏哀。”[3]228因为焦延寿既没有明确首章的“我”是否指“处子”,也没有明确后三章中的“我”是否全指“行者”或“役夫”。此说为后世学者理解《卷耳》诸“我”留下了极大空间,并极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启导了“杂二人说”的产生,使得一批学者解构了《卷耳》的主旨为“女子怀念征夫说”[4]。“模糊二人说”的主要问题是指代不明,无详细的论证。
(2)“杂二人说”。此说以方玉润《诗经原始》为代表。方玉润认为,“此诗当是妇人念夫行役而悯其劳苦之作”[5]78,但却不认为后二、三两章中的“我”全指思妇之夫,而认为第二章中的“我马”句中的“我”指思妇之“夫”[5]77,“我姑”句中的“我”指“怀人之人自我”[5]77,即“因采卷耳而动怀人念,故未盈顷筐而‘寘彼周行’”的思妇[5]78;第三章中的“我马”句下注“呼夫马曰‘我’,亲之之词耳”[5]77,由此可见,仍以“我马”句中之“我”为思妇之“夫”,“我姑”句中的“我”没有特别注明,当与第二章中的“我姑”句中的“我”所指相同,亦是指代“怀人之人自我”[5]77;第四章中的“我马”“我仆”亦未明确标注,当指思妇之“夫”。《诗经原始》虽然对首章的“我”没有直接注解,但由其内《眉评》所论“因采卷耳而动怀人念,故未盈顷筐而‘寘彼周行’”[5]78可知,是将首章的“我”理解为采卷耳人思妇。由于此说所论《卷耳》全四章中的二、三两章的“我”夹杂指代思妇与思夫,所以可谓之“杂二人说”。此说虽对后世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并未摆脱“三人说”的影响:表面看来“我”指代的人数是少了,“我”所指代的人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但其解构的方法与“三人说”的解构方法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也未受到后世学者广泛认同。
(3)“纯二人说”。此说认为首章的“我”指代思妇,后三章中的“我”纯指代思妇之夫,其代表人物有余冠英、程俊英、钱钟书等。余冠英认为,首章的“我”是“采者自称”[6]8,后三章中的“我”都是“思妇代行人自称”[6]9,也就是说,后三章中的“我”指代的是思妇“想象”中的自己“远行的丈夫”[6]8-9。程俊英等认为,第一章中的“我”是正在采卷耳的思妇——“一位贵族妇女”,后三章中的“我”都是“诗人想象中丈夫的自称”[7]。钱钟书认为,首章的“我”为妇自道,而二、三、四章的“我”为妇代夫言,也就是说,“首章托为思妇之词,‘嗟我’之‘我’,思妇自称”;“二、三、四章托为劳人之词,‘我马’、‘我仆’、‘我酌’之‘我’,劳人自称”,所指“劳人”亦即“征夫”[8]133-134。余冠英、程俊英等的研究成果极有可能是对方玉润研究成果歧读与修正后的结果,而钱钟书对方玉润的观点则有所扬弃。据此可认为,“纯二人说”即脱胎于“杂二人说”。
虽然钱钟书、余冠英、程俊英等都认为,首章的“我”指代思妇,后三章中的“我”纯指代思妇之夫,但钱钟书与余冠英、程俊英等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其关键在于附加的条件不同。为解决同一首诗中同一人称代词“我”如何指代不同的二人(首章的“我”指代思妇,后三章中的“我”纯指代思妇之夫)的问题,余冠英、程俊英等所附加的条件是:“思妇—幻想—她的丈夫”,也就是“思妇自言首章—思妇代言后三章”。对于这种解构条件,钱钟书明确予以批驳:“首章‘采采卷耳’云云,为妇人口吻,谈者无异词。第二、三、四章‘陟彼崔嵬’云云,皆谓仍出彼妇之口,设想己夫行役之状,则惑滋甚。夫‘嗟我怀人’,而称所怀之人为‘我’——‘我马虺隤、玄黄’,‘我姑酌彼金罍、兕觥’,‘我仆痡矣’——葛藤莫辨,扞格难通。”[8]133钱钟书正是看到了余冠英、程俊英等观点的不足。这种解构条件的不足尚不止于此:不符合主体一贯性原则,在结构上导致首章与后三章的断裂或者说断章分层,而断章分层是不可取的。为弥补这种解构条件的不足,钱钟书提出了自己的解构条件:“作者—托言—思妇首章与思夫后三章,亦是‘妇代夫言’”,也就是“作者—托言—思妇自言与思夫自言后三章”。钱钟书的解构条件明显有不妥之处。一是当思妇即为作者本人时,那么“作者—托言—思妇首章与思夫后三章”,也就是“作者—托为思妇自言与托为思夫自言后三章”,亦即“作者—托言—思妇自言与思夫自言后三章”,可解释为“思妇自言首章—思妇代言后三章”。也就是说,当思妇即为作者本人时,钱钟书的“作者托言说”与“思妇代言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种理解就出现在周振甫的论著中。周振甫认为,“嗟我怀人,寘彼周行”中的“我”是“采者女子自称”,后三章中的“我”都是“思妇代远行丈夫的自称”[9]6。周振甫的观点是典型的“思妇代言说”。而他又说:“钱钟书先生《管锥编》解《诗经》的《卷耳》,以先写妇人,后写丈夫,即‘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写法,是对的。”[9]6-7“思妇代言说”正是被钱钟书所痛驳的。二是如果钱钟书的观点成立,那么也就是说同一作品中,同一指称可指代不同对象,那么加上“作者—托言”的条件之后,则《毛诗正义》中的“作者—托言—托为我使臣自言与托为我君自言及或我使臣自言后三章”就也可通,而方玉润的解释亦可通。从表面看,钱钟书的观点确乎很有理论创建性,但其“作者托言说”在本质上仍没有跳出“‘我’指代二人论”的范畴,仍不可取。显然,《卷耳》中诸“我”只能指代同一人。
3.“一人说”:“我”指代一人
“我”指代一人,按抒情主人公性别身份划分,又可分为以下二种情况:
(1)“我”指代思夫。高亨认为,首章的“我”与后三章中的“我”都是指一个“在外服役的小官吏”[10]。郝翠屏等认为,《卷耳》中“我”的指称与《主题新解》中的“我”“为劳人自称,全诗均是以男子口吻写出”[11],首章的“我”与后三章中的“我”所指代的对象是同一人且是男性。虽然众多学者对“我”持男性论,一些学者也能立足《卷耳》全诗来探究,但由于他们更多的还是运用外求法,导致理解“嗟我怀人,寘彼周行”时出现了严重偏差。运用内求法结果显示,“嗟我怀人,寘彼周行”应表示“(她)嗟(嗟叹)我(非她自我) (这个)怀人(怀念意中人的人),寘彼周行”这一旨意[12];从这一旨意语境看,“她”应指采卷耳的姑娘,是“嗟”的施发者[13],“我”则应指一女性。持男性论的学者,尤其是对“我姑酌彼金罍”与“我姑酌彼兕觥”中的“我”持男性论的学者,很大程度上可能出于对女性饮酒的怀疑。方玉润认为,妇人饮酒有“伤大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赞同“饮酒非妇人事”[5]78。实际上,“西周时期农作物的积余催生了酒的酿造,也使酒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14],女性饮酒自然不应是不可能的事。
(2)“我”指代思妇。朱熹认为,《卷耳》首章的“我”与后三章中的“我”都指“后妃”[15]。郭全芝认为:“由诗中‘嗟我怀人,寘彼周行’,‘云何吁矣’等句看来,主人公及诸‘我’应是指一女性。”[1]87郭全芝立足《卷耳》内部的探求得出“我”是女性的结论是可取的,但还不够深入,角度也不够全面。实际上,从全诗抒情的曲笔手法看,“我”亦应指女性。
二、“我”与采卷耳人的关系
《卷耳》中首章的“我”与采卷耳人的关系的歧解主要集中于首章的“我”与采卷耳人到底是不是同一人。
1.“我”与采卷耳人是同一人
首章的“我”与采卷耳人是同一人。周振甫译注《卷耳》首章为“采啊采啊采卷耳,卷耳装不满浅筐。一心思念出门人,搁下浅筐大路旁。”[9]5且注“我”为“采者女子自称”[9]6。黄伦峰认为,《卷耳》全四章中的“我”为“同一男子”,首章叙述的是“该男子在外领兵打仗”,“征战闲暇之时率仆去采摘野菜以补军粮之不足,睹物思人”[16]。可见,黄伦峰认为首章的“我”与采卷耳人是同一人,只不过是男性罢了。相较而言,认为首章的“我”与采卷耳人是同一女性的学者远比同一男性的学者要多,如余冠英[6]8-9、程俊英[17]等学者都持同一女性论。持同一女性论的学者,大多会走入首章的“我”与后三章中的“我”前后分裂的歧途,因而持这种观点的学者都要加上“思妇代言”或“作者托言”的解构条件,否则,至少他们难以解决以下矛盾:如果首章的“我”与采卷耳人是同一人,那么首章的“我”在采卷耳(采卷耳,实际上并不是由“采采”决定的,而这些学者却认为是由“采采”决定的[18]),后三章又说“我”带着仆马酒器前去寄怀思人,或者说盼接意中人,在事理逻辑上产生了矛盾。显然,认为“我”与采卷耳人是同一人的观点是行不通的。
2.“我”与采卷耳人不是同一人
首章的“我”与采卷耳人不是同一人。《毛传》在“采采卷耳,不盈顷筐”两句下注“忧者之兴也。采采,事采之。”孔颖达疏解毛《传》郑《笺》 《卷耳》首章说:“言有人事采此卷耳之菜,不能满此顷筐。顷筐,易盈之器,而不能满者,由此人志有所念,忧思不在於此故也。此采菜之人忧念之深矣,以兴后妃志在辅佐君子,欲其官贤赏劳,朝夕思念,至於忧勤。其忧思深远,亦如采菜之人也。此后妃之忧为何事,言后妃嗟吁而叹,我思君子官贤人,欲令君子置此贤人於彼周之列位,以为朝廷臣也。我者,后妃自我也。”[2]37可见,孔颖达认为,首章的“我”为“后妃”,而采卷耳另有其人。雷庆翼认为,首章的“我”指“征人自我”,而采卷耳的是“征人设想自己的妻子”[19]。这些说法虽蕴含或直接得出的“我”与采卷耳人不是同一人的结论是正确的,但还不是从根本的辨析上得来的,还不够全面深入,不够妥帖自然。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要解决“我”的同一指代的问题,不能使首章与后三章前后断裂分层。二是“我”的性别问题。三是探究全诗的曲笔手法,如果首章的“我”与采卷耳人是同一人,那么“嗟我怀人,寘彼周行”就是“我自嗟我自我怀人,寘彼周行”,也就是“我自我嗟叹我自我这个思念意中人的人,寘彼周行”。那么“嗟我怀人,寘彼周行”就是直笔叙事抒情,与《卷耳》整体上的曲笔手法不协调:立足本诗实际,直笔叙事抒情显然没有曲笔手法更具说服力和表现力。
综上所述,《卷耳》“嗟我怀人,寘彼周行”中的“我”与后三章中的“我”只能指代同一人,且指代同一女性;同时,“嗟我怀人,寘彼周行”中的“我”与采卷耳人不是同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