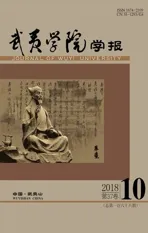晚清洋商奥立芬的商业形象
2018-03-07董利
董 利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自鸦片战争后,商人与传教士作为早期西方来华的两大群体,二者在早期中西关系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教士与商人对鸦片贸易的态度,较少涉及传教士与商人之间的关系。①受革命史范式的影响,来华洋商常常以“鸦片贩子”的形象出现在大众视野,传教士也被视为“帝国主义侵华的帮凶”。②事实上,面对晚清错综复杂的局势,不同商行与教派所采取的商业或传教策略不尽相同。奥立芬就是较特殊的一例,其不仅公开反对鸦片贸易,同时大力资助在华传教事业。这种独树一帜的贸易风格,为其赢得了良好声誉,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其树立良好商业形象。
已故中美贸易史研究的著名学者雅克·当斯(Jacques M.Downs)指出:“同孚商行在贸易、新教在华传教事业以及中美关系上,都非常重要。它的档案在鸦片战争中的被毁和缺失特别令人遗憾。”[1]但令人慰藉的是,仍有不少教会档案保存着关于奥立芬洋行资料,现试以耶鲁大学的奥立芬传记,以及美国海员之友协会 (American Seamen’s Friend Society)、美部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和中国医务传道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的档案资料,力图对广州口岸的洋行研究做一些补充。
一、唯利是图:晚清广州洋商与鸦片贸易
18世纪后期,中英贸易收支极度不平衡。在工业革命强有力的推动下,大英帝国发展迅速,急于开辟海外贸易市场。但在对华贸易中,英国始终处于入超的不利地位,垄断英国对华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对广州的整个进口生意无年不亏”[2],而且贸易额持续增长。英国人对自身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形忐忑不安。直到18世纪末,英国发现印度适合种植鸦片,从而利用印度鸦片改变了这种不平衡状态。在“奇货可居,本小利大”的巨额利润的引诱下,英国政府于1773年确立鸦片贸易政策,予东印度公司以贩运鸦片的专利权。
与此同时,美国也急于发展海外贸易。其原因有许多方面:首先,美国作为一个新生国家,刚刚经历了八年独立战争的洗礼,耗费了国内大部分经济力量。同时,出于经济报复,英国对美国输入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美国经济。另外,欧洲天主教国家对美国这个以新教为主的国家采取敌视政策,西班牙作为传统的天主教国家,严禁新教传教士进入其殖民地境内,禁止美国船只通行密西西比河;荷兰人几乎一样严厉地排斥新教传教士,对美国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3]襁褓之中的美国尚未享受独立的喜悦,就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有着3亿人口的中国成为他们眼中的黄金市场。
美国与英国随即在对华贸易中展开角逐,但与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相比,美国远远落后。1784年美国第一艘商船“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抵达澳门,对华出口人参和皮货,同时从中国进口茶叶、瓷器和生丝等。但不久之后,美国人发现,在这场贸易中毫无利润可言。19世纪初,美国人在土耳其和波斯发现鸦片,其质量虽不如印度鸦片,但是价格低廉,有利于在收入较低的中国市场推广。美国驻广州领事山茂召(Samuel Shaw)以贩卖鸦片是“有利可图的”“中国是很好的鸦片市场”“鸦片走私非常安全”为由敦促美政府参与鸦片贸易。[4]在其号召下,广州的美国洋行,几乎没有一家不从事鸦片贸易。众多美国洋行如普金斯洋行(Perkins&Co.)、旗昌洋行(Russell&Co.)、史特吉斯洋行(Russell,Sturgis&Co.)、 怡 和 洋 行 (Jardine Matheson&Co.)等率先加入从事鸦片贸易的行列。[5]其后威廉·怡和(William Jardine)、罗塞尔(Russell)、约翰·顾盛(J.P.Cushing)、塔尔 博特(Talbot)、魏特摩(Wetmore)等商人也加入其中。[6]鸦片贸易为商人带来丰厚利润的同时,也得到了大多数美国商人的默许。
在美商逐渐扩大对华鸦片贸易的同时,大量美国传教士也相继来华,不少洋行采取“商业+传教”的模式从事贸易。1842年《南京条约》签署后,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和宁波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大量商人和传教士得以在同一时期进入这些地区经商或传教,为二者的交集创造了客观条件。[7]传教士初到中国,往往面临资金短缺,国内差会无法及时应付他们的需求,使得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本国商人。此外,与商业的广泛接触也有助于减少传教工作被排斥的程度。[8]不少传教士为商人提供翻译或贸易信息,以换取他们对传教事业的支持。德国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就曾受雇于鸦片商威廉·查顿 (William Jardine),并为其鸦片贸易充当翻译和向导。[9]怡和洋行在致郭士立的信中公开表示:“鸦片的利润越高,我们就越能更好地安排你的工作,这笔款项以后用来帮助你的传教工作。”[10]首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曾任职于东印度公司长达25年之久。[11]1835年,在华传教士创办马礼逊教育会(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受到许多广州洋商的资助,其中不乏鸦片商人。[12]另一面,这些传教士普遍是受过高等教育,他们来华后往往刻苦学习,精通汉语,同时长期在中国人中间居住生活,对当地的文化有较深的了解,商人常常需要传教士的中文技能与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来开辟贸易市场,这些在客观上为商人提供协助预备了条件。[3]这种互补的需求为二者的合作提供了现实基础。
然而商人这种唯利是图的做法日益成为在华传教工作发展的障碍,也扩大了传教士与商人之间的分歧。[7]一名在伶仃岛从事鸦片贸易的美国船主面对传教士指责时解释到:“我只是跟从那些英国正派商人的先例,有什么错?等我赚足了钱,自然会回家颐养天年。”[6]这位船主的话反应了大多数来华洋商唯利是图的心态,同时也可一窥商人与传教士之间的内在鸿沟。自马礼逊来华后的30年间,在华传教士的传教工作几无进展。一大原因是国人对同是碧眼金发的洋人无法分清,认为所有外国人都是鸦片商,对传教士加以排斥,晚清不少教案的发生是出于对外国人贩卖鸦片的愤怒。1835年,传教士麦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和史第芬(Stevens)租了一艘双桅船休伦号,从伶仃洋沿着海岸线北上航行向国人散发宗教宣传册,然而他们在沿岸的每个地方都受到中国人的排挤,没有找到可以定居的地方,整个海岸都已经被鸦片贩子和走私者占有。[3]
对于这种现状,传教士无不心痛,认为在华鸦片商对传教工作负有责任。[7]麦都思强烈谴责鸦片贸易商,“认为商人的利润,是用中国人民的血肉和生命换来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在摧毁这个国家。”[13]由于不同的来华目的,早期美国来华商人与传教士由最初的相互合作走向了相互对立。
二、独树一帜:奥立芬“商业+传教”的策略
与众多美商从事鸦片贸易的现象不同,奥立芬的特立独行成为当时商业界中的一个特例,其所经营的同孚洋行是当时“唯一一个从未从事鸦片贸易的美国洋行”[14]。而奥氏对传教事业的资助,使他被传教士美誉为是“美国对华传教之父”[15]。这些方面,使他在来华洋商中显得尤为突出。
奥立芬(D.W.C.Olyphant,1789-1851年)是远东地区著名的美国商人。1806年,他在纽约加入金查理(Charles W.King)和塔尔博特(George W.Talbot)的对华贸易公司。[16]1820年他代表雇主到达广州,并于1828年在广州成立同孚洋行(Olyphant&Co.)。与当时在华洋行普遍从事鸦片贸易不同,奥立芬和贸易伙伴塔尔博特创立洋行之初,就确立了避免鸦片贸易和资助传教事业开展的原则。[17]其洋行主要经营“茶叶、丝绸、席子和工艺品”之类的商品。
在鸦片贸易日益被国人诟病的时期,其避免鸦片贸易和资助传教的策略,不仅有利于其树立良好的商业形象,也赢得了大部分在华传教士的好感,使其在鸦片贸易大行其道之时能够逆流而上,在华的商业规模达到数百万美元。1838年8月21日,奥立芬在《广州实录报》上发表了一封反对鸦片贸易的评论,引起热烈反响[18],同时设立资金征集优秀的反鸦片文章,也颇为引人注目。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在公开场合对鸦片问题大多是谨慎地发言,以免受到商人排挤。然而奥立芬不仅公开抵制鸦片贸易,还资助成立培训班,呼吁在华洋商反对鸦片贸易。
奥氏的呼吁得到了部分洋商的回应。金查理在奥立芬的劝说下最终拒绝了鸦片贸易。金查理在其回忆录中称:“奥立芬是我喜乐和智慧的监护者,让我远离诱人的迷途。”[17]在奥氏的影响下,金查理成为反鸦片的得力助手。1832年刚刚回到广州的金查理,邀请了美国公理会的史第芬和英国圣经协会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的代理人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在印度群岛的岛屿之间进行探险航行,拜访当地首领,表明他们将会把现代医疗和传教士带进他们的国家,而不是带来鸦片。[3]在美国的禁酒运动(America’s Temperance Movement)期间,金查理曾发动了一场激烈的反鸦片运动。1837年,他们一同督促所有的商人承诺放弃一个“充满了商业、政治、社会和道德罪恶”[17]的贸易。
除了反对鸦片贸易外,奥氏及同孚洋行更是积极支持在华的传教事业,成为早期美国洋商与传教结合的新典范。奥立芬对传教事业的支持主要有四方面:
首先,资助传教士的来华旅费并提供生活便利。在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身上,处处可以见到奥立芬的身影。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就深受奥氏的影响。1820年5月15日,浦老菲博士在致马礼逊的信中介绍奥立芬说:“奥立芬先生是一位充满爱心和信心的信徒,可以提供给你关于美国教会的许多消息。”[19]借此介绍,马礼逊和奥立芬相识。后来马氏在华的个人生活与传教活动,受到奥立芬的多方资助,两人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14]1829年10月4日,美国首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和作为海员之友协会牧师的雅裨理(David Abeel)乘坐着奥立芬的“罗马人号”商船,到达广州,并为他们提供住所,开始了美部会在华传教的历史。[20]此外,受到奥氏资助的还有史蒂文斯 (Stevens)和其它美国传教士。[16]从1827年起,奥立芬至少资助了50多位传教士及他们家人去中国,并为他们提供住所 “锡安之角”(Zion's corner)。[8]
其次,奥立芬还支持在华的报刊事业的发展。1832年5月,裨治文在奥立芬赞助下创办在华传教主流英文期刊《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该报从1832年5月至1851年12月每月出版,共计20卷,记载了鸦片战争前后20年间传教士关于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调查研究。[21]奥氏在很大程度上担负《中国丛报》的出版费用。[8]与此同时,奥立芬又资助了《英语月刊》《传教士著作集》《中国地区动态》等刊物。[22]1834年成立的中国实用知识传播会(The Society for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和马礼逊教育协会(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等,都与奥立芬的资助有着莫大的关系。[14]
第三,在华传教士的医疗工作也得到了奥立芬的青睐。1838年,中国医务传道会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在广州成立。同年,美部会医疗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乘坐奥立芬的船抵达广州并创办眼科医院。1858年到1877年22年时间里,中国医务传道会每年都在奥立芬的同孚洋行的办公处举行年会。同时,同孚洋行在财政上大力支持中国医务传道会的发展。从1862年到1877年,奥立芬每年向传道会都交纳至少100美元,1867年交纳了150美元,远远超过其它洋行。即便在奥立芬离世后的数十年里,其所创办的洋行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其资助的传教事业。
此外,奥氏还致力于海外传教活动。美国海员之友协会(American Seamen’s Friend Society)是奥立芬较早资助的传教组织。该协会成立于1826年,致力于改善海员的社会地位和道德状况,加强海员的传教工作和宗教活动。奥立芬从1829年起成为该会的长期负责人,他在1837年、1848年,奥立芬每年交纳会费,甚至在他去世后的10年间,每年都有以他的名字交纳会费的记录。截止1837年5月1日,以塔尔博特、奥立芬同孚洋行(Talbot,Olyphant&Co.)名义捐助给该协会的金额达4150美元,奥立芬从1849年到1850年捐赠该协会达2500美元,成为该协会的最大金主。此外,奥立芬还为该协会捐赠建造当地的教堂,供在华的海员与传教士使用[16],并建议协会包租一艘从纽约到广州的船,并为传教士提供在华传教资讯,以配合他们的传教工作,同时,奥立芬用自己的船免费运载传教士到海外传教。[14]其后续资助的美部会是当时美国最大的海外传教组织。美部会全称为美国海外宣教委员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是美国首批的基督教海外传教组织。1829年,在奥立芬的大力资助下,美部会开始派遣传教士来华传教。[5]奥立芬从1831年一直到1837年都是该会的荣誉会员,并且从1838年直到他去世,奥立芬一直是该会的理事会成员。1840年,奥立芬和内森帕金斯(Nathan Perking)等人联名提交一份关爱传教士儿女的提议,建议董事会监护并抚养海外传教士的孩子,以帮助海外传教士的国内家人。
这些活动,对当时面临中国禁教政策、资金不足的早期来华传教士而言无疑提供了巨大帮助。奥立芬同时因为其对传教事业的联系和支持,被美国在华传教士誉为“美国对华传教之父”。[15]
三、探源溯流:独特商业形象的动因
回顾奥立芬的一生和其创办的同孚洋行,其与众不同之处至少有两方面。其一,奥立芬鲜明的反鸦片立场。在广州的众多洋行中,同孚洋行是仅有的少数不从事鸦片贸易的商行之一。拒绝鸦片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失去高额利润,也可能受到其他洋行的排挤。事实上,奥立芬的事业并非一帆风顺,不少在广州的美国洋商对奥立芬的嗤之以鼻,认为其高调的反鸦片立场妨碍了他们的生意。美商拉塞尔(Russell)及其公司与奥立芬的同孚洋行也有特别对立的关系。在一份备忘录中,拉塞尔公司里的约翰默里 (John Murray Forbes)就建议他的同事奥古斯丁(Augustine)要对奥立芬保持“警惕”。[17]然而,奥氏从始至终未染指鸦片贸易。
其二,奥氏对传教事业的资助贯穿其在华商业活动,并涉及到传教士的医疗事业、报刊事业、教育事业和海外传教行动,同时支持传教士的生活开支和国内家人支出等。他在广州的房子多年来是美国传教士的家,他的船源源不断的把传教士送到他们的目的地,而不收取任何费用。[16]奥立芬对传教士的支持可谓是十分周全。而在华传教开支巨大,对奥氏而言是一笔不少的负担。[16]奥立芬对传教事业的热忱贯穿他的一生。他对信仰的坚定和忠实影响了他的后人,他的儿子来中国传教,也表现出同样的慷慨精神,继续资助许多传教士来华传教。
奥立芬长期坚持这种做法有诸多因素:
首先,奥氏对传教事业的支持与其家庭影响不无关系。奥立芬出生于一虔诚的长老会家庭,其父是辛辛那提协会的会员。在1805年他父亲逝世后,奥立芬继承了这一会员荣誉。[16]1812年至1817年,奥立芬在巴尔的摩生活,并在1814年被任命为在巴尔的摩长老教会的长老。[16]他当任过长老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美部会委员、美国海员之友协会主席、纽约医院的一位主管人员。[16]奥立芬作为虔诚的教徒,认为基督徒商人不应单纯为了赚钱[16],商业利益应该屈服于基督教的事业。[14]美部会在对他的悼念词中写道,“为了传教工作,他宁愿牺牲商业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在他的心中,‘基督的事业’都是第一位。”[23]《中国丛报》随后也做了评价:“奥立芬的离开,使传教士失去了一个最热心的支持者和最谨慎的顾问。在得知病入膏肓之后,奥立芬说,‘我不希望为世俗的财富或舒适而活;但为了传教事业,我希望可以活的久一点。’这是他三十年来一直遵循的原则,并不断敦促其他人遵守这一做法。因为他的帮助,我们在所有对华慈善事业中拥有美好见证……在美国,他对海外传教的热心支持,对慈善事业也采取了同样积极的行动。”[23]奥立芬因其对华传教士的卓越贡献,被称为是 “一个披着商人外衣的传教士”[17],被美誉为“美国对华传教之父”。
其次,奥立芬的反鸦片态度与其人道主义精神不无关系。作为一名在华多年的洋商,奥立芬对中国的鸦片问题深有感触。1850年11月23日,面对鸦片贸易横行,他在上海写信道:“那些鸦片商将人挡在生命与光明的入口之外。”[34]反映出其对鸦片贸易的看法。他认为鸦片对清政府而言,是“卑鄙的污垢”“流动的毒药”,对国家和民众造成了经济和道义上的破坏,并且是非法的。[10]基于道德原则,奥立芬致力于反鸦片活动。
最后,奥立芬作为一名早期来华的商人,其主要目的还是进行商业活动,赚取财富,这也是早期美国政府鼓励商人来华进行贸易的目的。但早期美国商人在华的商业活动却受到重重阻碍,迫使商人不等不向传教士寻求帮助。同时来华传教士也有此能力,正如保罗·瓦格(Paul A.Varg)所说:“每一个传教士都是基督教国家制造商的推销员。”[24]因此奥立芬和来华传教士的交往,大力资助在华传教活动,也赢得传教士的好感,开启了商业与传教结合的模式。[10]奥氏经营的贸易规模往往涉及到数百万美元,加之他的管理能力很强,财富通过他年复一年的快速增长。[16]此外,奥立芬的反鸦片活动也为其赢得了一些声誉,从而在商人和民众间中树立起高大正直形象,使其在商业贸易中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也有利于其进行商业贸易活动。
四、结语
早期中美关系时期是一段颇为复杂的时期,大部分的来华美国商人屈从于商业利益,从事鸦片贸易,为中国人民施加了一份沉重的苦难。然而,奥立芬作为一位早期来华的美国商人,其商业活动并不像其他商人一般为利而行,其所创办的同孚洋行与在华传教事业紧密相连,其本人与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关系更非一般。他和其商行形成了“商业加传教”模式,既不符合英国和法国的刻板印象,也没有与美国同胞同流合污,却独自站在鸦片贩运的对立面,并大力支持传教事业。[10]奥立芬就宛如一名披着商人外衣的传教士,其特立独行的形象在早期中美关系中十分突出。这也为我们揭开了早期洋商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一方面,奥立芬这种独特的商业形象,得到了美国教界内人士的崇高称赞,其本人对推动早期美国对华传教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1827年8月6日,当时在广州的奥立芬就写信回国,呼吁美国教会对华传教,他写道:“在中国有亿万没有基督生命的人,他们活在死荫幽谷之中……忽略了中国的福音,也是不够的,我认为美国教会对华的传教计划是件势在必行的事情。[14]奥立芬同时提议,基督教商人的重大事务应该对基督教服从,并且建议将来华的美国商人应致力于对华传教事业。”[14]此后奥立芬对来华传教士的资助与支持体现在方方面面,正如1851年7月24日,美部会纽约观察员对奥立芬所作的评价:“他对远东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明智的头脑,为传教工作做出了莫大贡献,他具有守时、耐心和细心的特性……为促进传教事业而做的事是令人喜乐并伟大的。”[23]同年,中国医务传道会广东分会举办年会盛赞奥氏的贡献。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年会上高度评价奥立芬道,“奥立芬是在华少有的杰出商人和基督徒,他对中国医务传道会的存在和繁荣具有难以估算的贡献。作为对华医务传教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没有一个人能比上奥立芬,人们对他的怀念将存到永远。”裨治文评价他道,“我从未见过奥立芬这样的人,若是我们的商人都像他一样,传教事业将会大大促进。”[15]卫三畏(Samuel Well Williams)称他是“诚心诚意为中国人民的慷慨朋友”。1875年,中国医务传道会主席奈伊(Gideon Nye)在年度汇报中同样对奥立芬表示深挚感谢。[25]
另一方面,我们也该看到作为美国来华的商人奥立芬,尤其在早期中美复杂的外交环境下,其在华的经商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商业交往活动。无论是传教士还是商人,他们都是普通的西方人,在自己的国家与中国发生利益冲突之争时,他们会在思想和行动上更容易倾向于自己的国家,较少有人能超越民族和国家意识而采取公正、客观的立场。在华美国商人奥立芬所资助传教士的一系列传教活动,例如办报刊、出版社、开设学堂和办医院,这都是以传扬西方的社会文明来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与此同时,来华美国商人与传教士之间也都有着某些共同目标,即不仅扩展美国的商业利益,而且也要把美国文明传遍到全世界。因此,奥立芬在华独特的商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美国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冲击,但客观上也对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影响。
注释:
① 相关著述参见王立新:《近代基督教传教运动与美国在华商业扩张》,《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何大进:《19世纪中叶美国舆论、传教士和商人对鸦片战争的反应》,《世界历史》1998年第2期;吴义雄:《基督教道德与商业利益的较量——1830年代来华传教士与英商关于鸦片贸易的辩论》,《学术研究》2005年第12期;顾梦飞:《早期来华传教士活动特点及其影响——以马礼逊和东印度公司的关系及其参与英国对华外交政治为例》,《金陵神学志》2007年第1期;纳扬·昌达:《绑在一起:商人、传教士、冒险家、武夫是如何促成全球化的》,刘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 ;HADDAD J.R.:America's First Adventure in China:Trade,Treaties,Opium,and Salvation,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13;许晓冬《传教士与早期中美贸易关系》,《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② 相关论述参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龚缨晏:《浙江早期基督教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10年;罗冠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史实述评》,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