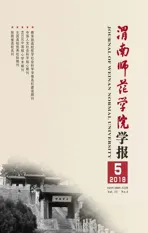《史记·货殖列传》与《汉书·地理志》地理风俗记载关系考论
2018-03-07叶文举
叶 文 举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史记·货殖列传》虽然主要是记载货物交易、表达司马迁经济思想的重要篇章,“就其内容来说,实可说是我国古代经济地理学的创例”[1]14,但司马迁在涉及各地材物分布的同时,也谈到了各地地理民俗的特点,并且作了有意识的分区。后来班固《汉书·地理志》则彰明其目地对各地风俗进行了分区,对各区的风俗特点加以细致地分析、归纳。笔者在研读这两篇传记时却发现两者在记载上有许多共通之处,只是《地理志》记载地理风俗的部分比《货殖列传》更为丰富、细腻。笔者认为,《地理志》在地理风俗的文字记载、结构框架和基本思想上继承了《货殖列传》,并结合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加以丰富、发展,班固自己的创建可能并不是很多。研究者多注重《地理志》的贡献*如王成组认为,《地理志》“由于许多内容涉及这些封国的古代历史,就带有古代历史地理的意义。这一特点超出《汉书》自己规定的断代限度,而填补了《史记》在地理志方面的空白。”参见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先秦至明代),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3页。这一论断不完全符合客观事实,《史记》虽未有“地理志”专名,然《货殖列传》却有较为系统的历史地理记载之实,故王氏所云《汉书》“填补空白”之语显然有点偏离本质上的事实。,而对其材料来源讨论不多。说到在地理志方面的贡献,就《史记》而言,学者们也多注意《河渠书》的成就而不太关注《货殖列传》在风俗地理方面的业绩。本文主要针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甄别《地理志》地理风俗部分的创新性,从而重新定位《地理志》。
一、《地理志》对《货殖列传》记载的沿用与改写
曾有论者根据《货殖列传》认为司马迁将地理风俗分为关中、三河、赵地、燕地、齐地、邹鲁、梁宋、夏地、楚越九个区域来描述,而班固《地理志》则分为秦地、魏地、周地、韩地、赵地、燕地、齐地、鲁地、宋地、卫地、楚地、吴地、越地十三个区域*关于两汉民俗地理区域的划分,请参见王大建《两汉民俗区研究》,《山东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这种分法大致是正确的。这两篇传记中有些区域名称虽然不同,但实际上就是一个地域,如关中与秦地,都是指以长安为中心的区域。通过比照,笔者发现在同一地域地理风俗的记载上,班固与司马迁的看法极为相近,表现在文字形式上非常雷同。笔者以对照的方式将两者记载的文献胪列于下:
(一)秦地(关中之地)
公刘处豳,大王徙歧,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地理志》)
(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歧,文王作豊,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货殖列传》)
(二)魏地、周地(三河之地)
魏地……其界自高陵以东,尽河东、河内……河内本殷之旧都……康叔之风既歇,而纣之化犹存,故俗刚强,多豪杰侵夺,薄恩礼,好生分。……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周人之失,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不好仕宦。(《地理志》)
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迁俭习事。(《货殖列传》)
(三)赵地
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跕躧,游媚富贵,徧诸侯之后宫。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其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钟、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气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时,已患其剽悍,而武灵王又益厉之。故冀州之部,盗贼常为它州剧。(《地理志》)
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北贾赵、中山,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悲歌忼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治,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徧诸侯。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货殖列传》)
(四)卫地
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而野王好气任侠,有濮上风。(《地理志》)
郑、卫俗与赵相类。……濮上之邑,从野王,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货殖列传》)
(五)燕地
蓟,南通齐、赵,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上谷至辽东,地广民希,数被胡寇。俗与赵、代相类,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隙乌丸、夫余,东贾真番之利。(《地理志》)
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冦,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货殖列传》)
(六)齐地
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临淄,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中具五民云。(《地理志》)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货殖列传》)
笔者按:太史公在《货殖列传》的序言中,曾以姜尚为例,说明经济发展对人口迁徙的影响,其云:“(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繈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班固则对文字稍加改变,将其整合到对齐地专区地理风俗的解说中去,其曰:“古有分土,亡分民。太公以齐地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故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
(七)鲁地(邹鲁地)
周兴,……其民有圣人之教化……言近正也。濒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是以其民好学,上礼义,重廉耻。……今去圣久远,周公遗化销微,孔氏庠序衰坏。地陿民众,颇有桑麻之业,亡林泽之饶,俗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地理志》)
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货殖列传》)
(八)宋地(梁宋之地)
昔尧作游成阳,舜渔雷泽,汤止于亳。故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能恶衣食,以致蓄藏。(《地理志》)
(九)楚地(楚越之地)
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啙窳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地理志》)
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羮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货殖列传》)
从上面《地理志》和《货殖列传》所进行的对照情况可以发现,《地理志》的地理风俗部分在文字上有直接搬抄《货殖列传》的痕迹,尽管《货殖列传》并不是专门记载地理风俗的专记,但其中关涉了地理风俗的内容,这些内容基本上为班固所承继。不可否认,班固有时在文字上对《货殖列传》稍加改造,并对《货殖列传》中相对概括性的语言进一步加以了丰富、解释,偶尔也有对《货殖列传》语言进行简摄、归纳的现象。细而言之,有下列一些情况需要注意:
第一,班固有时在文字形式上基本沿袭了太史公之文,只是在用字上稍作改变而已,一般是用同义词或近义词替代《货殖列传》中的用字。如在秦地地理风俗的记载中,将《货殖列传》“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歧”中的“适”改为“处”,“在”改为“徙”,从意义上来说,就是将《货殖列传》的两个动词调换了一个位置。后面将“关中之地”换成了“秦地”,实为一地,“什居其六”就是“居什六”之意。再如燕地地理风俗的记载中,将《货殖列传》中的“民雕捍少虑”改成是“其俗愚悍少虑”,“北邻乌桓、夫余”中的“邻”改为“隙”,两字意思相似,皆为靠近之意。还有一些属于异体字或古今字的问题,如“邠”和“豳”,“豊”和“酆”,“屣”和“躧”等字。*唐颜师古曰:“躧字与屣同,屣谓小履之无跟者也。”请参见《汉书》卷二十八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55页。其他类似的情况,上面所胪列文献中两文一经对照,相信读者一眼就可以察之,笔者不再一一赘述。
第二,班固有时还对《货殖列传》的文字记载进行了语序上的换位或语法上的变动。如《货殖列传》记载赵地地理风俗时,说女子“游媚贵富,入后宫,徧诸侯”,班固则云:“游媚富贵,徧诸侯之后宫”;《货殖列传》云:“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班固则将其语序加以变动,“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意义完全一致。又如《货殖列传》记载鲁地风俗时说道:“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而《地理志》则云:“地陿民众,颇有桑麻之业,亡林泽之饶,俗俭啬爱财。”意思一样,也仅仅是对语序稍加调整。再如在对宋地地理风俗的记载上,《货殖列传》说“舜渔于雷泽”,《地理志》则云“舜渔雷泽”,省略了“于”字,而意思则同。
第三,班固有时对《货殖列传》的文字稍加整合,或删减,或添加,但基本上不改变《货殖列传》的意义。如在对秦地地理风俗记载时,《货殖列传》说:其民“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说“地重”为“言重耕稼也”,而“重为邪”则是:“重者,难也。畏言不敢为奸邪。”请参见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一百二十九,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5151页。,而《地理志》则曰:“好稼穑,务本业”。“务本业”者,意指老百姓以种植五谷为本事,以土地为生,不为奸邪之事,即归纳“殖五谷,地重,重为邪”为一句话,意旨却相同。又如记载赵地地理风俗时,说此地男子“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治”,《地理志》对其进行了整合,曰:“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再如《货殖列传》记载鲁地地理风俗,说其民“俗好儒,备于礼”,并云:“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地理志》则曰:“是以其民好学,上礼义,重廉耻。……今去圣久远,周公遗化销微,孔氏庠序衰坏。……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意思是一致的,谈的都是此地民风由淳朴好礼到好商重利作奸的变化。
第四,班固有时还对《货殖列传》中极其简要的话语加以解释,分析其具体的内涵。《货殖列传》毕竟主要不是记载地理风俗的内容,故语言有时略显简洁。《地理志》则对其进行了解释性地补充、说明。如《货殖列传》记载秦地(关中之地)汉代的风俗特点时说道:“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说明了“地小人众”、人口迁移对地方民俗的影响。但司马迁并未对“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的人口来源具体加以说明,《地理志》则对其进行了补充,其曰:“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这样就使读者详细了解到汉代初年长安迁徙人口的组成部分,从而理解为什么会产生风俗不纯、民去本事末的现象。
同时,还有一种情况也当引起我们特别的兴趣: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地理志》在分区的大致顺序上和《货殖列传》庶几一致,这也显示了班固《地理志》在描述地理风俗这一部分内容上,基本承袭了太史公行文的框架,尽管名称上略有区别;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地理志》在分区上更为细化,但这种细化和《货殖列传》关系同样也较为紧密,它的细化主要表现为将《货殖列传》中亚地理风俗区单独列为一个分区,从而增加了四个地理专区。如《货殖列传》将三河之地作为一个专区,并未分别介绍河东、河内、河南各自风俗的特点,而是阐述了它们作为一个风俗专区的共同特征,即“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迁俭习事”。而《地理志》则将其分为两个专区即魏地和周地,并分别对其风俗的特点加以阐说,没有完全袭用《货殖列传》关于其风俗特点的介绍。《地理志》言魏地“尽河东、河内”,而周则是“今之河南”。关于魏地河内的风俗,《地理志》云:“康叔之风既歇,而纣之化犹存,故俗刚强,多豪杰侵夺,薄恩礼,好生分”,关于魏地河东的风俗则曰:“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其民有先王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与《货殖列传》所介绍三河之地的风俗不太相类,这可能是《地理志》和《货殖列传》唯一一处差别较大的。而关于周地的风俗,《地理志》云:“周人之失,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不好仕宦。”《地理志》只不过对《货殖列传》的分区作了更细致的划分和总结。此种情况更有意味的是,《货殖列传》关于一些地理风俗区的亚分区在《地理志》中单独被列为一区时,太史公总结其特点的文字记载却直接为班固所使用,如《货殖列传》将楚越之地分为西楚、东楚、南楚、越地四个亚区,并云:“越楚则有三俗”,而《地理志》则将南楚专列为一区,名曰吴地,对其特点的介绍也基本上沿袭了《货殖列传》,只是在文字的次序上稍微做了些调整,我们将两者加以比较就可以得知,《货殖列传》云:“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在《地理志》则云:“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其失巧而少信……吴东有海盐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豫章出黄金,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江南卑湿,丈夫多夭。”可以看出,两篇语言相近,只是在语序上做了一些变换而已。同样,《地理志》将《货殖列传》中的越地亚区单独列为一个专区,《货殖列传》云:“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地理志》则云:“粤地……今之苍梧、郁林、合蒲、交址、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处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文字记载也极为相似。*《地理志》有时把春秋时越国误入粤地,它在粤地的限定上,虽然说明了“今之苍梧”等九郡,“皆粤分也”,但后面又提到“其君禹后……后二十世,至勾践称王……后五世为楚所灭,子孙分散,君服于楚”等内容,这是越国的事情,当放在吴地一段内描述才算正确,而班固却将它误入到粤地中去。当然,后面提到的“秦南海尉赵佗亦自王,传国至武帝时,尽灭以为郡云”,史称南越王,说的正是粤地之事,《史记》和《汉书》皆设《南越传》。可见粤与越这两个地名,在秦汉时是非常容易淆乱的。再如《货殖列传》中的夏地,实际上是《地理志》中韩地的主干区域,故《地理志》关于韩地地理风俗的介绍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货殖列传》,《货殖列传》论及夏地的风俗时说到:“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而《地理志》在介绍韩地地理风俗时说到:“韩分晋得南阳郡及颍川……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夏人上忠,其敝鄙朴。……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故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藏匿难制御也。宛,西通武关,东受江、淮,一都之会也。”两相对照,后者明显是在沿袭前者的文字记载,只是稍稍做了修正而已。
从上面所做的比照及其分析,不难看出,无论在地理分区的基本框架上,还是在地理风俗的基本思想上,乃至在文字形式上,《地理志》都有袭用《货殖列传》的明显痕迹。这当然是史家记载传承的一种表现,也许为了避免文字记载上过度的雷同,班固在用字上,抑或在语序上做过一些改动或调整,但这并不影响《货殖列传》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思想。故而,我们可以确凿地认为,尽管司马迁没有做过专门的地理风俗专记,但《货殖列传》关于地理风俗的文字记载却成为班固《地理志》部分基本内容的重要来源,由此可见,作为“史家之太祖”的太史公其影响是何等的广泛。令人质疑的是,尽管班固在地理风俗的研究上作了一些发展(下文笔者尚有专论,暂且按下不表),但在《地理志》关于地理风俗的序言中,他只字未提太史公,班固说:“汉承百(年)[王]之末,国土变改,民人迁徙,成帝时刘向略言其(域)[地]分,丞相张禹使属颍川朱赣条其风俗,犹未宣究,故辑而论之,终其本末著于篇。” 师古曰:“辑与集同。”[2]1640换而言之,班固自己认为《地理志》的撰写是在综合了刘向划判地分和朱赣缕析风俗的基础之上,糅合自己的观点而成,班氏未言司马迁的影响,显然是不够客观、公允的。
二、《地理志》对《货殖列传》地理风俗思想的承袭与发展
《地理志》的地理风俗记载搬抄了《货殖列传》的大部分文字,毋庸置疑,班固在沿用了《货殖列传》文字记载的同时,也就认同了其中所蕴含的地理风俗思想,因此我们有必要先讨论一下《货殖列传》所包含的地理风俗思想。《货殖列传》尽管主要是讨论经济地理的相关问题,但司马迁涉及了各地地理风俗的状况,虽寥寥数笔,却言简意赅,弥足珍贵。他首先注意到了自然地理环境对各地风俗的影响。《货殖列传》的分区主要是根据各地自然地理以及风物特点,也即人类所生存自然环境的不同,由此论及自然环境对各地风俗、人们的习性所产生的影响,如关中之地,“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其民)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因为它有广阔而肥沃的土地,都是上好的良田,故老百姓安于以农事为本,也就“重为邪”,不愿意去做不法勾当,故其民风淳朴而本色。而处于狭小而贫瘠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习性也许与此就大为迥异了。如三河之地,“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同样,“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土地本来就很少,又极不适于种植庄稼,再加上聚集了极度膨胀的人口,那么老百姓为了能够生存,只有心存机心,做着偷奸取巧的事,如此就易于“纯白不备”[3]318,心性不定,其俗则难免纤巧而急躁。自然环境有时甚至会对人的生命、生存状况产生影响。《货殖列传》在谈到南楚风俗时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而楚越之地总体状况是:“地广人希,饭稻羮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是自然环境对人们生存方式影响的显著表现。不过自然环境并不是决定地方习俗和人们习性的唯一关键因素,社会环境同样是影响它们的重要因素,甚至可以在历史的演变中改变原有自然环境所促成的习俗,司马迁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也说明了司马迁看到了人们的习性既有其延续性和稳定性,也有它动态变化的特性,这是司马迁史识的伟大之处。当然,我们从《货殖列传》的记载中可以看到,社会环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君王的政教,司马迁非常注重此因素的作用,他多次谈及政教对风俗的影响。如关中之地:“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豊,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三河之地:“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赵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邹鲁之地:“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夏地:“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国君作为一国之主,实际上是起到模范的作用,引领风气,故对地方习俗有很大的导引力。又如军事状况,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赵地的边界,“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懻忮,强直而很也”,是说人的性格勇猛而凶狠。请参见《史记会注考证》卷一百二十九,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5153页。,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云:“(羯羠)皆健羊也,其方人性若羊,健捍而不均。” 参见《史记会注考证》卷一百二十九,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5154页。,正因为这个地方的人民经常受到胡人的侵扰,他们就需要防卫,需要战斗,故也就形成了他们“懻忮”“好气”“任侠”的特性。处在军事边境的位置同样对燕地人的性格特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冦,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再如人口迁徙,它对地方习俗和人们的习性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司马迁谈到关中之地长安风俗时,就曾论及人口迁移对人们习性的作用问题,他说:“武、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迁徙的人口众多,而且贫富贵贱参差不齐,成分复杂,人们为了生存,不免就有了机巧之心,也就不会太自守本分了。司马迁在论及夏地的风俗时,同样说到了人口迁移对地方风俗的影响,“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既然是不轨之民,那么人员自然就会庞杂,而且好滋事生非。
《地理志》既然在文字形式、分区框架上基本袭用了太史公的《货殖列传》,那么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太史公地理风俗的思想。正是基于此,笔者认为,《地理志》对古代地理风俗的研究上并无太多的创新贡献。如果说《地理志》在地理风俗的研究上尚有业绩的话,它主要在理论概括和具体细节的补充上做出了一些成就。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理志》第一次对“风俗”一词进行了理论上的界定。毫无疑问,这种界定是在对“风俗”二字进行微殊的划分上完成的。《地理志》写道:“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地理志》认为“风”和“俗”是有细微差别的,用今天的话语来区分,就是“风”系水土等自然环境,这是静态的客观存在;而“俗”指的是君王政教等社会环境,这是动态的,具有很大的主观性。这说明《地理志》对“风俗”的形成原因是有自觉、清醒的认识,即它是主客观因素的相互影响下形成的。不过,笔者仍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点在《货殖列传》中已有萌蘖,《货殖列传》说:“至若诗书所述……使俗渐民久矣。”并且在讨论各地风俗时具体加以了运用,只是太史公未做理论上的概括和定义。
第二,《地理志》在地理风俗的分区上更为细致。对此,上文已经进行过一些讨论,班固在《货殖列传》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分离、调整,将原来的九区再次细化为十三区,并且在亚区的分类中作了一些增加,如秦地风俗区,《地理志》在《货殖列传》的基础上增加了河西四郡亚风俗区,风俗特点是“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古)[故]凉州之畜为天下。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这一亚风俗区在《货殖列传》中并没有,《地理志》添加了进去。班固之所以能够如此细致地划分,一是与其生活的年代有关,他毕竟比司马迁晚了一百余年,其间地域的分化也愈加明晰,班固自己也说:“汉承百(年)[王]之末,国土变更,民人迁徙”,故而在司马迁的时代,有些情况没有发生,司马迁也就没有办法能够了解;二是班固在写作《地理志》时已经有了成文的地理域分的著作可以参考,班固自己就说:“成帝时刘向略言其(域)[地]分,丞相张禹使属颍川朱赣条其风俗……故辑而论之,终其本末著于篇。”这就是说,班固更细致的分区很可能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第三,《地理志》在考察地理风俗所形成的社会环境因素时,涉及的因素大抵沿袭了《货殖列传》,但也稍稍旁及了其他方面,虽然不多,也可见出班固辨识的敏锐性。尤其是《地理志》察觉到游宦风气,乃至士风、文学创作对风俗的影响,这是非常不易的。如在介绍秦地巴、蜀亚风俗区在汉初的特点时写道:“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相如以文辞游宦成功,巴、蜀一带向风而行,影响了这一带的风俗,产生了许多的辞赋家。又如《地理志》谈及韩地韩都颍川风气时说:“士有申子、韩非,刻害余烈,高(士)[仕]宦,好文法,民以贪遴争讼生分为失。”士人好法定名,直接影响到老百姓,他们更容易聚讼纷争。再如《地理志》论到了吴地风俗区时说:“寿春、合肥……亦一都会也。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其失巧而少信。”由屈原肇始的《楚辞》创作,后来文人竞相模仿,却很少是出于作家主体的“发愤以抒情”(屈原《九章·惜诵》)[4]121,走向了炫耀词采的末流,也影响了其品格,故“失巧而少信”。这些因素是《货殖列传》所未加考虑的。
第四,《地理志》在分析地理风俗时,开创了“诗史互证”研究方式的先河。这一点也是《货殖列传》没有注意到的。《地理志》在阐述某一地的风俗史时,多引《诗经》中的风诗之语来印证自己的观点,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大的历史事件在史传中也许有所反映,但在风俗的具体细节上,包括名物、地理、人的情性等方面,史传常常无暇顾及,而这往往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汉何休曰:“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参见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卷十六,《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8页。、“多出于里巷歌谣”*朱熹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考之于《诗经》之《风》诗,其观点大抵是正确的。参见朱熹《诗集传·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的《诗经》尤其是风诗当中,会得到侧面的反映,也是最真切的体现。《地理志》能够注意到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地理志》几乎在每一地的风俗介绍时,都有“诗史互证”的现象,兹举几例以明之。如秦地:“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髙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臷》《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就是分别引用了秦风的《小戎》《无衣》《车辚》《四臷》等篇章来说明此地家居风俗及人们射猎习气的真实性,这无疑也是很可靠的文本内证。再如《地理志》在谈到魏地河东之地“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人们有富于理性思考的特性,又引用了诗歌加以旁证,“故《唐诗》《蟋蟀》《山枢》《葛生》之篇曰:‘今我不乐,日月其迈’;‘宛其死矣,它人是媮’;‘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皆思奢俭之中,念死生之虑。”借以说明此地的人们喜欢对生死作思考,好发议论,也就印证了《地理志》所说“君子深思”的判断。《地理志》在男女情性的看法上也常常引用风诗加以佐证,如在谈到韩地郑国的风俗时写道:“土陿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则引“《郑诗》曰:‘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又曰:‘溱与洧方灌灌兮,士与女方秉菅兮’,‘恂盱且乐,惟士与女,伊其相谑。’此其风也”,借用《郑风》之《出其东门》和《溱洧》两诗的描写说明了郑人“好淫”的品性。
三、对《汉书·地理志》地理风俗部分价值的重新定位
综而论之,笔者认为,班固《地理志》关于地理风俗记载的部分在文字形式、地理风俗分区的框架以及地理风俗思想上多循依司马迁的《货殖列传》,颇有因人成事的成分。即使上文所讨论《地理志》地理风俗思想的一些贡献时,也未必完全是班固的创造。班固既然说《地理志》这一部分内容是对刘向、朱赣成果的“辑而论之,终其本末”,那么《地理志》地理风俗部分比《货殖列传》多出的内容是否因袭了刘、朱二氏的论著,也未为可知。耐人寻味的是,现在能够看到较早对地理风俗之书进行评价的《宋书·律志序》说:“朱赣博采风谣,尤为详洽。”[5]203而只字未提《地理志》。而在关于地理方志书籍的评述中,如《元和郡县志》《吴郡国经续记》等也未尝论及。《隋书·经籍志》则云:“史迁所记,但述河渠而已。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隋书·经籍志二》只是注意到了《河渠书》在地理志上的贡献,其实《货殖列传》对后世地理风俗的记载和研究影响更大,《隋书》的结论稍有偏颇。参见《隋书》卷三十三,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88页。,认为班固是依照刘、朱二氏的记载而作《地理志》。可惜,此二人的地理著述已经亡佚,故笔者很难将《地理志》和它们进行比勘。从《地理志》对《货殖列传》的搬抄可以类推,它比《货殖列传》所增加的内容,也极有可能沿用两人的著述而稍加润色。由此,也许可以推断,班固在《地理志》关于地理风俗部分上创新并不是很多。宋代郑樵说班固是“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并云:“后世众手修书,道旁筑室,掠人之文,窃钟掩耳,皆固之作俑也!”[6]1虽然刺之过激,但却也道出班固《汉书》在沿袭他人之文的事实,《地理志》地理风俗部分的记载就是一个鲜明体现。
当然,如果避开《地理志》因循前人文字记载这个问题不谈(史书的编撰可能也存在着“述而不作”的倾向),就司马迁和班固的地理风俗思想比较而言,班固似乎更看重社会环境对人们习性的影响,借用班固对“风俗”二字的定义,后天性“俗”的影响比先天性“风”的影响更大,也更为重要。在班氏的视野下,政教也是后天性“俗”的重要元素,政教尤其是君上的行为对人的习性起到了引导的作用,《地理志》花了大量的笔墨描述了这一方面的内容。如燕地,“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待宿,嫁取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战国以后燕地人的习性显然就是受到了燕太子丹行为的影响而形成的。再如班固谈到齐地风俗时,“始桓公兄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齐襄公的行为通过政令的方式直接促成了齐地如此怪异风俗的产生。吴地寿春到汉代的风俗也比较怪戾,“初淮南王异国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 如淳曰:“得女宠,或去男也。”臣瓒曰:“《周官》职方云:‘扬州之民,二男而五女’,此风气非由淮南王能使多女也。”颜师古注曰:“二说皆非也。《志》亦言土地风气既足女矣,因淮南之化,又更聚焉。”[2]1668颜氏之意是说淮南王的教令助长了吴地重女的风气。这与淮南王刘安通过召集众多女子,使之嫁给来吴国的人才,从而达到聚集并安抚人才、为之所用的特别举动有直接的关系。《地理志》注意到了人们的习性有其稳定的一面,但这只是相对的,在历史的延展中,它可以渐渐地被改变,而这种改变很大程度上和政教乃至君上的行为有内在的联系,班固作了详尽的考察。一方面,本来好的习俗可以慢慢地颓坏,如鲁地早期因为“有圣人之教化”,“是以其民好学,上礼仪,重廉耻”,但后来随着这种教化的丧失,人们的习性也开始有所变化,“今去圣久远,周公遗化销微,孔氏庠序衰坏。地陿民众,颇有桑麻之业,亡林泽之饶。俗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丧祭之礼文备实寡”。另一方面,人们坏的习性随着良好政教的实施也能潜移默化地得到改变,如韩地,战国时本来是“好文法,民以贪遴争论生分为失”,但到了汉代,“韩延寿为太守,先之以敬让;黄霸继之,教化大行,狱或八年无重罪囚。南阳好商贾,召父富以本业;颍川好争讼分异,黄、韩化以笃厚”,班固借用《论语·颜渊》之言感叹道:“‘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信矣。”在相同的客观条件下,政教实施的不同,其风俗也就可能有所差别,如同样是人口迁徙,同样是属于秦地,汉代长安诸陵则“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而汉代河西四郡,“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这样一经比较,也许可以看出《地理志》记载重在强调政教对风俗影响的用意之所在。班固作为今文经学家,思想充满了极现实的致用性,故他更强调政教的作用。无怪乎,他在《地理志》中喟叹惜:“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2]1660
[1] 翟忠义.中国地理学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
[2] 班固.汉书: 卷二十八下[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 沈约.宋书:卷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4.
【责任编辑朱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