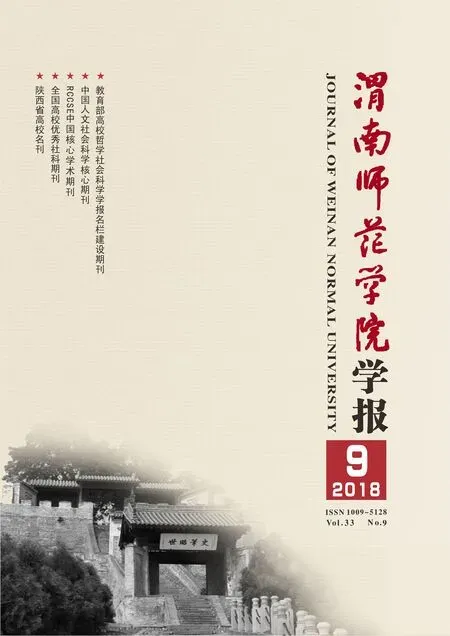《史记》三家注之特点比较
2018-03-07杨炜
杨 炜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67)
一、《史记》三家注成书背景分析
据《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史记》写成后,“藏之名山,副在京师”[1]4027,司马迁殁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2]2737。魏晋时期,《史记》流传逐渐稍广。晋末徐广研核众本兼作训释,作《史记音义》。刘宋裴骃增演徐氏,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作《史记集解序》;至唐代,司马贞、张守节二人在裴骃的基础上探求异文,考证史实,训释音义,分别作《史记索隐》与《史记正义》,《史记》的三家注释由此具备,为《史记》通行文本奠定了基础。“作为《史记》传本,宋时出现了将《史记集解》《史记索隐》及《史记正义》三家的注本一并散入《史记》正文下的刻本,这种以合注形态刊行于世的《史记》版本,即《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俗称《史记》三家注本。”[3]318
(一)《史记集解》成书概况
《史记集解》,南朝宋裴骃著。裴骃(生卒年不详),字龙驹,河东人,出身于著名世家大族,其父乃著名史学家、史注家、《三国志注》之作者裴松之。据《宋书》记载:“上使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既成奏上。……子骃,南中郎参军。松之所著文论及《晋纪》,骃注司马迁《史记》,并行于世。”[4]1701父亲裴松之注释《三国志》,取得了辉煌成就,裴骃注解《史记》亦是情理中事。
《史记集解》的问世,除家学之风的影响外,也离不开特殊的时代背景。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失去两汉独尊的地位,经学急剧衰微,文学、玄学、艺术得以发展,尤其是史学,更是脱离经学而逐渐走向独立并得以蓬勃发展。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两晋六朝,百学无秽;而治史者独盛,在晋尤著。读《隋书·经籍志》及清代丁国钧之《补晋书·艺文志》可见也。故吾常谓晋代玄学之外,惟有史学;而我国史学界,亦以有晋为全盛时代。”[5]25史学的兴盛,使《史记》愈加受到人们的推崇。
裴骃的《史记集解》成为后世研读《史记》不可或缺的范本,唐代张守节在其《史记正义序》中借班固评《史记》的话,说其“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4057,给予裴骃高度赞扬。朱东润先生在《裴骃史记集解说例》中提到:“今所传《史记》注本之最古者,独有裴骃《集解》,其后刘伯庄、司马贞、张守节诸家训释《史记》,兼为《集解》下注,此则比毛传、郑笺,同为不刊之作矣。”[6]54可见,《史记集解》是裴骃继裴松之注《三国志》后的又一史籍注释力作。
(二)《史记索隐》成书概况
东汉末年至隋唐时期,为史书作注者不胜枚举。除以裴骃为代表的对《史记》作注外,亦有裴松之所注《三国志注》以及以颜师古为代表的注释《汉书》者等等。他们对史书的研究、注释,促进了史学的发展。初唐时期刘知几编纂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更是将史学的发展推向了顶峰。然如刘知几所说:“次有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立微不能自达。庶恁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词补前史之阙,若裴松之《三国志》,陆澄、刘昭《两汉书》,刘彤、晋刘孝标《世说》之类是也。”[7]219即使如唐初取得巨大成就的颜师古所注的《汉书》,亦只是“翼赞旧书,一遵轨辙,闭绝歧路”[2]3215。可知当时的史注,亦鲜有人敢于直言批判、质疑所注之书的,直到唐开元间的司马氏《史记索隐》出现,才改变了这种情况。
《史记索隐》乃司马迁的后人司马贞所撰,司马贞,新、旧唐书均无传。据《史记索隐序》载,司马贞,唐河内人,曾为朝散大夫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后来又做润州别驾。“家传是书,不敢失坠”[1]4044,因家传影响,司马贞对《史记》颇事钻研,初愤发而补《史记》,“续成先志,润色旧史”[1]4048,然叹此“千载古史,良难间然”,唯“退撰《音义》,重作赞述”,即每篇末之“索隐述赞”[1]4046。《史记索隐序》中赞《史记》:“年载幽邈,简册阙遗,勒成一家,其勤至矣。”《太史公自序》篇末“索隐述赞”云:“太史良才,寔纂先德。周游历览,东西南北。事核词简,是称实录。报任投书,申李下狱。惜哉残缺,非才妄续!”[1]4029尽管如此,司马贞对于《史记》的失误处或前人注释不合理处,则采取怀疑、批判的态度。
(三)《史记正义》成书概况
《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撰,新、旧唐书均无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守节始末未详,据此书所题,则其官为诸王侍读、率府长史也。是书据《自序》三十卷,晁公武、陈振孙二家所录,则作二十卷。盖其标字列注,亦必如《索隐》,后人散入句下,已非其旧。至明代监本,采附《集解》、《索隐》之后,更多所删节,失其本旨。”[8]1233
《说文解字》注:“正,是也”,“义,己之威仪也。”虽号曰“正义”,然与经籍注释之“正义”却有所不同。统观《史记正义》,其不似孔颖达疏解《五经正义》,处于“寸步不离,犹恐失之的状态”[9]169,张守节继承了包括裴骃、徐广在内的《史记》注家之大成果,借鉴了《史记索隐》中“释文演注”的辩述方法,他“引致旁通”,阐发义理;观采“六籍九流地里苍雅”,“评《史汉》诠众训释”,謏“郡国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窃探其美,索理允惬”[1]4057,更为重要的是,《史记正义》以引《括地志》为主。今人贺次君先生曾对《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进行了辑校,撰成《括地志辑校》。其中提到“张守节完全依据《括地志》注释古代地名,《括地志》则因其征引得以部分保存。今搜集的十之八九来自《史记正义》”[10]前言5。可见,地理类注释是《史记正义》价值最高、成就最大的部分。
二、《史记》三家注之特点比较
《史记》三家注注重从史记文本的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进行注解,侧重的方向有所不同,如《史记集解》字句雕琢的严谨态度,《史记索隐》敢议前人的批判精神,《史记正义》赅博翔实的地理资料,使得每个注解独放光彩,成为注解史记中极有代表性的三家。
(一)《史记集解》之严谨
所谓“集解”,即辑集众家相关解释而作注,正如裴骃在《史记集解序》中所说“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1]4038。统观《史记集解》, 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它对材料的取舍相当严谨,这也使其有别于考证论说的《史记索隐》《史记正义》。姑以《高祖本纪》为例,具体而论,其表现在:
第一,“删其游辞,取其要实。”《史记集解》集结了百家之言,但并非毫无准则,而是去其浮言藻语,取其精旨要义。且在列前人对同一词或句的注释时,包含有不同的信息。如:“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集解》:“李斐曰:‘沛,小沛也。刘氏随魏徙大梁,移在丰,居中阳里。’孟康曰:‘后沛为郡,丰为县。’”此解释让研读者了解到“刘氏”与“沛”的关系以及“沛”的发展过程。再如“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集解》:“应劭曰:‘抵,至也,又当也。除秦酷政,但至于罪也。’李斐曰:‘伤人有曲直,盗藏有多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张晏曰:‘秦法,一人犯罪,举家及邻伍坐之,今但当其身坐,合于《康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这一解释既有对字和句的注释,又包括对当时法律的说明。内容翔实但不繁杂,信息丰富而有序,取其所当取,弃其所当弃。
第二,“义在可疑,则数家兼列。”《集解》多引而少论,更强调对《史记》文本原意的呈现。尤其是对于诸家意见相左,但未能辩其实,“是非相贸,真伪舛杂”的观点时,裴骃秉持“具列异同”而“弗敢臆说”的态度,如:“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集解》:“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李斐曰:‘休谒之名也。吉曰告,凶曰宁。’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告又音喾。汉律,吏两千石有予告、赐告。’”又“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集解》:“服虔曰:‘准音拙。’应劭曰:‘隆,高也。准,颊权准也。颜,颌颡也,齐人谓之颡,汝南、准、泗之间曰颜。’文颖曰:‘准,鼻也。’”“雍齿雅不欲属沛公”,《集解》:“服虔曰:‘雅,故也。’苏林曰:‘雅,素也。’”“因张良遂略韩地轘辕”,《集解》:“文颖曰:‘河南新郑南至颍川南北,皆韩地也。以良累世相韩,故因之。’瓒曰:‘轘辕,险道名,在缑氏东南。’”其对字音、词义、人名、官职、地理等多方面孰是孰非的前人注释,裴骃“具列异同”,以供研读者自择。
第三,“时见微意,有所裨补。”《史记集解序》云:“时见微意,有所裨补。譬嘒星之继朝阳,飞尘之集华岳。以徐为本,号曰《集解》。”裴骃并非单纯罗列众辑百家之言,而对于其中解释未完备的,会复引他家之说,甚或兼下己意。一般有“骃案”语。“乃立季为沛公”,《集解》:“徐广曰:‘九月也。’骃案:汉书音义曰‘旧楚僭称王,其县宰为公。陈涉为楚王,沛公起应涉,故从楚制称公’。” 徐广只说到季为沛公的时间,裴骃引《汉书音义》解释为什么立季为“沛公”。“以沛公为高祖原庙”,《集解》:“徐广曰:‘光武纪云“上幸丰,祠高祖于原庙”。’骃案:谓‘原’者,再也。先既已立庙,今又再立,故谓之原庙。”裴骃对徐广之解进一步扩展,将句意理解严谨深入至字上。“文之蔽,小人以僿”,《集解》:“徐广曰:‘一作“薄”。’骃案:《史记音隐》曰‘僿音西志反’。郑玄曰:‘文,尊卑之差也。薄,苟习文法,无悃诚也。’”
《高祖本纪》中“骃案”为引徐广之释后,列他书或他说互证,或进一步释义,罕有辨言。观《史记》他篇,其中表明己意者甚少,既有己意,亦态度严谨,几不贸然断论。如《孝景本纪》“置南陵及内史祋祤为县。”《集解》:“徐广曰:‘《地理志》云:“文帝七年置。”’骃案:《地理志》《百官表》南陵县文帝置也。分内史为左右,及祋祤为县,皆景帝二年,不得皆如徐所云。”据统计,《集解》中裴骃“案语”只有二百五十余条,只占全部集解注文中的很小一部分[3]373。且多用“未详”“或曰”“不得皆如”“似误”等语气和缓的词。这足以说明《史记集解》慎于论说,“依违不悉辩也”[1],裴骃注解风格十分严谨。
(二)《史记索隐》之质疑批判
《说文解字》中云:“隐者,蔽也。”[11]305下司马贞“探求异闻,采摭典故”,强调对《史记》文本背后不为人知的东西加以申述,“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从而“释文演注”[1]4044,编撰《史记索隐》。
《索隐序》《索隐后序》中评价了前人对《史记》做的的注解:论裴骃《集解》“虽粗见微意,而未穷讨论”。批南齐邹诞生《音义》“音则微疏,义乃更略”。评刘伯庄“达则宏才,钩深探赜”,《音义》二十卷“比于徐、邹,音则具矣”,然“残文错节,异音微意,虽知独善,不见旁通”[1]4043-4046。此种敢议前人之非的批判精神,在注释《史记》文本中亦展露无疑,可谓是《史记索隐》最突出的特点,最独特的注释风格。兹以《太史公自序》为例,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质疑或批驳他说或他家注者。如:“葬于华池”。《索隐》:“晋灼云在户县,非也。案司马迁碑在夏阳西北四里。”此批驳《集解》所引晋灼的对“华池”的注释。司马贞根据司马迁的碑之所在地,推断司马靳所葬之地非户县。
又如:“喜生谈,谈为太史公。”《索隐》:“案《茂陵书》,谈以太史丞为太史令,则‘公’者,迁所著书尊其父云‘公’也。然称‘太史公’皆迁称述其父所作,其实亦迁之词,而如淳引卫宏《仪注》称‘位在丞相上’,谬矣。案《百官表》又无其官。且修史之官,国家别有著撰,则令郡县所上图书皆先上之,而后人不晓,误以为在丞相上耳。”指出如淳所认为司马谈“位在丞相上”的错误观点。
第二,古今字、音批驳。如:“厄困鄱”,《索隐》:“鄱本音蕃,今音皮。案:白褒《鲁纪》云‘灵帝末,有汝南陈子游为鲁相。子游,太尉陈蕃子也,国人讳而改焉’。若如其所说,则‘蕃’改‘鄱’,鄱皮声音近,后渐讹耳。然《地理志》鲁国蕃县,应劭曰:‘邾国也,音皮。’”司马贞对“鄱”的古音、今音都作了追根究底之释。再如:“小子何敢让焉”,《索隐》:“让,《汉书》作‘攘’。晋灼云:‘此古‘让’字,言己当述先人之业,何敢自嫌值五百岁而让也。’”
第三,质疑《史记》文本有误。如:“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索隐》:“南正重以司天,火正黎以司地。案:张晏云:‘南方,阳也。火,水配也。水为阴,故命南正重以司天,火正黎兼地职。’臣瓒以为重黎氏是司天地之官,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字,非也。扬雄、谯周并以为然。案:《国语》:‘黎为火正,以淳曜敦大,光照四海’,又《幽通赋》云‘黎淳曜于高辛’,则‘火正’为是也。”司马贞引张晏之语及《国语》《幽通赋》驳迁之书有误,认为“北正”应作“火正”。“汉兴以来,至于太初百年,诸侯废立分削,诸纪不明,有司靡踵,强弱之原云以世。”《索隐》:“案:踵谓继也。‘以’字当作‘已’,‘世’当作‘也’,并误耳。云,已,也,皆语助之辞也。”司马贞认为此末句应为“强弱之原云已也”。
另外,司马贞的敢于批判,还体现在对《史记》的体例修改上。司马贞对《史记》“颇事钻研”,初“愤发而补《史记》”,号曰《小司马史记》[1]4048。司马贞认为《史记》“阙三皇”,“载籍罕备”[1]4051,于是自撰《三皇本纪》,并为之作注,以置卷首。同时他批驳司马迁“邾、许春秋次国,略而不书;张、吴敌国藩王,抑而不载”。质问“又列传所著,有管、晏及老子、韩非。管、晏乃齐之贤卿,即如其例,则吴之延陵、郑之子产、晋之叔向、卫之史鱼,盛德不忝,何为盖阙?伯阳清虚为教,韩子峻刻制法,静躁不同,德刑斯舛。今宜柱史共漆园同传,公子与商君并列,可不善欤?”他大胆批判《史记》“其中远近乖张,词义踳驳,或篇章倒错,或赞论粗疏”[1]4047-4048。《史记索隐》全书约六千条,其直接指出司马迁疏略错误、与他书之不同者,达五六百余处。其中明确攻驳者,达一百五十多条,范围极广[8]1234。司马贞在其中质疑所记之史实;指出记史前后矛盾;指出司马迁所见史料未完备;指出衍字、别字……其质疑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其多有“可疑”“……非……”“谬说”“盖无可取”“故今……为……是也”“此说皆非”等字眼,足见其研学之功,其注史之辩正疏略、探求异闻、敢申其所未申的质疑批判精神。
(三)《史记正义》之地理释义
“地理释义”,即是对地理方面的资料注释清楚详细。其作为《史记正义》中价值最高、成就最大的部分,后世学者亦给予了高度评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正义》:“是书征引故实,颇为赅博。于地理尤详。”[8]1233钱大昕在《三史拾遗》中赞《正义》道:“司马长于驳辨,张长于地理,要皆龙门功臣,难以偏废。”[12]97张守节对于地理的注释极为丰富翔实。估以《匈奴列传》为例,具体分析。
第一,地理注释内容丰富。包括释山脉、释国家、释战场、释地名、释河流、释祠庙等多方面所处地理位置。如:“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正义》:“《括地志》云:‘阴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自此之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正义》:“铁勒国,匈奴冒顿之后,在突厥国北。乐胜州经秦长城、太羹长路正北,经沙碛,十三日行至其国。”“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正义》:“《括地志》云:‘汉居延县故城在甘州张掖县东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有汉遮虏鄣,强弩都尉路博德之所筑。李陵败,与士众期至遮虏鄣,即此也。长老传云鄣北百八十里,直居延之西北,是李陵战地也。’”《史记正义》中引用《括地志》《地理志》《汉书》等多部经典著作,释山川河海,释典章制度,更是对其关涉的地理位置作以详细的说明,更助于研读者对当时的地理、风俗等有一定认识,对《史记》的理解更加深入。
第二,对地理演变、地理沿革加以详细考证。如:“居于河西圁、洛之间。”《正义》:“《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盐州白池东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绥州、银州,本春秋时白狄所居,七国属魏,后入秦,秦置三十六郡。’洛,漆沮也。”在《索隐》引《地理志》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河西圁”的地理位置说明,并说明春秋、战国至秦统一天下“河西圁”的地理位置演变。再如“故自陇以西有緜诸”,《正义》:“《括地志》云:‘緜诸城,秦州秦岭县北五十六里。汉緜诸道,属天水郡。’”张守节引《括地志》中对“緜诸”秦汉时的地理位置沿革做了说明。又如“翟、豲之戎”,《正义》:“豲道故城在渭州襄武县东南三十七里。古之豲戎邑。汉豲道,属天水郡。”
第三,地理考证与文字考证相结合。《史记正义》在地理释义时,同样注重对其中文字的考证。如:“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正义》:“‘城’字误也。《括地志》云:‘彭城故城在泾州临城县东二十里。’案:彭城在妫州,与北地郡甚远,明非彭城也。”再如,“故自陇以西有緜诸、绲戎”,《正义》:“上音昆。字当作‘混’。颜师古云:‘混夷也。’韦昭云:‘春秋以为犬戎。’”指出其中“绲”应为“混”。
《史记正义》这种注释地理的方法,尤为详备,为研读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同时用考证地理的方法来考证字,为史注又开新篇章。
《史记》三家注的特点是多样的,除上所列,也有在音韵训诂、引经据典、释文演义等多方面值得研究探讨的,在此不做申述。因成书的先后关系,《史记索隐》和《史记正义》多继《史记集解》而发,存在着疏解和承继关系。[3]333《史记》三家注各自所突出的特点,无论是对文献目录及资料保存方面,版本价值及校勘成果方面,抑或保存丰富的注释材料及训诂材料、注释方法多样、地理资料详备方面,或是补正史学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对后世《史记》注释乃至其他典籍的注释之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2] 班固.汉书:卷六二[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张玉春,应三玉.史记研究集成:第十二卷[M].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
[4] 沈约.宋史:卷二十四[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6] 朱东润.史记考索[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7] 刘知几.史通·内篇·补注:第十七[M]. 北京:中华书局,2014.
[8]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五[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9] 程金造.史记管窥[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10] 贺次君. 括地志辑校[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1] 许慎.说文解字[M].长沙:岳麓书社,2006.
[12] 钱大昕.三史拾遗 廿二史考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