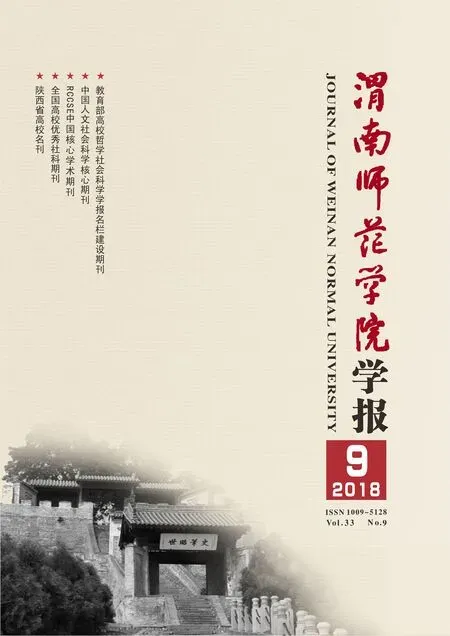《史记》编撰对西汉图书文献事业发展的贡献
2018-03-07党晓红汪庆春马光华
党晓红,汪庆春,马光华
(西北大学a.地质学系;b.历史学院;c.图书馆,西安 710069)
一、《史记》编撰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
(一)西汉国家文化政策对《史记》编撰的影响
西汉王朝是继大一统秦王朝之后崛起的一个国祚绵延两百余年的强大政权,其中司马迁生活的年代处于中国文化发展第二时期(春秋战国时代的宗法社会破裂后文化自由发展时期)和第三时期(秦汉两代统一安定向外发展时期[1]6-7)重要的转折点上。
汉初社会凋敝、百废待兴。统治者逐步意识到转变文化思想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意义。刘邦接受了儒生陆贾天下可以“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观点,逐渐转变了轻视儒生的态度并到鲁地祭祀孔子。他在写给太子的书信中谈到自己对读书的认识:“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阼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2]13惠帝因遗策废除挟书律,“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3]1701,强化了西汉文化自由、开放政策。到文帝时期,开始向天下广征图书:“孝文帝时,天下无治《尚书》者,独闻济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可征,乃诏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便宜事,以《书》称说。”[4]118西汉中叶,汉武帝命令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到汉成帝时竟取得“百年之间,书积如山”的丰硕成果。
西汉统治者制定施行的一系列自由、开放的文化新政,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一次深刻改造,同时也是对国家文化体制的一次积极重构。它最大限度地收集和保存了先秦失落于民间的大量珍贵史料,初步建立起图书档案事业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为《史记》的编撰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储备和宽松的文化环境。
(二)西汉国家藏书体系对《史记》编撰的帮助
中国传统王朝普遍重视资料的记录与保存,在秦始皇颁布“挟书律”之前,国家、私人和相关团体都重视藏书的传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说明远在周朝,国家就专门设立了“史”职管理守藏室。“公元前206 年刘邦至咸阳,丞相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并着手建多处宫廷藏书处,石渠、天禄 、麒麟 、兰台、石室等成为我国早期的图书馆。”[5]71在西汉政府与民间共同努力下,国家藏书体系有了极大完善。特别是石渠阁建成之后,西汉前职能比较单一的藏书机构逐渐演变成为兼具收藏、编校和学术研讨的重要场所。
石渠阁位于未央宫北,开始主要收藏入关所得秦朝图书,后历经数代积累,藏书日趋丰富。汉武帝时期,司马迁编写《史记》正是得益于在此博览群书、耙梳史料。石渠阁会议(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 51 年)召开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又对汉成帝时期刘向、刘歆父子在天禄阁开展的大规模校书编目工作产生了深刻影响。班固在《西都赋》记载道:“又有天禄石渠,典籍之府,命夫谆诲故老,名儒师傅,讲论乎《六艺》,稽合乎同异。又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大雅宏达,于兹为群,元元本本,周见洽闻,启发篇章,校理秘文。”[6]67全面介绍了石渠阁在典藏图书、讲论六艺、校理秘文等图书档案事业方面的核心功能。可见石渠阁代表的西汉藏书机构不仅成为 “天下图书源头”,更是中国古代藏书体系逐渐走向专业化的历史节点。“西汉搜集的大多数图书在这里接受整理从而更加系统,然后通过传抄复制等方式流传到民间,这样既普及了文化知识,又促进了图书的流通。此三处(作者按:指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奠定了西汉一朝图书典藏的基础。”[7]17
(三)西汉史官制度与儒家思想对《史记》编修的影响
《史记》编撰始于太初元年,成于征和二年,历时十三年之久。这一时期正处于汉武帝统治的中后期,《史记》成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儒家礼仪制度和史官制度的影响。
首先,《史记》带有浓重的儒学色彩。司马迁师从名儒董仲舒,《史记》编撰又处于儒学作为意识形态统治地位不断强化时期。司马迁把孔子列为“世家”并为孔子诸弟子作传,表明他尊崇孔子及其儒学流派的社会地位,而行文对人物的臧否更不乏以儒家标准为依据。近人梁启超认为“太史公最通经学,最尊孔子”[8]216,进一步佐证了儒家思想对司马迁影响之深。
其次,《史记》的编撰得益于史官制度的确立。西汉以前,“史官和史学家没有独立的政治保障,职业和信仰没有自由。一方面承受极端残酷的专制主义的压制,使他们成为统治阶级的附庸。没有独立的人格,就失去了创造性。另一方面,身心上经常遭受黑暗势力的摧残……尽管良知和生存的需要促使他们去探索,但仍不能被社会承认”[9]44,汉武帝设置太史令后,正式确立了史官制度,这对司马迁任太史令期间“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的著述工作以及作为职业史家反思历史、以资镜鉴的治史观念提供了良好的体制保障。使其有条件承担起反思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为统治集团提供历史借鉴的使命:“闻其过失而改之,见义而从之,所以永有天下也。”[10]2330
二、《史记》对西汉图书文献事业的历史贡献
(一)对于古代图书分类学初创的贡献
“中国古代图书分类(简称‘传统分类’)是中国古代先贤对当时所有既成文化的一种表述和组织的认知模式。”[11]64图书分类学是一门关于图书分类研究的学问,它“是目录著作的重要内容,恰当的分类能帮助读者因类求书、因书究学,起到指示读书门径的作用。”[12]186对图书文献保存、利用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我国历史悠久、文献资料浩如烟海。成书于西汉末年的《七略》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图书分类法。然而新生事物必不是凭空出现的,追根溯源,《史记》的编撰对《七略》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史记》对图书分类学的首创之功应得到充分的认可。
古代图书分类“不仅是一门注重实用的操作技术,而且还是一套价值体系和意义系统”[11]65,具有高度实用性的特点。《史记》编撰的指导思想及其文章结构、内容体系本身就是对图书分类的积极探索和具体展示。《史记》体例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之分,其中“本纪”“世家”和“列传”的人物部分构建了一种按照人物社会地位和社会贡献进行排列的分类规则,能够便捷地定位、筛选相关内容,而其取舍标准本身即体现了分类思想;“书”分为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等,形成了一套按照一定标准划分社会生活的分类体系,既能勾勒出历史轮廓又囊括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列传”按不同标准分列出循吏、酷吏、佞幸等章节,是以儒家意识形态为准则品评人物的分类体系,反映了儒家思想主导下人们的世界观。这些知识组织方法、文献分类思想的创设,为《七略》校书编目工作提供了重要借鉴。
“《史记》是《七略》产生之前一部有关目录学的最近力作”[13]15。司马谈曾把先秦思想流派“厘为若干派,所分儒、墨、名、法、道和小说六家”[14]404,这种梳理学术流派的思想和方法构成图书分类的重要基础。司马迁深受其父影响,在目录学和图书分类领域也做了“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探索。司马迁叙述历史创造性使用了“互见法”,即“将同一传主的不同事迹分散在其他篇章中来写,以本传为主,而散见于其他传记的事迹则起着补充的作用”[15]4。在描写汉高祖刘邦事迹时,《高祖本纪》主要记述刘邦的功绩和作为,而其贪财好色、残忍自私等负面形象多是散布于其他人物纪、传之中,历史上“复杂事迹往往牵涉许多人物,而人物又是分散于数篇,一处不记则疏漏,处处反映则重复”[16]47,“互见法”使用“语在某篇”“事在某篇”等词条使相关内容之间互为参见,规避了历史的重复记载,做到了行文详略得当、简洁明晰。“《史记》具有一定的目录学价值,它对人物传记的分类思想影响了《七略》的分类方法和后来序录体目录的形制,有些篇目还对儒家、道家、史家等学术源流进行了考辨,而《自序》一篇则确立了一书目录的体制,显然具有目录学上的发凡意义。”[13]显然,《史记》在目录学和图书分类领域的探索对古代图书分类学和目录学的形成有着重要历史意义。
(二)对古籍文献整理方法的贡献
文献整理对文献传播有重要意义,科学的文献整理方法能够有效避免古文献错乱散失,日渐佚亡或妄加窜改,贻误后人[17]绪言1。我国文献整理传统历史悠久,“早在先秦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就已经开始了对文献典籍的整理工作,形成了自己的文献整理的思想和方法”[18]61。经过不断发展与完善,“文献整理方法在汉代,就个体和整体而言,都已成型,显示了汉代文献学发展的承上启下、超越前人的成就。”[19]其中司马迁编撰《史记》也对文献整理方法做出了重要贡献。
古籍文献资料整理有辨伪、考证、补缺、训诂、翻译、整序等科学方法,司马迁在编撰《史记》时不仅能够灵活运用,而且还在此基础上互相考核加以筛选、剪裁、补史、训译、熔铸等手段。
首先,司马迁在“网罗天下放佚旧闻”时做了大量辨伪、考证工作。古代图书中存在不少伪书,司马迁考辨史料既奠定了《史记》作为“信史”的地位,也为辨伪、考证的文献整理方法做出重要贡献。例如司马迁在《仲尼弟子列传》“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厥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中考辨出古文《论语》关于孔门弟子的记载接近事实的结论;在《郦生陆贾列传》“世之传郦生书,多曰:‘汉王已拔三秦,东击项籍,而引军于巩洛之间,郦生被儒衣往说汉王’,乃非也。自沛公未入关,与项羽别,而至高阳,得郦生兄弟”中根据考证得出了郦生与刘邦相遇是在高阳并不是古史记载的“巩洛之间”。对无法考证的传闻存疑也是司马迁考辨方法之一。司马迁在考证辨伪中遇到无法确定的分歧就谨慎陈述而不做判断,在无法考证老子是“老聃”还是“老莱子”时他搜集罗列了当时不同的版本以供后人参考。
其次,司马迁的文献整理方法还包括走访乡贤名宿开展实地调查的方法。“文献”一词古今语义变化颇大,“文”表示典籍,“献”则包含了贤人及贤人的经历及言语等。司马迁的文献整理方法既有对“文”的考证辨伪,也有对“献”的走访访谈。他早年游历山川大泽,履迹明宿故里不仅是为了获得情感上的共鸣,更是走访调查书面文献资料所遗漏的口耳相传部分。其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在当时很具创新性。
第三,灵活的翻译也是司马迁文献整理的重要方法。司马迁大量使用西汉文字使古文语言表达通俗化,通过增减词语使古文表达更加清晰,显示出对古文的高超翻译技巧。例如《尚书》行文非常晦涩,许多篇章一般人很难理解。司马迁征引《尚书》材料时一方面通过对其中艰涩字句的巧妙翻译,使《史记》行文用语通俗易懂;另一方面针对《尚书》语言简短的文风适当增加主语等语句结构使表达内容更加清晰,真正做到了后人提出的(翻译作品)“信达雅”原则,不啻对《尚书》的一次大规模文献整理。
当然在今天看来,司马迁文献整理方法也并非尽善尽美,但其历史贡献则无法磨灭。
(三)对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贡献
“图书馆学”是近代欧风美雨裹挟下输入的新概念。耙梳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古代虽无“图书馆学”之名却实有“图书馆学”之实。“中国古代藏书肇于殷商甲骨的收藏,至汉代已基本成型,但是那时的藏书思想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和方法。从现存的文献来看,有关藏书理论 (包括收集整理、保存、利用等方面 )方面的记载往往只是只言片语,且并无专论,因此我们只能称其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萌芽时期。”[20]司马迁时代正处于古代图书馆学上承先秦、下启隋唐的重要历史阶段。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最基本的学术思想。学术界一般倾向认为这种思想始于刘氏父子。然而梳理历史会发现司马迁在《史记》的编撰中已经深刻贯穿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学术思想。从《史记》结构上分析,“本纪、世家、年表、列传,这些正是考源流、辨异同的写法”[21]。司马迁把“本纪”追溯到上古黄帝,而且还在诸子百家的言论中区分黄帝的异同,辨别其中的真伪,目的即是阐述“黄帝”的来源与流变。内容方面注重考查诸子学说的兴起与发展:在《老子韩非列传》中考查了道家学说在老子、庄子、韩非三人时期的发展,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老子学说的源流;在《孔子世家》和《儒林列传》中考查了孔子创立儒学及儒家代表人物对儒学的继承与发展;而“《日者列传》与《龟策列传》有对数术史的概述。《历书》为中国古代第一篇历法简史,《天官书》为中国第一篇天文简史,《封禅书》是中国古代封禅简史,《河渠书》是一篇水利简史”[22]。凡此种种,既有对文献的考辨又有对历史知识的梳理。《史记》对图书馆学思想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三、《史记》对古代文献保护与传承的历史贡献
(一)收集和整理古代文献的历史贡献
《史记》许多内容都有取材于先秦作品的烙印,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司马迁将许多珍贵古代文献直接或间接地保留于《史记》之中。“司马迁对于比较欣赏的著作则反映其全文”[23]直接保留于《史记》中,例如司马相如的列传就收录了其本人《子虚赋》《上林赋》等八篇赋文。此外,一部分著作则采取收录书名的方式得以保留于《史记》中。司马迁还通过引用文献的办法收集了一批古代文献,他编修《史记》有大量称引文献,兹列举其中部分史地档案如下[24]106。《五帝本纪》:《百家》言黄帝,其文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六国年表》记载有太史公读《秦记》,此外,《谍记》《历谱谍》《终始五德传》《五帝系谍》等众多史地档案均有引用。当然这仅是冰山一角,根据张大可《史记研究·史记取材》提供的信息可以确信司马迁看到的古书达到102种。[25]232这些直接或间接的方法对古代文献的保存与传承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二)确保文献客观真实的历史贡献
《史记》保存历史文献的过程也是对其去伪存真的过程。司马迁在引述历史文献时非常注重史料的真实性:一是通过身临其境的机会开展实地考察,二是通过详近略远的方法去伪存真,三是通过兼收并取、广开史料来源的方法尽可能保证材料的客观性。
司马迁年轻时经历过一段游历生涯。他南游江淮到会稽,探访夏禹的遗迹;到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淮阴,访问韩信故事;到丰沛,访问萧何、曹参、樊哙故宅;到大梁,访问夷门,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情形;游历楚地,访问春申君遗址;亲临薛地,访问孟尝君丰邑;拜谒邹鲁,访问孔孟故乡。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通过踏勘祖国山河故居,搜集了许多翔实的口碑传说和名人轶事,了解了大江南北的风俗民情、社会生活等。其身临其境的游历极大地充实了他的人生经历,扩展了他的学术研究视野,也为后来编修《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如胡佩韦先生所言:司马迁“实地考察秦汉之际的大小战役和地理环境、寻访许多资料(其中有些是不见史册的遗闻轶事),熟悉了各地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状况,对于刘邦和汉初经济集团有了全面的了解。”[26]19这些经历与当代史事相互补充,使司马迁建立起相对客观的取舍标准,对保存相对客观真实的历史做出独特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详近略远”的叙事原则。刘知几在《杂说上》评论:“迁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史记》虽是一部上起远古传说,下讫汉武帝年间,但司马迁明确把史书记载放到了西汉“当代”。因为从史料考证角度而言,远古时期史事缥缈多不可考,而汉朝“当代”史事则大多有迹可循。
第二,“述而不作、阙而不录”的治史理念。“述而不作”是“依据已有的史料且不掺杂自己主观见解来编撰史书”[27]33;“阙而不录”是对有关虚假或缺乏依据的事物不予收录。《史记·三代世表》:“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对于有疑惑之处不予以推测,保存了文献的原貌。
第三,“兼收并录、勘辨真伪”的选材方法。司马迁通过陪驾汉武帝巡行封禅的机会亲临涿鹿等地探访民间关于黄帝的传说,最终在编修《五帝本纪》中明确记载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对黄帝管理疆界范围、教化百姓同样有确切的记载,使黄帝形象由神的缥缈虚无转变为人的真实不虚。此外在《蒙恬列传》中司马迁明确批判蒙恬认为自己修长城、修驰道犯有“绝地脉”的迷信思想,认为“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何乃罪地脉哉?”反映他在史料方面对其甄别真伪的严谨态度。
第四,“采经摭传、秉笔直书”的“实录”风格。司马迁秉笔直书的精神令人敬佩,对于当朝皇帝刘邦的描写也不例外,既反映了其知人善任和深谋远虑的政治眼光,也刻画了他狡诈、凶残的无赖形象[28]2。对于孔子著《春秋》的曲笔传统也给予批判:“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29]2919。司马迁编撰《史记》一贯坚持秉笔直书的原则正是《史记》“实录”性质的保障。
第五,“兼收并取”的求真务实精神。《史记》中保留了大量先秦古书的资料充分体现了司马迁广阔的史料收集视野,他不以儒家经典作为唯一的编撰史料来源。《史通》认为“马迁《史记》,采《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此并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秋。”对司马迁采取可信度较高的史料且据实直书的编撰特点给予充分肯定和极力推崇。
(三)文献传播学意义上的历史贡献
“文献传播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于社区、群体及所有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文献互动过程,同时也是使文献信息活化,实现文献资源共享的过程。”[30]16《史记》作为在文献传播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史记》的许多故事在西汉后广为流传,成为后代小说戏剧重要的取材对象。元代的《列国故事平话》,明代的《列国志传》以及流传至今的《东周列国志》等,所叙人物和故事有相当一部分取自《史记》。明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也是大量利用《史记》中的材料。《史记》的许多人物故事相继被写入戏剧,搬上舞台。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后来的京剧也有不少剧目取材于《史记》。总之,《史记》成为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的材料宝库,它作为高品位的艺术矿藏得到反复的开发利用。
《史记》的编撰既是我国古代史学发展重要的里程碑,同时也具体展现出西汉中叶我国图书文献事业在草创阶段的辉煌。今天,图书馆学科面临“计算机信息技术冲击后发生了变异,非专业学科话语侵蚀了图书馆学的传统领地,导致专业活动迷失了发展方向”[31]的严峻现实, 追本溯源,回顾司马迁与《史记》对西汉图书文献事业发展的历史贡献,不仅仅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原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科创建初期的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可以重温图书馆学科传统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学习和继承司马迁严谨的治学思想、求真务实的职业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气概和以实践为基础的专业思维方式。
参考文献:
[1] 常乃惠.中国文化小史[M].上海:中华书局,1929.
[2] 董志安.两汉全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3] 班固.汉书·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 班固.汉书·文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97.
[5] 韩淑举.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述略[J].四川图书馆学报,2002(1):70-75.
[6] 萧统.昭明文选·西都赋[M].北京:中华书局,2013.
[7] 李真.西汉文化政策研究[D]. 青岛:青岛大学,2011.
[8] 梁启超.读书分月课程[M]//刘太祥.汉代政治文明.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9] 陈维,胡建华.中国古代档案学思想发展缓慢原因初探[J].档案管理,1989(3):44.
[10] 班固.汉书·贾邹枚路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1] 傅荣贤.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学研究的研究[J].四川图书馆学报,1996(6):64-67.
[12] 段雅萍.图书分类法发展历程回溯[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1(8):186-188.
[13] 王珂.论《史记》的文献学价值[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7.
[14] 王焕.文献分类学[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0.
[15] 过常宝.论《史记》的“太史公曰”和“互见法”[J].唐都学刊,2006(5):1-7.
[16]王锦贵.论司马迁在编辑学领域的原创性贡献[J].中国出版,2005(5):47-49.
[17] 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4.
[18] 万妮.先秦文献整理的思想、方法和时代特点[J].四川图书馆学报,2006(2):61-64.
[19] 王国强.论汉代文献整理的思想和方法[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5(4):72-76.
[20] 程焕文.略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形成时期的几个问题[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89(2):14-18.
[21] 王友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文献整理宗旨的秉承[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1(2):71-72.
[22] 傅荣贤.中国古代目录学学术价值之反思[J].图书情报知识,2008(2):47-51.
[23] 王锦贵.为司马迁目录学成就正名[J].图书情报知识,2014(3):12-13.
[24] 赵生群.史记编纂学导论[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25] 张大可.史记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26] 胡佩韦.司马迁和《史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7] 郑先兴.论司马迁的史学思想[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25-35.
[28] 吕利平.《史记》与档案文献[J].河南图书馆学刊,2008(2):135-137.
[29]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0] 李日禾.试析文献传播的社会价值[J].贵图学刊,1995(4):16-18.
[31] 王宗义.专业话语:实践描述与思维构建——关于当代图书馆活动的若干思考[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43(2):1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