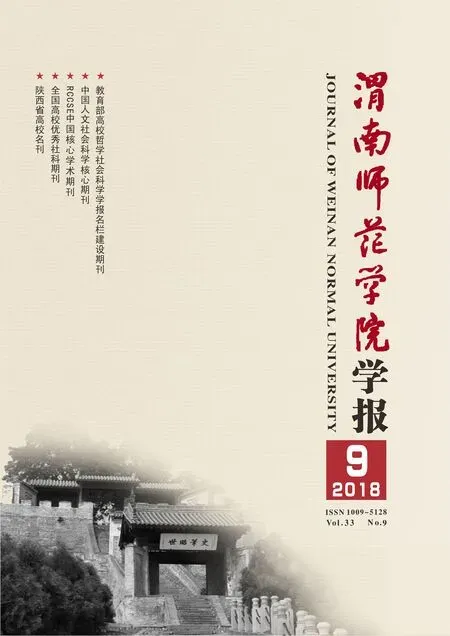论近现代《史记》文章学评论之特点
2018-03-07王长顺
王 长 顺
(咸阳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
《史记》从传世之时起,就有文人开始评论。“到了宋代,真正开《史记》评论的风气,此后不断发展,明清时期出现兴盛局面,对于促进《史记》的广泛传播与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清代是《史记》研究的高峰期。”[1]57在《史记》文学经典进一步加强的近现代时期[2]154,关于《史记》的评论内容非常丰富,其中一些评论有着一定的文章学价值,并表现出显著的特点。
一、对《史记》文章叙事详略评论的具体性
详略是把握文章叙事的重要方面,行文中对详略的把握影响文章的表达效果。刘勰《文心雕龙》:“略语则阙,详说则繁。”[3]95“谓繁与略,适分所好”[3]65,说明文章应当详略适当。因此,从文章学角度来说,作文要“繁约得当”“简而不漏,简而有法,简而意远”[4]367。
汉代以来,对《史记》文章叙事详略多有评论。班彪《略论》评价《史记》“甚多疏略”(《后汉书·班彪传》);唐代刘知几《史通》也曾评论《史记》繁简;宋代王充《论衡》、张辅《班马优劣论》、金代王若虚《滹南遗老集》等立足班马异同,评论《史记》《汉书》繁简。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论《史记》“叙有详略”;清代吴见思《史记论文》论《史记》:“序法有分合,有繁简,有排有宕,变化有错综。”这些评论基本上都是总体评论《史记》繁简之宜,详略之当。近现代学者也有对《史记》叙事详略从总体上评论,如陈元棫认为:“史公之书,自黄帝讫麟止,备载历代,而卷帙不及《汉书》,似乎简矣,然简人所不能简,亦详人所不能详。事无论大小,但不铺叙则竟不铺叙,一铺叙则必使其音容笑貌,与夫性情心术,跃跃纸上,至其摹写精神,如东坡所言传神法,但观其意思所在,或在目或在颧颊而已。若此则一二言不为少,千万言不为多也。”*陈元棫《蛟川先正文存(卷一八)·史记选序》(光绪八年刻本)。评论《史记》详与简恰到好处,合理运用繁简之法,达到了“一二言不为少,千万言不为多”的效果。然相对于前代评论,近现代关于《史记》叙事详略的评论体现出具体性。
一是具体分析《史记》篇章中的详略之事。如梁启超认为:“(《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蔺相如完璧归赵及渑池之会两事,从始至末一言一动都记得不漏,这是详写大事之法。因为这两件大事最足表现相如的个性,所以专用重笔写他,其余小事不叙。廉颇的大事,三回伐齐,两回伐魏,一回伐燕,传中前后只用三四十字便算写过,绝不写他如何作战,如何战胜,因为这些战术战功是良将所通有,不足以特表廉颇的人格。倒是廉颇怎样的妒忌蔺相如,经过相如退让之后怎样的肉袒谢罪,失势得势时候怎么的对待宾客,晚年亡命在外思念故国怎么的‘一饭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马示尚可用’,这些小事写得十分详细,读之便可以知道廉颇为人短处在偏狭,长处在重意气识大体。”[5]4753意谓司马迁为了表现人物性格,在行文时将蔺相如大事详写,小事略写;把廉颇大事略写,小事详写,以突出蔺相如、廉颇个性之不同。梁氏对司马迁所详之事、所略之事具体罗列,蔺相如的大事有完璧归赵、渑池会,廉颇的大事有三回伐齐、两回伐魏、一回伐燕等,廉颇的小事有嫉妒蔺相如、肉袒谢罪、对待宾客、念故国、尚可用等,详细具体,分析透彻。
二是具体评论详略之法的运用。如曾国藩从《吴王濞列传》中“悟为文详略之法”。其《求阙斋读书录》(卷三)云:“《吴王濞列传》先叙太子争博,晁错削地,详致反之由。次序吴誂胶西,胶西约五国,详约初之状。次序下令国中,遗书诸侯,详声势之大。次叙晁错绐诛,袁盎出使,详息兵之策。次序条侯出师,邓都尉献谋,详破吴之计。次叙田禄伯奇道,桓将军疾西,详专智之失。六者皆详矣,独于吴军之败不详叙,但于周丘战胜之时,闻吴王败走而已,此亦可悟为文详略之法。”*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刊。在曾氏看来,司马迁在《吴王濞列传》中,详叙吴王刘濞反叛的起因:皇太子与吴王太子争博致吴太子死,晁错削减吴王封地;再详叙反叛之谋:吴王刘濞私约胶西王,胶西王约五国;再详叙叛乱声势之浩大:吴王下令全国,并给诸侯写信;再详叙平息叛乱之策:晁错被诛,袁盎出使吴国;再详叙平叛的计谋:周亚夫进军,邓都尉献计;再详叙叛军智谋之失:吴臣田禄伯出奇道、桓将军西进之策未被采纳。一篇之中,对“致反之由”“约初之状”“声势之大”“息兵之策”“破吴之计”“专智之失”等都进行详写,单对“吴军之败”一笔带过,只是略写,具体分析司马迁在《吴王濞列传》中“详因略果”之法的运用,认为可以成为文章详略之法的借鉴,分析深刻。
三是具体分析详略之法的效果。如李景星在评《留侯世家》时说:“子房乃汉初第一谋臣,又为谋臣中第一高人,其策谋甚多,若从详铺叙,非繁而失节,即板而不灵。且其事大半已见于《项》《高》二纪中,世家再见,又嫌于复,故止举其大计数条著之于篇。而中间又虚括其辞曰:‘常为画策臣,时时从汉王。’篇末又总结之曰:‘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用笔如此,乃觉详略兼到,通体皆是。”[6]54李氏假设司马迁若从详铺叙张良一生的策略计谋,不仅会“繁而失节”“板而不灵”,而且又会与《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相重复。因此,只略举“其大计数条”,且篇中篇末仅用简短之辞虚括和总结,这样就会达到“详略兼到”的效果。
总之,近现代关于《史记》叙事详略的评论,分析详略之事、详略之法的运用、详略之法的效果,都具体详尽,能给为文以指导。
二、对《史记》为文之法评论的丰富性
古人重视“文法”。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位体”“置辞”“通变”“奇正”“事义”“宫商”等文章写作法则。传统文章学中“文法”指“属文的方式、方法,其中包括具体写作中的技法,结构安排上的章法,表现过程中的手法,修辞造句中的词法等等。”[4]373然为文之法,当为“活法”,“法寓于无法之中”*唐顺之《荆川文集》(卷一○),《董中峰侍郎文集序》,四部丛刊初编。。关于《史记》文章方法之论,起于汉魏六朝。班固《汉书·公孙弘卜式倪宽传》中说:“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概括论《史记》文章之优。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南朝裴骃《史记集解》“三家注”揭示司马迁《史记》作文之法,唐独孤及论史迁文章“有以取正”,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苏轼、苏辙等皆学《史记》之文,自苏洵发现“互见法”,后世对此则多有评论。明茅坤评《史记》:“于中欲损益一句一字处,便如于匹练中抽一缕,自难下手。”说明司马迁文章功夫。明唐顺之评《项羽本纪》领会“大纲领”,清李晚芳评《项羽本纪》中“以义帝为关炤”(《读史管见》)。这些对《史记》作文之法的评论,多概括评价风格和效果。而近现代文人学者认为《史记》有丰富而广泛的为文之法。
一是评论《史记》为文方法灵活。如李景星认为《酷吏列传》文法灵活。他在《史记评议》中评论道:“《酷吏列传》开首曰酷吏独有侯封,罪侯封之作俑也。晁错非酷也,而亦先列之者,以其文法深刻,为用刑者之倡,故推本及之也。《张汤传》独详,以其为酷吏之魁也。叙杨仆,以其严酷,不详本末,意不在为仆传也。《杜周传》不终,以周为当时人,未有结束也。或前或后,或分或合,或单说,或互见,极行文之乐事,开无限之法门,那能不令人佩服。赞语与传,意义各别,传言酷吏之短,赞取酷吏之长,褒贬互见,最为公允。”[6]113说明文法多样以“极行文之乐事”。
二是评论《史记》为文技法之名丰富多样。近现代学者评论《史记》,概括出的行文方法名称多种多样。有“独力搏众兽”之法。李景星评《魏其武安侯列传》:“太史公用独力搏众兽手段构成一篇极热闹文字,真是神力。传以武安魏其为经,以灌夫为纬,以窦王两太后为眼目,以宾客为线索,以梁王、淮南王、条侯、高遂、桃侯、田胜、丞相绾、籍福、赵绾、王臧、许昌、庄青翟、韩安国、盖侯、颍阴侯、窦甫、临汝侯、程不识、汲黯、郑当时、石建许多人为点染,以鬼报为收束,分合联络,错综周密,使恩怨相结权势相倾杯酒相争情形,宛然在目。而武安侯田蚡,恃其宠骄,以琐屑嫌隙,倾杀窦、灌,此尤千古不平之事,故传又特意写出。曰蚡为诸郎未贵,往来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曰武安侯新欲用事为相,欲以倾魏其诸将相;曰武安由此滋骄;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曰使武安在者族矣。赞语又重责武安,曰‘迁怒及人,命亦不延,众庶不载,竟被恶言’。奇文信史,兼擅其长,宜乎于古今史家中首占一席也。”[6]98说明“独力搏众兽”之法能够对纷繁复杂的事件叙事精到,而且详细分析了《魏其武安侯列传》一篇之“经”“纬”“眼目”“线索”“点染”“收束”“线索”“特意之笔”等。
有“阶级法”“钩连法”。李景星评论《刺客列传》“行文用阶级法,一步高步步,刺君、刺相,至于刺不可一世之王者,刺客之能事尽矣。是以篇中叙次,于最后荆轲一传独加详焉。其操纵得手处,尤在每传之末用钩连之笔,曰:‘其后百六十有七年,而吴有专诸之事’;‘其后七十余年,而晋有豫让之事’;‘其后四十余年,而韩有聂政之事’;‘其后二百二十余年,秦有荆轲之事’。上下钩绾,气势贯注,遂使一篇数千言大文,直如一笔写出。此例自史公创之,虽后来迭经袭用,几成熟调,而兰亭原本,终不为损,盖其精气有不可磨灭者在也。”[6]79以《刺客列传》为例,详细分析文章写作之阶梯法、钩连法。
有转折之法。刘师培在《论文章之转折与贯穿》中说:“《史记》《汉书》之所以高于后代史官者,亦在善于转折。……虽述两事而文笔可相钩连,不分段落而界划不至漫灭;此其所以可贵也。”[7]127可见转折与钩连之重要。
有驰骤及顿挫之法。刘师培《史汉之句读》云:“文章本有驰骤及顿挫两种,《史》《汉》中二者皆不废。文章有顿挫而无驰骤则失之弱,有驰骤而无顿挫则失之滑。”[7]136文章当顿挫、驰骤并具不废。
有“收笔”之法。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篇云:“大家之文,于文之去路,不惟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其最擅长者无若《史记》。《史记》于收束之笔不名一格。如本文饱叙妄诞之事,及到结束必有悔悟之言;偏复掉转,还他到底妄诞,却用一冷隽之笔闲闲点醒,如《封禅书》之收笔是也。又痛叙奸谗误国,令读者愤懑填胸,述到收局,人人必欲观其伏诛,此似行文之定例;乃不叙进谗者之应伏其罪,偏叙听谗者之悔用其言,不叙用谗者之以间成功,偏叙诛谗者之不忠垂诫,如《吴太伯世家》之收笔是也。有叙开国之勋臣,定霸巨子,功高不赏,幸免弓狗之祸,却把其退隐之轶事尽情一述……寓其微旨,如《越王勾践世家》之收笔是也。有同等之隐事,同恶之阴谋,同时之败露,是天然陪客;文中且不说明,直到结穴之处,大书特书彼人之罪状,与本文两不关涉,然句中用一‘亦’字,见得同恶之人亦同抵于族,不加议论,其义见焉,如《春申君列传》之收笔是也。……此等收笔,直入神化。”[8]127论《史记》收笔之法多种多样。
有“关锁”“筋节”法。李景星评《李斯传》:“《李斯传》以‘竟并天下’、‘遂以亡天下’二句为前后关锁。‘竟并天下’是写其之所以盛;‘遂以亡天下’是写其后之所以衰。盛衰在秦,所以盛衰之故,则皆由于斯。行文以五叹为筋节,以六说当实叙。‘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云云,是其未遇时而叹不得富贵也;‘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云云,是其志满时而叹物极将衰也;‘斯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云云,是已附赵高计中不能自主而叹也;‘仰天而叹曰:‘嗟乎悲夫’云云,是已居囹圄之中不胜急悔而叹也;‘顾谓其中子曰’云云,是临死时无奈何以不叹为叹也。以上所谓‘五叹’也。记说秦王,著斯入秦之始也;记谏逐客,著斯留秦之故也;记议焚书,著斯佐始皇行恶也;记劝督责,著斯导二世行恶也;记短赵高语,著斯之所以受病,藉其自相攻击,以示痛快人意也;记上狱中书,著斯之所以结局,令其自定功罪,以作通篇收拾也。以上所谓‘六说’也。洋洋洒洒,几及万言,似秦外纪,又似斯、高合传,而其实全为李斯作用。文至此,酣畅之至,亦刻毒之至,则谓太史公为古今文人中第一辣手可也。”[6]80分析文章“关锁”“筋节”,见解独到。
有“筋脉”之法。如林纾在《春觉斋论文》中论及《史记》文章之“筋脉”:“太史公文,筋脉最灵动,亦最绵远。”《大宛传》“以张骞为总脉,则奉使诸国,遂可以连贯而下。”“然张骞中道陨谢……则直舍去张骞,又以宛马为脉。其下则处处言马,仍可将文势蝉联而下。”而《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筋脉之妙,别有神解。”[8]81
论《史记》文章有“关键”“眼目”“根”之法。李景星评论《游侠列传》“通篇以‘缓急人所时有’句为关键,以‘儒侠’二字为眼目,开首即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以侠之犯禁与儒之乱法者比,便非一味推许。以下遂以儒侠对发,见儒固有以文乱法,而季次、原宪等非其伦也;侠固有以武犯禁,而朱家、郭解等非其伦也。后文又以卿相之侠形出布衣之侠,而更言游侠之士与豪暴之士不同,以终一篇之旨,意思最为深厚,评量极为公允。”[6]116李氏又评《司马相如列传》道:“而又以‘好读书’三字,作通篇之根,以前后‘三为郎’作眼目,以下而见知女子,上而见知天子作照应,驱相如之文以为己文,而不露其痕迹,借相如之事为己写照,并为天下后世怀才不遇者写照,而不胜其悲叹。洋洋万余言,一气团结,在《史记》中,为一篇最长文字,亦为一篇最奇文字。”[6]109例证精准。
三是评论《史记》为文表现手法丰富多样。评论《史记》合传中以虚实之法表现人物。如李景星评论《屈原贾生列传》:“以古今人合传,一部《史记》,只得数篇。鲁仲连邹阳外,此篇最著。盖鲁仲连、邹阳,以性情合,此篇以遭际合也。通篇多用虚笔,以抑郁难遏之气,写怀才不遇之感,岂独屈、贾两人合传,直作屈、贾、司马三人合传读可也。中有‘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此数句,是一篇关键,亦是两人合传本旨,得此,而通篇局势,如生铁铸成矣。至于全部《离骚》,篇篇金玉,而屈原只载《渔父》及《怀沙》二篇。《渔父》若屈子沉江之志,《怀沙》乃屈子绝命之辞也。全部贾谊书,字字珠玑,而《贾传》独载《吊屈》《鵩鸟》二篇。《吊屈》见贾生怀古之贤,《鵩鸟》乃贾生超世之思也。他篇虽佳,在此传中,都用不著,故不得不从割爱,若无此明眼辣手,又乌得成其为太史公乎?赞语凡四转,全以骚赋联合屈贾,沉挫中有流逸之致。”[6]77-78认为司马迁安排屈原、贾谊合传,乃属“遭际之合”,文多用虚笔。
评论《史记》有“奇笔”“正锋”之法,增强表现效果。如李景星评《孟子荀卿列传》也论及虚笔与实笔之法。他说:“战国之时,诸子争鸣,而学术最纯者惟孟子,其次则荀子,故太史公此传,即以孟荀为题。文法以拉杂胜,与《伯夷列传》略同,但彼以虚写,此以实衬;又与《仲尼弟子传》略同,但彼用正锋,此用奇笔。合观通篇,其于诸子之中,独推孟荀,则如百川并流,而江河最显,其于孟荀之中,又归重于孟子,则如晨登泰山日观峰,遥望万叠云霞,捧出一轮红日,末后单出墨翟,更是奇中之奇……至他传赞语,俱列于后,此传置赞语于篇首,后不再出,亦是别格。”[6]69-70评论《史记》运用“正锋”与“奇笔”之法,其文别具一格。
评论《史记》有烘托法。如郭嵩焘评论《项羽本纪》:“案项王自叙七十余战,史公所记独巨鹿、垓下两战为详。巨鹿之战全用烘托法,不及一战事,而于垓下显出项羽兵法及其斩将搴旗之功。项羽英雄,史公自是心折,亦由其好奇,于势穷力尽处自显神通。巨鹿、鸿门、垓下三段,自是史公《项羽本纪》中聚精会神、极得意文字。”*郭嵩焘《史记札记》(卷五上)。《项羽本纪》用烘托法,成为司马迁极得意文字。
评论《史记》有旁敲侧击法。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信陵君这样一个人,胸襟很大,声名很远。从正面写,未尝不可,总觉得费力而不易出色。太史公就用旁敲侧击的方法,用力写侯生、朱亥,写毛公、薛公,都在这小人物身上着笔,本人反为很少。因为如此,信陵君的为人格外显得伟大,格外显得奇特。这种写法不录文章,不写功业,专从小处落笔,把大处烘托出来,除却太史公外,别的人能做到的很少。”[9]81旁敲侧击法的运用,把信陵君写得生动传神。
四是评论《史记》句法、词法丰富多样。李景星评《酷吏传》“立格遣辞,以短悍为主,以穿插见长……叙酷吏之所以见用,曰‘上以为能’,曰‘天子以为能’,曰‘天子以为尽力无私’。叙酷吏之转相效法,曰‘治效郅都’,曰‘治效于禹’,曰‘声甚于宁成’,曰‘治放尹齐’,曰‘治与宣相放’,曰‘治大放张汤’,曰‘酷甚于温舒’。”[6]113-114评《史记》词法“以短悍为主,以穿插见长”,评论精妙。
论《史记》句法“劲炼”。陈衍以《吴王濞传》为例评论《史记》句法:“《史记》叙事以简洁见工者,如《吴王濞传》云:‘吴兵欲西……士卒多饥死,乃畔散’。条理井然。上云‘欲西’,下即云‘不敢西’:上云‘欲战’,下即云‘不肯战’,又云‘数挑战’;上云‘走条侯军’,下云‘夺条侯壁’;中必先云‘条侯壁’,乃使于易军言壁也。下文言‘条侯使备西北’,上两言西,下两言西北,中一言东南;上言‘卒饥’,下言‘多饥死’,皆条理也。而句法特劲炼,如短兵相接然。多二字、三字以至四字、五字,最长者惟一句,亦仅六字。”[10]32认为《史记》叙事有条理,句法“劲炼”,简短有力。
评论《史记》词法“每得言外之神”。刘师培评论《史记》用词“每得言外之神”,“尝有词在于此而意见在于彼之处。以其文中抑扬顿挫甚多,故可涵泳而得其意味。”[7]130
评论《史记》语句有“累叠”之法。钱钟书评论《项羽本纪》《袁盎晁错列传》:“《项羽本纪》写‘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马迁行文,深得累叠之妙,如本篇末写项羽‘自度不能脱’,一则曰:‘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再则曰:‘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三则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心已死而意犹未平,认输而不服气,故言之不足,再三言之也。又如《袁盎晁错列传》记错父曰:‘刘氏安矣!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叠三‘矣’字,纸上如闻太息,断为三句,削去衔接之词,顿挫而兼急迅错落之致。”[11]272-273句子、词语累叠,文意得到强化。
总之,近现代学者或总体评论《史记》文法,或以单篇传记论属文技法,或选取典型篇目论述表现手法,或举例论说句法、词法,内容广泛,涉及面广,名称繁富,多种多样,丰富了文章之学。
三、对《史记》“文有主旨”评论的集中性
文章学认为,主旨是文章通过内容表达出的基本观点,是文章写作的目的和意图,是文章的核心。《易·系辞下》谓“其旨远,其辞文。”指文章用意深远。《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论及文章应当“其调也尚远,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贵当,其辞也欲巧。”文章应当“调远”“旨深”“理当”“辞巧”。
关于《史记》“为文主旨”,历代评论较多,然大多都是评论整部《史记》撰作之主旨和目的,较少从文章学角度评篇章主旨。清王又朴《史记七篇读法》曾评《项羽本纪》的主旨在于阐明“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之理,是以明“道”为矢的。评论《淮阴侯列传》,称“以报德不报怨为微旨”,且言“赞内‘学道谦让’四字是一篇纲领”。近现代文人学者评论《史记》,则主要集中在评论表达主旨之方法。
一是论《史记》文章以一线贯穿表达主旨。如陈衍认为“《史记》有通篇命意一线到底者。《淮南王列传》始言时欲畔逆未有因,继言拊循百姓为畔逆事,继言谋反滋甚,继言计犹豫十余日未定,继言王自度无何不发,继言王从故不发,又继言淮南王患之欲发,又继言恐国险事且觉欲发,又继言王欲发国中兵,又继言计未决,断言未发,继言欲杀而发兵,又言王犹豫计未决,又言王以非时发恐无功,又言王欲偷欲休,是始终未发而反也。乃忽总承以一笔云:‘伍被自诣吏,因告与淮南王谋反,反踪迹具如此。’”[10]16《淮南王列传》通篇淮南王谋反为主旨,统领全篇。陈衍还评论《萧相国世家》“叙何功特简,叙何所以委曲获全者甚详”,写萧何因功受封“三大段,命意一线”[10]16。
再如李景星评论《平准书》:“盖平准之法,乃当时理财尽头之想,最后之著。自此法兴,而闾阎之搜括无遗,亦自此法兴,而朝廷之体统全失。太史公深恶痛绝,故不惮原原本本,缕悉言之。开端曰接秦之弊,已有无穷之感。继曰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只一变字,所有后来层层坏政,一齐摄入其中。末以卜式事作收,非尊式也,正以其甚务财用诸人,谓此乃善于谋利之卜式所不忍为也。烹弘羊,天乃雨,六字结束,有声有色。赞语从历代说到秦,更不提汉事,正与篇首接秦之弊遥应。其意若曰,务财用至于此极,是乃亡秦之续耳。”[6]35认为《平准书》以“平准法”一线贯穿、逐层深入、首尾呼应,表达主旨。
再如陈柱评论《孟子荀卿列传》:“此文以孟荀为主,仁义为线索。孟子荀卿主仁义者也,邹衍则始滥而终仁义,其余如淳于髡之徒,则或专志乎利矣。吴汝纶云:‘姚郎中言作文如小儿放纸鸢,愈放愈高,此在手中线牢耳。此文叙邹衍著书,即姚氏纸鸢之说。’此说是也。”[12]文中线索明显。陈柱还评《李斯传》以叹字为线索。“此篇以叹字为线索。由李斯之一生,以叹字为生活也。盖李斯一生以喜富贵,悲贫贱为主。其未得之也患不及之,则不得不叹矣。乃其既得之也,又患失之,则又不得不叹矣。苟患得之,无所不至,则尤不得不叹矣。”[13]这些评论都认为《史记》为文用“一线贯穿”表达主旨。
二是论《史记》文章以人物体现主旨。梁启超认为《史记》以传主人物体现主旨。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人的专史》中说:“一个人的性格兴趣及其作事的步骤,皆与全部历史有关。太史公作《史记》,最看重这点,后来的正史,立传猥杂而繁多,几成为家谱墓志铭的丛编,所以受人诟病。其实《史记》并不如此,《史记》每一篇列传,必代表某一方面的代表人物。如《孔子世家》《孟荀列传》《仲尼弟子列传》代表学术思想界最重要的人物,《苏秦》《张仪》列传代表造成战国局面的游说之士,《田单》《乐毅》列传代表有名将帅,四公子《平原》《孟尝》《信陵》《春申》列传代表那时新贵族的势力,《货殖列传》代表当时经济变化,《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代表当时社会上一种特殊风尚。每篇都有深意。大都从全社会着眼,用人物来做一种现象的反影,并不是专替一个人作起居注。”[9]41说明《史记》一些篇章主旨是通过人物体现的。
三是论《史记》文章以某字词联络主旨。如吴汝纶在《点勘史记》中说,《越王句践世家》“以‘忍’字为主。句践能忍亡国之耻而霸,陶朱长男不能忍开千金而杀其弟。”*吴汝纶《点勘史记》,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李景星评论《越王勾践世家》时说:“越之上世世系事迹,皆荒略无稽,惟句践之事最详,故太史公于此篇不曰《越世家》,而曰《越王勾践世家》。通篇极写句践之霸越,而佐句践以成霸业后,厥惟范蠡,故以范蠡传附之。其君臣得力处,只是一个‘忍’字,故一路叙事,即以此作骨。”[6]44认为《越王勾践世家》以“忍”字为其主旨。再如吴汝纶评《吕不韦列传》以“贾”字为主:“此篇以‘贾’字为主。立楚子进美姬,所以贾利;作《吕氏春秋》,所以贾名;进嫪毐、所以贾祸。而贾祸之由,则自进美姬始。作《吕览》事颇难入此篇中。文以家僮万人,引起食客三千人,因入宾客著所闻为书,又以悬金市门终之,仍寓贾人伎俩,与前居奇钓奇为一类,此可识文字联络之法。不韦相业甚伟,兼能文章,而史公以贾人待之,是其识力闳远处。”以“贾”为主旨联络全篇。再如陈衍论“《留侯世家》始终以计策二字作主”[10]17,字词联络主旨,线索明晰。
因此,关于《史记》文章主旨,近现代学者大都评论表现主旨之法,体现出一定的集中性。
参考文献:
[1] 张新科.论清代的《史记》文学评论[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57-65.
[2] 张新科.《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及其意义[J].文学评论,2012(5):144-156.
[3]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M].黄霖,导读.黄霖,整理集评.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4] 任遂虎.文章学通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5]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卷17 [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6] 李景星.四史评议·史记评议[M].韩兆琦,俞樟华,校点.长沙:岳麓书社,1986.
[7] 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8] 林纾.春觉斋论文[M]//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范先渊,点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9]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人的专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
[10] 陈衍.史汉文学研究法[M].无锡: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11] 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2] 陈柱.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讲记[J].学术世界,1935(6).
[13] 陈柱.李斯列传讲记[J].学术世界,193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