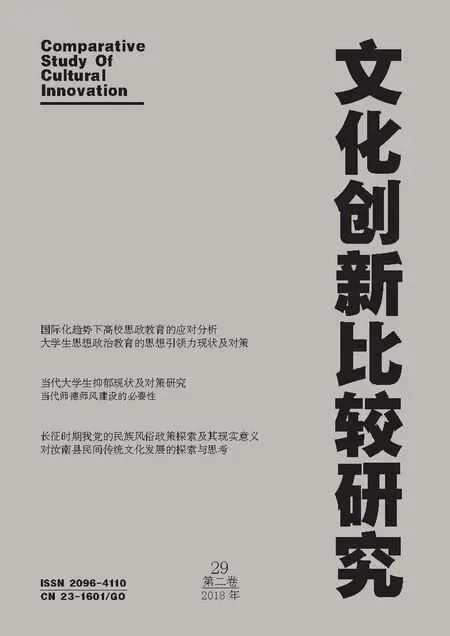19世纪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海盗问题探析
2018-03-07卢虹
卢虹
(云霄县博物馆,福建云霄 363300)
19世纪,清政府施行海禁政策,进行私人海上贸易的船舶只能从厦门港出发,每年11月到次年3月间,大批私人商船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涌向中国南海,商船靠近巴拉望和沙捞越周边海域就等于进入了“三不管”地带,极其容易成为各种海盗的目标。从印度洋经马六甲海峡返航至南海的商船被海盗劫掠的情况也相当严重。从马六甲海峡经苏门答腊岛至加里曼丹岛,海盗会盘踞于这一区域内的珊瑚岛上来俯视沿途经过的商船,来自欧洲或者由印度来往亚洲商船频繁遭受劫掠之灾。
1 海盗来源及活动情况
猖獗劫掠商船的海盗大部分来自苏禄群岛和婆罗洲、苏拉威西岛,海盗的快速帆船装备齐全,从棉兰老岛出发,几乎每年都不间断地在东印度群岛和马来半岛至南海海域进行扫荡。来自苏拉威西岛南面的布吉斯人是海盗群体的主要构成,他们充满智慧又富于侵略。最初,欧洲人与东印度群岛的统治者争夺香料控制权,都争先雇用布吉斯人,布吉斯人经常代表荷兰人去讨伐那些与其发生纠纷的马来半岛统治者。这群海盗技术娴熟,但是他们的船舶设备简陋,在风暴来袭之际,凭借对马来半岛—东印度群岛—菲律宾群岛各种地形的掌握,毫不费劲地找到避风港。久而久之,这种对航线的快速判断能力是海盗可以成功避开清剿的关键所在。
荷兰人在马来半岛失势之后,布吉斯人自立门户、招徕人手。到了19世纪30年代,东南亚海域的海盗人数剧增。马来半岛、中南半岛、东印度群岛及菲律宾群岛的大陆出海口时有海盗隐匿其中,河道两岸的茂密森林经常有海盗蹲守,待有商船进入,顷刻窜出,杀人越货。除了由雇佣兵演变而来,其余海盗的出身无不相似,“他们大多是破产的渔民与农民,由于贫困和缺乏文明礼教,变得贪婪和缺乏信仰,手段极其恶劣,在马来半岛上已经臭名昭著。”这些各种身份的海盗,劫掠之余主要从事渔业,海盗活动的发生取决于季风和海上贸易活跃指数的规律。2月到3月,海盗活动有所减少,这阶段则忙碌于捕鱼、打捞海带以及在闲暇时到各个港口收集各地商船出发的情报。较具规模的布吉斯海盗通用的帆船一般由30块船桨组成,这些船桨用麻绳按一定角度的坡面安装,每把船桨重达4磅,另外配有舷炮,每名水手配有步枪、长矛。劫掠方式比较随意,遇到一些独立航行的船舶,便在其未有觉察时悄悄尾随伺机而动。
新加坡东海岸,每年都有不止一艘的商船像献祭一样落入海盗的虎口,航行在中国至东南亚的一些商船甚至包括途经马六甲海峡至马尼拉越洋前往太平洋的商船客轮大部分犹如惊弓之鸟,英属海峡殖民地的商人更是惶恐不安,认为海患甚于内部安危,海盗未除,他们的生存、财产、经营等便岌岌可危。来自苏禄与棉兰老岛的海盗,每年都会驾驶他们的快速帆船光顾马来半岛,苏拉威西的布吉斯海盗也频繁洗劫新加坡。布吉斯海盗劫掠船只同时还热衷于奴隶贸易,甚至在英属海峡殖民地建立前频繁将劫持而来的人口进行贩卖,英国人盘踞马来半岛后,布吉斯的海盗往往让英商们闻风丧胆。来自马来半岛周围的海盗无时无刻不影响途经此处的贸易。“1832年,10月一艘舢板拖网公司所属的商船运载着大批鸦片、烟草以及由全副武装的33名船员准备前往彭亨,途中遭到6艘快速帆船海盗的洗劫。”半岛的鸦片供应开始短缺,商人们开始为获得鸦片而陷入烦恼。
这一区域的海盗问题极其深刻,运往马来半岛的物资不断遭到劫掠,半岛与英属殖民地的物价高涨,商人备受其害,1832—1833年,新加坡华人商会自发组织了几艘船舰在各港口进行巡逻。“1833年11月,海盗又袭击了吉打附近行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炮舰,这艘炮舰竟然被打得无力反抗,疲于奔命。”另有婆罗洲沿岸基本上毁于达雅克海盗之手。
2 海盗猖獗的根源
2.1 海盗活动职业化
海盗首领的位置一般世袭祖传,并默认海盗已然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甚至更加专业化。通过吸收破产渔民,海盗认为自身的行为充满正义感,甚至认为其一系列劫掠是劫富济贫的行为。“在他们认为这些海盗行为并不是犯罪,而是祖先延续给他们的传统,后代们只是承袭祖传家业;事实上,来自婆罗洲的海盗认为其一系列的巡航都是值得尊敬的行为,只有正人君子才有资格从事。”到了1825年,海盗群体的更职业化,队伍的分工更精细,从槟榔屿到新几内亚群岛,爪哇到菲律宾群岛等一系列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到处可寻海盗快速帆船的踪迹,频繁可闻他们扫荡劫掠贩卖人口的事件,另外在苏禄群岛、文莱、苏门答腊等地方都存在兴旺的海盗销赃、奴隶买卖的市场。
2.2 与政治势力的联系
海盗不仅是属于治安范畴,还与东南亚各种政治势力间错综复杂的争斗联系颇深。“当岛上的政治势力分化时,各苏丹王国在半岛上相互攻伐,而海盗则奉命相互劫掠;当岛上的势力和平重组时,海盗则转向掠夺非半岛势力的船只。”有着半岛上的政治势力的支持,海盗便变得有恃无恐,海盗掠夺渐渐成为一种职业,海盗们也无罪恶感可言,当然这也是环境的宽松所致。例如,半岛上的王国通过支持海盗的行为来损害其邻国的利益,因此海盗事业就在该国苏丹的支持下蓬勃发展起来,“荷兰与英国人一度怀疑廖内-龙牙苏丹与海盗相互勾结,支持海盗的劫掠。其他国家的苏丹,甚至参与支持且同海盗分赃,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布吉斯雪兰莪苏丹。”海盗们劫掠完毕也要寻找下家来卖掉赃物,为得到这些财富就不得不寻找与收购商有联系的政治势力来充当保护伞。然而这些海盗也不是从一而终的,当这些保护伞意图占据大部分财富时,海盗便背叛他们,去寻找其他政治保护伞,甚至会反过来劫掠他们的旧主子。
2.3 欧洲势力对海盗活动的消极态度
19世纪前,海盗劫掠时会避开欧洲装备精良的船队,每次的海盗劫掠事件的发生都建立在最低风险之上,海盗们的帆船规模较小,配置较为低矮的风帆以及简陋的武器,他们认识到去袭击欧洲装备精良的商船必将血本无归。被袭击的欧洲商船一般是那些搁浅迷途的,海盗一般不主动去袭击,而是追逐驱赶这些商船进入一些没有通道的港湾,在其弹尽粮绝时才发起攻势。
除去以上这些特例,欧洲商船基本上很少受到海盗的袭击,遭袭的对象主要是来自中国的、一些规模较小的、没有很好装备的、缺乏影响力的私人舢板。因此19世纪前海盗活动很容易给欧洲人造成一种不足为患的假象,这就客观上助长了海盗的猖獗气焰。1807年英国政府战备用途的小型单桅帆船“胜利号”在爪哇遭遇了一艘婆罗洲海盗船,英方在未觉察的情况下就被对方全副武装的水手偷袭,“胜利号”的船尾遭到重创,据统计,大约有三十几名船员被杀。类似这样的欧洲船舰被袭的事件在19世纪初开始频繁发生。19世纪30年代英国加尔各答当局虽然也开始对海盗感到恐惧,但是并不就意味着要采取行动。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孟买也只有一小块海军基地,海峡殖民地孟加拉舰队必须听从他们的调遣,这时印度总督本廷克正专注于参加竞选,对前往中国的贸易也没有多大兴趣,对海盗的袭击也无动于衷,“他甚至提议废除公司在此的海军,来赢得支持率”
这半个世纪欧洲陷于相互之间的交战,引发混乱的政治与经济模式,中南半岛、马来半岛、东印度群岛上的政治势力相互攻伐,忽略了对海盗的治理。另外由于各种势力暗中扶持海盗劫掠对手的商船,就为海盗提供了战略上、物质上的支持,无形中助长了海盗气焰,海盗更加有恃无恐公然挑战欧洲势力。
3 结语
19世纪前的东南亚海丝一线的海盗活动类似于“散兵游勇”的独立、分散经营,但是随着劫掠区域的扩大、财富的积累、武装的逐步精良。19世纪后海盗群体开始呈现吞并小群体、垄断、一家独大的趋势,最典型体现于布吉斯海盗由原先星罗棋布于南海到东南亚的海丝沿线各自经营到婆罗洲达雅克海盗的一家独大。随着东南亚局势的复杂化,海盗活动开始呈现出一种可以洞察的规律:各种政治势力互相攻伐时就是海盗活跃之时,政治势力的代表们不约而同地接洽海盗,收买海盗头目进攻对手的船舰、商船,海盗也是乐意为之;劫掠完毕,政治势力在充当保护者、情报提供者的前提下与海盗瓜分赃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