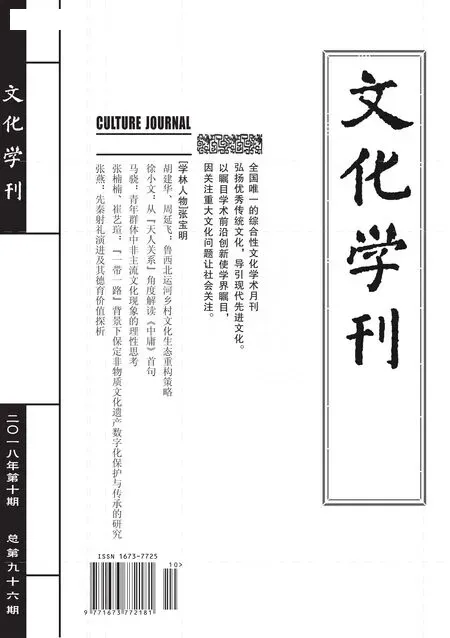宫廷文人的日常生活与齐梁宫体诗的价值取向
2018-03-06向恩锐
向恩锐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宫体诗的创作在鲍照等人笔下便已产生,但宫体诗之名产生于萧纲入主东宫后与身边的文人互相唱和,因其内容多以宫廷生活及男女私情为主,形式上追求词藻靡丽,故而名为宫体诗。宫体诗的价值取向是基于齐梁宫廷的日常生活文化,它不仅以日常物品入诗、以日常行为入诗,更是无所顾忌地在诗中注入日常情感的表达(其中以女性情感为主)。
一、日常生活文化在宫体诗领域的发展
总的来说,自魏晋以后,日常生活文化开始进入文学创作,这种对于日常生活文化的纵容到齐梁宫体诗创作中达到鼎盛。日常生活文化的融入意味着人的自我意识在诗中的觉醒,人们不再压制自己的感情而选择正视它。这种对于日常生活文化的尝试创作从魏晋开始一直延续到宋,至明清时期才逐渐不占主流地位,但类似的创作仍在继续。纵观整个发展过程,魏晋是开始阶段,齐梁是探索阶段,唐朝是成熟阶段,宋朝是完成阶段。明清时期,由于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控制,大力宣扬儒家伦理纲常,将人的正常私欲也归于禁忌的范围,由于得不到统治阶级的允许,文人开始在诗中有意避写日常生活文化,而着重渲染儒家伦理道德和圣人思想,但这并不影响业余文人对于它的描写。齐梁宫体诗在探索阶段主要是对日常生活文化的大力宣扬,因而从中暴露出不少弊端,然而正是这些弊端,给唐宋时期的文人创作提供了经验,使他们在“放”的基础上开始有意识地“收”。因此,笔者认为唐朝文化的繁荣并不只是一个朝代文人的努力,而是承继先秦至隋以前千年的文化在唐朝历史环境中的一次文化大爆发。
本文认为日常生活文化在诗歌领域的发展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即日常物品、日常行为和日常情感,而这三个方面又因其自身特性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首先是日常物品的入诗扩大了意象的范围,开阔了文人的眼界,启示后继文人在创作时凡所看、所听、所取之物皆可入诗,由此,诗歌系统得以不断发展,并创造出一个庞大的具有中国古典美学意识的意象群。其次是日常行为在诗中的运用大大刺激了宋一代士大夫文化的发展,在时代环境的刺激下,娱乐活动雅化,诗中所描写的日常行为也更加符合文人士大夫的身份要求。最后,日常情感的入诗影响了明清小品文等文体的发展,促使文学创作从政治教化中独立出来,诗文不再只是枯燥乏味的圣人说教,并至此开拓出一条新的具有独立文人审美意味的文学发展道路。
二、齐梁宫体诗的价值取向
(一)日常物品的入诗
以日常物品入诗,扩大了诗中可取意象的范畴,不仅将镜、灯、扇等日常生活用具写入诗中,还将女子日常所穿所用也写入诗中。如庾肩吾[1]《咏美人看画诗》中写道:“绛树及西施,俱是好容仪。非关能结束,本自细腰肢。镜前难并照,相将映渌池。看妆畏水动,敛袖避风吹。转手齐裾乱,横簪历鬓垂。曲中人未取,谁堪白日移。不分他相识,唯听使君知。”[2]该诗不仅以镜子、美人衣裙和首饰入诗,还将女子的形态也描写得十分细致。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宫体诗的创作虽流于形式,但它促进了咏物诗的发展,它促进了咏物诗中意象的独立审美价值,为咏物诗的创作开启了一个新的方向。在宫体诗之前,诗人作诗借景抒情,往往使用情景交融、物我两感之类的表达手法,诗中所写意象不过是自己人格化的外向表现,意象只是作为情绪的一种言说方式存在,不具有独立的意义。而在宫体诗创作中,意象处于独立的地位,诗人在状物时,只是在写意象的本身,因而这些意象得以还原本性,以一种独立的审美价值在诗中存在。如《山池应令诗》:“阆苑秋光暮,金塘牧潦清。荷低芝盖出,浪涌燕舟轻。逆湍流棹唱,带谷聚笳声。野竹交临浦,山桐迥出城。水逐云峰暗,寒随殿影生。”[3]庾肩吾作为文学侍从,其诗大部分为应制唱和之作,这首诗即是萧纲《山池》的和作,全诗只是一首单纯描写秋天景观的咏物诗,看不出诗人有何寄托,反倒是真实还原了当时秋日暮时的风景。
(二)日常行为的入诗
既然是宫体诗创作,那么它的描写范围也仅限于对宫廷娱乐活动的描写。自魏晋起,人们逐渐开始追求日常生活的享乐,而在宫廷娱乐活动中的日常行为无非是宴飨奏乐、应制唱和,所以宫体诗的创作内容以统治者和身边文人的唱和及对当时宴会情景的描写为主,这类宫体诗诗风伤于轻艳、缺乏内容、流于形式,因此只能努力追求形式上的突破,以声律的工整、句法的对偶、辞藻的华丽为主,这种发展是对永明体的“四声八病”的继承,同时也为律诗在唐诗的完成奠定了基础,是古体诗向近体律诗转变的过渡阶段。如《咏花雪诗》中写道:“瑞雪坠尧年,因风入绮钱。飞花洒庭树,凝瑛结井泉。寒光晦八极,同云暗九天。已飘黄竹路,共庆白渠田。”[4]其中,“年”“钱”“泉”“天”“田”押先韵,用词对仗工整,平仄除“洒”“庭”“井”“光”“晦”“八”外,其他已符合律诗的平仄标准。
(三)日常情感的入诗
自魏晋以来,自我意识的觉醒赋予欲望的合理性,人们开始重视己身的情感,但在魏晋时期,人们对于情感的表露仍处于压抑时期,期于通过谈玄使自己的情感处在一个理想的状态。到了齐梁,受其生活条件和乐府民歌的影响,人们开始释放自己真实的情感,这表现在对男女感情的书写上。宫体诗在写男女感情时习惯将最后的感情表达引入床帏之内,营造一种暧昧不清的氛围,以至于萧纲在写其妻时在最后特意点明“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咏内人昼眠诗》)[5]这种感情大多从女性的角度出发,从女性本身正视女性的情感需求,而不是作为男权的附庸应该有什么行为举止及情感。在此之前,儒家所主张的“发乎情,止乎礼”,压抑了男女情感的表达,而《女诫》《女训》等书又是从男性的角度对女性提出的种种要求,这些都没有从女性真实的情感出发。宫体诗则突破了以前种种束缚,写了大量从女性角度出发的抒发感情之作,这些情感虽然含有艳情的成分,但也是对女性情感的一种正视[6]。如《咏主人少姬应教诗》:“故年齐总角,今春半上头。那知夫婿好,能降使君留。”[7]女性开始在诗中大胆表露自己的心声,同时,这种真实情感的表露带来了女性形象审美的转变,即从神话到现实的转变。以前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女性形象,如《楚辞》中的湘夫人、山鬼及《洛神赋》中的洛神等,都是以一种神的姿态给人一种朦胧美。就算不是神女的形象,对其外貌姿态也没有具体的描写,如《陌上桑》中对于罗敷美貌的表达是通过外人在看到罗敷时的种种表现,即从侧面去烘托罗敷之美,而对其究竟是何等面容并没有细致的描述。到了宫体诗中,因其对于女性的描写也如同对器物一般的审美观照,使诗中的女性形象变得鲜活立体起来。如“细腰宜窄衣,长钗巧挟鬟。”(《南苑看人还诗》)[8]“安钗等疏密,着领俱周正。”(《咏美人看画应令诗》)[9],这些细节的描写使人们得以看到不一样的女性姿态,使女性人物形象变得真实可感,在人物描写方面是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