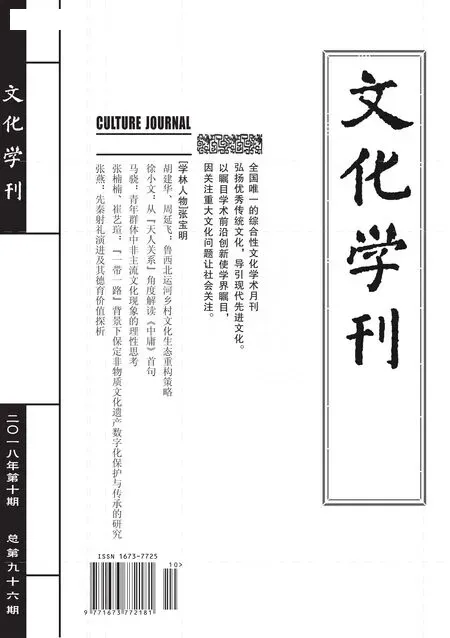先秦射礼演进及其德育价值探析
2018-11-15张燕
张 燕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上海 201418)
与先秦时期“冠礼”所关注的是对即将成年之人的德育品行的先行性教育不同,先秦“射礼”所关注的是对成年之后参与者道德品行的检视与再教育。前者的教育带有期许性,后者的教育带有检验性,这便是冠礼与射礼的最大不同。因此,在射礼复杂的仪程规范下便展示出对于德行的高要求,这是射礼德育教育功能最突出的表现,而这一表现的形成往往伴随着射礼的演进循序而成。
一、“射”之起源与演进
关于“射”的起源,为世人所熟知当属唐孔颖达言:“其射之所起,起自黄帝,故《易·系辞》黄帝以下九事章云:‘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世本》云:‘挥作弓,夷牟作矢。’注云:‘挥、夷牟,黄帝臣。’是弓矢起於黄帝矣。《虞书》云‘侯以明之’是射侯见於尧、舜,夏、殷无文,周则具矣。”[1]此处“射”的重要功能已经专注于武力,目的是借助弓利以威天下。后世学者大都以此为依据,遍寻史料来证明射礼“周则具矣”的盛况,以及寻找“夏殷无文”的原因。不过,随着出土资料的发掘“夏殷无文”的说法已无法成立,也因此得见较为全面的射礼演进与发展的过程,在此基础上,笔者所关注的是:伴随着“射”由单纯的狩猎活动转变为“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军事活动,“射”之活动也逐渐被赋予了具有礼仪规范性质的德育教化功能。
事实上,弓箭的出现本身便是时代发展的标志:“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需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2]。因此,弓箭的发明、使用及其对于蒙昧时代的作用“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3]。1963年山西朔县峙峪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一件燧石箭头,用很薄的长石片制成,尖端同正,肩部两侧变窄似呈铤状。结合过去萨拉乌苏河、水洞沟遗址也曾见到石镞的实物材料,说明弓箭的最初使用,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4]”显然,弓、弦、箭作为生产工具服务于生活,正是学界所普遍认可的观点即“射”衍生于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狩猎活动。
在后世所追述的文献记载中,以后羿为典型,其作弓习射也常见于生活中,如《左传》襄公四年所云“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5],又如《论语·宪问》“羿善射”[6]。而后羿所擅长的便是改制弓箭,如《墨子·非儒下》“古者羿作弓”[7],又如《吕氏春秋·勿躬篇》“夷羿作弓”[8],同时后裔还善于教人习射,如《孟子·告子上》“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9]。后裔事迹中所聚焦的善射作弓及教人习射的记载,正反映出源起于狩猎的习射活动确实是人们得以生存的最基本技能,一直延续保留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这一点在《诗经》的相应篇章中便得以验证,例如《诗经·齐风·还》《诗经·齐风·卢令》等篇章便描写了普通百姓行猎以及猎手之间相互尊重和技能相较的场景。
1966年春在江苏沛县大墩子遗址,其时代相当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在此遗址的第316号墓中,葬有一具中年男性的尸骨,“长1.64米,在左股骨上,发现被骨镞射伤痕迹,三角骨镞残段射进人骨达2.7厘米,骨镞尚留在骨内”,据研究者推测“死者中箭原因,很可能是在集体围猎时,被同伴所误伤”[1O],得出结论的依据主要来自于墓主人右手中的骨匕和左肱骨下的石斧。不过,这条史料大都被学者应用于证明原始弓箭所具有的强大杀伤力,加上弓箭本身“以威天下”的作用,则弓箭的应用便不仅仅应用于狩猎活动,原始弓箭所具有的强大杀伤力正是其日后入主战争武器的最直接原因。
二、先秦射礼性质的转变及射礼的特征
至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商周,伴随着殷商甲骨及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出土,有关“射”的记载为我们研究先秦射礼性质的转变提供了宝贵资料,而随着其性质的转变,单纯的“射”也便演化成了内涵丰富的射礼。
(一)商代习射及射礼的特点
1991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发掘出土了一个编号为91花东H3的甲骨坑,在刻有文字的有689片甲骨中,有一部分甲骨专门记载了殷商时期的“射”,再结合商代晚期的青铜铭文对于“射”的记载,可以看出商代习射及射礼存在着如下特点:

其次,商代贵族子弟所进行的习射活动已经颇具规模的礼仪活动。
《花东》7:“己亥卜,在吕:子●。弜射于之,若。[16]”
综合看来,商代射礼呈现如下特征:
其一,与单纯的习射的教育性活动不同,商代射礼是一场持续时间约二十余日的大型礼仪活动,以《花东》37所记载的射礼所持续的时间为例:从甲午起,至乙卯日,已经持续了二十二日。在这一过程中,问卜求吉贯穿始终,也说明了商代贵族对于射礼活动的重视。
其二,随着进程的推进,商代射礼也出现了程式的变化,例如“射礼仪程的高潮是在甲午‘弜射于之’后第12日乙巳日出之际的‘弓’、‘彝弓’和第13日丙午‘疾弓于之’,以及第15日戊申的‘乎匄马’、‘疾弓用射崔’,地点都在地”,在这一过程中展示出了“‘弓’、‘彝弓’、‘疾弓’,可能指常规射、慢射、快射三种不同的射仪,或三种不同弓的习射竞技。[19]”除了三种不同的射仪之外,在射程中,还讲求射箭者之间的竞争,因此才有“叀三人”的记载,谓“三人竞射得中”,因其射技出众,得以计入龟甲,这本身便是对其技能的褒奖。

再次,在射礼过程中,关注对参与者习射技能的评判。例如《作册般铜鼋》:“丙申,王于洹,获。王射,(作册般)射三,率,亡(无)灋(废)矢。[20]”其中“亡(无)灋(废)矢”便是对作册般射箭技能的赞许,除了参与射礼本身便具有纪念意义而言,专门将优秀的射技评定记于器皿之上,无疑是此次纪念活动的点睛之笔,原始狩猎行为与程序化的礼仪规则相结合是此时期射礼的最大特征。
(二)周代射礼特点
行至周代,射礼日趋成熟,是学界研究射礼的主阵地,在继承殷商射礼的基础上,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
其一,种类多样化。据《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谷梁传》等能够反映周代礼制的文献记载来看,周代时期的射礼主体类型有四:大射、乡射、宾射和燕射,另有其二:主皮之射和军旅之射。从不同射礼的目的或功用来看,射礼又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服务于王室贵族,大射礼用于天子、诸侯郊庙祭祀时参与祭祀及陪位人员的选择,宾射礼用于天子、诸侯飨来朝之宾、燕射礼用于天子、诸侯燕群臣与宾客。第二类乡老、乡大夫及群吏以礼会民。第三类主皮射之礼,此项射礼还保留着“射”的源起含义,是指大田狩猎后颁赐余货之射,只是因大田狩猎活动归属于王室,那么参与此礼及获得颁赐的对象集中在诸侯、卿大夫、士、群吏等阶层。第四类甲革勘质之射即军旅之射,目的是为了“试弓习武”。由此可见,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21]的周代社会,射礼在融入于祭祀和军事活动的同时,贯穿于飨宾、燕宾、礼民等重大活动中,其地位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其二、程序复杂化。事实上,礼射是研究先秦传统礼仪的主要类型,射礼的仪程结构严谨,层层推进。以《大射礼》和《乡射礼》所记进行比较,两者的礼仪进程基本一致,均经历了射前准备、一射、再射、三射和射后燕饮等环节,前者所推进礼仪程序有五十余项内容,后者所推进的礼仪程序有六十余项内容,不同之处在于:大射礼更注重射礼过程及射后燕饮中的主宾关系,乡射礼则更注重对三射参与者的礼仪规范及射技表现。
其三,射礼议程中将对道德品行的凝练与检验置于核心位置。正如姜楠先生所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其实用价值逐渐为审美价值所取代,并演化为一种礼乐传统。自孔子之后,‘射’再次摆脱了外在修饰的色彩而转为内在的道德实践。[22]”这样的转化,便决定了在射礼演进的进程中,更看重的是对内化于心的道德品行的检视,而射礼繁杂的议程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层层保障。
三、射礼的德育功能与价值
有关射礼的目的,在《论语·八脩》中有所提及:“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23]。这里的射已经不是射猎或军事之射,专指礼乐之射,由于每个人力量大小的不同,这里的射技也不再专注于射透箭靶,只要能够射中即可,并且这一现象已经成为传统的习惯被认可继承下来,也就是“古之道也”。这样一来,仅以准确度来定胜负便不足以支撑一场盛大的礼仪活动,那么射礼的根本目的又是什么呢?
《礼记·射义》有明确记载:“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24],唐孔颖达疏:“射义者,以其记燕射、大射之礼,观德行取于士之义。[25]”已经明确地指出:射礼最重要的目的便是通过繁琐的礼乐仪程来检验与射者的德行,达到“观德取士”的目的,使衍生于原始涉猎的活动,通过竞技的方式被赋予了德行检验与教育的内涵,这便是古老射箭活动的新的灵魂。
既然“观德行取于士”是行射礼时所关注的核心,那么习射者应该展示出怎样的“德行”呢?
首先,克己复礼——习射者要正心修身。
因射礼所带有的竞技性的特殊性质,决定了胜负考验下所展现出来的“礼”与“行”将成为射礼所要求德行品定的最重要方面,这也是射礼区别于祭、昏、冠等展示性礼仪的最大不同,而往往在胜负得失面前才能考验出参与者最真实的品行,这也是射礼“观德取士”的根本原因。因此,在《礼记·射义》中专门记载:“天子以备官为节,诸侯以时会天子为节,卿大夫以循法为节,士以不失职为节。故明乎其节之志,以不失其事,则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则无暴乱之祸矣。功成则国安。故曰:射者,所以观盛德也。[26]”这里的“节”及“节之志”便是射礼“观德胜”的关键,从文意可知上至天子下至士阶层,在立身处世时均有自己志向和法度,亦可理解为关键,尽管“节之志”已是君子立德成事的关键,那么如何在同一平台上得到展示和验证,则将礼乐溶于一体的射礼便是最佳的选择。
这里如何才能明其“节之志”呢?
《礼记·射义》中亦有提及:“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27]”习射者凭借“内志正”而进退有度,在射礼仪程中展现出的仁人君子之道,而这里的“内志”无疑是习射者所节之志,如此“内志”与“节志”都是习射者的锻造德行的关键。而射礼是怎样帮助习射者正“内志”与“节之志”的呢?《礼记·射义》记道:“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28]”强调:习射者通过习射来观察自己的内心,射箭之前,先端正自己,然后发射,射中了固然好,射不中也不会埋怨胜过自己的人,而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同时《中庸》有言:“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29]”由此可见,“求证诸己”才是仁者习射的关键,也就是“内志正”和“节之志”的目的。有关“求证诸己”的目的,我们可以参见《论语·宪问》所载“修己”的内容即“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30]”修己的目的是“安百姓”,这样射礼所专注的习射者所节之志及所正内志即“求证诸己”,也可以理解成是达到安民的目的。除此之外,即便是普通的日常狩猎活动中,人们在歌颂猎手时所关注的仍是:“美且仁”、“美且鬈”、“美且偲”[31],“洵美且仁”、“洵美且好”、“洵美且武”[32],除了外在的健美,仁、鬈、偲、好、武等所代表的便是仁慈和善、勇敢健壮和多才多智,这些无疑是修己的内在要求。这样看来,射礼将原本衍生于带有原始性与野蛮性的狩猎活动,通过融入竞技精神、礼乐规范和儒家思想等文明的要素,使其具有了符合于时代、服务于政治的灵魂。
其次,谦敬礼让——习射者要展示谦谦君子之风。
在《论语·八佾》中“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33]”如孔子言,习射是君子体现其所“争”的一项活动,也就是指习射所要求的竞技精神,但在竞技过程中孔子所强调的是“其争也君子”,那么“揖让而升”便体现了射礼中的所要求的谦谦君子之风。事实上,“揖让”之礼贯穿于射礼始终,使得带有竞技对决精神的习射活动因这一环节的存在变得谦敬礼让。
以《仪礼·乡射礼》为例,在整个射礼演进过程中,除了对相关仪程的详细记载,着墨最多的便是“拜礼”和“揖让”,但就习射参与者而言,从“司射犹挟乘矢,以命三耦:‘各与其耦让取弓矢拾’[34]”开始,便奠定了“揖让”与竞技相伴的礼仪进程,而司射自己在完成教射过程中,自身便进行了13次“揖”礼,作为射礼竞技的主要环节“三耦”射,在其习射仪程中更是处处体现出以“揖”相待的君子之风,如从上耦进射开始:“上耦揖进上射,在左并行,当阶北面揖。及阶,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从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并行。皆当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还视侯中。合足而俟。……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乃射。上射既发,挟弓矢,而后下射射。拾发以将乘矢。获者坐而获,举旌以宫,偃旌以商。获而未释获。卒射,皆执弓不挟。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从之,中等并行,上射于左。与升射者相左,交于阶前,相揖。……三耦卒射。宾揖。[35]”以上射而言,在单程行“揖”礼约9次,下射约7次,那么全程下来,上射行礼至少17次,下射行礼至少15次,而处位于三耦中间一组的上射因要行两次“交于阶前”的揖让之礼,则需行礼至少18次,三耦射所行的揖让之礼仅仅是漫长复杂的乡射礼中的一部分,显而易见,即便是带有竞技性质的三耦射,在整个过程中却将孔子所言的“揖让而升”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演绎,凸显了君子在竞争面前仍然克己复礼、谦敬礼让的品行,淡泊名利、平心静气始终是射礼竞技精神的最终体现。
事实上,在日常的涉猎生活中,揖礼亦常用于猎手之间以表达对彼此的敬意,例如《齐风·还》以便捷轻利言语呈现出“揖我谓我儇兮”、“揖我谓我好兮”、“揖我谓我臧兮”[36]等猎手之间的相互敬佩与夸赞,揖让之礼已经深入到现实的涉猎活动中,礼让之美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再次,志体相合——是射礼要求习射者德艺双馨。
“志体相合”强调的是心志与体态的相合,具体说来射礼中的“志体相合”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参与者仪容要完全符合于礼乐,因此,在乡射礼中除了繁复的揖让之礼外,还要求习射者从穿着到站姿、行姿、射姿均要与礼乐相合。例如乡射礼的第一番射不计成绩,人们观察的往往是习射者的容体姿态,这往往是习射者深层修养的外在表现。而在计算成绩的第三番射的环节中,射礼又加入了“合乐”的要求,其依据来自于孔子所言“立于礼,成于乐”[37],又《礼记》载“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38]。因此,射礼中所要求的“志体相合”实际上就是对习射者内在品德与外在礼仪的综合考察。
其二,志体相合也往往会展示出高超的技艺。实际上,无论射礼中礼仪程序如何繁复,人们在给予礼以充分的认可和展示之后,仍然关注竞技的结果,射礼也寄希望于寻找到既有高尚德行又有高超技艺的良士。在有关射礼的文献记载中,人们更直言对于射技的赞颂,例如《郑风·大叔于田》以街巷一空反衬出猎郊外的盛况“襢裼暴虎,献于公所”[39]、“叔善射忌,又良御忌”[40],又如《齐风·猗嗟》的“射则臧兮”、“射则贯兮”[41]等,便是对猎手善射技艺的赞扬。射礼当中对于射技的赞扬则更加简明,例如商代末期甲骨文中的“亡废矢”,商代末期的青铜器《作册般铜鼋》刻“王射,(作册般)射三,率,亡(无)灋(废)矢”[42],西周青铜器柞伯簋铭文同样有“无法(废)矢”的记载,宋镇豪先生认为:“此器用语‘无废矢’,与晚商铜鼋铭文相一致,也是射礼场合班赞品论竞射优胜的评语”[43],将比赛结果镌刻于青铜之上本身便是对习射者或者参赛者高超技艺的肯定,这样的习惯一直被延续下来,至射礼则更加繁复,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因此,在射礼中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筭筹计成绩,对技艺高下进行有效区分,体现对胜负的尊敬。《仪礼·乡射礼》更有“释获人”“唱获者”的存在,负责对于筭筹的计算、监督和公布。习射者在参与射礼过程中,既要将内在德行通过射礼细节化的仪程加以展示,力求做到于细微之处展示植入于身心的礼仪修养,又要将外在技艺通过射礼竞技环节加以凸显,力求以高超的技艺俘众人之心,由此可见,射礼所寻找的有德者必“志体相合”德艺双馨。
综上所述,在射礼的演进过程中,射礼的核心不再以竞技角逐作为根本目的,由竞技所衍生的对道德的检验和再教育则成为射礼所关注的核心,这与当今体育竞技角逐重成绩、轻精神现象截然相反。事实上,赛场奏响的国歌和升起的旗帜似乎不足以焊铸参与者品行,成绩角逐已经深植于参赛者的内心,这无疑与先秦射礼所传递的精神内核背道而驰。面对当今竞技已经广义化地深入到学习、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那么将先秦射礼所具有德育价值引入到现代大学德育教育与仪式体验中,便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