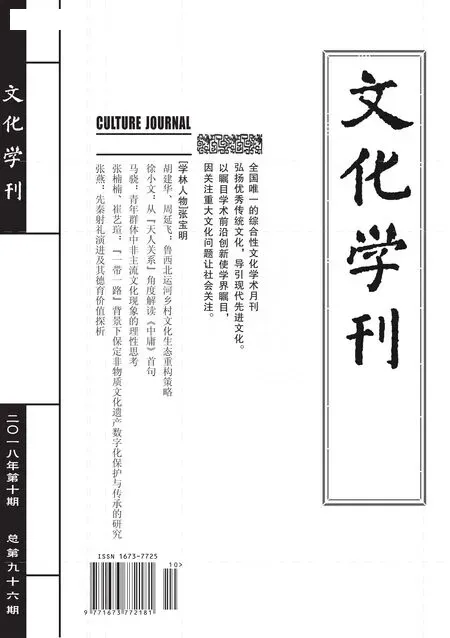乐以化俗
——阮籍《乐论》的乐教思想新诠
2018-03-06张锦波
张锦波
(中国哲学与安徽思想家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039)
《乐论》是魏晋玄学家阮籍讨论传统乐教理论的重要作品,也是其研究玄学思想的重要文本。以往研究由于对中国传统乐教理论存在误解,不能正确地分辨古今论乐的差异,所以不能充分地评判该文对于中国传统乐教思想发展和魏晋玄学研究的学术价值。
一、阮籍所论之乐
阮籍《乐论》以“乐”为研究对象,而乐有古今之别,论乐也有古今差异,因此,我们有必要先行辨别阮籍所论之乐究竟是何乐。
乐有古今之别。在现代语境,如现代学术话语系统、现代学科体系下,音乐首先被界定为艺术或表演艺术的一种,艺术性是现代音乐的基本规定。如《辞海》解释“音乐”时说:“(音乐是)艺术的一种。通过一定形式的音响组合,表现我们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情态。音乐是表演艺术,通过演唱、演奏,为听众所感受而产生艺术效果。”[1]而在传统语境,尤其是传统乐教理论下,音乐首先被界定为乐教之乐,是与“礼”“政”“刑”同为“治化之具”,且具有同等社会性教化地位的乐教之乐。《礼记·乐记》说:“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2]具有规范性内涵和社会性教化功能是乐教之乐的基本规定。音乐不仅仅是可供人们宣导情志的重要工具,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或表演艺术形式,而是具有规范性内涵、具有社会性教化功能的乐教之乐。
论乐也有古今不同。在现代语境下,音乐是艺术或表演艺术,它与人的情感,尤其人的情感表达相关,更多的是人们情感表达的重要工具或重要形式,多侧重于分析音乐是否能够充分地表达人的情感,而音乐的社会功能更多地是在音乐的社会性使用,尤其是音乐使用引发的社会效果层面说的。在传统乐教理论视域下,音乐首先是社会性规范,它不仅仅强调音乐对于人的情感(尤其是人的情感表达)的有效反映,还更加突出对于人的情感(尤其是人的情感表达)的合规范性引导,强调以“乐”导情、正行,强调使人的情感(尤其是人的情感表达)的最终呈现符合社会性规范的要求,实现在“乐”的引导、规范下个体与其自身、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实现动态地和解,如孔子所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3]另外,乐教之乐规范着、引导着人们的情感(尤其是人们的情感表达),但这不意味着束缚着、阻碍着人们的情感(包括人们的情感表达),人们以“乐”来表达出来的仍然是人们在特定时空境域的生命体验和社会体验,特定时代境域下音乐也体现出统治者治理社会的成效,如《礼记·乐记》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4]观乐以知政,知政而知其得失,进而才能更好地治理社会。
那么,阮籍《乐论》所论之乐为何呢?这还需要回到阮籍《乐论》文本本身。在《乐论》中,阮籍将音乐基本界定为:“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5]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音乐是“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乐之为乐,其根据不在于人和天地万物,而在于“天地之体”“万物之性”。高晨阳先生指出,“所谓‘体’或‘性’也不同于正始玄学家所说的宇宙本体,而系指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特定结构或秩序,或说宇宙整体的和谐性本质。因此,乐作为‘天地之体,万物之性’的体现,当然也应该有类似于自然的结构或秩序而具备和谐性的特质”[6]。音乐独立于具体的人与天地万物之上,具有某种相对独立性,且是规范着具体的人和天地万物的宇宙整体性规范或秩序的具体表征,宇宙整体性规范或秩序赋予音乐本身以规范性内涵,而音乐所固有的规范性内涵因这一宇宙整体性规范或秩序的赋予具有了宇宙论或本体论层面的终极保证,进而可以发用、规范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
第二,“(乐)合其体,得其性,则和;(乐)离其体,失其性,则乖。”音乐是“天地之体”“万物之性”的具体表征,需与“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保持一贯性,体现“天地之体”“万物之性”对具体存在的,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的本质要求,达到这一本质要求的,则“和”,称之为乐;达不到的,则“乖”,不可称之为乐。这里的“和”与“乖”不是指人自身情感表达的和谐,也不是人与天地万物之间交互关系上的“和谐”,而是指宇宙整体性规范或秩序本身之和谐性,且要求人以“乐”这一具体形式体现出这种和谐性,以“乐”通达这种有序性、和谐性。音乐之存在和发用,音乐所固有的规范性内涵之具体呈现,也因此有了终极性根据(“天地之体”“万物之性”)和现实的实践方向(“和”)。
综上来看,阮籍《乐论》所论之乐,而是本身固有的规范性内涵,且可以用作社会性教化活动的乐教之乐,并非是要论述作为艺术或表演艺术的现代意义上的音乐之乐。
二、乐以化俗:《乐论》的基本主题
那么,阮籍《乐论》又是如何由乐而论及乐教之现实可能的呢?阮籍《乐论》假托“刘子”与“阮生”二人对话,由“刘子”发问,阮生作答,刘子的问题就为:“夫金石丝竹、钟鼓管弦之音,干戚羽旄、进退俯仰之容,有之何益于政?无之政何损于化,而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乎?”[7]即乐教之现实可能问题。
与其他乐教文章不同,阮籍《乐论》积极运用“辨名析理”玄学方法,具有鲜明的玄学色彩。冯友兰曾指出:“玄学的方法是‘辩名析理’,简称‘名理’。……‘辩名析理’是就一个名词分析它所表示的理,它所表示的理就是它的内涵。”[8]“辩名析理”就是要通过对“名”(名词概念)本身所固有的“理”的分析,将“理”从“名”中抽绎出来,将一个名词“发展”,分析为一个命题或一条命令。就“乐教”这一“名”来看,乐(乐教之乐)本身就具有规范性内涵或社会性教化功能,“教”不过是“乐”自身内在规定性的“现实性地”拓展而已,但“教”在“乐”中,“教”是“乐”之用,“教”也需以“乐”为体,有“乐”才有“乐教”,无“乐”则无“乐教”。
《乐论》中,阮籍立足于“乐”(乐教之乐)本身的考察,从“乐”(乐教之乐)本身说起,从“乐”(乐教之乐)本身所固有的规范性内涵和社会性教化功能说起,具体考辨圣人作乐之义,立论为:因乐而有教,因教以化俗。
首先,音乐具有独立于人的情感(包括人的情感表达)和现实社会性教化活动(尤其是圣人作乐)之外的内在规定性,而这一独立性之根据,在于音乐自身,在于音乐本身乃是宇宙整体规范性的具体彰显。阮籍说:“八音有本体,五声有自然,其同物者以大小相君。有自然,故不可乱;大小相君,故可得而平也。若夫空桑之琴,云和之瑟,孤竹之管,泗滨之磬,其物皆调和淳均者,声相宜也,故必有常处;以大小相君,应黄钟之气,故必有常数。有常处,故其器贵重;有常数,故其制不妄。贵重,故可得以事神;不妄,故可得以化人。”[9]高晨阳先生指出:“阮籍认为,八种乐器(八音)必须由特定的材料制作而不允许有丝毫苟且,……‘必有常处’而‘不可妄易’。这些乐器的制作方法必须遵循‘大小相君’‘应黄钟之气’的原则而不可随意更改。……乐器的制作或组合必须符合一定的规律,所以说‘必有常数’。……所谓‘大不相君’,不单系指不同乐器和不同音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相互补充而形成的一种特定的结构关系及其所具有的和谐特性,而且也系指宇宙整体的结构及其所具有的和谐特性。换句话说,八音之‘大小相君’的关系及其和谐性乃宇宙整体‘大小相君’关系及其和谐性的象征,所谓‘其物似天地之象’。”[10]音乐(乐教之乐)有其“本体”“自然”“必有常处”“必有常数”等,而这些为乐本身所固有,证成这些“本体”“自然”“常处”“常数”等之为乐所固有的,乃是宇宙整体性规范。
第二,圣人作乐,乃是因“乐”而作,作乐以成“乐(教)”。阮籍说:“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阴阳八风之声,均黄钟中和之律,开群生万物之情气。”[11]圣人之作乐,在某种意义上是将音乐本身所固有的这一规范性内涵现实地、具体地“做出来”,“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因“乐”而作乐,“圣人立调适之音,建平和之声,制便事之节,定顺从之容,使天下之为乐者,莫不仪焉”[12]。圣人根据“音”“声”“节”“容”等要素及其符合“乐”本身规范性内涵和社会性教化功能的本质规定(“调适”“平和”“便事”“顺从”),制作符合时代需要和社会性规范本质要求的音乐,“自上以下,降杀有等,至于庶人,咸皆闻之。……入于心,沦于气,心气和洽,则风俗齐一”[13],以引导民众习乐以正心、正行,达到“移风易俗”的社会治理效果。
第三,圣人作乐而有教,有教则以化俗。阮籍说:“造始之教谓之风,习而行之谓之俗。……八方殊风,九州异俗,乖离分背,莫能相通,音异气别,曲节不齐。”各地风俗不一,乃因“风”而成“俗”,在于各地社会治理者的各种具体的社会性教化需要及其活动(“造始之教”),也在于各地民众对这些社会性规范的惯性遵循(“习而行之”),而风俗之所以不一,在于统一的、整体性的社会性规范或社会性教化活动的现实贯彻。乐(乐教之乐)本质上是整体性宇宙规范或秩序的具体表征,它超越于各地域各种具体的社会性习俗,通适于包括所有社会性个体和天地万物在内的所有存在,其规范性具有整体性、普遍性的特质,因此,圣人作乐而有教,因而有了统一的,适用于所有社会性个体,甚至于天地万物的社会性规范。而“先王之为乐也,将以定万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14],有教则能以化俗,“《雅》《颂》有分,故人神不杂;节会有数,故曲折不乱;周旋有度,故頫仰不惑;歌咏有主,故言语不悖。导之以善,绥之以和,守之以衷,持之以久。散其群,比其文,扶其夭,助其寿,使其风俗之偏习,归圣王之大化。”[15]总的说来,在《乐论》中,阮籍以乐而论乐教,又因乐教而以化俗,而这些都基于对音乐(乐教之乐)本身尤其是音乐(乐教之乐)本身所具有的规范性内涵和社会性教化功能的分析,彰显出玄学家高超的思辨能力。
三、结语
文本的解读,需要回到文本本身。立足于《乐论》文本本身得知,阮籍对乐教现实可能性问题的思考始终建立在对音乐本身(乐教之乐)的考察之上,建立在音乐本身所固有的规范性内涵和社会性教化功能的“辨名析理”之上,因“乐”而有“教”,有教以化俗,显现出鲜明的玄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