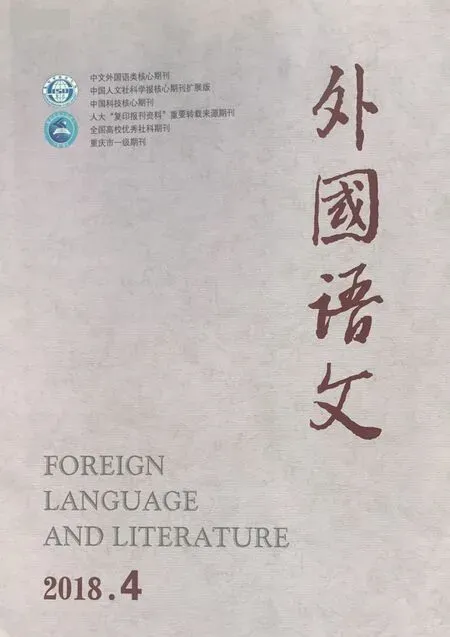“音乐诗学”中的语言乌托邦
——试论诺瓦利斯“音乐诗学”中的语言批判与诗学内涵
2018-03-05张硕
张 硕
(柏林自由大学,德国 柏林 10115)
早在1795年,席勒便在其《论天真的诗与感伤的诗》中提出了“音乐性诗歌”的概念:“诗或者像造型艺术那样模仿一个特定的对象,或者像音乐那样只是唤起一个特定的心境而无须一个特定的对象,视此种情况之不同,可称之为造型的(雕塑的)或音乐的。因此,这后一个名称所指的,不仅是诗里在材料上真正是音乐的东西,而且一般也指它不用特定的客体去支配想象力也能产生的诗的一切效果。”(席勒,2005:120)席勒将音乐性的诗歌定义为非模仿的、以“唤起一个特定的心境”为目的的艺术,这样的一种构建将诗歌从“模仿”的艺术形式中解放了出来。这种试图挖掘诗歌中所蕴含的音乐性并将诗歌与音乐并列相比较的思想到了早期浪漫主义诗学中成为一种主流思潮,在1800年前后发展成一个相较完整的诗学体系,其论述贯穿了从瓦肯罗德、蒂克到诺瓦利斯、施莱格尔兄弟的文学作品和断片。音乐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被引入了诗学领域——“音乐是这个世纪真正的艺术”(Schlegel,1980:166)。反思音乐并进而提炼出“音乐性”的诗学概念,这一点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有着不可割裂的指导意义,“音乐”一跃成为浪漫主义诗歌的创作标准。诺瓦利斯就曾在其断片中强调,诗人必须使用“音乐的语言”来尝试进行“确切的表述”(Novalis II,1965:517)。在另一篇断片中,诺瓦利斯又说:“我们的语言应该重新成为歌声。”(Novalis III,1968:283)同样为早期浪漫主义代表人物的弗·施莱格尔也曾指出:“每一种艺术中都包含着音乐的原则,只有音乐才是完整的。这一点甚至适用于哲学,也适用于诗歌,也许还适用于生活。”(Schlegel,1981:213)面对这样的断片文本,我们不禁要问,音乐缘何拥有如此高的地位以致竟成为诗的模板?语言与音乐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媒介又何以在诗学领域被融为一体?若要理解早期浪漫派断片中这些看似无法理解、甚至自相矛盾的表述,必须从诗哲们对音乐的反思这一角度来理解和阐释,以便归纳出“音乐性的诗”所具有的特点,进而依循此路径去接近“浪漫之诗”的本质。
早期浪漫主义者们最初对音乐的兴趣萌生于他们对语言表述能力的怀疑,这一点最先、也最明显地体现在瓦肯罗德的“艺术宗教”(Kunstreligion)中(Auerochs,2011:323)。早在1796年,早期浪漫派尚未在耶拿成型之前,瓦肯罗德便与好友蒂克共同出版了《一个热爱艺术的修士的内心倾诉》一书,并在其后一年由蒂克整理亡友的遗稿,出版了该书的下册《艺术的想象力》。作为整个早期浪漫主义时期最早出版的两部作品,书中两位诗人将各种艺术门类混杂在一起进行评论,并用了整整一半的篇幅描述了音乐这一艺术门类所独具的特点和神秘性。作为虔诚天主教家庭成长起来的年轻诗人,瓦肯罗德在这两本书中发掘了艺术家创作的深层心理过程,并第一次提出了艺术神圣性的问题,认为艺术家创作的过程乃是神赐予的天启经验,因而艺术作品,尤其是音乐中必然包含仅靠人力和语言难以企及的神秘本质:“它们并非借助话语的帮助,而是通过与之迥异的渠道进入我们的内心;它们会以一种神奇的方式猛然触动我们的灵魂,深入我们的每一根神经和每一滴血液里。”(瓦肯罗德,2002:67)瓦肯罗德这种对艺术神圣性的发掘使得艺术所能表达的最高“真实”被置于人类语言可以表述的彼岸,“逻各斯语言”失去了通达艺术本质的能力,而只有“天才”才能够通过“莫可名状”的神秘体验获得艺术中所蕴含的至高真理,一窥“上帝”赏赐给人类的“艺术真实”,而艺术中一切不可见的、不可用言语表述的神圣性都被理想化为通过音乐可以传达的神秘体验。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前浪漫主义思潮中出现了将“语言”与“音乐”逐渐剥离开来的趋势,瓦肯罗德和蒂克便深受这种影响,将音乐置于语言的对立面,强调音乐的纯粹性和自律性。卡尔·达尔豪斯(Carl Dahlhaus)在其后来的重要浪漫主义研究文献中便将瓦格纳提出的“绝对音乐”(absolute Musik)概念的形成历史追溯回早期浪漫主义时期,指出正是早期浪漫者们将“纯粹音乐”当做语言难以企及的理想模板引入了诗学之中,影响了其后整个时代的艺术观以及诗学观(Dahlhaus,1987:9)。
作为早期浪漫主义团体的核心成员之一,诺瓦利斯同样对音乐神秘特性充满好奇和热爱。1799年,诺瓦利斯在耶拿施莱格尔圈子里结识了好友蒂克。蒂克曾在其个人传记中讲到,诺瓦利斯非常热爱音乐,虽然他对音乐并没有深入的了解,甚至始终只是个门外汉。值得一提的是蒂克曾在1799年7月下旬与自己的作曲家内兄约翰·弗里德里希·莱夏特(Johann Friedrich Reichardt)一同拜访了诺瓦利斯,两家人一起度过了极其美好的时光。正是因为这一段短暂而亲密的友谊关系,莱夏特在诺瓦利斯死后将他的诗作谱曲成了歌曲(Mahhoney,2004:85)。从生平角度来看,诺瓦利斯作为浪漫主义诗人既不会作曲,也不曾学习过乐器演奏,因而他对音乐的热爱并非旨在将音乐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加以研究,而是试图将音乐与诗歌相比较,并将音乐作为一种理念上升为一种崇高的诗学理想。而诺瓦利斯这一诗学理想的开端,与蒂克和瓦肯罗德相似,肇始于诗人对诗歌语言的反思。随着交响乐与器乐在17世纪风靡欧洲,音乐这一概念逐渐成为一门独立于“歌唱”的艺术形式,仅仅指涉乐器所发出的纯粹音乐。诺瓦利斯对“音乐”作为一种纯粹概念的理解也同样明显受到时代风潮的影响,力图将带有唱词的“人声”与“乐声”区别开来,并强调器乐的独立性:“舞蹈音乐和歌曲音乐并不是真正的音乐。它们只是音乐的变种。奏鸣曲、交响乐、赋格、变奏——这些才是真正的音乐。”(Novalis III,1968:685)这一观点与蒂克在《艺术的想象力》一书中对交响乐的描述如出一辙:“交响乐是器乐最高的凯旋。”(Wackenroder,1984:329)同蒂克与瓦肯罗德一样,诺瓦利斯试图将音乐纯粹化,将音乐的本质定义为一种“声响”,并认为这种声响中不应包括任何语义性的特点,从而使音乐脱离了语言不可逾越的指代性界限,进而成为一个独立而自律的艺术类型。在早期浪漫主义者们看来,纯粹音乐显然超越了语言能够企及的高度,其真正的内涵变得“不可言说”,进而拥有了神秘的特点;与此同时音乐本身既是现象又是本质,在音乐中所表现出来的东西便是其所要表现的东西。这种与语言相脱离的、自成一体的“绝对音乐”经由早期浪漫主义者们的构建摆脱了自身仅仅作为一种媒介而存在的命运,将“能指”与“所指”同时集于一身,并以神秘的方式拒绝明晰的语言阐释。
作为一种纯粹的声响存在,“绝对音乐”这种飘忽不定、难以言说的旋律性特点首先被诺瓦利斯拿来用以克服语言的死板和僵化。关于诗歌语言与音乐旋律的共通性诺瓦利斯在断片中写道:“正如哲学家将一切归类而置,诗人则将一切绑缚都解开。他们的词句不是普遍的符号——而是声响——是充满魔力的咒语,成群结队地盘旋而动……他(指诗人)需要经常使用反复出现的、因使用而发挥到极致的词语。他的世界是如此简单,正如他所用的乐器——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创造出无穷无尽的旋律。”(Novalis II,1965:533)诺瓦利斯明确要求诗歌语言应富有旋律性,并且将诗人与音乐家进行类比,称诗人乃是在用一种“乐器”创作,韵律美应为诗人追求的第一位目标。在诺瓦利斯的诗学理念中,人类语言——尤其是逻辑语言——有着先天的缺陷,人类语言随着理性的萌发进入了一种退化的状态,越是理性就越远离美和真理:“我们的语言——它在初始的时候极具音乐性,从那之后就变得散文化了——去声响化了。它现在更多的是一种噪声——喧闹,如果人们非要贬低这个美好的词汇。我们的语言应该重新成为歌声。”(Novalis III,1988:283)因而对诺瓦利斯来说,诗歌语言是否富于优美的韵律性成为一首诗是否是好诗的重要评价标准。依此标准,诺瓦利斯对同时代的诗歌做出了相应的评价:“席勒充满音乐性的创作非常具有哲学性——赫尔德和施莱格尔也是。歌德的麦斯特也可算入其中。让·保尔诗化音乐性的想象。蒂克的诗歌也完全就是音乐性的。”(Novalis III,1968:320)好友蒂克确实配得上此番夸赞,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位狂热的诗歌创作者。他的玛格洛娜组诗(Magelone-Gesänge)就曾因其优美的韵律性特点而被勃拉姆斯谱曲为艺术歌曲。可以说,尤以蒂克的诗歌为代表的早期浪漫主义文学在诗歌语言的韵律性上下足了功夫。
但是早期浪漫主义者们这种对“诗歌语言的音乐性”的过度强调也带来了相应的问题——这种诗学使语义功能附着于语音功能,在诗歌创作中不得不以牺牲语义的深度为代价,只为建立起声音效果的精致结构。为了追求这种诗歌语言的“悦耳”,诺瓦利斯甚至认为可以以牺牲诗歌的“意义”为代价:“诗歌——仅仅是悦耳而漂亮的词句——没有任何意义和关联——顶多是一些诗节可以理解——它必须如此,就如不同的东西所产生的多样的碎片。真正的诗顶多在大体上拥有象征性的意义,并且像音乐一样间接地产生效果。”(Novalis,1983:572)声音作为语言的重要财富被过度强调,以至于语言排斥了声响效果之外的一切指涉性,语言被剥夺了所有的其余资源而仅仅剩下声音。简言之,所有的好诗都成为声音的诗而非意义的诗。诚然,作为一种诗学理念的构建,音乐的声响性理论上固然能够表现语言无法企及的神秘意义,让诗人们为之疯狂,但是这一点却给实践层面的诗歌创作带来了困难。例如蒂克的某些诗歌就必须大声朗读出来方能体现其美感,而在内容层面上则乏善可陈,不具很好的可读性,以至于它们成为一种听觉的诗歌,近乎成为无关乎意义的纯粹声音。作为一种“诗学乌托邦”,音乐诗学在语言层面标示出的是诗歌无法达到的绝对高度——诗歌即使再追求音乐的旋律性和节奏性,也无法摆脱其只能使用语言作为媒介的命运,语言所言说的意向必然都指向自身之外,词汇绝不仅仅是声音的集结,诗歌的声响只有通过意义的理解才能获得,否则只能是无意义的呢喃。歌德便首先认识到了这种只停留在语言层面的声响诗歌中所蕴含的“陷阱”,在写给席勒的一封信中,他便针对蒂克在其小说《施特恩巴尔德的游历》中漂亮的语言和空洞的内容提出了批评:“精致的器皿腹中空空,真是令人难以置信。”(Goethe,1881:146)蒂克的确在小说的第二部分为了追求诗歌语言的音乐性而过多地牺牲了其应有的内涵,本应是诗歌借助节奏性使自己在声响层面臻于完美,然而蒂克却本末倒置,反而使诗歌成了过于喧嚣的噪音。早期浪漫主义者们根据音乐诗学的理念仅仅对诗歌语言进行的音乐化尝试陷入了绝境,音乐性语言的乌托邦终究无法实现。但是对诺瓦利斯来说,“音乐性的诗歌”这一断语有着不仅仅拘泥于语言层面的、更加深邃的含义,诗人所构建的“音乐诗学”必然在诗歌语言的乌托邦之外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
诺瓦利斯固然认为早期人类的语言的确更优美、更具有音乐性,但让浪漫之诗仅仅拥有原始的节奏和韵律并不是其音乐诗学理念的真正核心,究其音乐迷思的本质乃是因为声响作为一种非语言性的艺术门类表达出了前理性、前逻辑的意义世界,最原始的音乐性韵律中蕴含的力量无限接近世界的本源。诺瓦利斯认为音乐的形式中内含一种节奏性,而这种节奏性乃是世界的根本规律。“一切的方法都是节奏。如果人们剥夺了世界的节奏,那么也就剥夺了世界。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Novalis III,1968:309)音乐的节奏感在诺瓦利斯那里不仅是一种诗学原则,更扩大成为整个世界运转的内在规律,万事万物均遵循自身的节奏,人自身同样包含节奏,他甚至认为人类思想史的发展都遵循一种音乐的节奏性。诺瓦利斯将人类历史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音乐性”的历史,即哲学史,而另一种则是“雕塑性”的历史,即编年史(Novalis III,1968:355)。这样的历史观使得诗人认为思想史在本质上是一种“运动”(Bewegung),其发展遵循某种特定的节奏。他在其《全面题材装订草稿》中便指出,费希特无非是发现了哲学的节奏并将其抽象地表达了出来(Novalis III,1968:310)。这种内涵于世界万事万物中的节奏性吸引着诺瓦利斯,以至于他不断地尝试在诗歌中去揭示或者靠近这种节奏性,试图用文学的方式具体而非抽象地再现这种节奏性。这一点构成了诺瓦利斯“音乐诗学”的重要内核之一,即为要尽可能地让诗歌像音乐那样与世界自身的节奏产生共鸣,以再现世界所内含的节奏性。
倘若我们进一步探求,为什么单单是“哲学史”而非“编年史”会被诺瓦利斯认为是“音乐性”的呢?这一点与他对人类灵魂本质的认识不无关系。灵魂对于诺瓦利斯来说本身就是一种类似声响的存在:“词语产生的氛围指向一种音乐性的灵魂关系。灵魂的声响性仍旧还是一个晦暗不明的、但却可能是极其重要的领域。和谐以及不和谐的震荡。”(Novalis III,1968:473)灵魂的声响性本质在他的另一个断片中则被表达得更加明确:“词句和声音是灵魂真正的形象和表达。破解的艺术。灵魂由纯粹的声响组成,被敲响的声响。”(Novalis III,1968:463)因而对诺瓦利斯来说,灵魂的声响性本质使得人类精神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类似音乐的存在——像音乐一样,人类的精神不需要依赖任何外物的存在,而纯粹是一种自发的、无形体的、无质料的震动。心绪之流动经过外化表达便成为声响性的音乐,因而音乐的频率反过来也能与灵魂的震荡产生共鸣,这也是音乐作为一种主观的艺术比雕塑或绘画更容易打动人心的原因。正是因为“由内而外”展现出来的人类思想史乃是一种脱离了外部规定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外显,因而在诺瓦利斯看来是类似于音乐的存在;由客观史实堆叠罗列而成的编年史则与之相对,是“雕塑性”的。造型艺术的雕塑性终究只能赋予世界以可见的外形,但若探求世界万物的本质,则人们必须重回人类的精神内部去探究。对诺瓦利斯来说,外部自然不可能脱离人类的精神而独立存在,或说在人类对外部自然的认识过程中必然不可能摆脱精神的构建:“什么是自然?——就是我们精神所做的百科全书式的、系统的索引或计划。”(Novalis II,1965:583)在另一组断片中他也曾说:“我们在世界中寻找一种设计——这种设计就是我们自己。”(Novalis II,1965:541)世界因而是意识所构成的集合,在其中“诗性想象力”(poetische Einbildungskraft)占据核心的地位,成为整个世界得以存在的前提。
诺瓦利斯这种“由内而外”的世界观深受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尤其是费希特的“自我哲学”的影响,从而让诗人断定自然不可能是一种客观存在,外在世界必然是内在诗性想象力的产物。在唯心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下,诺瓦利斯甚至将物理学予以诗化:“物理学不是别的,就是关于幻想的学问。”(Novalis III,1968:558)诺瓦利斯用“魔幻唯心主义”(magische Idealismus)将外在世界加以魔化,亦即由内而外地感知世界,将自我认识世界方式的起点放置在想象力之上,用主观意识为外在世界披上一层魔幻的外衣,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被予以重置。艺术的标准因此也就不再是对外在自然的模仿,而成为想象力的外化表达,“自我”一跃成为艺术的核心。正如在断片《塞斯的弟子们》中,诺瓦利斯笔下的人物便对一种不断向外探索来认识世界的方式提出了质疑:“我们何须在这可见事物的浑浊世界艰苦跋涉?纯净的世界原来就在我们心里,在这泉水里。这里表现出伟大的、绚丽多彩的、喧闹混乱的戏剧之真实内涵。”(诺瓦利斯,2008:13)这种内心与世界关系的定位导致诗与真实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重新定义:“诗既是绝对的真实。这是我哲学的核心。越是诗意,就越是真实。”(Novalis II,1965:647)真实不再被当作一个客观的、需要从外部去予以寻找的真理,而完全蕴含在人的心灵内部。正因诗更贴近人的心灵,是心灵的直接表达,因而诗也就更加趋近绝对的真实。
在关照纯粹的内心世界这一点上,诺瓦利斯恰恰是找到了音乐这一模板作为纯粹的诗所能达到的至高境界:“再没有什么比在音乐中更存在纯粹的精神,这种精神将对象和质料的变化诗化,至美,也就是艺术的对象再没有在哪里像在音乐中这样被给予并完全地显现出来了。”(Novalis II,1965:573)恰恰由于音乐家“并非由外而内地听”,而是“由内而外地听”(Novalis II,1965:574),所以作为一种非模仿的艺术形式,“绝对音乐”本身极大程度地脱离了外在世界的限制,它既不模仿自然,又无须质料形体,而仅仅作为心灵的外化表达而存在。而真正的诗,或说浪漫的诗,恰恰就应该表达纯粹的心灵世界:“诗歌就是心灵的展现——展现整个内心世界。仅仅是诗的媒介,也就是语言,就显示了这一点,因为它就是那种内心力量的外显。正如雕塑与外部造型世界对应,音乐与声响对应。效果却是刚好相反——只要它是雕塑性的——确实存在音乐性的诗,它将心灵本身置入一个丰富多彩的、运动着的游戏中。”(Novalis III,1968:650)作为音乐诗学的核心理念,诺瓦利斯要求诗必须如音乐一般,成为一种由内心而发的艺术,力求其脱离对外界事物的模仿,专注于纯粹地表现精神性;浪漫之诗的产生必然是“由内而外”的,只有如此,诗才能臻于达到音乐性的境界,也只有如此,诗才能成为浪漫之诗。
总而言之,按照诺瓦利斯的构想,浪漫之诗应该展现世界的本质,而他认为世界乃是内心诗性想象力的产物,外在自然的存在源自灵魂,因而越是能贴近灵魂的艺术,就越能展现世界的本质。音乐恰恰因为源自灵魂,并且同时与灵魂有着相同的存在方式,因而音乐最终被诗人神话为一种完美的、浪漫诗歌应该追求的理想模型。只有基于诺瓦利斯这种对音乐、世界本质和诗歌的综合理解,我们才能提炼出一套相较完整的“音乐诗学”观:它首先在形式上要求诗歌语言必须声响化,试图摆脱语言僵化、死板的语义学界限;其次它在内容上要求诗歌反观人的内心,正如音乐不对任何外在事物进行模仿,浪漫诗歌也必须“由内而外”生发出来;最后,诺瓦利斯认为,按照这样的音乐性原则所产生出来的浪漫之诗,必然是“最高的真实”,这一真实的本质源自诗歌表达出了外在世界与主观心灵的同构——这便是诺瓦利斯的“音乐诗学”较为完整的表达。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再反观诺瓦利斯那条最著名的105号断片“世界必须浪漫化”,便可以透彻理解诺瓦利斯的诗学追求:“世界一定要浪漫化,唯其如此才能发现世界的真义。浪漫化是质的倍增,在质的倍增中低级的自我升华为高级的自我……我赋予卑微以高深,俗常以神秘,已知以未知的威严,有限以无限的灵光。如此这般我便完成了浪漫化的进程。”(Novalis II,1965:545)——世界的“浪漫化”必须通过构建浪漫之诗而完成,而在“音乐诗学”原则之下产生出来的浪漫之诗便足以完成这一使命。在这一意义上“浪漫化”与“音乐化”是等价的。
但是反过来我们必须承认,诺瓦利斯的这种诗学构建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理想,只能无限接近,却无法企及。诗人是在对诗歌语言的反思中提出了“音乐诗学”的概念,表达了言说的边界和困难,“音乐诗学”固然是诗人对语言怀疑论一种积极的、正面的解决之道,但是作为一套完整的诗学理念,“音乐诗学”在文学创作层面没有实现的可能性,“诗歌”最终不可能成为“音乐”。诗的完美形式应该是在声音与意义上不断平衡推进,无论诗歌语言的声响性多么独特,它必须仍然是这样一种结合。这种内核支撑着每一个“词”作为“词”的存在,而非虚无缥缈的声响形式,逻辑语言的形式固然可以被抛弃,而内核必须保留下来,否则如果认为诗歌的体验在语言之外,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对它进行表达,诗歌创作也就不再必要了。在这个意义上,诗歌从未从语言的牢笼和枷锁中被解放出来进而成为音乐,而只是在二者之间某个飘忽不定的点上找到了平衡点。在这个游移而又不可动摇的支撑点上,浪漫主义诗歌才能即获得无限丰富的意义和可能性,又不至于成为纯粹的声波回响而消散在空间中无法把握。后期的诺瓦利斯认识到了“音乐诗学”的这个内部矛盾,因而在《全面题材装订草稿》断片中他也曾试图重新界定诗的地位:“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诗介于造型和声响艺术之间……节奏性和旋律性的音乐,雕塑和绘画。诗的元素。”(Novalis III,1968:297)作为一种在语言层面只能向往却无法企及的理想,“音乐诗学”的体系构建的真正诗学意义反而体现在文学创作的内容层面。在抛弃了语言形式的外壳之后,诺瓦利斯“音乐诗学”的本质才逐渐显露:诗人并非想让自己成为音乐家,而是在追求一种诗歌内容层面的解放——诗歌语言不能成为音乐,但是可以像音乐一般追求语义上的模糊性,追求脱离模仿的牢笼反观内心,追求将“无限的”世界本质在“有限的”诗歌中予以表达。而恰恰因为浪漫之诗拒绝僵话死板的语言、信息明确的意向,所以浪漫诗歌才能在言说出来的不确定性中保持不可穷尽的完整。按照诺瓦利斯的构建,浪漫之诗非但没有因为语言的模糊性而减弱自己的表达性,反而却因为无限的阐释可能而变得更加丰富。形式与内容、有限与无限、可见于不可见、主体与客体、可言说与不可言说的之间的张力最终在“音乐诗学”的构架中消解了。“音乐诗学”作为早期浪漫主义时期的核心诗学观点之一,可以说是对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表达媒介的否定和重新肯定。
作为超越自身时代的先驱们,早期浪漫主义者们——尤其是诺瓦利斯——对语言表达边界的颠覆性批判已经带有了现代性的特征。自启蒙之后,必然走向现代性的命运早已写入了人类思想史的规划中。由于逻各斯的介入,我们注定不再能与世界融为一体——这把人从世界中隔离出来,造成了那已成为我们命运的分裂。如果说诺瓦利斯通过“音乐诗学”的构建并非在语言层面,而是在诗歌意义的层面解决了“言说”所遇到的危机,那么这种危机在进入现代之后则成为彻底不可逾越的屏障,人类的世界观更加的破碎,诗歌已经不能再支撑它许诺过的永恒,世界的本质和诗人的遣词造句之间最终产生了不可逾越的裂痕。到达20世纪,“沉默”的诗人们最终对放弃了语言,迈入了真正的“音乐境地”,即“不表达”。正如里尔克所言:“沉默吧。谁在心中保持沉默,谁就接触到言说之根。”(Rilker,1996:302)追根溯源,20世纪以来一直困扰诗人们的语言表达困境早在早期浪漫主义时期就已经初露端倪,而诺瓦利斯正是通过“音乐诗学”这样一种独特的诗学构建了摧枯拉朽的现代性到达之前诗歌最后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