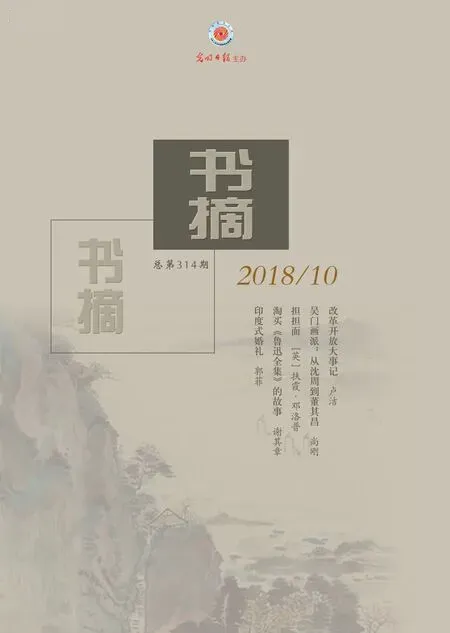三国小札
2018-03-04刘逸生
☉刘逸生
曹操的兵法著作
曹操有一本军事著作,称为《孟德新书》,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据《三国演义》说,西蜀刘璋派别驾张松到许昌,张松言语不逊,曹操不予礼遇,张松只好投向刘备,献出西蜀地图,又陈入蜀之策,在这段故事中,插入张松为难杨修一节。杨修取出曹操所著《孟德新书》,说是仿《孙子十三篇》而作。张松看了一遍,立即朗诵出来,并无一字差错。又故意说此书是战国时无名氏所作,曹操盗窃而得。于是,曹操把《孟德新书》扯碎烧了,自此不传于世。
这段描述自然又是有真有假。《三国志》引《益部耆旧杂记》说:“(杨)修以公(曹操)所撰兵书示松,松宴饮之间,一看便暗诵。修以此益异之。”并没有曹操烧掉兵书的事。
曹操确实有过军事著作,王沈《魏书》云:“太祖自统御海内,芟夷群丑,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这里出现了“新书”二字,“新书”者,别于古代兵书也。
但是这部十万余言的“新书”又确实不曾流传下来,难怪《三国演义》有烧了的说法。曹操注解过好几种兵书。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列举有《太公阴谋解》三卷、《司马法注》(不知卷数)、《孙子略解》三卷、《续孙子兵法》二卷、《兵书摘要》十卷、《兵书要论》七卷、《兵书略要》九卷、《魏武帝兵书》十三卷。后一种也就是《魏书》所说的《新书》,出于自己著作,其他都是注解或抄撮古代兵书的。
《新书》固已不传,其他注解古代兵书的著作,现在也仅存《孙子注》一种,也就是上文的《孙子略解》。清人孙星衍校刊的《孙子十家注》收录曹操的注文,这是曹操军事著作中惟一幸存的了。
未看过曹操注《孙子》的人,也许以为其中有不少精彩的发明,其实相反,非常简略。例如《孙子》说“强而避之”,曹操注云:“避其所长也。”“怒而挠之”注云:“待其衰懈也。”“卑而骄之,佚而劳之”注云:“以利劳之。”“亲而离之”注云:“以间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注云:“击其懈怠,出其空虚。”大抵都是这样的注解,这样的注解,可以说是注也如此,不注也如此,读了只有使人失望。
不知所谓《孟德新书》者,是否也如此简单概略?
看来曹操读了不少古代兵书,但不过是粗知其意而已。赤壁大败证明了这一点。
关兴、张苞是“好心人的产物”
《三国演义》写到关羽、张飞遇害以后,就用强烈的笔墨浓厚的兴趣来描写两员小将,一个是关羽的儿子关兴,一个是张飞的儿子张苞,在刘备征吴一役中,两小将冲锋陷阵,屡立战功,而又互相呼应,彼此救援,仿佛又是一对兄弟,写得颇为出色。读者真会以为这是实有其人,也确有其事了。
关兴、张苞是实有其人,但却不是实有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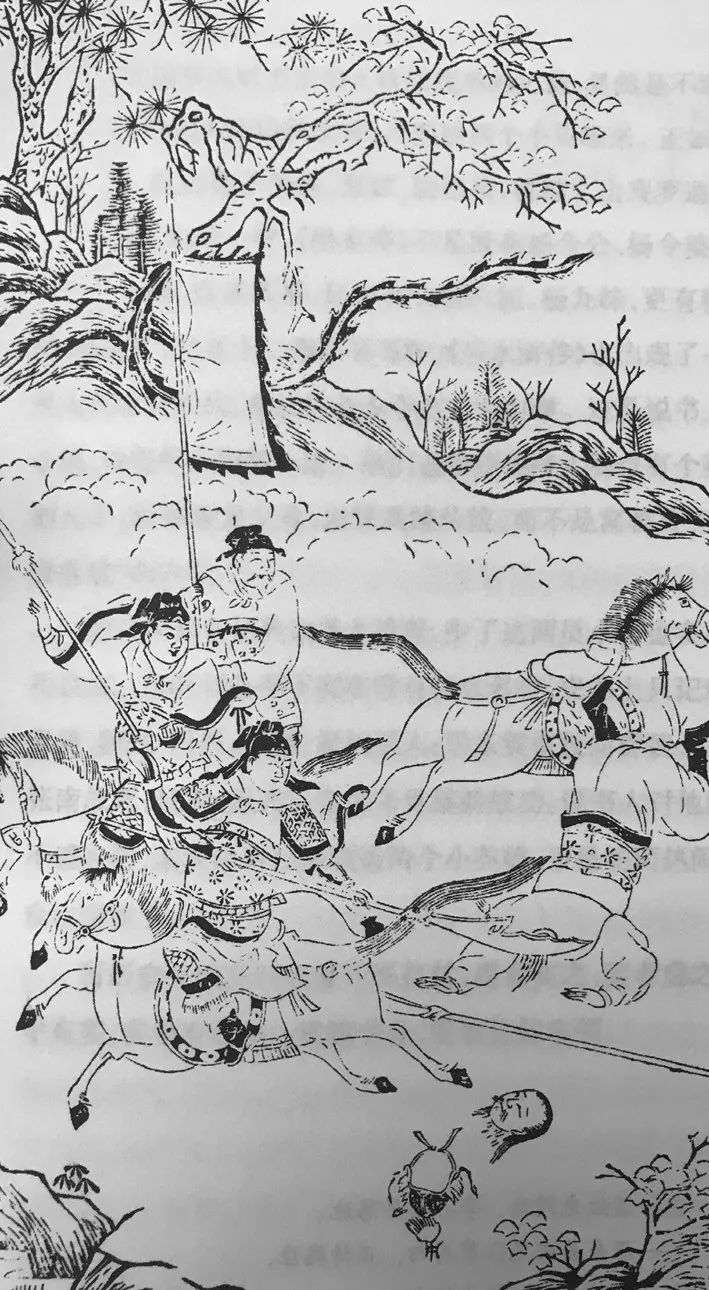
关兴救张苞
关兴是关羽的儿子,但他不是一员武将。《三国志》对他的记载很简略,不过是“少有令问,丞相诸葛亮深器异之。弱冠为侍中、中监军、数岁卒”这几句。“令问”是好名声的意思,可知他早就有点名气;侍中是皇帝的近臣,主持朝廷礼节,保护皇帝安全,以及答复皇帝咨询等;中监军则是在京城监督军事的。这两种职务固然重要,但却用不着亲自带兵打仗。关兴二十上下就担任这两种官职,说明他是年少有为的人物,但死得太早,说不上有大的建树。
张苞的记载更简单了,仅仅得“长子苞,早夭”五个字(《三国志·张飞传》)。张飞的继承人是次子张绍,可知张苞死于他父亲遇害之前。他也没有当过什么官职;倒是他的儿子张遵官至尚书,后来在绵竹同邓艾作战时牺牲,不愧为名将的后代。
古代说书人对于史书上这样简单的记载,显然是不满意的。于是他们大胆驰骋想象,再塑造两个小英雄来。正如《说唐》故事,既出现了罗成、秦琼、尉迟恭,就继之出现罗通、秦怀玉、尉迟宝林一样,《杨家将》不是既有杨令公、杨令婆,一郎至七郎,这还不够,还有什么杨八姐、杨九妹,更有穆桂英、杨文广,乃至十二寡妇等等吗?《后水浒传》也出现了一批梁山英雄的后代,在反抗金人中出了大力哩。这是说书人的心愿,也是听众们的心愿。他们总希望英雄人物也有个英雄的儿子,能够继承父业,发扬英雄传统,而不是窝囊废,更不是变成“衙内”。
而且在刘备征吴这场大战里,少了这两员小将也实在显得寂寞。当时刘备手下实在没有什么名将,史书上只记载了吴班、陈式、冯习、张南、黄权五人;后来黄权投向曹魏,冯习、张南战死,吴班、陈式一生又未见赫赫战功。说书人对他们都不感兴趣,索性由自己来创造两个小英雄,于是场面热闹,听众也满意了。
写历史小说有时也像行军打仗:虚者实之,实者虚之;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腾挪变化,要看你的本领。
《三国演义》的严重败笔——刘后主可曾怀疑孔明
《三国演义》有一段颇为读者不满的情节,那就是在第一百回里,杜撰了一段刘后主听信谗言,说诸葛孔明“有怨上之意,早晚欲称为帝”,又说“孔明自恃大功,早晚必将篡国”。于是“后主惊曰:似此如之奈何?宦官曰:可诏还成都,削其兵权,免生叛逆。后主下诏,宣孔明班师回朝”。于是孔明“仰天叹曰:主上年幼,必有佞臣在侧,我如不回,是欺主矣。若奉命而退,日后再难得此机会也”。于是班师回朝。
这段叙述,在历史上是没有的。事实上,那年是建兴八年,即魏曹睿太和四年(公元230年)。这一年魏国要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主动派了大军,由曹真率领,司马懿为副,分数路向西蜀进攻。曹真一队,由子午道(长安之南通向汉中的小路)南入;司马懿则从汉水上游进兵,企图与曹真会兵于南郑。还另遣军队由斜谷(五丈原之南)深入,又以另一支军马,由武威(南安郡西北)南下作呼应之势。魏国此次决心很大,以为数路并进,一定收到战果。当时诸葛孔明闻讯,命李严率二万人守汉中,自己另带一支人马开到城固(今陕西省城固县)、赤坂(今陕西省洋县东)一线,准备迎敌。是时正当秋季,汉中一带下了连绵大雨,一连三十日不曾停止,山路绝断,运输不继,于是魏军数路皆退。
魏军撤退时,蜀兵并未前去追赶。这也是一种常识:大雨已一个月之久,加上山谷险阻,道路断绝,人马难行,即使追赶也没有什么收获的。而《三国演义》为了热闹,却写孔明数路出兵攻击,大败曹真,又写了一封书信,把曹真活活气死。这便夸张得过了分了。此时又不好收场,便只有杜撰一个情节,说司马懿用计,使人离间刘后主和孔明的关系,而后主也居然相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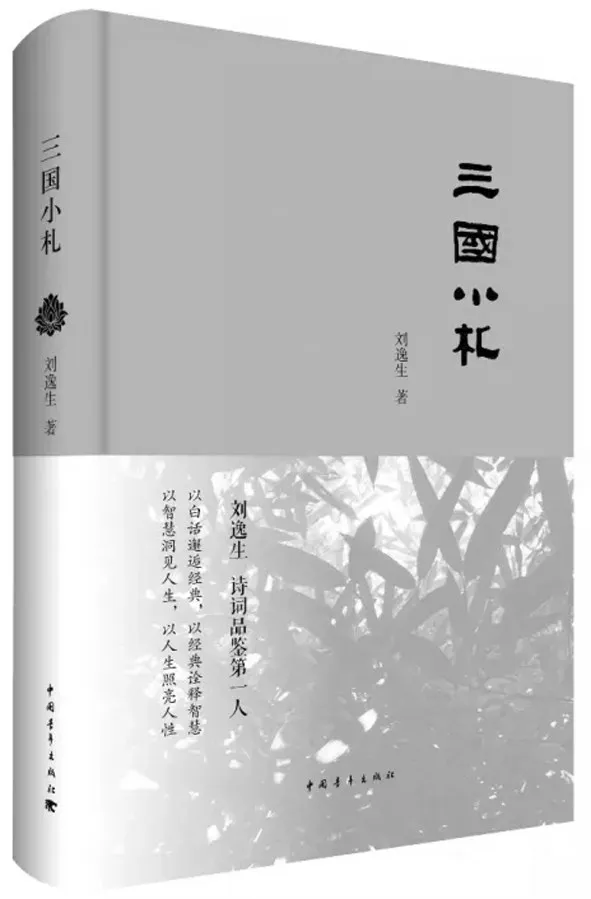
这是为了凑足“六出祁山”之数。事实上,孔明只有五出祁山。建兴八年这场仗,是魏军主动进攻,双方主力并没有交锋。倒是魏延另领一支兵马,西出雍州,大破郭淮于阳溪。这和出祁山是无关的。
《三国演义》作者为了弄出一个孔明战胜而又退兵的理由,就说刘后主中了谗言,硬把孔明宣诏回来。却不知道这就把历史上孔明和后主的关系破坏了。须知后主在孔明当政之时,对他是绝对信任的,一些宦官的谗言,怎能动摇后主的信心?何况孔明奉了托孤之命,是个事实上的监督人,后主也不可能随随便便把孔明调遣回来。这同对姜维完全是两回事。所以《三国演义》这一回书,不特诬了刘后主,连孔明的形象也受到贬损。说它是罗贯中的败笔,实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