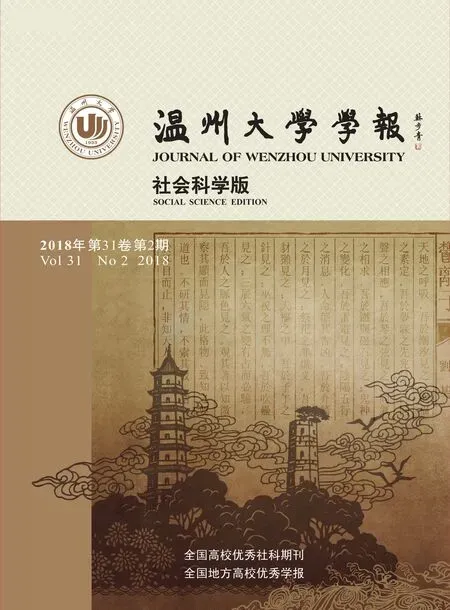儒家道德情感主义的根本原则
2018-03-03邵显侠
邵显侠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 210023)
儒家道德是一种情感主义的道德,可以称之为道德情感主义。儒家的道德情感主义主张人类的情感(如恻隐之心)本身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可以为人的行为提供理由,为伦理道德规范提供根据,为人的道德修养提供源泉。因此,人类天生的情感能力,而不是西方哲人所说的理性,是道德伦理规范的最终根源。“恻隐之心”为代表的情感能力所产生的移情反应是我们评价道德是非的最终依据或标准。人类的道德生活实践和经验告诉我们,这一判断道德是非的标准往往更为可靠,更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一
人的情感多种多样,尽管按照儒家的道德情感主义,它们都具有初始的合理性,但并非任何情感都可以成为道德规范的来源。儒家道德情感主义主张只有“恻隐之心”(相似概念有“四端之心”、“良知”、“良心”、“本心”、“移情心”等)所产生的移情反应才是我们评价道德是非,建立伦理规范体系的最终来源与根据,也可说是最终的道德标准。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孟子说:“夫道一而已矣。”(《孟子·滕文公上》)孔子所说的“吾道”,孟子所说的“道”,主要是指做人的伦理规范或应然之理,他们所说的“一以贯之”的“一”其实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指忠恕之道,曾子在解释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时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忠恕之道就是孔子的“仁之方”,按照我们的理解,就是源于“恻隐之心”或“四端之心”之道;其二,强调它是判断一切伦理是非的最终的标准,故曰:“一以贯之”。儒家认为“恻隐之心”或“四端之心”人皆有之,所以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正是因为人人皆有“四端之心”,因此,“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孟子·公孙丑上》)伦理之理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即“恻隐之心”,且人人都有,古往今来的儒家伦理经典无数,但道理只有一个,这就是衡量一切是非的“恻隐之心”。我们这里用了“一切是非”,也就是所有的应然之理,它们不仅包括“五伦”的伦理道德是非,也包括日常琐事纠纷的是非,还包括治国平天下的应然之理。这就是为何孟子说:“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宋明儒学反复强调“性即理”,“理即心”,“心即理”,“致良知”,“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其道理都是如此。
“恻隐之心”或“恻隐之心”的移情反应是儒家道德情感主义者判断一切道德是非的最终标准,其涵义有二:其一,它是儒家其他伦理规范之源,其他伦理规范都是由这一最终的、根本的标准派生而来;其二,当其他伦理规范与其发生冲突时,应当以“恻隐之心”的移情反应作为最终标准。如,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是儒家核心的伦理规范,即“三纲”,可是当它们与“恻隐之心”发生冲突时,“三纲”要么服从“恻隐之心”,要么需要依据“恻隐之心”重新解释。这就是为什么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1]“视臣如犬马”、“视臣如土芥”都是违背“恻隐之心”的行为,在孟子看来,一旦君的行事违背了“恻隐之心”或“不忍之心”,那么臣子就不必遵守原来的君臣伦理关系,臣可以“视君如国人”、“视君如寇雠”。这应当也是孟子为何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的含义之一。这里所说的“惟义所在”可以理解为唯良知所在,为恻隐之心所在。如果在某些情境下施行“三纲”违背“恻隐之心”的要求,那么就需要对“三纲”重新解释。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君应为臣的表率,父应为儿的表率,夫应为妻的表率,身处某种位置,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正人先正己。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君为臣纲,君不正,臣投他国。国为民纲,国不正,民起攻之。父为子纲,父不慈,子奔他乡(子必参商)。子为父望,子不正,大义灭亲。夫为妻纲,夫不正,妻可改嫁。妻为夫助,妻不贤,夫则休之。”①参见:百度百科. 三纲五常[EB/OL]. [2017-09-2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7%BA%B2%E4%BA%94%E5%B8%B8/326306?fr=Aladdin.这一解释是符合儒家的道德情感主义,特别是孟子的道德情感主义的基本精神的。
二
儒家的道德情感主义将“恻隐之心”或“恻隐之心”的移情反应,视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最终的根本标准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其一,它符合当代道德心理学所揭示的人类道德或利他主义产生的心理事实。道德的本质,或者说不同于其他理性或自利理性的本质特征就是利他性。孔子所说的“仁”其实也是对道德最一般的本质特性的一种概括。当樊迟问孔子何为“仁”时,孔子回答:“爱人”(《论语·颜渊》),这里的爱人当然是爱他人。孔子的回答其实正是揭示了道德的利他主义的本质特性。宋明理学所强调的理欲、公私之分也是强调的道德或伦理规范的利他本质。而当代道德心理学的研究表明②参见:威尔逊. 论人的天性[M]. 林和生,吴福临,王作虹,等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第 7章;迈尔斯. 社会心理学[M]. 侯玉波,乐国安,张智勇,等译. 第8版.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第12章。,人们的移情心或移情反应是解释人们真正的利他主义行为,亦即是无条件的利他主义行为的真正心理原因。自利的心理动机或自利的本能反应只能解释有条件的利他主义,并不能真正解释道德的利他本性。
其二,它也符合我们日常道德判断形成的实际心理过程。当人们从网上或电视中看到某则新闻,比如,2016年网上有一则报道:“(2016年)8月14日去世的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兰州交通大学二级独立学院)女教师刘伶利,生前因患癌被学校开除,致使人生最后一段路不但饱受病痛折磨,还承受着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同时为了维持生活,刘伶利还要强忍病痛去摆摊卖衣服。”[2]当人们最初获悉该事件时的第一反应是:这位女教师太可怜了,对学校开除的做法十分反感。人们的这一反应并非建立在某种价值判断基础上,而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情感反应,人们的这种情感反应几乎是立刻的、下意识的,也就是说,无法通过推理等理性因素来加以解释,按照道德心理学的解释,这是移情反应,按照儒家道德情感主义的术语则是“恻隐之心”的作用。按照道德情感主义的解释,人们的移情反应只是帮助人们形成某种赞同或反对的态度,然后,才会在道德态度形成的基础上进行道德判断。也就是说,道德态度的形成在先,而道德判断在后。这是符合日常人们的道德判断形成的实际过程的。人们在进一步了解了相关情况之后,甚至进行了某种反思之后(这种反思可能归于某种移情的过程,因为移情既可以是即刻的、不由自主的,也可以是认知移情,换位思考的移情,这种移情可以包含将心比心的移情推理过程,孔子的“仁之方”就类似于这类移情),才会下最后的道德判断。这一最后的道德判断有可能与最初的移情反应一致,也可能不同。据报道,刘伶利是 2014年夏天患病的,当时已经在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教了两年英语。当年秋天开始休病假,但是到了 2015年初,当她的母亲申请准予她更长的假期来恢复身体并要求校方继续支付她的医疗保险费时,学校以她缺勤太多为由将其开除。学校的做法是一种基于自利理性的做法,但却与人们普遍的移情反应,也就是儒家所说的“恻隐之心”背道而驰。有少数网民站在院方的立场“换位思考”,试图为院方辩解,但马上招致网上排山倒海的批评。据悉,中国法律禁止用人单位在员工患病治疗期间解除劳动关系。北京对外经贸大学法学教授卢杰锋表示:兰州交通大学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明显违反了劳动法。他说:“单位不但没关心,还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从背后捅了一刀。”综合这些相关信息,博文学院开除刘伶利的做法与情不合、与法不符的情况十分明显。事实上,刘伶利2015年曾诉诸法律,同年10月,榆中县人民法院判决双方恢复劳动关系,但校方选择上诉。然而,在事情披露出来之后,在舆论的压力下,也可以说在人们移情反应或“恻隐之心”的压力下,校方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据报道,2016年8月23日,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院长向刘伶利的父母道歉。双方对补偿问题具体商谈,达成和解,并签署了《和解协议书》,校方赔偿总计50万元。有评论说:“寻求和解、积极补救,远胜过怙恶不悛,院方的道歉补偿行为值得肯定。”[3]这些都可以说是基于“恻隐之心”或移情心所形成的相关道德评判。
其三,道德的核心部分是由否定性的义务(Negative duties)和肯定性的义务(Positive duties)所组成。所谓肯定性义务是指帮助他人、见义勇为,甚至有时包含自我牺牲等蕴含“应当如此”的义务。一般来说,肯定性的义务往往意味着行为者需要付出自己的利益,如时间、精力、财力、健康,甚至生命,这样义务通常应当是一个社会里理性人们经过反复讨论与反思之后所达成的共识。这样的义务往往是有条件的,正常情况下不会太多,且往往会限于特定的职业或人群。比如,制止歹徒行凶是警察的义务,普通人,特别是妇孺儿童,通常没有这样的义务,能够做到,人们会赞赏、歌颂,但不能做到,也不会谴责。然而,否定性义务则不同。否定性义务通常不要求行为者付出,而是要求行为者不要伤害他人、不要偷窃、不要说谎,尤其不要损人利己,要求行为者限制自己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这类义务均蕴含“不应”、“不许”等意思。否定性义务构成了通常所说的道德的底线,“害人之心不可有”说的就是这一底线,这一底线一旦突破,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就会崩溃,变成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这对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利的。“恻隐之心”可以很好的解释否定性的义务,因为“恻隐之心”最容易对他人遭受伤害产生感同身受的移情反应,从而形成对伤害他人行为的反感,进而形成对伤害行为的否定性的道德判断,亦即形成否定性的义务。“恻隐之心”也可以解释肯定性的道德义务,这主要是通过对需要帮助的人的困境产生移情反应,从而形成怜悯、同情等情感态度,并进而形成肯定性的道德判断,亦即形成肯定性的义务。以“孝”的义务为例,正是因为人们对自己的父母最易产生移情反应,移情反应通常也最强烈,所以“孝”的义务在儒家伦理体系中占据首要的地位,“百善孝为先”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儒家的“恻隐之心”理论正是抓住了道德义务形成的最根本的心理原因并将“恻隐之心”的移情反应视为了最为根本的道德原则或道德是非的判断标准,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最后,人类以往的道德实践和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以恻隐之心或不忍之心的移情反应作为判断道德是非的最终标准往往比某些“理性”的标准更为可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文革中发生的大量的冤假错案进行了纠正与平反。现在仔细反思这些冤假错案,我们会发现,它们本身其实已经违背了恻隐之心的道德要求,违背了以恻隐之心的移情反应为基础的忠恕之道,如果当事人当时能够坚持恻隐之心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许多冤假错案是可以避免或减少的。此外,以恻隐之心的移情反应作为判断道德是非的最终标准,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和解释儒家的其他伦理规范,如三纲五常,孝,五伦等。任何后者可能导致的不合理的结果,都可以根据这一更为根本的原则或标准加以矫正。
三
儒家道德情感主义的这一根本的道德标准不同于西方理性主义的道德标准。功利主义是西方理性主义之一。功利主义将行为后果的好坏视为判断道德是非的最终标准。康德的义务论是另一种西方理性主义,按照这一理论,理性行为者的理性或出于理性的绝对命令是决定一切道德是非的最终标准。儒家的根本道德标准是情感主义的,即归根结底以人对外部事物的移情反应作为决定一切道德是非的最终判断标准。
儒家道德情感主义的根本标准也使得儒家的伦理规范有可能从实然的事实(即关于人性的心理事实)中推导出来。“恻隐之心”或移情心是人类的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即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性或人的心理结构问题是一个实然性的问题,亦即事实问题。然而,实然之心理特性何以能够成为应然之理的道德规范?儒家“以情为理”,将实然之“恻隐之心”视为天然之合理的事情,亦即“恻隐之心”本身即蕴含“应当”之义,而一切道德伦理规范均源于此蕴含“应当”的“恻隐之心”,因而也就获得了应当之义。这就是儒家为何能够从实然之人性延伸出伦理规范的应然之理的缘故。
[1]朱熹. 孟子·离娄:下[M]//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北京:中华书局,1983:290.
[2]顾明君. 她开除了患癌女教师,现在被扒得“一丝不挂”[EB/OL]. [2017-09-28]. http://news.ifeng.com/a/20160825/49836093_0.shtml.
[3]王石川. 刘伶利事件背后的暗点该见光了[EB/OL]. [2017-09-28].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6/0825/c1003-286634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