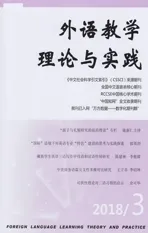历史的机缘与承诺*——美国著名汉学家倪豪士《史记》翻译专访
2018-03-03淮北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
淮北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 魏 泓
提 要: 本文是篇对美国著名汉学家倪豪士《史记》翻译实践的专访文章。倪豪士教授所主导译注的《史记》译本颇具特色、极富学术价值。对于古典西方著作(希腊与罗马的),西方学者通常出版两种翻译: 一种是为了普通读者的注释很少的流畅翻译,另一种是针对学者的对文本与上下文都进行广泛注释的翻译。华兹生的《史记》译本是优秀的流行版本,而倪豪士的翻译目标是提供一种学术性译本,倪译本因而主要被西方的学者、专家与学生所阅读。倪豪士教授采用国际性合作翻译模式与文本细读翻译法,译著谨严,意义非凡。他翻译《史记》已长达近30年的实践与精神值得我们深切关注。
I.引言
William H. Nienhauser Jr.(倪豪士),1972年获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亚洲语言文化系Halls-Bascom(霍尔斯特·斯科姆)讲座教授,并兼任德国、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等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他是美国《中国文学》(Chinese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i.e.CLEAR)杂志的创办者,并长期担任主编(1979—2010)。2003年,倪豪士教授因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的突出贡献而获得洪堡基金会(Humboldt Foundation)终身成就奖。他从事汉学教学与研究几十年,编、撰著作近十部,发表论文上百篇,成果丰硕、影响弥深。同时,倪豪士教授还是享誉世界的文学翻译家,他曾把法语著作译成英语,如《古代经典的中国文学》(ChineseLiterature,AncientandClassical);也曾翻译过一些中国文学作品,如《唐传奇》(TangDynastyTales)等。他于80年代末开始领衔翻译《史记》,弹指间已近30年,迄今已译注出版了7册( Vol.1、2、5.1、7、8、9与10)。他严谨治学,在译注《史记》之初,就撰写了《〈史记〉翻译回顾》(1991)、《百年来西方的〈史记〉研究》(1996)等知名论文。倪豪士教授所主导翻译的《史记》是项意在全译的工程,资料详尽,精益求精,极富学术价值。倪译本整体结构为: 致谢、介绍、使用说明、度量衡对照表、缩写表、译文,每页译文的下面附有详尽的歧义考证、地点考证、文化背景知识注释等,每篇译文后附有译者评注和相应的中外翻译与研究文献,而在每整卷译本的后面还附有全书的参考文献目录(包括《史记》相关翻译与研究的文献)、索引、地图等。国内关于倪豪士教授的访谈已有几篇,而本访谈专门关注于他的《史记》翻译实践。这篇文章是笔者在当面的英文访谈后再译成中文的,并得到了受访者的最后确认。笔者在翻译时力求本真再现受访者的话语特点与内容,以期予国内相关研究以启示与借鉴。
II.访谈内容
笔者有幸在春光明媚的2017年4月23日(周一上午十点),在麦迪逊碧波荡漾的曼多塔湖畔的Van Hise Hall里对倪豪士教授进行采访。
提问: 您好!非常荣幸您能接受我的访谈!我们知道您的《史记》译本迄今已经出版了七卷,分别于1994、1994、2002、2006、2008、2010 与 2016年出版。请问关于《史记》翻译,您一共准备出版多少本呢,有什么计划吗?
Nienhauser: 尽可能多出版(as many as we can),这就是我明确的回答。很久以前,大概十五年前,就有人开始问我这个问题,我从来不回答。我的答案很简单: as many as we can。我们一直努力在做!
提问: 中国典籍卷帙浩繁,请问您为什么选择翻译中国典籍《史记》?
Nienhauser: 多年以前,我不太了解司马迁的《史记》。我努力去读唐传奇的时候,发现文本很难读懂,台湾的教授王秋桂说其中有几个原因,他建议我去读《史记》。当时台湾的文建会准备为翻译项目提供学术资助,于是我向文建会建议进行《史记》项目的翻译,后来我们申请到了这个项目,项目基金是十四万美元。于是我们开始翻译《史记》,那是1989年。我翻译《史记》没有特别的原因。我确实喜欢《史记》;我想大家都会喜欢《史记》,但我也不是超乎一切的喜欢。我翻译《史记》,是出于一种机缘(chance)。刚开始,我们只准备翻译没有被沙畹(Edouard Chavannes)和华兹生(Burton Watson)翻译过的30篇《史记》内容,但后来考虑到没有全译本会误导西方读者,同时也考虑到西方目前还没有英语全译本,于是我们决定全译《史记》。
提问: 《史记》体大思精,文化内蕴极为丰厚,您觉得翻译《史记》是件艰巨与棘手的工作吗?
Nienhauser: 翻译中国任何典籍文本都很难,把汉语翻译成英语是件很复杂的事情。《史记》可能有更为难以翻译的地方,因为它和许多文本都有互文关系,比如《史记》和《汉书》、《左传》、《尚书》、《春秋》、《战国策》等所有这些文本都有关系。西方有些学者认为《史记》散轶了很多章节,它的许多内容后来是后人复制《汉书》的内容,我不相信这是事实,但许多西方学者这么认为。
提问: 我们知道在您翻译《史记》之前,西方已有法国沙畹与美国华兹生的译本。汉学家沙畹所译注的《史记》共出版了五卷本,闻名遐迩。汉学家华兹生所翻译的《史记》(RecordsoftheGrandHistorianofChina)于1961年问世以来,一直颇受欢迎。这两个译本在西方都久负盛名,那么您的《史记》翻译定位和他们有什么不同呢?
Nienhauser: 华兹生的翻译没有脚注,没有评述,只是翻译,和我们的译本大为不同。华兹生的译本很重要,至今仍然有很多读者阅读,但他的译本对学者们来说不太有用。沙畹的翻译和我们的翻译类似,他从1895到1905间进行翻译。他的翻译很有用,但遗憾的是他只译出了47篇。而且沙畹的翻译是法语翻译,多数美国人、甚至有些美国学者们都不懂法语,于是我们提供学者们需要的英语译本。
提问: 在美国,您的译本和华兹生的《史记》译本都颇受关注,许多学者,比如卜德(Derk Bodde)(1995)、阿巴克尔(Gary Arbuckle)(1996)与侯格睿(Grant Hardy)(1996)等,都认为您的译本是力求精确的学术性译本,而华兹生译本是可读性强的文学性译本,您赞同这样的观点吗?
Nienhauser: 是的,我赞同。精确性、确切性首先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它是第一位的,优雅、可读是第二位的。华兹生翻译出一种流行的优秀译作,而我们的翻译目标是提供一种精确的学术性译本。一般而言,西方学者总是产出两种翻译,一种是为了普通读者的翻译,注释很少而非常流畅,而另一种是为了学者的翻译,这种翻译对文本与上下文都给予广泛而详尽的注释。
提问: 您在所译注的《史记》第一卷“介绍”中说: 翻译目标是“译出一种忠实的、注解详尽的,并尽可能拥有文学可读性与文体统一性的《史记》译本(Our goal is to produce a faithful, carefully annotated translation which is as literate and consistent as possible.)(Nienhauser,1994 Vol.1: xviii)”,您会一直坚守这个目标吗?为什么呢,能解释一下吗?
Nienhauser: 是的,会一直坚持这个目标。原因其实我已经解释过了,西方的现实接受环境需要两种《史记》翻译,一种是为了普通读者的文学性翻译,一种是为了学者的学术性翻译。华兹生的翻译是前者,而我们正在进行的翻译是后者。在这个英语句子中,“literate” 的意思是“有文学成分的(to have a literary component)”“有些文学素养的(to have some qualities of literature)”“文体优美的(to be in a good style)”;“consistent”指的是“我们的翻译团队有许多译者,我们尽力让译员们的译文保持一致(refers to the fact that we have many translators and are trying to keep their translations as similar as possible.)”。
提问: 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您是如何操作来达到译文的精确性、实现自己翻译目标的呢?您是尽量采用靠近原作内容、尽量直译的异化策略来达到翻译目的吗?
Nienhauser: 我们尽量阅读所有的关于《史记》的传统评注,参考一些翻译,特别是沙畹与日本译者的译本,并进行不同译本的对比思考。通常有一位译者提供翻译草稿,一组人再对其进行评论。我们总是尽力讨论出最适合原文的翻译。我们有许多翻译工作坊,许多地方的学者们来到麦迪逊讨论译本。我们在威斯康星麦迪逊有六个翻译工作坊(workshops),其中有来自中国与欧洲的学者。我们还有几个德国翻译工作坊,一个法国翻译工作坊,一个香港翻译工作坊。有很多学者参与了《史记》翻译工作,它花了我们大量的时间。那就是我们取得精确性、实现翻译目标的过程。
提问: 俄国学者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曾提出“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的概念。一般认为,中国典籍外译要经过语内(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翻译与语际(从汉语到英语)翻译两个阶段。对于《史记》翻译而言,您觉得哪个阶段最为关键?
Nienhauser: 我不认为有两个翻译阶段,就一个翻译阶段。我不同意你这种观点。我翻译时就一个阶段,把原文直接译成英文。把古典汉语翻译成白话,再译成英语,这是没有意义的。我翻译时在脑海中直接把汉语译成英语,这可能和中国人不一样。西方人不会有两个翻译阶段,我认为沙畹、华兹生应该也只有一个翻译阶段。沙畹不会说汉语,但他能翻译得很好。
提问: 您本人英语与汉语功底深厚,您还精通德、法、日等国语言,翻译时参考了《史记》中文的多个注解本与法国、日本的多种翻译本,不过,您在具体实践中不是独自翻译,而是采用一种合作性翻译模式。汉学家卜德认为您的译著是一项杰出的汉学成就、是集中于一座美国大学的国际性团体合作的优秀成果(the book is an outstanding sinological achievement and a fine product of international group cooperation centered at an American university)(Bodde, 1995: 142),您也在《史记》译本中多次介绍过这种合作翻译模式,那么您为什么采用这种国际性合作模式来翻译中国典籍?
Nienhauser: 《史记》内涵丰富,而我们的翻译又是为了学者的精确翻译,所以我觉得合作模式更为合适。美国没有多少学者懂《史记》,我认为麦迪逊也没有多少学者关注《史记》。我获得奖学金到德国留学, 发现有许多德国学者对《史记》感兴趣。于是我和欧洲的学者合作,学者们来自德国,也有的来自英国。我一年至少去德国两次,和他们见面讨论《史记》的翻译。自从2003年以来,《史记》的一些翻译由德国学者完成。我们《史记》译本的第八、九、十卷里面都包括德国学者的翻译。在美国,几乎每个处于我这样年纪的学者,若他们拥有博士学位的话,基本上都懂法语和德语,这是正常的。我自己有学生在香港,如陈致、吕宗力,我们有时一起合作。我们没有和中国大陆的学者进行翻译合作,因为他们通常英语不够好,大多数中国的《史记》研究专家与学者都不甚懂英语。
提问: 汉学家德效骞(Homer H. Dubs)说过:“我总认为汉语的翻译必定是项需要合作的事业(I have always considered that translation from the Chinese must be a cooperative enterprise)(Dubs, 1960: 140)”,国际性合作模式有优点、也有缺点。有书评认为: 倪豪士主编译本的散文风格因译者不同而变化颇大,整体风格上不如华译优美;……篇章之间的风格与质量有着明显的不同(Klein, 2010: 462-463)。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评论?您觉得该如何避免合作模式的缺点?
Nienhauser: 首先,我们的翻译目标不是优美,我们的译本确实没有华兹生的译本优美。第二,我们是一组人合作努力的结果,要翻译风格一致不太容易。很自然,不同译者翻译的章节之间会有所不同,有的译者的翻译可能会比另外的译者更好一些。这确实是个缺陷(flaw),但那也警示了我,我们会一直尽最大努力去做。怎么避免这个缺陷?这是不能避免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能力与风格。当然,我们会尽量最小化(minimize)这个缺陷。我们一组人读一个翻译草稿,并进行讨论、提出意见。我们还有个统一的术语表,译者们翻译时可以参照遵守。例如,对于《史记》里面的“贤”字,术语表里的翻译是worthy;对于“德”字,术语表里是to owe a favor to,power, virtue, potency;“攻”是to attach,“击”是to assault, “伐”是to campaign against, “袭”是to make a surprise attack。我们用术语表来统一词汇与风格。我们也做了相应的规定,翻译时要尽量忠实于原文,不仅在意思上、而且在句法上。
提问: 一些学者认为您的译本给更多的读者带来益处:“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对于选择《史记》篇章以传统语言对学生进行训练的老师,对于渴望熟识中国古代主要人物的学生,对于希望探寻其他世界帝国的成长轨迹及其先人踪迹的历史学家们(Loewe,1998: 167)”。另一方面,您的译本以文献学的丰厚而著称,因此有学者认为:“不幸的是,我怀疑非专家们,特别是本科生,会不太乐意去读这样的翻译(Nylan,1996: 137)”。您觉得您的《史记》译本在美国现实中的接受环境与接受情况怎么样?
Nienhauser: 我们的译本不是为了普通的读者,我们是为了学者与专家而翻译的。我认为,对于中国文学,美国读者主要对中国现代文学感兴趣,有限的美国读者对中国古典文学感兴趣,其中,很少的读者对《史记》感兴趣,而更少的读者会真正去阅读《史记》文本,所以读者群很小。不过,那没关系,西方的学者、专家与学生们需要阅读我们的译本。幸运的是,我们的译本都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那家出版社非常好。出版社一直在售出《史记》,我们的译本不是为了普通读者,但一直在售出、一直有读者。
提问: 您觉得中国文学在美国的整体接受环境与传播情况是怎样的?
Nienhauser: 没有多少美国人对中国文学感兴趣。对于中国文学,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关心。美国人不喜欢中国文学,而中国人也只关注中国文学。从根本上说,美国人对外国文学不感兴趣,不仅仅是对中国文学。当然,对于中国重要的文学作品,人们渐渐地越来越有兴趣。但是大多数美国人还是不知道中国文学,甚至连《红楼梦》,他们也都不知道。绝大多数美国人,大概美国有98%,可能还更多,约99%的人不知道中国文学。很多美国学生不知道中国文学,就连教授、英语系的教授也都不知道。怎么改变这样不乐观的接受环境?那要提升美国人对中国事情的兴趣。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比较复杂,难以在这里去一一论述。
提问: 最后,关于《史记》的翻译以及中国典籍的外译,您还有什么体会可以谈一谈吗?
Nienhauser: 我认为对非英语本土的人来说把中国典籍翻译成英语是非常困难的。大多数汉语翻译成英语的中国典籍,大都是对普通读者来说有用的翻译,而不是为了学者的翻译。原因是真正懂中国典籍的学者都是中文系的,但他们不大懂英语,也不在意翻译情况。而做翻译的往往是外文系的学者,但他们对原著内容的理解不够深入。对于《史记》翻译而言,不妨说他们都是外行。
另外,《史记》翻译项目对我来说意味着两件事最为重要。一是这个工作让我结识了世界范围内的很多学者,年轻的与年长的,让我有机会和他们一起合作共事;二是我看到许多学生参加了《史记》阅读小组进行学习,后来他们告诉我他们在阅读组里所获得的体验比他们所曾参加过的课程都更为受益。我的《史记》译本不仅对美国读者有用,而且对世界范围内的读者都有用,有助于在校学生怎么阅读文本,这是极为重要的。
III.总结与启示
在访谈即将结束时,笔者想请倪豪士教授总结一下他的翻译思想,他说: 他是位实践翻译者(a practical translator),没有成熟的翻译思想。确实,他不谈理论,只专注于翻译实践。本访谈沿着翻译目的——过程——结果的思路,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倪豪士教授所主导的《史记》翻译实践情况。本访谈词约意丰,引人深思。因为时代的呼唤与历史的机缘,才识卓著的倪豪士教授承担起《史记》学术性翻译的任务。倪译《史记》意义非凡。
华兹生的《史记》译本虽广受欢迎,但一直颇受争议。早在华译出版不久,捷克汉学家鲍格洛(Timoteus Pokora)就提出了学术接受期待: 但,最需要的是新的《史记》全译本,这个全译本由最优秀的译者所组成的学术团体按照高标准所译成,同时他还提出了国际性合作翻译模式,认为“国际性的合作更为理想、更有希望(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ould be much desired and promising)”(Pokora, 1962: 157)。华兹生本人也指出《史记》全译的重要性: 《史记》这样负有盛名的中国历史作品,在塑造国人的思想与表述方式上起着重要影响,若这些作品没被翻译或仅存在部分的、不充分的翻译,就难以全面而确切地理解中国文化,因为《史记》所体现的不只是过去事件的叙述、而是人类事件变化的整个哲学(Watson,1995: 205)。随着西方汉学与全球文明的快速发展,世界越来越需要一种精准而统一的英译本,于是倪豪士领衔的《史记》全译工程顺时而生。为了呈现给西方学者一部学术性精确译著,倪豪士教授采用“互文见义”文本细读翻译法和国际性合作翻译模式,译注谨严,极尽忠实与确切,力求保留原著的语言与文化特质,以便传达出《史记》真正的话语内容。笔者有幸于2017年跟着倪豪士教授做访问学者,参加了他的《史记》翻译研讨课与他课余另开的《史记》阅读课,发现他翻译时不仅参考《史记》的多种注解本与不同语言的多个译本,而且还参考了涉及到《史记》内容的《汉书》《左传》《战国策》《尚书》《春秋》等书的注释本与外语译本。每次上课,他都会发给我们他亲自打印或复印的各种与《史记》有关的资料。“倪豪士持续的贡献众所周知,甚至瞥一眼他正在进行的《史记》译本,就会明白他工作的价值。为了创建明确的《史记》西方语言译本,他和他活跃的翻译团队查阅了无数的从古到今的材料”(Galer, 2008: 31)。 倪豪士教授既是共同译者,也是主编,他对团队译员的译稿都字斟句酌、耗时巨大。
倪译《史记》的译注力求精确度与高水准,对西方学生学习中国古典文本很有帮助,同时让西方学者们更为受益。倪译本诞生后,美国许多关于中国研究的著作都会把其列入参考文献。倪译本不仅在美国作用斐然,而且在整个西方影响深远,推动了西方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它最大程度上本真再现了司马迁的《史记》,让西方读者一睹中国真正的历史内容,有助于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倪译《史记》尽可能完整而忠实地保留原著的风貌,它必将使世界更加真切地了解中国、了解人类共同的历史文明。美国汉学家张磊夫(Rafe de Crespigny)对倪译评价道: 翻译可靠,注释清晰、有帮助;译著能让英语读者感知到《史记》的学术性;通过这部译著,西方的学术界和文学界将对早期中国的辉煌和浪漫有更多了解,并对由伟大史学家所展现出来的人类教训有更好理解(Crespigny, 1996: 598)。倪译《史记》继往开来、独树一帜,填补了西方缺乏《史记》学术性翻译的空白,是中西跨文化交流中的里程碑译著。汉学家阿巴克尔对倪译与华译进行对比评论道: 华译《史记》保持了一贯可接受性的标准,但华译轻视学术性,注重可读性;倪译试图满足谨严、详尽而又可读的译本需要,它是一项相当大的成就,为更广泛的读者带来益处(Arbuckle,1996: 263)。倪译《史记》是西方最完备、最富有学术价值的《史记》英译本。它适应了时代发展与跨文化交流的需要,利于世界文化的共享与共荣。倪豪士教授因为历史机缘而担当起历史的重任,并将其视为一生的承诺。他的《史记》翻译实践与精神都值得我们深入借鉴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