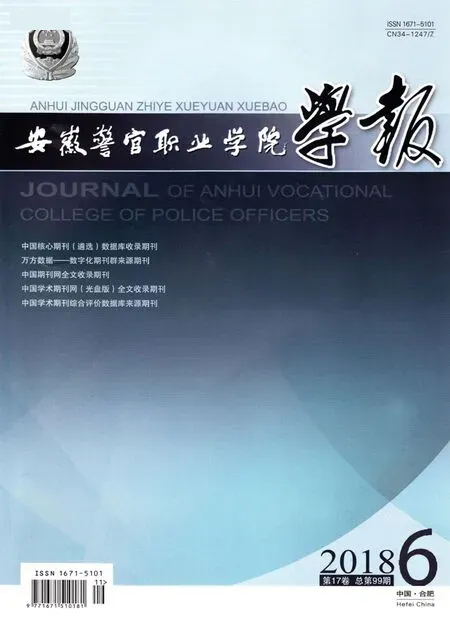“骗领”型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案件的侦查与认定
——以侦办苏某福等人妨害信用卡管理案为例
2018-02-27刘奕武
刘奕武
(安徽公安职业学院 侦查系,安徽 合肥 230031)
电信诈骗等涉卡类侵财刑事案件的高发,带动银行卡非法买卖活动的兴起,由此催生了一种新的犯罪形式:冒用他人身份证“骗领”信用卡并出售,由此形成了一条“黑色产业链”。从公安机关近几年破获的案件来看,电信诈骗犯罪分子使用的银行卡均为冒用他人身份证骗领的银行卡。正因假冒他人身份办理信用卡、买卖信用卡的非法行为,其背后都隐藏着电信诈骗、银行卡盗刷等涉卡类犯罪行为,《刑法修正案(五)》对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规定进一步完善,将“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从而为严厉打击该类非法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本文以“苏某福等人妨害信用卡管理案”为例,从实证角度分析“骗领型”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案件的侦查与认定过程。2016年5月,金安分局从一条细微犯罪线索入手,深挖细查、成功打掉一专门从事冒用他人身份证骗领银行卡并出售、以获取非法利润的犯罪团伙。该案在侦查过程中充分运用轨迹研判、情报分析,完成证据的固定、收集,直至顺利起诉。此案的成功侦破,对今后打处此类犯罪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基本案情
2016年5月23日,犯罪嫌疑人苏某福等人驾车从湖北潜江至六安木厂镇时,在六安农商银行木厂支行冒用他人身份证办理银行卡时,被银行工作人员发现并报警,金安分局木厂派出所及时出警并控制苏某福等三人,从其车上搜出100张身份证和18张银行卡。
二、侦查过程
(一)从扣押的银行卡入手,查明骗领银行卡的犯罪过程
侦查途径可分为人、事、物、信息四大类,在与物有关的侦查途径中,从查控赃物入手开展侦查是较为重要的侦查思路之一。
苏某福等人到案后,侦查员从其车上搜出18张银行卡及大量身份证、手机卡及U盾。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讯时,只有一个犯罪嫌疑人交代了三人来六安的目的以及自己冒用他人身份证骗领银行卡的犯罪事实,但哪些卡是自己办理的,其他银行卡是谁办理的,何时何地办理的,却说不清楚。另外两人否认自己办理银行卡。如果这些细节查不清,就无法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从而无法认定每个人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甚至有可能放纵犯罪。
侦查员从扣押的银行卡入手,对银行卡进行分类,18张银行卡中有6张是六安农商银行卡,经与六安农商银行联系,了解到六安农商银行的办理银行卡的过程:申请人在申请办理银行卡时,银行将申请人办理银行卡时的现场照、传票照片、申请人身份证照片、电脑系统界面截图等多张照片实时传输到授权中心永久保存。于是侦查员到六安农商银行授权中心调取这六张银行卡的开户影像资料,根据开户影像资料,确定这6张银行卡分别是谁办理的以及办理的时间、地点等,开户影像资料的调取为本案划分刑事责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二)从审讯入手,查明作案目的,体现主客观的一致,实现“人”“案”合一
侦查员根据从银行调取的影像资料,再次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讯,由于银行的影像资料比较直观,既能反映出办理银行卡的时间、地点和过程,也能反映出每张银行卡分别是哪一个人去办理的,这些直观的证据对嫌疑人威慑比较大,在证据面前,犯罪嫌疑人分别交代了自己办理哪些银行卡以及办理银行卡的目的。通过审讯,查明了犯罪嫌疑人通过冒用他人身份证办理银行卡,然后卖给有需求的人,以获取非法利益的犯罪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冒用他人身份证办理银行卡的,并非都是卖出,也有些是为自己今后实施诈骗或者洗钱等犯罪行为做准备,因此审讯必须问明嫌疑人办理银行卡的目的,体现犯罪构成中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三)从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轨迹入手,扩大战果
从审讯中得知,犯罪嫌疑人以前曾在六安冒用他人身份证骗领过银行卡,但多在乡镇银行骗领,办好即走,由于是流窜作案,其无法说清都是在那些地方办理的银行卡,另外嫌疑人办理银行卡的目的是为了贩卖,不是为了自己使用,有些银行卡办好后,连同被冒用的身份证通过网络、快递卖给他人,因而无法查找这些银行卡的下落。于是侦查人员从犯罪嫌疑人车辆行驶轨迹、手机轨迹入手,根据其在某乡镇(犯罪嫌疑人多在乡镇银行网点办理银行卡)逗留时间,结合银行工作时间,又发现苏某福等人先后于2016年 3月 10日、2015年 12月 5日、2015年 12月20日、2015年12月30日分别在六安新塘、平桥、九里沟、城北四个乡镇银行网点冒用他人身份证办理了4张银行卡。
从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轨迹入手,深挖犯罪,扩大战果,最大限度地消除了这些骗领的银行卡对社会的危害。
三、“骗领”型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取证要点
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作为一个罪名,《刑法》早有规定,但其表现形态却多种多样,2005年《刑法修正案(五)》将“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之后的几年,此类犯罪并不多见,随着电信诈骗等涉卡类犯罪的高发,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犯罪呈爆发式增长,由于此类犯罪行为比较隐蔽,给侦查取证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因此侦查取证工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证明犯罪的证据
1.信用卡:包括信用卡实物、信用卡照片、信用卡卡号。有些犯罪分子骗领信用卡后,通过网络进行交易,交易后信用卡实物往往难以查获,这时可以通过查询犯罪嫌疑人聊天记录,从而获取已经卖出的信用卡照片,通过信用卡照片上的卡号从开户行反查开户资料,从而证明开卡行为;另外,还可以通过银行提供的异常卡号,通过开户行反查开户资料,通过申请人办理银行卡时的现场照和申请人身份证照片的比对,确定是否为冒用他人身份证骗领信用卡。
2.U盾:“U盾”是网络环境里银行用来识别客户身份的数字证书,是一种带智能芯片、形状类似于闪存(即U盘)的实物硬件。
3.被冒用的身份证:包括身份证实物、身份证照片。
4.被冒用者的证言:主要内容包括身份证曾经丢失,没有委托过任何人或者没有委托过犯罪嫌疑人办理信用卡。
5.开户行办理信用卡资料:包括办理即时影像资料(电子数据)和《银行服务申请书》、身份证复印件等纸质材料。
6.开户行营业厅视频监控。
7.作案手机:办理银行卡需登记手机号码,银行工作人员也往往通过登记的号码核对信息,通过对作案手机号码的反查,可以查出犯罪分子曾经办卡的银行网点。
8.电子数据:对嫌疑人使用的手机、电脑等进行电子数据固定。
(二)证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
证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即证明该人实施了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犯罪行为,达到“人”、“案”合一。
1.户籍证明。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行为人必须达到法定年龄才构成犯罪。
2.犯罪嫌疑人供述与辩解。
3.证人证言。
4.辨认笔录。
5.笔迹鉴定。办理银行卡时,办理人应在《银行服务申请书》上签字,因此可以通过笔迹鉴定识别认定作案人。
6.搜查笔录。
四、“骗领”型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认定
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信用卡管理制度,客观方面表现为妨害信用卡管理的行为,具体包括四种情形:(1)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持有、运输的,或者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数量较大的;(5)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数量较大的;(3)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4)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
“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作为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一种形式,客观方面表现为妨害国家信用卡的管理,犯罪对象集中在信用卡本身,“但是由于这些行为是犯罪分子实行信用卡诈骗犯罪常用的手段,其行为本身就有一定的危险性”,[1]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妨害信用卡管理犯罪对社会危害的严重性,加大对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从源头上遏制电信诈骗等涉卡类侵财犯罪的蔓延。在办理此类案件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刑法意义上信用卡的的认定
从功能上看,银行卡分为信用卡和借记卡两种。信用卡,又称贷记卡,是一种非现金交易付款的方式,是简单的信贷服务;借记卡是指先存款后消费(或取现)没有透支功能的银行卡。银行卡是信用卡、借记卡等银行发行的卡片的统称。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借记卡虽然没有透支功能,但它是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信用卡,2004年12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规定:刑法规定的 “信用卡”,是指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该立法解释采取了广义信用卡概念,将实践中引发争议颇多的借记卡纳入了《刑法》中有关信用卡的范围中。因此从《刑法》意义上来讲,借记卡属于信用卡的一种,这一规定既符合《刑法》立法原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司法实践与立法不统一的问题,有利于打击电信诈骗等涉卡类的犯罪活动。
(二)对“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认定
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是指行为人在办理信用卡申领过程中,违背发卡行的有关规定,向发卡机构提供了与自己身份不相符合的身份证件,骗取发卡机构的信任而获取信用卡的行为。简而言之,即身份证件是真的,使用者是假的,导致“人”、“证”不符。一般来讲,信用卡的申领人提供真实有效的身份证明是其申领信用卡时向银行履行的最基本的义务,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信用卡管理秩序。身份证明是信用卡申请人主体资格的最关键信息,是信用卡申领者个人资信证明的基础。[2]当纠纷发生时,确定信用卡使用者的身份是解决纠纷的前提条件。使用冒用他人身份证件申领的信用卡,司法活动中往往很难确定使用者的身份,使用者一旦利用这些信用卡从事非法活动,将给侦查工作带来一定难度,使国家、集体或个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中国人民银行《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规定:申领信用卡,应当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各商业银行发卡机构在个人申领银行卡时也都明示“个人卡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申领”,即使个别发卡机构规定“可由他人代为申领”银行卡,但“必须同时提交代理人和被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第2条第三款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使用其居民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护照等身份证明申领信用卡的,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身份证明申领信用卡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177条之一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
因此,申请人在申领银行卡时冒用他人身份证并以被冒用者名义签字确认,或者使用别人身份证申领银行卡而不同时提交自己身份证的,即构成“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行为。
(三)对骗领银行卡的数量的认定
“骗领型”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是行为犯,只要实施即为犯罪,骗领10张以上为数量巨大,因此骗领银行卡的数量是量刑的重要情节,实践当中冒用他人身份证骗领银行卡的犯罪嫌疑人,骗领的银行卡不是自己使用,往往是通过网络上联系、物流运输卖给他人牟取非法利,有些车站码头等人流密集的地方,也成为银行卡买卖的交易地点。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打击,即办即卖,因此,骗领银行卡的犯罪分子被公安机关抓获后,侦查人员从其身上、住处扣押的银行卡只是其骗领的银行卡的一小部分,大量“骗领”的银行卡流入犯罪分子手中,成为涉卡类犯罪的工具,仅仅根据扣押的银行卡来认定骗领银行卡的数额,既不利于打击此类犯罪,也不利于从源头上遏制电信诈骗等涉卡类犯罪的高发。因此,在查办此类案件时,侦查人员应充分利用银行数据、通讯资料等电子数据,穷尽侦查手段,深挖犯罪。
事实上,一些新兴的银行由于起步晚,更容易利用先进电子技术记录办理银行卡业务过程,以六安农商银行为例,其申请人办理银行卡的程序是:申请人提交身份证、填写《银行服务申请书》并签字确认、银行工作人员核对后为其办理银行卡。在这个过程中,系统会自动拍摄申请人的现场照片,银行工作人员也会将填写好的《银行服务申请书》及办好的银行卡拍照,这些照片连同综合业务系统界面截图一并上传给银行授权中心,由授权中心长期保存。这些电子数据,完整记录了办理银行卡的过程,即使没有银行卡这一实物证据,也能证明申请人申领过银行卡及其银行卡号。有了这些电子数据,只需证明申领人是否为犯罪嫌疑人即可。(附图:苏案中调取的银行电子数据截图)

(办卡人现场照)

(办卡人提交的身份证)

(综合业务系统界面,含卡号)

(申请书及办好的银行卡)
因此,骗领的银行卡是否被查获,并不能作为认定骗领信用卡张数的必要条件,只要有其他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了信用卡,应当计入骗领银行卡的数量。
综上所述,“骗领”型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是当前多发的一种犯罪活动,其“骗领”的信用卡大量流入社会,为电信诈骗等涉卡类犯罪的高发起到推泼助澜的作用。通过深挖犯罪、准确定性,对于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最大程度削减涉卡类犯罪可利用的工具,有利于从源头上阻断电信诈骗等涉卡类犯罪活动高发态势,保障信用卡的管理秩序,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