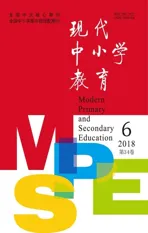学校教育中的文化符号传播与国家形象认同研究
2018-02-26傅金兰
傅 金 兰
(枣庄学院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山东 枣庄 277160)
各个国家都会以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理想塑造儿童,以使儿童认同现存的政治制度;各个国家也都有其所独有的、与其整体运作相一致的教育理想,并以不同的方式将这种教育理想施加于个体身上,以使个体认同这种教育理想。任何一个国家在进行国家形象传播的时候都不能回避信息传播内容和行为本身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联系。因此对于儿童的政治教育方面,国家不但要使儿童做一个有生活道德的人,还要做一个具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和政治觉悟的人。
一、制造认同:国家形象建构之诉求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国家”只是一些共同世界人的理念型的高度复杂网络的一个缩影[1]。国家象征符号,如国旗、国歌或纪念碑等,进一步将国家形象具体化,使人们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和想象国家。正如美国戴维·柯泽所言:“ 国家是不可见的,它必被人格化方可见到,必被象征化才能被热爱,必被想象才能被接受。”[2]国家形象建构,需要基于一种国家认同的社会心理的自觉行为,如何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也成为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指出,说服的整个过程就是在听众心目中“制造印象”的过程。国家形象在什么样的场域中形成?借用社会心理学的互动场论以及国际关系中的控构主义理论视角,形象的建构是形象的塑造者与信息接受者在社会这个“场域”内彼此交流影响、行为互动、相互建构的结果。国家形象认同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念的认同,教育者会力求使每个儿童都能树立起这样一种个人对于国家的态度:强烈地希望维护她的尊严、伟大、光荣和强盛,认同“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培养他在少年时期就能认识到祖国的意义,培养起对祖国的热爱、感激、兴奋和关切的感情,关心祖国的现在和将来,在感情和意识上真正产生一种对自己国家的归属感。这种信念被作为儿童的一种习惯化意识被教育者所强调。
二、学校文化符号与国家形象
世界充满了符号,符号对我们具有不同程度的意义。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人们所使用的物品都可以看作符号,各种符号标志渗透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symbol”(象征)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symbolon”,字面意思是“比喻”“符号”“标志”。象征物代表着某物或某人,符号象征是符号意义和内容的物化表达。在象征中,不同维度的符号或事物会聚集在一起,这样,人就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世界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象征意义世界中。西方政治象征理论的开拓者梅展·里亚姆所关注的符号:“纪念日以及应该被人们所铭记的时代;公共场所和纪念碑等建筑物;音乐和歌曲;旗帜、装饰品、雕像、制服等艺术设计;故事和历史;精心组织的仪式;游行、讲演和音乐等大众活动”[3]。
符号表征着某事物,意味着它所意指的符号的意义功能,符号也会表征符号使用者的意识体验。沃洛辛诺夫建立了符号学和意识形态研究之间的紧密联系。“没有符号,就没有意识形态……一切意识形态性的东西都具有符号价值。”[4]这里,他是在一个特定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一词。作为一种象征,符号一定被建构成它所意指的真实存在的体现。依据这些符号、形式和象征,我们能够看出事物之间的关联。这些象征物的作用是非物质的,我们必须懂得如何读懂它们,因为在可见的象征中也许承载着另一种真相[5]。如国旗、队旗、红领巾等,最开始它们只是一块布,但它们被赋予特有的政治意义后,就变成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当然,符号也只有被赋予某种意义并被接受后才能发生作用。
国家形象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来理解的,它存在于一定的文化符号系统中。每个国家都创造出专属于自己的特殊符号,以标明自己的身份。如国家形象会符号化为该国的国徽和国旗等,中小学校每周一所进行的升旗仪式即是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方式。象征符号和其含义之间建立起一种固定的联系,而且它们的意义还可以不断延伸。如上甘岭上的队旗、南极长城站中国少年纪念标、60周年国庆阅兵群众游行的队徽队旗、“神舟六号”搭载少先队队旗……它们所代表的符号的意义使它们成为现在孩子们崇拜的对象。这种基于国家形象建构的象征性符号教育儿童如何去认同自己的国家地位。“老师告诉我们:在长征时,红军脖子上会系上一个毛巾。战士们的鲜血染红了他们脖子上的毛巾,就这样,才有了我们现在所戴的红领巾。”(一名二年级学生)这样的政治话语开始正式介入儿童的生活。
《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指出:“五角星加火炬的红旗是我们的队旗。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火炬象征光明,红旗象征革命胜利。五角星加火炬和写有‘中国少先队’的红色绶带组成我们的队徽。队旗、队徽是少先队组织的标志。”在这里,红领巾还表征着一个群体、一个组织的概念。儿童戴上红领巾,就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具有高度同质性的群体。它是共产党指挥下的集体,要服从党的领导。由此,红领巾赋予每个儿童以另一重新的身份——少先队员,也给原子式的单个人提供了新的“庇护”,使他们产生一种新的依赖与安全感。学校正是通过这种身份符号建立起儿童与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引导儿童认同自己作为这个国家的一分子,并使他们为此而感到自豪和骄傲。文化符号以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文化价值、文化意义影响着儿童对本民族、本国家的情感认同。
三、学校符号教育与国家形象建构
个体对某个集体或文化的归属感并不会自动转化为一种成员式的同属感,一个“我们国家”的认同并不必然随之产生,因此学校需要将儿童推入公共的政治符号群体中,慢慢使他们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学校文化符号包括校训、校歌、标语口号、仪式、楼房场所、雕塑、绘画等符号,其中,作为“国家在场”的重要仪式活动——升旗仪式与纪念活动是对国家形象建构有直接影响的重要活动。
1.升旗仪式作为一种政治教育活动
儿童对国家形象的认同是基于他们对国家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而考虑到儿童的发展特点,学校需要采取适合、适当的方式来进行。国旗是国家形象的重要标记,凸显着这个民族和国家的个性、尊严。升旗仪式属于中小学校每周一必须举行的仪式,营造了一个特殊的时空,这个特殊的时空必然会成为学校对学生进行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阵地和主要途径。升旗仪式作为承载政治话语的重要媒介,其目的是增强儿童对国家形象的深刻认识,对参与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升旗仪式上国旗下的讲话不仅担负着传递信息的功能,而且也是激励儿童情绪的一种重要手段,它能够使儿童更好地理解国家的形象与意义,这种强调国家认同的政治话语试图使儿童产生一种精神上的聚合和情感上的归属。当然,这种价值体系如若完全不涉及儿童日常话语的内容,其效果必然远离教育者预先的设计。
在升旗仪式中,孩子们整齐划一的出旗方队、冉冉升起的国旗以及振奋人心的国歌,这些视觉、听觉符号共同营造了一种神圣而又庄重的仪式情境,作为未来接班人的少先队员政治身份此时被重新提起。组织者试图利用这种作为国家成员之一的象征性身份,通过特别营造的氛围以及精心设置的仪式环节,激发其为国家而奋斗的豪情壮志,进而达到儿童对国家形象认同的目的。升旗仪式提供了一种亲身到场才能获得的体验,增进了儿童对象征意义上国家形象的了解,提供给儿童一个认同国家形象的空间,重新唤起国家形象建构的共同记忆,体会到一种与国家共荣辱的休戚相关性。儿童在升旗仪式这一时空状态下,共享仪式互动过程所产生的与国家“共在”的一体感。这时,国家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将国家这个政治观念演化成亲历的体验、情感和日常的事物”[6]。儿童在仪式中不断地确认自己对国家归属的内心感受。教育者也期望升旗仪式能够产生一种神圣的力量,使儿童获得对国家形象的符号化的整体感。通过这样的仪式活动教育者可以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强化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甚至可以利用政治象征符号向学生传达政治信息,培养他们对国家制度、法律制度的合理性认同。
2.纪念活动作为一种社会记忆活动
国家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并不必然凭空产生,人们需要找到某些能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象征符号,历史就成为重要的来源,纪念活动“提供了一个重温这些故事并将之与现实联系在一起的机会”[7]。纪念碑是一个公共符号,被认为是纪念战争中阵亡将士的重要标志物。纪念活动是组织者试图将革命时期的历史记忆嵌入孩子们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活动,这是一个提供社会记忆的过程。烈士陵园也由此成为学校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组织者要精心打造的重要“记忆场所”。学校教育者通过纪念仪式引导未来的接班人回忆起革命时期奠基式的过去,期望通过对民族和国家历史的回忆、对革命烈士事迹的回忆,使少先队员们形成对党和国家的认同。这样的活动,学生作为一种代表,代表的是一种身份,代表的是一类群体。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一起回忆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感受纪念空间的庄严与肃穆,形成对党和国家的朦胧认同。
纪念碑、革命旧址等政治符号凝聚了民族的历史记忆,使儿童产生一种强烈的信号意识,唤起儿童对革命烈士事迹的记忆,从而确立自己的民族或国家身份,这一政治教育过程也是教育者试图对儿童进行价值唤醒与政治教化的过程。纪念仪式也是一种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使参加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8]。组织者试图通过纪念仪式这种指向国家神圣历史的活动,在儿童心目中建立起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紧密关系,建立起一种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这种纪念仪典的目的就是要唤醒某些观念和情感,以借此表示对革命先辈的崇高敬意。这种活动是对“奠基式的过去进行现时化,回忆着的群体通过忆起过去,巩固其认同”[9]。整个活动要促成儿童对现存政治制度所实行的政治信念和规范的认同,并使这些“未来接班人”形成对国家政治或历史的认同,从而促进他们的政治社会化。
学校如要使这些活动真正有效果、深入人心,活动的设计就要遵循儿童的需要,听从儿童内心的声音,使少年儿童形成强烈的信号意识。如在“我为核心价值观代言”“红领巾心向党”等演讲活动中,儿童与父母共同查阅资料,或者讲述古代伟大人物的爱国事迹,或者刻画革命战争时代的英雄人物,甚至对“中国梦”也开始有了雏形的理解。在纪念革命先烈活动中,儿童一起回忆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形成对党和国家的朦胧认同。旗帜、口号、纪念革命烈士的纪念碑等政治符号,“其实都是在唤起公民的政治集体记忆,这种唤起是在一种历史语境中产生对价值的肯定与敬仰,进而产生向往之情”[10]。这一政治教育过程是一个使儿童对国家形象产生感性认知的过程,也是对国家形象神圣性强化的一个过程,儿童在对历史英雄的追思中不断产生对国家的认同与理解。在这些纪念仪式活动中,儿童不断加深对革命英雄人物事迹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对革命人物的敬仰之情,激发起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
[参考文献]
[1] 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M].游淙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79.
[2] 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43.
[3] 克鲁普斯卡姬.论无产阶级文化[G]//无产阶级文化派资料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49.
[4] 霍奇,克雷斯.社会符号学[M].周劲松,等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20.
[5] 辛格霍夫.我们为什么需要仪式[M].刘永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5.
[6] 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控制: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M].司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90.
[7] 黄东兰.身体·心性·权利[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110.
[8] STEVEN LUKES.Political ritual and social integration[J].Sociology,1975,9(2):291.
[9] 杨·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47.
[10] 刘学坤,戴锐.政治、政治教育与公民的意义生活[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24-28.